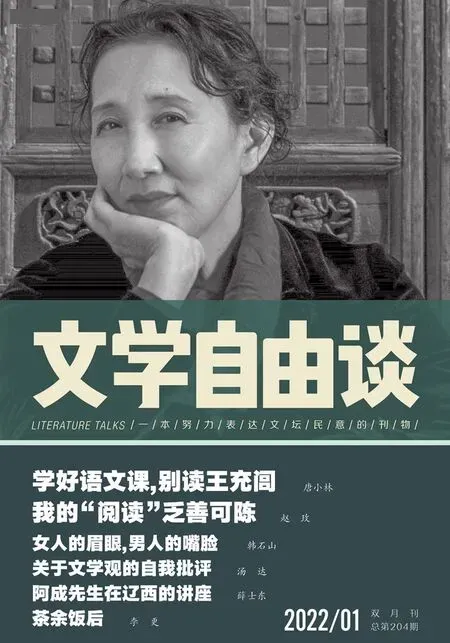学好语文课,别读王充闾
□唐小林
说到王充闾,笔者曾看到这样两则雷人的评论:“他的五十多篇文章被收入上百种语文教材、教辅书目;他的十多篇文章被选入几十种语文考试试卷;他是当代散文大家,与余秋雨并称‘南余北王’;收录三十六篇精选文章,全面提升中小学生的阅读和写作能力;读王充闾,学好语文课。”“在温和从容的书写中恰恰表现出了一种铮铮傲骨,在貌似散淡的述说中坚持了一种文化信念。这是王充闾散文获得普遍赞誉重要的原因,也是他能在散文的困境中矗立起一座丰碑的真正原因。”
这两则评论,前者出自书商,后者出自文学评论家孟繁华。书商的评论,可归入广告一类,听着是可打些折扣,不可全部采信;就像当年书商将《废都》誉为“当代《金瓶梅》”“当代《红楼梦》”的“骚操作”,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不信。至于孟繁华的书评,也无非是配合书商的集体起舞、激情合唱的“软广告”而已。
在我看来,王充闾的散文,一直沉疴在身——因为长期在故纸堆里“觅食”,其字里行间总是弥漫着一种老气横秋、陈年老屋的暮气。他的写作天赋、文史功底,能担当得起帮助学生学好语文的重任吗?
“知道分子”式写作
多年来,王充闾写作了大量的散文,出版过多部散文作品集,获得过鲁迅文学奖等诸多大奖,应邀到北京大学等高校讲学,并被誉为“文学大师”,研究他创作的各种学术专著也竞相出版。面对鲜花和掌声,王充闾没有冷静下来沉淀一下,反而进一步“提速”,开启了“畅销书”的写作模式。他先后出版了《国粹——人文传承书》《文脉——我们的心灵史》,以及《说帝王》《读文人》《话女性》等系列著作。这些机械化生产的“历史串烧”,被涂抹上浓艳的“文化唇膏”,经过书商的精心包装和文学评论家们的不断点赞,最终成功“打造”出了一个“南余(秋雨)北王(充闾)”的散文品牌。
在写作这些贴着“文化散文”“历史散文”商标的文章时,王充闾采取的是以故事性取代文学性的策略,将二十四史和众多历史书籍中适合“推销”的故事,按不同需要和类型,进行归纳分类,把人们早已耳熟能详的历史故事,添油加醋、不厌其详地再重复讲述一遍、两遍,乃至N遍。于是,一本本看似新鲜出炉,实则大炒历史书籍冷饭的“文化散文”和“历史散文”就迅速上市,奉献给读者。
对于写作“文化散文”和“历史散文”的作家来说,要想赢得读者,第一是材料要新,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其次是文笔要好,不不卖弄僵死的知识。而这些恰恰都是王充闾非常稀缺的。
读王充闾的这些文章,我总觉得就像是在乡村的大槐树下,听说书人说书。尽管在当代文坛上,出现了一大批这样的“说书艺人”,但像王充闾这样在故纸堆里翻箱倒箧,把文章写成“故事会”和裹脚布的,并不多见。在这些文章中,几乎看不到作者对历史有什么独到分析、深刻见解,其讲述的帝王故事、皇后故事、文人故事,乃至名胜古迹的传说和各种名人逸事,只要是读过几本历史书、懂得一点传统文化的读者,都不会感到有什么陌生和稀奇。
王充闾的“文化散文”“历史散文”,动辄堆砌资料,大掉书袋。他把文章写得就像拉丁鱼罐头,密不透风,找不到一条活鱼,而且常常把话说尽、说绝,根本看不到文字的灵动。在表现手法上,这些文章大都长成相似的一副面孔,要么炫耀某名胜古迹的有关人员邀请自己去题写诗文、留下墨宝,要么一开篇就是想起各种各样的名人名言,紧接着就喋喋不休地讲述一些古籍里老生常谈的故事,说一些貌似很有见解、人所共知的“大道理”——就像中学生作文的写法——除了用历史故事来充实论据,还要用名人格言来支撑论点——
西方有一句格言,说:“‘人生最奢侈的事,就是做你想做的事。’难道‘做你想做的事’,竟是那么难能可贵……”(《宋徽宗:作个才人真绝代》)
莎士比亚在喜剧《皆大欢喜》中借杰奎斯之口说,世界是个大舞台,所有的男男女女不过是一些演员。(《收拾雄心归淡泊》)
“闲翻旧籍,看到渔洋山人有这样一句话:‘物情厌故,笔意喜生。’脑子里顿时产生许多意念,许多联想。”(《笔意喜生》)
宋代诗人陈与义有两句诗:“客子光阴诗卷里,杏花消息雨声中。”千古脍炙人口。(《节假光阴诗卷里》)
望着窗外渐渐消融的冰雪,脑际蓦地浮现出秦观的“梅英疏淡,冰澌溶泄,东风暗换年华”的名句。(《冰城忆》)
“冷知识”的搬运工
在引用了一些古诗文后,王充闾生怕读者理解力不够,读不懂原文,还会“体贴”地引用众多古代名人、学者对该诗文的评论。比如,他写到西汉政论家、文学家贾谊,就说宋代诗人张耒写过一首名为《贾生》的诗,然后对这首诗的主旨和立意尽情发挥、倾情阐释。接着,他又告诉读者,唐代诗人李商隐也写过一首题为《贾生》的诗,然后对此进行详细的解析。这还没完,他又重新回到宋朝,把王安石的《贾生》翻出来复述一遍……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三位古人作同题诗这事,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冷知识。要知道,如今,即使是冷到快要结冰的知识,也只需百度一下就能知道,何必去读这样的散文呢?
在贩卖冷知识的道路上,王充闾并不孤独,陕西作家穆涛比他走得更远、更极端。比如穆涛的《先前的风气》一书中,将“三百六十行”方面的知识做了不厌其烦的“搬运”。这种文章如果是一位普通作者写的,恐怕早就被编辑扔进垃圾桶,但它居然获得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的散文奖。而在此之前,王充闾的《春宽梦窄》早已获得第一届鲁奖的散文杂文奖。这无疑告诉读者,诗人靠回车键,作家靠掉书袋,也是可以获奖的。
王充闾的《镜子上面有文章》,采用的就是这种掉书袋写法:首先是大段转述汉代文学家刘向在《新序》一书中,讲述的赵鞅虚心听取周舍诤言的故事;接着,对唐太宗以魏徵为镜的故事发了一番议论;然后,又将唐代诗人郑谷写镜子的诗、刘禹锡的《昏镜词》诗照抄出来,并对这些并不难懂的诗大加解释……
读了这样文章,读者就会知道,王充闾的作品为什么写得这么快、拉得这样长。他高产的“秘诀”,只不过是对历史文化知识的“转手”操作而已。
生僻古怪,便是文采?
王充闾说:“散文写作是一种极富个性特征的创造性劳动,而现在许多作品,由于缺乏个性化的支撑,难免陷入思想平庸化和话语共性化的泥潭。……现今散文作者的语言功力、语言质地太差,缺乏文采、文化含量不足已成普遍现象。”
为了显示自己很有“语言功力”、很有“文采”、很有“文化含量”,王充闾的文章使用了大量生僻古怪,甚至早已死去的词语:
本校的校友、编辑家诸荣会先生撰写了《碑记》,备述恢复古迹插竹亭的颠末。(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
其中的奥蕴无穷,但一经勘破,就十分简单……
父亲年岁又小,门衰祚薄,支撑不起这个家当,遂使家道中落。
我也乐于以笔墨为媒介,实现一次暌隔千古的两个灵魂的慧命交接。
剥啄的叩门声、清脆的电话响,整日间不绝于耳……
象征性地描绘出了国事蜩螗,生涯愁苦,萦萦难以去怀的故园心眼儿。(“心眼儿”疑为衍文——笔者)
如今,随着旅游事业的发展,人们暇豫的增多,这种集游观、遣兴、健身于一体的活动,逐渐成为老少咸宜、雅俗共赏的一个“热门”项目。
“惟陈言之务去”。对于写作者来说,文从字顺是最基本的标准,或者说是起步阶段的最低要求。王充闾写作几十年,写的虽然是白话文,却偏偏要拿“已故”的文言词语来为难读者。倘若不借助《汉语大词典》这样的大型工具书,即便是大学毕业,也未必能够将“慧命”“蜩螗”“暇豫”的意思真正弄懂吧。如此故作高深、卖弄学问的架势,活脱脱一副孔乙己卖弄“茴”字有四种写法时的神气。这种文章居然能发表、出版,靠的恐怕只能是“诗外功夫”了。
“历史散文”也八卦?
王充闾的文章,常常是不能自洽,乃至逻辑混乱的。在《话女性》一书中,王充闾把《三国演义》里的貂蝉,当作中国女性来论述;这就如同将孙悟空、猪八戒当作中国男性来研究一样滑稽可笑。《貂蝉:凄惨人生》一文,只不过将有关貂蝉的真伪问题,故事来源、民间传说,以及在戏曲、小说中的演变,和历代学者的质疑、评价等等,巨细无遗地一一罗列出来,而根本看不出学术见解和艺术书写。这种既非学术论文,又非文学创作的文字,同样属于晒学问、炫读书的“知道分子式写作”。
在《李师师的真爱》中,王充闾以想象和虚构,将古代“狗仔队”对宋徽宗、李师师、周邦彦之间绯闻的八卦,以及各种笔记、野史、小说、评话中的情色故事,添油加醋,尽情发挥,身临其境般地写道:“李师师温婉灵秀的气质使宋徽宗如醉如痴,慨叹过去枉活了二三十年。不过,在李师师心中,却并未作如是想,更不会留恋于枕席缱绻之情;相反地,她倒是一面应酬着委身于皇帝,一面却另外有所倾注——在她的心灵深处,还屹立着一个令她倾心钟爱的男子。这个人就是周邦彦。”王充闾还将宋徽宗说成是插进李师师与周邦彦之间的“天字第一号”嫖客。这种凌空蹈虚的书写,使王充闾的文章大失品格,毫不足信。
宋徽宗与李师师、周邦彦之间的“情色故事”,一看就是假新闻、真虚构,只是由文人杜撰而来。王充闾难道真的相信,古代皇帝就像村里的二流子一样,成天东游西逛、猎艳寻芳,并为与一个文人争风吃醋而伤透脑筋吗?他写的这种像雾像雨又像风的地摊文字,就是所谓的“历史散文”“文化散文”吗?
或许,王充闾对宋徽宗、周邦彦、李师师这段艳情故事实在是太着迷了,其《插竹亭逸事》的内容,明明与李师师八竿子都打不着,却也把《李师师的真爱》中,周邦彦和李师师偷情,宋徽宗驾到,周邦彦情急之中藏匿于床下这一桥段,几乎原封不动地“复制”过来。
王充闾说:“散文呼唤创新,要强调独创性,要独出心裁,不能嚼人家的剩饭。”“针对当下有些历史文化散文脱离现实、堆砌史料、把本应作为背景的东西当作文章的主体,抹杀散文表达个性、展示心灵的特长等弊端,我还有意识地剖析、描写了一批历史人物,以彰显现实关怀,主体意识与批判精神。……我的散文写作,一直在不断地变化、摸索之中,谈不上有成型的散文观。我只是坚持这样一点:既不重复他人,也绝不重复自己。创新是文学的生命。一旦发觉自己闯不出固有的藩篱,亦即再端不出新鲜的货色,丧失了创造能力,那就赶紧刹车,再不要枉抛心力。”
说的真好。但事实上,王充闾的许多文章,都有类似的重复;有的书甚至只是把原来的文字做些局部调整,换一个书名,就当作新书出版上市了。或许因为写得实在是太匆忙,王充闾甚至连仔细检查和推敲一下的耐心都没有。大量的低级错误和硬伤,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
在《母亲:望》中,王充闾说他有个姐姐,大他二十二岁,在他两岁时就故去了。姐夫把两岁的女儿,即王充闾的外甥女托付给母亲。外甥女“出生在市井繁华的著名商埠营口,习惯了车水马龙、灯红酒绿的都市生活,乍一来到穷乡僻壤,油灯不明,道路不平,茅檐低矮,不见楼房、电车,不见熙熙攘攘的闹市,终日哭诉着要电灯,要上楼,要逛街,要妈妈……”
这段文字,一看就是杜撰。一个两岁的孩子,连基本的语言表达都不具备,最多也就只能说一些简单的单词,更不要说有什么思维能力和观察判断能力,哪里分得清什么车水马龙、灯红酒绿?更不要说会嫌弃什么穷乡僻壤、油灯不明、道路不平、茅檐低矮、不见楼房和电车。如此胡编滥造的描写,即便是以虚构见长的小说家,也要瞠乎其后。
是学好语文,还是“玩坏”语文?
就像笔者撰文批评过的某些著名作家,其作品非常平庸,写作观念非常陈旧,却屡屡被选入中学教材一样,我担心,王充闾的作品大量入选各种教材、被各色人等大力推荐,对提高中学生的阅读鉴赏能力和写作能力,不但没什么益处,反而可能把他们引入误区。
如果天真未凿、求知若渴的学生,相信了各种“推荐”,以为买了、读了王充闾的散文,就能学好语文,也许就要连呼上当了。他们会发现,王充闾的文字竟是如此粗糙——
那一年出访义乌,可说是事出偶然;但我对于这里的思慕却是由来已久的。说来,人的情感的发生确也十分奥妙。(《骆宾王祠联》)
这么短短的一段文字,就将王充闾尴尬不堪的语文水平暴露无遗。1、“出访”本是一个常用词,指“到外国访问”。义乌地处我国浙江,他去了一趟,怎么就成了到外国去访问?2、“思慕”是指对自己敬仰的人的思念,而并非表示对某个地方的关注,如“哀痛未尽,思慕未忘”(《荀子·礼论》)。3、“十分”是程度副词,“奥妙”是名词。根据汉语语法,程度副词通常是不能直接修饰名词的,如,我们不能说“很思想”“最食品”。“十分奥妙”这种搭配,可说是典型的语病。
体味活泼泼的宇宙生机中的至深的理,追摹一种光明鲜洁、超然玄远的意象。(《陈桥崖海须臾事》)
“追摹”和“追慕”两个词,意思完全不同。前者指“摹绘死者画像,追忆摹仿”,后者指“追念仰慕”。这个例子里,王充闾应是把它们的意思搞混了。
不堪设想,对于皈依人间至纯至美的真情的恋人,失去了爱的滋润,他(她)们还怎能存活下去?他(她)们都是为情所累,情多而不能自胜的人。他(她)们把整个自我沉浸在情感的海洋里……(《三王:诗人的妻子》)
以上这段文字,怎么看怎么别扭。原因有二:一是把“皈依”和“恋人”生拉活扯地绑架到一起;二是反复使用“他(她)们”。关于第二点,其实并非王充闾的首创。语言学家吕叔湘、朱德熙先生早在1952年出版的《语法修辞讲话》一书中,就已明确指出:“‘他或她’、‘他们和她们’、‘他(她)们’听在耳朵里是莫名其妙的。尤其是‘他(她)们’,某些方言区的人听起来,倒像是‘太太们’。这个形式,书面上也没有需要,并没有人规定‘他们’不准包括女性在内。”
再看下面的句子——
在凤阳街头我看到一幅联语:“华灯一夕梦,明月百年心。”(《庄子:寂寞濠梁》)
在主少国危的情势下,某些人即使图萌•不轨,只要有吕后在,还足以镇伏、控制。(《吕雉:母后临朝第一人》)
中国汉代文学家司马迁读了屈原的《离骚》,不禁热血喷张,深心向慕……(《一夜芳邻》)
是的,草木花鸟都是有知觉的。这在古今中外的传说中可说是连篇累牍。(《开美久命金:殉情》)
有一回,我们游览医巫闾山风景区,在感到十分餍足的同时,却又产生了一种兴意阑珊的味道。(《五岳还留一岳思》)
即使不给任何提示(比如加着重号),把这些句子拿给初中生看,他们大概也会猜到这是一组改错题。太多的字词句法方面的错误,已经让我目瞪口呆了。但吊诡的是,它们何以会受到大肆青睐、疯狂热捧,并被选入中学教材、试卷?奇葩文章得以大行其道,无疑是对当下语文教学的极大讽刺。
在我看来,与其把这样的文章当作范文,倒不如把其中的病句整理出来,用以充实“改错题库”,或许对中学生学好语文会更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