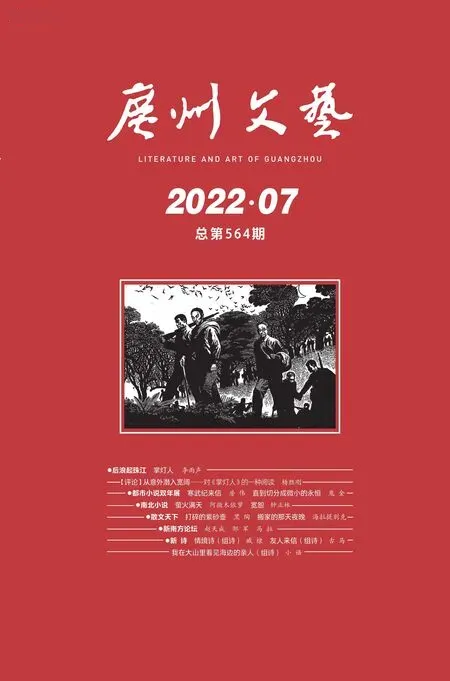打碎的紫砂壶
黑 陶
“万二千余字呼醒有觉生灵”
“万二千余字呼醒有觉生灵”。云南省云龙县诺邓村玉皇阁,一根原木柱子上,贴着上述半句对联。昔日鲜艳的红纸,已经破损泛白,但墨汁书就的每一个汉字,质朴,又依然清晰。每一个墨字的内里,宛如都住有仓颉神灵。
我被猝然击中。这一列汉字,似乎专候我来。
偏僻的、崇山峻岭间的滇西小村。这是我遭逢的、震撼我心的一句话。
林散之艺术观
读林散之,知其艺术观。
艺术从何而来?首先是师造化。能师造化,你就有无数高妙的老师。从雨淋墙头月影移壁中,悟书画之源头;偶然的天际乌云,也能助你:那是一团最有生命的“墨气”,移来眼前,供你揣摩。其次是学古人。学习古人,重要的是“变古”,是学之后的叛,唯有叛,才会生。如若不然,只会辜负芸窗十年灯,只会“死”。
师造化和学古人之后,林散之强调“得天机”。一旦入手天机,那么,即使纵横涂抹似婴孩,满纸也是弥漫精气神。
何谓艺术的高境界?林散之认为,应从深处悟心源,只有写出了“真灵”,笔墨才能“泣鬼神”。他追求我书意造本无法。林散之有《作书》诗:“不随世俗任孤行,自喜年来笔墨真。写到灵魂最深处,不知有我更无人。”艺术的使命,就是对抗世俗,一任孤行。当你的“真笔墨”进入“灵魂最深处”时,恭喜你,这就到达了“忘我”“忘他”的艺术高级境界。
林散之有极强的艺术自信。他清醒,关于他的作品:“亦识有人应笑我,西歪东倒不成行。”但正如老子所言: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林散之自信于他刚柔吐纳之笔所藏有的生命真力,他坦白:“岂肯随人脚后尘,笔未狂时我已狂。”
“嚣嚣”与“乾乾”。林散之云:“文艺之道,不在多言。小人嚣嚣,君子乾乾。”嚣嚣,犹蝇类之营营不停;乾乾,既敬又慎,不言而作。
红色,强烈的色彩印象
滇西诺邓。诺邓,老虎摔下山坡的地方。“崇山环抱,诺水当前,箐簧密植,烟火百家,皆依山构舍,高低起伏”。偏僻古奥的山村。我品尝过它薄至透明的生的火腿片。紧致的、奔跑的野生动物的陈年肉香中,我感觉到盐,特别的诺邓之盐,山中人家随处可见的压实成晶莹月饼之状的诺邓井盐。
一名村中的红衣女子,牵一匹枣红骏马,在狭窄的溪边山道上,与我擦肩而过。盐。马。山中古道。顽强存在的昔日马帮气息,扑面袭来。
红色。强烈的色彩印象。汹涌如瀑流的群山浓绿之间,微小山村是红色心脏:裸露的山壤是红色的,人家的房墙是红色的,起落的巷道是红色的,粗糙的石阶是红色的,木门上的秦琼骑马持锏像是红色的,连进入山村前偶尔目睹的莽野江水,也是惊心动魄的土红色。
北海梦
北海,北部湾,实际的南中国海,就寂静波涌在我身边。碧蓝、无涯的南中国海,在午夜,在它原本应该漆黑的深渊内部,现在,被合浦明珠的美丽光芒,恢宏照耀。深渊的南中国海,因此,璀璨如宫殿。
在我心中,北部湾之神,或者说南中国海之神,是中国唐朝的王勃。
这片海域,在1300多年前,收藏了“初唐四杰”之一的这位山西青年。书载,王勃自交趾(现属越南)探父返回,渡此海溺水,惊悸而殁。想象的此刻,在南中国海内部,英姿焕采的诗人,他发亮的眼神,和头顶的南珠之冠一样,在熠熠生辉。“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吟哦声中,巧笑倩兮的鲛人,穿行服务在如云的高朋胜友之间。
俊采星驰。璀璨的海底宫殿,我看见那个微胖却洒脱的熟悉身影,在宾朋中招呼、移动。在这方浩渺的海面上,他也曾经漂浮:
是日六月晦,无月,碇宿大海中。天水相接,星河满天,起坐四顾太息:‘吾何数乘此险也!已济徐闻,复厄于此乎?’稚子过在旁鼾睡,呼不应。(《记过合浦》)
是的,他是著名的苏东坡。宋代的苏轼和唐朝的王勃,他们手中闪烁蚌壳银光的酒盏,在斟酒鲛人含笑的注视中,碰撞在一起。
现实中的夜晚,我们的酒盏,同样碰撞在一起。在温暖的车上,穿越夜的北海城,到达“陈军石头埠海鲜食街”。新识的朋友们,带有入海前南流江的清澈气息。餐桌上,是海的丰盛馈赠;我同时受赠的,还有刘忠焕、严广云二兄的《合浦文史符号》,还有庞白兄的《唯有山川可以告诉》。夜的玻璃杯中,啤酒金黄的酒液,隐晃近侧大海波涛的微音。
海,平静似太古;海,又摇晃如婴床。我置身的北海,大海无处不在。
北海城区老街。独具特色的岭南骑楼,常有像花瀑一样泻下的三角梅,美得让人心惊。那些与老街垂直的长长的石头窄巷,全部通向大海,近在咫尺的大海。磨损的老街,盛满我嗅得到的旧时岁月,盛满因陌生人到来而被轻搅的夜。空气中飘荡的,除了海货的腥烈,也有后来友人叙说中的咖啡醇香。
涠洲岛。童话园地。火山喷发堆凝而成的中国最年轻的火山岛。在南宁城中,就听张凯兄说过涠洲的美。
涠洲的那个正午,从无人的小路穿过树林,荒凉、广阔的大海,突然就出现在我们眼前。白色的海滩,白色累累的珊瑚化石。
正午的荒凉。永不疲倦的蓝色波浪轻拍。“大海,你来自何方?”永恒之问。
眼前,是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没有尽头的寂寞海岸线。
我始终无法弄清:大海与陆地的相吻之线,这到底是难得的重逢,还是最后的告别?一种深深的精神切割。
涠洲之暮。我珍藏过一小块海滨黑色的火山岩。浑圆微小的岩石。地老天荒。手握它,表面似乎是海水浸透的冰凉,内里,能感知亿万年前南国火山的滚烫。
我记住的涠洲之夜,是住处边侧的烟酒小卖部。住家型的小卖部前,是一条弄堂般的露天通道,茂盛的树冠下,我们在简易的塑料桌旁挤坐。有很大的带着夜海气息的穿堂风,吹过我们。啤酒,花生,有伙伴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买来的大捧烤串。人的相遇,人的歌声,原始的海的气息,一起由夜风融合、携带,去往夜的大海,去往夜海之上的星空深处。
伟大的南中国海填满了我。我想到庞白,相交多年却首次相见的北海友人。庞白,庞大、白色之盐。这个词语,是一整座潜隐的身体大海。做过海员的这位诗人,这样叙述浸入他生命的南方海洋:
此岸到彼岸,有时很遥远,远得一辈子也望不到边际。
彼岸到此岸,有时近在咫尺,瞬间,已然抵达。
大海,除了用辽阔、壮丽、恐惧、神秘来形容,还能想出什么别的词语?
蔚蓝的海拔,无边的从容,凹凸的不规则,无法回避的关注,不由自主的摇晃,漫天的寂静……
在北海,我再一次亲口品尝到这个星球表面的大海,是咸涩的。它有着我们需要的无尽之盐。
舌上的盐。身体里的盐。刚健、浩瀚、力量蛮荒的海的气质,我,乃至我们的民族,是否应该主动吸收?
我还想记下的,是在北海的日子里,幸运目睹到的两次海上彩虹。一次是在旅馆的窗前,一次是在去涠洲岛的渡轮上。神性、绚丽,又宁寂、内敛的弧形彩虹,让我深信:这里是南珠之乡,这里是古老的珠池,“珠还合浦”之后,这里的海底,又有无穷的、闪闪发光的夜明珠。众多从蚌壳内微微溢出的明珠之光,就在海上,凝结成了炫示于我的美丽彩虹。
感谢从中国的正北方迁徙并定居于中国正南方的作家兄长阮直,是你,让我完成了一个神异的北海之梦。
她知道中国的《易经》
她是波兰的女性作家,比我大6岁。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文字中的她,冷静、严谨、自律,她是一位旅行爱好者,也是一位旅行中的观察家。
每次出远门,往她的红色旅行箱装东西时,她发现,随着岁月流逝,她旅行时需要带的东西日渐变少。她用第三人称记述自己:“至今为止,她已弃用了裙子、摩丝发胶、指甲油以及和指甲有关的所有小玩意儿、耳环、便携式熨斗、香烟。就在今年,她还发现自己不再需要卫生巾了。”
她总是飞行,总是认为这是奇迹:“大楼般的庞然机械体竟能如此轻盈优雅地飞翔,摆脱地球引力,慢慢升高,再升高。”
她从俄罗斯的伊尔库茨克向西飞往莫斯科。飞机早上8点起飞,在同一时间降落于莫斯科。整个飞行,似乎没有用掉一分钟。“时间在机舱内消失”。
所以,时间是什么?所以,“要想忏悔整个一生,时间都够用”。
即使在酒店大堂的短暂时间,她也在观察。有个男人陪着一个女人走出电梯。女人“很娇小,黑头发,穿着紧身小短裙,但看起来并不俗气”。她看出来了,这是一个“优雅的妓女”。走在女人身后的男人,“个子很高,头发泛灰,穿着灰色西装”。男人和女人没有讲话,在大堂行走中一前一后保持一定的距离。“真的很难想象,就在片刻之前,他们的黏膜还在胶着摩擦,他用舌头彻头彻尾地探索了她的口腔内部”。他们进入酒店旋门,叫来的出租车已在外面等候。女人随即坐进车里,没有说话,“顶多只有微微一笑”;那个灰西装男人,“他稍稍俯向车窗,但我认为他也没说什么”。载着女人的出租车开走了,与此同时,他也转身回进酒店,“轻快而满足,甚至嘴角隐约带笑”。
她在旅途中遭遇无法解释、略带神秘的事情。
在某个小镇,她入住一家廉价旅馆。拿到的是9号房间。服务员把房间钥匙——她特别注明是“普普通通的镀银钥匙,钥匙圈连着号码牌”——递给她时,随口关照了一句:请小心保管钥匙,不知道什么原因,9号丢失的次数最多。
前台服务员清楚记得:每年为旅馆钥匙补货时,9号房间钥匙的数量总是最多的。连锁匠都感到惊讶。
于是,在小镇逗留的4天里,她非常谨慎地对待钥匙:出门时,把钥匙交到前台;回旅馆后,第一时间把钥匙放在房间显眼的位置。只有一次,她一不留神把钥匙带出去了,于是,她就把钥匙放在最保险的裤袋里,那一整天里,她“随时都用手指去摸摸,确保它还在口袋里”。
因为行程突然有变,她匆忙离开了那个小镇。几天以后,她震惊地发现:那把9号房间的钥匙,仍然在她的裤袋里。
前台的预言又一次成真——“他又要订购一把9号房间的钥匙。锁匠也会再一次惊讶”。
她知道中国的《易经》,她晕眩于东方哲学的“迂回复杂”。在谈到世界各地的飞机场时,她说,从俯视的角度看:悉尼机场的形状,就是一架飞机;东京机场,其造型是一个巨大的象形文字;旧金山机场,像脊椎的横截面;法兰克福机场,则完全就如精密的计算机芯片;而中国机场,让她想到中文拼音,或者,“就把它们当作《易经》的六十四卦好了,每次降落都像是卜了一卦”。
一块巨大、伤感的墨蓝宝石
大理仍然陌生,仍然,似乎没有到过。细雨的石头古城。暂宿的旅馆中,庭院内部,走廊边侧,似乎所有湿漉漉发亮的空地,都被雨夜和茂盛得近乎疯狂的植物挤占。这是一个充满深刻告别气息的石头夜城。
就像到达时的深夜,飞机擦着如墨的苍山和浓云,缓缓滑降。舷窗外,近在咫尺的洱海,就像我如此熟悉的,一块巨大、伤感的墨蓝宝石。
黄酒的忧伤,水的忧伤
想到海飞,我总会想到海明威,想到《流动的盛宴》,想到巴黎时期,那个还未成名、疯狂写作的美国青年。
“杭州是别人的城市,就连杭州的秋天也是别人的。”未成名的中国县城青年海飞,来到天堂杭州城,在借居的简陋民居内,同样疯狂写作。这是他最初的杭州生活:“水龙头没有关严,滴滴答答的声音让你想到,卫生间里放着的久未使用的吉列剃须刀。头顶上转着老牌子的乘风牌吊扇……胡子很久没有刮了,屋角有许多方便面的盒子,你的面容有些憔悴。点上一个句号,合上手提电脑的时候,突然觉得要去进行一场狂欢,因为刚刚完成了一个小长篇……去了卡那酒吧。卡那酒吧在南山路的南端,一幢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建的老洋楼的底层……你喝这座城市里显得较为另类的棕啤,缓慢地喝,总是不能把自己灌醉……经过西湖天地的时候,你看到一对情侣从星巴克的玻璃房子里出来,一人握一个哈根达斯,杯子里顶着一黑一白两个球。有女孩子走过,线条逼人,无可挑剔。就想到,爱情和你已经很远,像陌生人……回到借居的老式民居,冲一个凉水澡,坐在有气无力的吊扇下,扳脚指头计算余下的日子和钱。在钢床上躺下来,想,明天清晨该把胡子拉碴的脸修整一下了。”
出生于浙江省诸暨县枫桥镇丹桂房村,海飞有着70后作家少有的复杂经历:
当过兵,务过农,在制药企业编过报纸,在学校做过文书,现在是,硕果累累的作家和编剧。
海飞的父母,也都属中国底层。当年,“我从部队回来的时候,提前给家里写了信。结果由于赶不上车,第二天才到小镇。那年的冬天特别冷,父亲连着两天去车站接我,见到我时塞给我两个包子,并且接过了我的包。”——想到我的父亲,每年骑着自行车,去老家的镇汽车站迎接暑假回家的我。
“今年春天我回小村看望父母,在镇上的汽车站,我远远看到了我的母亲,她正在招揽顾客买她的甘蔗。汽车一辆辆地驶过,掀起的黄尘扬起又落下。母亲裹着头巾站在尘土飞扬的公路边,兜售着她的微笑和她的汗水。我走过去,叫了一声‘妈’,她正低着头替一位客人刨甘蔗,许是没有听到,我又叫了一声‘妈’,她抬起头,看到了她的儿子。飞扬的尘土里,母亲那张灰蒙蒙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尘土中刨甘蔗的母亲,是海飞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
海飞充满忧伤。海飞式的忧伤,是江南雨季的忧伤,是黄酒的忧伤,是水的忧伤。
他记录他的县城恋爱。“我开始恋爱的时候,女朋友有一台黑白电视机。那时候我从部队回来没多久,我傻愣愣地坐在她家里……那时候我用28寸的自行车把她驮来驮去……我们开始看一部叫《过把瘾》的电视剧,每天都会在午夜播放。我喜欢上王志文的演技,但是我永远不会想到,有一天我会写一个叫《旗袍》的剧本,有一天王志文会来演这部电视剧,有一天会和王志文在横店影视城的一个饭店喝酒。”
人的一生,就是一位小学生趴在课桌上做的一个梦……在杭州城中某幢大楼的某间房子内,这位疯狂的写作者,如是对我说。
冰凉的杜柯河水激越喧腾
位于四川北部、青藏高原东缘,四川省阿坝州壤塘县,是“喜马拉雅神光照耀的地方”。那天,红色炉火和酥油茶滚烫的夜晚,听见一位藏族女子虔诚又幸福地说出这句话时,我有特殊的人生感觉。
在偏远的壤塘,有幸认识藏传佛教觉囊派第47代法主、1974年出生的嘉阳乐住仁波切。
觉囊派是藏传佛教的重要流派之一,拥有非常出色的唐卡艺术。
唐卡是藏族文化中独有的绘画形式,指用彩缎装裱后悬挂供奉的宗教卷轴画,被誉为中国民族绘画艺术的珍品。嘉阳乐住仁波切就是一位著名的唐卡画师。
有感于当地民众生活交通不便、生活贫困、青少年缺少发展机会以及传统文化传承后继无人的困境,壤塘于2010年创办了公益性的非遗传习机构——觉囊唐卡传习所,嘉阳乐住当仁不让,在传习所传授唐卡技艺。
四川作家熊莺和嘉阳乐住仁波切是多年的朋友。借此因缘,我和仁波切也有过交流。他是修为很高的年轻大德,他的许多话语,表面似乎全是在说他的学员和唐卡教学,但又处处超越,给我启发。他说——
从根本上来讲,唐卡不是在表达一个宗教的什么内容,其实它所表达的全部内容,都是我们自身生命本来具有的、一些善的本能或者本性,它是这种生命境界的一种呈现。
在传习所,绘画技艺的传授不是核心,对生命的启发、探索和求证才是最主要的功课。
给孩子们一门手艺,便于让他们凭借手艺跟外界交流。所有人都能学好,学不好、做不好,那是因为生命没有打通。跳个舞,唱个歌,画唐卡时你的线条也许就画好了。
完成作品不是最后目的,主要是培养孩子们的耐力、专注力,达到生命的完成。
把所有的技法学会,融会贯通后,自己的审美、自己的表达,就是艺术。
看唐卡,看一件艺术品,就是看它背后的心灵。
……
那晚告别时,身旁冰凉的杜柯河水激越喧腾。魁梧沉稳的嘉阳乐住仁波切,在黑暗里安静微笑,给我们一一摩顶。
无从驯服的斑马
对自己喜爱、并自认为理解的作家,总想更多地进行了解。读沈从文(1902—1988)纯粹文学作品之外的文字,感触很深。
沈从文的写作理想:“认真尽力做我所能做到的,只希望通过长时期努力,写出些作品,对于新的中国短篇小说,在文字语言和内容两方面,或多或少有些新的表现成就,对后来的接手人起到一点儿推动作用。能做到这样,我得到的报酬已够多了。做不到,我得不怕困难多努点力。”
他同样有竞争心:“同时作家如鲁迅、冰心、茅盾、巴金、老舍、张天翼、丁玲等人的成就,也不断刺激我在工作上的一种竞争心。”
沈从文内在的自信:“至于成就得失,不应当用吹嘘的方法争取,应当交给时间或历史,国内外千万读者,自有比较公平的判断。也因此我认为这工作并不是几个编辑以私见取舍,或商人给我几个钱的事情。”
自认弱于人事:“我早就发现我自己,虽能用极力耐心和劳动克服工作上遭遇到的困难,但是毫无能力适应社会人事上的变故。”“同时在一切场合中,我发现对于应付他人我毫无能力,与人合作同样感到十分困难,独自为战管理我自己,即再苛刻些也可以做到。”
他外在柔弱中藏着的生命倔强:“有些作家的工作(如歌德、托尔斯泰),固然能活得极其光辉,也有些作家在生活上完全败北(如曹雪芹),我个人渺小得很,不能不更加认真努力下去,用工作来锻炼自己,在工作上付出全部劳动力,并学习接受一切失败的痛苦。也不企图用其他简捷方法取得成功。”
沈从文固执地认为,作家不是普通宣传员:“以为作家和社会发生关系及影响社会,主要应当是靠个人生产劳动,既不能靠他人帮助,也不应受拘束。所以即到社会变动最剧烈时,我还固执地认为作家应当有他最大的用笔自由,才会产生好作品。他的工作不是普通宣传员,勉强他去做许多人都可完成的任务,极不经济。”
以上引文,均见《无从毕业的学校》(中华书局2017年6月第1版)中《沈从文自传》一文。
沈从文在1983年写有一篇未完稿《无从驯服的斑马》,82岁的他,在此文开头,有一个对自己的大致总结:“我今年已活过了八十岁,同时代的熟人,只剩下很少几位了……就我性格的必然,应付任何困难,一向是沉默接受,既不灰心丧气,也不呻吟哀叹,只是因此,真像奇迹一般,还是依然活下来了。体质上虽然相当脆弱,性情上却随和中见板质,近于‘顽固不化’的无从驯服的斑马。年龄老朽已到随时可以报废情形,心情上却还始终保留一种婴儿状态。对人从不设防,无机心……政治水平之低,更是人所共睹,毋容自讳。”
祖宗传下的中国文化
在酒镇贵州茅台,在四川泸州1573年所建的窖池群旁,我领悟到中国白酒的本质:无形却激烈的火焰,藏于不动声色的水中。
水与火。东方中国,从来就是水火相容的神奇国度:对外示柔,内含极刚。这就是祖宗传下的中国文化。
费里尼给我的启发
在写作一本新书的过程中,我重温了意大利导演费里尼(1920—1993)的《我是说谎者:费里尼的笔记》。此书扉页左下角,有我的铅笔字迹:“2000.12.27上午,汉源”。书是在无锡学前街上的“汉源书店”买的。这家体量很小却好书集聚的温馨私人书店,早已消失。
费里尼是一位作家,只不过,他是用电影写作。
费里尼的全部电影之根,是他的祖国意大利,是罗马,是他的出生地里米尼。跟自身生命密切关联的地域,成为他电影写作的不竭源泉。
“一个人的根与他的目标紧紧相连,如影随形。”费里尼说。
费里尼拍电影,是为了清空记忆,是为了告别。
“我仍然觉得自己好像被所有那些跟我家乡有关的人物、事件、氛围、真真假假的回忆所填塞,甚至打扰,所以为了彻底摆脱,我不得不把它们都整理到一部电影里面去。
“我拍电影的感觉,与一个人把房子搬空、拍卖家具、丢开所有杂物俗事那种感觉一样。”
他拍电影,有“腾出空间的急切心情”。
1972年,费里尼52岁,拍电影《罗马》。他要腾空自己关于罗马的记忆。
他的内心,“神经质地想榨干我和这个城市的关系,平息最初的激动,并抵制最初记忆的勒索”。
但是,电影拍完以后,“我却有连主题都还没碰触到的奇怪感觉。资料不仅没有耗尽,甚至还原封不动”。
“罗马,依然纯洁无瑕,跟我拍的关于她的这部电影一点儿也不相干”。
在费里尼的著作《我是说谎者》中,他曾自问:“罗马是什么?”他觉得很难回答,“我最多只能试着说说我听到‘罗马’这个词时联想到什么”。
费里尼拍罗马,“我放弃的东西不计其数”。
他想拍而没有拍的:
一场关于夜游的戏。
一场罗马对拉齐奥的足球比赛,一个球迷打赌输了得潜水到英雄广场上的喷泉中。
罗马的女人。
罗马的夏季风和云。
维拉诺墓园的戏。
罗马如画的街景。
有大喷泉的小巷弄。
被庞然阴影切割的庄严大楼荒芜的景象。
在白天交错的明亮中或夜晚淫荡的紫红中所撷取的影像……
“我开始思索一个旁观者所观察到的罗马,一个近在眼前又远在另一个星球的城市。”
最后拍成的电影《罗马》,剧情是这样的:
里米尼小男孩一心向往首都,一满20岁便出发前往罗马要揭开其真面目:阿匹亚大道上的妓女,在街上玩耍的小孩,表演开场小戏的剧院。镜头跳到1972年,费里尼在观光客、责备他不关心政治的年轻人的包围下拍片;地铁挖到一半,因为碰到古迹只好停工;西班牙广场上的嬉皮士;交通警察追逐着发出巨大噪声的摩托车。一个混乱、漠然、遥远的城市。(倪安宇整理)
1973年,费里尼53岁,拍电影《我的回忆》。里米尼,费里尼的出生地,意大利东北部的一个海港小镇。
“《我的回忆》想对里米尼做最后的告别。
“主要是想告别生命中的某个时期,那差一点儿就驾驭了我们的狂飙的青少年期。
“想办法把它存档。”
费里尼脑海中的里米尼家乡,仍然是画面和细节:
学校的朋友、教授。夏日和冬季的大饭店。国王视察。海上扁舟。克拉克·盖博。琼·克劳馥的丰唇。还有在丽求内湖中游泳的索里尼,以及他身边像鲨鱼鳍环绕成圈、拍打着水面的军人游泳队……
《我的回忆》电影剧情:
30年代,亚得里亚海岸边的一个小镇。蒂达在天主教、法西斯和高压式的家庭教育下长大。爸爸是泥水匠,妈妈是虔诚的教徒,舅舅是游手好闲的法西斯分子,叔叔则住在疯人院里。他和学校同学捉弄老师;贪婪地想从葛拉蒂丝卡和大胸的杂货店老板娘那儿满足对性的好奇;向神父告解。直到母亲的死才让蒂达从青少年的懵懂中觉悟。(倪安宇整理)
我喜欢的这位意大利导演,他的许多话,都能给我触动和启发。
“我拍过的各种片子,如今只有一些无用、不可解的细节还留在我脑海中,比如某个技工的绿毛衣,有一次在棚外拍某一段落,雨点鸣金击鼓地敲在我们搭的塑料帐篷上,大家在漆黑中缩挤在壕沟中。”
——细节。细节之河流构成整个文本世界。那么,汉语中我的细节呢,有关家乡、火焰、世界,以及四季景观的细节。
“你越想模拟现实,就越容易陷入模仿的假象中。
“在人生的诸多探险中,最值得去经历的旅程,便是探索自己的内在。”
“这部片子是一个幻想或梦境之旅。”——幻想,梦境。文字更有能量塑造。
“我告诉自己古代的世界从来就不存在……是我们将它梦想出来的。”20世纪,庄子有了西方的弟子。
“具体现实和抽象现实”。
艺术家,“他必须被他所看到的事物吸引,但同时又有偏居一隅所带来的疏离。”吸引和疏离,尤其是疏离,极其重要。
长江的生命和我的生命
“日暮长江空自流”。李白的句子。李白遭遇过这样的长江:日暮,寂寥,伟大却孤独的野性长江,在他的默视下,空空自流,永无停歇。
我也见过这样的长江,伟大却孤独的野性长江:在上海,在南通,在江阴,在镇江,在南京,在马鞍山,在芜湖,在池州,在安庆,在九江,在黄冈,在武汉,在宜昌,在重庆,在泸州。
在长久的注视中,长江恍惚经由我的血管,流过我的身躯。长江的生命和我的生命,总在无数个瞬间,连接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