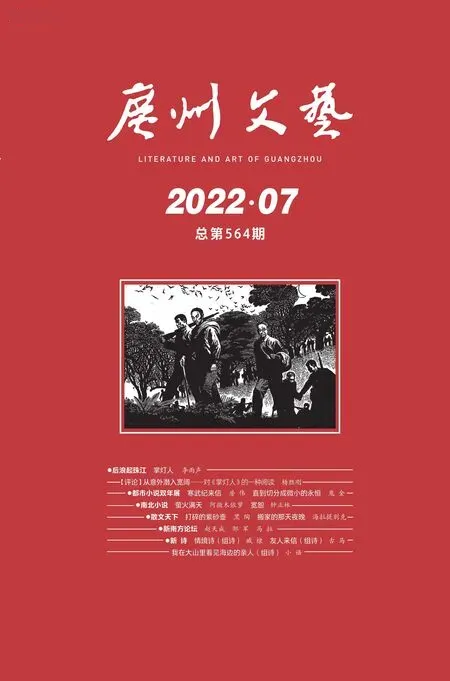革命,海洋与热带的忧郁
——“新南方人物”论纲
赵天成
夏晓虹先生有本小书《旧年人物》,简笔勾勒晚清民国文人,诸如王(韬)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品格一角。尽管人各有异,但总而观之,仍可见出一时代之人情心性。所谓时有古今,地有南北,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与人,一区域亦有一区域之文与人。由南方写作中的南方风格、南方气质、南方腔调、南方意境综合生成的“南方人物”,便在空间的维度上被赋予了文化的意义。
在肇始于2018年的“新南方写作”的讨论中,“新南方”之于笼统的“南方”概念,区别首先在于地理格局的划定。在对“新南方”中心和边界的讨论中,无论是“我们探讨的‘新南方写作’,在文学地理上是向岭南,向南海,向天涯海角,向粤港澳大湾,乃至东南亚华文文学”(张燕玲),还是“将新南方写作的地理范围界定为中国的广东、广西、海南、福建、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以及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东南亚国家”(杨庆祥),都体现出“向南”和“越界”的努力,即从既定的江南中心,扩展至华南、岭南、海南乃至南洋,我喜欢将其统称为“南国”。因此,“新南方人物”,也就可以理解为上述区划的“南国人物”。以下对于其中南国性(新南方性)的探讨,不求面面俱到,只是点出我认为最具问题性和生长性的三个特质、三种语境:革命、海洋、热带及其忧郁。
让我们从相对“短时段”的因素开始。对全球绝大多数的地域来说,20世纪都是革命的世纪。某种意义上,我们今天依然生活在“后革命”的延长线上。如果说在文学版图上超越地缘政治的边界,是“新南方写作”最令人兴奋的议题之一,那么“革命”无疑是最具渗透性和越界性,也最需要在国际大背景中思考的东西。在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中,即使是具有世界性视野的学者,也几乎都将“苏联·中国”的“北方”,作为关注和考察的整体性区块。然而,若将“(新)南方”作为反思革命的整体视域,将文学作为想象革命的重要表征,我们将会发现许多曾被忽略的线索。首先,如论者所说,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岭南始终是20世纪中国革命的策源地,也是革命历史小说和革命传奇故事的材源库。其次,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在激进政治发展和所谓“格瓦拉主义”的双重背景下,越境(尤其是中越、中缅边界)打游击成为一部分青年人的情感寄托和行动方向。1979年引起争论的剧本《在社会的档案里》,主人公王海南(注意他的名字)就是一个随手不离《格瓦拉日记》、多次尝试越境参加游击队的特殊年代的人物。20世纪30年代生于贵阳的苗族作家李必雨,也在其20世纪80年代的小说(如《野玫瑰与黑郡主》)中,借其笔下人物艺术性地呈现了他在60年代末越境参加缅共人民军的经历。
而对于东南亚革命的“内部”书写,则以马华作家张贵兴、黄锦树蔚为大观。在黄锦树的“南洋人民共和国”(借其一部小说的名字)中,“马共”是萦绕在全部人物身上的历史幽灵。如朱天文在《雨》的序言所说:“怎么能不‘马共’呢?锦树的父亲辈那一代,只要你识字,你读书,读华文书,差不多你就会走进森林做了共产党。”也就是说,左翼革命是黄锦树父辈普泛化且日常化的处境。而这种革命,又牵连着移民与后移民、殖民与后殖民、遗民与后遗民、难民与后难民的复杂历史。黄锦树笔下人物通常是抽象化的,但也因此可以说是共名性的,例如《迟到的青年》和《雨》中反复变形现身的男孩辛。在隐喻的意义上,“迟到的青年”既是这一位青年,也是包括作者在内的所有的青年,另一个他或她。他呈现出这一代人(及其后)与父辈历史之间不可逆转的时间关系。作为子一辈,革命不是自身的历史,但又渗入成长经历的方方面面。即使在公认“马共”因素淡薄的《雨》中,也能看到男孩辛身上的历史负担。《另一边》(《雨》作品七号)里,辛的家中晚间来客,是希望让辛参与聊天,“提早接受革命教育”的父亲的当年同志。在母亲嘱其去睡后,辛还是透过隔音极差的薄墙,听到客厅里的高谈阔论,话语逐渐在半梦半醒间混淆:“你们要做革命的后盾。支援革命。赶走英国佬。消灭资本家。……无产阶级专政。建立没有阶级的国家。”“辛听到他们谈俄国十月革命。国共内战。伟大的毛主席。不抗日、腐败的蒋帮。日本鬼子的邪恶。越南、印尼的独立建国。……但突然——像风吹断了高树上的枯枝——你们到南洋没几年,哪来一大笔钱买地?”正如此处突如其来的转折和断裂,真实的革命遗产不只有理想和光荣,也有私欲和狼藉。后来廖克发的纪录片《不即不离》,则用镜头记录了“不在家的父亲”和“被抛弃的孩子”(即那些当年在丛林中出生,后被迫遗弃或送养)的人物命运。
通过以上粗略描摹的南方革命的三种形态,可以看到这块区域革命历史的多元、复调、错综和交叉。是否可以在“南国”的总体性视野下,为共产主义接班人、格瓦拉主义者、迟到的青年和不在家的父亲,提供更丰富、融通的文学书写和批评视角,需要“新南方”作者和评论者的持续探索。
相对而言,历史一页总会风云流散,海洋则是南国人的永恒处境,也是人间命运的舞台和对照。海洋古老而又常新,用林森一篇小说的题名和寓意来说,一代代人年华来去,“唯水年轻”。水是南国文艺作品的发生场域和核心主题,比如出生在马来西亚古晋的台湾地区导演蔡明亮,成名作就是“水”三部曲(《青少年哪吒》《爱情万岁》《河流》)。但诚如评家所言,华语文学历来罕有真正的海洋作家。茅盾在1922年的《小说月报》上曾介绍过一位意大利的“海洋小说家”米莱尼息(Guido Milanesi),称其“一生在海船上过活,他知道海上的种种事,他的血管里是带着海洋气的”。近年来,同样可谓“血管里带着海洋气”的青年小说家林森,正在创造自己的海洋文学世界。李壮在评论林森的长篇小说《岛》时说道:“这部小说的真正主角,既不是叙述者‘我’,也不是居住在‘鬼岛’上的怪人老吴,而是大海,是被大海隔绝于人世的孤独的岛,甚至就是这种隔绝本身。‘我’和老吴的人生经历和内心世界,与这海、这岛是同构的,他们在海和岛的躯体上取得了自身的表达,进而用自己的躯体赋予海和岛以表达。”(《蛮荒及其消逝:林森小说中的海与人,兼及“新南方写作”》)大海恒长久,但落在人事圜局中也非一成不变。米莱尼息20世纪20年代的小说,就因是欧战时海洋上的写照,所以格外惹人注目。纵观林森近两三年的小说,其中心人物也常为两代人的设置,如“我”与父亲、“我”与伯父。两辈人都有与海洋同构的部分,但也随着世事变迁,有了不同的人生轨迹;在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上,他们面对的也不再是同一片海洋。
与人的状态直接相关的环境因素,还有气候。南国多数区域处于热带,天热无君子,人们在闷热潮湿的雨林、丛莽、城镇乡间出入,躁动、浮荡、炽烈、不拘小节、不知四季,理性时或处于半悬置的状态。“热带的忧郁”,自是化用列维·施特劳斯描绘美洲大陆的名著,但是表现南国历史的文学和电影,哪怕仅从题名看来,也多笼罩着一层浓得化不开的忧伤:《投奔怒海》《千言万语》《南国再见,南国》《悲情城市》《伤心太平洋》。如果说“革命”是短时段,“海洋”和“热带”是长时段,那么“忧郁”是短时段还是长时段的呢?这是一个迷人而又复杂的问题。在中国的历史语言系统里,“南下”“下南洋”中的南方,都是被置于“下位”的历史,又都隐藏着漂泊的艰辛和危险。在世界文学的历史中,“南方”的文学又近乎巧合的,往往是阴郁和悲剧性的。比如20世纪美国的南方文学,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其中大多数主要人物,都是旧南方庄园主的遗老遗少,或由南北战争制造的孤魂野鬼。因此有人认为,福克纳全部作品的暗线,就是南方“历史的瘫痪(historical paralysis)”。在被问及为什么美国南方突然产生了如此多的好作家时,南方作家佩西(Walker Percy)曾经给出了极为精练的解释:“因为我们输了(We lost)。”朱天文曾用极其相似的话评论黄锦树的意义:“胜者自胜,败者的一方却开启了故事。”Lost是失败也是迷失,黎紫书的写作,从《告别的年代》到《流俗地》,大多关乎主人公的自我迷失和寻找。我特别重视她写于马航(MH370)失事后的中篇小说《迷航之岛》(曾刊于《花城》2016年第3期,“迷航”也是“MH”的双关义),叙写女主人公“我”,如何在世界与他者之中,体验和追踪自我的痕迹。
总而言之,“新南方写作”中的“新”,是时间轴的箭头方向,如论者所说,它应该是朝向未来的。但是“新南方”的作者和他们笔下的人物,又总让我想起萨特对福克纳小说时间观的概括——在一辆飞驰前进的车中向后看。是的,“新”是“旧”的反面,但它也是全部历史——长时段和短时段的历史——生成的结果,是从具有实感的旧时中挣扎出来的一点点新质。也只有这个意义上的“新”,才真正具备问题性和生长性。毕竟,在这里,如福克纳在《修女安魂曲》中所言,过去从未死去,甚至从未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