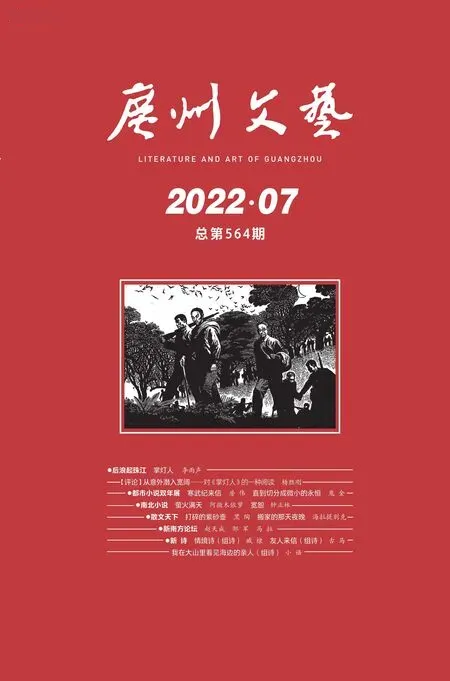南方的忧郁
马 拉
从地理位置上讲,中国大陆西北部位于亚欧大陆腹地,东南部则面向浩瀚的大洋。地理位置不同,受自然条件影响,必然导致物产及人文风貌的差异。这并非强调先天决定论,实在是因为人类活动自始至终都得借助自然的伟力。现代物流业的兴起,部分实现了“物”的共享,但在亲切感上,并无建树。具体来说,满洲里的市民吃着香蕉和荔枝时,对他们来说,那只是单纯的水果。由于对其生长过程缺乏直观的了解,日常生活中也无从亲近,他们不大可能产生情感的投射。一地之出产,又影响着器物的生产和使用。中国北方之苦寒和中国南方之溽热,对当地百姓生活及心理影响之大是显而易见的。这些因素交杂在一起,必然会让地方文化属性及文化心理产生微妙的差异,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大约二十年前,我从湖北到广东谋生。在地理概念上,乃至心理认知上,我认为我是南方人。毕竟,我从小生活在江南。到了广东之后,我惊讶地发现,广东人概念中的南北并不符合科学精神。在本地人的认知中,广东之外皆为北方。对我们这种人,他们还有略带歧视的专门称呼“北佬”“北妹”。湖南籍作家盛可以以《北妹》之名写过一部长篇小说,由此可见这个词对人刺激之深。从北方进入南方,首先必然是语言的侵袭。我们熟悉的语言消失,代之以另一种难度极高的方言。我在不少广东外来作家的作品中,看到过他们遭受的语言暴力,甚至羞辱。他们偶尔在作品中使用白话词汇,多半情况下,那不是一个好词。近些年,这种情况日益少见,哪怕在广东如此固守自身文化特性的区域,方言依然在以加速度消失,以至时不时响起“保护粤语”的呼吁。我女儿告诉我,同学们哪怕在课后,也都以普通话交流。即使在家庭中,由于跨省婚姻变得越来越普及,为了让交流更加自然,不少家庭都放弃了各自的方言,加入更为普及通用、更带有平等色彩的普通话行列中。沃尔科特说过,“要改变语言,先得改变你的生活”。这句话不仅在文学中适用,在社会生活中依然是适用的,生活确实有力地改变了我们的语言。我刚到广东那会儿,认识了一个在酒吧做服务生的姑娘。后来,成了朋友。她第一次喊我“lao sei”,我认为这可能不是一个好词。她告诉我,这是“老板”的意思,相当于尊称。我固执地不相信。为了证明她没有骗我,她领着我上街,买了一堆东西,喊了几十句“lao sei”,才让我对这个词的意思勉强予以确认。这也是我第一次把语言和南方人的形象结合起来。
当“新南方文学”这个词变得热闹,和所有对理论一知半解的写作者一样,我首先想到的是它的覆盖范围,为此,我读了杨庆祥《新南方写作——主体、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权》。在那篇文章中,杨庆祥写道:“我将新南方写作的地理范围界定为中国的广东、广西、海南、福建、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以及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东南亚国家。”这当然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定义,它不仅是中国文学的概念,也是亚洲文学的概念。这里面没有我想当然地认为应该有的云南和贵州。可以肯定的是,无论站在哪种范畴上,广东作为“新南方写作”的构成主体是没有任何疑问的。谈到新南方文学人物形象,我想到了惠能和弘忍的一段对话。《坛经》中记载:
惠能安置母毕,即便辞违。不经三十余日,便至黄梅,礼拜五祖。
祖问曰:汝何方人,欲求何物?
惠能对曰:弟子是岭南新州百姓。远来礼师,惟求作佛,不求余物。
祖言:汝是岭南人,又是獦獠,若为堪作佛?
惠能曰: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獦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
这段话细细读来,很值得玩味。佛性有无差别,且不论,显然无论五祖弘忍,还是六祖惠能都认为人是有南北之分的。应该说,在古典文学中,南北人物形象差异更明显一些。在当代文学,尤其是新世纪文学部分,仅从人物形象上,很难辨析南北之分。这当然是因为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化。无论广东还是海南,随着大量外来移民的涌入,想保持原有的状态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些来自天南海北的写作者,在创作中表现出各不相同的姿态。这使得他们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不具备单一的地区性人物形象特征,而呈现出交流、融合的特性。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它表现出了一定的世界性、公共性和现代性。也有少数入粤作家,表现出强烈的书写本土题材,展现本土文化的热情。比如说现居深圳的邓一光,这个著名的硬汉作家,创作了一系列深圳题材的中短篇小说,在小说标题中急切而热烈地使用深圳符号,比如《深圳在北纬22°27′~22°52′》《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如何走进欢乐谷》《万象城不知道钱的命运》《离市民中心二百米》等。还有陈继明的《平安批》,聚焦潮汕侨批文化。吴君、盛可以、蔡东都写下了大量以深圳为创作背景的小说。如果我们再深究一下,不难发现,广东作家写的多半不是我们所强调的“新南方人物形象”,而是在南方生活的外省人形象,概而言之写的是“外省人在南方”。这应该是新南方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我在一篇文章里写过,很多广东作家,尤其是生活在广深的作家,即使他们身处中国最为发达的一线城市,他们心里依然住着一个无比强大的故乡。这导致他们在写作中时常保持回望的姿态,而对生活的这片土地缺乏应有的激情。即使他们在写作中大量使用南方符号,依然只是为了给写作提供一个现实背景,他们依然自觉地把自己当成“外省人”。
可以和广东作为对比的是广西。广东作家多为外来,本土作家很少。尽管这种状况近年来随着陈崇正、陈再见、林培源、路魆等本土青年作家的崛起有所改观,但外来作家作为主体的面貌并没有得以改变。广西则不同,读者熟悉的广西作家多为广西本地人,外来作家广为人知的恐怕只有湖南人田耳。相比较广东,广西外来人口少,本土成长的作家对本土历史文化、自然环境有着天然的亲切感和认同感。在他们笔下,往往会带有独特的本土色彩。同时,广西作家中少数民族作家众多,我熟悉的代表性作家有壮族的凡一平、李约热、黄土路,瑶族的光盘。那么,在他们的作品中看到一些民族文化特征再自然不过了。在这里,我想荡开提一下贵州作家肖江虹,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无疑是《蛊镇》《傩面》《悬棺》,不难发现,他将笔落在了贵州本土文化上,人物形象具有显著的贵州特色。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大部分广东作家,很难沉下心书写广东元素,像邓一光那样的作家并不多见。就我个人写作而言,我是在广东生活了十多年后,才在小说中接受了广东,才有了部分的广东元素。这里面有个难以启齿的原因,由于地理空间的间隔,我对北方经验变得越发陌生,而南方经验更多地涌入观念中。我近年常常写到的“铁城”,就是我现在生活的中山,铁城是它的古称。就像前面写到的一样,我的写作依然有着强烈的“外省人”意识,在精神融入度上是不够的。这和广西作家、贵州作家有着一望可知的分野。这几年我常常在想一个问题,如何在写作中呈现地方经验,有些对我来说熟视无睹的东西,对别人来说,可能是完全陌生化的经验。我记得有几次,和外地的朋友谈起波罗蜜,他们都认为长得太不讲究了,果实不应该是在枝头吗?怎么跑树干上去了。文学需要这些,出其不意,又自然生成。
回到人物形象这个话题。如果硬要回答,我想说新南方文学的人物形象暂时还是模糊的。至少对广东,或者大湾区来说如此,它还没有构成一张足够鲜明的面孔。这些从全国各地走向南方的人,他们的影子将会随着时间重叠,成为某个便于概括的符号。这种符号,将不再以地理学、人种学为判断标准。它在形成广泛公共性的同时,也将失去某些意味深长的独特性。就像当人类都穿上了西装,汉服难免伤感。如果可能的话,我理想中的新南方文学,它应该具备足够的敏感性和独特性,不试图形成标准,也不推行某种尺度。这可能不符合批评家的期待,缺乏解释的便利性。对读者来说,在南方的雨林和海洋之外,如果还有新的发现,并没什么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