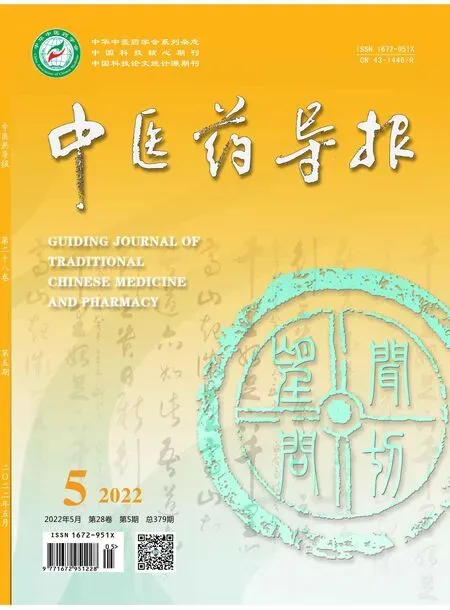日本儒医贝原益轩的养生观*
谢海金,李良松
(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学院,北京 100029)
贝原益轩(1630—1714年),名笃信,号益轩,日本江户时代著名的儒学家、哲学家、医学家,被誉为日本朱子学的代表、“海西学派的巨擘”[1]246。他精通汉语、学贯中日,一生著述了《大和本草》《颐生辑要》《养生训》等百余部作品,涉及医学、哲学、本草、养生等多个领域,对日本近代的医学、朱子学、本草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板仓胜明为其作传,称其“博学强记,和汉之书,无不穷综,其著述之富,与罗山白石相颉颃,裨益天下后世,匪浅鲜也”[2]。笔者通过分析贝原益轩在养生方面的著作,试探析其养生观及其思想渊源。
1 贝原益轩的思想特色
1.1 医学兴趣 贝原益轩主要生活在江户时代(1603—1868年)。在这个时期,一方面日本的思想由中世的佛教转为尊崇儒学,因此,汉学倍受推崇,汉方医学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3];另一方面日本“实施了禁止传教,排除基督教的闭关锁国的国策”,“中医学的传播仅能通过书籍文字,客观促成了日本汉方医学独自的变容发展”[3]。在这个尊儒崇汉又闭关锁国的时代,儒者与医家紧密关联在一起。
此外,作为社会的知识分子、精英群体乃至统治阶层,儒者们在亲近儒学的同时也会关心实学,其中,尤以关心医学的儒者为多。有些儒者不仅通晓医术,甚至还会看病行医,被冠以“儒医”之称。贝原益轩就是这样的儒医。他自幼体弱多病,因而在读书之余还会涉猎医书药典。其对医学抱有浓厚的兴趣,不仅博览医书、遍搜医方,而且有行医用药的经历[2]。他曾在《养生训》中评说过医与儒,认为医学(这里指中医)与儒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要正确地理解中医之意就离不开“儒学之力”和“《易经》之理”[4]148。
1.2 怀疑精神 竹田定直为贝原益轩撰写了墓志铭,称其“恭默思道,极精造微,爱物为务,事天不欺”[5]10。冈田武彦则对他的思想作过这样的评价:“在博学多识方面,他在当时是首屈一指的学者,可是在思想方面,固然称得上宏博,不过,说到深潜缜密,深渊透彻,就不免有所不足了。”[5]10虽然他思想宏博庞杂、深邃不足,但特色颇为鲜明。概言之,即在推崇与继承朱子学的同时,又抱持着怀疑的态度对其进行批评与改造。
他之所以对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儒思想抱持着这种矛盾的态度,与他自身的致学经历密不可分。朱谦之总结贝原益轩的思想有“三度变迁”[1]247:(1)早年苦学而无所主,既涉猎医书药典,又好读佛经,同时也受到了陆王心学的影响;(2)中年尽弃旧学,专致朱子,“纯然朱子派的人物”;(3)晚年疑宋儒之说有佛老遗意,因而在85岁时作《慎思录》与《大疑录》,对朱熹等宋儒的思想进行了质疑、批判与改造。这样的思想变迁,使贝原益轩的思想极具怀疑精神与批判色彩,整体呈现出多样化、博杂化与实学化的倾向。
1.3 实学倾向 实学化的倾向是贝原益轩思想的另一个特色,具体表现出3个特征:(1)主张格物穷理,重视自然科学;(2)强调经世致用,倡导有用之学;(3)富有怀疑精神,重视调查实践。他对医学的兴趣与关切,及其在本草学与养生学中的实践,都是这种实学倾向的表现。
实学指的是“以直接或间接有助于人类生活的科学技术为对象”[5]92,“以实证性和合理性为依据且对实际生活有用的学问”[6]。李甦平[7]曾对中国、日本、朝鲜的实学作过比较研究,并将这3个国家的实学分别简括为“经世实学”“开明实学”与“厚生实学”。日本从中国和朝鲜学习了实学思想,并根据日本的历史和社会条件对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造与发展,使之成为“日本近代化过程的中心概念”和“近代日本发展的知性的动力”[6]。
贝原益轩在日本实学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主张以‘礼乐之教’实现‘经世济民’政治理想”的日本实学代表人物之一[8]。他的实学思想以朱熹的全体大用思想为根源,在综合了日本的社会条件与现实需要的情况下,对朱子学进行了改造与发展,最终完成了朱子学的实践化与实学化。冈田武彦对“全体大用”作过这样的诠释:“全体是指虚的心体具备众理的意思,大用则是指灵活的心的活动顺应万事的意思”[5]110,其重点在于“必须穷尽万物之众理才能达到心的全体大用”[5]111。朱熹的格物穷理之说,即此全体大用思想的具体化。
贝原益轩继承了朱熹“格物穷理”思想中的合理成分,并由此出发,发展出“经验合理主义”[9],强调要重视自然科学的研究。“他将‘穷理’思想与‘实学’志向相结合,经国利民的实学观成为穷理的先导意识,而格物穷理又成为实学志向的实践指南。”[7]他还亲自践行了朱熹格物穷理的思想,如从化石入手研究地质变迁而著《筑前土产制》,又从中草药入手研究日本植物的分类与分布,编著完成《大和本草》。
贝原益轩以儒学闻名于世,他自己也常以儒者自居。因此,他的实学并不是独立于儒学之外的其他学问,而是内化于儒学之中、区别于佛老虚言的实用之学。正如冈田武彦评析的那样:“益轩所说的实学指的就是儒学”[5]95,它“以道德为中心,包括了人文、社会、自然的广泛领域”[5]92,其中涵盖了与人类生命直接相关的医学。
2 贝原益轩在养生方面的著作
贝原益轩对日本的实学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特别是他在晚年所作的几部著作,如其在74岁所作的《筑前国续风土记》、79岁所作的《大和本草》、84岁所作的《养生训》等,对日本近世的本草学、博物学与养生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养生学方面,他主要撰述了三部作品,除《养生训》是和文(较通俗的日文)所写的“训语”(启蒙书)以外,《颐生辑要》和《慎思录·养生说》皆用汉字书写而成。
2.1 《养生训》 贝原益轩著有“十训”,其中《养生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不仅在日本脍炙人口,而且还远播海外,并先后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如:1982年伊藤友信翻译的日文本《〈养生训〉全现代语译》[10],1991年由林意晶翻译的中文本《养生之道》,以及2009年由美国学者WILSON W S翻译的英文本Yojokun: life lessons from a Samurai[11]。
该书以贝原益轩八十余年的亲身体验与养生实践为基础,融合了他多年阅读医书药典后掌握的医药养生知识,并借鉴和参考了中国的养生学说与理论。该书分总论、饮食、慎病、用药、养老等8卷,广泛涉及卫生疗养、饮食健康、临床预防、养老保健与医疗制度等诸多方面,是研究日本近代养生观的重要著作。“《养生训》的内容具有浓厚的儒家思想,即养生的要点在于‘忍’、‘畏’、‘慎’及‘中庸’。但也有部分记载强调人的心情应当‘顺其自然’,这主要是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12]。贝原益轩虽然以儒者自居,且对朱熹推崇备至,甚至奉朱子学为圭臬,但他极具怀疑精神,又倡导有用之学。因此他撰写《养生训》时,并没有囿于一家一派,而是广泛吸收了各家之说。譬如,他不仅提倡儒学的静坐,而且还吸收了道家的导引之术与呼吸之法,甚至对他极力排斥的佛家,他也没有全盘否定,而是活用禅修之法,以补益他的养生之道。
2.2 《颐生辑要》 1682年,已是天命之年的贝原益轩以辑录汇编的方式,编著完成《颐生辑要》。该书共5卷,分别是“总论、养心气”“节饮食、戒色欲”“慎起居、四时调摄”“导引调气、用药、灸法”“养老、慈幼、乐志”。
第一卷主论养性,主张薄名利、寡嗜欲;第二卷强调饮食宜暖、宜淡、谨和五味、不可过饱等禁忌,又强调欲不可绝、纵、避、早等房中保养方法;第三卷罗列居处、言语、洗浴、坐卧等修养宜忌,以及精神、饮食、房事等四时调摄之法;第四卷载述五禽戏、胎息法等按摩、导引、气功之法,以及用药法度和艾灸禁忌;第五卷论述老年人药食导引之法、胎教之法和新生儿护养之法,以及种植、收藏等多种怡情养性之法。
《颐生辑要》摘引了《老子》《庄子》《论语》《抱朴子》等中国典籍中的修养理论,以及《黄帝内经》《备急千金要方》《医学入门》等中医名著的养生知识。该书以辑录汇编的形式,搜集了大量中国明代以前的养生学说与理论,是研究养生学的重要著作。该书的和刻本最初由竹田定直汇编发行,2017年肖永芝将其收录到“海外汉文古医籍精选丛书”在中国出版[13]。
2.3 《慎思录·养生说》《养生说》是贝原益轩晚年所作《慎思录》中的一卷(第三十二卷),收录在井上忠收藏的《益轩资料·补遗》中。冈田武彦将其转录于他的著作《贝原益轩》,并命名为《养生说》[14]164-172。
贝原益轩在《慎思录·养生说》中以条目语录的形式,逐条论述了他对养生的理解与诠释。第一条记载:“保生之道以畏为本,畏者以忍为勤……而畏之道复在忍欲而已矣。”[14]164“畏”即敬畏、畏惧,就是“遇事要小心,一畏惧便生谨慎之心”[4]7。人们因对生命的敬畏和对死亡的畏惧,而知养生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从而在日常生活中谨慎应对,尽量避免病痛的侵扰。“忍”即忍耐、克制。正所谓“食色,性也”,食欲与色欲都是人之本性与常情,需正而视之、克而制之,切勿纵情恣意、毫无节制,否则对身体有害而无益。此即贝原益轩所说的“忍欲”。
《慎思录·养生说》中关于养神、惜气、防疾、摄养、节饮食、养元气、慎起居等养生要点的论述,都是以类似的条目形式展开的。总体来看,它虽然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且体量稍小,但内容却颇精深。该书是贝原益轩养生观的总括性作品。
3 贝原益轩的养生观及其思想渊源
3.1 仁孝一理、养生报德 在《养生训》的开篇,贝原益轩开宗明义,强调养生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他说:“人之身体,受之父母,始之天地。”[4]1人的身体是父母所生、天地所育,同时也是事亲奉天之本。因此,每个人都应该珍爱自己的身体,注意保养、注重养生,如此才能向父母尽孝、向天地报恩。这种主张根源于儒家事亲立身之“孝”与万物一体之“仁”的思想。贝原益轩将二者贯通,总结出“仁孝一理”的思想。他说:“盖仁孝一理,事天与事亲,其事虽异,然其心同,其理一也。”[15]117由此,贝原益轩进一步提出“事天如事亲”的主张。
《孝经》开篇便将爱身、事亲与尽孝紧密联系在一起,申明了“孝始于事亲”的思想。贝原益轩在《养生训》中不仅多次援引《孝经》之说,而且进一步将爱身扩大至养生、将事亲扩展到事天、将尽孝扩充为存仁。在他看来,天地也是人的父母,所有人都不仅仅是父母之子,更是“天地之子”[15]15。天地对所有人都有“生育之德”“罔极之恩”,人们如果不想做“天地之不肖子”,就应该“存仁心”以“报天地之德”[15]136。这种爱身以爱人、养生以报德的具体实现进路,即“从孝悌出发,由近而远,由浅及深,最终可达于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境界”[16]。
贝原益轩不仅将爱身与养生、事亲与事天、尽孝与存仁贯通为一,而且还从伦理道德的层面强化了爱身养生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爱身养生不再是只关乎个人健康、全凭好恶选择的个体行为,而是个人品德与社会责任的综合体现,是一种对仁孝之理与天地之道的必要实践。这种观念对人们的思想意识、心理结构和行为习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使人们更加重视养生,对养生理论与方法的宣传和普及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贝原益轩论析了养生的可能性与可行性。他引“人命在我不在天”的古语,反驳了寿命由天定、人为不可行的观点。他认为“人的寿命的长短很少是天生的”[4]4,生来健康的人,如果不注重养生,也可能失寿夭折。反之,哪怕是天生体弱多病的人,只要“不断学习养生术,不断地实践,身体也会健康、无病,保命又长寿”[4]2。因此,“养生惜命,须从年轻时始”[4]2。
3.2 道气一体、养气为本 贝原益轩认为保养身体、养生延寿首先要了解作为“生命之源”[4]45的“气”。这个观点根源于他对朱熹道气观与理气论的继承与改造[17]。“道”是贝原益轩哲学架构的基础与出发点,他强调“天地之间,只有一个道而已”[15]101。“气”则是贯穿贝原益轩哲学架构的核心范畴之一,他认为“天地之间,都是一气”[18]239。
关于道与气的关系,贝原益轩主张“道必有气”[15]102、“气”在“道”中[15]102。“气”不是由“道”产生的,而是“自有”,即自然而然产生的。如果道中无气,则不可以为“道”,既非“道”,又非“非道”。“道”之所以会流行变化,是因为“气”会变化流行;“气”之所以会变化流行,则是因为“道为之主宰”[15]102。二者互为因果,这也是道气一体的另一种表现。
在对“道”与“气”作出阐释之后,贝原益轩又引出了“理”的范畴,提出道理为一的观点。他说:“理与气一而二,二而一,可谓同而异也。”[15]101他还撰《理气不可分论》[18]238-240,对朱熹主张的“理气二物”“理先气后”“理为形而上之道,气为形而下之器”等观点提出质疑。总之,贝原益轩将“道”“理”“气”三者的关系总结为:“以其流行谓之道;以其主于气,而有条贯,又谓之理。”[15]101
基于上述思想,贝原益轩提出了以保养元气为根本的养生之道。他说:“得元气者滋息,失元气者枯涸,人物皆然。”[15]109元气是人的身体之本和生命之源,因此,“养生之道,以保元气为根本”[4]11。由于人们身体中的“元气”根源于“天地之气”,而人获取“天地之气”的来源主要有两种途径:(1)人生来禀有的自然之气;(2)通过饮食等方式从外物中摄取而来[4]5。因此,保养元气的方法主要有两种:(1)通过节制内欲和抵御外邪的方式来消除伤害元气之物;(2)通过注意饮食、规律起居等方式来吸收和保养元气[4]11。
他还借鉴了《黄帝内经》“百病生于气”[19]的观点,从养气以防疾的角度强调了保养元气的重要性。他认为:“养元气厚,则疾病之生亦自少。”[15]95饮食过量、酒色过度、久坐久卧、不事劳动等不良习惯都不利于养生,而且会泄耗元气,导致元气滞行乃至堵塞,进而使人易受疾病侵扰[4]7。
3.3 静以养心、动以养身 贝原益轩认为周行于天地之间的“气”是“一动一静,循环而不息”[18]238的,人体之中的“元气”也不例外。静有利于元气的保养温存,动则有利于元气的流行循环,因此,“适时的静养和适量的运动都是养生之道”[4]36。
一方面,静养之道,重在养心。养生的重点在于养心,因为“心为身体之君”[4]104。心可支配四肢五官等身体器官,身体各部位都要听从心的命令与指使才能发挥各自的作用。因此,养心是修身养生的重点。保持心平气和、寡言少语的静态,可以在养德的同时养身。这其实是对中国的身体观与养生论的借鉴。
《管子》《黄帝内经》等古籍早已揭示了“心之在体,君之位也”[20],以及“五脏六腑,心为之主”[21]的身体观念。董仲舒则更进一步将这种身体观念与身心修养结合,不仅提出了“身国相通”的观点,而且明确提出“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22]。这样的身体观流传至宋、明时期,逐渐被理学家吸收,发展出居敬、持静的工夫修养理论,呈现出儒医互融、互通、互显的融合趋势。譬如医道与儒家工夫论的融合,“主要表现为以儒家的心性修养工夫论来诠释医学理论并将之运用于医学实践中”[23]。贝原益轩借鉴了上述思想,提出了“静心养德”[4]28、“闭目养神”[4]115、“养生如治国”[4]8等养生观点,并将这种以儒论医、医儒融合的思想与养生理论的践行联系在一起。虽然这种医儒融合的取向可能会面临“医学层面的可信性”与“儒学层面的可适性”的“困境”[24],但这种儒学与医学、理论与实践、工夫与养生融通互鉴的模式,无疑是值得肯定与尝试的。
另一方面,运动之法,重在动身。《三国志·方技传》载华佗语:“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尔。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户枢不朽是也。”[25]贝原益轩赞同此说,并引《吕氏春秋》“流水不腐,户枢不蝼(蠹)”[26]之言,强调身体之动的重要性。他认为“气血流通是健康之本”[4]18,因此,身体应常动,不宜久静。久坐久卧会导致气血滞塞,易引疾病缠身。
此外,他还重点推荐了中国的导引按摩之术。他引明代胡文焕辑录的《寿养丛书》中记载的按摩之法,说明了按摩的顺序与要点,强调按摩是“促进周身血液循环,使皮肤滋润,元气通畅、促进食欲的良好方法”[4]109。同时他详细介绍了练气养生的导引之法。他先后引用了《黄帝内经》关于“导引行气”的论述,以及明代医家李梴《医学入门》记载的导引之术,说明了导引对养生的意义。此外,他还详述了导引的具体细节,如晨起时要逐步伸开双脚、平面仰卧、呼吸吐纳、舒展身体,之后再揉搓面部、按揉五官、拍打腰背、揉压手足、搓摩手心脚心[4]111。细节颇为详备,充分说明了他对导引之术的认可与重视。
3.4 节制内欲、抵御外邪 贝原益轩认为内欲和外邪都对身体有害,因此内制欲望、外御邪气是养生的首要法则。内欲外邪的说法,中国古已有之,如《淮南子》曰:“中欲不出谓之扃,外邪不入谓之塞”[27]。贝原益轩借鉴此说,用“内欲”指人身自有的欲望,如人的七情六欲;其又用“外邪”指“来自外界的邪气”[4]3,如风寒暑湿四气。
为了更加生动地解释内慎与外防,贝原益轩又将“内欲”与“外邪”比喻为“内敌”与“外敌”,主张对内敌要“勇”,对外敌要“畏”。所谓“勇”,就是正确地认识与对待人的内在欲望,并坚决地节制自身的欲望,将自己的身体保养成坚固的城墙,阻挡外邪的入侵。所谓“畏”,“就是遇事要小心,一畏惧便生谨慎之心”[4]7,并以畏惧谨慎的心态和远避近防的策略来对待外邪。总之,贝原益轩主张对内欲要勇而慎之,对外邪则要畏而防之[4]10。
贝原益轩还指出,对外邪要畏而不能勇,但对内欲则不仅要勇,而且还要有谋、有畏、有忍。“畏”不仅仅是抵御外邪的原则,更是内慎外防的总纲。因此,他总结说:“保生之道以畏为本,畏以忍为勤。”[14]164他引《诗经·小旻》“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28]之言,用以强调“畏”的重要性,并认为人一旦有了畏惧之心,就不敢肆意妄为或纵情恣欲。他又引《尚书》“必有忍,其乃有济”[29]和武王铭文“忍之须臾,乃全汝躯”[30],用以说明“忍”是制心之法、克欲之方[14]164。
贝原益轩特别指出,相比于抵御外邪,节制内欲更为重要,甚至被他视为养生之根本。因为内欲一旦被节制,人的精气神就更饱满,不易受到外邪的侵害;反之,则元气受损,无法抵御外邪的入侵。节制内欲的要点除了注重饮食、保障睡眠以外,尤其需要“节制七情”[4]3,避免大怒大悲、忧思过度等极端情绪。
3.5 慎病为主、预防在先 贝原益轩深受中国医学与哲学的影响,他非常赞同中医“治未病”的思维与传统,如《养生训》卷六就以“慎病”为名,专门论析了慎病为主、预防在先的观点。
有学者[31]对中日医学界关于“未病”认识的源流进行了梳理与比较,研究指出:江户时期是“未病”概念日本化的重要时期,具有鲜明特色的日本汉方医学的治未病传统就是在此时期逐渐形成的。在此过程中,日本儒医贝原益轩、汉方医家曲直濑道三、日本古方派代表吉益东洞等都对“治未病”作出了不同的论说。其中“儒医贝原益轩在其撰著的《养生训》中引用《黄帝内经》解释未病概念及成因,针对未病介绍了一系列的措施,表现出对中医治未病学说的推崇和继承;此外,贝原益轩还以脾胃功能为切入,强调了中日两国人体体质的差异,如日本人肠胃功能较弱,主张其在饮食、用药等方面要酌情减量,以达到未病时预防、已病时疗养的目的[31]。
贝原益轩特别将“预防医学”设为“慎病”卷的首篇[4]130,并援引了中国古语“居安思危”和日本俗语“无病想病”,劝导人们要时刻保持小心谨慎的态度,兼顾节制欲望和防范外邪,切不可随心所欲、纵情恣意。他还以邵雍《仁者吟》“与其病后能求药,不若病前能自防”[32]的诗句作为该篇的总结,重申了预防于无病、防患于未然的重要性。
他还在“慎病”卷中逐一列举了日常养生的注意事项,如:勿忧勿骄勿躁、注意防避湿气、出汗时避凉风、肥胖之人易中风,以及病初愈时需更谨慎,以免复发,导致病上加病。其中,有两点值得细说:(1)防中风。贝原益轩认为中风并不是中外风,而是中内风,是外邪引发人体的内风紊乱而导致的内疾。肥胖、气少和嗜酒之人是最易中风的人群,平时需要特别注意保养。(2)防湿气。贝原益轩认为风寒暑湿等邪气之中,湿气是最厉害的一种。因为寒暑等邪风对人的伤害快而浅,易发现、易医治;湿气则不然,它对人体的侵害是缓慢而严重的,湿病十分难治。因此,人们应该格外注意防避湿气,特别是生活起居之所,一定要注意通风透气、防潮防湿。此外,他还提出湿气有内湿与外湿之分,瓜果茶蔬等食物,入腹之后就可能产生内湿。因此,他建议人们在饮食方面也要有生冷之忌,避免内湿引发腹痛、腹泻等问题。
他还分别论述了四时养生的不同要点。四时养生是中国养生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历代医家对此作了丰富全面的论析,形成了四时、月令、节气、时辰等诸多养生理论,涉及宜忌、运气、饮食、起居等诸多方面[33]。贝原益轩关于四时养生要点的论述,大体是对中国四时养生理论的提炼与总结,但在部分细节处综合考虑了中日的水土差异与体质差别。譬如:他认为春季须避春寒,阳春四月又易外泄元气,因此还需节制性欲。夏季则要禁生冷之食,少吹冷风、喝冷水,避免腹泻、呕吐、中暑乃至霍乱等疾病。此外,由于酷热比严寒更会消耗人的元气,因此夏季还需适当辅以药养,以补气清热。他例举了明代张三锡《医学六要》记载的清暑益气汤,以及绿豆汤等清热解毒的汤药。秋季除需防风以外,还需勤于洒扫,避免蚊虫滋生。冬季则需以静养为主,穿衣方面除保暖外,也需避免身体太热,否则火气侵袭,有害健康。若冬季不幸染病,若非急症重病,贝原益轩认为不宜使用针灸疗法,以免元气泄露,同时也可避免宽衣导致的风寒侵害。
此外,他还特别重申了“畏”与“慎”的心态在预防中的作用。
4 讨 论
4.1 贝原益轩养生观评述 日本儒医贝原益轩对日本近代养生观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1)撰写了相对专业且易于普及的养生著作。贝原益轩撰述的《养生训》《颐生辑要》《慎思录·养生说》等著作,为当时的日本民众普及了养生理论和方法,也为后世留下了较为详尽的文献史料,让我们得以管窥日本江户时期养生事业的发展状况与大体面貌,了解中医养生思想的海外传播历程与经验。
(2)完善了兼具中医色彩与日本特点的养生理论。贝原益轩的养生观深受中国哲学与医学的影响,具有非常浓厚的中医色彩,其中有很多理论与思想都根源于中医。譬如,他认可并发扬了中医“治未病”的理论思维,强调要注重内慎与外防,倡导用“畏”“忍”“勇”“慎”等原则来节制内欲、抵御外邪,对慎病为主、预防在先的养生观作了详尽的论析。此外,他的养生观还吸收了许多中国哲学的思想,表现出比较明显的儒家精神,特别是他提出的仁孝一理、养生报德的养生思想,既是对儒家事亲立身之“孝”的继承,也是对宋儒万物一体之“仁”思想的发展。而他提出的道气一体、养气为本的养生之道,以及静以养心、动以养身的养生之法,则是对朱熹的道气观与理气论的改造与实践。
(3)普及了许多具有实用价值且容易操作的养生方法。贝原益轩以其数十年的养生经验为依托,在查阅了褚胤昌的《达生录》、李梴的《医学入门》、陈元靓的《事林广记》、陈藏器的《本草拾遗》等数十种养生医书的基础上,综合分析了日本的风土人情和日本人的体质特点,最终整理出了许多实用的养生方法,涉及睡眠、沐浴、汤治、用药、养老、饮食、房中、针灸等诸多方面,为江户时期日本民众提供了养生指导。其中,有一些养生法至今都还活跃在日本民众的日常生活中。
不过,由于时代的局限,贝原益轩的养生观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与缺陷。譬如,他在《养生训》中这样论述二便:“在外面解大小便的时候,不可面向日、月、星、辰、北极、神社等庄严肃穆之地……因为大小便排出的是秽物,见不得人,更见不得神灵。”[4]122这段话带有鲜明的日本神道教的色彩,缺乏基本的医学根据和科学论证,属于典型的迷信意识。类似的表达夹杂在《养生训》之中,既不可信,亦不可取。我们在分析贝原益轩等日本近代医者的养生理论与方法时,应坚持科学客观的眼光和去粗取精的态度。
4.2 贝原益轩养生观的启示 贝原益轩的养生观可以为我们提供许多借鉴与启示。一方面,他提出的仁孝一理、养生报德的养生思想,将儒家强调的伦理道德与医家重视的养生保健结合在一起,为身体的养护保健增添了道德伦理的要求与约束,强化了养生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既提高了人们对养生的重视,又有利于将养生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这种从文化精神的高度来强调养生的思路,既强化了文化的属性,又淡化了专业性的医学色彩,是值得我们思考与借鉴的地方之一。
另一方面,贝原益轩将学理性强的养生理论与操作性高的实用方法作了比较明显的区分。他用汉字撰写的《慎思录·养生说》具有一定的哲理性。虽然该书体量较小,且不成体系,但内容却比较精深,对读者的学识要求比较高。与之相比,他的《养生训》则是专门为日本平民撰写的手册式著作。为了照顾民众的识字水平与理解能力,他还特意使用了言简意赅、通俗易懂的训语,分门别类地向民众讲述了大量实用的养生技巧与方法。这些养生方法对专业的要求不高,操作难度也不大,易于理解,也易于传播,且比较容易成为常识性的技巧融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其中有一些易行且实用的养生方法,如温泉汤治法,至今都还存在于日本人的生活中。这种区分理论与应用的思路,将比较深奥复杂的思想理论转化为实用易行的技巧方法,既不影响思想理论的探讨,又有利于养生方法的宣传与普及,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贝原益轩的养生作品被多次外译,逐渐流向欧美,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医养生思想在海外的传播。关注和研究他的养生观,既有利于我们了解中医养生思想的海外传播情况,也有助于我们思考中医养生事业的现代化发展方向与国际化传播理论,同时又具有“异域之眼”的作用与价值,可以为我国新时代养生产业的发展提供一种比较与借鉴的视域,让我们可以从中吸收经验、吸取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