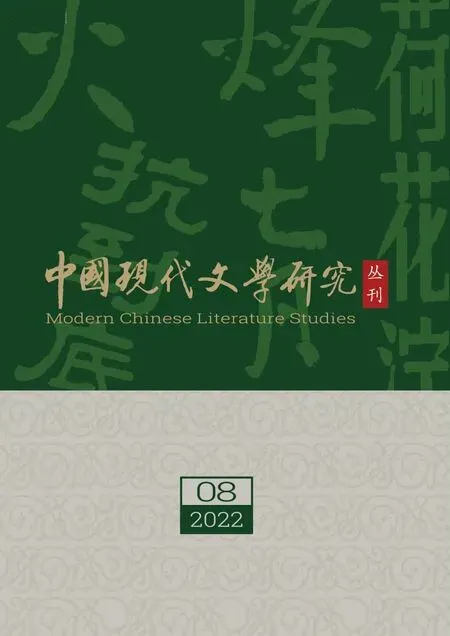新当代书写:以《漂洋过海来送你》为例
张慧瑜
内容提要:当代书写是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社会意识,是与革命文化、现代文化相关但又不同的时代精神。相比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创造“当代”文化,七、八十年代之交重提“当代”,近些年出现了一种新当代意识,体现有三:一是重建古代(传统)与现代的连续性,讲述更具文化自觉的中国故事;二是弥合现代与革命的分裂,确立更主体化的中国位置;三是改变中国落后于西方的现代焦虑感,讲述更平等、更多元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石一枫新作《漂洋过海来送你》是一部具有新当代意识的作品,一是以那豆一家及北京胡同,串联起从满族到胡同青年的平民史;二是以那豆追寻爷爷那年枝、老太太沈桦等共和国一代的故事,完成1950.—.1970年代与改革开放时代的融合;三是以那豆(北京)/黄耶鲁(美国)/何大梁(阿尔巴尼亚)间的大尺度空间建立一种世界视野下的中国故事。《漂洋过海来送你》有理由被视作“新当代书写”的代表作。
“70后”作家石一枫的长篇新作《漂洋过海来送你》近期出版,这本书有着复杂的人物关系、横跨三大洲的空间尺度、贯穿1950 — 2020年代的时间线索,是石一枫小说中时空跨度最大的一部,这部作品也延续了石一枫小说的叙事特征,如一个人物串起所有故事、充满悬疑、带解谜色彩等。近些年,石一枫一直尝试用文学(小说)书写当下和“现实”①石一枫:《对于“写现实”的一点想法》,《文艺报》2016年4月8日。,这种转型本身是二十一世纪当代文学的新发展,是摆脱1980年代以来追求形式、审美之后的新尝试,也是回归到文学这一媒介诞生之初所扮演的角色:十八、十九世纪回应现代文明、工业社会所带来社会问题的现实主义小说。本文从“新当代书写”的角度来解读这部小说,认为这部作品反映了一种“新当代”意识。相比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创造“当代”文化,七、八十年代之交重提“当代”,所谓“新当代”是二十一世纪形成的一种新意识。在中国崛起、世界格局巨变的背景下,新当代意识体现为三个特征:一是重建古代(传统)与现代的连续性,讲述更具文化自觉的中国故事;二是弥合现代与革命的分裂,确立更主体化的中国位置;三是改变中国落后于西方的现代焦虑感,讲述更平等、更多元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就是说新当代意识改变了二十世纪以来在古(传统)/今、革命/现代、中国/西方的二元对立下讲述中国故事的框架。新当代意识形成于2010年前后,在学术界、思想界等不同领域有彼此呼应的体现。在文学领域表现为:一是克服了传统与现代的对抗关系,国潮、古风变成中国故事的文化标识;二是弥合革命与现代的张力,把革命作为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经验;三是中国故事从民族国家叙事变成全球/世界视野下的中国讲述。在这种背景下,《漂洋过海来送你》是一部具有新当代意识的作品,一是以那豆一家及北京胡同,串联起从满族到胡同青年的平民史;二是以那豆认同爷爷那年枝、老太太沈桦等共和国一代的故事,完成1950 —1970年代与改革开放时代的融合;三是以那豆(北京)/黄耶鲁(美国)/何大梁(阿尔巴尼亚)间的大尺度空间建立一种世界视野下的中国故事。因此,《漂洋过海来送你》是一种典型的新当代书写,呈现了新的时代意识和社会感。
一 三种“当代性”与新当代书写
近期出现了一些关于“当代性”的讨论,这些论述再次凸显了从“当代”视角理解1949年之后文艺实践的重要性。①在《当代作家评论》2022年第1期刊物上发表了一组“当代文学的‘当代性’与研究范式转型”的论文,分别是杨丹丹的《文学大数据与当代文学研究范式转型》、陈培浩的《从断裂到共生: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范式观的反思》、周展安的《“当代性”的绽出与当代文学研究的“反历史化”契机》、朱羽的《历史、形式与文化政治——当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构造》、卢燕娟的《“当代”作为问题的发生——以延安文艺运动到“十七年”时期的文学史为对象》、李静的《作为“新显学”的中国科幻研究:认知媒介与想象力政治》。这种当代性意识一方面与1950年代所确立的区别于现代文学的当代文学“规范”有关,另一方面也与1980年代以来形成的当代文艺想象有关。从历史的视角看,1949年以来有三次“当代性”的兴起。
第一次当代意识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出现的。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理解百年中国有三个关键词:一是现代,指的是现代化和现代性,现代化强调的是国家、经济、社会等工业化的硬指标,现代性指的是现代精神、现代文化,如个人、自由、民主等价值观,还有对现代化弊端的批判,即反现代的现代性精神。辛亥革命是现代中国的政治开端,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现代中国的文化开端;二是革命,现代革命主要指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在革命实践中产生了革命文化,如以工农兵为核心的人民文艺,还有集体主义、大公无私、劳动者文化等革命文化。在革命文化的视角中,现代文化有着清晰的阶级属性,是资产阶级文化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三是当代,相比现代和革命,当代的概念略微特殊。1949年之后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文化,因此,新中国又被称为当代中国,1949年之后的文学则被命名为当代文学。当代文学就是建立一种社会主义文化,以现实主义社会主义为基础的人民文艺。②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当代文学以及当代性被认为是以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基础的文学形态。在这个意义上,当代文化与革命文化有相通之处。这是第一次当代意识兴起。
第二次当代意识兴起是1970年代末“拨乱反正”时期,通过反思革命文化,重提当代性,出现了诸多以“当代”命名的刊物和文艺作品,如文学刊物《当代》创刊于1979年、第四代导演黄蜀芹的电影《当代人》拍摄于1982年、文学评论刊物《当代作家评论》创刊于1984年。1980年代的“当代性”追求的是一种现代文化和启蒙意识。1980年代出现了“重写文学史”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思潮,把1949年到1978年作为被革命中断的时代。①1987—1988年,王晓明、陈思和主持《上海文学》“重写文学史”栏目,“重写文学史”成为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最重要的文学思潮;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在《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中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这种从当代文学重回现代文学的意识带来三重文化后果:一是,开始以现代主义、以审美化、以回到文学自身等“纯文学”观念作为评价文学的标准,与此相关的是形式主义的文艺评论方法;二是,现代文学压倒当代文学,现代文学成为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显学”;三是,现代性取代当代性,现代中国与当代中国合并变成二十世纪现代中国。在这种现代压倒当代的过程中,革命文学被“再解读”为一种反现代的现代性,也就是说,革命文学并不自外于现代和现代性,是一种反思现代的现代文化。②唐小兵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在革命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的过程中,文化思想领域出现了两种思潮:一是形成了去政治化的文学观念;二是1990年代大众文化的兴起,通俗文化、流行文化开始重写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也借助古装剧抹除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的差异。
可以说,1950年代第一次提出当代性,最终走向了更加激进的革命文化,1980年代第二次提出当代性,走向了现代文化和现代意识。2010年前后,当代性和当代意识开始了第三次兴起。在美国领导的全球化遭遇危机与中国经济崛起的双重背景之下,这种新的当代意识与革命文化、现代文化形成了更为复杂和辩证的关系。一是传统与现代的隔阂和对立被打破,传统文化变成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国潮文化、二次元古风文化,传统不再是落后和守旧的代表,而是一种现代时尚和文化身份;二是革命文化并不外在于现代中国和传统,革命、现代与传统有机融合为新文明形态,形成了一种既现代化又反思西方模式、西方道路的中国道路、中国经验。③曹天予:《现代化、全球化与中国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俞可平等主编:《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潘维:《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60年》,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潘维、玛雅:《人民共和国六十年与中国模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赵剑英、吴波主编:《论中国模式》(上、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郑永年:《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姚洋:《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张旭东:《文化政治与中国道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白钢、丁耘、韩潮等:《中国道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等等。一方面从国家工业化的角度解释中国经济崛起,重新把1950 — 1970年代纳入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另一方面从文明论的角度阐释中国模式的特殊性和独特性,把当代史放在古代史和文明史的延长线上,建立了一种更具主体性和文化自觉的中国故事;三是对美国/西方现代性的平视和批判态度,更平等地看待西方现代文明的优劣,出现了对非西方区域研究的重视,扭转了以欧美为核心的世界视野。在这种背景之下,文学、文艺领域的研究也出现了新变化,一是文艺创作更有文化自觉和制度自信,改变了现代化焦虑和东方主义式的自我想象。与1980年代现代文学压抑当代文学不同,当代文学开始压抑现代文学,阐释赵树理、丁玲、柳青、周立波等作家与社会主义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把反现代的现代性变成一种更具中国独特性的社会主义文化经验,从社会史、革命史的角度阐释革命文化的独特性,当代文学或者1940—1970年代当代文学研究成为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显学”①张慧瑜:《打开理解20世纪中国的文化空间》,《文艺理论与批评》2019年第4期。;二是讲述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故事,重提人民文学、现实主义文学,重新讨论文学与时代、形象与典型、人物与中国故事的关系等问题;三是构建全人类共同价值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体现在中国文艺作品也开始从民族、国家叙事转向人类视角,关于中国的叙述不仅是中国的、民族的,也带着世界性的普遍价值,如电影《流浪地球》是一部带有全球视野的中国故事。②张慧瑜:《〈流浪地球〉:开启中国电影的全球叙事》,《当代电影》2019年第3期。
在这个意义上,我把反映这种时代与中国状态的文学命名为“新当代书写”,石一枫是新当代书写的代表性作家。选择石一枫作为案例的主要原因是,作为“70末”生人,石一枫的文学教养来自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2000年之后开始文学创作,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规范有所反思,从发表《世间已无陈金芳》(2014)、《地球之眼》(2015)等作品以来,他有意识地用文学来回应时代和社会的变化,尝试写出当下中国的现实感和时代意识,尤其是在《漂洋过海来送你》中借那豆苦苦寻找骨灰盒的线索展现中国社会内部以及中国与世界的新关系。这十年来,石一枫小说的变化恰好呈现了当代文学创作的典型意味,这种变化体现为从“小我”出发到书写“他人”,从北京故事到世界视角下的中国故事。
二 从“小我”出发到书写“他人”:当代文学发展的一条线索
作为一位作家,石一枫不是野路子出身,他本科、硕士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接受过完整的现当代文学训练,对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也了熟于心,这使得他对文学创作有高度自觉,坚持用文学的方式来处理现实经验。作为一位“职业选手”,石一枫重视叙事、语言,其笔下的人物能不能立住、人物语言是否得体,成为其写作中格外关注的“技术指标”。近些年,石一枫一直尝试突破“自我”经验,从写“我”熟悉的故事到写“他人”的故事,这成为理解二十一世纪当代文学发展的重要线索。下面从四个角度来阐释石一枫文学创作的特点。
一是石一枫文学的当代性和现实性。石一枫对文学、尤其是严肃文学有自己的执念,他的创作处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所确立的文学(小说)范畴内,尤其是经过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那个更为“纯粹”的文学范畴内。对石一枫来说,从老舍到王朔的北京文学对他的影响最深。王朔是石一枫青年时代的文学启蒙者,王朔式的语言、人物性格是其文学书写的底色,《漂洋过海来送你》的主人公那豆是胡同青年和大院顽主的复合体,他动不动就打架、起范儿,有点“轴”。这些年,石一枫的小说语言逐渐摆脱王朔的影响,变得更加平实和老到,人物形象和小说结构也越来越复杂,进入中年的石一枫开始处理更加宏大的社会结构和更复杂的人物关系,整体风格上有从王朔向老舍转变的倾向,从早期的《红旗下的果儿》(2009)、《恋恋北京》(2011)带有王朔文学的痕迹,到近期的《特别能战斗》(2017)、《心灵外史》(2017)、《玫瑰开满了麦子店》(2019)、《漂洋过海来送你》,越来越带有老舍文学的味道。小说中的人物,也逐渐从喋喋不休、插科打诨的顽主,变得更加丰富和多元,塑造了一组北京平民的形象,如北京大妈苗秀华、大姨妈、北漂王亚丽、胡同青年那豆等。石一枫的创作始终关注当下,始终写当代故事。从1950年代当代文学开启之后,写当下、写当代、写作家与时代的关系,是当代文学最核心的问题,当代作家的任务之一是赋予当代中国的实践和经验以意义。从这个角度看,石一枫是一个具有“当代意识”的作家。2010年以后,石一枫自觉转向“现实”写作,他经常谈到要塑造典型人物和故事,某种意义上回到了十九世纪的文学观,也就是通过典型性来呈现当下社会的变化。石一枫的文学不是经典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文学,他无法对现实做全景式的观察和叙事,只能借助“小我”或者“别人”的限定性视角来呈现一种社会图景。
二是石一枫作品中类型文学的特质。与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文学不同,石一枫的小说中有类型文学的影子①一个小的佐证是,2018年石一枫的长篇小说《借命而生》荣获首届梁羽生文学奖侦探悬疑类大奖。,这种类型文学不是中国的武侠、言情等文学样式,而是如日本、美国的侦探小说、黑色电影等,这也是石一枫阅读比较多的文艺类型。这种类型文学的叙事模式是个人遭遇悬疑、犯罪,如希区柯克式的黑色电影往往让主角陷入一场未知的圈套、阴谋或危险的旋涡,进而步步揭开真相、走出陷阱。这种叙事类型反映了个体在现代都市中的不安和焦虑,尤其是中产阶层对不可见的力量的莫名恐惧和担忧。石一枫的小说经常呈现一种叙事上的三段论,一开始是人物登场和环境铺垫,从一个线索铺陈出几个线索,中间段落是剧烈的戏剧冲突,如金融诈骗(《世间已无陈金芳》《地球之眼》)、传销(《心灵外史》)、越狱/自首(《借命而生》)、骗钱/绑架(《玫瑰开满了麦子店》)等突发事件,结尾部分则是最高潮,所有线索汇集在一起总体解决。《漂洋过海来送你》就像一部侦探小说,开始是那豆与那年枝的爷孙深情,随着爷爷去世、骨灰盒被错装而引发的一场横跨中国、美国和阿尔巴尼亚的“乾坤大挪移”,这种以小博大的荒诞感以及那豆如侦探般的追寻,把一个一个人物背后的历史展示出来。“结尾”和“结尾的结尾”把所有叙事线索、矛盾汇总,进行最终“解谜”。这种把严肃文学与侦探小说式的类型文学结合起来的笔法使得石一枫的小说一方面很好看、故事有传奇性,有好莱坞电影的效果,另一方面又在人世旋涡和沉浮中探究人性、信仰、道德、正义等社会话题。石一枫喜欢把社会矛盾与个体道德、精神问题结合起来,小说中经常出现国企腐败、矿山污染、野蛮拆迁、非法传销、金融诈骗等社会事件,这些社会事件往往给小说中的人物带来精神和灵魂拷问,如《地球之眼》中“我”与安小男讨论曝光李牧光的金融诈骗是否道德、《玫瑰开满了麦子店》中王亚丽被虔诚的信徒岳晓芬骗走十万块钱时讨论“是否对不起主”等。
三是从写“小我”开始。石一枫的早期作品《b小调旧时光》《红旗下的果儿》以北京顽主式的青年为主体,讲述他们的校园生活和“西征美国”“南下深圳”的“少年不知愁滋味”的人生故事,这与石一枫受王朔文学的影响有关。从《恋恋北京》中“我”与外地女大学生姚睫的故事开始,石一枫的小说转向《世间已无陈金芳》中“我”与陈金芳,《地球之眼》中“我”与安小男、李牧光,《特别能战斗》中“我”与北京大妈苗秀华和《心灵外史》中“我”与大姨妈的故事,也就是开始从“我”的故事转向“我”眼中的“他人”故事。这里的“我”是1980年代出现的“小我”,“小我”是1980年代文学对1950—1970年代大写的“我”的批判。集体性的“我们”以及代表性政治的失效,使得经典的现实主义叙事变得不可能。1980年代虽然出现了“小我”,但“小我”携带着“大写的我”的痕迹,也就是说借“小我”之口喊出时代的呼声。1980年代中后期的先锋小说家余华、莫言等创造了一个抽象的“我”,一个带有现代主义、普遍主义色彩的“我”。到了1990年代“小我”才变成一个具体的、有限定的、彻底的“小我”,“我”无法代言、也拒绝“代言”,“我”只能叙述“我”看到的历史、现实和经验,这就是王小波、朱文、韩东等作家的特点。石一枫写作的也是“小我”的故事,叙事者回归到“小我”的视角,“我”的在场提供了叙事的“真实”感,是一种限制在“我”的视角下的真实。石一枫的小说中基本都有一个贯穿性的人物,这个人物像“在场的摄影机”一样,为故事展开提供“现实”依据。这种“在场性”就是1990年代的“小我”,以“小我”的经验串联现实,否则就无法展开叙述。
四是从“小我”到书写“他人”。近两三年,这种“小我”眼中的“他人”变成了“他人”的故事,如《借命而生》中的警察杜湘东与越狱犯许文革、姚斌彬的故事,《玫瑰开满了麦子店》中北漂王亚丽的故事,《漂洋过海来送你》中胡同青年那豆的故事。这种从“小我”的故事,到“小我”眼中的“他人”,再到“他人”的故事,不只是单个作家风格的转变,代表着对1980、1990年代当代文学的反思,是新世纪以来当代文学的一种转向。那豆就无须“我”来作为叙事中介,其他人物和事件需要借助那豆引出,那豆听到的、看到的、想清楚的,所有的叙事都建立在那豆的“在场”上,这是一种单一视角下的叙述,这种叙事建立了一种“真实感”。如果那豆“不在场”,其他人物的故事就没法讲述。所以那豆要像“侦探”那样,一步步去解谜、去调查、去认识、去了解,每一步都有“现实”的依据,那豆把整个故事和世界串起来。因此,看起来是写“他人”的故事,“他人”里面装的还是那个“小我”,但写的是“他人”的经验。石一枫小说中的人物有一个典型特征,比较“轴”、比较真诚、较真,如《特别能战斗》中的苗秀华是与人斗、与天斗、与领导斗的“刺头”;《借命而生》中的逃犯许文革为了完成姚斌彬的遗愿,不仅接管了原来的工厂,还回收了那辆导致他俩入狱的“皇冠轿车”,而警察杜湘东也锲而不舍地要跟踪逃犯许文革,想找出他违法乱纪的证据;《心灵外史》中的大姨妈也是相信各种“信仰”的人;《漂洋过海来送你》中的那豆也是“一条道走到底”的人物。这类人物性格一方面来自王朔笔下不愿意妥协的小人物①1990年代有两部影视剧作品也呈现了这种“一根筋”式的人物,一是1995年反特剧《无悔追踪》,二是1997年张艺谋的电影《有话好好说》,两部作品中的主角都是有类似性格的人物。,另一方面也与石一枫赋予这类“一根筋式”的小人物以道德感有关。其实,这种小人物身上的执着、较真的性格,来自革命文学中的英雄模范,只是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这类革命化的英雄抽象为一种特殊的人物性格。
可见,石一枫无法像二十世纪的现实主义作家那样,进行一种全景式的描写。叙事的合法性建立在“小我/他人”的限定性视角中,从特定主体的特定结构位置出发,对社会进行一种个人化的总体性和整体性呈现。
三 “太平洋”视角下的中国故事
在二十世纪文学史中,北京文学、京味文学逐渐被建构为一种与海派文学不同的城市文化传统。2010年以来,石一枫的文学创作也被命名为京味文学的新发展。②白烨:《石一枫长篇小说 〈漂洋过海来送你〉:“新京味”的新力作》,《文艺报》2022年5月27日。《漂洋过海来送你》也是一部以北京为底色的小说,以胡同青年那豆为出发点,蔓延出一个更具时间(历史)跨度和空间广度的作品。在时间上,横跨1950年代以来的当代史,在空间上,涉及北京、燕郊、贵州等多个区域以及中国、阿尔巴尼亚、美国等多个国家。
首先,这是一部中国当代故事。那豆是一个纯正的老北京人,住在胡同里,是“根红苗正”的满族人,这些都像是回到了老舍的传统。但更重要的是,那豆的另一个身份是北京工人的后代,他爷爷和父亲都与北新桥酱油厂这个街道国营企业有关。这种带有工人视角的北京在北京故事中是比较少见的,一谈到工厂转型、工人下岗,更容易想到老工业基地东北,反而遮蔽了同样曾是工业发达城市的北京、上海——它们只是在转型升级中变成了去工业化的后工业城市。这种工厂叙事在石一枫的小说中经常出现,如《特别能战斗》中北京大妈余秀华在北京东郊一家电子设备制造厂当工厂干部,《借命而生》中的逃犯许文革、姚斌彬也来自北京第六机械厂,这种工厂经验一方面与北京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依然存在大量工厂以及九十年代国营工厂转型这一最重要的社会事件有关,另一方面与刘震云、朱文等作家在九十年代写单位、工厂的小说有关。那豆所居住的胡同不仅是鼓楼地区的老北京空间,也是以酱油厂职工为核心的单位家属区。从爷爷那年枝、父亲那三刀到孙子那豆,带出了1990年代工厂改制、变卖的历史。小说从爷爷的去世、葬礼谈起,以那豆拿回爷爷的骨灰告终。这种对祖辈的寻找、探究和解密,给人物的逻辑提供了更历史化和社会化的解释,历史化在于有因必有果,事情都有出处,那豆不再是无父之子、父亲缺席或解构父亲的故事主角(这曾经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当代文学中常出现的设定),而是在爷爷的影响之下,变成像爷爷一样的人。
在那豆寻找爷爷骨灰盒的过程中,爷爷的话“讲理的人家”“争的是个理儿”“为别人着想”等,都成为那豆心理逻辑的内在动力。这部小说不仅没有解构爷爷、李固元的劳模身份,反而把爷爷、李固元、抗美援朝护士兵沈桦当成一种榜样。在小说中有两个细节,使用了戏仿的修辞方式。一处是阴晴去美国之前,那豆与阴晴爬到鼓楼古城墙,完成成人礼,尽管那豆依然无法向阴晴表白、无法从男孩变成男人,但他们在鼓楼上的行为是对爷爷在1950年代替解放军照看医用绷带的戏仿,爷爷看到了奔赴朝鲜战争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成为他人生中最自豪的段落;第二处是那豆背着崴脚的黄耶鲁穿过森林走向海边私人游艇,这个情节是对受伤的沈桦被志愿军战士拯救的戏仿。①《漂洋过海来送你》中还有一处戏仿,是那豆在黄耶鲁别墅与美国警察抢夺骨灰盒,被美国警察用膝盖顶住脖子,那豆喊出了“我不能呼吸”,戏仿的是2020年美国“BLM运动”中被白人警察暴力执法的黑人乔治·弗洛伊德喊出的话。两次身体行为上的戏仿都是对祖辈精神的认可。在这个意义上,那豆不只是打架、“起范儿”的胡同顽主,也是携带着历史使命感的人。
其次,这是一部全球视角下的当代故事。借寻找骨灰盒,把北京胡同故事,与到埃及、阿尔巴尼亚打工的海外农民工和移民美国的中国富二代等不同的社会阶层的故事都展现出来,呈现了崛起时代中国与第三世界、第一世界密切的全球联系。这部小说从名字《漂洋过海来送你》到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来自太平洋西”“第二部分前往太平洋东”,都带有“海洋”气息,选择的是一种“太平洋”视角,中国在“太平洋西”,美国在“太平洋东”。这种海洋视角与近代以来西方对世界地理的理解有关,尤其是“环太平洋”的概念来自作为两洋国家的美国,这部小说可以说是一部中国作家书写的“环太平洋”故事,也就是把中国与美国放在太平洋的两端,这就使得“漂洋过海”具有了双重意味,一是漂洋过海到美国,二是漂洋过海到中国。
在关于北京的文学想象中,美国是不可缺席的他者。这在王朔、冯小刚的文学影视作品中体现为:主人公要不去美国留学、打工,要不从美国返回北京,如电影《大撒把》中的留守女士、《不见不散》中北京人在美国的奇遇记以及《非诚勿扰》中从美国回来的归国人士。其中最有名的作品是1993年热映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使得“纽约/美国”始终在19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北京文化想象的内部。石一枫的作品中也经常出现美国,如《红旗下的果儿》中张红旗的“西征”对象是去美国留学、《恋恋北京》中有来自美国的前妻茉莉、《地球之眼》讲述的是做中美贸易的李牧光的故事,可以说,美国内在于北京故事和中国故事之中。只是《漂洋过海来送你》呈现了一个更加复杂的美国。那豆踏进美国之后,是一种“陌生的熟悉感”,“他长了二十多年,可是连二环路都没怎么出过的呀。但也怪了,来了也不觉得生疏。这还真不是自作多情,从小到大,他早已跟着电视、电影乃至于电子游戏造访了无数遍‘美国’。和那些光怪陆离、惊心动魄的‘美国’相比,此刻这个美国既没有街头枪战更没有外星人入侵,那就没什么让人发怵的了。因此当那豆从防波堤上转身,穿过湖滨公路走向那片大学时,步态一如他晃悠在二环路里的胡同中那样轻松自如,透着不见外”①石一枫:《漂洋过海来送你》,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168页。。这不仅说明《北京人在纽约》等大众文化作品早就把美国想象植入中国当代的记忆,而且借助游戏、好莱坞电影,美国虽然在太平洋彼岸,却种在中国人的心里。借助那豆的目光和阴晴的引导,这部小说呈现了美国的另一面。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阴晴的妈妈郑老师对美国充满了向往,美国代表着高品质的生活,而留学美国的阴晴则遭遇了一个更加真实的美国,是金融危机时代种族问题、阶层矛盾丛生的美国。学习社会学的阴晴向那豆分享了偏左翼或“白左”视角下的美国,从那豆一到芝加哥,就看到了两极分化的城市空间以及特朗普时代阶层、种族分裂的美国社会。不过,那豆也感受到了美国的法治力量。无法无天的富二代黄耶鲁在与那豆交换骨灰盒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意料之外的困难,一些黄耶鲁的钞票无法完全解决的问题。
在“环太平洋”的故事之外,这部小说还涉及更多“世界”区域,这就是借田谷多、何大梁师徒来呈现的与黄耶鲁相反的另一种海外中国人的故事。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中国资本、商品走出去,中国工人也走向海外。农民工形象在石一枫的《恋恋北京》《玫瑰开满了麦子店》等作品中也出现过,他们是都市景观中的“他者”。在《漂洋过海来送你》中,田谷多、何大梁也是那豆眼中的“他者”。相比那豆、阴晴、黄耶鲁及其父辈们更加鲜活的形象,田谷多、何大梁略微概念化。田谷多是一个掌握了修桥技术的大拿,没有亲人,也没有历史,是孤儿式的存在,其形象主要来自徒弟何大梁的描述,他们长年在东南亚、中亚、非洲、欧洲等地区从事桥梁工作,承担中国国有建筑公司的海外工程,是层层转包的农民工,显示了中国资本、劳动力海外输出的能力。那豆与何大梁的联系方式主要是手机,通过微信等手段建立了北京胡同与阿尔巴尼亚工地的虚拟关系,那豆既没有到何大梁的工作地阿尔巴尼亚,也没有到田谷多的家乡贵州。不过,那豆对何大梁的态度从不了解到最终成为好兄弟。田谷多对桥梁事业非常热爱,他本想到阿尔巴尼亚修桥也是因为“梁式桥、拱形桥、悬索桥……就是没修过全机械化建造的特大组合体系桥”①石一枫:《漂洋过海来送你》,第232页。,这是一种工人的“荣耀”,这种技术工人对手艺的热爱,与爷爷那年枝对待酱油厂的搬缸工作和火葬场司炉工李固元对待工作的态度是一致的,他们都相信“人对得起手里的活儿”的道理。在田谷多的骨灰盒中有一个桥梁专用“螺丝”,螺丝本身是工业小说中对工人身份的修辞②李海霞:《螺丝钉精神的文学表达》,《文艺理论与批评》2020年第3期。,在这里,螺丝与田谷多的骨灰放在一起,变成了田谷多身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就是说,田谷多、何大梁虽然是农民工,但他们也分享国营企业工人的工业伦理和螺丝钉精神。他们对于北京文学、中国文学来说,是一群“新人”。尽管在小说中关于他们的描述有些刻板,但也显示了作家的“全球”视野。
总之,与二十世纪的全景、全知叙述的现实主义不同,也与过度抽象化、地方性的现代主义小说不同,这部小说是一种在有限度视角下的现实主义,是把地方经验与更宏大的历史、结构连接起来的现实主义“蛛网”。在小说中,那豆反复引述李固元的话“事儿都拴在一块儿了”,因一个事联系到人,又由人联系到新的人,这就形成了一张人与人的社会网。这种“拴在一块儿”的网不只是人与人建立了联系,而且是不同时空中的人都有了密切关系。那豆寻找骨灰盒使革命者沈桦、新富阶层与平民之家那年枝、那豆以及农民工田谷多建立了密切关系,他们并非彼此生活在不同空间的群体,而是同一个历史进程中的人。这些角色共同拼贴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故事,一方面经济崛起带来社会阶层的分化,另一方面中国更深入地走向世界。那豆试图把这些不同阶层的主体“拴”在一起,呈现一种总体性的当代中国的复杂性。这个“蛛网”没有清晰的出口和入口,可能是四通八达的通途,也可能是循环往复的陷阱。石一枫是一个织网的人,是一个在没有地图和标识的时代,把新的现实和经验变成一张可见的“蛛网”的作家。
四 “新当代书写”的可能性:中国经验的普遍性
石一枫的创作比较可贵的地方是,他一直在积极地回应时代和社会的变化,并尝试用“文学”、用“小说”这种“旧手艺”来处理这些新的经验,就像《漂洋过海来送你》借那豆这个典型人物呈现全球和世界视野下的中国故事,是一部具有新当代意识的小说。那豆在石一枫的作品序列中,既是新人,也是旧人。说其“旧”,那豆是北京胡同里长大的顽主、“老炮儿”,其内心活动、心理世界与王朔以来的顽主青年类似。说其“新”,体现在他的行动力上,一方面那豆有爷爷所留下的传统和做派,另一方面那豆敢于走出胡同,走向燕郊找李固元和飞到美国找黄耶鲁。
第一,那豆是一个有行动力的主体。在为爷爷找回骨灰盒的过程中,他走出了胡同的世界,也走出了爷爷给他讲述的家族故事,他来到燕郊,看到了二环里面的鼓楼与燕郊的差异,他跟踪李固元“体验”了一次从燕郊到北京的“跋涉”之旅;他来到美国,看到了美国城市空间的阶层区隔以及充满社会矛盾的发达社会;他与阿尔巴尼亚的何大梁建立了“虚拟”关系,看到了中国人和中国企业辐射到埃及、阿尔巴尼亚等遥远的地方。尽管出于为爷爷找回骨灰盒的一己“私利”,但这种“漂洋过海”的行为使得那豆深入了解中国与世界。这种“上天入地”的行动力,显示了那豆的自信,也显示了中国介入世界的深度和广度。
第二,那豆的角色是一个社会中介者和历史弥合者。通过爷爷的死亡,三个不同时空中的人归于同一个时刻,而那豆找骨灰盒、送骨灰盒的过程,也是重新寻找自我、自己的家族史、当代中国的历史以及与不同社会阶层建立联系、彼此理解的过程。那豆完成了三重弥合,首先,那豆的满族身份以及“讲理”“起范儿”的性格特征实现了传统与当下的融合;其次,通过那豆对爷爷、沈桦等老一辈人的致敬,1980年代曾经被放逐和负面化的1950 — 1970年代的历史,得以借“精神遗嘱”的方式回归,实现了当代史内部的和解;第三,那豆把这些人“拴”在了一起,说明他们之间有着“因果关系”,甚至小时候那豆、阴晴就与黄耶鲁、沈桦在烈士陵园偶遇过,“拴”起来也是把不同时空的社会阶层“黏合”起来的过程。只是那豆作为行动者、历史“黏合剂”的作用,又是“脆弱”的、临时的,这些彼此“拴”在一起的主体,生活在不同的“平行空间”。这就是全球化或后全球化时代的两面性,万事万物看起来“拴”在一起,但其实又隔着千山万水。
近些年,“70后”作家也在写一些大题材、大历史,如徐则臣创作《北上》,离开个人的、当下的经验,写京杭大运河的民族史诗。这一方面说明“70后”进入中年之后,对时代和历史有更多思考,另一方面也与中国整体位置的变化有关。如果说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到2010年前后,中国的主流文化还在一种去政治化的氛围里,那么2010年以来世界和中国的格局都发生了巨变,美国也不是原来的那个美国,中国更不是之前的中国,这个时候政治性的、历史性的因素越来越凸显,文学创作其实也在回应这些变化。对石一枫来说,他坚持文学的精神,用文学的方式来处理一些“宏大主题”,让他的人物离开北京,具有更多历史感和时代感,就像《漂洋过海来送你》写了一个当代史的故事,虽然人物、家族的变化有点简单化,但显然他意识到当下的问题不只是现在的问题,而是与当代史、与遥远的人们都“拴”在一起,包括埃及、阿尔巴尼亚等发展中国家也与中国密切相连,这些都是新的中国经验。那豆的位置,既是北京平民的位置,也是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那豆如同“摆渡者”,一头牵着美国等发达国家,一头拴着发展中国家。在这个意义上,那豆的故事,是北京故事,也是中国故事,还是世界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