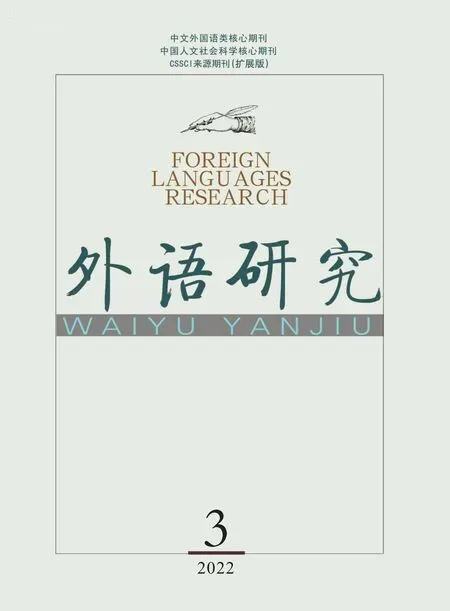译介多元现代的世界文学*
——以《现代》的转译活动为中心
史婷婷 刘叙一
(上海商学院商务外语学院,上海 200235)
0.引言
“转译”是现代文学汉译史上的一个较为特殊的现象,在我国起到了“巨大的、不可或缺的历史作用”(王友贵2008:27)。作为翻译活动的一种特殊形式,翻译活动在20世纪初叶的中国兴起与繁荣,间接翻译是当时频率很高的翻译方式(罗列2014:72)。然而,这种借助翻译进行文本传播的模式长期以来受到了研究者的忽略。现有的相关研究也多将重点置于语言层面,即考察转译的效果是否忠实于原文,或是聚焦于转译文本与直译文本的比较上。此类研究无法还原转译活动发生时真实的历史文化语境,从而低估了转译活动的价值、意义和在翻译史上所产生的重要作用。本文以“淞沪抗战”后创刊于上海的第一份大型文学杂志《现代》杂志的转译活动为对象,考察其独特的转译动机,所呈现的转译规范意识以及在转译过程中所凸显的审美现代性倾向,重新审视转译活动,尤其是《现代》杂志的转译活动在我国现代文学转型时期所承担的重要角色。
1.何为转译
我们在讨论转译的定义时,通常会发现“间接翻译”和“重译”这两个概念。《中国翻译词典》在“重译”的第三个释义中提到关于“转译”的定义是“非直接译自原著语言的翻译,即译自第三国语言的翻译”(林煌天1997:93)。也就是说,除了对自己旧译的润色修订以及对同一原著的不同译本,“重译”在范围上也包含了“转译”。在《描述翻译学及其他》一书中,图里(Gideon Toury)提到了“间接翻译”(Indirect Translation),与“直接翻译”(Direct Translation)相对应的问题,指出“间接翻译”是在翻译过程中假借了其他中介语译本所产生的翻译行为(Toury 1995:82)。在国内翻译学界,描述这一翻译现象的术语其实并不统一,有学者如王友贵(2008)、陈言(2005)遵循旧例,沿用历史上使用过的“转译”;罗列(2014)等则在翻译学国际视野的影响下开始采用“间接翻译”(李宏顺2019:110)。本文所讨论的“转译”行为是指《中国翻译词典》中对“重译”的第三重释义和图里所提到的“间接翻译”,以下统称为“转译”。
转译现象并不罕见,因为在一些历史阶段,“出于各种条件的制约,其中有大量作品未能实现从原著到中文理想化的直接翻译,而是以某一国语言译本为中介,进行了转译”(国蕊2019:205)。在中国翻译史上的历次翻译热潮中其实都有转译活动的参与,从以佛经为代表的宗教典籍翻译活动,到晚清时期林纾的“豪杰译”,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以日文为中介语言的翻译热潮以及之后对世界儿童文学的翻译,这些转译活动都是中国翻译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与直接翻译一起,参与了东汉到唐宋的佛经翻译,晚清时期的“西学东渐”,以及清末民初的科技翻译,见证了中国历史上文化交流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转型的几个关键时期。在我国对东欧诸社会主义国家文学翻译活动里,在对多数欧亚美洲非社会主义国家文学翻译活动里,仍不能摆脱转译,其中多数国家在1950年代仍以转译为主(王友贵2008:27)。根据陈言(2005:100-104)的总结,我国20世纪文学翻译中的转译所依据的中介文本有以下几种情况,晚清时期转译活动多依据日译本;到了1920至1930年代,主要是依据英译本转译东欧小国的文学作品;到了1930至1940年代,转译对象有所变化,开始聚焦在“十月革命”后苏联无产阶级文学作品以及除日本以外的东方各国的文学翻译。鲁迅在提到转译与直接翻译的优劣时,认为除非直接译本在质量上要优于间接译本(转译本),否则不能以直接翻译作为护身符(鲁迅1981:504)。很明显,鲁迅将转译视为与直接翻译对等的、传递文学性的另一种译介模式,转译的效果并不一定低于直接翻译。因此,作为我国翻译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转译活动的意义和价值不应该被忽视。
现代文学的塑造和构建始于报刊和书局,报刊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渗透和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李楠2007:47)。作为外国文学翻译史上重要的载体,期刊杂志在我国现代文学翻译史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小说月报》是20世纪初至二三十年代组织和开展转译活动的主要媒介,在其刊载的400多篇小说中,有50篇是由转译而来(刘庆元,刘柳2014:133-137)。然而,《小说月报》在1932年“淞沪抗战”的炮火中受到了重创,上海的文化出版业也一蹶不振,整个上海在战后几乎处于一种文化“真空”状态。在这一背景下,《现代》杂志作为1930年代上海仅有的几份大型文艺杂志之一,成为了见证当时文学生产的重要期刊。期间,《现代》是否开展了外国文学的翻译活动?转译活动在其所有翻译活动中所占的比例如何?所选择的转译对象,转译动机以及转译模式是否有不一样的特征?在我国转译史上发挥了怎么样的作用?本文尝试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
2.20世纪初对“弱小民族文学”的转译
作为翻译行为的一种,每个阶段的转译活动同样承载着特定的动机与目的。晚清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国内大多数的译者们由于受到所译原文文本的初始语言能力限制,只能从自己熟练掌握的语言译本中转译自己不熟悉的语言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如果是由于条件限制被动地由其他语种进行转译,那么其动机便在于填补直接翻译的空白且该转译行为较具时效性(佘协斌,陈静2004:48-51)。在这种情况下,转译本所起到的流通及传播效果其实是非常有限的。那么既然在语言上不具备直接翻译的能力,为何还要通过中间译本,千方百计地将这些作品迂回地传入中国呢?为何当时的译者不直接翻译用自己所掌握的语言撰写的别的作品呢?这便要涉及20世纪初我国转译活动的主体动机及选译倾向。
与直接翻译相比,20世纪初以来转译活动在我国同样是较为普遍的翻译行为,从世界范围内看,中国对转译行为的选择远超其他国家。郑振铎甚至用“在哪一国都是极少见的”“非常盛行”等字眼来形容当时频繁的转译活动(郑振铎1921:22)。受晚清中日权力变化、外语学习途径等因素的影响,经日本的转译在整个近代翻译文学中占据显著地位,成为瞩目而又特殊的翻译现象(国蕊2019:205)。到了20世纪初,由于当时形势的需要,以《小说月报》为主要媒介的外国文学转译为我国带来了除主流欧美大国之外的文学滋养。正如鲁迅所言:“倘不重译,我们将只能看见许多英美和日本的文学作品”(鲁迅1981:258)。此处的“重译”,指的就是转译。因为“至少在1920-1930年代,在中国‘重译’最主要的概念指的是‘间接翻译’”(田园2019:48)。而当时转译的对象,则主要来自那些在地理位置,民族规模以及世界地位中处于边缘位置的,与中国国情相似的域外被压迫的“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当这些蕴含着反抗主题的作品被间接译介到中国时,能向国人展示他国人民的悲惨境遇,以“警示”的方式来激励国人,激发其反抗斗争的意识,这便符合了当时国内译界整体“求进步”的译介意识和动机。然而这些作品大多都是用“弱小民族”的本民族语言所作,这些语种的使用范围不广,掌握这些语种的译者屈指可数,转译的方式也就成了译介这些作品的不二选择。值得一提的是,《小说月报》《文学》《译文》等期刊还专门开设“弱小民族文学专栏”,集中转译这些民族的文学作品。曾任《小说月报》主编的郑振铎用“万声寂绝,惟闻晨鸡偶唱,我们实不胜有凄凉,孤独之感”(郑振铎1921:21),来形容小语种译介缺乏译介人才的无奈。从译介数量上来看,以《小说月报》为代表的期刊翻译群体所开展的转译活动有效地促进了20世纪初期“被损害的弱小民族文学”在我国的译介和传播。包括匈牙利、丹麦、西班牙等在内的“弱小民族文学”作品几乎都是通过转译的方式为国内读者所知的。在这波转译高峰后,我国对弱小民族文学译介积累了一定数量。然而,应形势所需而大量依靠转译的译介行为导致了这些仓促译就的译文多数只有短暂的使用价值。如果说以《小说月报》为代表的期刊翻译界以转译的方式开展了对弱小民族文学的集中译介,彰显了其所要极力呈现的民族意识与民族矛盾,那么“凸显‘弱小’不仅是唯一的译介动机,也是其在翻译过程中反复强调并不断放大的重要元素”(刘叙一2021:178)。正是此类译介动机促成了“五四”时期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绝大多数转译现象的发生。在这种动机驱使下的转译活动中,译者也就不会过多地关注作品的文学价值和创作手法等问题,多数译作的文学价值不高,后期得到传播、复译、重译的机会也就相对少了。
3.《现代》杂志的转译活动
20世纪初期我国对以“弱小民族文学”为重心的转译活动让当时的中国读者能及时地阅读到由多种语言创作的域外文学作品,在范围和视野上推动了国内读者对世界文学的了解。其实,不仅仅是在数量及范围上,转译的方式还可以为当时正处于现代文学转型期的中国文学提供更为多元化的外域文学资源和借鉴。在此过程中,有两个现象值得我们注意,首先,《现代》杂志创立时期同20世纪初相比,多语种译者人数开始增多。在《现代》的译者群中,有熟练掌握世界语的孙用,有通晓朝鲜语的楼适夷和掌握西班牙语的戴望舒。在小语种译者队伍不断扩大时,转译不再是一种被动的“无奈之举”或是翻译选择的“下策”,而是除了直接翻译外的另一种选择。其二,与晚清、“五四”和1920年代的转译活动相比,《现代》杂志的转译活动有了明显的计划性。在转译活动开始之前,编者对于译本、语言及译者的选择有着针对性安排。作为一个有着明确文学审美指向的刊物,编者将是否具有文学价值设为选载文学作品的唯一标准,杂志全部的翻译活动无论在选材还是策略上也必然遵循此标准。因此,在拥有如戴望舒、李青崖、孙用等熟练掌握小语种译者的情况下,《现代》杂志在可以直接翻译大多数文学作品的情况下还是选择了转译,此时,转译是承载杂志编译群特殊诗学考量的主动选择。在《为翻译辩护》中,鲁迅提到马君武转译《物种起源》所依据的原本译文质量较差,因此“有重新翻译的必要”(鲁迅1981:504)。穆木天(1934)提出,无论是直接翻译还是转译,对作品的了解是先决条件,在转译过程中需要注意文学作品的表现方式。如果说鲁迅、穆木天等人对“转译”的争论与看法代表着他们对20世纪初以来转译作品缺点的担忧,那么作为1930年代初译介世界现代文学的重镇,《现代》杂志则是通过转译活动推进了规范性建设,弥补了转译活动对文学性重视的不足,在文学创作手法及审美等方面丰富并加深了国内读者对世界文学的认知,培养了具有现代文学审美的读者群体。
3.1 转译规范意识增强
首先,在《现代》杂志的转译活动中,我们看到了转译规范意识的明显增强。清末民初的转译作品发表时并不注明原作和原作者,只标注译者名的情况较为常见(罗列2014:71-76),还有“人名、地名、故事情节全都中国化,甚至连原作者都一笔抹煞”的情况(陈平原,夏晓虹1997:7)。李建梅在研究《小说月报》的转译现象时也提到,晚清至“五四”时期的翻译大潮中,多数译者对翻译与创作的界限不是十分清楚,对翻译文学本身的价值也缺乏深刻的认识。因此,翻译中尽管有大量的转译作品存在,也并未引起研究者的关注与重视。然而这种现象在五四时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李建梅2012:112-118)。规范意识的增强在《现代》杂志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值得注意的是,杂志刊载的转译作品几乎都在前言或者后记中明确标注了所依据的译本以及原作者,还有一些译者在“译后记”中介绍了该作品最早是由谁在何时翻译到中国,在此译本推出之前被转译的次数,译作在国内大致的接受情况等,以方便读者和研究者根据需要对照阅读各个译本。如在翻译时,有些内容无法在译文里面直接呈现,比如时代背景、原作者意图、相关背景知识等,译者会在注释里进一步补充说明。从《现代》杂志上对转译作品语言的选择和所标注译本来源来看,除了世界语是新创造出来的人工语言之外,《现代》杂志选取的译本主要来源是法语和英语。从转译作品的相关副文本中可以发现,除了对原作者和作品的介绍以外,多数译文都专门提及了转译时所依据的转译本信息。
从《现代》的编者到译者,都对转译的中介本有强烈的标注意识。施蛰存多次在“编辑座谈”或“社中日记”中呼吁译者来稿时必须注明译本的详细信息,最好附上作家介绍。杂志选登转译作品时曾发生过一个小插曲,有一封读者来信声称在三卷一期上读到的尹庚的转译作品《强悍的女人》与穆木天翻译的《维利尼亚》第十节十二节相同,由此发出疑问。其实早在读者来信之前,编辑已经发现这篇文章是《维利尼亚》中的一章,译者尹庚是根据日译本《劳农俄国农民文学集》转译的,因为日译本的原译者没有注明,因此译者也不知道是《维利尼亚》的一章。编者在处理读者来信时及时与转译者尹庚沟通,确定转译本所依据的版本后及时回复读者。在三卷一期刊登这部《强悍的女人》的译作时,转译者也清楚地注明是译自日文版的《劳农俄国农民文学集》,并交代了原作创作背景是“俄国二月革命”之后的农村。可见当时的读者,尤其是《现代》的读者对于转译的现象已经有了较强的意识,且对转译行为有一定的要求和期待———即转译需要保留原作的基本形式、主题及内容。读者能清楚地意识到转译和改写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编者将该信置于“社中谈座”栏目中,并命名为“重译的困难”,一方面体现杂志对转译重译行为的重视,另一方面也透露了编辑在选登转译或者重译作品时的考量。
在杂志四卷二期的“社中谈座”中也有一封读者来信,该信就杂志在三卷六期刊载的一篇译作《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论》提出质疑。读者对文中所提出的“社会浪漫主义”这个新名词有疑惑,不知如何去理解这个概念,读者想要了解它的实义是否就是“革命的罗曼蒂克”。此外,有读者发现,该文是1932年苏联作家同盟的演讲报告之一,由此提出译者森堡所依据的原文到底是日文、英文、法文、德文、俄文还是世界语的疑问。读者在信中要求译者说明所依据的版本以便他们阅读时候可以参考,并同时提出在告知依据版本的同时可以解释清楚这个“社会浪漫主义”的概念。在收到读者来信后,虽然编者没能马上联系上译者本人,但还是立即回信给了读者,因为他们对这篇转译作品所依据的版本非常肯定,即日译本。就“社会浪漫主义”一词的解释,编者因为没有足够的文献支持,在同期杂志中没有给予读者确切的答复。从这次读者和编者的互动中可以看出,不仅是《现代》杂志的编译群,当时的读者群都对转译现象有比以往更为清晰的了解和认识。读者能够参照不同语言的译本进行比较阅读,有些甚至还可以根据转译所依据的版本对某些重要的文学理论及概念进行判断和阐释。转译在当时也被视为一种更为便捷的渠道,对新引进的思潮或者理论进行追根溯源,充分认识其发展及传播的过程。
3.2 丰富多元的转译内容
与《小说月报》彼时的翻译条件相比,1930年代初译者对多种语言掌握能力普遍增强。对于期刊来说,完全可以直接从源语翻译各类作品。从转译的对象来说,除了同为其他杂志所热译的“弱小民族文学”,《现代》的转译活动还涉及了其他一些文类、题材及风格的作品。那些“弱小民族文学”也不再以单一的“被压迫”的民族文学形象出现。《现代》的转译活动的对象整体上呈现出丰富、多样、立体化的特点。其中既包含了戴望舒由法文版转译的西班牙现代派作家阿索林(Azorin,又译阿左林)独创的随笔体小说《西班牙的一小时》(第一卷第一期);也有朱寿百由法文版转译的访谈类作品《高尔基在苏伦多》(第一卷第二期);杂志主编施蛰存从英译本《西班牙小说集》中转译了西班牙“九八一代”作家巴罗哈(PíoBaroja)的代表作《深渊》(第三卷第二期);陈君涵由英文版转译了国内鲜少有人介绍的苏联青年作家里昂诺夫(Larionov)的《科夫雅金手记》(第四卷第五期);孙用从世界语版本转译了罗马尼亚心理分析小说《小尼克》(第二卷第四期);中国诗歌会成员森堡由日译本转译了苏联的文艺理论文章《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论》(第三卷第六期)。
在选择转译对象时,《现代》杂志的编译群主要关注的是作品的文类、题材及创作技巧的创新性。杂志主编施蛰存亲自转译了西班牙作家巴罗哈的《深渊》,并安排戴望舒翻译了一篇巴罗哈的访问记作为补充阅读。巴罗哈并不是由《现代》首译至国内的,赵景深、赵家璧等译者在此之前已经翻译过其小说,并对作家做过相关介绍。当时,国内的媒介多称巴罗哈为“高贵的革命小说家”或“纯粹的革命作家”。巴罗哈也因此在我国被贴上了“革命作家”的标签。对《现代》来说,对巴罗哈的译介是《现代》杂志开展的西班牙“九八一代”作家作品系列译介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系列在戴望舒赴法前基本都是通过转译的方式进行译介。《现代》译笔下的巴罗哈不仅仅是一个革命小说家,而是对人的恐惧心理有着深入刻画、有着明快的现代语言风格的小说家。除了首次将西班牙“九八一代”作家独特的创作风格转译至国内,《现代》还通过转译的方式,为国内读者呈现了一种新型的访谈式文体。高尔基的文学作品是当时世界范围内左翼文学盛行下的译介热点,在我国也不例外。朱寿百从法国画报《看见》中转译了一篇对高尔基的访谈,编者意在通过此种轻松的文体形式,给读者提供一些更有趣的内容。除了访谈文章,编者还安排刊载了作家在苏伦多城旅居时的照片,以文字与图片相结合的方式向读者展现生活及旅途中不一样的高尔基。在选译《科夫雅金手记》时,编者重点推介那些表现革命期间充满矛盾和苦闷情绪的小人物形象作品。此外,《现代》选译了在国内鲜为人知的苏联青年作家,向国内读者推介其具有独特文学创作风格的作品。除了译介欧洲大国的文学,《现代》还通过转译的方式挖掘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国家在“弱小”标签之外的文学特征。同时,通过转译,国外的一些新兴的文艺思潮也得以及时地引介到国内。《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论》是一篇对苏联文艺理论和创作进行阐释的文章,森堡对此文的翻译是国内文艺界对苏联解放“拉普”,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口号的迅速反应。该文首次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走向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观点,还首次强调真实性对艺术创作的重要作用,此观点对我国文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在中国的翻译来看,这篇转译的文章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我国传播的先声。因为在此篇译文刊出后不久,周扬便在《现代》发文,对该主义做出最早的深入阐释。由此,《现代》取材丰富而又多元的转译活动不仅向读者传递了多样的文学信息,扩大了国内读者对译作题材、文类和思潮的认知范围,更是进一步丰富了当时我国的翻译活动。
3.3 审美现代性的传递
在积极选译包含各文类、主题在内的世界各国文学,培养转译规范意识之外,《现代》的转译活动还加速了1930年代我国现代文学转型时期对国外现代文学审美特征的认知。以《现代》对西班牙文学的转译为例。西班牙文学在“五四”运动初期便进入了我国译者的视野,但一直以来,“译介者并未自觉对西班牙文进行身份定位上的考虑,这些小说在这些书目选集中的出现仅仅是由于转译书籍的选目限制,被选编入书后也并未产生振聋发聩之影响”(申欣欣,张昭兵2009:41)。《西班牙的一小时》是《现代》杂志唯一一部连载长篇小说,由对西班牙小说有过多年翻译经验的戴望舒通过法文版转译。在这篇转译小说中,国内读者第一次体会到情节流动如散文般的小说叙述风格。从编者对转译活动的安排来看,杂志主编施蛰存曾在《编辑座谈》中透露过对于此次转译行为的“赞助”与安排。编者在推荐该作品之前还提及了想要在《现代》杂志上系统译介外国文学作品和现代作家的计划,并将另外一位西班牙作家阿耶拉(Ramón Pérez de Ayala)的作品与《西班牙一小时》同步推介。《现代》对阿耶拉的译介是独具慧眼的,选译阿耶拉不仅考虑到他未经介绍的新作家身份,更是考虑到他的作品与阿索林一样在文体改革、主题选择、叙述方式等方面所呈现的现代性审美特征。该篇小说是阿索林提倡文体改革的代表性成果。戴望舒通过转译,将作家首创的散文化小说结构,流动、简明而又轻快的笔记体小说第一时间呈现给了国内读者。阿索林对笔记体散文小说的开创也奠定了其在西班牙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除了别具特色的文体风格,《西班牙一小时》的主题选择也颇具现代性意味。小说集中描绘了西班牙社会中所存在的各类“异端”人物的典型,作家将视角触及到了边缘人群,勾画出一幅幅旧日西班牙的风物画和人物画。在《现代》杂志的译介之前,西班牙文学汉译的重点在于将西班牙在美西战争中的情况与我国当时的国情相对照,凸显西班牙作家群体创作中的写实倾向。阿索林只是以“弱小民族”作家的身份被译介到国内,国内读者并不知道其所独创的散文体小说,更不用说领略其富有现代性特征的创作技巧,欣赏作家对那些特殊群体的细致描绘。经过了《现代》的转译,国内读者对西班牙“九八一代”作家在文体改革、现代性题材选择及反传统的创作特色方面有了全新认识。《现代》对以阿索林、巴罗哈等为代表的“九八一代”作家的转译活动标志着当时对西班牙文学的译介超越了民族及思想上的诉求,转向于对作品的形式技巧所展示的文学审美现代性的关注。阿索林的文体改革成果和创作特征对后来的作家卞之琳、汪曾祺等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包括施蛰存、戴望舒、李青崖等在内的《现代》编译群对“九八一代”作家创作中具有审美现代性的异质因素的发现、挖掘及译介。
4.结语
作为外国文学汉译史上的特殊实践,《现代》的转译活动除了在文类、主题、选材等方面上扩大了国内读者对世界文学的多元认识,还进一步提升了转译规范,有意识地建构了以传递现代审美特征为重心的转译行为。相较于20世纪初《小说月报》等杂志对“弱小民族文学”集中频繁的译介,转译活动在《现代》所开展的翻译活动中所占比例虽不高,却是我国转译史上不可缺少的一个篇章。《现代》的编译群打破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以凸显民族矛盾与国民情怀为动机的转译格局,促进了转译规范的形成,培养了读者的现代审美意识,在我国读者认知世界文学审美特征的关键阶段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现代》以转译的方式将多国文学纳入了颇具现代性的审美空间。在多语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下,这些转译作品与其他译介模式一起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同等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