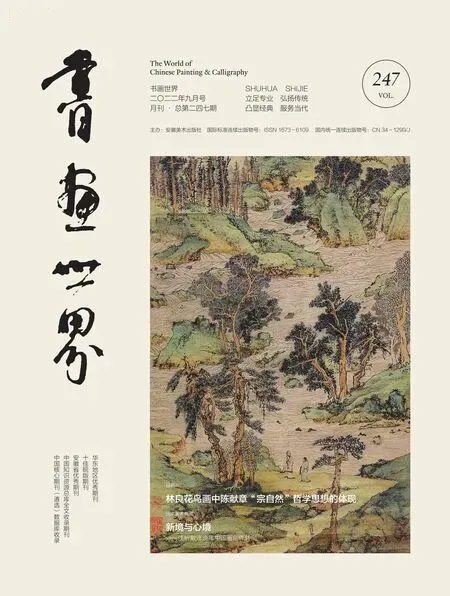新境与心境—浅析戴泽晚年中国画创作转向
文_董昕昕
中国美术馆馆员
2021年,戴泽个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展出了戴泽先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百余件。其中,有数件彩墨画作品颇引人注目,它们多为艺术家晚年所作,无论是在材料、形式,还是在表现手法方面,均不同于大家所熟悉的戴泽艺术特点。人们从中可感受到戴泽绘画在晚年时期的悄然变化。本文通过对中国美术馆馆藏的几件作品进行试读和赏析,以期让大家深入了解这位百岁老人的晚年绘画风格新貌及其形成的动因。
谈及艺术家戴泽,最令人熟知的是他创作的主题性绘画,以及围绕祖国河山、家人朋友等创作的油画和水彩画作。他坚持徐悲鸿的写实主义传统,秉持自然主义的创作法则,多年来深入生活,坚持写生,创作了千余件作品,其中的中国画创作虽数量可观,但未如油画及水彩为人所瞩目。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就开始以中国画颜料创作作品,当时被称为彩墨画。大众对他彩墨画的印象也停留在承继徐悲鸿中国画改良思想及“造型第一,笔墨第二”上,但细观其部分作品,我们仍可发现隐含其内的一条变化线索。这条线索指向了晚年戴泽彩墨创作新面貌之必然,也折射出他对自身艺术孜孜不倦的革新探索。
整体而言,戴泽晚年的水墨作品明显表现出了对线条笔墨趣味的追求,并有愈加平面化、抽象化的趋势。晚年的水墨作品画风更加轻盈洒脱,融现代艺术的构成意味和中国传统审美意蕴于一体。如其创作于1974年的《王家坪》(图1),在房屋的塑造和色彩运用方面仍遵循写实规律,但在树枝和山坡的塑造上,可以看出艺术家对墨线构筑形体轮廓的探索。其创作于2015年的《湖的印象》(图2),天空虽以大块墨团表现,但未有阴郁之感,反而将湖色衬托得更加剔透。画中满是洒脱率意的线条,色彩和笔墨自然交融,有笔墨淋漓之意,配以艺术家典型的抒情化气质,与他之前的作品相比已然具备了崭新面貌。

图1 戴泽 王家坪27.5cm×39.5cm1974 中国美术馆藏

图2 戴泽 湖的印象69cm×69cm2015 中国美术馆藏
戴泽晚年水墨之新貌,虽说有其身体状况、视力影响等客观原因,但结合他的人生际遇和创作经历,我们会发现这种笔墨意趣及作品中的抽象性、表现性,是随着艺术家数十年的深入思考和实践累积而成的。戴泽虽属于写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但其很早就开始了对现代主义绘画的探索,在他大放异彩的作品《和平签名》中,物体造型呈现出几何形体般的坚固感,反映出其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关注和体悟。1960年他曾撰写介绍印象派的文章。在作品《北大荒》中,我们也可看出他对西方现代艺术语言关注及探索的延续:在极小的画幅里,之字形的道路将观者引至远方。他以极简练、概括的笔触,营造出空间的纵深感,对近景物体大胆取舍,不做细细描摹,用笔松秀,但整体结构稳固,多重色调之间蕴含着微妙变化,从中可见艺术家对形式和构图的推敲精研。
早在重庆中央大学时期,戴泽已与中国画结缘,由于油画材料稀缺,国画便成了他日常的课外作业。他非常喜爱水墨画的作画方式,因国画材料的便携性,在之后的写生中他也会随身携带。戴泽居北平时期,在吴作人的家中,徐派艺术家组成了“十张纸斋晚画会”,戴泽是其中的活跃成员。画会成员们常以宣纸和速写为媒介,探索绘画语言,“可算作是徐派写生油画阵营推进中国画改良的沙龙”[1]。1972年,戴泽与李苦禅、李可染、吴作人等人一起在国务院宾馆绘画组时,工作之余他便向国画大师请教。可以说他一直保持着对中国传统绘画的创作热情,并一直在产出精彩的彩墨作品。在作品《工厂》中,艺术家以纸本水墨形式描绘了建设场景,在宏阔的视野下,管线交错的纵横线条和树林的浓淡生机相得益彰,画面细节丰富,富有节奏感和质感,反映了艺术家深厚的造型功力以及对墨线的娴熟运用。
除却技法层面的娴熟之外,戴泽绘画艺术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他对意境和精神性的不断探索。韦启美曾说“戴泽是富有情调的艺术家”。材料只是媒介,情调和意境才是戴泽艺术的核心。他的彩墨画融入了水彩的通透光感和油画的造型规律,色彩柔和明净;同时,常年的写生使得他的作品现场感极强,笔下万物生动鲜活,蕴含着艺术家对生活的热爱。戴泽晚期作品更多地融入了艺术家的情感,焕发了生机。
中国美术馆馆藏的《花卉》(图3)创作于1992年,可算是戴泽晚年笔墨趣味探索的典型代表之一。这件作品凸显了他对精神性和意蕴美的追求。淡雅的平涂背景有留白视觉效果;花叶俯仰舒展;叶面双钩设色;轮廓线笔意流畅,有微妙的曲线变化,具备书写意味;向背处有石绿到草绿的多重渲染过渡。画面中间一株嫩绿向右横出,增添了一抹灵动,整体画面通透而不失雅致。这件作品融汇了他的技巧、语言和文人学养,不仅具备中国传统美学特点,更将国画中的借物言志发挥得淋漓尽致。他曾说过:“我晚年喜欢画花,我认为花代表一种精神,人类在经受困苦的时候面临很多挫折,会显露出不同的人性,但不管怎样,花一直都会开放,努力展现它美的一面,所以每当我拿起画笔画花时都充满希望和热情,表达我对生活的认识和感受。”[2]花卉在戴泽笔下不仅是描绘对象,更具备了精神性的象征意义,也是温厚不争的艺术家本人写照,画外之意,余味悠长。

图3 戴泽 花卉69cm×35cm1992 中国美术馆藏
在近现代美术史的坐标中,大众多因戴泽对徐悲鸿写实主义传统的传承和坚守,以及数十年在艺术教育事业上的辛勤耕耘,倾向于定位其为沉默的耕耘者。然而,在漫长的创作生涯中,他从未曾停止过探索,作品材料和形式的变化是他数十年的思索和积累的必然结果。比起教育者、学院艺术家等多重身份,从其晚年作品中我们更多感受到的是他本人性情的流露。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视为从集体化到个人化的一个显性表达。晚年的戴泽凭心性挥笔,自由驰骋,用笔更加轻松概括。依旧是真实情感的倾注,依旧是画他所见,只不过此时所见的是他几十年积累于胸中的、更个人化的氤氲山水和润泽万物。这种自然情韵与心灵抒写的深层交融,带给我们精彩画作的同时,也给予我们新的意义和感动。
——中国美术馆、南京博物院藏明清肖像画展
——中国美术馆藏书画界全国政协委员美术作品广西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