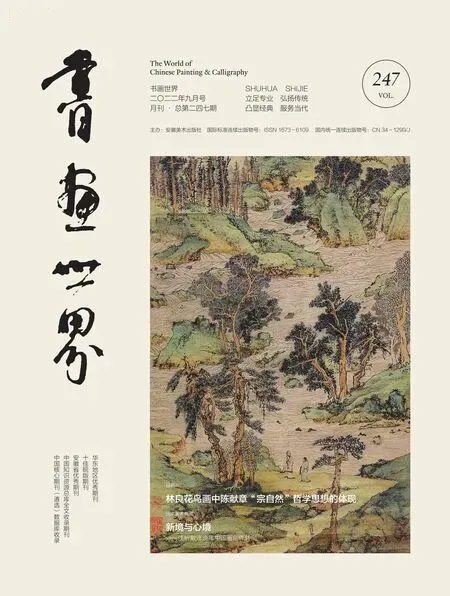因陀罗“禅机画”考
文_戴科峰
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
内容提要:本文以禅宗画东渡为切入点,通过中、日一手文献和现存画作信息爬梳因陀罗其人与交友圈,并从风格和图像学的角度探究因陀罗“禅机画”的形式和内涵,讨论题赞的终极动机—禅悟。
一、因陀罗“禅机画”的东渡
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中提出“且如世之相押字之术,谓之心印,本自心源,想成形迹,迹与心合,是之谓印”[1],认为书画是心灵的印记。禅宗讲求衣钵相传,讲究由禅师通过艺术、对话等反常的方式传授心法达到开悟,这样的传道过程亦称为“心印”,而禅师的墨迹也是其精神境界的延展。日本中世室町时期(1338—1573),幕府派出的遣唐僧是此期中国文化在日本最关键的传播者,也是中日禅宗思想、绘画交流最主要的中介。他们跟从唐朝名禅师参禅,返回日本时常随身携带业师的手迹或题赞的禅宗画。这些禅宗作品是禅宗精神的具象化,是师承的证据,也是两种“心印”的殊途同归。
室町幕府将军与僧侣的密切联系,以及对禅宗的喜爱,给中国禅宗作品东渡搭建了桥梁。室町至江户时代(1603—1868),往来中日两国的“唐船”带去大量中国古物和书籍。室町足利幕府对“唐物”①的追逐,可以从《君台观左右帐记》(以下简称《帐记》)中一探究竟。虽然已经有学者如近藤秀实、矢野环论证了《帐记》对《图绘宝鉴》编目的借鉴,但是从此书对中国艺术家和作品的评定中,我们会发现日本区别于我国鉴藏体系的取向—一些在中国无名的画师在日本中世时期的收藏界享有无上殊荣,而同期中国有名的米芾、赵孟等人却评价不高。日本特有的审美趣味和收藏取向实际上填补了我国收藏体系的不足,对梁楷、牧谿等禅宗画的研究也是自东洋开始,进而引发东亚文化圈乃至全世界的讨论热潮。
因陀罗在国内不以画闻名,鲜有作品流传,却有不少“禅机画”在上述浪潮中流传至日本。今有十余种留存于日本,并在日本收藏界处于殿堂级地位。日本根津美术馆藏《布袋图》、日本静嘉堂藏《智常禅师图》、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寒山拾得图》、日本福冈石桥美术馆藏《丹霞烧佛图》于1953年被认定为日本国宝。日本艺术界至今仍将因陀罗与梁楷并称,将类似风格定名为“梁楷因陀罗画风”,重要性可见一斑。日本学界的反馈近年也使国内部分学者将目光聚焦到因陀罗作品上,但研究还局限于《寒山拾得图》,其他内容涉及较少。
二、因陀罗其人与交游圈推论
记载中国绘画在日本中世流藏情况的重要文献《帐记》相传为负责足利幕府装饰、艺术品管理事务的同朋众(或称“阿弥”)所作,原本已不存,今存最早本为能阿弥《群书类从》所收。《帐记》为足利义政命著名画人能阿弥为幕府所藏古物书画所做的编目,一同编成的还有《御物御画目录》。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帐记》是日本室町幕府著史者的群体书写。《帐记》按时代对中国画家作“上、中、下”三品评定,井手诚之辅在《〈君台观左右帐记〉中的佛画师》一文中提出此目的体系是能阿弥参照《图绘宝鉴》所作[2]。《帐记》对牧谿的评价相当之高,为“上上”最高品,作为对照,赵孟仅得“下中”品。日本对牧谿的重视从占有其绝大部分存世画作收藏可见一斑,其最早的宋元画录《佛日庵公物目录》便载有牧谿作品[3],属于最早到达日本的“唐物”。当然,《帐记》的舛错也不能忽视,日本后来学者著作如《等伯画说》也对《帐记》持保留意见,但是《帐记》如今仍是我们讨论因陀罗除画作外少有的第一手材料。《帐记》载“因陀罗,天竺寺,梵僧,人物道释”,即因陀罗是天竺寺梵僧,擅长道释人物画。“梵僧”即印度僧人,《帐记》认为因陀罗是印度在华传道的僧人,日本《等伯画说》则有因陀罗是天竺赴华的游僧一说。而宗典由因陀罗《丰干寒山拾得》(日本长尾美术馆藏)的款识“王舍城中壬梵音笔”,结合《图画见闻志》载古魏国临清县城东北有王舍城古刹一则,认为因陀罗极可能是山东临清人[4]。同时宗典以元代著名禅僧楚石梵琦在元代至治年间(1321—1323)于燕都书《大藏经》时与因陀罗结识,二者法号皆为元顺帝妥欢贴睦尔(1320—1370)所赐。日本学者川上泾则认为楚石梵琦是元代至正十七年(1357)在浙江杭州永祚寺(又作中天竺)隐退后与因陀罗来往[5],然今学界公认禅师楚石梵琦受戒及隐退之处永祚寺位于浙江省海盐县,所以川上泾的推断存疑。要在浩渺的故纸堆里翻阅出一位洒脱的僧人身世铁证着实困难,各方学者都只是在一些材料的基点上作出推测,本文列出多方观点以期对因陀罗的身份、气质有初步认知。
除了《帐记》记录,因陀罗的身份只能从现存真迹上寻找。今学界对其认识主要来自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纸本水墨《寒山拾得图》(图1)。此图原为日本艺州浅野家收藏的四幅《禅机图断简》之一,图轴款署“佛慧净辨圆通法宝大师壬梵因,宣授汴梁上方祐国大光教禅寺住持”,钤有“释氏陀罗醉余玄墨”印,同时上面有元代著名禅僧楚石梵琦的题赞:“寒山拾得两头陀,或赋新诗或唱歌;试问丰干何处去,无言无语笑呵呵。”楚石梵琦与因陀罗的来往,在《楚石梵琦禅师语录》卷十四有载:“因陀罗为闻上人作《十六祖图》和《诸圣图》,皆请楚石为之赞。”如上材料或可佐证因陀罗法名壬梵因,活动在元朝,是汴梁大光教禅寺住持,同时也是一位漠视戒律的禅学大师。
张珩在《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识因陀罗楚石梵琦题赞《寒山拾得图》和慈觉题赞《拾得图轴》均有朱文“三昧正受”印,吴韧之考此印7次出现在因陀罗现存作品上,并且钤在今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赵孟《趵突泉诗》上[6]。因同钤有此印的《四祖传法图》曾被元代日本高僧关山慧玄收藏,关山与访华高僧一山一宁来往甚密,中峰明本禅师(1263—1323)又是一山一宁和赵孟的业师。或可推断因陀罗亦处于赵孟、一山一宁、中峰明本这一交游圈内。
三、因陀罗“禅机画”母题与风格分析
美国艺术史家李雪曼(Sherman E.Lee)在《艺术中的禅宗:禅宗中的艺术》曾提出大多数禅宗背景画呈现出“发于天然”和“简略”两个特征,这些艺术作品常常使用无拘束的简约笔法。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师清水义明在苏黎世“中、日、东亚艺术中的禅宗”研讨会上评价禅宗作品往往富有幽默感,画面表现直来直去,甚至内容有大不敬的意味[7]76,这与中国传统佛教、儒家等影响下的东亚艺术似乎大相径庭。这些禅宗画脱胎于中国的水墨传统,却不限于任何一种流派或艺术风格,他们为正统艺术带来开创性的新风。当然,我们并不能简单地用风格去界定禅宗画,谢恺[7]99-113和芜林香[8]、清水义明都指出区分禅宗画与世俗绘画、正统佛教画的重要标准是禅宗画使用的特殊母题,艺术家在教义背景下作出的题材选择是禅宗画形成的关键。这亦是目前学界达成的公开认知。这种观点与英国艺术史家约翰·史蒂文斯的观点相契合,他认为大部分流传日本的禅宗艺术作品题材是禅宗公案里的禅师语录和禅机故事,即“禅机画”[9]。
因陀罗现存作品几乎都是风格统一的“禅机画”,川上泾较为准确地将其划分为三个主题:日本岛山纪念馆藏《李渤参智常图》、日本静嘉堂藏《智常禅师图》中禅僧与俗人的问答称“禅会画”;《丹霞烧佛图》这样禅僧间的问答称“祖会画”;此外不属于正统祖师序列的《布袋图》《寒山拾得图》禅机图则属于“散圣画”[10]。《宋高僧传》以“禅宗有著述者,以其发言先觉,排普化为散圣科目中,言非员也”[11]将有先觉性发言的、通过非正统法脉悟道的禅僧收入“散圣”一列。宋真宗年间(968—1022)《景德传灯录》统计了宋以前的十位散圣,其中便有明州布袋和尚、天台寒山、拾得、丰干几位禅师,他们的公案夹杂着民间叙事,易为俗世接受而传布甚广。因陀罗的大部分“禅机图”是唐代的高僧五祖、雪峰、船子等众公案,通过画面传达的故事和禅僧的题赞,观众能清晰判断画作母题。
日本讲谈社1975年出版的《水墨美术大系》第4卷将因陀罗与在日享有殊荣的梁楷编为一册,实际上有很多人将因陀罗视为梁楷“减笔”风格的后继。梁楷虽是俗世中人,一时为南宋嘉泰年间(1201—1204)画院待诏,然而素喜与禅僧交游,已然是参禅悟道的居士,其《六祖斫竹图》与《布袋图》是禅宗画经典。可贵的是梁楷开简约笔墨捕捉人物形态的先河,极大影响了后世写意人物流派发展。以梁楷《寒山拾得图》(图2)和因陀罗《寒山拾得图》(图3)为例,二者都是以寒山、拾得作禅宗画题材。如今常见的此二僧狂放形象起源于被余嘉锡辨伪的《寒山子诗集》“闾丘胤序”[12],序中描写寒山、拾得(以及部分故事里的丰干)是活跃在浙江天台国清寺亦仙亦癫的僧人,三人常有机锋。二者画风确有许多相似点:都是用显拙气的减笔配合萧疏淡墨绘成,仅着数笔,禅师情状便已然呈现;寒山、拾得二位禅师的面部表情,都使用符号化的短线条刻画出区别于正统审美的粗鼻、龅牙、咧嘴形象,将观众的关注点集中到神态之间,在诙谐开朗的氛围之中直观感受禅师们豁达的人生态度;二位禅师的发型都以浅色表现蓬松的质感,与传说的“蓬头”形象呼应;人物衣领、袖口、腰带、发冠处都用重笔点缀,画面风格因此鲜明跳脱。二者画风同属一系又各具特点:梁楷使用了泼墨和破笔,刻画了寒山、拾得二僧散乱的头发和破烂衣襟;因陀罗作品中人物外形更为明确,画师用行云流水般的线条准确勾勒出因势造就的衣袍形状。他的作品常以秃笔渴墨带出古树、山涧、怪石、巨松,人物被置于恰当的环境描绘之下。二僧的头发处理则使用了吹墨,襟带使用了焦墨,画风苍劲而有古趣,在梁楷“减笔”画风上发展出拙朴的特质。值得注意的是,面对同样的母题,梁楷选择了二位禅僧更年迈的形象进行表现:他们头发更为稀疏,姿态和动作走向更加缓和。因陀罗表现的禅师形象更似青壮年,头发相对来说较青黑、浓密,禅师姿态更从容坚定,画作极具生命力。这样的表现手法出现在他每一幅禅机画中,这种生命力的选择亦是因陀罗的独到之处。

图3 因陀罗 寒山拾得图(局部)
四、题赞的终极动机—禅悟
楚石梵琦的题赞实为因陀罗的禅机画增色不少,二者可谓相互成就。楚石梵琦是元代释林著名的诗僧,亦是声名远播的书法家。自宋朝起,受文人士大夫影响,禅僧对偈颂和语录的追逐成为时风,在书画上特别是禅宗画上,题赞也是此风尚不可或缺的一环。题赞的位置布局和书风不仅影响禅宗画的构图美感,更是一起表达了禅机画想要传达的终极精神(通常是佛教教义和悟道灵光)。这些宋元时期流传至日本的禅宗画及其独有的画赞,在日本中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说山水、人物画上也常出现题诗,但是从岛田修二郎和入矢义高对日本室町时期诗画轴的统计可以看出日本对画赞的效仿依然集中在禅宗和释道题材上[13]。禅宗出世、隐逸等思想在中国和日本盛行是多重因素影响的结果,在此不做深究。
目前可查楚石梵琦共为因陀罗题了六首画赞,包括上文分析的《寒山拾得图》《布袋图》《丹霞烧佛图》《智常禅师图》《李渤参智常图》《闽王参雪峰图》,宗典在他的论文中一一列出,此不累述。除楚石梵琦外,为因陀罗禅机画题赞的另有三人,法膺题《五祖再来图》、普门题《维摩图》,另一人是学界尚未讨论的《寒山拾得图挂轴》中的题赞者慈觉。
从慈觉题挂轴可一探因陀罗禅机画及题赞行为的动机。此纸本《寒山拾得图挂轴》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形态与以上诸图有别。今截取慈觉的题赞(图4、图5)如下,题赞内容分别是“虚卷一张纸,藏尽人间事。对面似忘机,说出皆妙义。石桥飞瀑溅寒空,峨眉显出真嘉致。华顶沙门慈觉拜赞”和“拈起芭蕉叶,举笔欲题诗。离言摧峭峻,得意削玄微。五峰云净耸清奇,北海风和月满时。石桥刍草慈觉题”。题赞者署名“华顶沙门慈觉”,其生平不可知,或如其署名是华顶僧人,而华顶峰在浙江天台境内,是传说寒山曾经活动的地方。这几位题赞者都是禅僧,赞皆大体依因陀罗描绘的公案阐发。慈觉此赞却与宋代仿寒山诗的热潮密不可分,目前可见寒山诗有300余首。张伯伟先生《寒山诗与禅宗》一文探讨了寒山诗中的禅理,并论述后世禅师或渴望顿悟的文人对寒山诗的运用,他们将仿作寒山诗作为参禅的途径。寒山诗或仿寒山诗往往使用自然环境中的物象来表达开悟的愉悦,此赞中的“寒空”“五峰”“桥”“草”亦是寒山诗中出现频率极高的词,慈觉更以“刍草”作自谦。慈觉的赞忠实阐释了画作,此对挂轴不似因陀罗其他作品有充分的环境意象描绘,慈觉的赞则弥补了这一缺失。寒山、拾得“虚卷一张纸”“拈起芭蕉叶”都是明显的画面内容,因陀罗以此响应二诗僧在山林间题诗的典故,这也是禅机画的母题。“石桥飞瀑溅寒空”“五峰云净耸清奇”是慈觉读出因陀罗笔迹外的内容,画师的构想里有寒山诗中常出现的意象,慈觉题赞最终完成这对禅机画的终极动机,是寒山诗意,也是禅悟。元代仿寒山诗风气仍盛,楚石梵琦便有《和三圣诗自序》,其间有值得注意的虞集《寄谦上人》诗云:“不见谦公二十年,石桥依旧驾晴川。定应和尽寒山集,倘许人间一句传。”与慈觉使用了同一个地点石桥。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与这对挂轴(图6、图7)特别相似的传为因陀罗作《寒山图》中法元的题赞“吟得劝世诗,玄妙文字拙。寒山卷却纸,写向芭蕉叶”与慈觉题赞中“虚卷一张纸”“拈起芭蕉叶”有异曲同工之妙。此画形制与日本东京博物馆藏挂轴极为相似,然而藏地信息不明,不妨将它视为后世仿寒山诗和因陀罗禅机画之作。

图4 因陀罗 《寒山拾得图挂轴》题赞之一

图5 因陀罗 《寒山拾得图挂轴》题赞之二

图6 因陀罗 寒山拾得图挂轴之一75.8cm×31.5cm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图7 因陀罗 寒山拾得图挂轴之二75.8cm×31.5cm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结语
除了禅宗画,因陀罗对研究宋元以后写意人物画发展进程也有重要影响。而因陀罗等人的作品因日本学界的反馈在20世纪末才得到国人重视,国内学界对其画面和款识的解读依然不尽完善。
注释
①日本泛指来自中国文化影响地域的舶来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