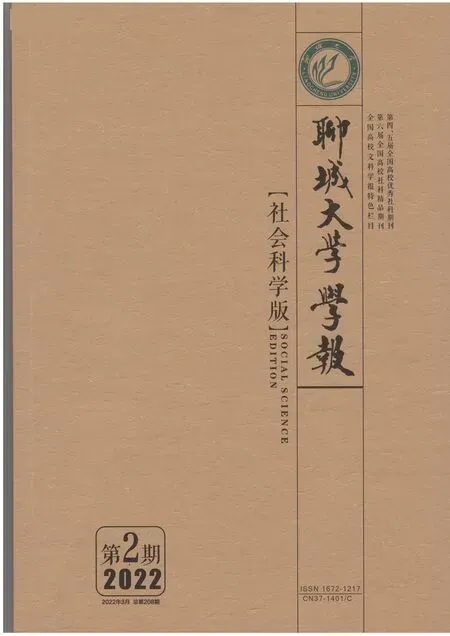清代民事纠纷解决机制探析
程 方
(济南大学 政法学院,山东 济南 250022)
受儒家“无讼”文化观念的影响,传统中国通常被认为是普遍厌讼的社会,百姓非不得已,是不肯轻启讼端的。①马作武:《古代息讼之术探讨》,《武汉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即便最终对簿公堂,州县长官也通常不会依据律例判决,而是进行“教谕式的调解”,即尽量运用情感、道德教化劝谕当事人自省、忍让,从而达到息讼的目的。②滋贺秀三:《清代诉讼制度之民事法源的概括性考察情、理、法》,载滋贺秀三等:《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19-51页。然而拨开儒家的道德面纱,我们看到的似乎是历史的另一幅画面,伴随着清代人口的爆炸性增长、生存危机的加剧、以及“义利”观念的变化,“万家诉讼”的社会现实使得官府越来越陷入穷于应付的尴尬局面。官方的无讼理想和民间的健讼诉求发生着激烈的冲突,官方始终致力于把百姓纳入“邻里和睦”、“长幼相爱”的道德伦理体系之中,而百姓则更多的借助“冤抑”、“伸冤”的话语表达实现官府最终受理案件的目的。
一、诉讼前的息讼举措
中国的“无讼”观念,至晚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儒家的创始者孔子云:“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③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26页。朱熹对此解释说:“圣人不以听讼为能,而以无讼为贵。”④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30页。如何达到这一价目标?统治者无不把道德教化视为圭臬,动之以情,晓之以利害,劝民息讼。
(一)无讼的宣传
延至清代,无讼作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价值追求已深植人心。清代统治者将教化视为比刑罚更重要、更有效的治国之术。清圣祖在颁布“上谕十六条”时详细阐述了自己对于教化和刑罚关系的认识:“朕惟至治之世,不专以法令为务,而以教化为先。盖法令禁于一时,而教化维于可久。……若徒恃法令而教化不先,是舍本而务末也。”①《清圣祖实录》卷34,康熙九年十月癸巳。在“上谕十六条”中,第三条“和乡党以息争讼”、第十二条“息争讼以全良善”等都是专门教育百姓止讼、息讼的。清世宗即位后也一再宣称自己“缵承大统,临御兆人,以圣祖之心为心,以圣祖之政为政”,“拳拳以敦教化、励风俗为务”,②《清世宗实录》卷16,雍正二年二月丙午。专门将“上谕十六条”各条目,逐一“寻绎其义,推衍其文”,纂成《圣谕广训》一书,“颁发直省督抚学臣,转行该地方文武各官暨教职衙门,晓谕军民生童人等,通行讲读”③《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397,光绪二十五年御制本。。通过这种方式,力图让息讼的思想深入民心。
教化,既是清代皇帝的重要治国理念,也始终贯彻于官箴中。为官者以“厚人伦、美教化”相标榜,以清圣祖倡导的“上谕十六条”为核心,致力于构建“父与父言慈,子与子言孝,兄与兄言友,弟与弟言恭”亲睦友爱的宗族关系,以及农商相资、工贾相让的乡党关系。在教化过程中,官府力图在百姓心中形成“好人不告状”的心理认同,将诉讼视为违背传统伦理道德的罪恶行为,从而使百姓产生诉讼的罪恶感,裕谦指出:“人既好讼,则居心刻薄,非仁也;事理失宜,非义也;挟怨忿争,非礼也;倾资破产,非智也;欺诈百出,非信也。”④裕谦:《勉益斋偶存稿·戒讼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2页。概而言之,统治者力图通过积极的教化措施,“尚德缓刑,化民成俗”,达到“民与民和”“非礼之讼,日为衰息”的积极效果。
不过,现实中人性不一,并非人人皆可德化,单一的道德劝诫并不足动人视听,因此,官员在教化的同时,也较为注意从百姓切身利害的角度入手,进行劝诫。汪辉祖指出:
谚云:“衙门六扇开,有理无钱莫进来”。非谓官之必贪,吏之必墨也。一词准理,差役到家,则有馈赠之资;探信入城,则有舟车之费。及示审有期,而讼师词证,以及关切之亲朋,相率而前,无不取给于具呈之人;或审期更换,则费将重出,其他差房陋规,名目不一。谚云:“在山靠山,在水靠水”。有官法之所不能禁者,索许之赃,又无论已。⑤汪辉祖:《佐治药言·省事》,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页。
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差役等向诉讼双方索取的讼费项目有戳记费、挂号费、传呈费、取保费、纸笔费、出结费、和息费等30余项,百姓负担是比较大的。乡间也广为流传着“赢得猫儿输了牛”“赢了官司输了钱”等说法。官府正是通过对诉讼费用的夸大描述,使诉讼者知难而退,不再诉讼。
(二)对诉讼程序的限制
言者谆谆,而听者藐藐,尽管官方刻意于宣传父慈子孝、夫和妻柔、邻里和睦的无讼社会,以及以高额诉讼费用相恫吓,然而现实却是“自有生民以来,莫不有讼。讼也者,事势之所必趋,人情之所断不能免者也”⑥沈家本:《寄簃文存》卷六《裁判访问录》,清宣统元年铅印本。。“无讼”的不可能,致使清代统治者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在受理程序上做出诸多限制性的规定,一方面旨在维护司法的严肃性,另一方面也是基于降低诉讼率的考虑。
1.状纸的要求。状纸由各地州县衙门印制并发售,格式固定,字数亦严加限制,以防“枝词蔓语,反滋缠绕”。黄六鸿制定的办法是:状纸“格眼三行,以一百四十四字为率,凡告户籍者,必以族长坟产为定;告婚姻者,必以媒妁聘定为凭;告田土者,必以契卷地邻为据……此其定式也。式定则不敢脱毋以全虚,字限则不得浮词以饰听矣!若状式有违,不与准理”。⑦黄六鸿:《福惠全书》卷十一,扬州:广陵书社,2018年,第184页。同时,状纸必须由官代书书写,“如无代书姓名,即严行查究”⑧《大清律例》卷30《刑律·诉讼·教唆词讼》,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526页。。
2.放告日的限制。黄六鸿在《福惠全书》一书中记载:“凡告期必以三六九日为定。”①黄六鸿:《福惠全书》卷十一,扬州:广陵书社,2018年,第188页。《庸吏庸言》一书中记载则是:“寻常案件,定于三八放告日当堂收呈。”②刘衡:《庸吏庸言》,《官箴书集成》第6册,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第197页。二书说辞互异。瞿同祖指出,这种差异分别适用于18世纪之前和19世纪之后,在17、18世纪每月有9天专门受理民事诉诉,19世纪之后则减少为6天。③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183页。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并不是每个月都有放告日,农忙时期是不受理的,《大清律例》规定:“每年自四月初一至七月三十日,时正农忙,……其一应户婚、田土等细事,一概不准受理。自八月初一日以后,方许听断。若农忙期内受理细事者,该督抚指名题参。④《大清律例》卷30《刑律·诉讼·告状不受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514页。日本学者夫马进依此推算,19世纪之后的清代每年的放告日为48天。⑤夫马进:《明清时代的讼师与诉讼制度》,载滋贺秀三等:《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392-395页。事实上,除了“农忙止讼”的4个月之外,清代还有一些停审日,“每年正月、六月、十月及元旦令节七日,上元令节三日,端午、中秋、重阳各一日,万寿圣节七日,各坛庙祭享斋戒以及忌辰素服等日,并封印日期,四月初八日,每月初一、初二日,皆不理刑名”⑥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刑法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4211页。。把这些停审日也排除掉,每年的放告日一般不会超过40天。放告日的规定,既是为了达到限制起诉的目的,另外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息讼、缓减当事人双方矛盾的目的,正如黄六鸿所解释的:“闾阎雀角,起于一时之忿争,……若得亲友解劝,延至告期,其人怒气已平;杯酒壶茗,便可两为排释,岂非为民父母者所深愿乎?”⑦黄六鸿:《福惠全书》卷十一,扬州:广陵书社,2018年,第188页。
3.诉讼的驳回。对案件真实性的判断,是决定案件是否受理的主要因素。状词上呈之后,州县官便会根据状词内容盘问原告,凡是答问含糊及举动可疑者,呈词将“当堂掷还”,不予受理。除了对案件真实性的判断外,决定呈词是否批驳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基于对对诉讼程序是否合法的判断。台湾学者那思陆通过梳理《大清律例》的相关条款,将地方官不受理案件的类型归纳为6种情形,分别为:以赦前事呈控者、呈词内牵连无辜者、事不干己而呈控者、无故不行亲赍者、被囚禁人呈控者、老幼笃疾妇人呈控。⑧那思陆:《清代州县衙门审判制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7页。付春杨在那思陆归纳的6种情形之外,又增加了状纸不符合形式要求、缺乏证据、一事不再理3种情形。⑨付春杨:《权利之救济 清代民事诉讼程序探微》,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1-52页。实际上,除上述9种情形之外,诉讼管辖也是州县官是否受理案件的一个重要原则,一般情况下遵循原告就被告的地域管辖原则。《大清律例》规定:“户婚、田土、钱债、斗殴、赌博等细事,即于事犯地方告理,不得于原告所住之州县呈告。”⑩《大清律例》卷30《刑律·诉讼·越诉》,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507页。此外,对于不在州县呈诉,径赴上司衙门呈诉,或州县尚未审结即赴上司衙门呈诉的越诉行为,以及事涉久远、超过诉讼期限,衙门也是拒绝受理的。
二、诉讼中的息讼、止讼策略
尽管官方采取了诸多的手段来预防诉讼的发生,现实中健讼的情况似乎仍较普遍。一份根据来自浙江、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山东7省的150余部地方志所做的研究显示,其中写明当地“健讼”的地方志有70多部,而在江南地区有诉讼风气记载的70多部地方志中,明确记载“健讼”的有57处之多。[11]侯欣一:《清代江南地区民间的健讼问题——以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法学研究》2006年第4期。面对“万家诉讼”的社会现实,如何在诉讼阶段有效的息讼、止讼,清代的官员们同样采取了很多措施。
(一)对讼师的态度和措施
官府无讼、息讼、贱讼的情感偏好,使得乡民中一般的民事细故很难进入法官的视野。同时,乡民对于诉讼程序也较为陌生,“每每不能自伸其词说”①转引自夫马进:《讼师秘本〈珥笔肯綮〉所见的讼师实像》,邱澎生、陈熙远编:《明清法律运作中的权力与文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0页,第34页。,因此不得不“求之能者”,即具有诉讼经验的讼师。讼师们也慨然以“代哑言,扶瞎步”“济弱扶倾,褒善贬恶,均利除害”相标榜。当讼师介入到诉讼的场域之中,一方面他们成为涉讼乡民的“智囊”和有力奥援,另一方面也成为官府不得不应对的头疼人物。在诉讼的过程中,官员与其说是与当事人之间进行互动和博弈,更多的则是与站在当事人后面讼师的斗智斗勇。
基于受理的目的,讼师在帮助原告书写的状词中多采取示人以弱、博取地方官哀矜之情的诉讼策略,从而达到地方官“着即究问”的目的。②寺田浩明:《权利与冤抑 寺田浩明中国法史论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33页。“或遇一时难准之状,不得不架捏者,亦要招诬无大罪方可。又必观者信之”③转引自夫马进:《讼师秘本〈珥笔肯綮〉所见的讼师实像》,邱澎生、陈熙远编:《明清法律运作中的权力与文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0页,第34页。。然而,这样的诉讼策略,在官方的话语体系中,则是颠倒黑白、变乱曲直、诈财取利。讼师“大率以假作真,以轻为重,以无为有”④王又槐:《办案要略·论批呈词》,北京:群众出版社,1987年,第70页。,“以搬弄是非为得计,以颠倒黑白而迷人”,“迨呈词既递,鱼肉万端,甚至家已全倾,案犹未结,且有两造俱不愿终讼,彼此求罢,而讼师以欲壑未盈,不肯罢手者”⑤刘衡:《庸吏庸言》,官箴书集成编纂委员会编:《官箴书集成》第6册,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第197页。。因此,汪辉祖云:“唆讼者最讼师,害民者最地棍。”⑥汪辉祖:《学治臆说》,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2页。《旴江治牍》的作者也认为:“夫民之患,莫深于水火,而讼师尤烈;莫惨于盗贼,而讼师尤甚。”这些言论基本上代表了官方对于讼师的普遍态度。于是,“严惩讼棍,以清刁告之源”成为地方官打击讼师,实现息讼目的的重要手段。
1.直接向当事人诘问主使讼师信息。穆翰记载:“讼师吓以利害之言,骗以决胜之说。……迨官研讯之下,多属子虚,追诘主唆代写呈词之人,尚执迷不悟,非捏称过路之人、不知姓名,即云算命先生、业已他往。”⑦转引自邱澎生:《当法律遇上经济 明清中国的商业法律》,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52页。可见,官府试图通过此种办法惩治讼师的努力往往难以成功。从文中“执迷不悟”一语不难看出,民众并不认同官府恶讼师的说法,对地方官的诘问采取蒙混应付的态度,官府较难从当事人那里得到情报和支持,不知姓名的算命先生,业已他往的算命先生,官府自是无从查找。
2.明察暗访,严惩讼师。如上所言,试图通过诘问当事人揪出讼师的努力往往是无效的。地方官更多的是通过衙役、乡绅,抑或亲自微服私访,获取讼师的情报,进而抓捕、惩治。大清律对此类人员处罚较重,轻者与犯人同罪,重者发极边充军。即便如此,仍不乏以身试法,屡教不改者。如何惩诫讼师,惩一警百,汪辉祖的办法极简单、独特而有效:“向在宁远,邑素健讼,上官命余严办。余廉得数名,时时留意;两月后,有更名具辞者,当堂锁系。一面检其讼案,分别示审;一面系之堂柱,令观理事。隔一日,审其所讼一事,则薄予杖惩,系柱如故。不过半月,惫不可支。”⑧汪辉祖:《学治臆说》,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2页。刘衡惩治讼师的手段与汪辉祖有类似之处,拿获讼师后,其稍轻者“仿照萧山汪龙庄先生《学治臆说》所载,将该犯锁置堂柱,令其鹄立,看本官审断他案,问日责决数板,旬月之间未有不惫甚告饶者,虽极繁难之缺,但须办一二案,惩两三人,则若辈闻风丧胆,外来者裹足,本籍者革面矣”。⑨刘衡:《庸吏庸言》,官箴书集成编纂委员会编:《官箴书集成》第6册,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第197页。情重者则是“照例详办”,视情节轻重,处以徒、流、充军等不同的刑罚。
3.通过对讼师秘本的销毁以减少讼学的传播,杜绝讼师的泛滥。在政府看来,讼师“得售其奸计,究其实,则此等构讼之书,阶之厉也严讼师而禁及此等秘本,亦拔本塞源之意也”⑩薛允升:《读例存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703页。。为此,乾隆二十九年特定一例,规定“坊肆所刊讼师秘本,如《警天雷》、《相角》、《法家新书》、《刑台秦镜》等一切构讼之书,尽行查禁销毁,不许售卖,有仍行撰造刻印者,照淫词小说例,杖一百,流三千里;将旧书复行印刻及贩卖者,杖百,徒三年;买者,杖一百;藏匿旧版不行销毁,减印刻一等治罪;藏匿其书,照违制律治罪;其该管失察各官分别次数,交部议处”①《大清律例增修汇纂大成》卷三十,清光绪二十九年排印本。。
(二)对当事人进行调解
受理的案件,州县官在“以调解为主,追求和合”的原则下,多采取灵活多样的调解策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维护和睦的家庭关系、宗族关系、邻里关系。具体的措施包括:
1.官批民调。对于百姓诉讼的案件,如果地方官认为情节轻微,不值得传讯,或事关亲族乡谊的一般纠纷,往往申令宗族、乡保等介入调解。《汝东判语》中多起词判均属此类型,如《刘金元呈词判》一案中,因族人争产诉讼,县令董沛批令“公正戚族查明妥处,以全亲亲之谊”②董沛:《汝东判语》卷一《刘金元呈词判》,清光绪正谊堂全集本。。《天台治略》所载23件批词中有9件是法官基于维护和睦的亲缘关系的目的,批令亲族调处。对于宗族、乡保等成功调处的处理意见,地方官一般均予以认可。因为,对于“鼠牙雀角”的民事纠纷,官府的着眼点并不在于纠纷自身的是非对错,让当事人双方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才是他们的最终目标。汪辉祖认为:“词讼之应审者,什无四五。其里邻口角,骨肉参商,细故不过一时竞气,冒昧启讼”,“果能审理,平情明切,譬晓其人,类能悔悟,皆可随时消释,间有准理,后亲邻调处,吁请息销者,两造既归辑睦,官府当予矜全,可息便息”③汪辉祖:《佐治药言·省事》,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页。。
2.地方官亲自调解。这一传统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西周时期的“甘棠之颂”,既是对召公在甘棠树下调纷解争惠政的赞美。唐代“兄弟饮乳”的故事更是为官方所津津乐道。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中,人们生于斯,长于斯,在这样的一个熟人社会中,人情既是社会交往的基础,也是维系社会关系的重要纽带,“动之以情”便成为州县官调解民事纠纷的主要途径。刚毅主张“审系同村相控者,则以‘和乡党以息争讼’教之;审系同姓相控者,则以‘笃宗族以昭雍睦’教之”④刚毅:《牧令须知》,官箴书集成编纂委员会编:《官箴书集成》第9册,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第221页。。“审系同村相控者,则以‘和乡党以息争讼’教之”,注重的是乡邻之情,其因在于“乡党中生齿日繁,比闾相接,睚眦小失,狎昵微嫌,一或不诫,凌竞以起,递至屈辱公庭,委身法吏。负者自觉无颜,胜者人皆侧目。以里巷之近而举动相猜,报复相寻,何以为安生业、长子孙之计哉”?⑤冯尔康主编:《清代宗族史料选辑》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6页。“审系同姓相控者,则以‘笃宗族以昭雍睦’教之”,则包括了父母子女之情、手足手足之情以及更广泛的宗族之情。此类案件,在地方官看来似乎更容易通过血缘亲情打动当事人。邵大业任黄陂知县时,“有兄弟争产讼,颂白,貌相类。令以镜镜面,问曰:‘类乎?’曰:‘类。’则进与为家人语曰:‘吾新丧弟,独不得如尔两人白首相保也。’感动罢去”⑥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循吏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023页。。这种“动之以情”的调解方式,在清代的官方调解中极为普遍,它既是官方所追求的司法价值的体现,同时从司法效益的角度来看,其效果也远远好于单纯的司法审判。
(三)以讼止讼
官方的息讼理想与百姓健讼的社会现实有着巨大的背离,面对民间诉讼的日益攀升,一些开明的官员也意识到防民之讼犹如防川的危险,有意的将息讼之道寓以诉讼之中。田文镜认为:“听讼者,所以行法令而施劝惩者也。明是非,剖曲直,锄豪强,安良懦,使善者从风而向化,恶者革而洗心,则由听讼以驯致无讼,法令行而德化亦与之俱行矣。”⑦田文镜、李卫:《州县事宜·听断》,官箴书集成编纂委员会编:《官箴书集成》第3册,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第672-673页。袁枚在与门生谈论为县之道时指出:“今之人不能听讼,先欲无讼,不过严状式、诛讼师,诉之而不知,号之而不理,曰‘吾以讼’云尔。此如防川,讼必愈多,不知使无讼之道即在听讼之中。”①《袁枚全集》第2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03页。包世臣也把听讼视为“无讼之基”,他认为民间雀角细故“若经年累月,奔走号呼,有司置之不理……则其憾无所释,搆怨泄忿,于是有纠众械斗者,有乘危抢劫者,有要路仇杀者,有匿名倾陷者,并有习见有司疲玩,不以告官,径寻报复者。此皆以积压小案而酿成大狱”②包世臣:《齐民四术》卷第七下《为胡墨庄给事条陈积案弊源折子》,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第252页。。通过听讼,可以避免当事人投诉无门而进行仇杀、械斗等私力救济的发生,避免使事件进一步升级,同时也可以在诉讼和审判的互动中达到教化的目的。方大湜谓:“欲得民心,全在听讼,随到随审,可结便结,毋令拖累日久,以致荡产倾家。即便是养民,惩一儆百,即此便是教民。”③方大湜:《平平言》卷二,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年,第78页。汪辉祖进一步将教化扩展到两造之外的旁听者,他极力强调大堂听讼断狱所具有的重要教化、警诫作用,他认为,“内衙听讼,止能平两造之争,无以耸旁观之听。大堂则堂以下,伫立而观者,不下数百人,止判一事,而事相类者,为是为非皆可引申而旁达焉。未讼者可戒,已讼者可息。”④汪辉祖:《学治臆说》,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6-17页,第?页。汪辉祖在其所著《梦痕余录》中记载,在他审案时常有三四百人前来观看审案,很好的达到了“寓教于讼”“以讼止讼”的效果。
三、关于清代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思考
钱穆在谈到他对制度的理解时指出:任何一种制度,决不是凭空的创立,决不是孤立存在,同时也决不会绝对有利而无弊,也不会绝对有弊而无利。⑤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前言》,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2-3页。如何评价一种制度,钱穆特别强调“历史意见”,即“在那制度实施时代的人们所切身感受而发出的意见”,反对现代人以“自己所处的环境和需要来批评历史上以往的各项制度”的“时代意见”。我们在研究和评价一种制度时,这是尤其应注意的。清代民事诉讼的相关制度,以今天的司法审判原则观之,可能批评多于肯定,但作为当时一项重要的国家制度,却有它的历史必然性。
(一)州县官职权的制度设计及理讼能力导致的必然结果
在清代的行政制度中,州县是最基层的行政建制,州县官“掌一县治理,决讼断辟、劝农赈贫、讨猾除奸、兴养立教。凡贡士、读法、养老、祀神,靡所不综”。⑥赵尔巽等撰:《清史稿·职官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357页。制度赋予了州县官综理地方一切事物的权力,是直接的亲民官,正如汪辉祖所言:“自州县而上至督抚大吏,为国家布治者,职孔庶矣。然亲民之治,实惟州县,州县而上,皆以整饬州县之治为治而已。”⑦汪辉祖:《学治臆说》,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6-17页,第?页。这一点,方大湜也给予了充分的注意,他认为:“兴除利弊,不特藩臬道府能说不能行,即督抚亦仅托空言,惟州县则实见诸行事,故造福莫如州县。”⑧方大湜:《平平言》卷一,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年,第10页。可以说,地方行政全在州县官手中,因其权专,瞿同祖形象的将其比喻为“一人政府”。
这样的“一人政府”在清代不同时期数量略有变化,但大体上保持在1400左右的规模。而随着摊丁入亩以及经济的发展,人口有了较快的增长。美国学者曾小萍指出:“在雍正朝,中国有1360个县,依照清初通行的比例,若使行政单位与人口相适应,县的数量应增加到8500个左右。”⑨曾小萍:《州县官的银两——18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董建中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85页。也就是说,按照同样的官民比,雍正朝的行政数量需要比清初增加4倍。正如钱穆所说的那样,任何一项制度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必须相互配合。行政制度的变化直接与财政制度相关联。如果行政数量增加4倍,那么与之相对应的国家财政支出也必须增加4倍。这对于一个农业型国家来说,其财政将不堪重负。因此,即使单单基于财政的考虑,清代的统治者们也将致力于简约型的行政体制和司法体制。在这样的体制下,地方官绝不可能做到事必躬亲,重钱谷、刑名,民事诉讼则缺乏主动积极的心态。
此外,州县官的理讼能力也决定了很多案件难以进入诉讼程序,或者即使进入诉讼程序,也往往被束之高阁,成为积案。尤陈俊的研究表明,晚清时期江苏、安徽等省州县官平均每月能审结的案件为10件左右。①尤陈俊:《清代简约型司法体制下的“健讼”问题研究——从财政制约的角度切入》,《法商研究》2012年第2期。南方如此,北方一些省份的情况尚不如南方。陕西各州县按月上报给省级衙门的词讼册显示,“各属月报册大抵三两案居多”,石泉县月报6案,樊增祥便称赞该令为“关中翘楚”。②樊增祥:《樊山政书》,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42-343页,第576页。正是理讼能力的低下导致了案件的大量积压。曾国藩以直隶为例,指出:“臣履任月余,见直隶日行公事,讼案居十之七八,……督署应题之本未办者二百三十余件,府局京控、上控之案未结者一百三十余件,各属委审及自理之案未完者殆以万计,或延搁二三年、或五六年、八九年不等,吏治之疲,民生之困,端由于此。”③曾国藩:《曾文正公奏稿》卷34《留臬司张树声清理积讼折》,光绪二年传忠书局刻本。
基于上述原因,统治者既无意于也无力通过扩充官僚队伍来缓解来自百姓的事务压力,作为亲民的地方官只能私人雇佣一些辅助性的人员,诸如幕师、长随等分担个人事务。这些被雇佣的人员薪水完全由地方官个人支付,从国家财政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清代国家不必因为吏役和官员私人雇员的人数增加而随之承受相应的财政负担。但需要指出的是,地方官薪俸固定,并不足以支付或无意于完全支付地方事务人员的薪水,这一部分负担最终仍会转嫁到百姓身上,同时这种将公务性和私人性糅杂在一起的办法,也导致衙门的实际效率越来越低。④尤陈俊:《清代地方司法的行政背景》,载朱腾主编:《原法》第3卷,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8年,第7-16页。另一个办法是,对于民事纠纷的呈控,衙门尽可能交给民间来解决,只有当堂外解决恶化到极为严重时,衙门才将所收讼案的处理权收到自己手中。此办法在于试图借助于宗族或社会共同体的力量,发挥它们的社会秩序维护功能,避免有限司法资源的浪费。
(二)判决的不确定性及上诉对地方司法的压力
正如上文所言,民事诉讼的很大一部分案件并未进入到诉讼阶段,或者在诉讼过程中通过调解等形式而退出诉讼程序,但仍有相当一部分案件依赖于地方官的审判。那么,地方官在判决案件时遵依什么样的原则呢?苏成捷认为:“在裁断现场中律例的沉默似乎显示县官的裁断实际上的依据真的是暧昧不明的——可能是社会规范或者大清律例,也可能两者皆有。”⑤苏成捷:《清代县衙的卖妻案件审判:以272件巴县、南部与宝坻县案子为例证》,《明清法律运作中的权力与文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509页。笔者较同意苏成捷的观点,地方官对于民事诉讼的审判,其决定性的因素更多的是特定案件引发呈控的具体原因,即使是同一案件,在不同的时间节点、不同的诉讼主体,都可能对法官的裁判产生影响,而不同的法官对于案件的认识本身也会存在一定的差异,这导致案件结果的可预期性充满变数,被一方认为公正如水的判决,另一方的感受可能是冤抑难伸。
出于司法平允的观念,制度赋予了陷入“冤屈”状态的当事人一方伸冤的权力,当事人如果认为审判官“审断不公”,便可以“冤屈未伸”的理由层层上控或京控。据《清史稿》记载:“凡审级,直省以州、县印官为初审。不服,控府、控道、控司、控院,越诉者笞。其有冤抑赴都察院、通政司或步军统领衙门呈诉者,名曰京控。”⑥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刑法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4211页。在所有的上控案件中,审断不公或当事人认为审断不公,是导致上控的最主要因素。潘文舫认为:“各省上控之案甚多,其刁徤惯讼砌词呈控希图翻案者固属不少,而其中实有冤仰者亦难保必无。”《樊山政书》的作者樊增祥也在一份牌示中指出:“语云‘无谎不成状’,故上控之状十控九虚。然又云‘久告不已,必有奇冤’,故屡断屡翻者,容有不公平之虑。”⑦樊增祥:《樊山政书》,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42-343页,第576页。有的上控案件,法官判决本身并无不当处,只是当事人自认为不公,迭行上控,而法官以循良自命,“每经审实,辄以‘俯首认咎,免其反坐’八字了结”,通过被告者让步、诉讼者得利的方式息事宁人,结果“上控风气愈惯愈坏”。①樊增祥:《樊山政书》,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57页。
上控对地方司法产生了较大的压力。不管是真正的冤抑难伸,抑或是为达到个人目的而采取的诉讼策略,最终上控的绝大多数案件仍要发回原州县重新审理,这使得本已不堪重负的地方司法更加雪上加霜。庄纶裔任莱阳令五年,“审结词讼案件不下数千起,惩办讼棍不下百余起,而刁风迄未尽绝……已控复结,已结又控,已息复翻者相随属也”。②庄纶裔:《卢乡公牍》卷1《上登州府宪吴论上控情弊虚实禀》,清末排印本。当事人反复缠讼,不达目的,势不罢休,“已控复结,已结又控,已息复翻”,从这样的描述中,我们也不难看出地方官的无奈。此外,地方官更大的压力却是来自上司。对于与上司意见相左的官员,随时可能面临警告、记过、降级、罚俸等处分,情节严重的,甚至有丢官的风险,这也对司法公正和司法的严肃性带来挑战。当然,一种制度总有它的两面。从另一个方面看,不管官员们对于民事案件是多么的不在意,但考虑到自己的官声、上司的观感以及可能因此导致的处分,也会倒逼地方官采取较为审慎的态度。对不予受理的案件,为避免上控的风险,驳词力求“语语中肯,事事适当”,“必将不准缘由批驳透彻,指摘恰当,庶民心畏服,如梦可醒,可免上控。……即有刁徒上控,上司一览批词,胸中了然,虽妆饰呼冤,亦不准矣。”③王又槐:《办案要略·论批呈词》,北京:群众出版社,1987年,第70页,第115页。对于受理的案件,力求公允无私,“处处妥协、周密,无隙可入”,这样,即使上控,“又何畏哉”?④王又槐:《办案要略·论批呈词》,北京:群众出版社,1987年,第70页,第115页。
结 语
总体上看,中国传统诉讼文化中呈现的司法理念受到儒家文化的深远影响,提倡教化,主张无讼。受行政理念和国家财政收入等方面的制约,清代统治者始终没有通过增设知州、知县等地方的亲民官来积极应对当时主要由于经济社会生活日益复杂和人口渐繁而不断扩大的民间词讼规模,使国家司法始终处于一种简约型的模式之中。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地方官“好人不告状”、恶讼师幕后挑唆的思维定势根深蒂固,对诉讼多持排斥态度,通过严格的诉讼主体限制、诉讼程序限制、多驳少批等方式严格限制诉讼案件的数量。即使进入到诉讼阶段,地方官也更倾向于调解而非审判,息讼、少讼的司法措施成为地方官用来缓解司法压力的必要手段。而基于为民伸冤而制定的上控、京控制度,既拓宽了民众诉讼的路径,也给司法带来更多的挑战和压力,同时倒逼地方官对于民事诉讼进行更加审慎、公允的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