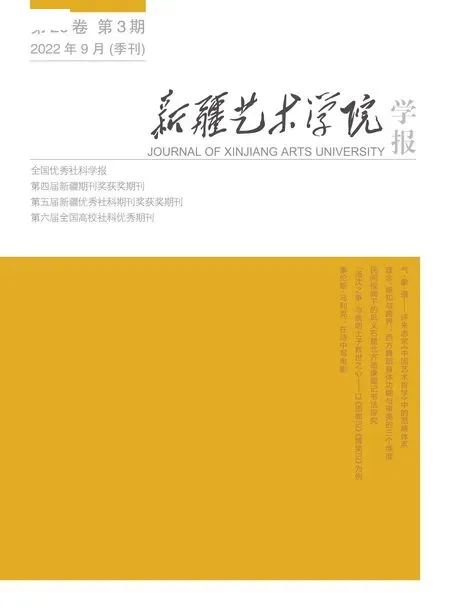戏曲真人秀节目的探索与创新
——以《最美中国戏》为例
邵 敏 刘常常
(安庆师范大学 安庆 246000)
2022年7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公布了2021年度广播电视创新创优节目名单,北京卫视的《最美中国戏》成功入选。作为一档带有沉浸式感受的新型戏曲综艺节目,《最美中国戏》以弘扬戏曲艺术为核心,组织文艺明星搭档戏曲演员融合汇演,并突破传统戏曲舞台限制,将展演主体置于户外园林,迎合当下年轻观众对综艺节目的审美需求。这种“戏曲+真人秀”的节目形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传统戏曲说教式或经典欣赏类节目观众日益流失的窘境,对当下戏曲艺术融合流行元素进行创新传播颇具借鉴意义。
一、《最美中国戏》的创新特色
传统戏曲类电视节目多以竞技或戏曲名家名段欣赏等方式呈现,但这类节目仅能吸引忠实的戏曲粉丝,对于戏曲艺术的广泛传播则稍显乏力。《最美中国戏》的节目形式突破了传统戏曲表演的实体舞台概念,以更加贴合新时代的审美需求,将节目录制和演出置于颐和园实景当中,以沉浸式体验方式展示戏曲艺术,实现了对传统戏曲综艺节目形式的突破,一定程度上吸引了年轻观众的观赏兴趣,在弘扬、传播传统戏曲艺术方面起到了较好的效果。
(一)打破桎梏,制作形式新颖
在文化多元、娱乐多元冲击的当下,人们的审美情趣、意识倾向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的以“戏迷”为主体受众的说教类、戏曲经典欣赏类戏曲节目逐渐呈现与时代脱节的颓势。年轻一代一方面深受“抖音”“快手”等平台影响,对于程式化、综合性较高的戏曲艺术难以欣然接受;另一方面,他们更多地受到时尚文化、大众文化的影响。因此在新时代,戏曲类节目如何走出受众流失的困境,迎合不同受众的观赏需求,进而迎来复兴是其首要之举。
《最美中国戏》不是以戏曲结合流行元素创新开播的首例,但仍是戏曲艺术创新传播的有益尝试。它没有像《非常有戏》那样以明星唱戏的火热手段呈现传统戏曲艺术;也不像《国色天香》那样以歌改戏,借明星之口,展示戏曲与流行音乐之间的融合创新;也不像《叮咯咙咚呛》那样,展现明星与戏曲非遗传人的融合演出,而是顺承国内沉浸式体验消费的火热需求,承袭真人秀节目的叙事方式,将戏曲艺术作为展示主体,同时邀请各路艺人实现对节目的“流行化”解构,使节目制作颇具创意。
一是节目选景底蕴深厚。区别于传统的室内戏曲节目,《最美中国戏》在取景上别出心裁地选择皇家园林——颐和园,其中听鹂馆、德和园等又是古代皇家听戏赏曲的场所,见证了中国戏曲的沧海桑田。节目将戏曲艺术的展示场所回归梨园圣地,在园林实景中演绎传统戏曲艺术的精粹,给人恍然隔世、耳目一新的观感体验。
二是“通关式”设计对戏曲元素的巧妙展现。如第一期中“好戏推荐官”以与社长会合为最终任务,途中经遇戏曲各派传承人,以闯关题目的形式展现戏曲著名片段。观众也可跟随“好戏推荐官”的步伐,在皇家园林闲庭信步之间,欣赏不同戏曲行当的古韵之美。
三是戏曲内容呈现的主题化布局。节目以弘扬戏曲艺术为宗旨,把传统戏曲艺术中具有代表性的戏曲行当或戏曲主题集中展示出来。如设置“三国”“红楼梦”等戏曲展示主题和“丑”“生”“旦”“净”等行当,循序渐进展示传统艺术的多元之美,实现对戏曲艺术新的巧妙解读。
(二)重置中心,展示主体突出
2015年央视开播的《叮咯咙咚呛》,与《最美中国戏》节目性质相类似,可以视为戏曲与明星跨界体验综艺节目的首次结合,在当时引起了较广泛的关注。明星跨界体验戏曲,或者说“戏曲+真人秀”之所以受到关注源于节目保有娱乐性和文化性的双重驱动力。真人秀节目具有较强娱乐性质,能够满足观众对未知领域的求知欲望以及窥探他人隐私的心理,同时实现对因身份、地位的悬殊差距而产生的交流隔阂的冲击与突破;明星体验戏曲艺术的过程,是利用明星对传统艺术知之甚少的特点,从普通人的视角对传统戏曲艺术进行现代化解构,也是对程式化较强的传统戏曲艺术进行“肢解”化的欣赏,使普罗大众与明星一起逐渐适应和亲近戏曲。
虽然也是以“明星跨界融合”方式呈现戏曲艺术,展示嘉宾与戏曲演员的融合汇演,但《最美中国戏》与《叮咯咙咚呛》有着明显的不同。《叮咯咙咚呛》展示的重心,主要向评委嘉宾、明星艺人倾斜,戏曲内容呈现相对较少,正如有论者所言,“以娱乐的形式来传播传统文化,创意虽好,但是实际操作起来却不容易。因为一旦娱乐成分过多,就会冲击文化的内涵,文化有可能沦为娱乐的牺牲品。”①史小建.当代明星真人秀节目的创新发展——评央视节目《叮咯咙咚呛》[J].当代电视,2016(01):61.
而《最美中国戏》,可以看作是对此类节目的进一步优化和中心重置。在明星的邀请上,节目组没有更多地考虑明星的“大牌”或“流量”因素,而是注重明星才能与戏曲艺术结合的适应性。如:嘉宾李响作为传统舞者与演员袁冰妍合作,以舞演绎戏曲《宝黛钗相会》《黛玉葬花》;张艺兴则以擅长的狂派街舞融合戏曲演绎齐天大圣;曾黎更是以自身戏曲青衣之功底,演绎经典《白蛇传》。同时节目邀请戏曲界前辈、精英前来坐镇,在讲解戏曲文化的同时,再现过往经典,增加节目内容展示的丰富性和厚重感。这种专业性的结合优化了之前明星跨界体验这种简单的融合方式,更加偏重嘉宾传播与普及戏曲的功能,使厚重的国粹富有时尚性与戏剧性,较好地平衡了节目的娱乐性与文化性,使弘扬戏曲艺术的宗旨得以充分显现。
(三)百姓视角,传播方式巧妙
《最美中国戏》的节目主旨是为传统艺术“拉新”出力,让戏曲艺术“破圈”前行,在弘扬、传播传统国粹艺术方面体现了较高超的技巧。
首先它仍采用了综艺效果较好的“明星跨界融合”的平民化叙事技巧,让文艺界各路“名角”加入戏曲的融合演绎中来。一方面,明星跨界到并不熟悉的戏曲领域,由职业舞者、演员或歌手等转为戏曲界的门外汉,会如多数普通人一样,暴露出对戏曲知识了解不多的特点,增加了情节新颖度和戏剧冲突,观众也能从他们身上找到对戏曲陌生化的共情感受。另一方面,充分利用了真人秀节目在年轻人中的消费市场,以真人秀的娱乐性、明星的号召力吸引年轻人走近戏曲。
其次,为适应当代年轻人多数对于戏曲的了解比较浅显的情况,《最美中国戏》把厚重、综合的戏曲艺术进行简单化提炼,从一件戏服、一个动作、一张脸谱或一段唱词等入手,以名家解读或字幕等方式充分展示各种戏曲元素,缩小戏曲艺术与观众之间的间隙,用他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对戏曲艺术进行简单化的解读,让“戏曲小白”愿意亲近戏曲、走进梨园世界。
再次,摒弃传统的说教或竞赛等呈现方式,将节目录制场景置于园林实景当中,并通过嘉宾做任务、融合汇演等情节对戏曲艺术进行展示,并把演员练功、舞台服饰及演出用品等展现于荧屏之上,增加了节目的新颖性、丰富性,也降低了观众欣赏戏曲艺术的门槛,更容易让受众产生更深刻的共鸣,较好地达到弘扬戏曲艺术的目标。
二、《最美中国戏》的编创缺陷
《最美中国戏》将戏曲艺术展示场景置于梨园圣地,加之情节的巧妙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戏曲艺术传播的新颖性,迎合了年轻观众的观赏兴趣。但也表现出一定不足,其根本在于对戏曲艺术的“流行化”解构稍显过火,弱化了对戏曲艺术深厚底蕴的多层次挖掘。
(一)真人秀环节叙事拖沓
《最美中国戏》以真人秀的娱乐性质简练化呈现戏曲艺术,较好地实现对年轻观众的吸引。比较之前同类型的戏曲真人秀节目《叮咯咙咚呛》,在本节目中,戏曲艺术、戏曲大师、戏曲作品是真正的主角,尤其在每期最后的戏曲作品展演当中,明星只起到了一定的辅助性作用,明星的作用更多放在真人秀环节当中,着重展现其对戏曲的学习与体验。但认真考察,明星的真人秀环节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节目整体节奏拖沓、戏剧性不强的特点,难以刺激观众的观赏味蕾。
在真人秀环节、在行家教学过程中,明星的反复尝试与体验占据了大量时间,使节目叙事节奏拖沓,同时戏曲行家对明星展示片段的点评有重新回到说教式戏曲节目形式之嫌。沉浸式体验的特点是让受众置身其中、感同身受、产生更多共鸣,但在节目设计上,没有设计竞赛与打擂、分出排名的环节,缺少竞争氛围和矛盾冲突,因此造成了嘉宾选用的荒废。换句话说,就是明星对戏曲的陌生化没有进一步被利用,文化差异造成的矛盾冲突没有进一步展现或处理。
无论是小说、话剧、电影或是其它艺术形式,重点在于戏剧冲突、共鸣情节、感人故事等,这些都要强于说教或平铺直叙的内容形式。因此戏曲综艺的创新应注重对戏剧节奏或是戏剧冲突的巧妙设计,提升节目内容吸引力。
(二)明星角色选用欠妥
戏曲艺术与舶来品真人秀的创新结合是不同文化间的碰撞,为戏剧冲突的产生留有巨大空间。而“跨文化的碰撞既产生了灵感与火花,也在节目叙事的编码/解码中遇到了不少难题,同时以明星为主角的限定又为戏曲真人秀的叙事平添了一道枷锁”。①杨玉.戏曲类明星跨界真人秀的叙事缺陷及提升策略[J].东南传播,2019(09):23.《最美中国戏》深知明星是时尚的符号,是吸引观众的不竭动力,那么如何运用明星自然成为关键因素。值得赞扬的是此节目并没有像其它戏曲综艺节目把明星当红作为选择的唯一标准,使节目内容游离出戏曲之外。在《最美中国戏》中,明星成为辅助戏曲行家表演的第二要素,利用明星的年轻化及时尚化对戏曲艺术进行现代化解构呈现,但嘉宾角色的选用上也出现了部分偏差。
一是没有对明星进行充分利用。由于职业身份的跨界,明星与多数观众一样,是戏曲艺术的“小白”“门外汉”,他们在学习戏曲过程中的出丑露乖,本应成为节目的有趣看点,成为引起观众共鸣的重要内容,但节目没有对此进行戏剧化处理。将明星嘉宾对于戏曲知识的陌生化转化为戏剧冲突,并在戏曲传播中充分利用,强化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既能增强节目的戏剧感,也能进一步强化观众对于传统戏曲艺术的认知,增加真人秀的吸引力。
二是在明星的选择上有随意之感,主要呈现出其对戏曲艺术承载力不足的缺陷。如《最美中国戏》第一期是开播大作,节目伊始就邀请了众多戏曲名家传人前来坐镇,为节目开播及宣传制作噱头,也确实实现了预期效果。但明星嘉宾在融合体验时,出现了“开口跪”现象,减少了戏剧冲突,降低了观众的心理期待。这种现象在节目中常有出现,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对于戏曲艺术的传播者的选择一定要具备承载性,有一定的角色定位,要为推动故事情节起到决定性作用,而不是简单的明星加入融合汇演的模式套路。
(三)节目制作定位不明确
《叮咯咙咚呛》标志着以“真人秀”形式演绎戏曲艺术的正式面世,而《最美中国戏》可以看作是在此节目的基础上进行优化升级。但真人秀与戏曲艺术的文化属性不同,在对戏曲艺术的平民化解构与融合中出现了受众定位不清晰的不足。
首先,综艺性不强。节目追求自然、真实的戏曲呈现方式,尽力规避此前戏曲综艺的泛娱乐化、戏谑等倾向,并力求在短时间内挖掘并展示更多、更丰富的内容。为此,节目设计了名家讲解戏曲、经典重现、嘉宾学习体验等环节,但也因之产生了节目内容平铺直叙、说教和叙事结构趋同等不良倾向,使节目的戏剧性偏弱,观赏性有所降低,总体上显得缺乏综艺节目的吸引力与刺激强点。
其次,受众定位不准。节目对真人秀的泛娱乐化弊病有所避讳,把重心放在戏曲艺术的展现上,但却又没有抛弃明星的加入,因此明星与戏曲行家的同时出现,造成身份的不匹配和节目受众不明确。戏曲行家提升了戏曲展示的专业性,而明星的参与又是出于对戏曲艺术去专业化、普及化的考虑,由此造成受众定位较为模糊。此外,在剧种的展现上也较为单一,着重展现的是京剧,虽京剧内容丰富且有昆曲夹杂,但相比于同类明星跨界戏曲真人秀《叮咯咙咚呛》中展示了京剧、越剧、川剧变脸、秦腔等戏曲艺术,则显内容单薄、受众相对较单一。
最后,置景特点稍显不鲜明。《最美中国戏》主体播出是在北京卫视,把节目场景置于颐和园实景园林当中,具有一定的创意。但对熟知北京卫视的观众来说,仍觉缺乏新意。因北京卫视出品的文化类综艺节目,大多是在类似的古建筑中,比如《上新了故宫》《了不起的长城》等,相同古建筑置景形式也造成一定的审美疲劳。
制作定位的不明确会造成既抓不住年轻观众,也迎合不了戏迷的观赏兴趣,处于尴尬境地。因此在节目编排上需要做出果断取舍和严谨编排,使节目特色更加鲜明、受众更加清晰。
三、《最美中国戏》对戏曲综艺节目创新发展的启示
《最美中国戏》沿袭了真人秀与戏曲融合的制作方式,“园林置景+主题化”戏曲演出吸引了更多年轻观众关注戏曲艺术。但如何进一步平衡好戏曲艺术底蕴与真人秀娱乐化之间的关系仍是难以回避的问题。继续创新节目形式、讲好戏曲故事,是当下及未来戏曲节目创新仍需注重之处。
(一)贴近时代,让传统与时尚相融
戏曲艺术与传统电视节目的早期结合,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电视栏目开播初期节目种类的匮乏,丰富了人们的文娱生活。在传播媒介还不发达的时期,传统电视戏曲节目确实得到了较为繁盛的发展,一时间以戏曲为主要内容的各种节目形态应运而生。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思维模式、审美情趣、休闲娱乐方式等也发生了改变,类似《相约花戏楼》《梨园春》等传统的电视戏曲栏目逐渐衰败,难以适应观众的文化需要。虽有《非常有戏》《叮咯咙咚呛》等开创戏曲艺术与流行元素的结合,但接续存在着重心错位等问题,因此戏曲电视节目仍需要不断革新与发展。
《最美中国戏》欲使戏曲艺术“破圈”前行,重视对国粹的宣扬和传承,在电视戏曲栏目发展艰难、“戏迷”大量流失下进行转型发展,取得了一定效果。在现代综艺消费市场下,观众受短视频文化、信息碎片化等的影响,会更加看重故事输出或情节冲突而产生的共情。因此让戏曲与现代电视市场最受欢迎的元素进行结合,借真人秀之姿,以明星体验融合加之沉浸式节目情节设计为叙事技巧传播戏曲艺术,从节目类型层面增添了诸多趣味性,也打破了传统电视戏曲栏目前进的制约要素,如播出的时间不够好、资源较为匮乏等。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无论是戏曲与流行歌曲的结合,还是与真人秀的结合,都是弘扬戏曲艺术的有益尝试。戏曲艺术需要不断地出现在大众视野之中,也需要着眼于社会流行发展趋势,不断探索节目形式的突破。在传播媒介日新月异的今天,观众的审美需求更加复杂和多变,戏曲综艺节目的再创新,更需要紧密结合时代潮流,着力实现戏曲艺术与时尚气息的交织融合,处理好戏曲作为展示主体与流行元素融合的适应性、平衡性,把握节目的情节节奏,给予受众以更舒适的观感,才能最大限度呈现戏曲艺术魅力。
(二)丰富叙事,使内容与技巧并重
《最美中国戏》展示戏曲艺术的高潮是剧尾的焕新大秀、融合汇演,中间穿插名家解读和明星嘉宾做任务的方式来进行情节推动。但第一季每期的呈现模式比较雷同,且如前所述,在编创上仍存在一些不足,一定程度上消减了观众的观赏兴趣。在后续的戏曲综艺节目中,可从以下方面进一步完善。
一是坚持以明星加入为导向,并充分发挥明星的作用。明星效应仍是当下吸引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走近戏曲的最有效方式之一。《最美中国戏》的表现重心是戏曲艺术本身,因此明星对戏曲艺术的平民化解构、百姓化视角尤为关键,要使观众能够跟随明星的视角去品味戏曲艺术,要为最后的名家名段欣赏和整合汇演做好铺垫,要放大呈现明星嘉宾与戏曲艺术之间的陌生化冲突,增强因文化差异而产生的戏剧冲突,使嘉宾的加入起到情节推进的关键作用。概言之,节目既然以明星作为传统戏曲的代言人,那就应在转化明星角色上多做编排,使受众为某位明星而来逐渐转化到为戏曲艺术真美的感叹上来,所以明星对戏曲陌生化的文化冲突转换成为节目的戏剧冲突仍大有文章可做。
二是在设置主题化呈现的同时,丰富节目呈现技巧。《最美中国戏》第一季各期“明星加入—名家解读—闯关游戏—学习戏曲—融合汇演”的固定呈现方式,加之相对平淡的叙事技巧,容易使观众失去新鲜感。每期节目需要一个最高任务或是“立主脑”,以之贯通节目情节的设计,并为节目最后的焕新大秀制造噱头,增强节目的戏剧冲突,丰富展现方式,从而让节目层次更加丰富、节奏更加紧凑。要通过导演技巧,更生活化地剥开戏曲艺术厚重的外壳,增加节目观赏度,进一步强化戏曲艺术对观众的吸引力。
三是在重视京昆的基础上,增加地方戏曲剧种类型。弘扬戏曲艺术,影响范围最广的京昆自是首选,但不能仅限于京昆。丰富多彩、特色各异的地方戏,如黄梅戏、越剧、豫剧等等,也各有其独特魅力。不同剧种在同一节目中的争奇斗艳,也应当是戏曲综艺节目的重要叙事动力。
戏曲综艺节目应进一步讲好戏曲故事,丰富戏曲综艺的叙事内容与层次,用广阔的叙事空间解决戏剧性较弱、节奏过慢等不足,让厚重戏曲艺术真正地适应观众的审美需要。
(三)延伸化传播,实现节目的长尾效应
《最美中国戏》以“明星跨界体验”的叙事方式展现戏曲艺术,实现对年轻观众群体的吸引,似乎仍是当下戏曲综艺化呈现的最优解。不过,真人秀节目一定要和观众建立情感关联,而这个关联就是观众能够看到自己,产生共鸣。而节目里明星对戏曲艺术的陌生及融合竞演的过程,是观众找寻自己身影、实现共鸣的最好方式。不过由于节目既想迎合年轻观众的审美趣味,又不想丢失“戏迷”群体的审美需求,造成了节目定位不清晰的弊端。因此戏曲与流行元素的结合应大胆突破传统壁垒,最大限度地让戏曲与流行元素结合,使之受众群体更加清晰。
不仅如此,一档戏曲综艺的出现,是想借流行元素的快车,吸引更多年轻群体关注戏曲艺术。然而想要仅仅通过一档节目的呈现,让观众瞬间喜欢上沉淀了几千年的戏曲艺术难度太大。加之戏曲艺术的综合性和程式化等特征,观众仍会停留在看完即止的现象当中,难以实现综艺的长尾效应,吸引观众真正了解戏曲或是走进剧场观看演出,实现戏曲的“活态传播”。因此除了戏曲艺术的综艺化展现需要继续迎合观众多元文化需求外,还应通过节目之外的努力,将戏曲传播渗透到观众日常中去。
《最美中国戏》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在电视之外,已经借助腾讯、百度视频、爱奇艺等多个互联网平台和抖音、快手等以短视频为主的自媒体平台展开播映。但还可以更进一步扩大戏曲传播范围,将戏曲的传播由传统的视觉听觉艺术向更广阔的受众生活空间延伸,以引导、增强受众对戏曲艺术的关注。如在节目的明星资源利用上更进一步,开发“明星+戏曲”的IP 产品、制作形象授权产品等,增加节目的附加值,实现戏曲艺术的立体化广泛传播,让戏曲综艺节目的影响延伸到受众的生活空间。又如,在电视节目之外,利用网络开设与节目内容相应的数字化信息资源库等,使有兴趣的受众有途径进一步强化对节目相关内容的深入了解等。
《最美中国戏》将戏曲艺术置于实景园林中进行展示,展现了传统经典与流行元素的新型融合,获得了较高的社会评价。在观众的文化娱乐消费倾向随着文化多元化、休闲娱乐多元化和传播媒介的繁盛而趋于复杂和多变的当下,戏曲综艺节目仍需不断探索,努力迎合观众的审美需求,更好地宣扬戏曲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