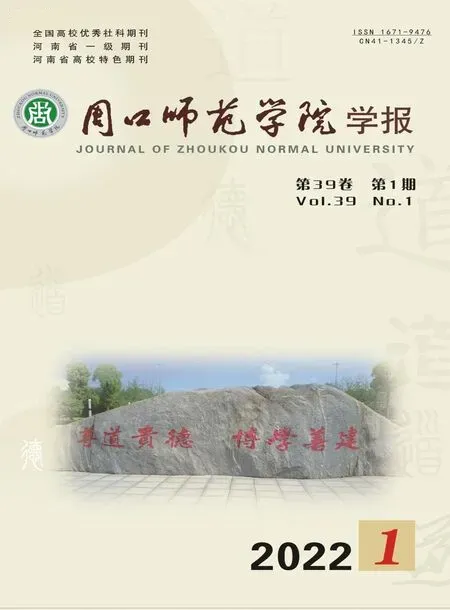无败事:老子对圣人成功之道的系统阐释
——以《道德经》第六十四章为中心的考察
谢清果,刘苏琳
(厦门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近年来,笔者常从《道德经》是一部成功学著作的角度来阐释老子思想,其原因一方面是,经典当转化为今人的实践智慧,亦即从古为今用的角度来把握经典价值;另一方面,《道德经》本身也是希望世人通过尊道贵德的根本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理想目标,进而为世界的和谐安宁做出自己的贡献。学习《道德经》,不难发现,老子正是通过大小、多少、难易、贵贱、高下等一系列的概念的辩证阐释,启迪世人行事当秉持“道法自然”原则,以“辅万物之自然”来定位自身,千万不要把个人的意志和能力凌驾于道与德之上,“孔德之容,惟道是从”是成功人生的必备素质。本文正是基于这一考虑,从《道德经》第六十四章出发来探索老子是如何教导我们走上成功之路的。
读过《道德经》的人都知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句世人耳熟能详的俗语,正是出自《道德经》第六十四章,常被用以激励有志之士由小事着手,通过实际行动的点滴积累逐步向最终理想靠近,亦即常和“只要坚持不懈的行动就必有所成”的衍生意相连,以更好地劝诫他人不以事小而不为,以向可能的成功靠近。但是,努力是否就一定会成功?老子在其著述中所要表达的本意究竟为何?本文希望通过对《道德经》第六十四章的整体解读以具体回答这个问题,并进一步探究老子的成功观。
河上公于《道德真经章句》中为第六十四章命名“守微”,宋常星的《道德经讲义》中则为其题名“辅物”。前者是对整章内容的概括性提炼。“守”字按《说文解字》注解,即“官守也。从门,寺府之事也”,作为名词,其本义为官吏的职守,同时作为动词,其又兼具遵守奉行和坚持保守之意。由此而言,“守微”即可解读为坚守微小之事物,结合《道德经》作为政治哲学著作的核心定位,这一行动的主体自然而然地指向帝王乃至其所统帅的治国之师——各级文武官吏。后者则取自全章结尾句“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意指“辅助万物”,顺应万物的自然规律而不违背。两者各有其源,对照来看更利于我们初步理解本章主旨。
下面,本文欲对本章进行导读,力求从当下的实际出发阐释其中的老子思想,以其成功观为时人提供一定指引。本章全文如下: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
一、持安之道:对事情发展状态的准确把握与积极处置
本章开篇两句,分别从事实性描述和理论性概括两个层面讲述了同一个道理,即事物的安定状态是易于保持的,但是假如没有居安思危的意识,不知在问题出现的肇始阶段去解决它,则安定也不可能长久。
“其安易持”。《尔雅》有言:“安,定也。”《庄子·天地》则载:“共给之为安。”[1]324于此,“安”指代事物稳定期的安定状态。不同于不断发展、持续变化的拓展期,进入稳定期的事物已于事实上形成了自身的一套范式。这是一个兼具规范性和稳固性的统一框架,起着维系和平衡各方力量以促进事物整体平稳推进的作用。这既为安定的长期存续创造了条件,也使得事物的发展模式可以被借鉴,乃至于复制。
高瞻远瞩的成事者常在建立这套范式的过程中便已预见性地考虑到了将来可能出现的各项问题,并提早就此进行了筹划,此即“其未兆易谋”。所谓“未兆”,王弼注:“无功之势”[2]166,指的是尚无作为之时。问题在还没有发端的时候就易于谋划。这就提醒欲成事者在事情尚未成为问题之时,当前瞻性地全面思量事情走向,一方面通过完善各项规章制度,扎好制度的笼子来规避问题的发生,另一方面为可能发生的不可规避的突发情况做好紧急预案。
倘若问题仍然出现了,则欲成事者须得赶在其发展壮大之前解决它,亦即“其脆易泮,其微易散”。“泮”,傅奕本、范应元本及焦竑本注解其为“判”,两者古义通用,《说文》载:“判,分也。”另有河上公本、景龙本、敦煌本等多种古本则以为其作“破”解,取破碎、破裂之意。两者实质上有其相近之处。整句即点出问题在脆弱的状态易于被分解,在微小的情况下容易消散。此句实际涉及了“软硬”和“大小”这两种不同的事物性质,分从两个角度同步指向了“莫等问题已成气候再着手整治”的提示。
针对前四句,王弼注:“此四者,皆说慎终也。不可以无之故而不持,不可以微之故而弗散也。无而弗持则生有焉,微而不散则生大焉。故虑终之患如始之祸,则无败事。”[2]165这是结合着下文的“慎终如始,则无败事”对此加以解读。《说文》载:“慎,谨也。”《尔雅》载:“慎,诚也。”“慎终”相连,可理解为以谨且诚的态度对待事情的终了,力求善终,达成一个圆满的结果。
《周易·系辞》有言:“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3]孟子概言之:“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4]这与老子所言有异曲同工之妙。安定的状态虽然有其可长期稳固发展的条件,但是成事者倘若就此安于现状,满足于享受眼前的安逸且仅图谋着简单维持现有的成果,忽视了对长远性问题的考量和对已显露端倪的问题的补救,则同样可能陷入倾覆的境地。其间蕴含着意指“居安思危”的谆谆告诫。
一言以蔽之,“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陈鼓应为此句注今译为:“要在事情没有发生以前就早作准备,要在祸乱没有产生以前就处理妥当。”[5]302这一理解有其合理之处,但结合上文观之,其未能完全说明与“其脆易泮,其微易散”相对的“治之于未乱”一句之意。所以,笔者倾向于认为此句可意译作:在事情尚未发生之前就开始采取行动,有所作为,但过程中如果不够细致周道,产生了漏网之鱼式的问题,则应赶在其引起紊乱之前就加以治理。
全句从不同的侧面分析了在事物的初始状态,成事者应当以怎样的心态去面对它。概言之,这要求成事者具备把控全局的能力。全局,既包括横向事情的铺展,亦涵盖纵向事情的发展,皆需处于掌控之中。其中后半句又尤为值得后人警醒,为了防止整体性的大危机发生和避免核心主力的溃败,成事者定当亡羊补牢,不得忽视已经显露的局部性问题。
二、作为之道:日积月累、坚持不懈的取胜要诀
针对事物发展的过程,成事者当如何作为,老子复又借助三个生活化的场景,以故事叙述的方式加以更为生动形象的解释,即“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毫末”同“合抱之木”相对,意指微小的萌芽。“累土”,其解释分作“低土”和“一筐土”两种,前者以河上公“从卑到高”和严灵峰“地之低者”为代表,后者则有如林希逸注“一篑之土”[5]302。此处联合上下文,后者可能更为恰当。从字面意思而言,全句意指:需展臂方能围拢的参天大树也是从毫末般的小树苗开始成长的,九层之高的高台也是从一簸箕一簸箕的土粒开始积累的,遥远的千里之外的地方也是从脚下的一步步开始走的。
其中,“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后化作俗语,广为人知。但各注本就“千里之行”一句的记载事实上存在争议。敦煌辛本、遂州本和赵志坚本等古本皆有将此句作“百刃之高”的记载,是以有人认为“千里之行”可能是传播过程中的误写。就此,朱谦之以《荀子·劝学篇》所载“跬步而不休,跛鳖千里。累土而不辍,丘山崇成”一句为证,认为“千里之行”即故书[6]。事实上,就全句加以体系化的理解,也当是“千里之行”更为贴合句意。“合抱之木”“九层之台”和“千里之行”,这三者事实上分别对应了宽度、高度和长度这三个事物发展的不同维度。而不论是从哪一维来看,事物的壮大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一方面要求成事者主动地采取行动。结合当代的历史现实,这在一定程度上与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有异曲同工之妙,是一种“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积极作为,即要求成事者主动地去接受磨炼,乐观地去迎接挑战,借此磨炼自身解决问题的意识和方法。另一方面也要求成事者始终保持小心谨慎的态度。乐观,但不可以盲目乐观以至于对出现的问题麻痹大意。承接上文而观之,未真正抵达目的地之前的每一步事实上都隐藏着失败的可能,若放松警惕则难免掉入失败的深渊。
三、不败之道:慎终如始的无为之为
那么,成事者如何才能避免失败?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明确什么举动会导向失败。就此,老子提出了“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历史上就此句争议颇多,常有人将此曲解为“作为的人必败,执着的人必失”,并以此批判老子,认为其思想倡导消极无为和消极避世。但是实际上,此句作为上一句正面分析的反面补充,显然绝非此意。
针对此句的“为”,误解者常直接认为此即老子所信奉的“无为”,但是实际上,“为”分“无为”和“有为”。何谓“无为”?“惟道是从”,遵道而行,即“无为”。葛荣晋指出“无为”“在老、庄的哲学思想体系中,最基本的含义就是‘道法自然’”,而根据王中江的考论,“‘道法自然’的意思是‘道’遵循‘万物’之自然”[8]44。 “道”生万物的观点被广泛接受,但另一方面,“作为万物之母的‘道’,它又让万物按照各自的本性(‘德’)自由发展,虽然万物的本性原本又是道所赋予的”[8]45。此即老子哲学思想的玄妙所在。
由此观之,“无为”所指代的并不真正是什么都不作为,而是顺应自然规律而为,即在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统一,方法、本体和认识论统一,这两个统一的基础上采取作为。例如,上文所述的三种行为如果采用正确的方式,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可谓是正为,即“无为”。毫末之木需居善地,有肥沃的土壤才能茁壮成长。松散的土粒需依照合理的方式堆砌才不至于垮塌,最终可建成高台。千里之行的每一步也需走对方向,朝着既定的目标一点点行进。如若不然,则终将徒劳无功,距离成功越来越远,成为老子于本章所言“为者败之”的典范。
“为者败之”的“为”理应属于“有为”的范畴,是老子所批判的一种“为”的存在形式。何谓“有为”?依照私心杂念任意而行,极富个人主观主义的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此即“有为”。此处的“为”“是特指违背事物发展规律,违背社会发展规律,违背民心或与民众的根本利益背道而驰的行为(behave),而不是行动(act)。”[9]
老子追求“无为”,反对“有为”。“无为”其实是“为”的理想状态,是“为”的指导思想。以“无为”的方式来“为”,“为”是为了“无为”。由此,“为者败之”即可被解读为“妄为必败”。如上述一般坚持不懈的作为,未必就可以成功,如果不顺应自然规律的妄为,仍将导致失败。积累到一定程度的量变向质变的转化仍然是有条件的。勤奋是成功的前提,但是勤奋不一定会成功。而“执者失之”则可被解读为“固执必失”。固执的人,撞了南墙还不肯回头,就一定会失败。诚如《道德经》第四十二章所言“强梁者不得其死”,强横凶暴的人死无其所。这同样说明了性格过于刚烈,脾气太过火爆的人最终必然没有好结果。这要求成事者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如此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综上,老子认为,胡作非为必然导向失败。明白了此点,“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便不难理解。所以品德高尚的人,顺应自然而为就不会让自己陷于危险之地,从善如流、兼听则明,没有执念就不会失败。
但此外,老子同样意识到,松懈亦将导向失败。“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即意指人们在做事的时候,常常是“行百里者半九十”,在快要成功的时候失败。行动者前面积累得再多,一着不慎,也将满盘皆输。在即将成功之时,胜券在握的感觉常使人麻痹大意,失败则可能就此降临。
所以,老子告诫世人,“慎终如始,则无败事”,要从始至终,保持如一的谦虚、谨慎的态度,才能避免失败的发生。早于老子的先人已提出了这一思想。例如《诗经》所言:“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此即意指世人所做之事往往都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能坚持到底,善始善终者却寥寥无几。通往成功的道路上常有诸多其余的诱惑,如果不能以坚强的意志抵制诱惑,则必然失败。这便需要成事者具备“不忘初心”的信念。
四、圣人之不同凡响:成大事者必有超越常人的思想方法
在从正反两面详细讲解了如何保持安定和避免失败的道理后,老子于本章的最后点出了圣人之所以不同于凡人的可贵之处,即在于他们具备了常人所不具备的三种思想方法。
其一,“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王弼为其注:“好欲虽微,争尚为之兴;难得之货虽细,食盗为之起也。”[2]166喜爱的欲望虽然微小,争夺尚且由此发端,难得之货虽然细微,盗贼也因此兴起。这同《道德经》第十九章所言的“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和“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有着共通之处,应将货利视作偷窃等行为的源头,提倡人们保持原有的纯洁本性,克制并减少自身的私欲和杂念。回归本章,此句即表明圣人可想常人所不能想,没有一般的财富观念,对金银珠宝之类难得的贵重财富不过分看重。
进而延伸到治国理政,老子在此劝诫着帝王不要被眼前的蝇头小利所吸引。“心底无私天地宽”,在国与国交涉的过程中常有许多不得不为之事,执政者如果贪图几座城池,则可能会失去整个国家的屏障,帝王需要具备全局谋划的意识。结合当今中国所面临的实际情况观之,在全球一盘棋的大背景下,我国要参与全球治理,就必然与亚非拉国家结盟,承担起大国担当。这一过程中,国家领导人也时常可能遭受百姓的误解。是以,如同《道德经》第七十八章所言:“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承担全国的屈辱,才能成为国家的君主,承担全国的祸灾,才能成为天下的君王。圣人要学会藏污纳垢,即承受民众的不理解。
其二,“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学不学”,《郭店楚墓竹简》作“教不教”[10],是以有学者经考证以为“‘学’是‘教’的变形”[11]。魏启鹏则以《说文解字》《广雅释诂》《墨子·小取》的解释为证,结合《道德经》的其余篇章加以分析,认为此当解作“效不效”[12]。但是,以《河上公道德经章句》和《老子道德经注》为代表的诸多通行版本中皆作“学不学”,为其注解作学习之意。在此,笔者仍倾向于赞同后者。
对应前后文,全句释义即圣人学习常人所不学的东西,不会重蹈覆辙,去重复犯别人的过错。这指代帝王在学习的内容和对象上相比常人有所超越。道生法,法生术。帝王学道,常人学术。“道”即千变万化之宗,“术”则不过普通的技巧。帝王学道,不陷于术,即便学术,也要以道驭术,如此才能把握正道,实现工具与价值统一。老子同时也在劝诫帝王不要过分急功近利,最大的浪费是决策的浪费,与其事后扼腕叹息,不如在学习和谋划的阶段即打好坚实的基础。
其三,“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就此句的“自然”,池田知久将其解释为“‘万物、百姓’以自身的力量,自律地自发地存在、变化”[13]。其作为状态对象的客体是“万物”和“百姓”两者。这一诠释有其合理性,但人存续于天地间,事实上同样可归于“万物”的范畴。“万物”的概念一定程度上即包括了“百姓”在内。是以,笔者倾向于认为此处“自然”应当包括自然界的自然和人心、社会的自然两个不同的层面。
圣人的非凡之处即在于其可以辅助自然界和社会顺应规律地发展而不妄为。《道德经》第十七章言:“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可见,老子所认为的最卓越的统治者可使百姓仅仅是知晓其存在。其悠然且慎重于发号施令,以至事成之后百姓常以为自己所为皆是源于自身内心的本愿,自身本便如此。《道德经》第二十三章开篇将其进一步精练地表述为:“希言自然。”“贵言”和“希言”莫不是希望统治者减少政令的颁布,理解并竭力顺应自然万物的规律,施行“无为”之政。此处需明确,圣人既非万物主宰,也不能凌驾于万物的法则之上。王庆节就此指出:“老子将这种帮助、支持而又不干涉、强制他者的自己而然的情形称为‘辅自然’,并视之为自然概念的消极性意义的一个必要的方面。”[14]但是,通篇来看,老子所倡导的仍然是积极的“为”,是实践和奋斗,只是以“无为”的思想原则来展开作为,亦即顺应万物的规律作为。这是一种“为而不争”的思想。借此我们可管窥西方和东方哲学的差异,西方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15],东方庄子则认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1]83。前者强调以人为中心,后者所代表的老庄思想则共同强调人与天地共生。
最后,回到本文最开始的问题,努力是否就一定会成功?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于老子而言,成功需要成事者脚踏实地地由点滴小事逐步积累,且必须是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如此方有达成质变的可能。过程中,他们需前瞻性地预估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并为此搭建好制度的框架且准备好预案。同时,他们需时刻警惕已经显露出的微小问题,哪怕是眼见胜利在望之时,在问题的初始阶段将其解决,以避免不可挽回的败局。这也就要求着成事者具备想常人所不能想,学常人所不学和顺应万物规律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