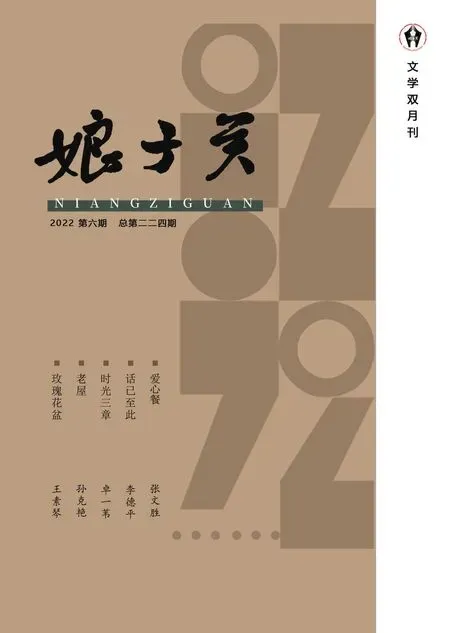光脚走他八里地
◇梁鸿斌
一阵电闪雷鸣之后,雨点落在了广场上跳舞玩耍的人头上,音乐声、孩子们的叫闹声逐渐散去。好多年没有在这个季节里下过如此大的雷雨,太行山西麓的盆地一般是在七八月份才有雷雨。一袋烟的工夫,房顶上流下的雨水已经将屋外的坛坛罐罐装满,家里安装了自来水后,父亲的习惯还是没有任何改变。
“爸,快九点了,该睡觉了。”我催促着坐在阳台前的父亲。
家里盖起了小二楼,临街的阳台就成了父亲的“专属领地”,为了父亲观看方便,特意给他装上了落地大窗,楼下的健身广场一览无余。每天晚饭后他准时坐在这里观看着跳舞健身戏耍的男女老少。父亲只是看着,很少言语,眉宇间看不出父亲的表情,偶尔有笑声也是轻轻地、淡淡地,更多的是凝望、沉思还有泪水。
走到父亲的身后,努力地想把父亲从这张大椅子上扶起来,可父亲并没有站起来的意思。大椅子是我给父亲特意从广州买的,是既能转又能摇的那种“老板椅”,和村东面耐火厂老板三胖子坐的一样。“唉!三小,你母亲要是在的话,和你张婶一样大了吧?”父亲叹着气,像是问我,又像是自言自语。每年进入雨季特别是三伏雷雨天气比较多的时候我就发愁,每当这个时候父亲总是眼含泪花,唉声叹气,安慰的话在父亲早已显得苍白无力,只能默默地陪着父亲回忆。
铺好被褥,搀扶着父亲睡下,父亲很快入睡,均匀的鼾声便回荡在了温馨的小卧室里,我静静地坐在父亲床边,看着眼角还挂着泪珠的他,好久好久……
“牛儿们,回来吃饭喽。”母亲的呼唤比钟表还准时。那是我们家唯一的一座“座式钟”,听说还是母亲的母亲留下的,然后作为陪嫁和母亲一起来到了我家,这是我记忆中家里最值钱的物件了。时间长了,母亲的呼唤竟然成了左右邻居“标准时”。我当时六七岁,往家里跑的时候总是被两个哥哥甩在后面,两个妹妹还小,只能在院子里玩。大姐是家里除了父亲以外的绝对顶梁柱,小学没读完就回家和爸妈一起担负起养家的重任,帮着母亲在家里照看我们兄妹五个,洗衣做饭、喂猪下地。几间破旧的窑洞是一家人遮风避雨之地,艰难的岁月里,父母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想方设法不让孩子们饿着。
“孩他妈,我看着这世道要变了,昨天上午我看见张大个背着家伙什儿出去了,我估摸着是出去找活儿去了,要不咱明儿也拾掇拾掇,把我那些家伙什儿整理整理,咱也出去试试?张大个子那臭手艺还敢出去找活儿,我这手艺比他强多呢,我就不信这事了,他能找下活儿,我找不下?”昏暗的灯光下,母亲一边收拾着刚刚缝补起的衣服,一边看着半躺在炕上的父亲。农电并网以后,三天两头停电的事成了过去时。邻家都换了四十瓦大灯泡,可我们家孩子多,母亲为了节省电费,还是一直用的十五瓦小灯泡。
“林哥,我就知道你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昨天我也看见张大个子背着铺盖出去了,这不今儿上午我就把你的衣服翻出来洗了,被子也晾晒了。”母亲说,“孩子们都上学了,家里用钱的地方越来越多,咱不能再耽误孩子上学了,大妮已经让咱后悔死了。”母亲轻轻地抹了抹眼角叹口气,“现在政策好了,但凡有点手艺就饿不着人。”
屋子里的烟味夹杂着衣服里的樟脑味,妹妹们早已熟睡,我把被子往上轻轻地拉了一点,眯着眼尽量不让母亲发现我还没有睡着,静静地听着他们说话。
母亲叫柳春花,年轻的时候父亲一直叫她“花儿、花儿”的,有了我们以后,父亲抹不开面子,便改口叫“孩他妈”。父亲叫杨树林,祖上是远近闻名的好木匠,到了爷爷这辈一直没有间断,听父亲说“杨树林”这个名字好像是爷爷为了日后能有更多的木材可以打家具卖,专门给父亲起的,爷爷把手艺传给了父亲。没过门的时候,母亲就叫父亲“林哥”,这个昵称一直没改过。
一缕晨光透过院子里柳树的缝隙洒在了窗上,嫩绿的柳条随着春风,轻轻地摇曳着,小鸟们总是起得很早,它们欢快地嬉戏鸣叫。丁零咣当的声音把我从睡梦中叫醒,父母早已收拾起了两个大包,一包装着木工工具,一包装着他的被褥。
“不等孩子们醒了说句话?”
“不了,看误了头趟车。”父亲背着铺盖卷,手提工具包走出了大门。
“下坡坡慢着点啊,看跌倒。”母亲说。
父亲说过他记忆中门口的小路就是这样:陡坡路的旁边是一条深沟,有几十米高,梅雨季节沟里的水流很急,坡上住的人们必须等河水消退些以后才能跳过去,走到唯一出村的“正路”。以前就有好多人失脚踩空掉下去,轻者伤、重者亡。母亲小心翼翼地陪着父亲走下这条蚰蜒陡坡,来到了“正路”。
“干活的时候悠着点,一定要吃饱,不管好赖,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儿挣钱呢。”母亲心疼地嘱咐着父亲。
高抬腿轻落脚一路小跑地跟着父母往村口走着,我一会儿躲在树后,一会儿猫在草丛里,生怕他们发现。
“回去吧,孩们快醒了,给孩们做饭去吧。”
“没事,还早着哩,再跟你走会儿。”母亲说。
“啥时候能修好这条路,坑坑洼洼的愁死人啦,要是遇上雨雪天,不用说推小平车了,单人也不能走。”母亲边走边埋怨。
“看现在社会的发展情况,以后肯定能好起来。”父亲的口气就像是在城里挣着钱以后自己就能把路修好。
“但愿吧,咱就盼着那一天了。”母亲边走边说。
“哎,林哥。”母亲歪着头紧紧地靠在父亲肩上,胳膊又往紧里挽了挽父亲,好像一松手父亲就飞了,看起来就像小孩子。在我们眼里父亲像一座山,母亲像一棵树,父亲无所不能,是我们生命的依靠,母亲神通广大,是我们生命的源泉。母亲在,我们就有吃穿,母亲就像一棵果实累累的大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还能遮风避雨。我睁大眼睛好奇地看着平常几乎看不到的母亲的另一面。
“等修好了咱村的路,就像到了城里,你说那是啥样啊?”母亲看着父亲,脸上幸福的笑容里流露出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晨光照射着母亲粉红的面颊,美得像一朵盛开的牡丹花。
“啥样?平展展光油油,还能照影子哩。”父亲的眼眯成了一条缝,笑呵呵地逗着母亲。
母亲轻轻地捶了一下父亲的胳膊:“看你说的,我是想着呀,等修好了这条路,老少娘儿们还不天天在路上撒欢呀。到那时,咱村的这些瓜桃梨枣呀,就不用发愁了,用小平车拉着进城里卖,咱村就有钱了。”母亲越说越兴奋,完全忘记了是要送父亲进城里做工。
“林哥,我有一个想法,你能不能答应我?”
“啥想法?”父亲回过头看着母亲。
“等修好了这条路,就像你说的,平展展光油油的以后,咱俩不要穿鞋,光脚走他八里地,好吗?”
“好!”父亲笑着说。
“到时候光景好了呀,咱不穿鞋,我陪你,光脚走他八里地。”父亲的声音拖得比较长,但肯定的语气中透着坚定、透着向往,就像拉过钩、击过掌,摁上手印一样。
“好咧,说定了啊。”母亲高兴得像一个小孩子,咯咯咯的笑声在清晨的山谷里显得格外清脆,好长时间没有见到母亲这么开心,要不是父亲背着包袱,母亲估计能扑到父亲怀里,这架势我从来没有见过。春日的暖阳照在父母的脸上,我第一次偷听到了父亲母亲在外面的“悄悄话”,第一次看到了没有我们打扰下母亲对父亲的似水柔情。
大姐出嫁以后家里的所有家务都落在母亲一个人身上,虽然每年的春耕秋收季节父亲会回来一起播种收割,大哥二哥也会帮着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可大部分的农活家务还是要靠母亲一个人来完成。
“妈,我不想念书了,我想回来帮你干活。”
“妈,我也不想念了,我要干活。”
大哥、二哥看着每天劳累的母亲,恳求着说。
“胡说,傻孩子,不念书将来有啥出息,家里的农活有妈呢,用不着你们,回去好好念书去。”母亲说话的声音不大,但她是那么的坚定,那么地不容反驳。人常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们虽然没有当家,但我们很听话,父母的话就像“圣旨”。
父亲在县城里走家串户打家具,做一些简单装修的活儿,收入相对种地好了很多,大哥二哥也都在县城里上了高中,我在镇里上初中,俩妹妹在村里上小学,那段时间邻居都投来了羡慕的眼光。
随着党的惠农政策不断延伸,父亲回村里承包了二十多亩荒地开始种植苹果树、核桃树、枣树等一些经济林,家里的收入也随之增加,大哥、二哥也都考上了大学。我们家不但有了彩色电视机,还添置了一台“长岭”两开门冰箱,逢年过节孩子们都回到家里,窑洞里总会传出欢声笑语。
“妈,我头疼得厉害。”小妮是我们兄妹中的老小,初中眼看就毕业了,连续熬夜备战中考,觉得身体实在吃不消了,喃喃地和母亲说。
“好烫呀!”母亲摸着小妮的头。
那时候我和二妹在县城上高中,家里只有父母和小妮。到了晚上,母亲一边在小台灯下做着针线活,一边陪着小妮熬夜复习功课,我们兄妹几个的好成绩几乎都是母亲一针一线缝出来的。母亲映在墙上的弓背就是我们好好学习的动力。
“林哥,不行的话咱领着小妮到镇卫生院看看吧,孩子烧得厉害。”母亲着急地催促着父亲。
打完点滴已经半夜了,镇上的卫生院没有床位,一般是不能住院的。
“咱回家吧,明天再来。”看着孩子好了许多,母亲和父亲商量着。
“看这风刮的,一会儿说不定要下雨。”父亲抬头看看阴沉沉的天说。
“咱走快点,也许下雨之前能赶回去,咱已经在这里折腾人家大夫大半夜了。”母亲不愿意在卫生院麻烦人家了。记忆中的母亲永远都是这样,只要自己能做的事,一般都不会去求人。
父亲前面拉着小平车,母亲后面推着护着躺在车上的小妹,在崎岖的山路上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回走着。
“啥时候能给咱修修这条路啊,唉!”母亲一边推车一边嘟囔着。
风刮得更大了,雨点吧嗒吧嗒地落了下来,他们加快了脚步,母亲努力地在风雨中撑着伞,尽量不让雨水淋湿小妮,就像呵护着刚孵化的小鸟,用尽全力撑开了她的翅膀。
一阵电闪雷鸣之后,天空像被撕开一个口子,毫无顾忌地把雨水倾倒在我的父母身上。父亲脚下一滑,一个趔趄,母亲赶紧上前扶住父亲,母亲担心雨水淋着小妮,把外套脱了蒙在小妮头上,冰冷的雨水中母亲只穿着一件贴身小袄,闪电就像按下快门的相机把他们定格成了泥塑。
好不容易到了家门口那条又弯又陡又长的坡路下面,小平车是绝对不能走了,父亲背起了小妮以后才发现母亲一直穿着单衣。
“你呀。”父亲心疼地说。
“林哥,你慢点。”母亲一手撑着雨伞,一手护着推着小妮,艰难地往坡上走着。雨越下越大,快到坡顶已经看到家了,一个急闪电伴着炸雷把天空劈成了两半,父亲突然感到身后猛地一松,回过头,母亲不见了。
“花儿……”父亲急切地呼喊着。
把小妮丢在炕上,父亲疯了似的冲出门外。
“救人啦,救人啦……”
雷声和雨声把父亲的呼喊淹没在黑暗的夜空,没有人能够听见父亲撕心裂肺地呐喊。
父亲连滚带爬下到河沟里,齐腰的水夹杂着树枝、石块、泥土向父亲打来,父亲哭着喊着胡乱地摸索着。
雨停了,早起的邻居发现了坐在水沟边呆呆发愣的“泥人”,父亲浑身湿漉漉的,身上到处都是伤口,血还在不断往外渗着。
母亲是在离掉下去五六百米的地方找到的。
“以前这里也掉下过人,可只是伤着了,没有死了呀,哪怕是折了胳膊断了腿也好。”
亲朋好友的劝说根本没有任何意义,父亲见了谁都是这句话,说了很长时间。
“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专找命苦人。往后他大爷和孩子们可咋过呀。”
“唉!傻了。”邻居张婶惋惜地叹着气。
父亲承包的经济林丰收了,沉甸甸地挂满树枝,张大个和张婶两口子也成了养猪大户。
“我说他大爷,你的瓜果也熟了,俺家的猪也养肥了,可咋往外卖呢?愁死人了。”张婶无奈地问父亲。
“小平车往外推呗,有啥法子。”父亲抽着烟蹲在院子里,一筐筐的水果堆着,本应该给盼着好日子的父辈们带来喜悦,看现在的情况倒是增加了不少的烦恼。
路太难走了,没有几个收购商愿意到这个山沟里来。
穿过旷野的风,吹开了春的梦,带着远方的消息,刮进小山村。乡村道路“村村通、户户通”的政策像雨后彩虹,把党和人民紧紧连在一起,把城市和农村紧紧连在一起。
父亲一声令下,兄妹六人全部到齐。夏日的夜晚,我们围坐在院子里的石桌旁。
“今天把俺孩们叫回来主要是说说咱家门前这条路的事,虽然这条路大伙都要走,可坡的起点在咱家门口,咱不领头谁领头?”父亲喝了口水接着说,“你大姐年纪也不小了,不算她,就你们兄妹五个再加上父亲,咱有钱的出钱,钱紧巴的出力,修好咱门前这条陡坡路。”父亲的语气非常坚定。
我们兄妹几个,除了大姐和二妹没有上过大学外,我们四个全是大学毕业,是全村出了大学生最多的家庭。小妮在城里的中学教书,我们弟兄三个全部在城里的大企业工作,我和二哥还是各自企业的骨干。
“爸,我看修路这事我们兄弟三人包了,你和姊妹们就不要参与了行不?”大哥带头说出了我们的意思。
“不行。”父亲语气更加坚定,“你姐妹们可以不参加,我必须干,我不但要出钱,还要出力,我这把老骨头还能干得动。”
我们心里其实很清楚,“村村通、户户通”肯定会把这条陡坡路给修好,无奈父亲是个急性子,他想自己动手修好这条带给他无尽思念和痛的小路,为了坡顶上住着的老邻居,更为了我的母亲……
开工那天,左邻右舍几乎能动的都来了,拿着铁锹,扛着镐头,争先恐后地加入了修路队伍,张婶说:“修路也不是你们一家子的事,我们大伙必须参加。”
就在大家齐心协力修好门前这条陡坡小路的同时,县交通局修路的大型机械设备也开到了村里,柏油路一直修到村中央舞台。通车剪彩那天,全村就像过年一样,女人们甩着大红绸子,男人们敲锣打鼓,小孩子们在路上尽情奔跑,老人们站在坡坡上眼含热泪,仿佛在梦里。
路修好以后,村里年轻人有的买了摩托车去城里上班,有的买了大卡车跑起了运输,有的还买了私家小轿车。村里的农作物,猪、牛、羊,果园里的水果再也没愁过销路。山村的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哎呀,哧溜一下就到城里了!”张婶用比平常高八度的高音开心地和父亲说。
村中央的舞台前修起了水泥地大广场,安装了好多健身器材,孩子们占据着广场中心位置,溜旱冰、骑小自行车,玩得不亦乐乎;小超市门前、凉亭下面成了老人们谈天说地的最佳聚集地;仿古长廊下女人们一边绣着准备出口展销的鞋垫,一边叨叨着谁家老婆最近又胖了呀,谁家儿媳妇减肥成功了呀这些“闲事”。打扑克,下象棋的“争论”声常常把父亲吸引到这里。
村里的小洋楼像雨后春笋拔地而起,父亲坐在大门外,看着张婶穿得花花绿绿,手里还拿着粉红色的绸子扇,一扭一扭地走过来。
“哼,老了老了越没个正形了,看你那嘴,抹的就和刚吃了生猪娃儿一样。”父亲撇着嘴嘟囔的同时把头转到一边。
“呦呦呦,看他大爷说的,俺还不到八十岁,你就笑话俺扭了?老张他嫂子今年九十了还在广场扭秧歌呢,嘴抹得比俺还红哩。”张婶走出去几步,又返了回来。
“俺年轻时候没扭过,不是俺不会扭,不想扭,那会儿肚子还吃不饱,咋扭?”
“现在好了,俺们赶上了好时代,俺们就要扭,还要唱哩。我看你是眼气了吧,要不咱一起去?”张婶声调像梆子戏里的道白,说着说着随手还用绸子扇轻轻地在父亲头顶敲打了一下。
父亲慢慢地抬起头,眼里含着泪水,呆滞地盯着张婶。
张婶瞟了一眼父亲,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她为刚才的话感到后悔,然后便急匆匆地走了。
父亲老了,有好多的事记不起来,眼前的事也是转眼就忘了。
下雨天仍然会摆出家里坛坛罐罐去接雨水,他忘了家里早已安装了自来水管。偶尔去他的果园看看,回来的时候总要捎一把“甜苣苣”。他忘了孙子外孙都在城里,早已不再吃那些过去的“宝贝”。冬天外出散步发现路边的柴火,回来的时候总要抱上一捆,他忘了小别墅里早已安装了电暖器。
父亲确实老了,保险公司上门服务,给老人们发放养老金的时候,父亲竟然给人家拿出了早已过期不用的医保本。村里给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发放福利,白面、大米、油、鸡蛋,父亲一次又一次的提着给村委会送了回去,说自己家里多了,根本吃不完。
父亲没老,他知道孩子们忙,虽然心里想让孩子们回来多陪陪他,可嘴上还是会说:“俺孩们忙哇,你们忙着,我心里踏实。”
父亲其实没老,他自己做饭,自己洗刷,自己照顾自己,自己能做的事绝对不会用人,哪怕是自己的儿女。这一点和母亲极其相似。他能清楚记得每个孩子的出生日期和出生场景,就像看过的电影,讲了一遍又一遍。他能准确地说出母亲的生日,唯独记不住自己的。
雷雨停了,月亮从厚厚的云层中挤出来,贴在天窗上静静地看着熟睡的父亲,像是在替刚才的风雨道歉。掖了掖父亲的被角,我趴在了父亲身边。
“三儿,三儿……”父亲的呼唤把我从睡梦中叫醒。
“你咋趴在这里睡着了,着凉了没?”
“没事的,我喜欢睡在您身边。”
说完这样的话,我两耳发热,就像小时候偷吃了玉米面饼,母亲问起时脸红扑扑的。
读完大学,在城里参加了工作以后就很少陪父亲,更不用说和父亲一起睡了,从来没问过父亲喜欢什么,也没有真正的琢磨过父亲想什么,需要什么。人常说“养儿知母恩”,不惑之年的我也有了自己的孩子,可一直觉得还是没有读懂我们的父母。
吃过早饭,父亲说:“三儿,今天天气不错,我想出去走走,你准备一下陪我去吧。”
“初升的太阳红彤彤,照在身上暖融融,洗过的天空蓝莹莹,朵朵云彩白灵灵,人间最美四月天,出门找我的情人人”。我一边擦车,一边哼唱着家乡小调,在大门外等着父亲。
“三儿,放下你的车车,今天咱出去走走”
“走走?”
“嗯,走走。”
“爸,去哪里?”
“村口。”
扶着父亲慢慢地下台阶,门前的这条陡坡在父亲的带动下修成了一条十几个台阶一个平台那样比较宽敞的阶梯形,后来县交通局又给加装了扶手护栏,往下掉人事件再没有发生。
其实“户户通”工程开始后,村里在我家院子的西面另开了一条能走汽车的路,直通百十米之外的广场,可父亲今天就是要走台阶。
“三儿。”走到“正路”的一半时,父亲轻轻地叫我,“还记得今儿是啥日子不?”
父亲问得很突然,我一点心理准备也没有,努力地回忆着今天是什么特殊的日子。
我搀扶着父亲,就像当年母亲挽着胳膊送父亲去城里做活儿一样。
我的搜索引擎卡住了,问父亲:“今天是什么日子?”
“唉!”父亲叹了口气。
“儿啊,今天是你母亲的忌日呀。”
母亲刚走的几年里,我能记得母亲的周年,后来大姐说父亲每到母亲的忌日这几天,都会很伤心,所以我们商量着不在父亲面前提起母亲的忌日了,近三十年过去,我几乎忘了。
不知不觉陪父亲走到了村口。
“爸,咱就走到这里吧,再走就上了通往县城的大路了。”
“哦,”父亲的回答比较吃力,毕竟八十多岁了,“我老了,累了,走不动了。”父亲的语速慢的几乎连不起来,一个字拖着一个字,我的眼泪在眼眶里打着转。
“爸,我背你走。”
父亲枯糙的双手交叉着搭在我的胸前,余光扫过他手里捏着的照片,是母亲的照片。
父亲歪着头,靠在我的肩上,我努力地控制着泪水。这样的场景曾多次出现在梦里,不过不是我背着父亲,而是父亲背着小时候的我。
“儿啊!”
在我的背上休息了一会儿,父亲声音比刚才有力了些。
“哎。”
“把鞋脱了。”
我疑惑着,我怀疑自己是否听清了父亲的说话。
“把鞋脱了吧。”
这次我听得真真的,父亲要我把鞋脱了。
“儿啊,咱光脚走他八里地。”
我光着脚,背着我的父亲母亲走在平展展、光油油的马路上。北方的四月很少开花,特别是路边的小花就更少。
“儿啊,你看路前面坡坡上那是什么?”
抬头顺着父亲手指的方向看去。我看到了似绿还黄的坡上野草。
“那是花儿,黄的、红的,还有白的。”
“看到了吗?”父亲问我。
“看到了,那是花儿。”
“那是你母亲在向我招手。”
“花儿,花儿。我看见你了,我来了”
父亲在我的背上睡着了,很安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