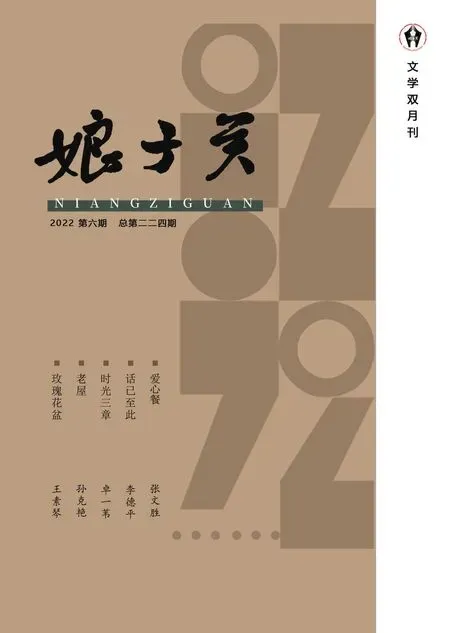老 屋
◇孙克艳
我的童年一分为二。而在上世纪80年代,住在老屋的那几年,是我人生中最恣意畅快的时光,也是最喧腾热闹的日子,更是一大家子四世同堂的岁月里最齐整的光阴。
“老屋”,在我们老家,有三个意思。
其一是故居、老宅,这也是当下最流行的说法。
其二是棺材,大约是缘于它是人老去后最终的归宿吧。从我记事起,我姥(曾奶奶)用作“老屋”的几块上好的寿木板,就一直存放在我家的杂物间,并从我幼时出生的老屋搬到我家新房的二楼。
其三,它是一种指代,是狡黠的村民创造的貌似隐讳却油滑而直白的称呼。从我慬事起,我就知道,“老屋”是我父母和叔婶们对我爷奶的称呼。“老屋让兑钱了”,“给老屋端一碗扁食去”,“老屋真样儿稠”……这些语句的主语,都是我爷奶。
他们老两口好像捆绑在了一起,不分彼此,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有好处时一起接着,有风雨或污秽时也一起迎着。或者,更多的时候,我觉得温和柔顺的奶奶只是爷爷的附属,她鲜有自己立场鲜明而坚定的主张,更没有什么特立独行的言行。因为奶奶不当家,也没有话语权。甚至,她连名字和姓氏都失去了。从我记事起,大家就叫她“克艳她奶”,或者“你们老婆子”等等,从未有人喊叫过她的名字,好像她就不曾拥有过名字一样。所以,每当我听到别人和我妈窃窃私语,说“老屋呀,真是……”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往往是我爷。
深究一下,便觉得老屋的这几个意思颇值得玩味,带着丰富的文化兴味和语言传统,甚至还隐含着强烈的人情世故。
而我印象中的老屋,是连成一片的老宅,包含了我家、我爷家和我三叔家的大院子,是一个躺倒的“目”字。我家在东边,东房和灶房之间留了一条一米多宽的过道,对着正东开着一扇不甚宽阔的大门。我家西房与爷爷家的东房相邻,并有一堵低矮的土墙相隔,土墙上爬满了奶奶种的仙人掌,并开了一扇小小的木门。
爷奶家夹在我家和三叔家中间,爷爷家的灶房和三叔家的灶房共用了一面墙。于是,那两座灶房恰好起了分隔门户的作用。爷奶家的灶房北山墙与三叔家的东房间留了一条一米多宽的过道,正好与我家留下的过道相呼应。
那时,我家的房子已有50多年的历史了,是我老爷(曾祖)盖的。而我爷奶家的房子,则是他们自己盖的,也有30多年了。那两座老房子,屋顶上都长着瓦松、狗尾巴草等杂草,彰显着浓烈的沧桑感。
三叔家的青砖瓦房,是爷奶盖来娶儿媳的,自然比我家和爷奶家的老房子气派多了,不仅高大崭新,地理位置也相当优越。开了院门,就是村里的主干大路。路边,正好是村里堰河的发源地,四季水流不断,清凌凌的,宛如一条碧色的绿带环绕着偌大的村庄,为村庄增添了鲜活的灵气。堰河流经的人家,都要在河里栽种一些植物,比如莲藕、芦苇、菱角等;或者在岸边养一些花草,诸如竹子、指甲花、美人蕉等;有的人家,还要养一些鸭子或鹅。因河水清澈,大家除了洗菜涮衣服,还经常下河洗澡。
一向喜欢排场的三叔,许是觉得自家挨着马路,人来人往的实在打眼,于是修了一堵红色的院墙,和颇有派头的楼门,楼门上还坐着两只青色的兽,威武极了。相比之下,我家和爷奶家的老屋,实在磕碜,简直有点“自惭形秽”。
这还不算完。三叔家的房子屋檐下,还修了一排精致的鸽子窝。那群神气的鸽子,不但有得体的窝,还有用青砖铺就的走廊。年幼的我,时常仰着脖子看着鸽子们肃穆地端着架子,在它们的廊道上一边“咕咕”地叫着,一边不紧不慢地走来走去。看它们神采奕奕的模样,简直像电视上那些拄着手杖的英国绅士。至于鸽子们吹着鸽哨,像一片快速移动的云在蔚蓝的天空中翱翔的情景,就更令人振奋了。小小的我,在心中萌生了一个强烈的渴望:希冀在未来的一天,我也可以像鸽子那样自由舒展,那样优雅自在。
鸽子是三叔养的,自然全权由他处理。不过,三叔家屋后那棵高过屋顶的老枣树,却是一大家人共有的。每到中秋前夕,红枣挂满枝头时,大人孩子打枣的成果,是要平均分了的。
我家的老屋相当古旧。墙身是灰色的老砖,瓦片是黑色的,它像一张穿越岁月河流的黑白照,显示着光阴的痕迹。它虽然低矮陈旧,却冬暖夏凉。睡觉时,每每抬头仰望,便可看到陈旧的黑色檩条上挂着的蜘蛛网轻轻摇曳,和簌簌而落的灰尘,以及蛀虫蚕食木头后的排泄物。无聊的我,每每仰望屋顶时,看到那些纵横交织的房梁和檩条,心中不免疑惑,那些历经风霜的木头,怎么就那么安稳呢?默默无语的它们,已然见证了一个家族从人丁凋零开枝散叶到繁盛的四世同堂,它们都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它们所知的秘密,大概比所有曾经住在这里的孙家人,都要多吧?而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又会以怎样的形式透露出来呢?
冬天的夜,总是来得特别早。躺在床上,听着窗外呼啸而过的北风,听着父母讲述孙家祖辈的故事,我在漆黑的夜里,总是瞪大眼睛,想要搜索这座老屋的每一寸土地,企图拥有孙悟空的火眼金睛,只扫一遍,就能从某个旮旯里挖出祖宗埋藏的宝藏。可惜,我不是天选之子,并不曾在某个时刻拥有某种特异功能,也不曾遇到什么能人异士,更不曾享受万众瞩目的高光时刻。我像老屋一样,慢慢地经受着风雨的洗礼与侵蚀,慢慢地长大,逐渐认识到一个真实而残酷的现实:我和这座老屋一样平凡,并终将被时光雕琢。而当我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老屋早已湮没在时光的河流中了,我甚至早已忘记了它详细的模样。它在我心中,只剩一个大致的轮廓,不明晰,不具体,像一个模糊的壳儿。
老屋木材雕花的窗户过于狭小,导致室内光线不足。东屋的卧室和灶房相邻太近,而西屋的窗外又矗立着一棵高大茂密的榆树。因而,即使是在晴天白日,卧室里也晦暗阴沉,一如老屋沉闷孤寂的格调。那时,为了改善室内光线不足的情形,有些老屋的房顶会开辟一片天窗,实用又富有奇趣。我也曾抱怨老爷当初盖房子时,缺乏深谋远虑,完全不懂得孩子们的心思。若是我家房顶也有一扇天窗,那该多好呀!
说起来,我对老屋最深刻的印象,反倒是堂屋的墙壁上挂着的一组画。中间的主画隐约是幅精致的工笔山水,两侧各有一对条幅,组成春夏秋冬四条屏。条屏上的花草有着鲜明的季节特征,可爱伶俐的猫咪与图画上的花草相得益彰,漂亮又不失灵动。这是国画对我最直接最深刻的熏陶:季节的变幻,世界的丰富,生灵的鲜活,全都呈现在眼前。无聊时,我或坐或站,眼睛总在那几张条幅上切换,不知为何,年幼的我,心中涤荡着满满的欢喜与恬静。
此后多年,我再也没有见过如此打动人心的图画了。不管是在邻居家还是在亲友家,我都没有看到过那样令人喜爱的中堂画了。搬到新家后,我家的中堂画也跟着潮流换了又换,从纸质到玻璃面,从伟人画到风景画。然而,这些画不但没有突破以往,反而不断挑战下限,实在令人赧颜。直到我在少年时,偶然看到张大千、林风眠、齐白石、吴冠中等巨匠的作品,这才算是洗了眼睛。我在被艺术的魅力深深折服的同时,不禁沉思一个问题:在家庭教育中,美育教育的普遍缺失,实在令人遗憾。它就像天窗一样,看似微不足道,却能在时间的浸染与沉淀中,为孩子们开启翱翔太空的翅膀。如此说来,我曾抱怨老爷不懂晚辈的心思,大概也不算狂悖吧?
不过,每日清晨,被老屋房后水压井畔“叮叮当当”的压水声,和人来人往的嘈杂声吵醒,却是令人烦躁又深觉安稳的日常。那时候,很多人家没有钟表,更没有手表,只要在清晨听到有人打水的声音,或者说话的声音,或者公鸡鸣叫,就知道该起床了。乡村生活不用对时间计较得那么严谨,大差不差地估摸着就行了。那几年,一听到水井边的声响,我妈就在被窝里踢我爹一脚,让他起来挑水,她则忙着做饭、喂牛等杂事。
大人们在忙碌的时候,我和弟弟总是在院子里溜达,一会儿跑去爷奶家,一会儿跑去三叔家,这儿摸摸,那儿看看。问问这,说说那,要把一大家子的日常都捋清了。今儿谁家要改善,明儿谁家会来亲戚,都打听得妥妥当当的,以便安排好我们总是馋着的嘴巴和肚子,捞点油水,犒劳下馋虫。
那时,饭菜的香味越过墙壁,随风飘逸,在院子里弥漫,飘摇,引逗着我和弟弟追着香味去寻觅。寻到根源时,我和弟弟就倚在爷奶家或三叔家灶房的门框上,眼睛巴巴儿地盯着灶台,不舍得眨一下眼,生怕错过了美味烹制的一刹那。似乎,在孩子眼中,观看美食从生到熟的过程,也是一种享受,它既能延展享受美食的前奏,又能拉足品味美食的气氛。自然,也只是在这座骨肉相连的大宅院里,我和弟弟才如此释放天性。出了这座宅院,那样掉价的事情,是万万不能的,否则被长辈们知道了,是要挨批的。毕竟,内外有别。
每到饭点,大家都先后端出饭菜,蹲在院子里,一边吃饭,一边闲聊。吃嘴的孩子们,总是一边端着饭碗,一边悠悠地晃来晃去,盯着与自家不同的饭菜,睁大眼装傻:“这是啥?”大人们自然瞬间洞穿馋嘴孩子的心思,微笑着回复后,使劲挑起几筷子饭菜,放进贪嘴的孩子碗里:“多吃点!吃百家饭蹿个儿!”
哎哎哎,说起来,这样丢份儿的事情,我也没少干过。不过,除了孩子们,我姥也干过这样的事情。那时,已经七十多岁的姥,虽然仍能自理,但是却没有一颗牙齿。空瘪的嘴巴,导致她能够进食的食物相当有限。于是,馋虫上来的时候,我姥就偷偷地溜进我家的灶房里,做点吃食,解解馋。可惜,一生清苦的姥,厨艺实在不敢恭维,她做的吃食,我总吃不下,比如水煮萝卜和土豆。好在,儿孙们都很孝顺,但凡有人上街或出远门了,总要给姥捎个适合她吃的零嘴,香蕉了,米花了,薄荷糖了,芝麻糊了,麦乳精了……把她当成孩子一样宠爱。
晴朗的日子里,姥喜欢坐在我家院子里,让我妈帮她洗头。解开脑后的发髻,姥那头花白的长发像贫瘠的庄稼地,稀稀拉拉地随风飘荡,犹如柔软的柳条。
洗好头发后,姥坐在椅子上,脱下她那造型别致的鞋子,散开裹脚布,耐心地清洗她的三寸金莲。顽皮的孩子们,总要趁机试试姥的鞋子,和她比试脚掌的大小,并在一片嬉笑中谈论姥的小脚。
面对晚辈们的质疑和疑惑,姥总是耐心地一一解答,她时常不停地咂嘴,感叹我们这些晚辈赶上了好时候,不必遭受他们曾遭遇的苦难。
姥的话,我不能十分理解。我一直不明白,她那双比我还小的脚掌,如何支撑着她的身躯,不仅能使她像不倒翁一样不摔倒,竟还能走亲串户、下地干活、操持家务。这,简直可以收录进十万个为什么了。不过,孩子们的禀性,往往是好奇,不求甚解。联想到很多村里的老太太都是小脚,似乎我姥的小脚,也没那么特别了。
孩子们散开后,姥独自躺在树荫下的躺椅上,一边晾头发,一边打盹。她干瘦矮小的身躯,像一段枯朽的木头,又像一只吐尽丝线的蚕蛹,干瘪而丑陋。谁能想到,这个可怜的小脚妇人,在丈夫早逝后,一个人拖着一双儿女,穿过抗战的硝烟,越过无尽的困苦,硬是凭着顽强的韧性和勤劳的双手,在一亩三分地里刨食,将一个人丁凋零的家庭撑了起来。姥的故事,在她逐渐流逝的韶华里,在她无法消弭的皱纹里。
那时,我总嚷着让姥给我讲故事。然而年幼的我却不知道,迟暮之年的姥就是一本行走的故事书。我想,即使她讲了,我也听不懂。何况,小孩子哪里坐得住。我总是惦记着吃喝,惦记着玩乐。更多的时候,我总是飞出院子,呼朋引伴,变着花样地玩耍。
那些年,老屋周边多的是与我年纪相仿的孩子,随便一招呼,就有玩伴。快乐与热闹是主打曲,刻骨铭心的疼痛也是有的。就是在老屋,我经历了人生最惨烈的暴揍,被我爹拿着棍子追着打。怎么回事呢?
那天,当我在闷热的午后醒来时,尚在癔症中。聒噪的蝉鸣,和饥饿的肚子都令我烦躁。我端着我妈递到手上的蒸面条,坐在东房与灶房的过道里,迷糊地吃着。这时候,奶奶摇着蒲扇过来了,她蹲在我身前,半真半假地对我说,她想尝尝我妈的手艺。我把筷子给了奶奶,她毫不客气地吃了起来。许是那天的蒸面条太好吃了,奶奶吃了一口又一口。这行为偏离了我所以为的“尝”,于是哭闹起来,还在气结中骂了她。
我爹正在东房睡午觉,透过窗户听到后,他随手抓起一根棍子,就朝我打过来,我妈和我奶都拉不住。棍子像雨点似的不停地落在我身上,也许还有拉架的我妈和我奶身上。我不知费了多大的劲儿才从我爹手上逃脱。谁知,他竟举着棍子追着我不放。无奈的我,所能想到的办法,竟是像毛毛虫一样,绕着我家的大宅院,从东门跑进西门,穿过三座房子,再从东门逃进西门……我在前面跑,我爹在后面追。这一幕,恰好被一个老汉看到了,老爷子笑着冲我呐喊:“跑快点,就要撵上了!”
最后,跑掉鞋子的我实在跑不动了,累瘫在我家晒得滚烫的院子里,边哭边求饶。不料,我爹还在气头上,即使他已经打断了一根棍子,仍不觉得解气,还想暴揍我。我妈又急又气,大约是哭了。我奶也在不停地拉扯,解劝我爹……很快,一大家人都被惊动了。
从此以后,懵懂无知的我说话办事开始过脑子了,并知道要遵守一些隐约的规矩,不再跟随一起玩耍的小伙伴们胡言乱语了。他们可以说脏话,可以学着大人们的腔调胡咧咧,甚至是骂长辈——用稚嫩的腔调骂他们是“老东西”“老不死的”,尽管他们并不懂得那几个字的意思和分量,不过人云亦云罢了。我不行,我被打怕了。从此,我再也没有辱骂过我奶,还成为爷奶的心头肉,成为他们心中嘴上的孝顺孩子。家里有什么好吃好喝的,我总是惦记着给他们送上一份。
长大后,再回想起这件事,我不禁有个疑问:那时我爹三十来岁,正是青春繁盛的时候,他为何竟追不上一个五六岁的孩子?也许,他是想在朗朗乾坤之下,当着众人的面狠狠地给我一个教训,让我在持续的慌乱恐惧中,让我在逃跑和挨揍的惊悸中,牢牢感受铭肌镂骨的滋味,让我知道他不可撼动的底线和原则,让我知道纵是孩子也要遵守的准则吧。甚至,他是想借着打娃的机会,狠狠地敲打村里的某些人,比如我鹦鹉学舌的源头,我目无尊长的苗头。
后来,在多年的生活细节里,我赫然发现:我爷对我姥的照料与尊重,跟我爹对我姥和我爷奶是一样的。小学时,我因偷吃了一根我爹买给我姥的香蕉,竟惹他发了好大的脾气。这件往事,我曾写在《香蕉、苹果和桔子》一文里。在“香蕉事件”上,我曾深深地抱怨过我爹,觉得他这个长孙简直把他奶奶宠成了老小孩,我心酸,我嫉妒,我不能理解。直到我更大一些,知晓了我姥这一生的曲折悲苦,知道了她对家族的付出与奉献,知道了她对我爹的疼爱,知道了我们曾经住过的老屋也有她的辛劳之后,我才慢慢明白了我爹的心思。
长辈们用一砖一瓦,用汗水和心血打造的新房,是晚辈们开启新生的起点。修筑老屋的人,总是在家庭细胞分裂之后,主动成为被老屋驱逐而出的人。直到岁月将长辈们健硕的身躯雕刻成易折的弓,直到他们在光阴里丢失了自己的名字,变成谁的父母或爷奶,成为“老屋”,他们的使命才算完结。不过,就算新房变成老屋,那里仍然不是他们最后的归宿。他们最后的希冀,不过是几块厚重的木材打造而成的小小棺椁,好湮没并埋葬他们平凡却不平淡的一生。而这样根深蒂固的传承,宛如命运的齿轮一般,深深地刻在人们的血脉之中,传了一代又一代,生生不息。
洞悉了这些以后,我就懂得了我爹,也懂得了我爷奶和我姥,并明白了我姥和我爷奶能熬过漫长而苦涩的岁月,以微薄的力量撑起四世同堂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