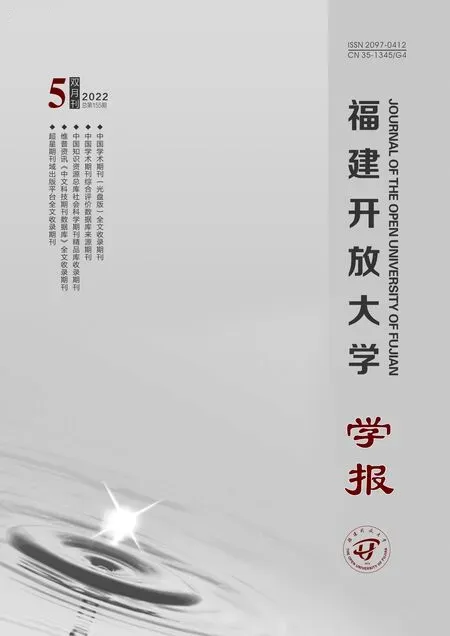探究方笔线条之于中国人物画的影响
——以陈洪绶为例
陈晓婷
(福建开放大学,福建福州,350013)
一、中国书法与传统绘画行笔方式的渊源
中国书法有别于西方艺术形式,是一种包含了中国独特传统文的艺术表达,其本身在于强调运笔线条的变化。而中国传统绘画所描绘的技法,也大多为各种线条的表达呈现。因此,在中国从古至今的艺术家口中,一直流传着“书画同源”的说法。唐张彦远于《历代名画记》中言:“是时也,书画同体而未分,象制肇创而犹略。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无以见其形,故有画。”[1]北宋画家文同在台北故宫和北京故宫各有一张“墨竹”,“墨竹”在北宋成为绘画主题,明显是用书法的撇捺笔法线条来入画。南宋赵孟頫著诗:“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2]明朝何良俊则说:“夫书画本同出一源,盖画即六书之一,所谓象形者是也。”清代董檠认为:“书成而学画,则变其体不遗其法,盖画即是书之理,书即是画之法。……书道得而可通于画。”这从历史上,说明了中国书法与传统绘画二者“同源”。
中国书法和传统绘画上的线条美是共同的、精神本源上是可以达成相互沟通的。书法家用点线构建出一个个文字,而绘画则是相同采用点线再搭配色彩来实现画家脑海中所要描绘的或真或虚的形象。而无论是书法还是绘画,运笔时注重水墨的轻重疾徐、浅深疏密、浓淡干湿、曲直正斜、聚散开合、虚实顿挫等变化却又不会相互冲突,在成品整体上达成和谐统一的韵律。苏轼有言“执笔无定法,要使虚而宽”,故可言二者“同法”。而所谓拟形于翰墨,在于其抽象之理。书画源于本心,二者均是由人以心为审美本体不断追求最高艺术成就而形成的。书法笔法少而变化多,绘画形态多而变化少。书法的以手执笔技法比绘画所需的难度更高,所写篇幅越长,书法家受制于手臂与腕部结构下笔越难以统一。而绘画线条相比书法则明快准确且丰富多样。二者研究对象不同,艺术媒介不同,在本质上也不尽相同。所以二者“同形”。千百年来,中国书法与传统绘画之间相互融合,互相促进,吸收对“线”运用的技巧并发展,最终互相成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极为重要的地位。
二、方笔线条之于中国人物画的艺术功能
因古往今来书法大家在兴趣、习性上的各不相同以及自身每个时期所处际遇的变化,在他们作品上往往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差异性和倾向性。反映在线条使用上,就会有人擅长法度严谨的唐楷,有人喜爱雄峻非凡的魏碑,有人迷恋遒劲郁勃的行书,有人痴迷放纵不拘的狂草。而方笔从汉隶时开始,其露锋折笔逐渐取代了春秋战国时期篆书的藏锋转笔,成为书写文字的主要特点之一。随着时代的变迁,方笔又融合了隶楷、魏碑不断发展,形成棱角分明、锋芒犀利、雄奇磅礴的笔法特征,往往寥寥数笔的线条就勾勒出立体感、节奏感和韵律感。
中国绘画最高技艺向来以塑造人物为首,花鸟鱼虫次之。中国人物画传统在于采用水墨线描的技法和人物形神兼备的境界两点。明清以前,传统人物画在表现内容上较为狭窄,人物画大多承载了教化功能。故该时期画上不是帝王贤臣、就是孝子贞女、文客雅士这些可以达到劝谏观者提升自我道德修养的标杆型人物。比如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和《洛神赋图》。这类作品主要采用圆笔线条,构图较为单一,画中多数留白刻意放大了主要人物形象,并搭配诗书体现教化与引导世人的主旨,形成了绘画上的模式化运作。明清时期,社会经济繁荣并且西方思想艺术流入中国,人物画逐渐摆脱原本教化功能,开始凸显人文尊重和主流审美。作画上追求既写实又不乏趣味,使得艺术家对笔墨造型的语言赋予了新的内涵。同时,当下流行的“高古”即对过去造型的继承来缅怀伟大朝代的作画主题,更将人物画线条偏好逐渐从圆笔过渡到了方笔。方笔线条神态美在于其笔型外拓富有阳刚、给人一种方严凝重、精气结撰、雄强峻利之感。明代邹德中《绘事指蒙》中记载“描法古今一十八等”,[3]其中具有方笔属性的线条就有钉头鼠尾描、橛头钉描、折芦描等。其中“钉头鼠尾描画法画有大兰叶小兰叶两种,皴法如写兰叶法。”线条叶顿头大,行笔方折刚劲,转笔粗如兰叶描,收笔尖而细。“橛头钉描画法用秃笔坚强挺拔中要舍婀娜之意最忌粗俗”顿头大而方,侧锋入笔,有“斧劈皴”之笔意,线条粗而有力。“折芦描画法此由圆笔转为方笔之法,仍须方中有圆,用隶法为之”用笔粗且转折多为直角,折笔时顿头方而大,线多为直线。[4]方笔线描画法通常采用中锋、侧锋与逆锋等方式来表现画面,是常用的一种技法。作画时直握着毛笔,笔锋持续位于笔画中心位的状态,以达到用笔灵活有弹性,线条细致有力量的目的。侧锋也属于运笔的一种形式及方法,持笔侧向下落,则水墨犹如人卧偏侧的姿势,以此让线条增添出方硬柔美的神情,也使写意人物画线条更为灵活、生动。此外,逆锋也是方笔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方笔不同于斜切的顺锋露锋,在落笔发力时笔锋先逆行而后转回形成方头。在作画过程中,中锋、侧锋、逆锋这三种笔法经常运用在写意人物画之中,任何一种笔法都不会被孤立使用。简洁粗犷的绘画线条变化丰富,能够区别于过去的流派,是当时艺术家所追求的标志体现,从而使得该时期人物水墨画中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构图大气磅礴,内容高度提炼、画面生机勃勃。方笔人物画精于形,重于意,成为明清绘画的主流之一。
三、方笔线条的行笔在中国人物画中的表达——陈洪绶
陈洪绶是一位个性鲜明且艺术风格独特的书画家和诗人,他在人物画中重视方笔线条的和谐之美,用线果敢大胆且精炼,擅长从方笔书法之中提炼出线条的力度与质感。可以说,他对方笔的运用已达当时的顶峰,这是继顾恺之之后中国人物画历史中又一座高峰。他不仅成为了明末清初时期的领军人物,而且他对后世的国内外各种绘画流派也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一)少时成名的早期
陈洪绶(1598-1652),字章侯,浙江绍兴府人。出生于官宦世家,祖父更是做到了明朝布政史一职,但他父亲陈于朝未能中举且在陈洪绶9岁时便撒手人寰。但陈家仍家境殷实,陈洪绶幼年时就展示出其优秀的绘画天赋。4岁时在岳父家墙上画出关公像更是让家人震惊;10岁时,拜明代著名画家蓝瑛与孙杕为师,其才能让老师们赞叹不已;14岁,陈洪绶已小有名气,悬画市中众人疯抢;21岁画坛盛名,外乡人慕名来求画。
陈洪绶早期受李公麟《七十二圣贤图》的影响,追求“高古”。人物线条刚柔相济,古雅细劲,绘画用笔高超、讲究工整,笔锋处处圆中见方。其《九歌图》以方笔为主,画面大多为单一人物,点线之间顿挫有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屈子行吟图》绘出屈原高冠博带,身着广袖宽衣,一人愁眉锁眼地徘徊在荒野,犹如凝望着故国山河。背景中的怪石、树影以及野草衬托出萧瑟幽寂的景象,同时人物身上衣纹的褶纹富有质感,腰间飘带更是渲染出人物独行落寞的心境。陈洪绶仅通过简练的线条勾勒、技艺高超的构图结构和面部神情的捕捉拿捏,便塑造出了屈原表面凄苦悲凉,又双关了其内心忧国忧民的情感。总体而言,其早期人物线条是“几次摹写而变其法,变圆折为方折,变整为散”,方中有圆,圆中亦有方。但早期的他依旧只是在学习前人的画法,还没形成完整的方笔风格。
(二)命运多舛的中期
陈洪绶走上了封建士大夫子弟们一贯的人生道路—考取功名。但此时明朝已日落西山,他求取功名多年,却同他的父亲一般屡试不第。43岁终于被授中书舍人,供奉内廷。陈洪绶在无法接受官场的世态炎凉后直接辞官回家。
陈洪绶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从内容与意境上都与其早期绘画作品有了鲜明的不同。他摒弃了青年时代细腻精致的笔触,追求古之意蕴而不拘用古之法,线条开始追求有棱有角的转折,用短粗且顿头结实的钉头鼠尾描绘制人物。起笔时执笔靠笔毛自身的弹性去保持中锋状态后,收笔时在四面转动形成顿挫感笔触,这种线条起承转合的变化中凸显出方笔线条的饱满感。故而笔下人物身体大都扭曲形变、手势夸张异常,整体表现具有个人色彩极高的辨识度。以《对镜仕女图》为例,画面背景用墨线勾勒出的树石衬托并突出了中间襦裙高系的女子,布局疏密得当,再搭配女子身上深色前襟和线条细劲的纹路予以视觉冲击,刻意将对比的效果放大,突出主题。两年后他为姑母庆贺所作的《宣文君授经图》画力更是上升到新的一个台阶。他将主要人物宣文君,青绿山水屏风以及夸张变形的青铜樽放置在同一轴线上,同时人物衣服纹路均一连到底,未有折挫不见停顿;各个人物神情得体,凝意其中,尽无任何松懈,足以道明陈洪绶该时期对方笔画高超的控制力。
陈洪绶方笔人物画不仅表现在水墨画上,其木刻版画也是一绝。在各类刻本中,他的版画向来是收藏的首选。《水浒叶子》是陈洪绶花了4个月为其朋友周孔嘉所绘的版画,他完美地刻画了宋江、鲁智深、武松、呼延灼、阮小七等40位水浒人物。其在设计这组版画时起笔略微用劲,下笔粗短而急促,收笔较为轻,此番一气呵成,化整为散、线如钢针,线条的转折完美地显现衣着纹路的变化,使得笔下人物抱骨藏筋,形象鲜明且性格突出。美国中国画史专家高居翰评价到方笔在这里的运用应是参考了古戏曲,极具夸张地、强烈地展示出水浒人物行侠仗义,品行刚烈的特点,已完全脱离传统画人物内敛的刻板典型塑造。
(三)狂放不羁的晚年
清军南下,陈洪绶因避难出家为僧,后来即使还俗,仍在卖画之余研究佛学。陈洪绶晚年如同一个小孩子放诞不羁,一旦不顺其意就立刻翻脸,情绪起伏不定,喜怒形于色,行为跌宕乖张,但这却是他创作最顶峰的时期。
陈洪绶晚年人物作品多且精,所包含的思想意境相比少年、中年时期更加深邃。所画的人物线条细如游丝,疏密有致中又蕴含闲散神逸,衣纹古雅细劲、清圆有力、潇洒委婉、刚柔并济。而背景山石的笔法苍老洗练,花鸟精细清丽,直道自然之趣味,用笔酣畅淋漓而又疏旷闲逸,展现独特的形式之美。他同时亦在追求更高远的形式技法,用最简明的线条语言描绘出饱满丰盈的人物形象,予人一种细腻工整、至臻化境的视觉美感。51岁时所作《蕉林酌酒图》是其晚年代表作之一。所绘人物生动传神,笔墨线条细劲高古,然而背景树石却显得颇为柔和素雅,这一前一后与人物衣纹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他所创作的《博古叶子》则为其巅峰之作,在绘制这组画中选用了春秋至唐朝期间共48位历史著名人物,借助他们特殊的故事所描绘而成历史断面以表达了自己他这一生中对人生的感慨。他所设计的人物造型极具童趣,线条苍老古拙却又自然闲逸,整体上带给人浑然天成、水到渠成、铅华洗尽之感。栾保群先生曾评价这套叶子牌为“三绝”,从文字-图画-刻工皆是一流,他这个作品可以说,在继承传统同时又超凡脱俗,线条使用已至最高境界。
(四)陈洪绶人物画中的线条之于后世的影响
陈洪绶在学习、参考与归纳前辈大家经验之后,将人物画中线条的运用冲破了传统束缚、打破既有模式。陈洪绶手法上溯晋唐两宋,早期各类人物画像深受吴道子、李公麟、张萱、周昉等人的影响。但陈洪绶“师古而不泥古”,汲取前人经验后采用大胆而夸张的形变线条,在效仿前人之“高古”的同时又注入自己独到的理解,塑造了丰富多变的人物造型,形成具有个人特色的艺术风格。随着对艺术的逐渐认真,他的人物画开始受到方笔书法的影响。虽然他未以书法闻名世界,但其画作深蕴书法用笔之道,控笔稳健洒脱,恬静中悦动雀跃,充满了真义和旋律,形成了极具特色的线条之美。方笔中的中锋运行、侧锋回藏、逆锋顿挫全都为他畅爽作画而服务,在人物点线面造型中增添独特的韵律美感。
陈洪绶别具一格的风格流派将中国人物画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同时影响了后世的绘画格局。其人物画影响到了中国画坛“海派三任”所绘的装饰线条风;徐悲鸿的人物画继承了陈洪绶作画刚毅特征;白石老人的人物吸收了陈洪绶“变形夸张”技法;当代画家程十发更是在艺术主张上与陈洪绶抿合,将其作画融入到自己创新突破之中。另外,陈洪绶的线条之美也传播到了日本,对浮世绘画人物姿态与细节刻画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在浮世绘画风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陈洪绶“大头身短”夸张造型、遒劲郁勃的书法运笔线条以及丰富的装饰之美。
四、“师古而不泥古”——中国人物画当随时代
综上,在中国人物画历史发展过程中,线不仅仅是一种造型手法,更重要的是其蕴藏着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它在中国画中重要的艺术地位是不会改变的。中国画中线的初步形成到进一步发展、再到不断完善,它的发展历程足以窥见中国文化的前进过程。[5]堪称一代宗师的陈洪绶被人谓之“明三百年无此笔墨”,他寄情于笔墨,学习古人的线描方法又不拘泥于传统,年少时易圆为方,绽放出独具个人特色的线条语言,待到年老又易方为圆,何尝不是经过时间磨砺后的沉淀。陈洪绶的方笔线条之于其人物画仿佛蕴含了人生起落、沧海沉浮,“以书入画”不仅能表达画家自身风骨,且从行笔的提按顿挫亦能使人感到书法线条的节奏之美,又能“以画明志”。
亘古亘今,从明代陈洪绶到近现代任伯年,再到当代画家张立奎,从他们绘画作品中可以看出方笔线条脉络的传承与发展。从行笔角度上讲,例如张立奎无论是平静厚重感的表达或是冷暖虚实感的表达,皆“师古而不泥古”,其笔下方笔线条都蕴含着古朴率真之美。当代中国人物画中运用到方笔线条的作品,其线条藏骨抱筋又含文包质,其意蕴遒劲有力又深刻长远。随着当代传统绘画艺术主题表达向多元性发展,方笔线条对指导我们今天的中国画作品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画线条的表现空间将会更加兼容并蓄、影响隽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