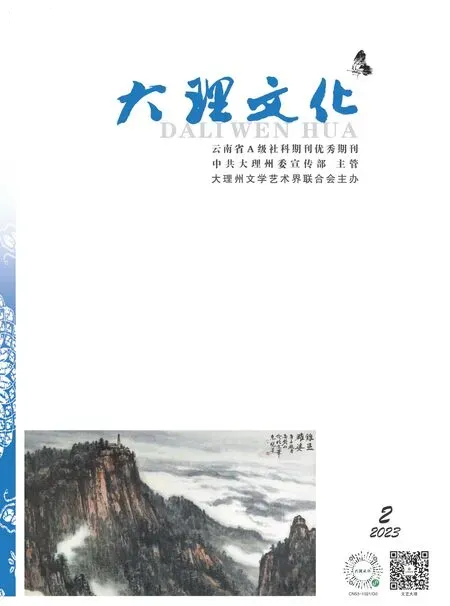安身立命
●陈苑辉
1
驱车行驶在宽阔的甬莞高速公路,我的目光不时投向更远的远方。或高或矮、静立的房屋由远及近飘移过来,最后快速跑向窗后消失了,一同消失的还有路两旁的指示牌、草地、树木以及河流。消失的房屋有各自的颜色、大小、结构与气场,它们忠实地保持主人赋予的格调。这样的消失,意味着另一端目标的靠近。
此次返乡乃受德军之邀,庆祝其乔迁新居。德军,是我二十年前的初中同学,高瘦且聪慧。9月某晚,他拨了我的微信电话,说在老家县城买了一套新房,即将装修完,入新居时邀我回去庆贺。过了几周,他又说选定了10月1日进新居。隔着手机的屏幕我能够想象出他飞扬的神情,仿佛中了一个大奖,且奖金已收入囊中。
拥有一套属于自己及家人的房子,其美妙不言而喻,我能感同身受。挂断电话后伫立阳台上,二十多年前的老屋从我脑海里浮现出来。那是粤东北的乡下,蜿蜒环绕的山岭如一条延展的手臂围拢着百来户人家,先辈迁居至此已繁衍二十代。岭臂下的居所多为泥瓦屋,墙体以土砖叠砌,或山土垒建,经过几十年的风吹雨打就沦为了老屋。
从记事起,我就居住在一幢颇具沧桑的老屋里。老屋上下厅结构,中间隔着天井,三户人家入住。后来,有一家人另起灶炉,在老屋后方建了一排厅房,他们取走了老屋右侧一房的横梁与瓦片,又削矮了两面土墙,东北角便敞开了,犹如一张裸露着的大嘴巴。雨水趁机渗进墙根,为若干年后老屋的倒塌埋下了伏笔。起先是上厅的房门隔几个月就卡住,开与关不顺畅,仿佛有一只手在暗中起反力。父亲拿出刨子,朝门板的上沿刨了刨,再往下敲打几下,那只隐形的手撤走了。接着是下一场大雨,老屋就像一艘即将沉没下去的航船,泛黄的雨水漫入大厅、房间、天井。父亲挽起裤管扛了几袋沙包阻挡在后门槛上。然后,他盯着改道奔涌而去的雨水,满脸愁容。
每一幢老屋都有自己的宿命。站立的力气用完了,它会像一棵大树倒下去,复归于脚下灰黄的尘土。父亲一有空就穿行于村庄的各个角落,寻找适合建房安居的地方。从那时起,我逐渐意识到有一座房子归属的重要性,也开始考虑一个人安身立命的问题。
如今,二十年的积攒让德军拥有了一处产权属于自己的栖身地,租房日子划上了句号。趁国庆假期,我携妻带子从东莞自驾出发,往他的小区定位风驰电掣般赶去。节假日返乡,堵车是一道无法绕开的关卡。途经惠州时,果然应验了。三车道车满为患,它们临时组成了一条逶迤几公里的巨蟒,导航中红黑的线条显示“通过时间需一小时”。德军来电话,问行至何处。我估计中午的宴席是赶不上了,叮嘱他不必等我,算不准下午何时才能到。堵在高速公路上,车子龟速般前行,我百无聊赖握着方向盘,寻思着小孩子叫德军什么呢?伯伯,或者叔叔?倏然,我眼前浮出一页纸,纸上写了几行祝福的话语,祝语下有一栏工工整整的字:“8月30日”,字体圆润、饱满,透出一股浓郁的书生气息,正是德军的笔迹。它来自于初中毕业的留言簿,红彤彤的封面很耀眼,为当年流行款式。这么多年过去了,它究竟压在哪个箱底?或被老鼠干掉了,还是误当垃圾扔掉了?若干年后的某一刻,我竟会突然忆起那些钢笔字,它们似乎一直在等待某个潜意识的召唤,令人倍感诧异。
下午三点多,我们才抵达县城。一下车,德军跟我来了个拥抱。毕业二十余年,我们见面的次数屈指可数,他还是老样子,高瘦,五官清秀,手臂修长,唯一不同的是脸颊上趴了些短须,看上去增添了中年男人的几分魅力。他喜上眉梢,脸微红,说话依旧客气,用词精准、得体,三两句便说到人心坎上。尽管来不及参加他家热闹的喜宴,但彼此的情分在、情谊在,也不会计较。下午五点多,他家人张罗了丰盛的晚餐,客家口味,亦有海鲜加持,摆满了一大桌。席中,与其父亲、弟弟四人小酌了几杯。

作为一个一毕业就扎根在农村小学兢兢业业的人民教师,德军的工资不算高,却靠着细水长流、积少成多的谋划,在县城大房地产公司开发的小区买了房,他解嘲为实现了一个小小的理想。他的眼神写满了谦逊、坚毅与执着,一如当年。
2
一直聊至夜幕徐徐落下,窗外亮起了点点灯光,轻轻映照着静谧的、灰暗的夜空,我们才依依不舍离开德军家。他反复诚恳地说着谦辞:“只要你回来了,务必过来,粗茶淡饭随时都有。”除了握紧他的手,我还能说什么呢?
我喝了少许白酒,妻子坐上了司机的位置。汽车谨慎地行驶在回村庄的乡道上,弯道开始越来越多,路面变窄,两旁黑漆漆的,偶见山峦轮廓向后移。女儿说,我们这些大人也跟小孩子一样,见了面就拥抱、握手。我和妻子听了,笑了。妻子说,你们俩同学的性格、穿着、动作太像了,很淳朴、真实,你们的关系令人羡慕。
在汽车的颠簸与呼呼风声中,我斜躺在副驾位上闭目找寻着一幕幕过往。
最近一次与德军见面,在2019年春夏相交之际。母亲打来电话,告知我二伯母去世了,我从东莞赶回老家奔丧。年方古稀的二伯母到了该享福的年龄却撒手人寰,大堂侄几乎哭到断气,众人七手八脚调了糖水服下才清醒过来。丧事后第二天清晨返莞,途经陂下村狭窄的村道,迎面驶来一辆小汽车。我来不及避让,停了车。对方迅速选择了谦让,尽量让自己的车子往边上靠,空出一辆车的宽度,却不小心压到了下水道的砖石,发出“哐咚”一声。我一惊,担心对方的车子陷进路边的水渠。侧看,幸好那车子有惊无险,快速地开了过去,又停住。我按下玻璃窗,回想刚才那张一晃而过的熟悉的面孔。
“德军!”我惊喜地喊道。未曾想,一别多年的我们竟以这样的方式、这样的时间和地点见上一面。德军也颇为惊喜,探出头跟我聊了起来。他两腮鼓鼓的,嘴里嚼着包子,看样子他正赶去上班。他先问我怎么回家了,又问我在外面买了房子没有。我叹息了一声,简单讲述了二伯母的事,接着提到房子。房子是要买的,外出教书那么多年,总得成个事。每次返回乡下,双亲也会语重心长叮嘱一番,房子问题成了他们的心病。聊以慰藉的是,前年终于七凑八借买了一套毛坯房,也不知何时才能装修。他说,他还没买房,一家人挤在县城的租房里,眼神中透出一丝迷茫、无奈。
在乡下,物质比较的心态已经演变到异常激烈的程度,甚至浓缩成单一的、片面的评判标准,是和非,好和坏,成功与失败,这种非黑即白的观念大行其道,生命历程中的鲜活体验则鲜有旁听者。车子多半为面子的象征,房子则是一个人内心免于飘荡的保障。一个家似乎拥有一套房子,才算画了一个完整的圆。我知道,德军捧着公家的饭碗,日子看似波澜不惊,内心也在较劲,也在期望改变现状。我呢,十几年受聘于私立学校,各种不公平已司空见惯,唯有独善其身,且行且文且吟。下午二点前,我须赶回任职的学校上课,只好跟德军匆匆分别了,然后各自奔向变幻莫测的前方。返莞后,我们聊过几次微信,都是问候寒暄,但未作深入的交流。他极少述说近况,似有隐瞒或顾忌。我只听说他辗转了几所小学从教,年纪轻轻就当上了主任、校长,才干与能力可见一斑。
与德军分别后的那个盛夏,我逮住一个难得的机会,考进了某个事业单位,签了聘用合同。德军获悉后颇为开心,自嘲道:“以前你没有伞,现在你的伞已经很大了,我的伞却还是那么小。”说完,他也许在空中比划了一下,以增加己方观点的说服力。我了解他骨子里的谦逊与正直,以他的能力和水平去获取更大的权力或更高的待遇并非难事,这主要取决于他的意愿。他似乎并不热衷于职场的攀爬,得失皆随缘,不急不躁。有些东西他却很执着,譬如笃信善念,他认为有善念的人才值得信赖与交往。他做到了,他认为我也做到了。这一点,我们还像当年读书时一样,美好且天真的想法仍在怀揣,纵使俗世的不堪如同沙尘般起飞,心中的善与真也绝不会蒙蔽、遮盖。
3
时光再往回溯,我仿佛看到一个少年站在风中,目光坚定地望着远山。那个爱望远山的少年就是我,对于村庄外面的世界满是憧憬。
抵达外面世界的最好方法就是读书,或者说,安身立命莫不寄予读书这条路。
入学读书,意味着拥有翻开无数个未知的主动权,并由未知带来更多的惊喜、收获。在简陋的村小耕读六年时光后,我进入了墟镇中学,同级的还有二百多名学子,德军便是其一。德军来自墟镇以南的贵人村,而我家处于墟镇往北高山绵延之中,方位一南一北,地势一高一低,也不知道两个人是怎样相识的,好像风一吹,两片类似的树叶碰到一起就熟络了,彼此谦让与关怀,譬如抢着帮对方拎冲凉的水桶,争着给对方打温开水,眼疾手快替对方拿饭钵,甚至抢先一步为对方收拾东西……
彼时,班里的走读生不多,像我这样的住宿生一个星期才回一次家。回家,无非也是带一罐干菜以及若干零钞,返校后用这罐干菜扛一个星期,我的初中生涯因此一直飘荡着酸咸菜和干萝卜的味道。寒气来袭的时节,猪油也怕冷,也怕冻,它们抱住玻璃罐里的干菜,凝固成一团奶白色,或者一坨坨依附在透明的罐壁上,用无辜的眼神打量外面的世界。蒸饭还未抬回宿舍,我赶紧从木箱里拿出冰冷的玻璃罐,张开红通通的手掌握住它,给罐里的干菜输送一些体温。待领到蒸饭后,我挖几勺冷冰冰的干菜,在温热的米饭中掩埋起来,等猪油渐渐融化了才下咽。只要前方有梦想的光在指引,没有什么苦挨不过去。我暗暗激励自己。最难过的莫过于抬饭回来后,发现自己的蒸饭钵竟然破裂了,白花花的米饭从裂缝里露出来。我捏着口袋里微薄的零钞,泪水直流。
升至初三后,我们的脖子仿佛被某种神秘的力量不断加轭。为了改变命运,每个人都铆足一股劲,每日奋战至深夜十二点,翌日凌晨五点多又起床学习。同学们踩在奋力一搏的钢丝上,脸庞均呈菜色。德军的家境比大多数同学好,可能是他双亲皆为老师的缘故。他的母亲多半选在周三这一天送荤菜到学校,给他增加营养。他曾叫我一起去校门口迎接,我见到了那位令人羡慕的母亲。她个子高、瘦,修长的手上拎一个白色薄膜袋,袋子里装了一个大搪瓷杯。她的身边,立着一辆单车。她轻声叮嘱德军好好学习,慈祥的脸庞散发出母爱的光芒。那时,德军的学习成绩已名列前茅,可他依然不放松。他小心翼翼接过搪瓷杯。我知道杯里必定盛着美味的排骨、肉丸等菜肴,对我而言简直如人间美味!望着我们进入校园的身影,德军的母亲久久不肯离去。
回宿舍后,德军让我一起分享美食,甚至毫无商量般强加给我,这令我有些羞愧与卑怯。事实上,我不知道该拿什么来回报他,或者我拥有什么东西可分享予他?我家在穷山僻壤,海拔为全镇之最,村庄里的人几乎穷得叮当响,大多数家庭根本供不起孩子读初中。终日艰辛劳作的双亲,只填饱了我们一家六口人的肚子,之后所剩无几。为了供我继续完成学业,我的哥哥、两个妹妹也相继辍学。双亲下了赌注似的,将家里唯一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我怀揣改变家境的使命前行。
七月,德军不出意外考进了五华师范,我却落榜了,命运第一次正式向弱小的我挥出一记重拳,“啪”一声,我身子趔趄、脚步踉跄……或许是老天怜悯于我,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一位家族长辈的指引下,我考进了一所当时的大专学校,也到了县城念书。我似乎抓到了一根救命的藤条,用力地、紧紧地拽着,不敢松懈。两校相隔只有二三公里,偶尔在节假日时,我走路前往五华师范,找德军玩。他带我进宿舍,闲逛雅致、宽阔的校园,又领我到食堂就餐,使用他的餐票,俨然一对兄弟。
“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孟子·公孙丑上》如是说。在中国古代的哲学里,“仁者爱人”“厚德载物”“上善若水”等皆包含向善的精神内涵,德军的善正源于他的家教。记得有一回,他曾自嘲道,其父亲原本期望他成为一名品德高尚的君子,应取名“德君”,然而事与愿违用了“德军”二字,恰也说明自己离这个期望尚存一些差距。此番睿智的解嘲令人觉得幽默,又令人敬佩。
当我的美梦才冒出一点点胚芽,两年后又遭到了命运更为冷酷、残忍的鞭笞,路上尽是砂砾,我光脚踩在上面,踽踽而行。
4
原以为依靠叔公的指点,我的命运会峰回路转,至少变得平坦一些、直一些,岂料糊里糊涂念了几年后,近十门科目“挂了红灯”,只领到一张薄薄的结业证书,前方又渺茫起来。祸不单行的是,我家的老屋也猝不及防倒塌了。没有了栖身之所,我们成了无家可归的人。望着残砖断瓦,我脑海里一片空白,仿佛瞬间被什么东西掏空了。
倒下去的一栋老屋,在我记忆中站立起来。它曾经默不作声隐忍地承载我的童年时光,成为我触摸记忆的一块载体,缺少了它,我十七岁前的回忆将会一片空白,仿佛跟它毫无瓜葛。当它带着愤怒与遗憾躺下去,也失去了职责与胸怀,再也无法收留我们的欢声笑语。我突然意识到我们并非老屋真正的主人,只有残忍的岁月才有资格和能力去支配其生命的长度与宽度。寄人篱下几个月后,我们才有了一处临时的家——双亲在村尾山地上建了一排瓦寮房,哥和我则住进旁边一间废弃的茅寮。我时常爬上山岭,俯视着蜷缩在山坳的瓦寮房,眼前一阵恍惚,顿生今夕何夕之感。
德军就是在这个时期到访我家的。从师范毕业后,他进入墟镇中心小学教书,又凑巧担任我表弟的班主任,当时我心血来潮书信一封,让表弟转交给他。他很快回了信,说想来我家聊一聊。从墟镇到我家,得翻山越岭十里路,外人难于想象其中的陡峭以及泥沙路给人的惊险程度。更令我担忧的是,德军来了后,看到我家如此尴尬的境况会怎么想?学业的坎坷、家庭的拮据与命运的多舛,叫我如何坦然面对曾经的同窗好友?我的心里仿佛藏匿了一条花斑蛇,它随时会爬到最敏感的部位制造难堪和惊吓。
客人或亲戚来串门,除了礼节性的打招呼,我几乎不说话,不交谈,一个人躲进房间。他们问什么,我答什么,尽量回避敏感话题。他们亮起嗓门问,你读的什么书呀?我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解释。他们又笑:你还没有拿到文凭?我已无地自容,这种嘲笑无异于将我的尊严残酷地摁在泥土上摩擦。假如人可以冬眠,我希望自己蜷缩到不见天日的洞穴,独自躲过寒冷的漫长的冬季,等到春暖花开时再与这个世界交流、对话或微笑。夜深时,我放下书本走出瓦房,环顾月光如水下的山峦,是那么静谧与绵延,我的泪水悄然滑落下去……冬夜,冷风刺骨,山谷深处偶尔响起呜咽的风声,令人不寒而栗,我心里一遍遍默诵着杜甫的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周六上午,德军在表弟的指引下来了。他没有嫌弃我的家境,指着旁边的空地安慰道:“那里很快会建出高大的新房子,曙光就在眼前。”家里连张像样的桌子和凳子都没有,午餐桌很矮,高约五十厘米,好像一个委屈的孩子立在瓦寮房前的空地上。桌面窄,摆上几道菜饭碗就放不下了。几张靠背的竹椅,屁股坐上去会发出“吱吱呀呀”的响声,仿佛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惨叫着告诉大家,它快要干不动了,要歇息了。竹椅不够坐,德军便选了一张矮小的木凳坐上去,身子立马矮一截,若不是他腰身修长,下巴也许会碰到桌沿。他倒是幽默,随口几句恰当的玩笑话就化解了我们的尴尬。
下午,我们在低矮的瓦寮房里闲聊。这间瓦寮房是我双亲住的,白天我在里面看书、做笔记。房子正对门有一张床,床头侧边摆了一张古老的、漆黑的桌子。桌子的抽屉里锁着双亲零碎的钞票以及记账簿、户口簿等,桌面上堆放着四十厘米高的衣服,衣服旁有煤油灯、药盒、剪刀、梳子、针织物品。德军见桌面笔筒插了一支毛笔,叫我写几个字看看。我只好翻开一叠草稿纸,背面是我前一天练习的毛笔字,自然不好看。我让他示范几个,他推辞不了,一脸平静地写下“陈”的繁体字和“永”字,好像印刷出来一样,圆润,饱满,方正。他顺便讲了毛笔字的间架结构,以及如何握笔、运笔等技巧。我听了,心悦诚服。他依然谦虚,说自己的水平也就那样,拿不出手。
安身立命,是一道普通的命题,也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修行、进阶。瓦寮房成了我心中的暗伤与痛点,它提醒我不能在村民的讥讽与冷落中自卑、堕落下去,用知识改变命运、改变家境。受德军的鼓励,我重拾了信心,选择半工半读,终于考取了毕业证书,踏上了三尺讲台。
5
2000年,我在临镇一所小学谋了一份代课教师的职务。那所小学依山而建,近山一排为瓦房,下接两层新式楼房,两侧垒起围墙,整个校园组成一个“回”字。虽为代课教师,校长和主任却待我不薄,给予我无微不至的关心、关怀。附近村民皆和善,待人甚热情,仿佛尊师重教的古风从远古之时便留下来,被时光映照得更显光彩。
平时,我住在学校宿舍,周末才搭乘一辆摩托车回家。一年后,我用微薄的工资凑上父母给的钱,买了一辆嘉陵牌摩托车。这辆车成了我往返两镇的交通工具。有时候,我会在往返的路途停下车子,凝望一栋正在建造的新房,内心浮想联翩。那砌墙的师傅将一块块方正的红砖垒起来,一圈圈往上空叠加,仿佛半空中隐藏了一条笔直的路。我设想那一家人肯定有个怀揣梦想的孩子,默默扛起改变命运振兴家族的重任,此刻正废寝忘食寒窗苦读。每次途经贵人村,我不禁想:此刻德军在不在家?他忙些什么?内心些许踌躇,纠结于自己的造访会不会太冒昧。
事实上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德军也期待我这个老同学的出现。当提前与他联系后,我沿着贵人村大路的一条岔道骑行。岔道两边是一畦畦稻田,稀疏的房屋伫立其间,偶有行人往来,一派悠然自得的样子。摩托车爬上一条并不太陡的坡,在德军的指引下,转几圈就到了他家。那是一座半成新的楼房,被一幢幢房子围绕着。站立于他家的门坪,可一眼望见不远处低矮成排的房子和一条弯弯曲曲的路。那时,德军已调至船肚小学教书,后来任教导主任。船肚村毗邻贵人村,沿路转几个弯就到了,他回家较为方便。听德军说,得空时他就约人打篮球。依他身高和手感来判断,前锋的位置较为适合他,他属于得分型的投手。或者,他化身骁勇的战士左冲右突,三步上篮,敏捷矫健的动作一气呵成。我依稀记得他兴奋地描述篮框下的抢夺与投篮,青春的汗水浸湿了他的球衣,他从中找到了运动的乐趣与某种天然的释放。
在德军的描述中,我一遍遍联想他篮球场上灵活利索的过人招式和精准优美的投篮动作,心里泛起钦佩的波浪。优秀如他,不管是教书还是运动,得益于敏锐与聪慧的大脑,更得益于他有趣的灵魂吧。善于自我解嘲的德军没有虚与傲,每一句话皆实在。他幽默起来依然一本正经,也会哈哈大笑露出两排洁白、整齐的牙齿。可惜我对篮球谈不上浓厚的兴趣,自知之明从小就掐灭了我对于运动项目的野心,像我这样的身高和体质,上了篮球场铁定会吃亏,也没有哪个位置适合我。前锋嘛,我没有那股灵活劲和精准的命中率,中锋位置更别奢望了,后卫则需要超强的控球能力,我的运球技术粗糙,篮球多半会往对方的怀里钻,或被直接断掉,场面会变得尴尬起来。
三四年未见,我们的情谊未变。我们聊到身边人、身边事,种种鸡零狗碎、奇闻异谈,聊到天下时事,彼此见解相似,争论甚少。聊到了我家的楼房,德军的脸庞舒展了笑容。尽管是一层的毛坯房,墙身还裸露着一块块红砖和灰色的泥沙,但是我们迫不及待住进去了。能言善辩的德军,引经据典随口而出又通俗易懂,大多数时候,我只能心悦诚服望着他,点头以示赞同。都说“虎父无犬子”,德军继承了其父亲的谦逊、务实与好客,典型的客家人,也是一个内心温暖、怀揣温情的读书人。他的父亲才华横溢,写过不少小说与杂文,我曾经在《梅州日报》看到他发表的一篇杂文,文笔朴实自然,每一个词汇都拿捏得精准,阅之亲切、流畅,绝对是一名创作经验丰富的作家。

在乡村小学教了两年后,我像一尾鱼卷进了珠三角汹涌的浪潮中,依然从事教育行业。德军则坚守在家乡的三尺讲台,我们像两条平行线,各自奔忙、挣扎、追寻。囿于文凭不达标的硬伤,或者说缺乏合适机遇,机关事业单位竖起的屏障一次次将我挡之门外,十多年匍匐于泥沙俱下的私立学校,心里满是辛酸、苦楚、无奈。
十七年来,从惠州到深圳,又从深圳到东莞,我换了三间私立学校。除了完成正常的教学任务,还有各种杂碎事,我被无形的力量驱成了陀螺。每当夜深人静,总有一个声音在耳畔响起:谁能给予深陷迷雾中的我一点点指引?我躺在空荡荡的篮球场上,望着寂寥而广阔的夜空,悲从中来,彷徨惆怅。德军则不同,他是事业编制。贫困山区学校的教师工资也不高,家庭成员又多,零零碎碎的支出已然瓜分了原本就不大的蛋糕。所幸,这几年国家为了振兴乡村教育一次次提高乡村教师的工资待遇与补贴,德军的生活有了较大改善。我唯有储蓄起飞或奔跑的能量,努力发出自己的光。令人欣慰与鼓舞的是,二十年来,我的从教之路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又勤于创作,迄今为止发表了几十万字的文章,获得了一些奖项。德军在电话里说:“没有伞的孩子,学会了奔跑。”在恩威并施的生活面前,我加速奔跑起来。
母亲常说,日求三餐,夜求一宿。小时候的我对此感触不深。多年后,当我目睹老屋的倒塌,饱尝求职的艰辛与谋生的酸楚,咀嚼着母亲的话,一丝苦涩从心房涌出来。我们在安身立命的命题下迷茫、失落又孜孜以求。人生,因此才有了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