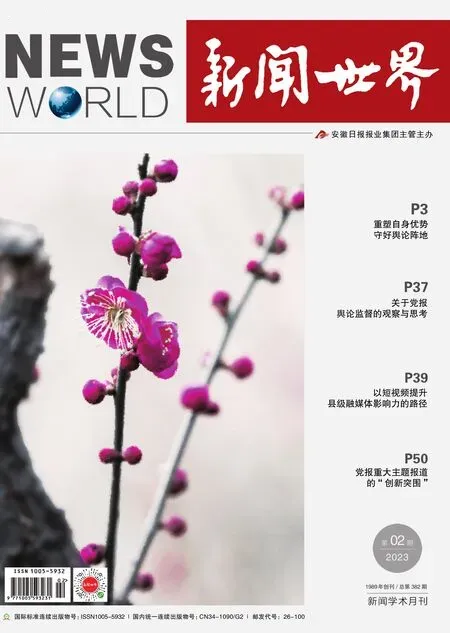央企企业报的集体记忆建构
○周晓雨
引言
作为当代中国最主要的媒介形式之一,报纸始终是宣传与思政工作的重要载体。对于关系国民经济命脉、承担巩固党执政经济基础责任的中央企业(下称“央企”)而言,企业报在宣传工作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宣传”的工作域面向个体精神世界,在此,“记忆”深刻影响着人的认知行为,人们通常以“记忆”为依托实现自我身份建构和社会定位。“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是由群体成员共享的记忆内容,这一概念强调记忆的“集体性”特征。近年来,随着国内外学者的不断开掘,集体记忆在强化成员共同体意识、促进群体凝聚力建设等方面的社会价值逐渐凸显。而央企宣传工作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加强企业成员归属感、增强团队精神,从而形成由精神世界向现实工作的正向助力作用。集体记忆概念自身所具有的特性,无疑为央企宣传工作的有效开展提供了新的理论资源。因此,从建设性视角出发,围绕央企企业报中的集体记忆建构进行思考讨论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央企集体记忆建构的现世价值
集体记忆的理论先驱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提出,集体记忆具有可建构性,集体记忆的本质并非对历史事件进行简单复刻,而是基于当前社会语境下的记忆框架,对“往事”意象进行符合现世认知与价值观念的重构[1]。同时,集体记忆还联结着群体的“当下”与“未来”,即通过作用于意识指导当下的社会实践,通过构筑共同体成员的身份认同影响群体的未来。[2]对于央企而言,助力生产经营活动的有序开展是其宣传工作的重要目标。既有研究指出,央企宣传工作具有维护员工队伍稳定与思想统一、对内凝聚力量、促进企业发展朝着良性轨道运行的作用。[3]可见,“集体记忆”所具有的社会学属性说明其本质上为亟待现世力量介入的“重构域”。而积极建构属于企业职工的集体记忆,充分发挥“集体记忆”在增强员工归属感、企业凝聚力等方面的作用,对于以实现特定目标为指向的央企宣传工作而言,无疑具有较为显著的现世价值。
“企业史”是央企集体记忆建构中最为核心的内容资源。一方面,其历史跨度涵盖了企业自身从成立之初到发展至今的全过程,具有典型的“记忆”属性和鲜明的企业身份烙印,是铭刻着每个企业专属标记的特殊回忆;另一方面,企业史在内容层面蕴含总结过往、借鉴经验、发展未来的潜在意义,不仅对于企业文化的建设不可或缺[4],更能使企业员工了解创业之艰难、守业之辛劳以及对未来发展之憧憬,增强员工爱岗之心与爱企之情[5]。因此,若要充分发挥央企建构集体记忆的现世价值,与企业史相关的历史内容是值得重视与引用的关键资源。基于这一考虑,本文所讨论的央企集体记忆建构,主要是围绕企业史内容开展的记忆实践。
二、企业报:央企集体记忆建构的重要阵地
集体记忆在现代社会中依靠专门化的社会机构进行生产与再生产,以报纸刊物等为代表的“信息供应”媒介是集体记忆建构的重要主体[6]。在我国,企业报虽然不同于面向社会公众发行的大众报刊,在社会整体影响力上稍有逊色。但也因此无需兼顾社会热点,能够专注于企业内部信息的传递,形成了相对封闭的组织传播空间[7],这使其成为员工群体获取企业相关信息的核心渠道,在目标群体中的“单位影响力”较为可观。有研究指出,企业报既是企业文化构建与传承的重要平台,亦是维系员工对企业认同感的纽带,在特定受众的传播效应方面优势得天独厚。[8]企业报作为企业党委的喉舌,以服务企业为己任,以促进企业发展为目的,能够发挥面向央企成员传达、解读企业政策、形塑员工团体认同的功能。[9]同时,企业报在对内凝聚力量、对外传播形象的双向作用中强化了员工对企业共同体“边界”的感知[10],因而天然具有形塑集体认同的身份“询唤”作用。
上述因素使企业报成为集体记忆建构的重要阵地。基于这一考量,以企业报中的媒介记忆实践为切入点探讨央企集体记忆建构的大命题,也能从一定程度上窥一斑而知全豹。
三、企业报的集体记忆建构策略
报纸中进行的与历史、记忆元素有关的内容生产,均可以被视作记忆实践的过程[11]。通过对国内主要央企报刊的长期持续性关注,结合亲身参与央企报刊运营、内容编辑的实践经验,现总结归纳目前央企报刊进行企业集体记忆建构时较为常见的典型媒介实践策略。
(一)强调企业史中的“高光时刻”
企业史的“高光时刻”指企业发展历程中较为特殊的关键事件与时间节点。这些“高光时刻”或彰显了企业之于社会的特殊价值与显著地位,或完成了凸显企业共同体成就的“荣耀叙事”,是企业集体记忆建构的核心关注点。虽然我国的中央企业数量众多、行业各异,但整体而言,在各类央企报刊中得到宣传工作者们统一认可并突出强调的“高光时刻”,大多可划分为以下两种类型。
首先是对企业建立时期的回顾。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语境下,组建中央企业大多基于人民的利益、源于国家的意志,肩负着发展与复兴的民族希冀。央企自然成为国家力量在特定行业领域的“化身”。其与生俱来的政治身份和历史使命,足以使央企“诞生”本身成为企业史中的“高光时刻”。其次是能够说明企业自身在生产能力、科学技术、运行架构等各类经营指标中出类拔萃、对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贡献的相关事件,属于因突出的行业地位、显著的社会价值而产生的“高光时刻”。央企企业报将这一类型的“高光时刻”作为集体记忆建构时着重强调的话语资源,能够有效唤起职工群体身为企业一员的身份自豪感和历史使命感,并在对过往成就的凸显中激发当前生产活动的积极性。
就具体操作而言,央企报刊一方面有意将“高光时刻”打造为各类日常叙事的历史背景直接融入新闻报道之中,通过记忆内容的反复“召唤”以强化共同体成员对“高光时刻”的切身感知;另一方面则围绕重大历史事件本身策划成体系、成规模的系列报道活动。例如,在“逢五逢十”的周年庆典中进行角度全面的密集报道,以此搭建读者群体关于“高光时刻”的整体性认知框架。
(二)整合个体叙事与记忆框架
个体记忆是集体记忆的来源,亦是集体记忆产生的必要条件。[12]个体记忆往往是生动的、鲜活的,从个体的视角出发,可以更多地呈现记忆内容的丰富与细致。[13]有关记忆的“一手叙事”往往来自个体的亲身经历与切身感悟,不仅内容上更为细致生动,其立足个体出发的叙事视角亦能在更大程度上引发读者的情感共鸣,使之在感同身受中增强对企业集体记忆的体认。
为发掘这些鲜活多样的个体记忆,央企企业报通常在内容层面采取开源模式,例如大型央企报刊《中国石化报》便开设了长期面向在岗职工、离退休群体广泛征稿的稳定渠道,源源不断地从新老员工的来稿中获取集体记忆生产的“记忆资源”。来自职工群体的投稿为央企报刊提供了大量时间跨度长、主题鲜明、内容丰富的回忆性文章,这些个体叙事能够有效提升记忆温度、描刻记忆纹理,帮助企业报在集体记忆建构中言之有物、言之有情。
但另一方面,集体记忆并非个体记忆的简单堆砌,其形成还需要一个整体性“记忆框架”对松散记忆内容进行叙事赋能,使之能够具有完整意义阐释的记忆叙事功能。央企报刊作为个体叙事的“把关人”和集体记忆的“工程师”,在搭建记忆框架时往往重视“个人”与“企业”的有机结合,即着意突出“个体奉献企业”与“企业关照个体”两种叙事角度。其选载的个体记忆叙事,或弘扬员工吃苦耐劳、甘于奉献的职业精神,或强调企业关爱员工、帮助成长所给予的福利保障。这两个面向的叙事内容,共同描绘出人企互惠共进的良性关系。央企报刊试图以此搭建起一个积极正向、指向明确的记忆框架,在个体叙事与记忆框架的整合中进行集体记忆建构。
(三)持续且稳定的内容输出
行之有效的集体记忆实践,是一个潜移默化的长期性过程。央企企业报除了在特定时间节点、围绕特定历史事件展开的纪念性系列报道之外,通常还会为企业“过往”开辟稳定的内容空间。以央企中国石化茂名分公司《茂名石化报》为例,自2012 年起,该报便在其第四版文艺副刊中常设“往事”和“老照片的故事”两个固定栏目。前者主要刊登报社通讯员关于企业史内容的描绘性记叙,以及老职工、离退休人员的个体回忆类文章;后者则以编辑部精心挑选、反映企业历史的老照片为主。这些照片大多来自官方留存的历史文档与职工投稿,灰白或相对暗沉的色彩基调,隐喻老照片的“历史”与“记忆”属性,照片旁配有介绍背景、描述事件、阐释意义的详尽文字,通过“语图互文”的方式充分发挥老照片作为一种象征性符号的传情达意作用。
除此之外,央企报刊不仅在版面编排上常设刊载企业史内容的专栏,还注重在其他日常报道中对企业史内容的融合与引征,采用“类比”或“发展”的视角从当下回顾往昔,以此为报道文本增添“以古喻今、以今忆古”的记忆视角与历史纵深,通过持续稳定的内容输出,潜移默化地进行企业集体记忆的建构实践。
四、企业报记忆建构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移动互联网与数字信息技术重塑了媒介生态格局,以报刊为首的传统纸媒渐露颓势。在这一背景下,央企企业报面向职工群体的集体记忆建构实践同样面临挑战。
首先,网络新媒体的“技术赋权”使不同主体得以在线上空间发声并产生一定传播效果,其中与中央企业历史相关的“反记忆”叙事内容冲击着企业报作为记忆“书写者”的权威地位。当企业报不再是大多数职工了解企业历史的唯一信息渠道时,企业报建构集体记忆的潜力便开始下降。与此同时,一些关于企业过往的歪曲解读与不实信息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也逐渐增强。
其次,职工群体对企业报的关注持续走低。曾几何时,“读报”是人们在闲暇时光主要的文化消遣,而以记录员工活动、生产信息为主体的企业报,更是得到企业职工群体的青睐。在操作车间、基层单位、工人宿舍等“员工群聚空间”内,时常出现多人传阅一份企业报的景象。然而,随着企业职工的业余生活更加丰富,越来越少的人通过读报消磨时光。接触的减少使得央企企业报的有效阅读率亦逐渐降低,其对于职工集体记忆的影响自然也被削弱。
同时,从企业报自身发展而言,数字化技术催生了QQ 群、微信群、钉钉群等新的群体“线上公共空间”,企业报作为员工集体交流、相互了解的文化公共场域的属性同样日渐式微,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威胁着企业报的发展活力与文化根基。
基于上述挑战,央企企业报在未来发展中或许可以作以下改进以恢复自身对央企集体记忆建构的能力。
其一,是对报纸本身进行优化升级,在内容层面提高记忆类文章的贴近性、趣味性,并注重强化企业报的权威与严谨。在策划层面进一步唤起职工群体参与企业集体记忆书写的积极性,发掘更多角度丰富、细节饱满的个体记忆叙事;在编辑出版层面,加快企业报的“互联网+”进程,推出融媒体形式的数字报刊,增强职工企业报阅读行为的便捷性。
其二,是将企业报纳入央企集体记忆建构的多媒介矩阵之中,形成与其他记忆媒介(如企业纪录片、线下纪念馆、企业史博物馆等)的“互文”。企业报一方面可以在内容上增强对其他记忆媒介形式的报道,例如对影像类企业史纪录片进行文字角度的内容介绍与意义阐释,促进形成不同媒介形式间有机互动的“表意网络”;另一方面,可以将企业报作为其他媒介记忆产品的“引流”入口,例如将各类涉及中央企业历史的影像资料、数字化呈现企业史纪念馆的H5产品等制作成二维码,搭配在企业报的相关报道内,方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扫码进入了解有关历史,实现央企集体记忆建构中的媒介联动。
注释:
[1]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2]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M].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
[3]丁沛然,康静珍.央企正面宣传的舆论引导思路[J].新闻爱好者,2012(07):58-59.
[4]赵文清.试析企业志在企业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J].黑龙江史志,2008(17):9-10.
[5]邵冰华.融媒环境下如何做好企业史志图书的编辑出版工作[J].新闻传播,2021(19):70-72.
[6]Carolyn Kitch,Anniversary Journalism,Collective Memory,and the Cultural Authority to Tell the Story of the American Past[J],The 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Vol.36,No.1,2002:47-67
[7]操瑞青,夏羿.企业员工刊物:被忽视的民国组织传播活动初探[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05):102-125+128.
[8]杨林.企业报:企业文化的构建者与传承者——透视中信人报在企业中的文化角色[J].新闻与写作,2008(01):59-60.
[9]朱向前.企业报如何更好地为企业服务[J].青年记者,2013(09):45-46.
[10]刘永瑞.整合资源 创新报道多向传播——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企业报工作的思考[J].新闻界,2002(03):50-51.
[11]李红涛,黄顺铭.新闻生产即记忆实践——媒体记忆领域的边界与批判性议题[J].新闻记者,2015(07):9.
[12]Kansteiner,W.Finding Meaning in Memory:A Methodological Critique of Collective Memory Studies[J].History&Theory,2002,41(2),179-197.
[13]龙彦儒,于德山.个体记忆与家国情怀:抗“疫”纪录片《英雄之城》的记忆实践[J].电视研究,2020(09):53-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