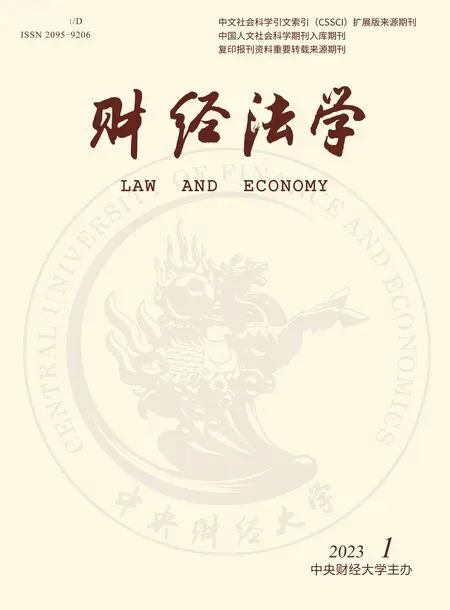授权资本制中不当发行停止请求权的建构与行使
李卓卓
内容提要:《公司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对授权资本制下不当发行的规制有所不足,后续修订应强化股份发行的事前规制。不当发行停止请求权是股东的保护性请求权,基于减少代理成本、禁令救济经济效率、股东权利的合同理论以及少数股东保护等正当性基础,应当在《公司法》中增加不当发行停止请求权。规制不当发行需兼顾公司融资与股东权利保护这两项价值,股东行使不当发行停止请求权需满足不当发行与股东遭受损害两要件,同时应规定股份发行之前董事的通知义务,尤其当特定认购人可能取得公司控制权时,董事会应事前向股东通知认购人的信息。《公司法》通过不当发行停止请求权事前规制不当发行,有助于强化授权资本制的体系效应与法律确定性。
调整董事行为是公司法的核心命题。(1)参见叶林:《董事忠实义务及其扩张》,载《政治与法律》2021年第2期;邓峰:《中国法上董事会的角色、职能及思想渊源:实证法的考察》,载《中国法学》2013年第3期;Armour, Hansmann, Kraakman & Pargendler, What Is Corporate Law, in Kraakman et eds., the Anatomy of Corporate Law, 3r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18.依据代理成本(agency cost)理论,法律应尽可能降低公司中董事与股东的代理成本,以提高当事人的交易效率。(2)See Jensen & Meckling,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3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305, 345-357(1976); 甘培忠、马丽艳:《董事会中心主义治理模式在我国公司法中的重塑》,载《财经法学》2021年第5期。股份发行与公司经营管理密切相关,股份发行既可以使公司取得发展急需的资本,也有可能引发公司原有股权结构及资本结构的变化。2021年公布的《公司法(修订草案)》(以下简称“一审稿”)与2022年12月公布的《公司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以下简称“二审稿”)确立了授权资本制,强化了董事会这一公司管理层的权力,意味着在公司特别决议或章程的授权范围内,股份发行成为董事会的一种经营事项,董事会可在商业判断的范围内决定股份发行的时间、数量、价格以及方式。这一变化可谓是《公司法》修订的亮点,然而对于董事会是否会滥用授权从而不当发行股份,二审稿却缺乏应有的关注。(3)参见蒋大兴:《公司法修订草案中的关键缺失》,载《中国法律评论》2022年第5期。二审稿第152条将董事会的授权比例调整至50%。与2021年一审稿类似的是,二审稿并未新增其他规制。在公司治理实践中,授权资本制下公司管理层可能滥用发行股份的权力,并结合协议收购、员工持股、股份赠与、表决权委托、公司担保或向第三人提供贷款等方式稀释或损害现有股东的权益,以形成对股东权利的复合型侵害。(4)See Condec Corp.v.Lunkenheimer Co., 43 Del.Ch.353, 230 A.2d 769 (1967); Klaus v.Hi-Shear Corp., 528 F.2d 225 (9th Cir.1975).这不仅显著提高了代理成本从而侵害了股东权益,降低了控制权市场改善公司治理的效率,还有可能降低上市公司的资本效率,不必要地增加负债,并有可能导致“管理层巩固”(management entrenchment),不利于董事履行其信义义务及管理公司的职能。
不当发行包括董事会违法发行、违反章程发行以及以不公正的方式发行等行为,不当发行停止请求权指的是当董事会决定发行股份存在不当事由时,股东等主体得以请求法院停止该股份发行。(5)参见沈朝晖:《授权股份制的体系改造》,载《当代法学》2022年第2期。不当发行停止请求权是授权资本制规范体系的重要内容,其系股份发行的事前规制。不当发行规制包含事前规制与事后规制两个部分,然而仅靠事后规制难以充分保护股东利益,发行无效的事后规制常常会引发法律关系的不稳定,(6)近藤弘二「新株発行無効の訴」上柳克郎ほか編『新版注釈会社法7新株の発行』(有斐閣、1987年)342頁参照。损害赔偿的事后规制则无法阻止不当发行,因此作为事前规制的不当发行停止请求权是股东的重要救济手段。(7)山神理「募集株式の発行等をやめることの請求」江頭憲治郎ほか編『論点体系会社法2』(第一法規、2021年)237頁参照。比较公司法中也存在不当发行停止请求权,如日本《公司法》第210条规定,特定股份发行或自己股份处分违反法律,或以显著不公正之方法进行时,股东如遭受不利益,可向公司请求停止《公司法》第199条1项相关之股份发行或自己股份处分等行为。又如在美国法中,一般而言董事会有权决定发行股份以及发行股份的价格,董事会发行股份的决定受商业判断保护,因此一个没有过错的独立的董事会的决定应当受到尊重。(8)See Davis v.Louisville Gas & Elec.Co., 16 Del.Ch.157, 142 A.654 (1928); Papalexiou v.Tower W.Condo., 167 N.J.Super.516, 401 A.2d 280 (Ch.Div.1979); Benihana of Tokyo, Inc.v.Benihana, Inc., 906 A.2d 114 (Del.2006).但当董事会决定进行不正当发行股份以损害现有股东利益时,股东可以向法院请求禁令,以禁止股份发行。(9)See Donald v.Am.Smelting & Ref.Co., 62 N.J.Eq.729, 48 A.771 (1901); Feero v.Housley, 205 Or.404, 288 P.2d 1052 (1955); Hill v.Small, 228 Ga.31, 183 S.E.2d 752 (1971).
我国对不当发行停止请求权缺乏深入探讨。一方面,不当发行停止请求权的适用场景为授权资本制下的股份发行,由于我国公司法长期未确立授权资本制,与不当发行停止请求权有关的讨论较为匮乏。另一方面,对于我国是否应引入不当发行停止请求权学理界仍存在争议。支持者认为我国需引入不当发行停止请求权保护少数股东,(10)参见陈景善:《授权资本制下股份发行规制的重构》,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2年第2期;岳冰:《论我国资本形成制度的规制坐标与自治重构》,载《法学杂志》2021年第5期。反对观点认为授权资本发行中需规制控制权变动,应适用股东会决议的程序要求。(11)参见李建伟:《授权资本发行制与认缴制的融合——公司资本制度的变革及公司法修订选择》,载《现代法学》2021年第6期。更重要的是,公司法如需设置事前规制与事后规制,意味着公司法设置了董事介入公司内部控制关系变动的边界,而这实质上是公司法的根本问题,需要得到理论上的慎重回答。(12)森本滋「新株発行規制の一般的検討」商事法務1070号(1986年)402頁以下参照。
如果公司法不能在事前有效规制董事会股份发行权力滥用,则无法促使我国股份公司采取授权资本制,更不论实现授权资本制的普及。本文先明确不当发行的规制缺失并探讨不当发行停止请求权的正当性基础,再通过考察比较法学说、规范与实践发展探究不当发行停止请求权的规范模式与法律构造,为我国公司法立法与实践提供参考。
一、二审稿中不当发行的规制缺失
《公司法》修订前,股份发行需经股东会决议,少数股东能够通过参与决议保护其利益。且股东可以通过股东会决议瑕疵制度实现对侵害其权利的股东会决议的事后规制。另外,如果股东会决议发行股票损害了少数股东的利益,则股东可依据《公司法》第20条的禁止股东权利滥用原则追究参与违法决议的股东的损害赔偿责任。二审稿中董事会在取得授权的情况下具有决定股份发行的权力,一定程度上公司法需同时实现董事会权力滥用规制以及多数股东权利滥用规制。然而,二审稿对于这一问题缺乏充分规制。
(一)50%的授权比例限制难以规制不当发行
二审稿第152条的50%授权比例限制无法发挥事前规制的功能。二审稿第152条确立了授权资本制,相比较一审稿第164条,二审稿删除了发行新股表决权超过20%时的股东会决议规则,新增了50%的授权比例,以期规制不当发行。
首先,公司法应当为股东提供普遍而广泛的保护。不当发行可能损害的是股东平等参与公司的权利,如以稀释少数股东持股比例或剥夺控制股东控制权为目的等一般不具有商业目的的股份发行。股东参与公司治理是公司法民主参与原则的要求,公司法应为实现股东的民主参与提供必要的制度支持,并为遭受权利侵害的股东提供法律救济,如公司决议瑕疵制度即是此例。(13)参见叶林:《股东会决议无效的公司法解释》,载《法学研究》2020年第3期。公司法应当为股东提供普遍而广泛的保护,并不能说持股比例较低的股东就不具有保护的必要。
其次,滥用授权发行股份与章程或股东会决议对董事会的授权比例并无直接联系。董事滥用授权发行股份的行为特征是发行股份并不是为了公司的整体利益,或者其发行股份的决定虽然是为了公司的整体利益,但其方式损害了部分股东或全体股东的利益。如以不合理的低价但欠缺合理商业目的的股份发行,虽然没有损害公司的整体利益,但对公司现有股东而言却是一种损害,只要发行了股份即影响了现有股东持有的股份的价值。
(二)股东会决议规制不符合不当发行控制权变动的规制逻辑
与一审稿第164条但书的20%持股比例限制类似的是,二审稿第152条的授权比例限制的目的是规制控制权变动,实质上是以股东会决议规制控制权变动,然而该思路却未能全面理解涉及控制权变动的不当发行。首先,除了促成控制权变动的不当发行,不当发行也包含阻碍控制权变动的情形,包括不公正的有利发行、稀释少数股东持股比例以及避免股东形成多数决的管理层巩固等。(14)参见温笑侗:《授权资本制度下公司控制权争夺的法律问题》,载《商法界论集》第8卷,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85页。不当发行与控制权变动的关系并非简单的不当发行导致了控制权变动的因果关系,而有可能是不当发行阻碍了控制权变动,如董事会滥用授权向第三方发行股份从而阻碍敌意收购人通过要约收购取得公司控制权。(15)参见前引〔7〕,山神理文,第239页。以控制权变动作为事前规制的边界不利于规制董事会滥用授权发行股份。其次,授权资本制中股东会决议或章程授权董事会发行股份,即代表了公司以及作为整体的股东群体认可了董事会发行股份的权力,这是授权资本制扩张公司自治、便利公司融资的目的所在,而授权发行股份难免会对公司的持股比例乃至控制权产生一定影响,也属于公司自治的合理结果。如果授权中并未将发行股份的权力限制为不发生控制权变动的场合,则法律强制规定控制权变动时需经股东会决议有过分干预公司自治的问题。另外,将控制权变动等同于损害,实质上体现了法律对损害的客观判断,然而是否构成对股东的损害并不完全取决于客观判断,更取决于股东的主观判断,如有的股东侧重股票价格,有的股东更愿意积极参与公司治理,如通过公司决议为控制权变动设置限制,则意味着法律替代股东进行了判断。最后,控制权变动虽与不当发行具有密切联系,但控制权变动属股东间利益冲突,并不是股东与董事利益冲突的重心。基于公司法中的股东平等待遇原则,董事具有平等对待股东的信义义务,董事会不当发行股份违反了这一平等对待股东的信义义务,因为董事不应参与控制权争夺。董事应在股东间利益冲突中保持中立,在公司的权力分配问题上,董事会不具有决定公司控制权归属的权力,因此在公司发生控制权争夺时董事会以影响控制权为目的决定向第三人募集股份原则上构成不公正发行。(16)参见前引〔7〕,山神理文,第242页。因此规制存在控制权变动的股份发行的意义在于避免董事会参与股东间利益冲突以致损害股东权利,从而偏离其中立的职权定位,并不是所有会发生控制权变动的股份发行均有规制必要。
二、不当发行停止请求权的正当性基础
不当发行中的股东停止请求权意味着允许法院通过干涉公司自治维护股东权利,而股份发行为公司自治之事项,所以不当发行停止请求权应具有制度上的正当性。对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察股东停止请求权的正当性基础。
(一)股东权利的合同基础与代理成本控制
股份发行包含两个行为,一为授权,二为发行。“授权”为公司通过公司章程中的条款授权董事会发行股份,这些条款规定了股份所有权的权利,当股份被授权(Authorized)后,董事会取得发行股份的权力。“发行”为公司将已经授权的股份出售给其他主体,在这个过程中受让人与公司之间成立股份合同(share contract)。因此公司与股东之间的法律关系不仅为组织法律关系,也为合同法律关系。一方面,股东与公司之间成立一种基于公司章程的合同。(17)See Kent v.Quicksilver Min.Co., 78 N.Y.159 (1879); Loewenthal v.Rubber Reclaiming Co., 52 N.J.Eq.440, 28 A.454 (Ch.1894); W.Chester & P.R.Co.v.Jackson, 77 Pa.321 (1875).公司成立的注册行为,使得公司章程成为公司与股东之间的合同,公司及其董事的章程违反即是违反了公司与股东之间的合同,因此受到影响的股东基于合同上的个人权利,可以要求公司实际履行(specific performance)该公司章程。(18)See Hannigan, Company Law, 5th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186.另一方面,股权是一种合同,是公司章程授权的一系列利益和参与单位之一,通过这种合同,公司取得资本的对价是股东取得股息和其他按比例参与利润和增长分配的权利。股票的认购人和买受人使自己成为合同法律关系的当事人,它赋予股东在解散和清偿债务后参与资产分配的比例权利,以及某些救济权利(remedial rights)。
阐明公司与股东间法律关系的合同法要素的目的,不是要分析股东与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能否在实质上等同于合同关系,也不是要否定公司法中就不存在不能通过当事人合意排除的对当事人的法律救济或请求权,而是要讨论是否应赋予股东类似于合同当事人的保护性请求权。(19)合同概念与公司概念存在显著差别,公司法学常采用合同框架来分析公司及公司法。See Williamson, Corporate Governance, 93 Yale Law Journal 1197, 1199-1205(1984); Posner,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Aspen, 2003, pp.405-407.公司法合同主义虽然认同公司法整体上为任意性或授权性,(20)合同理论并不是完全将公司等同于合同,而是主张公司应当以类似合同的方式实现自治,这一方法论的结论为“内容原则”(content principle)以及“选择退出原则”(opt out principle),然而选择退出原则并不是无限制的,公司法中的众多规范仍然是强制性的。See Gordon, The Mandatory Structure of Corporate Law, 89 Columbia Law Review 1549, 1550-1553, 1597(1989).但也不否认公司法中存在保护性规范目的的强制性规范。(21)See McChesney, Economics, Law, and Science in the Corporate Field, A Critique of Eisenberg, 89 Columbia Law Review 1530, 1531(1989).以公司法的合同自由为基础,我国学者也认为公司法中应存在授权规范与强制规范,为少数股东提供保护。参见汤欣:《论公司法的性格——强行法抑或任意法?》,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1期;冯果、段丙华:《公司法中的契约自由——以股权处分抑制条款为视角》,载《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观察公司法的合同性质的意义在于,在合同法律关系中公司法及私法秩序是否通过权利的方式赋予了股东特定的法益,以及此种权利是否应通过个人权利的方式予以保护。合同主体之间存在相互的交往保护义务(Verkehrspflichten),基于交往保护义务合同当事人应以诚信原则保护相对人的安全与利益。(22)Vgl.Schur, Leistung und Sorgfalt, 2001, S.20.保护义务满足的是民事主体在社会交往中安全的需要,并不限于合同法律关系。债务关系中的履行义务(Leistungpflichten)与保护义务(Schutzpflichten)存在区分,因为履行义务的目的是实现履行利益,而保护义务的目的是一个消极的目的,旨在避免另一方遭受特殊关系中可能发生的损害。(23)Vgl.Heinrich Stoll, Abschied von der Lehre von der positiven Vertragsverletzung, AcP 136.Bd., H.3 (1932), 257, 288.保护义务存在于独立于当事人意思的保护法律关系,其发生原因是当事人之间成立的事实上的信任关系以及诚信原则的实体法依据。(24)Vgl.Canaris, Ansprüche wegen positiver Vertragsverletzung“ und Schutzwirkung für Dritte“ bei nichtigen Verträgen, JZ 15/16 (1965), 475, 476.股东在参与公司的过程中,与董事虽无直接联系,但通过章程与董事形成了合同法律关系,而由于董事掌握了公司管理权且股东并不直接参与公司治理,董事与股东之间存在信任关系,(25)参见蒋大兴:《走向“合作主义”的公司法——公司法改革的另一种基础》,载《当代法学》2021年第6期。股东通过股东会决议的方式选任董事也体现董事与股东的信任关系。因此股东与董事之间存在基于信任关系和固有利益保护的保护关系,此种保护要求董事在履行职务时负有保护义务,不得故意损害股东的利益。
(二)股东间利益冲突及股东权利保护
我国存在大量股权治理结构为股权集中型的公司,这直接意味着董事有时实际上是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代理人,因此公司通过修改章程或通过特别决议实行授权资本制可能会延续法定资本制之时的股东间利益冲突,从而使大股东压迫小股东的问题转化为授权资本制下的董事会决定股份发行损害小股东利益的问题。董事会决定发行股份有可能是为了强化自己派系的权力而通过股份发行给另一派股东造成损害。(26)前田庸『会社法入門』(有斐閣、2018年)338頁参照。
然而公司实行授权资本制是一项团体内部多数人决定通过的程序,其不能减少对少数人的保护,因此需要为少数股东通过司法程序保护其权利提供途径。(27)Vgl.Schockenhoff, Gesellschaftsinteresse und Gleichbehandlung beim Bezugsrechtsausschluß, 1987, S.97.在公司团体中股东具有固有利益,私法秩序通过股东固有权的方式确认了股东的此种固有利益。因此当股东的利益遭到损害时股东有权向法院主张救济。股东权利包含自益权与共益权,财产性权利以及参与决策权利。(28)参见见江平、孔祥俊:《论股权》,载《中国法学》1994年第1期。股东的不当发行停止请求权为股东的权利,其意义在于股东得以通过行使不当发行停止请求权以停止不当发行避免其自身权益遭受损害,在法律性质上其一面为基于股东自身权利的诉权,而不是基于公司权利的停止请求权,(29)近藤弘二「新株発行の差止」上柳克郎ほか編『新版注釈会社法7新株の発行』(有斐閣、1987年)287頁参照。另一面则为股东的共益权。(30)不当发行停止请求权的效果及于公司和全体成员,因此也被认为是具有自益权色彩的共益权。北沢正啓「株主の代表訴訟と差止権」田中耕太郎編『株式会社法講座3』(有斐閣、1956年)1171頁参照。
(三)管理权的不当行使
公司决定事项可分为经营管理事项与结构事项,前者由董事会决定,后者由股东会决定。授权资本制下,公司通过章程或股东会特别决议授权董事会决定股份发行,实际上是公司以其意思自治决定了股份发行属经营管理事项而非结构事项。在授权资本制下股份发行属于公司的经营管理事项,因为股份发行为公司的融资手段,如何以及何时融资与公司的经营密切相关。司法介入公司自治具有一定尺度与界限,法院原则上不干预董事会对经营管理事项的决定,符合公司自治的基本理念。
然而董事对经营管理的决定既不是没有边界也不是没有规则的,其行使对公司经营管理事项的决定权时需符合信义义务。信义义务要求董事在执行职务时履行勤勉义务和忠实义务,这是董事的行为规范,董事在决定股份发行时负有对公司的信义义务,不仅需为了公司的利益而行事,还需具有正当目的。股份发行可能存在多重目的,关键在于其他目的与股份发行决定的事实因果关系,例如若不存在消解公司内部多数股东控制权的目的,则不会进行股份发行,则可认为消解多数股东控制权为非正当的其他目的。(31)See Howard Smith Ltd v.Ampol Petroleum Ltd [1974] 2 W.L.R.689.并非消解控制权目的本身不法,若多数股东意欲通过股东会决议侵害公司整体利益,则董事会可通过股份发行来消解多数股东的控制权,如当董事会决定发行股份的目的是抵御“绿邮欺诈”则具有正当目的。(32)伊藤靖史「募集株式の発行等をやめることを請求」酒巻俊雄ほか編『逐条解説会社法第3巻』(中央経済社、2009年)145頁参照;松井秀征「取締役の新株発行権限2」法学協会雑誌114巻6号(1997年)715頁以下参照。但当消解多数股东控制权与促进公司整体利益毫无关系以至于该目的超越了董事会职权范围时,该董事会发行股份则属具有不正当目的。(33)See Dignam & Lowry, Company Law, 11th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p.332.因此,当董事履行董事职责、行使对公司经营管理事项的管理权违反信义义务或法律要求时,法律应予介入以保护公司及股东权利。
(四)损害预防功能
不当发行股东停止请求权具有事前的损害预防功能,是私法在公司法及资本市场法中实现损害预防功能的重要环节,其对股份发行的参与各方具有重要意义。
一方面,有效的事前规制能够避免不法交易的发生,减少交易主体时间和金钱的浪费,并提高法院裁判效率。若无不当发行停止,则不当发行可能产生董事解任、董事对公司的损害赔偿责任、价格不公正时发行股份的认购人的损害赔偿责任,以及新股发行无效之诉等多重法律后果。(34)近藤弘二「新株発行の差止」矢沢惇ほか編『注釈会社法5』(有斐閣、1968年)175頁参照。与此相对,在董事会决定新股发行但并未开始时,股东可以主张不当发行的股东停止请求权,以实现在事前预防可能损害的目的。(35)大隅健一郎=今井宏『会社法論』(中巻)(有斐閣、1992年)652頁参照。如不能在交易之前完成对不当发行的阻却,则可能需要通过较为复杂的事后规制完成对不当发行的规制,然而在事后规制中法院需要在交易安全与权利保护之间进行十分困难的衡量。(36)参见前引〔6〕,近藤弘二文,第342页。事前规制具有降低法院裁判难度的效力,能够较好地实现公司利益保护的社会效益、司法裁判的司法效率、股东权利保护的法律正义之间的平衡。另外,损害赔偿可能也能够在股份发行中发挥作用,如当不当发行造成股东权利受损时,股东可能以董事违反信义义务为由向董事主张损害赔偿请求权。然而不当发行的损害如果仅体现为股东持股比例的稀释或控制权转移,则难以计算实际损失,更重要的是损害赔偿原则上遵循完全赔偿原则,而实际上股东可能并非百分之百会考虑提起诉讼,且董事并非百分之百被起诉,胜诉后也不一定会支持股东百分之百的赔偿数额,因此完全赔偿原则下的非惩罚性的损害赔偿无法发挥损害预防功能,难以遏制当事人的机会主义行为。
另一方面,损害预防功能需在私法秩序下实现,法律不能一味追求损害预防功能而忽略其所在的法律秩序。实现损害预防功能不能通过强加惩罚性赔偿,因为惩罚性赔偿是责任法损害填补原则的例外。通过停止请求权实现损害预防功能,也具有一定限度。停止请求权这一私法权利的行使效果的实现需依赖法院通过判决或命令等公法手段禁止或停止私法主体进行特定行为,是对私法自治以及个人自由的限制,不能为了追求规制目的而忽视私法的基本原则。类似地,美国公司法中禁令仅在多数股东进行最为恶意的行为(most heinous acts)时被用于保护少数股东,在多数人行为并非恶意时,法院可能只提供更为温和的救济,比如评估权,而在股东存在其他救济途径时,法院也不会为固有权(vested rights)遭受侵害提供禁令救济。(37)See Manning, The Shareholder’s Appraisal Remedy, 72 Yale Law Journal 223, 226-228(1962).因此,不当发行停止请求权需要在私法秩序的体系内部实现损害预防功能,其规范重心为可能严重损害股东权利且具有不正当目的的不法的股份发行行为。
(五)禁令制度的法经济学基础
禁令救济(injunctive remedy)虽然与损害赔偿的补偿救济(compensatory remedy)有所不同,但仍然会有是否具有效率的价值判断问题,从事后的角度来看,当事人主张禁令救济不仅是寻求法院的强制命令(coercive order),实质上是双方在事前并没有达成具有效率的协议。禁令制度赋予当事人谈判筹码(bargain chip),按照经济学的术语来说,禁令制度确立了当事人在讨价还价中的威胁点(threat point)。(38)See Robert Cooter, Unity in Tort, Contract, and Property,73 California Law Review 1, 27(1985).禁令制度可以产生理想的经济效果,因为主张禁令的权利(right to obtain injunction)能够使权利人在与侵害人的谈判中获得充分补偿,进而达成具有效率的协议。(39)See Avery Wiener Katz, Foundations of 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Law, Law Press(影印版), 2005, p.64.
不当发行停止请求权强化了股东谈判能力,在多数股东控制的董事会决定股份发行时,少数股东可通过行使不当发行停止请求权事前停止股份发行,这意味着多数股东如果要通过发行股份强化自身对公司的影响力,则必须在事前与少数股东达成一致,否则可能会导致股份发行无法进行。另一方面,如果董事会意图增加公司的现金以强化自身的管理职权,则股东可能以发行不当为由主张不当发行停止请求权,那么董事会就必须就发行事由与股东达成一致,或者在决定股份发行时充分考虑股东的利益。相较于不当发行停止请求权,完全将股份发行保留给股东会决议不仅不便于公司快速通过直接融资取得公司扩张经营所需的资金,从结果来看也并非所有的董事会发行股份决定均会造成股东权利受损,因此不必通过法律强令公司发行股份需经股东会决议。赋予股东不当发行停止请求权,意味着股东可以自行判断该股份发行是否可能损害其自身权利,既有助于促使董事会在发行股份之前充分考虑股东的利益,也可兼顾避免对股份发行赋予一般性的限制。
三、不当发行停止请求权的建构路径
(一)不当发行停止请求权的建构路径
基于不当发行停止请求权的合同权利基础、对不当发行的规制功能、对不当发行不利后果的损害预防功能,以及规制管理层不当行为的效率性,我国应增加不当发行停止请求权。从规范模式来看,日本公司法直接规定了不当发行时的停止请求权。另外,也有国家通过法院裁判的方式确立了不当发行停止制度,如在美国法中董事会若决定进行不正当发行股份以损害现有股东利益,股东可以向法院请求禁令。一方面,在封闭公司中如果董事会发行股份的目的是稀释股东的持股比例,又或是股份发行的价格过低以至于不符合公平要求时,股东得以主张衡平救济。(40)See Campau v.McMath, 185 Mich.App.724, 463 N.W.2d 186 (1990).另一方面,当董事会发行股份的目的主要为巩固管理层时,股东可以请求法院给予其衡平救济,例如撤销已发行的股份或停止股份发行。(41)See Co, Condec Corp.v.Lunkenheimer Co., 43 Del.Ch.353, 230 A.2d 769 (1967); Phillips v Insituform of North America Inc, Phillips v.Insituform of N.Am., Inc., No.CIV.A.9173, 1987 WL 16285 (Del.Ch.Aug.27, 1987).如有法院认为在公司董事会决定股份发行时,剥夺多数股东的控制权的目的不具有合法性,因为阻碍股东行使权利的目的不能被商业目的合法化。(42)See Phillips v Insituform of North America Inc, Phillips v.Insituform of N.Am., Inc., No.CIV.A.9173, 1987 WL 16285 (Del.Ch.Aug.27, 1987).又如德国法中,在董事会不当排除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发行股份的场合,通过法院适用德国民事诉讼法形成了类似的法律实践。股东可以通过提起停止之诉(Unterlassungsklage)或申请临时处分(einstweilige Verfügung)来阻止股份发行。(43)Bayer, in: MüKoAktG, 5.Aufl.2021, AktG§202 Rn.13.股东优先认购权是股东的一项基本权利,因此不当地排除优先认购权属于对股东权利的侵害。(44)Koch, in: Koch Aktiengesetz, 16.Aufl.2022, AktG§203 Rn.8, 35.如果董事会在使用授权资本发行股份时进行不法行为,则每一个股东在增资之前均有权提起停止之诉。(45)Bayer, in: MüKoAktG, 5.Aufl.2021, AktG§203 Rn.171.
(二)我国不当发行停止请求权的建构路径选择
整体来看,我国应在《公司法》中明确规定不当发行停止请求权。一方面,通过法官法实现不当发行停止需依托一定的法律体系。如美国法中的不当发行的停止禁令,与其说是美国公司法的制度或规则,不如说是美国衡平救济在公司法领域的扩张。股东主张禁令救济,必须满足衡平救济的基本原则,即被侵害或可能被危及的权利必须是明确的。(46)See§4848.Equitable nature of proceedings and clear right or title in plaintiff, Fletcher Cyclopedia of the Law of Corporations, September 2021 Update.这也导致了美国法中授权股份发行时的禁令适用范围较广,法院不仅在处理股东间利益冲突以及少数股东压迫时适用禁令救济,同时在处理董事会与股东之间利益冲突时也会通过适用禁令救济来规范董事会的行为。又如德国法中的停止之诉,其适用非常狭窄,德国商事登记规则要求公司在增资之前必须进行商事登记,登记后已经实施的增资的效力不受影响,而这增加了股东提起停止之诉的难度。(47)Bayer, in: MüKoAktG, 5.Aufl.2021, AktG§203 Rn.13, 171; Koch, in: Koch Aktiengesetz, 16.Aufl.2022, AktG§203 Rn.38; Rieder/Holzmann, in: Grigoleit Aktiengesetz, 2.Aufl.2020, AktG§203 Rn.34.
另一方面,通过法律直接规定不当发行停止请求权有助于快速构建完整的规范体系。例如日本公司法的不当发行停止请求权来自1950年的日本《商法》改正,为了提高融资的灵活性,日本《商法》于1950年采用了授权资本制,2005年前日本《商法》第280条之二第1项赋予董事会决定公司募集股份发行的权力,在章程规定的预定发行股份总数的范围内,为了满足经营上的需要董事会可以发行股份。(48)大森忠夫「発行事項に関する決定」矢沢惇ほか編『注釈会社法5』(有斐閣、1968年)15頁参照;森本滋「発行事項に関する決定」上柳克郎ほか編『新版注釈会社法7新株の発行』(有斐閣、1987年)14頁参照;参见前引〔32〕,伊藤靖史文,第141-142页。对于公开公司,除了有利发行的场合,原则上由董事会决定募集事项;(49)吉本健一「募集事項の決定」神田秀樹ほか編『コンメンタール5株式3』(商事法務、2020年)19-21頁参照。而对于章程规定的全部股份转让受限的非公开公司而言,(50)日本公司法中的“非公开公司”并非我国意义上的非公众公司,其指公司股份全部存在让与限制且股份不会在市场上广泛流通的公司。田中亘『会社法』(東京大学出版会、2021年)9、10、78頁参照。原则上非公开发行需经特别股东大会决议,不过也可以通过特别股东大会委任董事会来决定募集事项。(51)参见前引〔50〕,田中亘书,第493页。基于股东在股份发行的时候没有决定权,且董事会不当发行可能对股东造成损害,日本公司法确立了不当发行的股东停止请求权。(52)参见前引〔34〕,近藤弘二文,第175页;北沢正啓『株式会社法研究』(有斐閣、1976年)319頁。
法律移植是否成功的评价标准之一是该移植的规范是否在实践中得到了适用,以及是否进行了本土化改造来适应当地法律文化和法律体系。(53)See Kanda & Milhaupt, Re-Examining Legal Transplants, The Director’s Fiduciary Duty in Japanese Corporate Law, 51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887, 890 (2003).我国商法学中也有采用此方法来评价特定法律移植是否成功。参见汤欣:《法律移植视角下的短线交易归入权制度》,载《清华法学》2014年第3期。虽然日本参考了美国的禁令制度,但并未通过法律解释或判例规则的方式发展不当发行停止,而是通过成文法直接规定不当发行停止请求权。这一规定也在后续70多年通过判例伴随着日本的授权资本制不断前进,形成了“主要目的标准”等司法实践规则。(54)参见前引〔32〕,伊藤靖史文,第144页。可见不当发行停止请求权的法律移植不仅是成功的,更是在成文法系授权资本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因此,我国《公司法》可规定不当发行停止请求权,在《公司法》中新增如下内容:股份公司董事会发行股份违反法律或章程,或以显著不正当的方式发行股份,且损害股东利益时,股东可以请求公司停止股份发行。具体而言,我国未来《公司法》中不当发行停止请求权的规范表达为:在董事会依公司章程或股东会特别决议授权决定股份发行时,如果该股份发行违反法律或公司章程,或股份发行的方法存在显著不公正,且股东因股份发行而遭受损害,则该股东可以请求法院命令公司停止该股份发行。
四、不当发行停止请求权的行使要件
在明确不当发行停止请求权的正当性基础和建构路径后,应当对不当发行停止请求权的行使要件进行分析。不当发行停止请求权包含“不当发行”以及“股东遭受损害”两个行使要件,以下将分别论述。
(一)不当发行
股份发行尚未开始时可行使不当发行停止请求权。不当发行停止请求权是事前规制,如股份发行已经生效则不得主张不当发行停止请求权。例如在美国法中,股东主张禁令救济,必须满足衡平救济的基本原则,即被侵害或可能被危及的权利必须是明确的。(55)See§4848.Equitable nature of proceedings and clear right or title in plaintiff, Fletcher Cyclopedia of the Law of Corporations, September 2021 Update.不当发行包括违法发行、违反公司章程发行、有利发行、以不公正的方法进行的发行等情形。(56)参见前引〔5〕,沈朝晖文。进一步而言,不当发行可以归纳为“股份发行违反法律或章程”以及“股份发行存在显著不公正”两个类型。
1.股份发行违反法律或章程
违法发行和违反公司章程发行均属于具有违法性的股份发行。违反法律的股份发行具有违法性;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份发行的违法性在于其违反了作为团体生活共同规则的公司章程。公司章程是公司经营、管理以及治理的法律文件,是股东、公司、董事之间的契约。公司章程是公司法秩序中权利分配秩序的一部分,通过公司章程公司、股东以及董事的职权、权利以及义务得以明确化。因此股份发行如违反公司章程,则是违反了公司、股东和董事通过公司章程形成的私法秩序。是否依违反法律或公司章程进而对公司组织行为命令停止、认定不生效力或无效,涉及消除公司组织行为违法性与维护公司内外部法律关系安定性的平衡。(57)例如决议无效目的为实现消除违法性与保持安定性之间的平衡。参见前引〔13〕,叶林文。由于该停止请求权仅在股份发行之前允许股东行使,公司的利益相关者并未依据不法的组织行为形成复杂的内外部法律关系,自然其保护法律关系安定性的考虑也相对较弱,因此前述价值平衡中应侧重消除组织行为违法性。
有利发行指的是公司对第三方或特定股东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发行股份,其造成了旧股东和新股东之间的不平等,这一价格在不具有商业目的的情况下无法被正当化,以至于在规范上该有利发行被评价为以不公正的方式发行股份,因此有利发行在规范层面属于显著不公正发行的一种情形。日本《公司法》对有利发行设置了相对明确的规制,日本《公司法》第199条第2项要求有利发行需经股东会决议,且第3项要求董事在股东会上说明有利发行的必要性,所以也有学者将有利发行归为违法发行,(58)参见前引〔50〕,田中亘书,第516页。相比较而言,我国《公司法》及二审稿并未规定股份发行的价格规制,但行政规章中仍存在价格规制。
对于有利发行,《公司法》及二审稿并未规定公开发行以及非公开发行的价格下限,但证券发行监管体制存在对股份发行价格的监管。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2020年修正)第13条第3项规定,向不特定对象公开募集股份(简称“增发”)的发行价格应不低于公告招股意向书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或前1个交易日的均价;第22条规定,可转债的转股价格不低于募集说明书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1个交易日的均价;第38条第1项规定,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80%。(59)《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2020年2月14日证监会令第163号)。
是否应当在有利发行时适用不当发行停止请求权,其核心的事理在于规制有利发行时能够平衡公司取得融资的需求与股东保护需要。从公司经营的角度来说,股份公司发行新股的价格应由董事会自主决定,如董事会考虑到公司股价在未来可能因经营不力而下跌,相比较以市场价格发行新股,采用较低价格发行新股能够更有效地取得资金,则法律应尊重董事会的商业判断,以发挥资本市场支持公司发展和恢复的功能。行政规章虽然有助于通过发行价格规制保护现有股东,但可能从反面抑制了公司的融资能力,不符合证券法资本市场功能实现的规范意旨。(60)证券法或资本市场法的规范功能包含企业融资的“经济功能”与投资者保护的“法律功能”。参见蒋大兴:《公司法的观念与解释I:法律哲学&碎片思想》,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82页。并且考虑到资本市场的实际效率,证券价格可能难以在一定时间内下跌以反映经营不善公司的股票价值,所以法律应适当放松对有利发行的规制,不必因股份发行可能违反价格规制就直接支持股东不当发行停止请求权或认定股份发行无效的主张。
相对妥当的是,在《公司法》中规定董事应通知股东有利发行相关事项,令董事以及有利发行中的认购人承担举证责任,并将是否主张不当发行停止请求权的决定权交于股东来判断,要求法院在认定是否应当停止有利发行的场合关注是否存在多数股东对少数股东的压迫,以回归股东权利保护的规范目的,实现法律对股份发行价格的规范,并督促董事会妥善行使决定股份发行的权力。如在美国法中,公司向公司内部人(insider)以比外部人(outsider)可获得的价格低得多的价格发行股份,且股份发行会导致公司中股东的权益被稀释时,公司内部人承担证明交易公平(fairness)的证明责任。(61)See Lerner v.Lerner Corp., 132 Md.App.32, 750 A.2d 709 (2000); Schwartz v.Marien, 37 N.Y.2d 487, 335 N.E.2d 334 (1975); Dingle v.Xtenit, Inc., 20 Misc.3d 1123(A), 867 N.Y.S.2d 373 (Sup.Ct.2008).任何稀释现有股东权益的股份发行,如果价格低于现有股份,则相应受益人需承担证明该交易公平的证明责任,不过当股份发行具有商业目的且不存在违反股东平等的情形时,则可以以不同价格发行同一类别的股份。(62)See Bodell v.Gen.Gas & Elec.Corp., 15 Del.Ch.119, 132 A.442 (1926), aff'd, 15 Del.Ch.420, 140 A.264 (1927); Allied Supermarkets, Inc.v.Grocers' Dairy Co., 391 Mich.729, 219 N.W.2d 55 (1974).
同时,应当考虑公司的类型差异。美国法院在审查不当发行时对公开公司(companies whose shares are publicly traded)以及封闭公司(close corporation)有不同的审查标准。对于公开公司,股份的市场价格是判断董事会股份发行决定是否合理的有效标准,因为如果新股以低于市场价格的方式发行,则没有认购新股的旧股东就会遭受其所持有股权价值减少的损失,尽管董事会确定发行价格仍需考虑账面价值、可盈利能力、市场条件、发行规模、公司声誉等要素。(63)See Bodell v.Gen.Gas & Elec.Corp., 15 Del.Ch.119, 132 A.442 (1926), aff'd, 15 Del.Ch.420, 140 A.264 (1927).而对于封闭公司,法院主要关注特定股份发行是否打破了股东间微妙的权力与经济平衡,在封闭公司的不当发行中,股份的发行价格以及其对现有股东权益的稀释是争议焦点。(64)See Maguire v.Osborne, 388 Pa.121, 130 A.2d 157 (1957); Direct Media/DMI, Inc.v.Rubin, 171 Misc.2d 505, 654 N.Y.S.2d 986 (Sup.Ct.1997).但考虑到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现状,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同时存在股权集中型与股权分散型两类上市公司,从而使股份发行中的有利发行体现为股东间冲突与董事—股东冲突。因此,如该公司为公开公司,必须兼顾董事对商业目的的陈述与市场价格两项考察要素,若董事证明该有利发行具有商业目的,则法院需综合考虑该股份的市场价格,并判断是否应支持股东行使不当发行停止请求权。
2.股份发行存在显著不公正
所谓显著不公正,指的是发行股份的目的不正当。发行行为的目的不正当主要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围绕公司控制权争夺可能存在不正当目的,例如在公开收购场合中,董事会在章程授权的范围内为了反对敌意收购而进行股份发行,这不仅意味着董事会通过股份发行提高了收购门槛,稀释了公开收购人(binder)在目标公司中持有股份的比例以巩固管理层,也意味着授权资本制下通过公开收购实现控制权变更,导致更换效率低下的管理层的目的落空,从而无法通过控制权市场实现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制度目的。实践中股份发行的目的是剥夺多数股东的控制权也属此类。(65)See Canada S.Oils, Ltd.v.Manabi Expl.Co., 33 Del.Ch.537, 96 A.2d 810 (1953).另一方面,不公正发行也体现在股东压迫上,例如公司不是为了商业经营,而是为了降低反对股东/少数股东的持股比例而发行股份。(66)前田庸『会社法入門』(有斐閣、2018年)338頁参照。
日本法院常常采用“主要目的标准”审查股份发行,如果董事会发行股份的种种目的中,不当目的的程度超越了其他目的,以至于该不当目的形成了该股份发行的主要主观要素,则认定该股份发行存在显著不公正。(67)参见前引〔32〕,伊藤靖史文,第144页。可见,日本公司法中的主观目的标准实质是通过考察董事会发行股份的主观目的,进而判断是否应当支持股东停止该股份发行的诉讼请求。不过,在司法审判中考察行为人的主观动机或心理状态可能存在一定困难,因此主观目的标准比较模糊。法院需考察董事会决定股份发行的主观目的,但更应结合其他规则来明确认定逻辑。如果采取不正当目的与商业目的的比较方式来判断,则意味着完全交由法院自由裁量,这可能减弱不当发行停止请求权规范的确定性,不仅难以为受压迫股东提供合理预期,从而督促其合理规划其救济途径的选择,也不利于董事会妥善确立公司融资计划,行使其对公司的管理权。因此,需要为不当发行的规范适用提供简单的适用逻辑,并设置相对简单以及清晰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
如果要求股东承担举证责任,则有可能提高股东行使其不当发行停止请求权的难度,但如果要求董事承担举证责任,则意味着法律需推定董事的特定行为不符合管理权的正当行使,存在法律过度介入公司治理以及自治的嫌疑。因此,更为妥当的做法是在尊重公司自治以及董事会自由行使管理权的基础上,要求股东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但对证明标准不做较高要求。在股东初步证明后,要求董事会举证证明其股份发行具有正当目的、具有合理性,一方面,此时股东利益很有可能受到股份发行的负面影响,要求董事会举证股份发行符合商业判断不属于过分干涉公司自治;另一方面,董事会作为决定机关,对股份发行的决策掌握更多信息,相较于股东更有能力证明股份发行的合理性。
(二)股东遭受损害
1.“损害”的基本含义
股东遭受损害是不当发行停止请求权的行使要件之一,因为不当发行停止请求权的法律性质为股东的固有权,只有当股东自身利益遭受损害时,股东才能够主张不当发行停止请求权,因此其也为基于股东自身权利的停止请求权,这与董事、监事或股东以公司名义提起的针对董事等管理人员不当行为的停止请求权有所不同。类似地,日本法将不当发行时股东停止请求权的法律性质定为基于股东自身权利的诉权,这一点区别于基于公司权利的停止请求权。(68)参见前引〔29〕,近藤弘二文,第287页。如果董事不法行为将对公司造成难以恢复的损害,那么股东可以依据代表之诉,行使日本《公司法》第360条(2005年前日本《商法》第272条)的停止请求权,但是如果董事不法行为不会对公司造成损害,仅损害股东利益,那么股东不能代表公司主张第360条的停止请求权,仅能够主张日本《公司法》第210条的股东停止请求权。
具体而言,股东遭受的损害应达到一定程度方可主张不当发行停止请求权。如果损害较为轻微,则没有必要通过停止股份发行来保护股东权利,可以通过董事损害赔偿责任或反对股东回购请求权来保护股东权利,避免停止请求权行使效力对其他利益相关者预期和交易安全的影响。不当发行停止请求权旨在预防可能发生的不可恢复的损害,但停止股份发行会带来深远的影响,因此,不仅行使不当发行停止请求权的股东负有举证责任,法院也需要综合考虑股东的权利保护需要以及不作为之诉的判决对公司及投资者的影响。(69)See Levco Alternative Fund Ltd.v.Reader’s Dig.Ass'n, Inc., 803 A.2d 428 (Del.2002); Gimbel v.Signal Companies, Inc., 316 A.2d 599 (Del.Ch.), aff'd, 316 A.2d 619 (Del.1974); Bayard v.Martin, 34 Del.Ch.184, 101 A.2d 329 (1953).类似地,日本法认为,如果股份发行并未违反法律,则股东所遭受的损害需达到不当的程度,股东才可以行使不当发行停止请求权。(70)参见前引〔34〕 ,近藤弘二文,第176页;参见前引〔29〕,近藤弘二文,第288页;参见前引〔32〕,伊藤靖史文,第142-149页。
2.股东无需证明公司利益受损
股东主张不当发行停止请求权,不需要证明公司利益遭受损害。(71)参见前引〔32〕,伊藤靖史文,第147-148页。如果公司利益未遭受损害,仅股东利益遭受损害,股东也可以主张不当发行停止请求权,例如以已发行股份之市场价格发行股份,虽然不会对公司利益造成影响,但有可能降低现有股东的持股比例。(72)参见前引〔32〕,伊藤靖史文,第148页。股份的发行价格与现有股东利益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如不通过法律保护现有股东利益,可能会诱使董事会利用股份发行,采取平价或低价发行的方式,不当地降低现有股东的持股比例,从而强化管理层或双控人对公司的控制权。这一控制权强化机制是不当的,管理层或双控人控制权与提升公司价值之间存在一定关系,通过降低公司股价以及削弱股东对公司的影响的方式强化管理层或双控人控制权,很可能促使管理层滥用控制权,进而不利于提升公司价值以及股东保护。
3.损害的不可回复性
需要注意的是,股东所遭受的损害必须是未来不可恢复损害(irreparable injury)。不当发行停止请求权的规范目的不仅在于保护股东免遭不当发行的损害,以预防未来损害的发生,也需平衡授权资本制下公司对灵活便捷资金的融资需求,因此需要综合考虑是否有必要为股份发行中的少数股东提供保护。比较法上不当发行停止请求权之行使要件包含股东可能遭受不可恢复之损害。(73)龍田節=前田雅弘『会社法大要』(有斐閣、2017年)332頁参照。在考虑是否应当给予原告禁令救济时,原告必须证明其胜诉的可能性以及不给予时可能产生的不可恢复损害,且法院需考虑特定结果对原被告双方和公共利益的影响。(74)See Asarco Inc.v.Ct., 611 F.Supp.468 (D.N.J.1985).衡平救济要求损害为实质性损害(substantial injury),而抽象的、理论上的、名义上的权利受损不具有衡平救济的必要性。(75)See§4850.Character of damage or injury—need for irreparable injury, Fletcher Cyclopedia of the Law of Corporations, September 2021 Update.例如公司以资本重组为目的的股份发行违反了股东平等原则或没有考虑无表决权股东的利益,则无表决权股东可以请求法院停止该资本重组,因为相较于有表决权股东,无表决权股东更容易遭受资本重组带来的损害。(76)See Levco Alternative Fund Ltd.v.Reader’s Dig.Ass'n, Inc., 803 A.2d 428 (Del.2002); Kahn v.Tremont Corp., 694 A.2d 422 (Del.1997).
4.董事的通知义务
为了方便股东了解该股份发行是否可能对其造成损害并行使停止请求权,董事会负有通知义务。如果股东没有被通知股份发行相关事项,不仅不能及时了解股份发行事项并判断该股份发行是否对其利益造成了不可恢复之损害,也可能造成股东在股份发行之后才了解该股份发行事项以至于股东不能再行使停止请求权,因此,应要求董事会及时通知股东股份发行相关事项。二审稿未能规定股份发行时董事会对股东的通知义务,对此应予补充。德国有学者认为董事会在使用授权资本发行股份之前,需告知该股份发行的目的、发行数额以及新股认购权的排除情况,以便股东通过停止之诉维护其自身权利。(77)Bayer, in: MüKoAktG, 5.Aufl.2021, AktG§203 Rn.155.日本公司法中董事会在向公司外第三人募集股份发行时,需在付款日两周前公告该募集事项并通知股东,包括募集金额是否对第三人有利、募集动机与目的是否存在显著不公正等内容,未经公告与通知程序的股份发行原则无效。(78)江頭憲治郎『株式会社法』(有斐閣、2021年)789頁参照。尤其当股份发行可能导致控制权变更时,日本《公司法》在2014年改正时新增了206条之二,规定当新股认购人可能因认购持股超过表决权50%的新股发行场合,公司应将该认购人的相关信息以与募集事项相同的方法进行公示。
五、结 语
本次《公司法》修订开创性地引入了授权资本制,相应地应强化股份发行事前规制。不当发行主要表现为股东间利益冲突中的少数股东压迫与董事—股东的代理成本问题,其规制重心为保护股东利益,基于规范董事管理权行使、保护股东权利、禁令救济的经济效率、股东权利的合同理论等正当性基础,《公司法》应建构不当发行停止请求权。股东行使不当发行停止请求权需满足“不当发行”与“股东遭受损害”两要件。同时《公司法》应规定股份发行之前董事的通知义务。规制不当发行需兼顾公司融资与股东权利保护这两项价值,考虑事前规制与事后规制的救济路径异同,并实现消除公司组织行为不法性与公司关系安定性的平衡。除了事前规制以外,未来《公司法》需要在立法修订阶段考虑事后规制的规则,如股份发行无效之诉、股份发行不存在之诉与股份发行的损害赔偿制度,还应当在司法实践等方面发展具体的适用规则和判断标准,推动我国公司法律制度的精细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