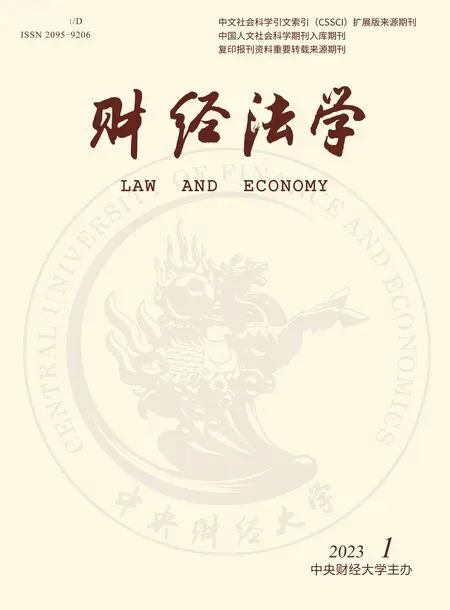《民法典》违约精神损害赔偿条款的司法适用
——基于《民法典》生效后202个案例的实证考察
许素敏
内容提要:《民法典》第996条系真正的违约精神损害赔偿条款,该条规定的精神损害赔偿属于违约责任,守约方可直接在违约之诉中主张精神损害赔偿,而无需再绕道侵权之诉。违约精神损害赔偿不以守约方的人格权遭受侵害为前提条件,也适用于其他可能导致合同当事人精神利益受损的情形。违约精神损害赔偿适用的合同类型应以可预见性规则作为判断标准,从“合同目的与当事人精神利益紧密相关”“合同标的物具有情感价值”“合同与人身安全密切相关”三个维度判断具体合同纠纷是否可以适用违约精神损害赔偿。
一、引 言
违约精神损害赔偿一直是学术界争议比较大的话题。传统民法理论认为精神损害赔偿不属于违约责任的范畴。(1)参见王利明:《侵权责任法与合同法的界分——以侵权责任法的扩张为视野》,载《中国法学》2011年第3期。《民法典》生效之前,多数法院认为违约责任不包括精神损害赔偿,(2)参见辽宁省盘锦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辽11民终1201号民事判决书。只有少数法院支持守约方在违约之诉中提出的精神损害赔偿诉求。(3)参见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苏11民终2969号民事判决书。2010年11月1日开始实施的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1条规定:“旅游者提起违约之诉,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告知其变更为侵权之诉;旅游者仍坚持提起违约之诉的,对于其精神损害赔偿的主张,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条款直接否定旅游纠纷中违约之诉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多数法院据此直接驳回旅游者的精神损害赔偿诉求。(4)参见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7民终3013号民事判决书。违约之诉不支持精神损害赔偿几乎成为司法实践的惯常做法。对于此种现象,学界也不乏批评之声。例如,以崔建远教授为代表的多位学者主张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并非侵权所独有,违约场合也可适用。(5)参见崔建远:《精神损害赔偿绝非侵权法所独有》,载《法学杂志》2012年第8期;陆青:《违约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研究》,载《清华法学》2011年第5期。《民法典》第996条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损害对方人格权并造成严重精神损害,受损害方选择请求其承担违约责任的,不影响受损害方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该条款首次在民事基本法层面明确违约产生的精神损害赔偿应获得支持,但其是否属于真正的违约精神损害赔偿条款,存有诸多疑惑,引发学界的激烈讨论。本文将以《民法典》生效后审结的202个民事案例(6)在中国裁判文书网,笔者在“全文检索”部分输入“民法典”和“第九百九十六条”,检索日期为2022年6月19日,检索结果显示符合条件的裁判文书共有247份。经过进一步的阅读、筛选,以《民法典》第996条为裁判依据的民事案例共有202个。在这202个民事案例中,有3个案例虽未明确以《民法典》第996条为裁判依据,但法院在裁判说理部分明确论述适用《民法典》第996条的法律后果,能够反映该条款的司法适用情况,因此本文也将这3个案例列为样本案例。这3个案例分别参见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2021)津0102民初527号民事判决书;河北省唐山市古冶区人民法院(2021)冀0204民初374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0604民初29126号民事判决书。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民法典》第996条在司法适用中面临的困境,并提出解决建议。
二、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困境
《民法典》第996条虽然明确守约方主张违约责任不影响其主张精神损害赔偿,但该条款存在诸多尚不明朗之处,由此导致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司法适用存在诸多疑难问题,未能形成统一的司法裁判观念,有待进一步厘清与明确。
(一)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正当性存疑
按照《民法典》第996条的规定,守约方提起违约之诉,并不影响其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由于立法者采用“不影响”的表述,导致该条款所规定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存在性质不明的问题,《民法典》第996条是否确立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在理论和司法层面均存在较大分歧。所谓的“不影响”,指的是守约方请求违约方承担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不因其主张违约责任而消灭,具体存在三种可能。其一,守约方可以在违约之诉中同时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侵权责任。例如,有学者认为《民法典》第996条实际是采用诉的合并的方式,将违约之诉和精神损害赔偿合并审理,属于请求权的聚合。(7)参见任明艳:《民法典中违约精神损害赔偿新规探析》,载《人民法院报》2021年1月7日,第7版。也有学者认为根据《民法典》第996条的规定,守约方既可以基于对方的违约行为主张财产损害赔偿,也可以基于对方的侵权行为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守约方可以同时行使两种请求权,这两种请求权不属于择一行使的相互排斥关系。(8)参见齐晓丹:《〈民法典〉人格权编理解与适用应注意的十个问题》,载《法律适用》2020年第17期。其二,守约方可以在违约之诉之外另行提起侵权之诉,向违约方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侵权责任。例如,有学者指出,根据《民法典》第996条,对于违约行为引起的精神损害赔偿,需要在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竞合时提起侵权之诉才可能获得。(9)参见刘小璇:《论违约精神损害赔偿》,载《法学杂志》2021年第6期。其三,守约方可以在违约之诉中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违约责任。例如,薛军教授认为《民法典》第996条应作如此解释:处于合同关系中的当事人,如果一方的违约行为损害了对方的人格权并造成严重的精神损害,守约方可以选择通过违约损害赔偿之诉来追究对方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而且这里不存在两个诉,只有一个违约之诉,而无需另行提起一个侵权之诉。通过这种解释模式,能够把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真正纳入合同责任的框架中,直接将《民法典》第996条规定的精神损害赔偿视为真正的违约精神损害赔偿。(10)参见薛军:《〈民法典〉对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发展》,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司法实践中,多数法院在援引《民法典》第996条做出判决时,并未对该条规定的精神损害赔偿的性质作过多的阐述。当然,也有部分法院进一步阐述该条文的精神损害赔偿的责任性质以及守约方实现精神损害赔偿诉求的路径,但存在较大分歧。
有的法院认为《民法典》第996条规定的精神损害赔偿属于侵权责任。例如,在“黄某某、李某某与陈某某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11)参见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20)沪0106民初14417号民事判决书。中,法院认为黄某某、李某某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其请求权基础为侵权。违约赔偿与精神损害赔偿可同时主张,但能否支持要视案件情况是否符合侵权责任的有关规定而定。在“袁某某与淄博市公共汽车公司临淄分公司等公路旅客运输合同纠纷案”(12)参见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法院(2022)鲁0305民初459号民事判决书。中,法院在解读《民法典》第996条时指出,违约责任和精神损害赔偿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并行赔偿,实际上否认该条款的精神损害赔偿属于违约责任,而是将其视为一种侵权责任。在“杨某某与石河子市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王某某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13)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人民法院(2021)兵9001民初389号民事判决书。中,法院援引《民法典》第996条,并认为守约方在违约之诉中,可以同时主张侵权责任。上述三个案例实际上是采用“诉的合并”方式,在违约之诉中支持守约方关于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诉求。
在“王某某等与台州朗高医养护理院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案”(14)参见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2021)浙1004民初50号民事判决书。中,法院认为违约责任的一般原则是不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但涉及人身权利或以精神利益满足为主要目的的合同,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格权的,可以采用精神损害赔偿方式对人格权遭受的侵害实行救济。显然,该案法院将特殊合同产生的精神损害赔偿视为违约责任。在“廖某某与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阳朔支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案”(15)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阳朔县人民法院(2021)桂0321民初1218号民事判决书。中,法院认为《民法典》第996条表明只有非违约方遭受严重精神损害的情形下,才能在违约责任中主张精神损害赔偿,也将此处的精神损害赔偿视为违约责任。在“张某某与桃江万基旅游置业有限公司等合同纠纷案”(16)参见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湘09民终129号民事判决书。中,法院则直接指出,《民法典》第996条已正式确立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有的法院则只强调基于《民法典》第996条的规定,守约方可以在请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时,一并要求其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但并未明确界定精神损害赔偿的责任性质。(17)参见湖北省宜昌市葛洲坝人民法院(2021)鄂0592民初117号民事判决书。由此可见,司法实践中,关于《民法典》第996条规定的精神损害赔偿的性质,未能形成统一认识。
(二)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要件不明
从文义解释的角度来看,适用《民法典》第996条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应包含以下要件:(1)双方当事人存在合同关系;(2)当事人一方存在违约行为;(3)违约行为侵害守约方的人格权并导致严重精神损害;(4)守约方已经提起违约之诉。从样本案例来看,很多法院并未严格遵循《民法典》第996条规定的适用要件。
首先,有的案件属于纯粹的人格权侵权案件,双方当事人之间并不存在合同关系,但法院仍适用《民法典》第996条做出相应的裁判。例如,在“刘某某与方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名誉权纠纷案”(18)参见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人民法院(2020)豫1322民初6295号民事判决书。中,原告刘某某未在被告方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处借款,其个人征信却有逾期贷款记录。法院基于《民法典》第996条,支持原告的精神损害赔偿诉求。该案双方当事人并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合同关系,故适用《民法典》第996条并不合理。此类案件属于纯粹的侵权案件,并不涉及违约精神损害赔偿。(19)类似案件可参见湖南省永州市双牌县人民法院(2021)湘1123民初316号民事判决书。没有违约行为,即便存在精神损害,也不适用违约精神损害赔偿,(20)参见徐静:《我国违约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制度的构建——以〈合同法〉第113条解释论为中心》,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不能适用《民法典》第996条,而只能考虑《民法典》第1183条第1款之规定。
其次,在部分案件中,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合同关系,守约方选择提起侵权之诉,法院仍适用《民法典》第996条进行裁判。例如,在“刘某某与川汇区玫瑰婚庆礼仪店一般人格权纠纷案”(21)参见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2021)豫1602民初765号民事判决书。中,原告刘某某与被告川汇区玫瑰婚庆礼仪店签订了婚庆服务合同,约定被告需保存好婚庆服务项目所拍摄的影像资料。被告因录像丢失未能如约提供婚礼的影像资料。法院认为被告的过失行为致使婚礼影像资料灭失,使原告无法获得婚礼场景的影像再现,侵害了原告享有结婚美好回忆这一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权利,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依据《民法典》第996条判定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民法典》第996条的适用要件之一在于守约方请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如果守约方请求违约方承担侵权责任,则可以直接依据《民法典》第1183条第1款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无须适用《民法典》第996条。(22)参见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人格权编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39-40页。
最后,有的案件中,违约方的违约行为并未侵害守约方的人格权,法院仍依据《民法典》第996条支持守约方的精神损害赔偿诉求。样本案例中有多个“婚庆服务类”案件支持守约方的精神损害赔偿诉求。例如,在“龚某某、王某某与宁波市鄞州琪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案”(23)参见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2021)浙0212民初3120号民事判决书。中,被告宁波市鄞州琪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为原告龚某某、王某某提供婚礼会场布置服务时出现新娘名字写错等违约行为。法院认为婚礼对于新人来说是一种精神利益的体现,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祝福,这种场景不可复制、不可再现,其承载的人格和精神利益要远大于其本身的成本价值,被告的违约行为给原告造成了一定的精神损害,支持原告的精神损害赔偿诉求。婚礼固然承载一定的人格利益和精神利益,婚礼未能圆满举办会对新人造成一定的精神损害,但难以说明其侵害了新人的人格权。《民法典》第996条规定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以守约方的人格权遭受侵害为前提,可能导致该条款在司法适用层面存在明显的解释漏洞。
(三)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不清
《民法典》第996条并未明确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是否意味着任何类型合同,只要满足该条款规定的要件,就能够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对此,司法实践也存在一定的分歧。以旅客运输合同为例,样本案例中,多数法院认为旅客运输合同纠纷中,守约方可以依据《民法典》第996条主张精神损害赔偿责任,(24)参见湖南省邵阳市北塔区人民法院(2021)湘0511民初43号民事判决书。也有部分法院明确指出旅客运输合同纠纷不能适用《民法典》第996条。例如,在“刘某某与张家口通泰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公路旅客运输合同纠纷案”(25)参见河北省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冀07民终1354号民事判决书。中,法院认为《民法典》第996条虽然规定非违约方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但当事人订立合同应主要以实现精神利益为目的,例如遗体、骨灰等人格物保管合同,医疗(美容)服务合同,婚礼服务合同,旅游服务合同等,本案属于旅客运输合同纠纷,刘某某要求精神损害抚慰金没有法律依据。该法院将“主要以实现精神利益为目的”作为界定违约所致精神损害赔偿适用范围的标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并不周延。旅客运输合同虽不是以实现精神利益为主要目的,但如果发生交通事故,将损害旅客的人身权利,也会导致旅客的精神利益受损,故以合同目的为《民法典》第996条的唯一适用标准并不周延。关于适用范围的问题,也有法院提出不同的见解。在“王某某等与台州朗高医养护理院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案”(26)参见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2021)浙1004民初50号民事判决书。中,法院则认为《民法典》第996条规定的精神损害赔偿适用于涉及人身权利或以精神利益满足为主要目的的合同,从而将与人身权利相关的养老服务合同纳入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
三、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正当性证成
因违约所致精神损害可以在违约责任的体系之下予以救济,《民法典》第996条系真正的违约精神损害赔偿条款,守约方在违约之诉中主张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具有充分的正当性,而无需绕道侵权之诉。
(一)精神损害赔偿并非专属于侵权责任
在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二元救济体系下,一般认为非财产损害赔偿只适用于侵权领域,而违约损害赔偿应限定为财产损害责任,不包括非财产损害责任。(27)参见尹志强:《论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正当性及适用范围》,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究其根源,在于传统理论认为精神损害赔偿通常由法律特别规定。(28)参见柳经纬:《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立法问题探讨——以〈民法典各分编(草案)〉第七百七十九条为对象》,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7期。《民法典》生效以前,我国有关精神损害赔偿的内容分布于《侵权责任法》、2001年3月10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等规范性文件之中。有关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基本都要求人身权益遭受侵害。故而,精神损害赔偿只适用于侵权之诉成为一般性的规则。《合同法》并未明确规定精神损害赔偿属于违约责任,在此背景之下,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缺乏正当性,多数法院以此为由不支持守约方的精神损害赔偿诉求。例如,在“罗某某等与重庆中国青年旅行社有限公司旅游合同纠纷案”(29)参见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2019)渝0103民初1207号民事判决书。中,法院认为精神损害赔偿属侵权之诉的赔偿范围,原告提起的系违约之诉,故不支持原告的精神损害赔偿诉求。在“叶某某与诸暨市长途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30)参见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2008)诸民二初字第724号民事判决书。中,法院认为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不属于违约民事责任,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前提是存在侵权行为,由于被告并不存在故意侵害原告生命权的情节,故而不支持原告的精神损害赔偿诉求。
在比较法上,2002年债法改革以前,《德国民法典》亦将非财产损害赔偿限定于侵权领域。《德国民法典》原第253条明确规定:“损害为非物质上的损害时,仅在法律有规定的情形下,始得要求以金钱赔偿损害。”(31)参见郑冲、贾红梅译:《德国民法典》,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51页。《德国民法典》原第847条则规定精神损害赔偿金适用于以下两种情形:其一,侵害身体或者健康,以及剥夺人身自由的情况;其二,对妇女犯有违反道德的犯罪行为或者不法行为,或者以欺诈、威胁或者滥用从属关系,诱使妇女允诺婚姻以外的同居的。(32)参见前引〔31〕,郑冲、贾红梅译书,第201页。从体系上看,该条位于《德国民法典》债法编的“侵权行为”之中。据此,精神损害赔偿只能在侵权之诉中主张。(33)2002年以前,《德国民法典》第651f条第2款规定:“旅游无法进行或者明显受损害时,游客也可以因无益地使用休假时间而要求以金钱作为适当赔偿。”参见前引〔31〕,郑冲、贾红梅译书,第158-159页。因此,旅游合同属于法律特别规定能够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情形。除此之外的其他类型合同均不得适用精神损害赔偿。2002年债法改革之后,《德国民法典》原第847条被重新整合,并作为《德国民法典》第253条第2款。(34)《德国民法典》第253条第2款规定:“因侵害身体、健康、自由或性的自主决定而须赔偿损害的,也可以因非财产损害而请求公平的金钱补偿。”参见陈卫佐译注:《德国民法典》(第5版),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95页。从体系上看,该条款位于《德国民法典》债法编的总则部分中,不仅适用于侵权领域,也适用于合同领域。故在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竞合的情形下,守约方可以在违约之诉中直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违约责任。《德国民法典》关于非财产损害赔偿制度的调整是一次历史性变革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35)参见韩赤风:《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划时代变革——〈德国民法典〉抚慰金条款的调整及其意义与启示》,载《比较法研究》2007年第2期。类似的,《墨西哥民法典》也规定,精神损害可以在所有类型的责任中获得赔偿,侵权者以及违约者都可能被要求进行金钱赔偿。(36)See Vernon Valentine Palmer ed.,The Recovery of Non-Pecuniary Loss in European Contract Law,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p.8.
按照《合同法》第107条、第112条、第113条第1款的规定,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的损失,但上述条款所规定的损失应作何理解,存在较大争议。有的法院认为上述条款规定的损失仅指财产损失,不包括精神损失。(37)参见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2018)川0104民初7837号民事判决书;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鄂08民终361号民事判决书。事实上,从文义解释的角度来看,上述条款所规定的损失并未排除“精神损失”。相关释义也指出,这里的损失包括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给另一方当事人造成的财产等损失,但同时也列举了一个摄影冲印单位因丢失客户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照片底片进而需要赔偿客户的精神创伤的案例。(38)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释义》(第2版),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82、184页。司法实践中,也不乏法院持相同立场。(39)相关案例亦可参见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粤09民终1702号民事判决书。如“谭某某与湘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茶陵客运分公司等公路旅客运输合同纠纷案”(40)参见湖南省株洲市茶陵县人民法院(2018)湘0224民初275号民事判决书。中,法院认为《合同法》第107条(《民法典》第577条)规定的赔偿损失并没有排除精神损害。《合同法》第113条第1款(《民法典》第584条)并未将违反合同所应赔偿的损失限定为物质损失,并没有排除违约精神损害赔偿。故而,法院支持原告的精神损害赔偿诉求。我国现行立法并未明确排除精神损害赔偿在合同法领域的适用。侵权责任法详细规定精神损害赔偿规则并不能当然推定精神损害赔偿不属于违约责任的范畴。“侵权责任不是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唯一乐园,精神损害赔偿同样游弋于违约责任。”(41)杨显滨:《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中国式建构》,载《当代法学》2017年第1期,第116页。违约和侵权只是造成损害后果的不同原因,“这些范畴本身不应该被赋予处置性的意义,因为它们只不过是一种便利的、能将那些在受保护利益、受制裁行为和制裁措施方面具有共同特征的诉因集中在一起的阐释性工具”(42)〔澳〕凯恩:《侵权法解剖》,汪志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25页。,不能直接决定精神损害赔偿的有无。《民法典》第186条肯定人身权益遭受损害时,违约责任所具有的补救功能,故伴随人身权益损害所发生的精神损害也理应在违约责任的救济范围之内,如果违约责任将精神损害赔偿排除在外,是人为地设置障碍,也与违约损害赔偿的完全赔偿原则相悖。(43)参见熊金才:《违约侵权责任之证成——以社会养老服务合同为视角》,载《河北法学》2020年第2期。在民法体系内,同样受到精神损害,却因责任基础不同而结果各异,依侵权可获赔而依违约却无法获赔,有违民法公平正义的法律价值。(44)参见前引〔27〕,尹志强文。
(二)精神损害赔偿符合违约责任的“可预见性规则”
英美判例法通过1854年的Hadley v.Baxendale案(45)该案的基本案情为:哈德利(Hadley)经营一家磨坊,由于磨面机的曲轴断裂,于是委托巴克森德(Baxendale)运营的航运公司将断裂的曲轴运送至原厂,以便以此仿制新轴。由于航运公司的疏忽导致曲轴延迟几日交付。因此,哈德利向巴克森德提出索赔,要求其赔偿因曲轴延迟交付而导致磨坊停业的利润损失。法院认为如果双方订立了合同,其中一方违约,则另一方因违约而应获得的损害赔偿应公平、合理地被认为是自然的,即按照事物通常的进程产生于此种违约本身,或者可能被合理地认为双方在订立合同时所考虑到的作为违约的可能后果。法院认为巴克森德不对磨坊的利润损失负责,因为他没有合理预见延迟的后果,哈德利也没有告知。See Hadley v.Baxendale,(1854) 9 Exch.341.确立了违约责任的可预见性规则。而在Addis v.Gramophone Co.Ltd.案(46)See Addis v.Gramophone Co.Ltd.,(1909) A.C.488(H.L.).中,英国判例法确立了违约精神损害不予赔偿的一般规则。美国和加拿大的一些法官也基于Hadley v.Baxendale案所确立的可预见性规则,认为精神损害赔偿在合同纠纷中不能获得支持,因为精神损害赔偿不可预见。(47)See Ronnie Cohen & Shannon O’Byrne,Cry Me a River: Recovery of Mental Distress Damages in a Breach of Contract Action—A North American Perspective,42 American Business Law Journal 97,97-98(2005).我国《民法典》第584条确立了违约责任的可预见性标准,即从一般理性人视角观察某种违约行为是否通常、很可能地造成某种损害。(48)参见张红:《〈民法典(人格权编)〉一般规定的体系构建》,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精神损害赔偿是否满足违约责任所要求的可预见性标准,也存在分歧。有观点认为,违约所造成的精神损失是违约方在缔约时不可预见到的损失,也不是其应当预见到的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因而不应该由违约方对该损失负赔偿责任。(49)参见王利明:《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区分标准》,载《法学》2002年第5期。无论是在英联邦的普通法体系中,还是在苏格兰或法国的民事体系中,因违约产生的精神损害赔偿都可能受到远隔性检验(50)“损害的远隔性”是英国法律使用的一项法律测试,以决定因违反合同或违反义务而造成的哪类损失应由被告赔偿。允诺人被默认为只对违反有关允诺的通常后果承担责任。如果允诺人知道(已被告知)如果他不履行合同,将会产生一种特殊的和不寻常的损害,并且没有获得另一方的免除或限制责任的同意,他将被视为默示地承担了这种损害的责任。参见前引〔36〕,Vernon Valentine Palmer主编书,第185页。(remoteness test)的限制。(51)See Nelson Enonchong,Breach of Contract and Damages for Mental Distress,16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617,638-639(1996).可预见性规则是合同法应当遵守的重要规则,但并非所有的精神损害赔偿都是对可预见性规则的违反,原因在于合同类型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当合同履行关乎当事人的精神利益时,违约方可以在订立合同之时合理预见到违约行为可能造成的精神损害。(52)参见前引〔9〕,刘小璇文。可预见性规则根本不能成为反对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理由,反而是肯定的理由之一。(53)参见前引〔27〕,尹志强文。
四、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要件
《民法典》第996条规定了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要件,但部分要件与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设立的目的不符。鉴于该类型责任的目的在于救济因违约行为遭受精神损害的当事人,故现行法规定的违约精神损害赔偿适用要件应作适当调整,以契合制度设立的本质目的。
(一)《民法典》第996条规定的实然适用要件
按照前文归纳的《民法典》第996条关于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要件,守约方人格权遭受侵害是其请求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重要前提。结合《民法典》第990条之规定,《民法典》人格权编所保护的对象并不局限于生命权、隐私权等具备具体“名称”的人格权,也保护具体人格权之外的人格权益。虽然《民法典》第996条规定的条件是“损害守约方的人格权”,但可以扩大理解为“损害守约方的人格权益”。例如,《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征求意见稿)(2018年3月15日稿)第12条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损害对方人格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受损害方选择请求其承担违约责任的,有权要求精神损害赔偿。”(54)参见何勤华、李秀清、陈颐编:《新中国民法典草案总览(增订本)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87页。该版本草案最初采用的是“人格权益”的表述,或许是基于“人格权益”的表述与《民法典》人格权编的“编名”不符,之后的版本在第一章“一般规定”的多个条款中均采用“人格权”的表述。从《民法典》人格权编所保护的对象来看,可以将《民法典》第996条规定的“人格权”理解为范围更广的“人格权益”。(55)《民法典》生效后审结的案件中,也有法院明确将《民法典》第996条规定的“人格权”解释为“人格权益”。参见辽宁省抚顺市望花区人民法院(2021)辽0404民初1400号民事判决书。因此,守约方在请求违约方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之时,需要证明违约方的违约行为损害守约方的人格权益,除了生命权、隐私权等具体人格权,亦包括个人信息等具体人格权益以及一般人格权益。当然,该限制是否具有合理性,有待商榷。
(二)违约精神损害赔偿适用要件的应然调整:不以“损害守约方人格权”为前提
《民法典》第996条之所以将“人格权遭受侵害”作为违约精神损害赔偿适用的要件,在于传统理论认为精神损害一般产生于人格权遭受侵害的场合。(56)参见王利明:《人格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34页。《德国民法典》第253条所规定的“非财产损害赔偿”也是以身体、健康、自由和性的自主决定受侵害为适用前提,亦强调人格权益遭受侵害。该条款所规定的严格标准实际上排除了基于纯粹的痛苦、悲伤或者心理伤害的赔偿,例如未能按时交付婚纱的情形很少会上升到健康损害的程度。(57)参见前引〔36〕,Vernon Valentine Palmer主编书,第106页。从《民法典》生效后审结的案件来看,法院在适用《民法典》第996条做出裁判时,并未都要求守约方的人格权遭受侵害。
同为精神损害赔偿条款,为何《民法典》第996条与《民法典》第1183条之间在适用要件方面存在如此差别?《民法典》第996条只适用于侵害守约方人格权的情形,而《民法典》第1183条则较为全面地列举受损害方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情形。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民法典》第996条位于《民法典》人格权编第一章“一般规定”,属于《民法典》人格权编的“总则性规定”,所以必须围绕“人格权”进行具体的条款设计。(58)柳经纬教授认为:“在民法典合同编规定违约精神损害赔偿,较之在人格权编规定违约精神损害赔偿,更符合民法典内在体系的要求。”前引〔28〕,柳经纬文,第59页。笔者赞同此种观点。如在合同编规定违约精神损害赔偿,既可以构建涵盖财产损害赔偿与精神损害赔偿的违约损害赔偿框架,也可与侵权责任编所规定的精神损害赔偿(《民法典》第1183条)一同构建起完整的二元精神损害赔偿框架,较为合理。如果直接规定身份权益以及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显然与人格权编不符,也必然造成体系的混乱。鉴于《民法典》第996条的限制过于严格,应该予以目的性的扩张解释,使之包括《民法典》第1183 条所提到的人身权益以及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59)参见前引〔10〕,薛军文。也有学者指出,我国《民法典》强调民事责任概念,并以“侵权责任”为最后一编,故侵权责任规范在民法上应有更高价值,在其他编责任规范不足时可提供参照,故违约精神损害赔偿还可准用《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第二章有关规定。(60)参见张红:《中国七编制〈民法典〉中统一损害概念之证成》,载《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2021年第1期。因为我国《民法典》并未采取《德国民法典》的体例设计,即并未设立统一的“债编”,而是采取“合同编”和“侵权责任编”并列的立法设计,所以未能在立法层面明确规定适用于合同领域和侵权领域的损害赔偿一般规则。损害赔偿规则是合同领域的重要规则,既然《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规定了损害赔偿的一般规则,理应允许适用于合同领域。
首先,《民法典》第996条并未直接规定身份权益遭受侵害也可以请求违约精神损害赔偿,但按照《民法典》第1001条的规定,在特定情形下,身份权利保护可以参照适用《民法典》人格权编的相关规定,故当违约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守约方的身份权益时,守约方也可以依据《民法典》第996条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例如,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少涉及“夫妻忠诚协议”的案例,亦有当事人基于双方签订的夫妻忠诚协议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的诉求。(61)参见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2011)黄民一(民)初字第2838号民事判决书。此类案件是否可以适用《民法典》第996条,取决于夫妻忠诚协议是否具有合同效力。按照《民法典》第464条第2款的规定,与婚姻有关的身份关系协议,如果没有相关法律规定,可以根据其性质参照适用合同编的规定。我国现行法律并未明确规定夫妻忠诚协议的效力。夫妻忠诚协议属于身份关系协议,可以参照适用《民法典》合同编的相关规定,将其视为一种合同。只要夫妻忠诚协议满足合同生效的诸要件,就具有法律效力。当夫妻一方违反夫妻忠诚协议时,另一方可以基于该协议请求违约精神损害赔偿。
其次,一般来说,单纯侵害物权性质的财产权益或者纯粹经济利益、知识产权的财产权益部分,不会导致受害人的精神损害,即使受害人提出这样的主张,法院也不宜支持,(62)参见张新宝:《侵权责任法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7-58页。但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遭受侵害可能产生严重精神损害。《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4条规定,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永久性灭失或者毁损,物品所有人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民法典》第1183条在承继《侵权责任法》第22条的基础之上,吸纳《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4条的规定,扩大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民法典》第1183条第2款规定:“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侵害自然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因此,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条件首次在民事基本法层面从“人身权益遭受侵害”扩张至“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遭受侵害”。而且,规定“人身权益遭受侵害”的《民法典》第1183条第1款与规定“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遭受侵害”的《民法典》第1183条第2款,二者之间属于并列关系,故不能将《民法典》第1183条第2款规定的情形扩张解释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遭受侵害”并导致自然人的人身权益遭受侵害。例如,在“陈某、李某与刘某某合同纠纷案”(63)参见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人民法院(2021)辽1421民初1405号民事判决书。中,被告刘某某为原告陈某、李某提供婚庆服务,后被告向二原告交付的婚礼录像不能正常播放,无法正常回放二原告婚礼的完整过程,原告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法院认为被告未向二原告交付完整清晰的婚礼录像视频,导致二原告无法回顾自己的婚礼过程,婚礼情景无法再现,侵害了二原告的一般人格权益,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本案属于“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遭受侵害”所引发的精神损害赔偿,但法院最终却是基于“一般人格权益遭受侵害”支持原告的精神损害赔偿诉求。此种裁判思路显然是受《民法典》第996条“人格权遭受侵害”要件的影响。相比之下,在“何某某、陈某某与阆中市时尚婚纱婚礼摄像部服务合同纠纷案”(64)参见四川省阆中市人民法院(2021)川1381民初1111号民事判决书。中,被告阆中市时尚婚纱婚礼摄像部为原告何某某、陈某某提供婚庆摄像服务,约定被告应当就原告婚礼进行摄像并保存好影像资料,交付给原告。之后,因为被告未将视频资料邮寄给原告,且被告无留存的影像资料,原告要求被告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法院认为,婚礼摄像影像资料对于二原告来说属于特定的纪念物品,具有人格象征意义,影像资料的灭失或损毁一定程度上侵害了二原告对结婚典礼享有美好回忆的特定纪念权利,判决被告承担8000元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该案法院只是认同“婚礼摄像影像资料”具有人格象征意义,并未上升到侵害原告的人身权益层次,实值赞同。
最后,虽然“人身权益、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侵害”能够涵盖大部分的违约精神损害赔偿情形,但司法实践当中存在人身权益、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侵害所无法囊括的产生严重精神损害的情形。例如,在上文所提及的“龚某某、王某某等与宁波市鄞州琪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案”中,被告将新娘的名字打错等违约行为确实给原告造成一定的精神损害,但原告的人身权益并未受损,亦不存在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故需要设置兜底条款,以涵盖应当救济的其他情形。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属于一种违约责任,而非侵权责任,这也意味着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不应比照侵权责任的要求,无需以侵害守约方人格权为前提,如此方与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责任性质相契合,也有助于充分救济守约方的精神损害。
五、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
虽然《民法典》第996条并未明确规定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但作为一种违约责任,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必须满足可预见性规则。同时,鉴于可预见性规则的理解存在较强的主观性,应不断积累司法实践经验,归纳常见的适用案件类型,以求法院判决的确定性和法官自由裁量的适当限制。(65)参见叶金强:《论违约导致的精神损害的赔偿》,载《安徽大学法律评论》2002年第2期。本文基于样本案例,归纳违约精神损害赔偿适用的常见案件类型,并以可预见性规则作为核心标准,合理地确定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
(一)合同目的与当事人精神利益紧密相关
如果一方当事人缔结合同的主要目的是获得精神利益的满足,那么另一方当事人在缔约之时可以预见到自己违约可能导致对方遭受精神损害。以旅游服务合同为例,旅游者与旅游服务经营者签订旅游服务合同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参与旅游活动获得精神上的享受。如果旅游服务经营者违约并导致旅游者的旅游计划受阻或者不能圆满施行,显然会对旅游者的精神利益造成一定的损害。旅游服务经营者长期从事旅游服务行业,在缔结旅游服务合同之时理应预见到此种精神损害后果。在样本案例中,有16个案例的案由为旅游服务合同纠纷,法院均依据《民法典》第996条支持旅游者的精神损害赔偿诉求。又比如,婚礼庆典对于当事人来说不可重复,所以婚庆服务公司在与婚礼当事人缔结婚庆服务合同之时应当预见到婚礼的不圆满会对婚礼当事人造成一定的精神损害。例如,在“叶某某、刘某某与四川墨晟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服务合同纠纷案”(66)参见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绵民终字第1970号民事判决书。中,原告叶某某、刘某某与被告墨晟公司签订《婚礼服务合同》,被告摄影师的工作疏忽导致无法制作婚礼全程录像光盘交付原告。法院认为被告作为专业婚庆服务公司,在订立合同时能预见到其违约行为会给原告造成精神损害,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原告的精神损失符合违约责任的可预见性原则。在样本案例中,有10个案例的案由为婚庆服务合同纠纷,法院亦依据《民法典》第996条支持原告的精神损害赔偿诉求。在英美法系国家,与婚礼相关的合同纠纷案件,也普遍支持精神损害赔偿。例如,在Baillargeon v.Zampano案(67)See Baillargeon v.Zampano,NO.CV90-0308672(S),1995 Conn.Super.LEXIS 3275.中,被告违反约定,未能为原告提供婚礼拍摄服务。法院认为被告的行为导致原告遭受情感痛苦,支持原告的精神损害赔偿诉求。在Diesen v.Samson案(68)See Diesen v.Samson,(1971) S.L.T.49(Sh.Ct.).中,一位同意在婚礼上拍照的摄影师未在婚礼上出现。法院认为婚礼照片有助于新郎和新娘回忆幸福时刻并带来愉悦。由于摄影师的违约,新郎和新娘已然无法享有这种感觉,故要求摄影师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二)合同标的物具有情感价值
如果合同标的物具有一定的情感价值,且违约方在缔约时对此能够合理预见,那么因违约行为导致该标的物毁损或者灭失时,应赔偿守约方的精神损害。例如,在“何某某等与马某某服务合同纠纷案”(69)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6)新28民终2262号民事判决书。中,何某某、赵某在其亲属去世后租用马某某的水晶棺,马某某跟随何某某、赵某将遗体装进棺材并将遗体运送至何某某、赵某住处。之后,何某某、赵某亲属的遗体出现了异味。法院认为马某某的行为给何某某、赵某造成了精神上的痛苦,应当向何某某、赵某支付精神抚慰金。在Mason v.Westside Cemeteries Ltd.案(70)See Mason v.Westside Cemeteries Ltd.,(1996) O.J.No.1387(Ont.Gen.Div.).中,被告丢失原告父母的骨灰。法院认为被告一定已经考虑到丢失原告父母的骨灰会导致他精神上的痛苦,故而支持原告的精神损害赔偿诉求。
有争议的是,以宠物为标的物的合同产生的纠纷可否适用精神损害赔偿。我国法院一般不支持此类案件的精神损害赔偿。例如,在“肖某某、田某某与郑州市郑东新区康诚宠物医院保管合同纠纷案”(71)参见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豫01民终12738号民事判决书。中,原告肖某某、田某某将其饲养的泰迪犬送至被告郑州市郑东新区康诚宠物医院处,交给工作人员看管。原告离开后,宠物犬丢失,原告就此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法院认为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于法无据,不予支持。(72)类似案例参见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1)渝03民终362号民事判决书。当然,也有少数法院支持此类案件的精神损害赔偿诉求。如“董某某与张店贝合宠物服务部服务合同纠纷案”(73)参见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2022)鲁0303民初1132号民事判决书。中,被告张店贝合宠物服务部将原告董某某的比熊犬丢失,法院依据《民法典》第996条判定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失费1500元。宠物的一个“宠”字,显示出主人所耗费的心力和倾注的情感。宠物身上承载着主人的精神利益,当宠物受到侵害时,主人将蒙受巨大的精神痛苦。(74)参见易继明、周琼:《论具有人格利益的财产》,载《法学研究》2008年第1期。国外有不少判例在宠物遭受侵害的情形下支持主人提出的精神损害赔偿诉求。例如,在Newell v.Canadian Pacific Airlines Ltd.案(75)See Newell v.Canadian Pacific Airlines Ltd.,(1976) 14 O.R.(2d) 752(Co.Ct.).中,被告违反安全运送宠物狗的合同,导致原告的一只宠物狗在被告飞机的货舱中死亡,另一只重伤。法院认为,从原告对宠物狗的安全与健康的明显关切来看,被告很清楚如果它们发生任何事情,可能会导致原告的烦恼、沮丧和痛苦,这是被告可合理预见的后果,故支持原告的精神损害赔偿诉求。宠物对于主人而言具有一定的情感价值,因而在以宠物为标的物的合同中,违约方在缔约之时应合理预见到宠物的健康受损、死亡或者丢失等情形会导致主人的精神损害,故应承担相应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三)合同与人身安全密切相关
在与人身安全密切相关的合同关系中,提供服务的一方当事人也可以合理预见到另一方当事人人身权利受损时,将产生精神损害。例如,运输合同虽不以实现旅客精神利益为主要目的,但如果承运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造成旅客人身权利受损,将同时给旅客带来精神痛苦。作为长期从事旅客运输的承运人对此能够合理预见。在样本案例中,有80个案例的案由为运输合同纠纷,其中有77个案例依据《民法典》第996条支持原告的精神损害赔偿诉求。在“许某某与湖南省衡阳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衡阳市分公司公路旅客运输合同纠纷案”(76)参见湖南省衡阳市衡东县人民法院(2020)湘0424民初804号民事判决书。中,法院认为客运合同的履行关乎当事人的人身安全,违约方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可以预见到,其违约行为将不但造成当事人的人身损害,同时也将造成精神损害,精神损害也是蒙受损失的一部分。医疗(美容)服务合同、养老服务合同也与人身安全紧密相关。如果医疗服务机构存在违反合同的行为,并导致患者人身权利受损,也应该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在样本案例中,有10个案例的案由为医疗(美容)服务合同纠纷,其中有9个案例依据《民法典》第996条支持原告的精神损害赔偿诉求。例如,在“姚某某与洛阳市瀍河区秀秀涵美美容院合同纠纷案”(77)参见河南省洛阳市瀍河回族区人民法院(2021)豫0304民初198号民事判决书。中,原告姚某某到被告秀秀涵美美容院进行洗眉和祛斑,因被告在原告面部使用成分不明的药水,造成原告面部损害,故原告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法院依据《民法典》第996条判决被告承担900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如果养老服务机构未尽到充分的注意义务和安全保障义务,导致老人人身权利遭受损害,应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在样本案例中,有9个案例的案由为养老服务合同纠纷,法院均依据《民法典》第996条支持原告的精神损害赔偿诉求。在“蔡某某与山东擎天医养集团有限公司龙堌医护养老中心服务合同纠纷案”(78)参见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鲁17民终2598号民事判决书。中,被告龙堌医护养老中心未尽护理义务,导致原告蔡某某健康权受损,法院依据《民法典》第996条判决被告承担3000元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四)小结
在202个样本案例中,169个案例的案由为合同纠纷,其中以运输合同纠纷(80个)、旅游服务合同纠纷(16个)、婚庆服务合同纠纷(10个)、医疗(美容)服务合同纠纷(10个)、养老服务合同纠纷(9个)为主,共计125个案例,且只有4个案例未支持原告的精神损害赔偿诉求。(79)运输合同纠纷、旅游服务合同纠纷、婚庆服务合同纠纷、医疗(美容 )服务合同纠纷、养老服务合同纠纷案件中支持守约方精神损害赔偿诉求的比例分别为96.25%、100%、100%、90%、100%。除此之外,还有44个案例涉及其他类型合同纠纷,涵盖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装饰装修合同纠纷等类型,仅有5个案例支持原告的精神损害赔偿诉求。这5个案例也可以纳入上述三类适用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常见情形。(80)参见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辽04民终3690号民事判决书;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湘09民终129号民事判决书;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2022)鲁0303民初1132号民事判决书;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辽03民终4634号民事判决书;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2021)津0110民初3935号民事判决书。虽然《民法典》第996条未明确限定违约精神损害赔偿适用的合同类型,但是司法实践中违约精神损害赔偿主要适用于运输合同、旅游服务合同等合同类型,同时,法院主要从“合同目的与当事人精神利益紧密相关”“合同标的物具有情感价值”“合同与人身安全密切相关”三个维度综合考量其他具体合同是否适用违约精神损害赔偿。上述三种情形只是基于司法实践经验的归纳,是能够适用违约精神损害赔偿最为常见的情形,也是法院在判断具体合同所引发的精神损害是否具有可预见性的重要考量标准,但并不意味着违约精神损害赔偿仅适用于上述三种情形。在具体个案中,仍应以可预见性为基本标准,以一般理性人的视角判断具体合同纠纷是否应适用违约精神损害赔偿。
六、结 语
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系长期困扰理论界与实务界的重要问题。《民法典》第996条的出台某种程度上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但相关概念的语焉不详引发了更多的歧义与争论,并导致该条款的司法适用面临诸多难题。我国应直接承认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正当性,明确精神损害亦属于违约责任救济的范围,由此,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所救济的损害类型便无二致,均包括精神损害和财产损害,以构建完整的“违约损害赔偿”与“侵权损害赔偿”的二元损害赔偿体系。在《民法典》实施背景下,应从解释学的角度阐释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具体适用要件,通过对相关司法案例的考察与总结,进一步明确裁判规则,构建更为完善的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