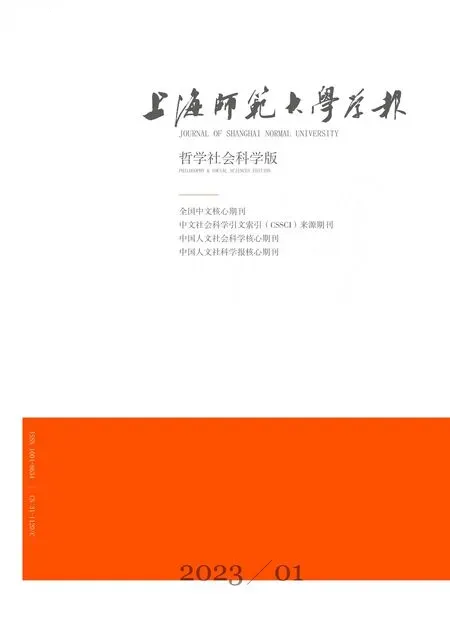从宇宙论体验到超越性体验
——沃格林论“天下时代”生存真理的分化
陈 赟
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理论刻画了人类在三个地区(中国、希腊与印度)从自然民族到历史民族的平行性演进,伴随着这一演进的是对宇宙论秩序体验的突破,以及随之而来的对经验与超越之间的生存张力的体验。①陈赟:《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理论与历史意义问题》,《贵州社会科学》2022年第5期。在对“轴心时代”理论的推进中,这一张力的重要性被强化了,如在史华慈那里。②Benjamin I.Schwartz,“The Age of Transcendence”,Daedalus,1975,104:2.p.3.沃格林以“天下时代”理论转进了“轴心时代”理论,“轴心时代”只是把握了“天下时代”的“精神突破”,而“精神突破”与“帝国征服”、“历史编纂”,乃是“天下时代”的“三元组构”。然而,二者的相通之处在于“精神突破”,沃格林以更为清晰的方式揭示了“精神突破”的实质。
沃格林以为,前天下时代的秩序典范是宇宙论秩序,人类的政治社会被内嵌到宇宙论秩序中,社会的法则与宇宙节律保持同步与一致。而天下时代秩序转换的本质是从前天下时代的社会之宇宙化原理到天下时代的社会之人化原理的转变:前天下时代“是把社会及其秩序符号化为宇宙及其秩序的相似物”,“社会将被符号化为一个小宇宙”,“把植物生长节律和天体的旋转作为社会的结构性和程序性秩序的典范,从而将以政治方式组织起来的社会符号化为宇宙的一个相似物,符号化为一个小宇宙”;而天下时代“是通过与存在十分合拍的人的生存秩序的类比来实现社会秩序的符号化”,“被符号化为一个大写的人”。①埃里克·沃格林:《以色列与启示》,载《秩序与历史》第1卷,霍伟岸、叶颖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45页。与上述秩序转型相应的则是人类体验方式从紧凑的原初宇宙体验(Compact or Primary Experience of the Cosmos)到意识之分殊化(Differentiations)的变化,这一分殊化打破了原初宇宙体验的紧凑与浑然,使得生存性真理的居间(In-between)结构得以明晰化:意识分殊化意味着原初宇宙体验转变为超越性体验,或者说转换为生存的张力性体验。
紧凑的原初宇宙体验与分殊化了的生存张力体验具有不同的象征形式。沃格林对之进行了如下的区分:
作为它们的充分的表达,这两种类型的经验产生了两套不同的系征体系。属于第一套象征体系的因素当中有:
(1)宇宙的时间;与宇宙共绵延
(2)宇宙之内的诸神
(3)神话故事和神话人物的语言
属于第二套象征体系的因素当中有:
(1)宇宙时间两极化为时间与永恒的张力;临在之流
(2)超越这个世界的上帝
(3)运用努斯的和灵性的生活的语言
因此,就“不朽”这个象征而言,我们可以说:来生的意象源自宇宙实在的笼统经验;由死亡来构造的生命这一象征,则源于人经验到他的生存朝向神性根基的张力。②埃里克·沃格林:《不朽:经验与象征》,载张庆熊、徐以骅主编:《基督教学术》第10辑,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59—160页。
以上区分包括三个层面:其一,在时间体验方面,从宇宙节律的时间到生存张力的时间的转变;其二,在神性体验方面,神从宇宙内的神到作为世界之根据的转变;其三,在符号形式方面,宇宙论秩序的体验采用的是神话的符号形式,但表达生存张力的超越体验的符号则有所分化:在古希腊通过智性意识创建了哲学符号,而在以色列则通过灵性意识创建了启示符号。沃格林对于意识从原初宇宙体验的浑然到分化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希腊—希伯来两大传统。
一、从宇宙论时间到作为生存张力的时间
宇宙论时间本质上是宇宙节律的体现。在原初宇宙经验中,时间与宇宙本身共同绵延,时间表现为四时的运行、昼夜的更替、生物的作息等所体现的宇宙节律。宇宙节律的时间往往展现为周期性的循环,任何例外、偶然与不规则都被视为不节律的表现,因而人们往往通过巫术、仪式对这些例外、偶然与不规则进行抚平,以保持宇宙时间的稳定性。在这一宇宙周期性运作的节奏时间中,有生必有死,人被经验为有死者(Thnetos),而永恒则被视为神的特质。③对于生活在更为古老、更加紧凑的形式,亦即神话形式之中的人,柏拉图将“史诗中的可朽者(Thnetos)”这一称号留给了他。参见埃里克·沃格林:《天下时代》,载《秩序与历史》第4卷,叶颖译,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第270页。人与神之间具有无法跨越的鸿沟。在上古社会中,只有少数的既是统治者又同时是巫师、垄断了通天权的领袖人物才能视为神—王(God-King),可以避免只能作为有死者的命运。但在天下时代的精神突破中,宇宙论时间被打破,人由此获得了生存张力的时间,时间本身展现一种连接时间与永恒的张力,是时间与永恒的居间——它既参与到时间之中,又不属于时间;既参与到永恒之中,又不属于永恒。居间性时间构成人之生存张力的“交叉点”,永恒与时间在人的生存体验中以相互参与的方式进入生存的当下——临在(Presence),而既是时间又不是时间的生存维度就是临在之流(Flow of Presence)。④埃里克·沃格林:《不朽:经验与象征》,第146页。
在原初宇宙经验中,事物是实质性的,不死和有死被分别归属于神和人这样一些各自独立的形体,因而,终有一死之人只能拥有与终有一死者相应的念头,而永恒不在其位分之内;这就导致了居间的生存张力不能彰显,人只是生存在时间中的存在者,无关于永恒;人是人、神是神,二者互不相属、互不相通。天下时代的精神突破,本质上是对宇宙论时间的突破,突破的结果便是在每一个人那里的生存张力被发现。这样,参与生存张力的神、人不再被作为宇宙中特定的实体性事物,而是被作为生存张力的两极被体验,宇宙论体验中的有死者与不朽者的鸿沟被跨越。
人性与神性(在中国先秦思想中则是性与天道)不再外在于人,而是构成人生存张力的两极:希腊人将这两极的一端视为人的探寻(Zetesis),另一端是神的推动(Kinesis);而以色列人则将人性的一极视为灵性意识,另一极则是来自神的牵引(Helkein)。处在生存张力中的人将会意识到他的意识不再是有死者的意识,而是作为有死者而追寻不朽的意识,其意识是参与神性根基的场所和感官中枢(Sensorium),同时分享人性和神性两极,意识既包含而又不全是时间的一端,同时又包含而不全是永恒的一极,更确切地说,意识就是这种时间与永恒之间的居间张力,既是时间又是永恒,既不是时间也不是永恒,就是这种张力性的结构。①埃里克·沃格林:《不朽:经验与象征》,载张庆熊、徐以骅主编:《基督教学术》第10辑,第157页。由此,原初宇宙体验中必由王者中介才能关联起来的分属必死性与不朽性的人神区隔被打破,人被重新定义为生活在临在之流中的生命,既不是有死者的生命,也不是不朽者的生命,而是生活在二者居间张力中的存在者。
原初宇宙经验中的不朽被属于神,整个宇宙都是具有神性意味的共同体。宇宙的永久表现为创造并维持了宇宙秩序的诸神的永久,人只能以调节自己的方式与诸神的秩序和谐,以便分享这种永久,因而不死的意向成为人与宇宙共同绵延的经验之产物。从宇宙体验到生存参与的张力体验的转变,便是打破宇宙论秩序,进入居间的生存体验,在时间与永恒之间加以连接,但又不陷于其中的一端。更进一步地说,宇宙论秩序中的不朽并非发生在普遍个体的意识内部,而是表现为以统治者(王者及其辅佐们)为主体的“来生意象”(the Imagery of Afterlife),“如在《辩论》中那样,成了太阳神帆船中的谋臣?或者如在《斐德罗》(Phaedrus)中那样,成了上帝的众多随员中的一员?”②埃里克·沃格林:《不朽:经验与象征》,载张庆熊、徐以骅主编:《基督教学术》第10辑,第158页。以中国的三代宇宙论秩序而言,作为人神中介的王者在其死后可以升天,在帝左右,无论是“宾帝”或“配天”,其所表达的都是三代秩序中统治者的不朽经验,而不是指向普遍个人的。但在天下时代的超越性体验中,由于人被体验为时间与永恒之间的交叉点,因而,每个人皆可与神相通,从而获得连接永恒的个人化路径,这一路径即隐藏在其意识的张力性结构中。
古希腊以“哲学”符号展开的智性体验,最早揭示出灵魂是时间性存在与永恒存在之间各种张力之位点(Locus of the Tension)。人凭借其灵魂而感知诸种张力,同时也感知超越性;正如他凭眼睛来感知视觉对象。③埃里克·沃格林:《记忆:历史与政治理论》,朱成明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65—366页。灵魂感知到“时间极”与“永恒极”的双极张力,其中的“时间极”在他自身之内,而超越性的“永恒极”则在世界的一切时间性存在之外。在时间极,“张力被体验为朝向神圣永恒的、某种充满爱意和希望的渴慕”;从永恒极,“张力被体验为某种带着恩典的召唤和穿透”。在居间的体验中,永恒不会被体验为时间中的某种客体,灵魂也不会被从时间性存在体验为永恒性存在。居间性的张力体验乃是灵魂通过向永恒存在的穿透充满爱意地敞开自身而展开的自我整饬。这意味着,通过临在之流的居间体验,人不再仅仅是有死者,而同时在他自己身上体验到朝向神性存在的张力,由此人的位置乃处在人神之间的“属灵之人”,即柏拉图所谓的Daimonios Anēr。在原初宇宙体验中,时间与永恒被归属于某种实质性的形体,但这只是神话语言的象征性表达。一旦在非神话的语境中,就会被执着为实体化或客体化的对象。通过哲学的智性体验,可以获得所谓的时间性并不是现成性的客体,而是一种“言语引得”(Linguistic Indices),也就是一种桥梁、道路或筌蹄,它将我们引向与永恒处在张力中的时间极上。这一时间极并不能切割为内在世界时间中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而是一个流动着的临在之场,在流动的任何一个时间点上,都保持着朝向超越时间的永恒存在的张力;而永恒存在,也是在时间中的“流动着的在场”。④埃里克·沃格林:《记忆:历史与政治理论》,第367、370、378页。相比之下,在以色列的灵性体验中,这一点进展比较迂曲。关于灵魂(Psyche)的思想之所以曾经无法在以色列得到充分发展,便是因为不朽的问题悬而未决。因为永恒的生命被理解为神的一种性质,死后灵魂的生活将会把人提升到神的境界。人性完美的思想不能打破关于一个在历史中、上帝之下正当生存的被选民族的思想。不是哲学,而是祖先历史的建构,一种特定的人文主义,以及最终是神介入历史的末世论希望被发展起来。参见埃里克·沃格林:《以色列与启示》,载《秩序与历史》第1卷,第453页。当然,在张力性生存的智性体验中,人是一个非现成的无定存在,他既可能受到来自神圣努斯(Nous)的牵引,也同时可能面对来自各种激情的反拉(Anthelkein),服从前者他将投向不朽化运动,服从后者则是选择死亡,人的灵魂就在这种有死者与不朽者较量的张力中。
二、神性体验的转变:从宇宙内最高存在者到世界的超越根基
从原初宇宙体验到超越的生存张力体验转型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宇宙内诸神转变为作为世界根基的超越之神。“原初经验所体验到的宇宙,既不是由对象组成、有待某个主体加以认知的外部世界,也不是已被某个超越于世界之上的神创造出来的那个世界。相反,它是由居下的地和位上的天构成的那个整体(to pan)——天体及其运行;季节的变化;动植物生命的生长节律;人的生活、出生和死亡;尤其是,正如泰勒斯一直知晓的那样,它是一个充满众神的宇宙。最后这一点(众神是宇宙内的)无论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因为在今天,像多神论、一神论这种轻易做出的分类几乎已经遮蔽了这一点。数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神性实在的意识,是要将其视为宇宙内的抑或超越此世的。”①埃里克·沃格林:《天下时代》,载《秩序与历史》第4卷,第127页。原初宇宙体验中的神是宇宙内之众神,是宇宙内最高事物,是宇宙整体的构成部分,神与宇宙一体,而不是作为世界根据的超越神。精神突破的结果则是神性体验从宇宙内神的体验到作为世界根基的超越神性的体验之转变,这一转变意味着神被从宇宙内同质化的参与成员中移除,有序化宇宙(Cosmos)转变为世界(World)之后,神被符号化为世界的存在根基。在古希腊的哲学与以色列的启示中,都发生了同样的事件,即对宇宙内众神的突破:“由启示和哲学带来的真理对那些宇宙内众神来说是致命的;将这些神从宇宙中移除。”②埃里克·沃格林:《天下时代》,载《秩序与历史》第4卷,第56页。这并不意味着宇宙的消失,而只是神性体验的结构性变化:“对生存真理的分殊化并未取消该事件所发生于其中的宇宙。不过,就宇宙的生存与结构而言,它被体验为由神创造出来并塑造秩序的。”③埃里克·沃格林:《天下时代》,载《秩序与历史》第4卷,第56页。神不再是宇宙内的一员,而是世界的创造者。这意味着神性体验形式的变化,即从原初宇宙经验到超越性体验的转变。
原初宇宙体验对这种体验自身的根基并不能形成清晰的意识,这是因为在宇宙体验中,物理世界,与神灵、国王和社会等,“均被视为宇宙的同质组成部分,宇宙囊括所有这一切,但又不等同于其中任何一方”;“实在的这些宇宙内区域彼此相互提供着对存在的类比,这些类比的有效性来自”作为万物之背景的宇宙之“非生存模式下的实在性”。换言之,原初宇宙经验的根基在于那种出自非生存的生存,源自某种生存与非生存的居间。但原初宇宙体验所经验的宇宙是一种不稳定的平衡中的宇宙,它的两端分别是:从虚无中出现和复归于虚无。④埃里克·沃格林:《天下时代》,载《秩序与历史》第4卷,第131—132页。然而,这种居间性的张力结构在宇宙论意识的浑然一体性中无法被清晰呈现。非生存的神性本源在同质化的宇宙体验中被象征化为宇宙内众神,生存的万物则被体验为由神塑造秩序的宇宙的同质构成部分。换言之,无论是生存还是非生存都被压缩为宇宙内事物,从分化了的智性视点看,那意味着一种彼此的混淆;而对身处原初宇宙经验中的人来说,生存与非生存者则浑然一体,没有以分殊化方式加以显现。“天体意义上的宇宙和宇宙内众神,处在生存中的万物的非生存本原变成某个既非生存着的,亦非非生存的实在的一部分。来自实在的这种张力已被吸收进那种作为整体、被称为宇宙的中间性实在。宇宙实在的居间将生存与生存的本原之间的张力封闭在它的紧凑性之中。”⑤埃里克·沃格林:《天下时代》,载《秩序与历史》第4卷,第136—137页。展现这种紧凑性与浑然性的一个例子是,人是在动物而不是人自己身上感受到更高程度的对存在的参与,这是因为“由于动物的种类历经许多代都一直保持不变的恒定性……动物的种类比个体的人生存得更为长久,所以(被认为)更接近世界和诸神的永恒存续”。⑥埃里克·沃格林:《以色列与启示》,载《秩序与历史》第1卷,第129页。埃及的宇宙论秩序中,通过某种动物来彰显真理的方式尤其引人注意:“显现的本质在具有神性的动物身上比在具有神性的国王身上体现得更为清晰。”参见埃里克·沃格林:《以色列与启示》,载《秩序与历史》第1卷,第128页。对照黑格尔的理解,埃及的神并不是思想所呈现的精神,不是一个抽象物,而是在一个节点连接了对自然的诸多直观,一个象征他物的象征。埃及人对最高存在者的直观方式是:“在被自然的东西束缚住以后,依赖自然直观,打破这种束缚,转向{自相}矛盾,把精神的东西变为动物的东西”;精神“再次被贬低为自然的象征物,与自然形态相连接”,“不是作为纯粹的精神性,而是在其特殊的本质中被把握的”。在埃及,“在被束缚于自然东西的精神中,精神是一种渴望,却不能返回到自身”,“内容在材料中使自己成为表象,而这种材料不可能是思想,它只能是感性的自然材料,是天然性的材料”。参见黑格尔:《世界史哲学讲演录(1822—1823)》,刘立群等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240—255页。
由于原初宇宙体验的核心是居间的张力,但这种张力受制于体验的紧凑性而使得居间的体验两极被以同质化神话象征加以表达,在那里,生存与非生存的居间体验以被给予的方式在神与王的同质化类比、宇宙与社会的同质化类比中被削弱,而无法向着个人的意识开放自身。但位于宇宙论意识深层的生存(王、社会)与非生存(神、宇宙)是非同质性的,同质化的体验方式也无法解释宇宙论秩序中的王朝更替与社会兴衰,尤其是当王朝易代之际的统治阶级一旦失势,那么这种同质化就会在宇宙论意识内部受到质疑。因而原初宇宙体验的内核(居间体验)必然要求突破宇宙论风格的紧凑性与浑然性的封锁,以至于内部就包含了最终自我解体的要素,“宇宙分裂为一个去神化的世界和一个超越于世界之上的神”。①埃里克·沃格林:《天下时代》,载《秩序与历史》第4卷,第137页。神从宇宙内的与人的同质化事物到超越世界之上并且作为世界的神性根基,必然发生在人的意识中。在希腊哲人那里,灵魂的发现,使得努斯被体验为神性根基的感受器,同时又是神性展现其形塑力量的场所;而人则凭借其人性努斯即可与神(神性努斯)相通,如是,把人引向王者支配的宇宙论秩序的体验转变为在精神层面朝向神性根基的超越体验。
在超越体验中,宇宙分殊化为世界与世界的神性根基。而这个超越的神性根基在哲学探究中则对着灵魂开放自身:在超越体验中,灵魂站在神的面前,并将自身体验为在存在[共同体]中向神敞开的位点(Locus of the Openness toward God in Being),随着这种体验,一种全新的、哲学与神话之间的关系得以呈现出来,这意味着,“唯有这些体验促使人把神认作世界的彼岸(the Beyond),同时,世界通过这种洞见成为内在之物——亦即神的此侧(this-Side-of-God)。对于神性[之物]来说,唯有在这种分离之后,才没有必要在神话的—发生的层面将存在释放为它的生成,而是迁动到世界的某个超越的创世造主的地位来与世界发生关系”。②埃里克·沃格林:《记忆:历史与政治理论》,第173—174页。存在的同质化经验模式被打破了,“唯有在超越体验的亮光之下,神、世界之内的事物才分别获得相对的自主性;正是这种自主性,让两者都得以放置在存在这个公分母之上。诸神因宇宙的解离变得无家可归之后,就在神之真理性(truth of God)中重新安住下来,而神性[之物]与世界的关系也因此变得清晰”。③埃里克·沃格林:《记忆:历史与政治理论》,第173—174页。神不再是宇宙论秩序中与宇宙内事物具有同质性或相似性的具体生存者,超越体验将神从与生存者的同质化想象中解放出来,只有将其与生存者同质,才有将其实体化的可能性,神现在就是神性自身,即超越的唯一神自身,神性自身就是神的真理性或现实性,因而在这种智性的超越体验中,神来到了自身。神性并不是宇宙内的具体生存者,也不是超感官的实体,而是生存张力体验中作为超越性极点的一端,它与人性极点处于结构性的张力之中。宇宙论秩序被突破之后,人的生存不再是与宇宙节律相协调,而是人性极(人)与超越极(神、天)在张力状态下的协调。
正是作为生存体验的超越极点,故而原初宇宙体验被解离而后的神性存在与世界存在,并不能被理解为分处“某条空间割线之两侧的事物”,真实的情形是,“一旦宇宙被超越体验确定地解离出来,超越与内在不过是附着于存在的(言语)引得(indices attached to being)”。④埃里克·沃格林:《记忆:历史与政治理论》,第176页。“引得”意味着体验的方向与道路,同时也意味着一种连接而抵达的“居间”,在“居间”性两极加以连接,被表达在象征中的体验,才能作为即将到来的体验之方向与引导而被重新激活。在这个意义上,神并不是一个对象,不是某个事物,当我们用象征去显现这个非对象的对象、非事物的事物时,并不能以描述客体的方式进行,只能提供指引性的方向,体验及其内容则必须由每个人以自己的方式获致,而作为他者体验之表达的象征,则是这种引导。甚至,世界的神性根基自身也并不能被实体化,因为它本来就不是作为生存者的事物,而是一种激唤性的象征,对于上达而求索的人而言,它具有一种牵引和激发的意义。即便宇宙被解离为内在性的世界与超越性的神性根基,“但那种殊显化的知识并不消解神与世界之间的存在纽带(我们将这种存在纽带称为宇宙)。对存在之宇宙性纽带的意识,是一切哲思的背景。这种意识逐渐削弱时,就会出现一些众所周知的危险:一个被祛神的世界,或一个被剥离世界的神;一个被祛神的世界,就是被还原得只剩下存在物间关系联结的世界,这样一个‘世界’不再成其为世界;一个被剥离了世界的神,就是被还原得只剩下神本身之存在的神,这样一个‘神’不再成其为神”。①埃里克·沃格林:《记忆:历史与政治理论》,第176—177页。只要陷入上述危险,人便不再会生存在居间的张力结构中,而是被错置为对象化实体或客体,或者一种从居间结构而来的将生存的天平趋向于以两极中的一极消解另一极而带来的生存论畸变(existential disformation)中。
三、从宇宙论神话到承载生存张力的哲学和启示:生存真理的分化
不难看出,神性体验的模式转换——从宇宙内的神到作为世界之超越根基的神的转变——关联着的是人性的新理解。在宇宙论秩序中,宇宙的各成员(人与神、宇宙与社会)是实质性的(substantial),存在的共同体之间具有某种交感共生的关系,彼此渗透,可谓神性秩序的同质参与者。作为由神和人、世界和社会构成的原初的存在共同体,宇宙并不能通过一种外在的旁观者视角被给予,而是以参与者视角获得对之的原发性体验,以其整个生存全身心地投入这一并不知晓剧情的演出。在紧凑而浑然一体的参与体验中,“人对存在共同体的体验如此亲密,以至于参与者们的同质性(consubstantiality)压到了各种实体所具有的独特性”。②埃里克·沃格林:《以色列与启示》,载《秩序与历史》第1卷,第42页。神话作为象征之所以更能表达原初宇宙经验,乃是由于法兰克福氏夫妇(Henri and Henriette A.Frankford)的神话研究所揭示的如下真理:在神话中,神人两者具有同质性,如果人不能与他所经验的实在同质,就不能经验到实在。③埃里克·沃格林口述、桑多兹整理:《自传体反思录》,段保良译,华夏出版社2018年版,第92页。关于神话的理解,参见亨利·法兰克福、亨丽埃特·格伦莱韦根-法兰克福:《神话与实在》,张小霞、张静昭译,载杨国荣主编:《沃格林与中国》,《思想与文化》第29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对存在共同体的各个参与者的持续与流逝(即持久性与暂时性)的高度关注,成为原初宇宙经验的特点。④埃里克·沃格林:《以色列与启示》,载《秩序与历史》第1卷,第42—43页。
生存与非生存的差异及其居间结构在这种紧凑的经验中并不能清晰给予,但却是作为一种潜在的结构而发生作用,影响生存体验。人的生存在原初宇宙体验中意味着与宇宙整体的合拍:“鉴于行动者的成功依赖于他与社会、世界和神所具有的更持久、更全面的秩序合拍,人在那部存在戏剧中的角色的含义第一次有所显示。”⑤埃里克·沃格林:《以色列与启示》,载《秩序与历史》第1卷,第43页。但在生存的超越性体验中,人不再是宇宙论秩序中的类比物或相似物,“在其人性中发现的那个既是神的显现所发生的处所,又是这种显现的感受器的东西;他找到诸如 Psyche(灵魂)、Pneuma(灵)或 Nous(努斯)这样的东西,来对这个东西加以象征化。当他参与到某个神显事件时,他的意识获得智性光辉,认识到他自身的人性是由他与未知神(the Unknown God)的关系构成的”,“新的真理与人对其人性(处于以神性本原为目标的参与式张力之中的人性)的意识相关,而与超出这片区域之外的实在无关”。⑥埃里克·沃格林:《天下时代》,载《秩序与历史》第4卷,第55—56页。超越性体验的核心是神显,它意味着对世界根据的体验。
在宇宙论秩序中,人性与王者所中介的宇宙秩序与礼法秩序密切相关,《诗经·鄘风·相鼠》云:“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它将人界定为礼仪性的存在,其存在是由礼法秩序来界定的,而礼法秩序又是对宇宙秩序的模拟。在那里,人只能作为具体社会的成员,在礼法秩序所规定的等级性名分中而确证自己的身份,在那里并没有达成从脱离具体宇宙论王国及其社会的成员资格而获得的对人性之理解。哲人、圣贤、先知所实现的“精神迸发”,正是要突破原初的宇宙经验,“向个体切身的超越经验的方向前行”。这一超越经验关联着如下洞见:“人的秩序,无论是个人的还是社会的秩序,都不得不有赖于人直接在神下面的生存。”进一步地,这一洞见意味着:“人的本质就是imago Dei(神的形象),这个本质无需法老的中介就能达到。”这种新的人性自我理解,意味着,秩序的主体从“宇宙论的统治者转移到作为新公共秩序之核心的先知、圣人或者哲人”。⑦埃里克·沃格林:《不朽:经验与象征》,载张庆熊、徐以骅主编:《基督教学术》第10辑,第134页。精神迸发或存在的飞跃,都是对紧凑性的宇宙体验的突破,以实现对生存真理的超越性理解。譬如,以色列人通过启示而达到对原初宇宙经验的灵性分殊化,突破了宇宙体验:“以色列人对启示的经验,连同由此带来的被选民族在耶和华律法之下的生存,确实都属于历史模式的生存,而不是宇宙论模式的生存。但是,以色列人位于神之下的生存所具有的真正历史性特征,绝不可以理解为某种普遍主义人类观的结果;相反,我们必须认为,是启示将以色列的历史建构为一种人类普遍的生存形式……来自荆棘丛和西奈山的启示被直接传达给人和社会;这些启示将人置于神之下,从而剥夺了宇宙论帝国的统治者作为神性秩序与人的中介者的地位。”①埃里克·沃格林:《天下时代》,载《秩序与历史》第4卷,第162页。宇宙论秩序往往通过神话来表达自身,在以色列人那里出现了与宇宙论神话的决定性抵抗,即不再借助神话,与神话彻底决裂,由此而脱离宇宙论王国的统治秩序。②埃里克·沃格林:《天下时代》,载《秩序与历史》第4卷,第161页。
原初宇宙体验所采用的象征化表达方式是神话。神话并没有采用一神论的方式,往往采用神谱论方式将支持宇宙论王国的最高神与地方神以谱系的方式加以分层,从而形成与地上秩序相类似的天上秩序,这两种等级性的秩序也为政治社会中的礼法秩序提供了作为类比物或相似物的参照体系。只要神还没有被作为与人、世界、社会的非同质物来对待,只要神还是宇宙内的诸神,那么,原初宇宙经验所依赖的类比这种体验方式就不会受到根本性的质疑。③埃里克·沃格林:《以色列与启示》,载《秩序与历史》第1卷,第49页。神话由此被理解为精神突破或存在飞跃之前人类文明所采用的符号形式。“宇宙起源论神话是一个更为古老的、更加无所不包的表达存在秩序的形式。”④埃里克·沃格林:《以色列与启示》,载《秩序与历史》第1卷,第142—143页。神话作为一种体验的表达方式,远比人们所能想象的更为丰富和具体。“神话首先包含各种不同的经验组合(experiential blocs),它们在分殊化的进程中会分离出来;其次,神话包含了这样一种经验,它将上述经验组织融合成为一个有生命的整体。在埃及的宇宙起源论中,具有粘合作用的因素就是同质的经验。”⑤埃里克·沃格林:《以色列与启示》,载《秩序与历史》第1卷,第143页。在宇宙论秩序的神话经验中,同质化意味着内在者和超越者的浑然不分或者相互嵌入,因为“说内在就预设了对超越的理解,而超越尚未实现,尽管从关于神显现的经验中毫无疑问可以发展出一种对神性超越的终极理解”。⑥埃里克·沃格林:《以色列与启示》,载《秩序与历史》第1卷,第144页。
在沃格林看来,虽然宇宙论风格的真理包含着自我解体的因素,但只有通过意识的智性进展(哲学的符号形式)或灵性进展(启示的符号形式)所导致的分殊化,才能有新的风格的真理对之加以替代。这种分殊化意识的实质是对原初宇宙体验中处在生存与非生存的浑然、同质的紧凑状态的突破,即生存(如人)与非生存(如神)两极各归其位,在分殊化的基础上才有重新连接的可能性。而分殊化的结果则是生存与非生存的居间性张力,既不是一方将另一方吞并,也不是二者互不往来,更不是两种不同的客体化实在,而只是生存体验中的两极保持结构性的平衡与张力,彼此相互参与对方。非生存极以牵引着生存者的方式参与生存极,生存极或以智性的探寻或以灵性的启示参与非生存极。这就有了三种不同的真理,紧凑性的宇宙论真理、以智性探寻为核心的人学真理以及以灵性启示为核心的救赎论真理。
宇宙论真理(Cosmological Truth)是由早期宇宙论王国所代表的真理,它对应于原初宇宙论体验及其象征化,它包含最小程度的自我反思,在这个体验领域,人、神、世界、社会四元结构体,以一种整全性、浑然性、紧凑性的方式显现居间存在张力,但这种显现方式是不充分的,生存与非生存的居间张力以神话的方式被象征性地以同质化方式加以表达,生存的真理被紧紧地包裹在宇宙论真理的形式里。当然,关联着原初世界经验的宇宙论真理,也就是前天下时代或前轴心时代的真理风格,在希腊的表现是《荷马史诗》的诸神世界,在以色列则是《旧约》和摩西神话,在中国则是三代的礼法传统。⑦这里,对希腊与以色列的总结来自帕森斯,而对中国的理解则来自余英时。参见余英时:《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88页。伊利亚德以上古存有论理解这种宇宙论秩序。⑧M.耶律亚德(Mircea Eliade):《宇宙与历史:永恒回归的神话》,杨儒宾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1—39页。杨儒宾将作者译为M.耶律亚德,一般译作米尔恰·伊利亚德。
然而,一旦意识或人心成了实在的场所,成了超越性显现的场所,那么神之临在的象征化就会从宇宙内诸神转移到作为神之临在场所的人心。而人心中的不同部分,智性的探寻与灵性的启示,就成为人学真理与救赎论真理的承担者。“人学真理”(Anthropological Truth)在雅典的政治文化里,尤其是悲剧里出现,这一真理类型包含了以心(灵魂)作为感受超越之中枢相联系的全部范围内的问题,它对应于从原初宇宙体验中的智性分殊化,其符号化形式是哲学。“救赎论的真理”(Soteriological Truth)在犹太—基督教中出现,它对应于原初体验的灵性分殊化,其符号化形式是启示。①埃里克·沃格林:《新政治科学》,段保良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81—82页。宇宙论风格的真理通过同质化体验显现,譬如在古埃及,“创世与统一、世界与埃及,神与国王,神与土地,国王与土地就这样被融合在一出从混沌中生出秩序的神话戏剧中,融合在一出贯穿存在的各个领域的戏剧中”,②埃里克·沃格林:《以色列与启示》,载《秩序与历史》第1卷,第150页。紧凑性与同质性是宇宙论真理的特色,而无论是人学真理还是救赎论真理,则都是经由分殊化而达致的非同质化真理。
人学真理与救赎论真理之不同,乃在于从紧凑体验中展开分殊化的方式不同,这种方式之差别又表现在对居间性的生存张力结构的极点的不同关切上。在生存结构的神、人两个不同体验极点的张力中,哲学探究所关联着的智性分殊化,侧重人神两极中的人极(生存极)的一面,也就是人的智性探寻的一面,当然这一探寻也是以来自另一极的推动为背景的;而救赎论真理则侧重神圣性极点的有序性呈现,尤其是来自神的牵引的一面。由生存体验中的神、人两极构成的生存张力,构成沃格林所谓的居间性生存体验的内核。这是沃格林研究意识哲学的重要收获。他从威廉·詹姆斯《意识存在吗》中获得启发,纯粹经验即参与的意识,既能够置于主体的意识之流,又能置于外部世界客体的脉络,这其实是将存在于参与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某种东西等同于经验。③威廉·詹姆斯:《意识存在吗》,陈亚军译,载万俊人、陈亚军编选:《詹姆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版,第392—410页;又见威廉·詹姆斯:《彻底的经验主义》第1篇,庞景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20页。而沃格林又通过柏拉图的Metaxy的概念,确证了经验的本质在居间,即在人和他的体验的实在的两极之间,更确切地说,在人与神(超越性)之间。以此,神性临在的经验可以获得居间化理解,“经验是神和人之临在的实在……或在启示的名义下被安放于神的脉络”。④埃里克·沃格林口述、桑多兹整理:《自传体反思录》,第93页。居间的概念使得沃格林彻底摆脱了神与人的实体化理解,即不再将“参与经验的两极”看作“是在经验发生时构造一种神秘交往的自足实体”,由此沃格林获得了对意识的如下理解:“不再是指对人的意识之外的实在有知觉的人类意识,而必定是指参与性的纯粹经验的间际实在。”⑤埃里克·沃格林口述、桑多兹整理:《自传体反思录》,第94页。
在意识的智性分殊化中,神性本原被辨识为神性理智,在人对本原的寻求中,神性理智不仅在场,而且作为一种推动力量推动着人的理智,二者彼此参与(Metalepsis),属人的参与到属神的之中,属神的参与到属人的理智之中。灵魂被“对象”所推动,由人进行的探寻以来自神的推动为前提;没有来自本原的吸引,那么也就没有人的求知欲;没有人的求知欲,也就没有处在困惑中的提问,也就没有对无知的认知。⑥埃里克·沃格林:《天下时代》,载《秩序与历史》第4卷,第273—274页。在意识的智性分殊化中,体验的神人两个极点的出现,也就是生存与非生存两种不同质的领域被分辨出来,而人自身并非生存在其中的任何一个区域,而是立足于生存的区域向着非生存的敞开,生存在作为参与式实在的居间之中。在人极的探寻与神极的吸引的交互作用中,朝向实在的生存张力为人所意识到。“对张力的意识并不是一个由某一认知主体接收到的对象,而恰恰是实在得以在其中照亮自身的那个过程。”⑦埃里克·沃格林:《天下时代》,载《秩序与历史》第4卷,第305页。生存的万物(人极)与非生存的无定(神极),并非两种不同的处于静态关系中的对象化实在,而是“被体验为存在的模式”,或是“被体验为处在唯一整全的实在之中的一项张力的两端。这种整全意义上的实在被体验为进行着一种超越自身的运动,它以卓越的实在为方向。实在是流动的”。⑧埃里克·沃格林:《天下时代》,载《秩序与历史》第4卷,第305页。
对于智性的神显而言,人的连接神性的所在乃在于他的智性(努斯),这是其身上不朽的、接近于神的元素。“人的生存对本原的开放性有赖于人身上的某物,它能回应神显,探寻本原。随着人身上的这个东西在进行回应的时候被发现,柏拉图将它符号化为daimon(《蒂迈欧》90A),亚里士多德将其符号化为 theion(《尼各马科伦理学》1177b28ff.)。心灵中最接近神的部分(theiotaton)是人的理智(nous),它能参与到神性理智(Nous)之中;最接近神的部分所具有的本性和文化,通过该部分对本原的探寻(theoria theou),而成为通往不朽的行动。因此,人的以本原为目标的张力和他对实在之结构的认知开放性之间的关联,在同他的全方位‘求知欲’相混合后,变成了他的理智性不朽和他的生存之间的关联,该生存是在一个有着生成与衰亡、出生与死亡的世界上进行的。只有在这个世界中,对不朽的追求才是可能的。只有当人接受作为无定负担的可朽时,他才能得以不朽。在高处与深处、理智与无定之间保持的意识均衡,变成在理论生活(bios theoretikos)中,亦即在这个世界上的智性生活中,在不朽与可朽之间保持的均衡。”①埃里克·沃格林:《天下时代》,载《秩序与历史》第4卷,第330页。译文据英文版,略有改动。智性分殊化而抵达的神显经验,重在对人生命中既在人极而又能连接神极的智性的探寻,更为关键的是,这一探寻基于不朽与可朽的平衡,因而他并不是废黜人的人性部分而仅仅关注神性维度,而是在血肉、血气与接近神性的心智之间保持某种平衡,进一步地,在神显事件与宇宙的经验之间保持平衡,也即在心灵的不朽同宇宙之中的创生和衰亡的节律保持着均衡。②埃里克·沃格林:《天下时代》,载《秩序与历史》第4卷,第332、335页。沃格林强调,哲人所从事的哲学活动本身在天下时代的统型中应该作为一种事件来对待,通过它,历史场域(the field of history)显现为存在中的各种张力(a field of tensions in being),“该事件把 nous[智性]为存在而显亮这一特征用来作自我理解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这种体验说成是智性体验。对于由此而变得清晰可见的存在中之诸结构,我们将其说成是实现的逻各斯(the logos of realization)”。③埃里克·沃格林:《记忆:历史与政治理论》,第363—364页。
何以智性分殊化重在居间张力中的人极一端的探寻,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智性自身的品质有关。从智性的视角切入存在之奥秘,可以与亚里士多德对政治友爱的论述相参照:“这种友爱是政治社会的本体;它存在于人们之间的精神上的和谐一致(homonoia);只有人们活得与努斯协调一致,也就是与他们自身最神圣的部分协调一致,友爱在他们中间才是可能的。一切人都参与努斯,尽管紧张程度不同;因此,人们对他们自己的纯知自性(their own noetic self)的爱,使努斯成为他们之间的共同纽带。只有人们因对他们的纯知自性的爱而彼此平等,友爱才是可能的;不平等者之间的社会纽带是脆弱的。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提出了他的论旨是,上帝与人之间的友爱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极为不平等。”④埃里克·沃格林:《新政治科学》,第82页。译文据英文版,略有改动。在此,沃格林道出了智性体验的核心,人与人的友爱之所以可能,在于共同且平等地参与努斯,对努斯的爱则是参与的纽带;而上帝与人之间由于不平等,故而上帝与人之间的爱是不可能的,这种上帝与人之间的爱的不可能,“或许可认为是所有人学真理的特性。神秘主义哲学家们将之纳入一套理论来加以解释的那些经验,都会侧重于人这一方的灵魂对神性的取向。灵魂使自身趋向一个上帝,这上帝止息于其寂然无动的超越;灵魂向神性实在(divine reality)发起征逐,但它不会遇到来自彼岸的回应性运动”。⑤埃里克·沃格林:《新政治科学》,第82—83页。对于智性而言,人所及的是自尽其在己之努斯,在于自己朝向神性根基彻底敞开,做好接纳神性的一切准备;至于神性自身是否临至,则唯有听诸神性本原自身,而不在人之努斯可及范围之内,那里乃是神性的深渊。智性对上帝的感知,无法绕开智性自身,智性固然是人身上最接近神之部分,但更是人得以感知其同类者的方式。人凭其智性而与同一宇宙中的人们结成友爱的共同体,以其智性与社会的有序化,是否也是俟神之临在的一种准备甚至条件?
但对于保罗式的灵性神显而言,“生存真理的推动力已从人的探寻转到神的恩典(charisma),从人通过因爱欲而生的张力向神的上升,转到神通过因为爱(Agape)而生的张力向人的下降”。⑥埃里克·沃格林:《天下时代》,载《秩序与历史》第4卷,第340—341页。灵性神显拒绝一切属人的东西,血肉身体无法进入神之王国,它必须被转化为灵性的身体(soma pneumatikon),因而重点不再是“化身于这个世界之中的神性智性程序”,而是转变为“脱离这个世界之无序的神性灵性救赎”;从“实在所包含的矛盾,转变为对该矛盾的克服;从对带有方向性的运动的经验,转变为它的臻于完善”。灵性神显与智性神显的关键在于对衰亡(phthora)的应对,人的不朽不再是与宇宙节律保持平衡,而是与对宇宙中衰亡的克服紧密相连,因为必衰亡的不能承受不朽,“实在转变到不朽状态,这就是保罗对那件奥秘之事的解释”。①埃里克·沃格林:《天下时代》,载《秩序与历史》第4卷,第334—335页。基督作为复活者的意象,使保罗相信,向圣灵敞开自身,应答式参与活跃于耶稣这一符号上的同一个圣灵,人就可以不朽。“对那一个超自然的形式加诸人之本性的恩典的经验,是基督教真理的种差。这恩典在历史中的启示,通过基督的道成肉身,明确地完成了神秘哲学家身上的精神冒险运动。灵魂曾因它的敞开及趋向不可见的尺度而获得的对旧有的社会真理的批判性权威,如今由于尺度本身的启示而得以增强。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或许可以说,启示这个事实就是它的内容。”②埃里克·沃格林:《新政治科学》,第83页。灵性神显的理路便是全面地搁置甚至废黜属人的灵、属于这个世界的灵(to pneuma tou kosmou),而为来自神的灵(to pneuma ek tou theou)自行到来提供条件;属人的智慧构成神之灵的干扰,它不能理解也无法接纳圣灵的恩典。人必须从属人的一切机制中退出,而将自身一切虚无化之后,属神的灵才能临在。③保罗强调,福音并非从人处领受,也非他人教导,而是完全来自耶稣基督可见的显现(Apokalypsis)。参见埃里克·沃格林:《天下时代》,载《秩序与历史》第4卷,第352页。
因而属人之灵在保罗这里是由圣灵塑造的,而不再是人的努斯。灵性分殊化专注于神性的突入,而不是人的探寻,由此而形成新的生存意识,这个生存意识指向的不是在宇宙中的生存,而是经过变形的实在。在灵性分殊化中,如果信与望仍然可以归在人极这一边,它们是人接纳神性所需的德性,它们仍然属不完美的世俗领域;那么,爱(Agape)则是更高的德性,它出自神性而下降到人这里,从永恒完美之域延伸到不完美的生存中,处在完美状态的人超越了对居间视角下的向着神性根基开放自身的世内生存。救赎论真理所指向的体验,是那种为终极性所俘获的体验,是那种以不容己的被牵引且忘我地沉浸在对真和善之终极根源的爱中,在这种终极根源面前,人类的一切才情、事业、功德,皆无足称道。耶稣与保罗不需要任何世间的东西而只需要超越性在自身的呈现,就可以将世间的生存所仰仗的一切甩开,一切上出的个人只要遭逢这种超越之终极性的神显,无不低头忏悔,自觉卑微,无不感受到被提升和净化之渴望,甚至居间的生存在保罗这里都被降格为一种驿站,而作为目标的不朽,才是保罗灵性分殊化的末世论终点。从保罗的灵性神显而言,柏拉图的智性神显仍然不够充分,未臻终极。尽管柏拉图关于宇宙及其秩序的神话不再是宇宙论神话,而是神在人、社会与历史和宇宙中的造物主式显现的故事,他意识到在神性作为努斯(Nous)来加以启示之外,还有不可知的神性奥秘,但毕竟生存真理被限制于意识的智性结构,因而神和人的故事并未超出一个其智性努力仍然受必然和命运限制的造物主形象。而保罗则超越了受造世界的结构,进入其源头——作为自由与爱的神的创造性。由此,在保罗那里牵引着人的超越性的神极,已经不同于智性分殊化,它现在是对于超越宇宙的神和他的爱,正是它构成了神显事件的真正牵引者,而这一神显事件则构成了历史的意义。“一旦处于神性实在之中、超越智性之外的那一灵性深处得到了阐发,柏拉图类型的神话便不再适合作为有关神和人的终极真理了。柏拉图式造物主受到必然(Ananke)的制约,而保罗的创世神则必定在他与宇宙中各种相反力量的斗争中胜出。进一步来说,通过将带有方向性的运动的目标,将其完全状态(teleion)阐发为不朽状态,它超越了人对阿那克西曼德式奥秘(关于无定与时间的奥秘)的介入,保罗由此充分分殊化了对该运动的经验。”④埃里克·沃格林:《天下时代》,载《秩序与历史》第4卷,第344—345页。译文据英文版,略有改动。
智性分殊化所能达到的乃是对居间生存中的人之自身的清晰认识,譬如,“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大人](spoudaios)是一个完整的人(full man),他在最大限度上受到那种宇宙性——神性存在之运动(cosmic-divine movement of being)的穿透,并凭着这种德性成为伦理学的创立者,将关于何为自然正当的知识往下传达至社会。一旦存在之思背后的宇宙背景(宇宙[超越与内在之间那不可分割的存在纽带]作为背景)失落,对于完整之人的古典构想将面对完整之神这一构想所遭受的同样危险:人被还原为一个存在物之后,成了这样一个在纯粹内在世界中的、存在着的事物;同时,在他与存在秩序(Seinsordnung)的关系中,他不再是[存在共同体中的]一个伙伴(partner),而是被还原为一个认知主体”。①埃里克·沃格林:《记忆:历史与政治理论》,第179页。相比之下,“保罗充分分殊化了对人的经验”,它不需要存在之思及其背后的宇宙背景,②宇宙论秩序的担纲者乃是王者,王者垄断通天权,其所制作礼法乃是一种具有神圣化了的礼法秩序。归属于神之下的生存,即归属于该礼法秩序,摩西时代则意味着信奉上帝,必归属于犹太人的集体生存礼法。彻底突破宇宙论秩序必然要真正突破礼法秩序。在保罗那里则是突破律法。“律法是惹动忿怒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罗马书》4:15)神显事件的关键,不再是践行律法,而是信仰(Pistis)(《罗马书》4:3)。参见埃里克·沃格林:《天下时代》,载《秩序与历史》第 4卷,第 353页。当神带着他的神性所具有的完满(Pleroma),将自身化身在作为受造物的人的身上,将人变形为神—人(God-man),这表明,在人身上神之子的身份乃是可能的。③保罗在耶稣基督可见的显现,也就是神显事件的真理符号化为“有关他儿子的福音”,对由神进行的呼召和有关他儿子的福音加以区分,称自己为师徒,以区别于先前的先知。参见埃里克·沃格林:《天下时代》,《秩序与历史》第4卷,第352页。这样的人“能获得摆脱宇宙必然(cosmic ananke)束缚的自由,能进入神的自由(the freedom of God),能被来自那个神(他本身是不受宇宙控制的)的爱之恩典所救赎”,④埃里克·沃格林:《天下时代》,载《秩序与历史》第4卷,第346页。译文据英文版,略有改动。这意味着在保罗那里,生存真理彻底摆脱了宇宙论秩序的束缚,而展现为创造的自由与出自超越之神自身的爱。
如果说智性分殊化重在人的探寻,即“发现生存的智性秩序,并意识到该发现是神显历史中的一个事件”,在此“重心在于对结构的认知”。而保罗所代表的灵性分殊化,其重心则在“从结构逃离”。因而在古典希腊哲人那里,历史的思考只是结构分析的附属物,它并不重要。是以亚里士多德写作《伦理学》与《政治学》,但却没有写作《历史学》。然而在保罗那里,信仰的历史主导了《罗马书》,而政治学与伦理学被贬谪到历史的边缘地带。保罗所关注的是“历史的意义”(meaning of history),以此取代的是古典哲人那里“在历史中的意义”(meaning in history),历史被缩减为通往变形的逃离。“当实在所包含的矛盾在意识中变得对自身明晰起来时,它创造出一种历史所具有的矛盾,该历史悬置于宇宙的必然(the ananke of the cosmos)和终末论运动的自由(the freedom of eschatological movement)之间。在天下时代,该矛盾的两条分支分布在古希腊哲学家的智性神显(the noetic theophanies)和以色列—犹太先知的灵性神显(the pneumatic theophanies)之中,这一点必须得到承认,但无法得到解释。历史的过程是一个奥秘,正如在历史过程中变得明晰起来的那个实在也是一个奥秘。”⑤埃里克·沃格林:《天下时代》,载《秩序与历史》第4卷,第354—355页。由于保罗那里,政治学与伦理学被贬谪到朝向神性超越的边缘,因此,这里隐藏着的灵知主义危险在于:“社会和宇宙往往被体验为一片无序领域,致使实在的有序领域只剩下处于朝向神性超越的张力之中的个体生存。”“神性秩序退缩至对意识的超越。”参见埃里克·沃格林:《天下时代》,载《秩序与历史》第4卷,第72—73页。译文据英文版,略有改动。
四、余论:不同形式生存真理的等价性问题
尽管生存的真理具有宇宙论真理、与智性神显相应的人学真理和与灵性神显相应的救赎论真理,但三者就实在的真理本身而言又是等价的,所不同的只是通过分殊化而获得了更为清晰化的意识。尽管原初宇宙体验分裂为一个去神化的世界和超越世界之上的神性本原,但沃格林提醒我们不要扩大分殊化与分裂的结果。“解体的是宇宙论风格的真理,这是就其倾向于将所有实在均以居间式实在为模板来看待而言;分裂的是原初经验所体验到的宇宙,但所有这些分[殊]化结果均未影响到原初经验的核心,即对某种居间式实在的经验。相反,它仍然与我们在一起。”⑥埃里克·沃格林:《天下时代》,载《秩序与历史》第4卷,第137页。无论是柏拉图通过智性神显,神将自身启示为创造结构的造物主,还是保罗通过灵性神显,神将自身启示为摆脱结构的救世主,“启示均未被体验为与神性实在相等同,而是被体验为对神性实在的参与”。⑦埃里克·沃格林:《天下时代》,载《秩序与历史》第4卷,第362页。无论是灵性启示,还是智性启示,“它们都发生于居间,亦即发生于当具体的人遇到神性显现之时的具体心灵中。关于实在之结构的古希腊洞见只来自那些哲学家,智性神显发生在他们的心灵中;关于变形的演变机制的以色列、犹太和基督教洞见,则只来自那些先知和使徒,其中首先是耶稣,灵性启示发生在他们的心灵中”。与其说是哲人成为智性启示的承担者,先知与使徒成为灵性启示的担纲者,毋宁说,正是在智性启示与灵性启示的体验中,哲人才成为哲人,先知与使徒才成为先知与使徒自身。“意识的智性和灵性明晰并不是某个人碰巧发现的‘对象’,而是一个出现在天下时代的具体历史事件;它的承载者们通过自己身为承载者的功能,成为‘哲学家’和‘先知’在历史上的类型”,①埃里克·沃格林:《天下时代》,载《秩序与历史》第4卷,第368页。译文据英文版,略有改动。从而超越了紧凑性的宇宙体验中由国王或祭司承担的宇宙论秩序。取代宇宙论秩序中对礼法秩序及其集体生存形式的归属,智性与灵性的分殊化,将人引入生存性参与运动,它“是一种以更高程度的实在(而不是以毁灭)为目标的运动;它被体验为哲学家所说的athanatizein(不朽)或保罗所说的aphtharsia(不朽)。可以说,对实在的经验天生地偏向于更高程度的实在”。②埃里克·沃格林:《天下时代》,载《秩序与历史》第4卷,第370页。尽管如此,就居间生存而言,两者的等价性必须被充分意识到。一个是根植于希腊哲学探究中的智性(noetic)经验,一个是根植于犹太—基督教传统中的灵性(pneumatic)经验,“就被象征化的实在结构而言,它们之间并没有不同”,“是居间结构(Metaxy),即哲学家在分析人参与到其生存之神性根基的意识时,所遇到的那个结构。中保(Mediator)的实在与意识的中介实在,具有相同的结构”。③埃里克·沃格林:《不朽:经验与象征》,载张庆熊、徐以骅主编:《基督教学术》第10辑,第147页。译文据英文版,略有改动。
对经验与符号等价的强调,是沃格林克服线性进化思维的关键。从分殊化之前的神话形式表述的宇宙论秩序经验到分殊化之后以哲学和启示表达的人学真理和救赎论真理,在传统的历史哲学中它们被视为一种线性的进步—进化,然而,沃格林指出了它们是在不同历史情境下对张力性生存的不同体验形式,就体验的内核而言是等价的,并不存在优劣、文野或先进与落后的区别。“分殊化并不是绝对的善;它充满了危险,包括极端地把由神话所糅合在一起的经验组合分解开来,以及在此过程中丧失同质的经验。相反,宇宙论神话的优点在于它的紧凑性:它起源于一种对于存在秩序的整体性理解,提供了恰当表达相互平衡的多重经验的符号,它是一种充满活力的力量,在信仰者的心灵中保存了均衡的秩序。”④埃里克·沃格林:《以色列与启示》,载《秩序与历史》第1卷,第144页。事实上,沃格林虽然不同意以线性的进步—进化看待从精神突破之前的宇宙论风格的真理到突破后的两种真理(哲学的人学真理和启示的救赎真理)的变化,他也不同意泯灭它们之间差异的平等主义或同质主义意识形态。“如果我们用关于经验的紧凑和分殊化的原理来取代观念史中的进步原理,那么,在一个古代文明中出现特定的思想观念和思考方法就不再有任何不同寻常之处了……这种分殊化在各种文明形式中都是可能的。”⑤埃里克·沃格林:《以色列与启示》,载《秩序与历史》第1卷,第157页。如果历史的内核就是生存与非生存的居间性真理的展开,那么历史的表层就是生存真理从紧凑性到分殊化的转换。当然,对沃格林而言,也可能是居间体验的畸变(deformation)。重要的是居间之两极的均衡,而原初宇宙体验以同质化方式保证了这种均衡。原初宇宙体验的这种品质“是由同质的经验(the Experience of Consubstantiality)承载的”;神话简洁的同质性经验,并“不是联结各种不同经验组合的机械纽结,而是在存在的各个领域之间构建秩序的一条原理。诚然,存在的共同体被体验为一种实质的共同体(a community of substance);不过,是神性实质(divine substance)在世界中得到显现,而不是宇宙的实质Cosmic Substance在众神(gods)中得到显现。存在共同体中的各个伙伴在一种动态的秩序中被联系在一起,其原因是神的实质弥漫于世界、社会和人之中,而不是人或社会的实质弥漫于世界和众神之中。这样,同质性秩序(the order of consubstantiality)就是等级制的(hierarchical);实质从神性存在流向世俗的、社会的和人的生存”。⑥埃里克·沃格林:《以色列与启示》,载《秩序与历史》第1卷,第144页。译文据英文版,略有改动。
在原初宇宙体验中,生存与非生存之间的同质化体验模式使得二者的居间在意识中的均衡是以某种被给予的方式呈现的,它并不是个人修为的成就,而且作为宇宙论秩序的体验内核,它自身具有一种不稳定的特征。启示与哲学能够取代宇宙论真理的神话,带来存在的飞跃,就根源于宇宙论风格真理的这种不稳定性。这种存在的飞跃意味着新的符号化形式(哲学与启示对神话的替代,社会秩序被刻画为小宇宙到大写的人的变化)。如果说,在雅斯贝尔斯那里,三大文明都曾在其轴心时代通过思想突破的方式为自己的文明进行奠基,这一奠基很大程度上主导了这些文明在其后两千多年的方向,在这个意义上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理论就以精神突破的方式提供了多元文明的平行景观,以回应此前根植于犹太—基督教传统的线性一元文明史观,从而深刻地改变了普遍历史的普遍性;那么,对沃格林来说,轴心时代的精神迸发的实质则是对人类上古时代共同经验的宇宙论秩序的不同形式的突破。多元乃是从一中的分殊化进展,由于有了这种符号化形式的改变,将历史划分为之前阶段与之后阶段的历史意识才得以产生;然而生存论真理体验内核又是普遍历史的保证,由于分殊化方式与时地之不同,因而又有了一中之多。当然,值得注意的是,沃格林对于天下时代生存真理的分殊化理解,依赖的仍然是希腊与以色列的生存体验,虽然不乏洞见,且对中国思想轴心突破的理解颇具启发,但中国的突破是否从神话所表达的宇宙论体验转向超越性体验,仍然有待进一步考察。中国在精神突破运动中发明了何种符号形式,这一点则在沃格林的视野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