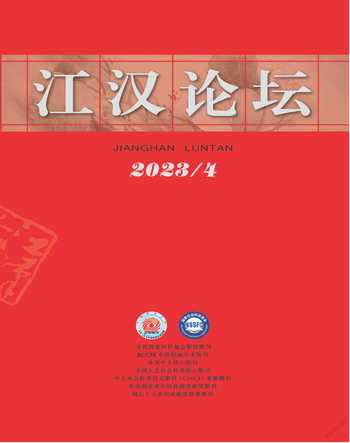后发国家现代化角落的权利贫困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超越
摘要: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总体上呈现出边缘性和依附性,存在被遗忘的现代化角落,以偏远农村和城市贫民窟为空间承载的现代化角落生存着大量权利贫困的农民和贫民。权利贫困是交换权利与可行能力的组合贫困,一些后发国家权利贫困的政治根由是“不自由的民主”,而基于私有制的社会保障则是导致权利贫困的政策因素。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其光芒之所以能够照耀每一个角落,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对边缘空间和弱势群体的权利赋予,相应体现在两个方面:通过全面脱贫、乡村振兴和社会保障,国家资本取代私人资本实现对现代化角落生产和生活要素的持续输血和合理赋值,杜绝逐利资本无序扩张对边缘空间和原子化个体的剥夺和排斥;以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和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一体建设来尽可能地创设机会平等和权利均衡。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全面超越,将为后发国家跳出现代化角落的窠臼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样本。
关键词:现代化角落;权利贫困;中国式现代化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时代县域政府治理效能评估及提升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AZZ011)
中图分类号:D61;D5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3)04-0051-05
一、问题的提出:现代化角落与权利贫困
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最剧烈、最深远并且无可逃避的长周期社会变革,而“社会中没有任何一对因素能以同等速率适应这些变革,社会动荡可能会变得不可收拾以致广泛的暴乱突如其来,大批大批的人被迫出走”(1),这将彻底瓦解传统社会长期封闭和静止的稳态。现代社会的个体相应地日益原子化,即“脱离了传统共同体的系留之地,除了直系亲属外,他和其他人都隔离了。在这种境遇下,孤独、不安全和人际密切关系的削弱,使个人丧失了宜于心态稳定的环境”(2)。而且,即使经济增长实现了总量提升,“有些阶层也仍有可能遭受极为严重的绝对贫困”(3)。事实上,现代性的自由与平等理念虽是批判封建特权的利刃,但它不意味着对物的平等占有,而仅是指人们享有占有的平等资格。同时,市场自由竞争的“优胜劣汰”和结果的“赢家通吃”必然生成实质不平等。西方的道德观念为资本主义的不平等作了诡辩:“有劳动能力的人失业永远是咎由自取”(4),“清教把任何穷人都视为好逸恶劳或者罪犯”(5)。这种道德观念亦得到了相关经济理论的支持,譬如萨伊定律就强调供给会创造需要,自动实现市场均衡,而大规模的失业并不存在,所谓失业仅为摩擦性或自愿性失业。
历史与现实证明,无论是主动拥抱还是被动裹挟,传统制度延存、经济基础薄弱和资本积累匮乏的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总是外部呈现出边缘性和依附性,内部制造着被遗忘的现代化角落,即以偏远农村和城市贫民窟为空间承载,生存着大量权利贫困的农村居民和城市贫民。后发国家现代化角落的权利贫困累积,形成了贫富分化和社会对立,民主衰败和政治动荡,经济停滞和福利低下。权利贫困是贫困的深层内核,其实质是交换权利和可行能力的组合贫困。交换权利是指一个人在市场经济中可以将所拥有的商品通过贸易、生产或者两者兼有的方式转换成另一组商品的能力。(6)事实上,正是由于除劳动力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可出卖的工人阶级不断壮大,造成了“不依赖贸易的保障”的普遍缺乏,这导致在一个庞大的工资劳动者阶级出现之后、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之前的经济发展阶段更容易发生饥荒。(7)可行能力则是一个人所拥有的有理由享受和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实质自由,贫困就源于基本可行能力被剥夺,而不能按照通行标准将其简单地归为收入低下。(8)可行能力方法的提出超越了对生活手段的关注,而转向实际的生活机会的视角。(9)因此,社会个体交换权利和可行能力的欠缺源于生存资源的社会剥夺和排斥、获取机会平等的能力不足和社会权利的相对缺失,关注的焦点“不在于一个人事实上最后做什么,而在于他实际能够做什么,而无论他是否会选择使用该机会”(10)。如果不抑制资本的无序扩张,不规范财富的积累形式,则“企业家不可避免地渐渐变为食利者,越来越强势地支配那些除了劳动能力以外一无所有的人”(11),后发国家也必然沦为“金融资本的仆从,变成了从属于金融资本的债务国家”(12)。
基于此,本文试图以拉美国家为例来分析后发国家现代化角落权利贫困的政治根由和政策因素,并揭示中国式现代化是如何跳出现代化角落的窠臼,从而实现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全面超越的。
二、后发国家现代化角落权利贫困的政治根由和政策因素
后发国家现代化角落的权利贫困源于硬性照搬西式民主而形成的“不自由的民主”窘境,而基于私有制的社会保障则成为权利贫困生成的政策因素。这表明,权利贫困的治理需要政治秩序和政治民主的实现,需要作为共享机制的社会保障来促成权利的均衡赋予。
(一)权利贫困的政治根由:硬性照搬西式民主而生成的“不自由的民主”
后發国家现代化角落的消解,需要实现交换权利和可行能力的均衡配置,而均衡配置的实现依赖于几种工具性自由,阿马蒂亚·森将其划归为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和防护性保障五种,这几种工具性自由有助于形成社会个体的交换权利和可行能力。他认为,“自由不仅是发展的首要目的,也是发展的主要手段……政治自由有助于促进经济保障。社会机会(以教育和医疗保健设施的形式)有利于经济参与。经济条件(以参与贸易和生产的机会的形式)可以帮助人们创造个人财富以及用于社会设施的公共资源”(13)。透明性保证所涉及的是满足人们对公开性的需要:在保证信息公开和明晰的条件下自由地交易。防护性保障可以提供社会安全网,以防止受到影响的人遭受深重痛苦甚至挨饿和死亡。(14)不同类型的自由可以相互补充,并相互强化。从根本上讲,民主政治“有助于防止饥荒或其他经济灾难……民主政府需要赢得选举并面对公共批评,从而有强烈的激励因素来采取措施,防止饥荒或其他类似的灾难。毫不奇怪,饥荒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在有效运行的民主体制中,不管是经济富裕的国家,还是相对贫穷的国家”(15)。
问题在于后发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民主体制衰落,无法生成工具性自由,不能实现对交换权利和可行能力的培育,从而形成了严重的权利贫困。以拉美国家为例,其现代化进程中的民主化事实上将建立民主与维护民主完全割裂。周期性的选举活动表明民主制度建立了,但在投票结束后,选举期间相互争论的诸多议题似乎在惊人的默契之下被束之高阁,并没有多少人关心议题能否进入政治议程和得到解决。从世界范围看,后发国家对西方选举制度的模仿,如果没有带来令人满意的民主治理绩效,就只能说建立了选举民主体制,但并没有形成维护这一体制的能力,选举并没有为民主体制输入足够多的正当性。事实上,选举政治对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折射功能在弱化,这集中反映在政党政治的深刻变化上,即政党的组织动员功能日益让位于媒体,政党体系日益碎片化,公众的政党倾向日益转向对政治人物的认知和认可,公众对政党的信任感下降,这势必造成政治精英和政治权力的个性化,使政治人物放弃本应关注的深层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而将能否讨好媒体与选民、能否骗取曝光度和选票作为政治议题的选择标准。
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增长当然可以提供部分政治合法性,特别是在经济发展时,社会公众可能并不在意民主参与问题,但如果出现了普遍性的经济衰退或重大突发自然灾害,“民主的保护性力量——如在民主国家防止饥荒中所起的作用那样——就被强烈地怀念了”(16)。“经济的激励因素尽管是重要的,却不能取代政治的激励因素,而且,如果缺少适当的体系来提供政治的激励,由此造成的空白是不可能由经济激励机制的运行来填补的”(17)。消解权利贫困,生成交换权利和可行能力,当然需要市场交换来提供经济自由,也需要政治自由所创设的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来促成工具性自由中的社会机会和防护性保障。
(二)权利贫困的政策因素:基于私有制的社会保障
经济富裕与实质自由并不必然呈现简单的因果关联,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弱势群体的受剥夺程度与发展中国家相差无几。这就需要关注社会组织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因素,“包括公共卫生、医疗保障、学校教育、社会凝聚力与和谐程度。我们是只看生活的手段,还是看人们实际享有的生活本身,这两者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别”(18)。在后发国家现代化初期,当然也存在着大量的失业或不充分就业,“但它在很大程度上却会被农业部门所缓解甚至掩饰。在较低发展国家,城市工人通常不割裂与乡村共同体的联系,以便在需要的时候可以转身回去求得支持”(19)。而伴随着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乡村社会的解体,社会个人日益被原子化,“只能在那些能够提供他就业、医疗、社会福利和退休金的较大的非人格的公共或私人组织之间寻找出路”(20)。
问题在于贪婪资本驱动的放任自由竞争会形成弱肉强食的丛林资本主义社会,带来失控的劳资冲突,累积生成“末日危机”,资本家被迫接受基于私有制的适度社会保障(福利国家),以图部分矫正初次分配不公,淡化劳工大众革命与改革的意愿,维系资本统治秩序。在利润和效率取向的市场机制下,与稀缺的资本和技术要素相比,劳工大众的赋值偏低,且禀赋存在差异的劳动者会遭遇不均等的机会配置,从而带来初次分配的不公。市场是迄今为止人类基础性资源配置的最有效模式,但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基于市场机制的初次分配必然导致收入不平等,累积生成贫富分化。“如果没有作为社会共享机制的社会保障制度安排,不可能化解社会成员可能遭遇的各种生活风险,也不可能缩小初次分配或市场化分配下的收入与消费差距,更遑论共同富裕”(21)。
后发国家将经济发展视为现代化的主体,但需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间保持动态平衡。没有经济发展保障的社会福利不可维系,而没有社会福利保障的政治稳定难以持续,政治动荡会让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化为泡影。历史事实表明,后发国家坚持经济发展优先,政治民主和社会福利的相对滞后是合理的,但不能长期滞后,“逐步跟上”和“小步快走”是可取路径。需要关注的是,欧洲奉行的“社会凯恩斯主义”虽然带来了福利国家,但出现了“福利主义”的危机,而美国奉行的“按揭凯恩斯主义”放任超前消费,则造就了丰饶与贫困孪生的美国式奇景(22)。后发国家如果基于私有制的社会保障予以政策回应,显然难以消解现代化角落的权利贫困,无法真正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
三、中国式现代化何以能跳出现代化角落的窠臼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其光芒能够照耀每一个社会角落。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跳出现代化角落的窠臼,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主要通过以下两种路径实现了对现代化角落权利贫困的消解。
(一)通过全面脱贫、乡村振兴和社会保障,国家资本取代私人资本实现对现代化角落生产和生活要素的持续输血和合理赋值
中国体制的社会主义属性要求用国家资本对现代化角落的生产和生活要素进行合理赋值和持续输血。目前分布在基础性行业和支柱产业的国有资产关系到国民经济命脉、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可以成为全面脱贫、乡村振兴和社会保障的排头兵和主力军,其持续发展壮大可以为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回顾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扶贫战略,可以看出其具有显著的阶段性特征。其一,体制扶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最会种田的農民掌握土地经营权,结合农村水利建设和农业技术推广,让农民增产增收;同时,允许农村兴办乡镇企业和村办企业,农村集体资产和农民非农收入得以增加。二是允许城市个体工商业经营,以缓解下乡知青大量集中返城带来的严重就业问题和生存问题。这一阶段虽然没有正式的扶贫战略和扶贫目标,但是通过体制改革和经济增长实现了减贫的间接目标(23),这是中国经济发展初期实施的一种生存型反贫困政策(24)。其二,开发扶贫。国家通过专设扶贫资金和财政转移支付,将财政资源集中投放到贫困人口聚集的偏远地区,着力解决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滞后问题。农村水利和电力建设改善了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条件,而农村道路修筑既可以畅通物流,让贫困地区的农产品顺利进入市场,降低农民交换权利实现的交易成本,又可以促成农村劳动力便利地进入城市务工,实现非农收入增加,促成农民可行能力的提升。其三,精准脱贫。经过开发扶贫的持续投入,大量贫困人口相继摆脱贫困,“撒胡椒面”式的扶贫资源配置成效边际递减,原先以贫困县和贫困村为单元的笼统区域扶贫战略难以覆盖到真正的贫困户。(25)新时代十年,我们坚持精准扶贫、尽锐出战,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需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的内生发展动力。(26)
全面脱贫是共同富裕的前期工程,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则是共同富裕的基础工程。乡村振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依托,它反映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系统转变,体现了城市化向城镇化发展战略的实质调整,旨在实现城乡的均衡发展。这依然需要社会经济体制的相适调整,要进一步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同时,要逐步废除户籍制度,顺畅要素流动,促成要素竞争,均衡要素收益。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能够以基于公有制的社会保障实现基础性社会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创设生存资源的兜底配置,杜绝逐利资本无序扩张对边缘空间和原子化个体的剥夺和排斥。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生活的安全网和社会运行的稳定器,现代化角落的权利贫困治理需要公平性、覆盖性和可续性兼具的社会保障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进入新时代十年来,我们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教育普及水平实现历史性跨越,基本养老保险覆盖10.4亿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27)未来五年,我们要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劳动报酬提高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基本同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升,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健全”(28)。另外,对于特殊人群的权利贫困,党的二十大也提出了明确要求,如“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29)。
国家资本对现代化角落生产和生活要素的持续输血和合理赋值,需要通过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和完善按要素分配制度,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构建;同时,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通过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和创设多种渠道来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的财产性收入(30),实现由外在“输血”到内在“造血”的结构转变。
(二)以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和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一体建设来尽可能创设机会平等和权利均衡
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困境,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政治衰败、无序党争和政府腐败是根本原因。这表明,民主发展本身就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无法被经济增长简单替换。后发国家现代化角落的权利贫困治理离不开民主政治的顶层设计、强大政党的有效领导和法治政府的廉洁有为。“政治自由和民主权利是发展的‘构成部分,并不需要通过其对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这一渠道间接地建立它们与发展之间的联系”(31)。同样,现代化各项硬性指标的“价值必须取决于它们对相关人的生活和自由产生什么影响,这是发展理念的核心”(32)。
当然,腐败问题既是弱势群体权利贫困感知和生成的重要影响因素,又是导致社会保障制度难以合理创制和良性運行的“顽疾”。“当信息公开与条件明晰这两项自由交易的必要条件被严重破坏时,很多人——交往的双方以及其他人——的生活可能因为缺乏公开性而受到损害”(33)。腐败的盛行必然会消解政治信任,衍生合法性危机,危害社会稳定;同时,腐败会扭曲经济激励,导致发展乏力且乱象丛生。从某种意义上讲,腐败是对事后利润的附加税,寻租收益的递增最终可能挤走生产性投资,抑制新产品和新技术的流动(34),迟滞现代化进程。后发国家要消除腐败就必须“有一个能够减少政治俘获和权力寻租活动机会的发展战略……创造一个减少此类产生外部性活动的机会和相应收益的政策环境”(35),这就需要用政治民主约定权力边界,用全面法治纠正权力妄为。区别于后发国家对西方选举民主的照抄和对腐败盛行的容忍,中国式现代化依靠全过程人民民主来保障中国人民的政治权利和政治自由,并将反腐败视为一场决不能输的重大政治斗争。“高调且激进的政治一般都是现代后发国家的政治主调”(36),“问题不仅在于从旧体制转变到新体制之间的峡谷有多深多宽,还在于什么样的政治势力最有能力跨越它”(37)。中国式现代化当然意味着新旧体制的结构性转变,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既是这种转变的组织者和推动者,又是这种转变取得成功的关键。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基于原发民主元素,审慎借鉴外来民主理念和形式,注重提升人民的民主参与体验和实际的民主治理绩效。它不是高调且激进的,而是务实且渐进的,既有顶层政治设计,又有中宏观制度创设,还有微观运行机制调适。与中国式现代化相伴而行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统合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建构过程。另外,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一体建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当然需要,它与全过程人民民主共同捍卫中国人民的机会均等和权利均衡。这就需要在扎实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同时,“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38)。同时,“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序”(39)。因此,需以完善的法治体系规范政府透明性建设,以有效的政府制度安排打造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政府信用支撑与防护性兜底保障。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优化政府职责体系和组织结构,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提高行政效率和公信力”(40)。中国式现代化要努力促成全能主义政府向有限法治政府的转变,通过构建公开透明、边界清晰、分工合理和权责一致的政府职能体系实现政府的有为和高效。
四、结语
现代化是人类共同的事业,但也是“一个创造与毁灭并举的过程,它以人的错位和痛苦的高昂代价换来新的机会和新的前景”(41)。由资本逻辑驱动的西方式现代化无法以福利国家梦想的编织来真正化解贫富分化、社会对立和政治冲突,而后发国家对西方式现代化的附庸和西方政经模式的照搬更会衍生现代化角落的权利贫困,带来难以承受的现代化之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本逻辑超越资本逻辑,通过国家资本实现对现代化角落权利贫困空间和人群的权利赋予,并用全过程人民民主和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一体建设尽可能创设全社会的机会均等和权利均衡,进而真正消解了现代化角落权利贫困存续的内外根由。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全面超越,将为后发国家跳出现代化角落的窠臼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样本。
注释:
(1)(2)(19)(20)(41) [美]C·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段小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7—38、113—114、113、113、38页。
(3)(6)(7) [印]阿马蒂亚·森:《贫困与饥荒》,王宇、王文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55、4、205页。
(4)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57页。
(5)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29页。
(8)(13)(14)(15)(16)(17)(33) [印]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5、7、32—33、11、181、180、32页。
(9)(10)(18)(31)(32) [印]阿馬蒂亚·森:《正义的理念》,王磊、李航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16、217、210—211、323、322页。
(11) [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589—590页。
(12) 宋朝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后发国家现代化制度症结的破解》,《科学社会主义》2020年第6期。
(21) 郑功成:《共同富裕与社会保障的逻辑关系及福利中国建设实践》,《社会保障评论》2022年第1期。
(22) 顾昕:《美国按揭型凯恩斯主义的前世今生》,《读书》2018年第1期。
(23) 吴国宝:《改革开放4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成就及经验》,《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24) 王春光:《社会治理视角下的农村开发扶贫问题研究》,《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5年第3期。
(25) 袁明宝、余练:《精准扶贫嵌入与全面脱贫的基层治理逻辑》,《开放时代》2021年第3期。
(26)(27)(28)(29)(30)(38)(40)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
(34) Romer Paul, New Goods, Old Theory, and the Welfare Costs of Trade Restriction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4, 43(1), pp.5-38.
(35) 林毅夫、[喀麦隆]塞勒斯汀·孟加:《战胜命运——跨越贫困陷阱,创造经济奇迹》,张彤晓、顾炎民、薛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9页。
(36) 任剑涛:《人权、共和与革命:潘恩思想与现代政治的调性》,《江苏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
(37) [美]亚当·普沃斯基:《民主与市场——东欧与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改革》,包雅钧、刘忠瑞、胡元梓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9页。
(39) [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
作者简介:沈承诚,苏州大学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苏州大学新型城镇化与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苏州,215123。
(责任编辑 刘龙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