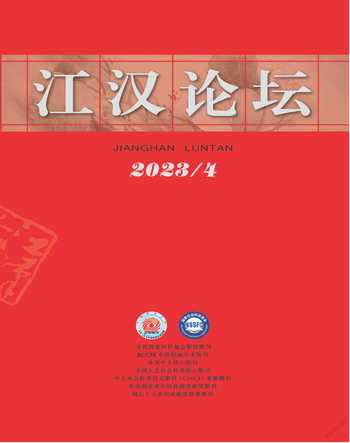论柳宗元流寓文学创作的意象图式与隐喻编码
周水涛 张学松

摘要:在符码性质与符码组合层面讨论柳宗元愁苦愤懑情感的意象化,解析其流寓诗文创作的隐喻思维,具有重要意义。承载柳宗元隐喻思维的意象图式可大致分为两个大类。第一类是源域与目标域只存在一组对应关系的单质意象图式,这个类别包含三种隐喻建构方式:一是基于自己的审美情趣与流寓心理,选择带有民族印记、积淀着历史文化的“表象”以构建意象图式;二是在传统隐喻结构上添加语码,赋予已有意象图式新的隐喻功能;三是进行个人化的“表象赋值”,在特定语境中自然生成单质意象图式。单质意象图式在柳宗元的流寓文学创作中使用频率较高。第二类是源域与目标域之间至少存在两组对应关系的化合意象图式,这个类别包含两种隐喻建构方式。第一种方式是采用古代典籍中的人和事作为“表象”,通过化用、截取、转喻、串连、融汇等方式,建构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子域(子集)的隐喻结构。第二种方式是利用“表象”的复杂属性作为映射源,构建源域与目标域存在多组对应关系的隐喻结构。化合意象图式能够高效阐释柳宗元特殊而复杂的流寓心理。
关键词:意象图式;隐喻编码;映射;源域;目标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古代流寓文学理论研究”(21AZD132)
中图分类号:I20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23)04-0076-08
所谓“流寓”是指官员贬谪外放任职、外交出使被扣,或者文人因战乱灾荒而迁移、因生存而旅居他乡;他们记写自己生活与情感的文学作品即为流寓文学。(1)流寓文学的外延宽泛,在此特指柳宗元贬谪永州、柳州阶段的诗文创作。愤怒出诗人,从某种意义上讲,流寓成就了柳宗元。古老的艺术传统、特殊的政治环境、独特的创作个性等因素,使柳宗元执着于借助意象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因此,透视柳宗元诗文的意象,解构其诗文创作的隐喻思维,具有重要意义。
在认知语言学视域中,“意象”或“表象”被看作是一种心理表征,是客观事物留在人们头脑中的印象或形象。图式是指人们在感觉、知觉和表象的基础上加工所形成的认知结构。“意象”与“图式”融合而形成“意象图式”,是一种“在我们的日常身体体验中反复出现的”、融感性理性于一体的认知结构(2):这种结构既有意象的表象概括,又有符号的抽象,主要“发挥抽象结构作用”(3)。意象图式是认知语言学的核心概念或范畴。本土学者王寅在研究西方认知语言学理论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现实—认知—语言”是人类语言生成的主要途径(4),隐喻或类比是认知思维的主要方式,而意象图式则发挥着关键性作用:意象图式把喻体的内在结构映射到陌生的本体上,经过经验性的“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从而生成新的概念或范畴。(5)德国学者温格瑞尔等人认为:隐喻是从源模型向目标模型的单向映射,二者产生关联的关键因素是同一性。(6)美国学者莱考夫和约翰逊认为:“日常生活中隐喻无所不在,我们思想和行为所依据的概念系统本身是以隐喻为基础……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每天所做的一切就充满了隐喻。”(7)也许就是因为隐喻的“无处不在”及隐喻思维在方法论层面的价值,意象图式理论进入了文学批评疆域。莱考夫在专著《不仅仅是冷静的理性》中讨论了隐喻思维在诗歌等文艺作品中的运用,特纳在专著《死亡是美丽之母》和《文学心灵》中,比较深入地研究了“日常概念隐喻”与寓言情节结构的映射关联。因此,规避传统的“意会”意象分析,从认知语言学切入审视柳宗元诗文的意象构建,可能会更直观、更透彻地揭示其隐喻思维及艺术编码方式。限于篇幅及探索的难度,本文仅在符码性质与符码组合层面讨论柳宗元愁苦愤懑情感的意象化或符码化,且仅讨论诗文创作的两类意象图式及其艺术编码方式。
一、单质意象图式与流寓文学创作的艺术编码
单质,是一个化学名词,是指同种元素组成的纯净物。在此,我们借用这一概念来描述意象图式的建构相对单纯与隐喻指向单一。(8)莱考夫和约翰逊认为每一个隐喻结构都包括三个部分:源域(source domain,喻体)与目标域(target domain,本体)以及关联二者的基域(ground domain);(9)斯坦哈特称这三者为“三位一体单位”,并用公式(S,T, fm)来描述三者的函数关系,其中fm是生发映射关联的“结构-保存映射”。(10)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从本土认知习惯出发,将源域与目标域分别看作隐喻结构的喻体与本体,将发挥映射作用的基域看作二者的映射关联。由此,“单质意象图式”的隐喻结构的对应映射关系可以描述为:A—Α1,亦即喻体与本体仅存在相似点“A”,因而喻体与本体在“A”点上发生映射关联。例如,在柳宗元的“永州八记”等诗文中,“峭石”以其峭立坚硬而隐喻一种人品——人格的刚毅挺拔 ;尽管喻体以其形状与硬度两个“类比点”关联一种人格,但我们认为这一类比结构只有一个映射点,即“峭石”映射“刚毅挺拔”,峭石与刚毅挺拔的人格构成了一个单质的意象图式。
在柳宗元的艺术编码体系中,单质意象圖式的类型众多。单质意象图式所用“表象”可以分为许多系列,如奇峰怪石、嘉木幽树、香草香花、秽草恶木、清泉溪流、险地恶境、善兽好鸟、凶兽毒物,等等。每一个“表象”集合都包括诸多“元素”,如嘉木幽树集合中包括桂、木芙蓉、梅、灵寿木、石榴、斛、橘柚、柳、榕、松等十几种“元素”,这些“元素”或“能指”构成隐喻结构之后各有“所指”,在许多情况下只表达一个义项。
莱考夫、约翰逊等人认定:每一意象图式结构中,源域与目标域的映射关联都是在人类“经验互动”中产生并被固定下来的。以此论断为基准,根据物象的选择及隐喻方式的差异,我们将柳宗元流寓文学创作的单质意象图式分为三个类别。
(一)单质意象图式的沿用与选择
我们知道,许多隐喻结构都是人类长期实践与“经验互动”的结果。毋庸赘言,柳宗元诗文中的许多意象图式带有鲜明的民族印记,是长期历史文化沉淀的结果。例如,由山石、驳岸、柳、蓬、茅、竹、芙蓉、苍鹰、鹘、鹤、猿、瘴、射工(蜮)、飓母、蛟涎(水蛭)、缧囚等“表象”所构成的意象图式反复出现在其诗文中,这些意象图式积淀着深厚的历史文化质素,其隐喻指向有着明显的承袭倾向。
对于单质“表象”的选择与赋形赋性,柳宗元虽遵循了历史的“经验互动”,但又有自己的特点。以苏轼的选择为参照,柳宗元有两大特点。一是,因为景仰先贤屈原,柳宗元在很大程度上传承了屈原“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的手法,大量使用植物“表象”,尤其是对橘、柑、柚、薜荔、木芙蓉等“嘉木”情有独钟,因而倾向于以香草嘉木为“表象”构建意象图式;而苏轼的“香草嘉木”比德倾向不及柳宗元明显,且橘、薜荔等植物很少出现在苏轼的流寓文学创作中,由于仰慕陶渊明,菊、兰、梅等植物用為喻体的频率远远超过柳宗元。二是柳宗元对于某些“表象”的赋形赋性有着独特喜好。例如,对泉、鸿、猿、鹤等“表象”的禀赋认定,柳苏二人存在明显差异。对于泉,柳宗元诗文的隐喻侧重于清幽,如“永州八记”的泉水大多先闻其泠泠之声——或“如鸣佩环”,或“锵鸣金石”,再现其幽幽之形,而苏轼诗词则侧重于清亮——“劝客眠风竹,长斋饮石泉”“霭霭藏孤寺,泠泠出细泉”“仆夫寻老木,童子引清泉”“堂虚泉漱玉,砌静笋遗苞”,这些诗句中的泉水色清亮,望而可见,渲染着明朗、和顺,甚至是欢愉的情调。在柳宗元笔下,鸿(雁)的赋性比较单一,主要以“孤鸿”“哀鸿”的形象出现,如“杳杳渔父吟,叫叫羁鸿哀”“日照天正绿,杳杳归鸿吟”;而在苏轼笔下,当鸿(雁)作为单质意象图式的“表象”时,在不同的语境有不同的赋性:在“自顾尘缨犹未濯,九霄终日羡冥鸿”中,鸿是志在九霄的“冥冥之鸿”,在“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中,鸿是卓尔不群的“孤鸿”……“征鸿”“冥鸿”“离鸿”“孤鸿”“归鸿”等物象的负载各异。——除开“师承”(包括学养)等方面的原因,导致二人选择与赋形赋性差异的最关键的因素是脾性气质,如柳宗元性格内敛沉稳,苏轼心性豁达、性格外向。
在柳宗元流寓文学的艺术编码中,单质意象图式是使用频率最高、运用最广泛、最灵活的隐喻结构。奇峰怪石、嘉木幽树、香草香花等集合中的“元素”,不仅单独构成单质意象图式,频繁出现在柳宗元的诗文中,而且还与另外的单质意象图式组合,构成“组合意象图式”,用于表达复杂的流寓情感。例如,在“永州八记”中多次出现的“僻山”意象图式、《得卢衡州书因以诗寄》中的“炎方”意象图式、《江雪》中的“江雪”意象图式,就是使用多种单质“元素”组合而成的隐喻结构,这些组合意象图式用于隐喻孤独、愤懑、抑郁、不屈、放达、超脱等多种因素纠结缠绕的复杂流寓情感。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师承屈原等方面的原因,奇峰怪石、清泉溪流、嘉木幽树等集合中的“元素”在柳宗元诗文中出现的频率极高,而苏轼则在更大程度上倾向于以动物“表象”构建意象图式。——在《苏轼海南诗文选注》收录的130首诗赋和部分散文中,有动物71种,其中鸿出现80次,鹤出现180次。(11)与同贬“炎方”的挚友刘禹锡的创作相较,柳宗元的单质意象图式构建也显现出独特个性。清泉溪流、嘉木幽树等“元素”在刘禹锡流寓诗歌中出现的频率远远低于柳宗元,而奇峰怪石的隐喻指向也与柳宗元有着明显差异:在柳宗元的流寓诗文中,奇峰怪石有两大寓意承载:挺拔刚毅(如“山之特立,不与培为类”)与孤寂幽峭(如“海畔尖山似剑芒,秋来处处割愁肠”等),而刘禹锡虽有以奇峰承载孤苦冷寂的诗句(如“秋水清无力,寒山暮多思”等),但在更多情况下,奇峰怪石多用于外化诗人的雄心壮志,如《望衡山》以衡山的高峻宏伟抒发自己的宏图大略,《九华山歌》通过描摹九华山的险峻壮观,展现自己博大的胸怀与鸿鹄之志。
(二)构建个性化的单质意象图式
对于柳宗元而言,构建新的意象图式,就是在原有单质意象元素的基础上添加新的“语素”或“表象因子”,使之成为新的单质意象图式。例如,“江”的本义是人工河道,在文化演进的过程中生成了多种意象图式,因而“江”作为一般的传统表意元素,频繁出现在柳宗元的诗文中,其意指不断变化,在不同的语境中有着不同隐喻指向。例如,在“高岩瞰清江,幽窟潜神蛟”(《游朝阳岩遂登西亭二十韵》)“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等诗句中,“江”或凭其外形,或因其水色,构成了一般的意象图式,其隐喻思维方式具有“一般性”,亦即“江”的隐喻指向立足于普泛的“经验互动”。然而,“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江雪》)“寒江夜雨声潺潺,晓云遮尽仙人山”(《雨中赠仙人山贾山人》)等诗句中的“寒江”则是立足于柳宗元个人的审美经验认知,构成了具有柳宗元个人色彩的意象图式。前者借寒江独钓的渔翁,表达自己的孤傲高洁,后者则借隐居山巅的玄豹之眼俯瞰尘世泥涂,隐喻叙事主体的卓尔不群,二者异曲同工,而“寒江”表象参与了主旨表达或“形象塑造”:作为“源域”的寒江以其“孤冷清澈”映射“孤傲高洁”这一“目标域”,二者发生映射关联。很明显,柳宗元在普通的“江意象图式”之前加了语素“寒”,构成“寒江意象图式”,用以自我人格标榜、隐喻自己独特的流寓处境。鸟兽虫鱼、草树山河、星月云雨,柳宗元基于这些传统的“表象”构建了许多个性化的意象图式,如幽树、愚溪、毒蜃、窗蠹、潜蝎、羁鸿、惊鳞、穷鳞等等,这些意象图式隐喻了诗人特有的流寓情感。
从表面上看,赋予已有意象图式新的隐喻功能,是在已有“经验互动”的隐喻结构上添加“语码”或“义项”,但这种添加涉及“叙事主体”的诸多方面,如个性气质、审美情趣、流寓体验、师承学养等。以苏轼为参照,柳宗元的“语码”添加及相关的隐喻建构,有着鲜明的个人特征。例如,同样表达身陷南荒、壮志未酬的愤懑与悲哀,柳宗元添加的是与囚禁、惊恐、幽闭、孤苦、激愤相关的义项,从而形成笼鹰、羁鸿、跂乌、惊鸿等“表象”,而由这些“表象”所构成的隐喻结构大多渲染了郁闷、忧惧、幽怨、孤寂等情绪情感,甚至隐喻了某种绝望心理。例如,在《跂乌词》中,诗人自喻为伤残独足的乌鸦,被群乌猜忌遗弃,提心吊胆地活着(“还顾泥涂备蝼蚁,仰看栋梁防燕雀”),最后“支离无趾犹自免,努力低飞逃后患”。苏轼添加的则是另一套“语码”,如病、瘦、孤等。由病鹤、瘦鹤、病马、瘦马、蹇驴等“表象”所构成的隐喻结构,在隐喻愁苦、困顿、孤独之际,还以喻体的精瘦、遒劲、卓尔不群表达了叙事主体对苦难孤独的蔑视与超越,对操守的矢志不移。例如,《鹤叹》中的驯鹤虽然“三尺长胫阁瘦躯”,但睥睨主人的呼唤,不屑于食用投喂的饼饵,俄而“戛然长鸣乃下趋”。
人们一般认为,“骚怨”传承、个性的内敛沉稳、挥之不去的南贬忧惧等因素,决定了柳宗元的“语码”选择及相关的编码方式,而对陶潜、白居易等先贤的仰慕、对释道的更多接受、豪放豁达的个性、北宋书画崇瘦尚孤等因素,驱使苏轼添选另一套语码。当然,构成柳苏二人选码编码差异的关键因素是个性气质。例如,同样绝境明志,内向沉稳决定了柳宗元以峭石、幽泉、愚溪等“表象”来呼应内敛、清幽等禀赋脾性,而豪放外向的个性决定了苏轼选择幽人、野鹤、飞鸿、瘦鹤、大江、扁舟、明月、美酒等符码来渲染飘逸闲适、放荡不羁的心性;同样显现叙事主体的超迈解脱,柳宗元的“为乐”具有“一过性”:“闷则出游”,但最终因“不复为乐”而回归“凄神寒骨”,而苏轼的“为乐”大多奔放豁达,更多表现为对流寓凄苦孤独的超越化解。也因此,前者风格幽深、清峻、悲婉,后者豪放、刚健、超迈。从某种意义上说,“骚怨”与“东坡界”既是两种文风,也是两种流寓心态与人生境界。
(三)在特定语境中自然生成单质意象图式
莱考夫等认为:“文化中最根本的价值观与该文化中最基本的隐喻结构是一致的。”(12)这一观点隐含着关键性论断:文化价值判断影响隐喻思维与隐喻结构的形成,或者说隐喻结构的价值判断与文化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对于柳宗元的隐喻思维而言,我们应该考虑两个问题:柳宗元通过何种“表象”来外化自己的思想情感?其外化依托了何种初始价值判断?
莱考夫等将人类隐喻分为方位隐喻、实体隐喻、结构隐喻等三大类型共27种模式。他的“方位隐喻”分析比较直观地展示了文化价值判断对隐喻思维的影响:“好为上”(up or high is good)这一初始价值理念决定了某些隐喻模式。他列舉了这样的例子:
I am feeling up.我今天很高兴。(与“好为上”一致,up)(13)
I am feeling down.我情绪很低落。(与“好为上”相反,down)
My spirits rose.我心情越来越好。(与“好为上”一致,rose或rise)
My spirits sank.我的心情到了低谷。(与“好为上”相反,sank或sink)(14)
莱考夫通过两两相对的“隐喻概念”说明:“好为上”这一思维倾向或初始价值理念决定了“方位隐喻”的基本模式:高兴的、健康的、进步的、光明的、明天的……就是“向上”,反之,就是“向下”。
人类的思维方式更多的是共性与互通性,隐喻思维也不例外。毋庸赘言,柳宗元诗文的隐喻思维体现了人类思维的共性,但其诗文的许多意象图式带有鲜明的个人印记,尤其是那些在特定语境中自然生成的单质意象图式。在此我们以《钴潭西小丘记》等三篇游记为例说明问题。这三篇游记有着相同的叙事目的:展示卓然特立的人格,抒发被弃置炎荒的郁闷;相同的叙事指向决定了相同的叙事结构与叙事内容:叙事主体寻觅景点——整治荒僻——佳境显现——叙事主体俯瞰高蹈,超脱凡世,心与神游,与自然融为一体。特定的叙事方式与叙事内容、叙事重心,构成了特定的叙事语境,而这种特定的叙事语境决定了铲刈秽草、斫榛莽、焚茅茷、枕席而卧、颓然就醉、箕踞而遨等行为和秽草、恶木、榛莽、茅茷、翳朽(枯枝败叶)、嘉木、美竹、奇卉、奇石等物体的“意象性”,也就是说,在特定的语境中,铲刈秽草等行为与秽草嘉木等物体具有了隐喻性,成为了构成意象图式的“表象”。
例如,“箕踞而遨”这一怡然放纵的坐姿,它构成的意象图式的隐喻指向是:挺拔刚毅的人格与暂忘苦痛之后的超然物外、怡然自得,因而这一意象图式真实揭示了柳宗元因贬谪炎方所致的精神状态:“时到幽树好石,暂得一笑”,“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但随之回归抑郁苦闷,“已复不乐”。再例如,在“永州八记”中,“石”作为“表象”所构成的意象图式主要指向叙事主体的人格精神。例如,“其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中的“石”被赋予了“骄傲不恭”的意绪,同时也渲染了困顿窘迫之意。
上述个性化的单质意象图式的生成,事实上关联两大紧密关联的因素:个人化的“表象赋值”与特定的语境构建。个人化的“表象赋值”,即叙事主体根据个人的价值认定与审美嗜好对“表象”进行赋形赋性,即审美主体将自己的主观审美体验赋予审美对象,使之成为具有为我所用的表现性或王国维所说的“有我之境”。例如,“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出”的形状与个性,是柳宗元根据的主观审美感受所赋予的,也许只有柳宗元认为石头的尖削凸起、兀然高耸,是人格挺拔刚毅的象征,而丘石骤然突起,在柳宗元眼中有破土而起、负重抗争之勇,因而与负重拼搏、不畏艰险的品格形成同构。语境,在此是指马林诺夫斯基所说的“情景语境”,是上下文、时间、空间、情景、对象、话语前提等因素所构成的言语氛围。在《钴潭西小丘记》《始得西山宴游记》等散文中,荒野的草木山石在物理层面没有本质差异,但在特定的语境构建中,“中性”的草木山石被一一赋值:同为草木,有的被认定为“嘉木”“美竹”“奇卉”,有的则被归入“恶木”“榛莽”“秽草”;同为山石土丘,但有“奇石”“特立之山”与“诡石”“培”之分。显然,柳宗元基于具体的语境,根据自己的个人价值取向及审美嗜好,对这些物象进行了赋值,因而这些物象成为构建单质意象图式的“表象”,最终生成带有个人印记、具有特定隐喻指向的单质意象图式。
语境构建,自然要涉及“表象”的选择。柳宗元的物象选择与刘禹锡、苏轼等流寓作家有着明显区别。例如,同样自我标榜、明志示德,柳宗元习惯于以橘、木芙蓉、薜荔、渔翁渔父等为核心“表象”,语境以促狭险峻为主调,而苏轼则以幽人、鹤、鸿等为主要载体,语境以平和开阔为底色。同样表达身居贬所的惊恐悲凉,柳宗元通过“阴森野葛交蔽日,悬蛇结虺如蒲萄”“蛇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茂树恶木,嘉葩毒卉,乱杂而争植”等诗文塑造了奇异怪诞,阴森恐怖的炎方绝境,“野葛”“蓬蒿”“蛇虺”等是构建险恶语境的符码,而苏轼仅在《到惠州谢表》《与钱济明十六首》等诗文中谈及身处“瘴疠之地”的艰苦,使用了“魑魅”“夜雨梧桐”等古老的符码,构境与表意大多在“适度”范围之内,不会“读之令人惨然不乐”(瞿佑《归园诗话卷上》)。同样“咏史”,柳宗元与刘禹锡的隐喻建构存在明显差异。柳宗元的叙事对象多为命运多舛、人生坎坷的历史人物与激荡人心的史实,叙事符码多为冷色,从而构成充满张力的语境。例如,《咏荆轲》《咏三良》等诗作“吟诵”的是惨烈的史实,“函首”“朔风”“易水”“风雷”“幽隧”“黄肠”等“冷色”艺术符码构建了凝重乃至肃杀的叙事氛围,叙事主体在凝重的语境中谴责批判当权者的失策(“从邪陷厥父,吾欲讨彼狂”),同时倾诉自己遭遇昏君而被贬谪流放的怨愤。刘禹锡多使用“暖色”的“表象”构建平和、舒缓的语境,借古讽今,在哂笑与感叹之中完成嘲讽批判,《西塞山怀古》《乌衣巷》《石头城》《金陵怀古》等作品无不如此。
我们还要看到,带有柳宗元个人印记的意象图式的隐喻结构,既体现了莱考夫所说的本民族“最根本的价值观”,又有其个人化的价值认定与隐喻表达。柳宗元在给“其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出”“山之特立,不与培为类”中的峭石尖山赋值时,无疑遵循了“好为上”的“最根本的价值观”,因为“负土而出”或“特立”有“克服阻力,奋勇向上”之意向,体现了类似于“up”的正向价值理念,而清流、修竹等“表象”被用于比附美好品格,也在于它们暗合“好为上”的普泛初始价值理念。然而,这些物象,何时被赋予正值(up),何时被赋予负值(down),那就看具体的文本诉求了。峭石尖山在《钴潭西小丘记》《始得西山宴游记》等文本中被赋予正值,而在《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得卢衡州书因以诗寄》等作品中,峭石尖山则被赋予负值。——在“海畔尖山似剑芒,秋来处处割愁肠”“林邑东回山似戟,牂牁南下水如汤”等诗句中,尖山峭石成为构建炎荒苦境的核心元素,用于表达诗人的贬谪流寓之苦。至于草木何时视为榛莽,何时认作香草嘉木,皆听任于柳宗元的心情。例如,尖山、尖峰在柳宗元流寓文学创作中,更多取用“表象”的“刺”“割”功能,用于倾诉思乡之苦,渲染灵魂撕裂之痛,而在韩愈诗作之中,尖山化为“石剑”,如“地遐物奇怪,水镜涵石剑”(《喜侯喜至赠张籍张彻》),“泉申拖修白,石剑攒高青”(《答张彻》),同为流寓制作,但韩愈的“石剑”主要用来描摹岭南石峰之奇,抒发讶异惊艳的观景心情。
很明显,意象图式建构的不同價值选择,也是柳宗元赋予已有意象图式新的隐喻功能的方式或途径之一。
当然,在韩愈、刘禹锡、苏轼等“南贬”文人的意象图式构建中,这种“背向赋值”的现象也存在,但存在“表象”选择差异与价值认定侧重。例如,苏轼的艺术编码中,舟、鸿、月等“表象”的使用频率极高,这些符码有时被正向赋值(up),指向自在、闲适、淡泊等目标域,有时则被反向赋值(down),是承载诗人颠沛流离、流放之苦的能指。
二、化合意象图式与流寓文学创作的艺术编码
化合物是指区别于单质、由两种或两种以上元素的原子组成的纯净物。在此,我们借化学概念“化合”二字,用之于描述意象图式结构的交融性与隐喻指向的多向性。所谓化合意象图式,是指隐喻对应在两组或两组以上且映射过程曲折复杂的隐喻结构。
斯坦哈特认为,类比是隐喻思维的基石,而相似性则是类比推理的起点,是连接源域与目标域的纽带。他用“细胞是工厂”这个“概念”来说明源域与目标域的多点对应,他认为“细胞”与“工厂”二者之间存在“细胞是化工厂”“大细胞有机体是通用工厂”“细胞核是董事会”等8种对应关系。(15)我们可用以下公式概括斯坦哈特所说的“多点类比对应关系”:
源域映射点 目标域对应点
A…………………………Α1
B………………………… B1
……………………………
N………………………… N1
此公式重在说明:在一个意象图式隐喻结构中,喻体的映射点A与本体的对应点Α1发生类比关联,依此类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对应结构构成“化合意象图式”。依托斯坦哈特的类比隐喻理论,我们可以将柳宗元流寓文学化合意象图式归纳为两种类型。
(一)典籍事迹化合意象图式与映射编码
此种意象图式建构的基本特点是:采用古代典籍中的人和事作为“表象”,通过化用、截取、转喻等方式,建构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子域(子集)的隐喻结构。在此我们以橘为“表象”的化合意象图式说明问题。
在《南中荣橘柚》《得卢衡州书因以诗寄》《柳州城西北隅种甘树》《吊屈原文》等作品中,橘(包括柚与甘/柑)作为隐喻“表象”,建构了一个有三个映射子域的化合意象图式。
第一个映射子域是橘德。柳宗元通过艺术编码,赋予橘三种德性:守南橘北枳之志,不服迁徙,有狐死首丘之忠;身被利刺,刚直不阿;内外兼修:果形优美,果肉“精色内白”。毋庸赘言,橘的三种德性即三个映射点,与之相对的是流寓文人的三种高尚人格。这三个映射点是橘德这一子域的“孙域”,即“橘德子域”的下位映射点。橘德映射的形成,在于柳宗元通过暗示、融汇等手法,化用、移用了《橘颂》等经典性作品对橘的定性与赞美,借用了与之相关的语境及渲染手法。
第二个映射子域是屈子人格:《南中荣橘柚》《吊屈原文》等作品通过对《离骚》《橘颂》等作品主旨的移用、对橘形象的渲染、对抒情主人公(屈原)的赞美,使橘德与屈原人格互文叠加,形成“屈子人格”映射结构。这种映射结构被打上了鲜明的“个人化”印记,被柳宗元用于表达对先贤的敬仰,展现自己的志向,倾诉自己的流寓的悲苦。
第三个子域是屈原命运。这一映射结构的艺术编码具有鲜明的“想象迁移”特征。《南中荣橘柚》《吊屈原文》等作品渲染橘眷念南国、不服迁徙的品性,赞扬屈原投身汨罗以守皓皓之白、洗蒙尘之冤、明高洁之志的壮举,以至橘的品性、命运与屈原的品性命运叠加互文,从而暗示高洁人格与悲凉结局的因果关联,进而形成“人格命运”的类比映射结构——柳宗元将自身命运与屈原命运进行对比。这种隐喻结构既有对先贤命运的喟叹、对“佼佼者易折,皎皎者易污”等规律的映射,又承载了自我心迹的表白、自我人格的标榜以及对流放命运的哀吟。
“人物表象”所构成的化合映射结构,其映射过程相对简单,隐喻指向比较集中。在柳宗元的诗文中,乐毅(《咏史》)、屈原(《吊屈原文》)、马援(《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樊重(《冉溪》)等“人物表象”所构成的源域或映射结构,一般包括“人物品性”与“人物命运”两个子域(映射子域)。个别映射子域还有孙域(上文中的橘德子域包括三个孙域)。品性映射与命运映射是高效而凝练的隐喻方式,因为源域的“映射蕴涵”大多意蕴丰富,且“内涵”多为文人们所熟识,所以可以省略相关的渲染烘托。正因如此,其使用频率极高。
然而,由“事迹”或“人事交集”而成的映射结构,大多编码复杂,蕴含丰富,映射多向,尤其是那些有化用过程的映射结构。有些映射,十分微妙,甚至还包含互文、转译、转喻、隐喻叠加、对照等环节,读者只有经过繁琐的解码才能完全明白编码者的意思。例如,诗句“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中的“濯缨”,在融汇《孟子·离娄上》、先秦《沧浪歌》、屈原《渔父》、李陵赠别诗等多种古籍“沧浪濯缨”的基础上,楔入了“以泪洗缨”义项,赋予“濯缨行为”新的隐喻指向:一是标榜品性高洁——你我都是高洁清白之士,一尘不染,因而不必到河边濯洗冠缨了;二是渲染两人再次南贬之后的生离死别与深哀剧痛:垂泪千行,可以濯缨;三是同病相怜,哀叹二人命运不济,前途渺茫,抒发悲痛、愤懑、伤感、失落。显然,这种隐喻的生成,采用了串连、融汇、转用、添加“义项”等多种映射手法。
再如,《湘岸移木芙蓉植龙兴精舍》的诗句“芰荷谅难杂”句,化用了《楚辞·招魂》诗句“芙蓉始发,杂芰荷些”:仅取屈原诗句之外壳而舍其内涵,将水芙蓉与木芙蓉对比——荷花因与菱为伍而被作为反衬对象,凸显木芙蓉的耐寒耐旱与芳洁,用以映射人格的超凡脱俗与坚贞刚毅,以及心灵的孤独与被弃置的失落。其映射包括融汇、迁移、对比、反衬、反接等复杂过程:“芰荷谅难杂”反接“杂芰荷些”的芰荷同伍,“杂芰荷些”迁移为“芰荷谅难杂”,将经受秋霜的木芙蓉与临秋颓败的水芙蓉对比,以水芙蓉与菱为伍反衬木芙蓉的高风傲骨、卓尔不群,等等。
“正典别用”也是化合意象图式的映射方式复杂性的表现之一。《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一诗将汉代著名将领马援作为“人物表象”构成意象图式,但在此马援并未像屈原、乐毅等人物那样,用于比附作家自己的品性与命运,而是以马援辉煌的人生反衬自己仕途夭折的人生悲凉,从而抒发郁闷与悲哀。在《愚溪》等作品中,由愚溪等表象构成的系列源域的映射赋值,可能是正向的(up),也可能是反向的(down),因为柳宗元对典籍事迹的取义是多方面的,加之对“愚”的定义有自谦、幽愤、怨怼、抨击等多种成分,从而导致“愚”的含义具有“似是而非”的多向性。正典反用或反典正用,在柳宗元的流寓文学编码中,应该不在少数。当然,典籍事迹化合意象图式大多带有个人经验,因为其编码方式密切关联柳宗元本人的价值取向、人生经历与流寓处境。
柳宗元熟读古书,其典籍事迹化合意象图式的建构“取材”极广:“典籍”上自远古文献,下至当代制作,可任意采撷,而史部、子部、集部为其主要“资料库”;至于文字之外的轶闻传说,因其不可胜数而随手拈来。典籍事迹化合意象图式的使用频率极高,几乎“无诗不典”—— 一般短制,典籍事迹“表象”总有二三个,至于《同刘二十八院长述旧言怀……》之类长篇,“用典”则达40多个。(16)
柳苏二人的典籍事迹化合意象图式的建构,仅有小小差异。例如,在师承方面,柳宗元追随屈原,许多“表象”取自楚辞骚赋,苏轼则仰慕陶潜,范滂、李白、白居易、欧阳修等前贤则为其追随对象,其流寓文学创作的编码与这些先贤的著作及事迹有着诸多关联。此外,由于个性、学养等方面的原因,柳宗元流寓文学创作的编码的繁复程度大于苏轼。限于篇幅,在此暂不展开比较。
(二)多种差化合意象图式与映射编码
一个属,可能包含多个种,种与种的差异就叫种差。种差,事实上就是此物不同于彼物的本质特征,为了行文的方便,我们把描述种的属性特点的文字称作种差。
假设鸟这一属中有白鹤、白鹭、鹌鹑、麻雀四个种,那么,与白鹭比较,白鹤获得“长寿”种差,与鹌鹑比较白鹤获得“形态优美”种差,与麻雀比较有“高翔于云端”种差,于是白鹤这一概念的定义就是“白鹤是一种长寿、形态优美、高翔于云端的鸟”,而“长寿”“形态优美”“高翔于云端”就是白鹤不同于其他鸟类的三个种差,也就是白鹤的本质特征。如果我们用白鹤“表象”构成意象图式,那么三个种差就成了源域的三个映射点,根据中国文人的隐喻习惯,这三个映射点的目标对应物可能是长寿、人格精神高尚、高蹈于世、超凡脱俗,等等。由此不难看出,如果使用有多个种差的“属”作为“表象”来建构意象图式,那么这个隐喻结构就可称为“多种差化合意象图式”。
在柳宗元的诗文中,多种差化合意象图式主要用于表达比较复杂的流寓心理。在此我们以诗句“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中的薜荔意象来说明问题。薜荔是一种攀援或匍匐灌木,从生物学角度看,它有这样的特征:常攀援于大树、断墙残壁、庭园围墙等处,蔓生浓绿,四季常青,具有观赏价值,耐贫瘠干旱,经得住风吹雨打……据此,我们可从文学角度归纳出多个种差:生长于荒僻之处;耐贫瘠干旱,生命力强;外形优美……这些种差构成了多个映射点,具有多种隐喻指向。事实上,在柳宗元之前,薜荔作为一种正值意象反复出现在文人的笔下,例如,薜荔作为香草佳物在屈原的《离骚》《九歌》等作品中出现了十来次。在柳宗元的诗句“密雨斜侵薜荔墙”中,仅有三个种差发挥了隐喻作用,种差及其映射的对应项列举如下:
生于荒僻之处——暗喻身处炎荒的孤寂悲凉;
浓绿长青—— 自诩人格高洁、品性美好;
耐贫瘠干旱——暗指身处蛮荒而坚韧刚毅。
显然,多个种差所构成的映射点使薜荔意象图式具有多重隐喻指向,适宜于隐喻柳宗元复杂的流寓心态与独特的流寓处境,构成一种所指繁复、意味深长的艺术效果,也因此诗句“密雨斜侵薜荔墙”具有多重意蕴。
事实上,在柳宗元的流寓文学创作中,许多化合意象图式的所指的繁复程度或“综合性”,远远超过薜荔意象,如渔父(钓翁)、炎州、幽泉、溪流等。《江雪》中的垂钓老翁可以这样定义:“冰天雪地在大江边独自垂钓的老人”,于是垂钓老翁可能具有这样几个映射点:不畏严寒,特立独行,不与俗人为伍,这些种差映射的可能是柳宗元剛毅坚韧的品性、高洁挺拔的人格、孤独寂寞的心境、孑然一身的处境。同样,《渔翁》《湘口馆潇湘二水所会》等作品中渔父或渔翁也有其多个映射对应物。很明显,渔翁多种差化合意象图式生动地展现了柳宗元的人格特征、身处炎方的处境及复杂流寓心理。同理,泉、幽泉、石渠、小溪等与水流相关的意象在柳宗元笔下另有新意——我们可以根据这些“表象”的种差概括出关键词或隐喻因子:隐僻、荒弃、遮蔽、清亮、清泠、幽深、幽静……这些隐喻因子所构成的能指,具有展示高尚人格精神、重申“利安元元”理想、倾诉贬谪郁闷凄苦等多种“意指功能”,承载了柳宗元复杂的流寓心理,表达了柳宗元特有的价值追求和独特的审美情趣。
多种差化合意象图式的生成,除开语境之外,最关键的是“表象”自身的“表现性”(阿恩海姆语),亦即“表象”或“属”是否具有多个种差,而某个“表象”是否具有多个种差,关联两个因素。一是叙事主体的认定,即主观的赋性赋形,例如,周敦颐认定“水芙蓉”品格高尚,但柳宗元认为木芙蓉更为高洁;至于同一“表象”,何时认定为单质,何时认定为多种差,皆由语境或叙事主体而定。二是“经验互动”的文化积累。例如,薜荔的“坚韧”“美洁”“孤野”、渔父或渔翁的“自由”“淡泊”等属性认定,是艺术历史沉淀和文人约定俗成的结果,而这种认定,是柳宗元化合隐喻构建的逻辑起点。
与典籍事迹化合意象图式比较,因为种差与种差之间的界线分明,义项的融汇度较低,所以多种差化合意象图式的映射过程相对简洁直观,但指向丰富,因而能够高效而直观地解析柳宗元特殊而复杂的流寓心理。
柳苏二人的多种差化合意象图式建构的主要差异,在于对于同一“表象”的赋性偏移,如单质与多种差的主观认定差异。例如,二人对“鹤”的赋性存在明显不同:在柳宗元诗文中,鹤在许多情况下被用为单质,而在苏轼的诗词创作中,鹤“表象”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显现出多种差特征。——在收录有限的“搜韵”数据库中,鹤在苏轼笔下出现146次,诗人对鹤“表象”的赋值赋性多种多样;在柳宗元笔下出现次数屈指可数,其隐喻主要指向高洁超凡。
前面所议苏柳二人在选码编码、“表象”的赋形赋性等方面的差异,在多种差化合意象图式建构范围内也存在,限于篇幅,略而不论。
研究柳宗元流寓文学创作的艺术编码意义重大,因为柳宗元的隐喻思维具有独特性,其意象图式构建拓展了源远流长的隐喻思维,还因为隐喻表达是柳宗元远祸全身的重要创作策略。
从本土传统文学批评角度看,本文尝试突破源远流长的意会感悟批评,力图在认知语言学、结构主义、符号学等层面揭示“主观之意”与“客观之象”的映射关联,从而考察柳宗元流寓文学创作的艺术编码,揭示其流寓心理的艺术化过程及特征。这一尝试具有挑战性,因为,笔者要同时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使用全新的工具考察柳宗元流寓文学创作的隐喻思维,二是揭示柳宗元流寓体验的外化方式方法及其特点。选题的挑战性可能致使拙文疏漏多多,因而笔者期待大家的批评。
注释:
(1) 张学松:《论中国古代流寓文学经典之产生机制——以苏轼、杜甫为中心》,《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2) 吴念阳:《隐喻的心理学研究》,上海百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17页。
(3)(9) 乔治·莱考夫:《女人、火与危险事物:范畴显示的心智》,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7年版,第17、95页。
(4) 王寅:《认知语言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71页。
(5) 王寅:《解读语言形成的认知过程——七论语言的体验性:详解基于体验的认知过程》,《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6) 弗里德里希·温格瑞尔、汉斯尤格·施密特:《认知语言学导论》,彭利贞、许国萍、赵微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94页。
(7)(12)(13)(14) 乔治·莱考夫、马克·约翰逊:《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何文忠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20、12、13页。
(8) 何谓“相对单纯”?——根据美国学者斯坦哈特的专著《隐喻的逻辑——可能世界之可类比部分》(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的论述,不存在仅有一个隐喻指向的隐喻逻辑结构,所以在此我们只能说“相对单纯”。
(10)(15)埃里克·查尔斯·斯坦哈特:《隐喻的逻辑——可能世界之可类比部分》,兰忠平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134、13页。
(11) 參见海南师范学院古籍研究室主编:《苏轼海南诗文选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16) 构建典籍事迹化合意象图式并不完全等同于简单机械地“用典”。
作者简介:周水涛,信阳学院中国流寓文化研究中心特聘教授,河南信阳,464000;张学松,信阳学院中国流寓文化研究中心特聘教授,河南信阳,464000。
(责任编辑 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