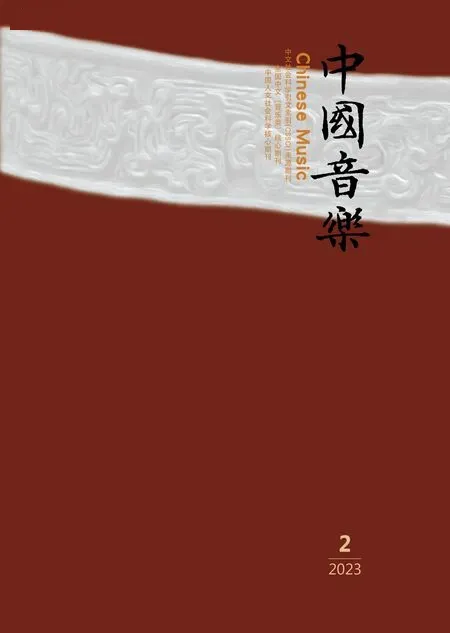“国家在场”视域下藏传佛教寺院的汉传伎乐供养
○孙云
在佛教文化的发展历史中,帝王赐予佛教领袖、僧官、高僧大德“伎乐供养”实为重要传统,从汉传佛教到藏传佛教皆有相关的文献记载,由于汉传与藏传不同的历史渊源,其伎乐供养也应该呈现出汉、藏不同的音乐形态特征。但是从当下的寺院遗存来看,藏传佛教寺院里却出现了“汉传音乐”,比如北京的雍和宫,五台山菩萨顶、镇海寺,甘肃的拉卜楞寺,青海的塔尔寺,西藏的楚布寺等皆有“笙、管、笛、唢呐的音乐供养”,如此现象,值得关注,但是目前涉及的相关研究并不多见。
田联韬《藏传佛教寺院的汉传佛教音乐》揭示出甘肃拉卜楞寺的道得尔音乐、青海塔尔寺的花架音乐、西藏楚布寺的甲瑞居楚乐、青海当卡寺的加若乐、北京雍和宫的佛乐皆为汉传音乐。①田联韬:《藏传佛教寺院的汉传佛教音乐》,《民族艺术研究》,2014年,第3期,第23–31页。
包·达尔汗《蒙古地区藏传佛教器乐“经箱乐”初释》②包·达尔汗:《蒙古地区藏传佛教器乐“经箱乐”初释》,《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第137–140页。,和佳庚、吴学源《中甸县藏传佛教音乐考查》③和佳庚、吴学源:《中甸县藏传佛教音乐考查》,《民族艺术研究》,1992年,第3期,第39–46页。分别针对蒙古、云南地区存在的藏传佛教寺院笙管笛音乐进行了分析研究,揭示出当地藏传佛教寺院里汉传笙管笛音乐的大量存在。格桑曲杰《西藏佛教寺院音乐中的汉地器乐形式—楚布寺甲瑞居楚乐(汉乐十六种)》指出:
甲瑞居楚乐所使用的乐器、演奏形式、音调风格等无不显出中原汉族器乐音乐的特点,体现出中原汉族地区佛教寺院吹打乐和民间鼓吹乐对楚布寺寺院宗教音乐的影响……而且体现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西藏噶玛噶举教派与明朝廷、清朝廷之间在历史上的特殊的宗教、政治关系和文化艺术方面的交往,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噶玛噶举教派形成与历史上政治、宗教关系沿革的缩影。④格桑曲杰:《西藏佛教寺院音乐中的汉地器乐形式—楚布寺甲瑞居楚乐(汉乐十六种)》,《西藏艺术研究》,2009年,第1期,第42–55页。
从既往研究可以看出,藏传佛教寺院里所存在的汉传音乐实为一种客观遗存,但是相关研究更多地关注了这一表象存在,对其背后产生的原因分析很少。格桑曲杰所分析的西藏与明清朝廷之间的政治、宗教关系带给我们重要启示。
藏传佛教寺院之所以会有汉传音乐的存在,不仅仅是汉藏文化的自然传播交流,而且是古代帝王对藏传佛教、番僧的礼遇优待相关,这种礼遇具有历史的传承性特征,上行下效,以皇帝为代表的“国家”与佛教建立一种稳固的“供施关系”,国家成为佛教最强有力的“檀越主”,皇寺、官寺、大寺成为国家法事活动实施的重要场域,佛教领袖、活佛、高僧大德一切供养皆为国家供给,这是当下藏传佛教寺院中存在汉传音乐供养的重要原因。
一、国家伎乐供养的历史渊源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用最美好的音乐奉献给佛、菩萨实为佛教之重要的供养传统,并且与中国古老的礼乐文化、祭祈文化融合发展,形成了具有佛教色彩的供养文化传统,供养的地点从皇寺、官寺拓展到佛教领袖、僧官驻锡地,供养对象也从佛、菩萨等诸神拓展至佛教领袖、僧官、高僧大德等。
(一)皇寺、官寺、大寺的国家供养
佛教传入初期,在伎乐供养还未被深入理解之时,“佛”就被当作神来祭祀,桓帝把佛教与黄老道同等奉祀,用郊天乐。《后汉书·祭祀志》:
桓帝即位十八年好神仙事,延熹八年,初使中常侍之陈国苦县祠老子;九年,亲祠老子于濯龙……设华盖之坐,用郊天乐也。⑤〔宋〕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188页。
至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发展迎来了第一个繁盛时期,“丝竹杂技皆有旨给”非常形象地揭示出当时寺院的供养情景。《洛阳伽蓝记》载:
石桥南道有景兴尼寺,亦阉官等所共立也……像出之日,常诏羽林一百人举此像,丝竹杂伎皆由旨给。⑥〔北魏〕杨衒之著,周振甫译注:《洛阳伽蓝记》,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63;101;31页。
景明寺,宣武皇帝所立也……四月七日京师诸像皆来此寺,尚书祠曹录像,凡有一千余躯,至八日节,以次入宣阳门,向阊阖宫前,受皇帝散花……梵乐法音,聒动天地,百戏腾骧,所在骈比。⑦〔北魏〕杨衒之著,周振甫译注:《洛阳伽蓝记》,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63;101;31页。
景乐寺,太傅清河文献王怿所立也,怿是孝文皇帝之子……至于大斋,常设女乐,歌声绕梁,舞袖徐转,丝管寥亮,谐妙入神……后汝南王悦复修之,悦是文献之弟,召诸音乐逞伎寺内。⑧〔北魏〕杨衒之著,周振甫译注:《洛阳伽蓝记》,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63;101;31页。
上述三所寺院的建立者分别为阉官、皇帝、皇子等,实为名副其实的官寺、皇寺,“丝竹杂伎皆有旨给”揭示出“国家在场”下伎乐供养的鲜活场景,隋唐亦是如此。
《法苑珠林》:“若是国家大寺,如似长安西明、慈恩等寺,除口分地外,别有敕赐田庄,所有供给并是国家供养,所以每年送盆献供种种杂物,及举盆音乐人等,并有送盆官人。”⑨苏渊雷、高振农选辑:《佛藏要籍选刊》(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481页。
《唐长安西明寺塔碑》:“遂赐田园百顷,净人百房,车五十两,绢布二千匹,征海内大德高僧……幡幢之阴,周四十里,伎乐之响,震三千界。”⑩苏頲:《唐长安西明寺塔碑》,载《全唐文》(卷二五七),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597页。
慈恩寺、西明寺分别是为追念皇太后以及太子病愈而设立,唐太宗与唐高宗敕令而建,是不折不扣的皇家寺院,玄奘先后充任两寺上座,不论是落成还是送寺碑都有专门的音乐供养,皆出自皇家与官府,彰显出“国家在场”的印记。
《册府元龟》载:“天成三年九月九日应圣节,召两街僧道谈经于崇元殿,宰相进寿酒,百官行香,修斋于相国寺,宣教坊乐及左右厢以宴乐之……乾祐三年三月丙午汉隐帝嘉庆节群臣入相国寺斋,赐教坊乐。”⑪〔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23–25页。
大相国寺是在北齐建国寺的基础上构建形成,712年唐睿宗为庆贺其由相王登基而赐名“大相国寺”,北宋时期,受到皇家尊崇,多次扩建,成为当时京城最大的寺院和佛教活动中心,祭祀求雨、帝后祝寿等国家大典甚为频繁。
至明代,皇家寺院主要集中在南京与北京,南京的灵谷寺、报恩寺、天界寺皆为皇家寺院,被誉为金陵三大佛寺。其中灵谷寺始建南朝梁天监十四年,元朝及明朝初年时被称作蒋山寺,自洪武元年至洪武五年,此地每年都会举行超度法会,敕太常谐协歌舞之节。
洪武五年壬子春,即蒋山寺建广荐法会,命四方名德沙门,先点校藏经,命宗泐撰《献佛乐章》。既成进呈,御署曲名,曰《善世》,曰《昭信》,曰《延慈》,曰《法喜》,曰《禅悦》,曰《遍应》,曰《妙济》,曰《善成》,凡八章。敕太常谐协歌舞之节,用之,着为定制。⑫〔明〕宋濂:《护法录卷五》,载《大藏经补编》(第28册),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118页。
上述文献中涉及的皇寺、官寺、大寺仅仅是历史长河中很少的一部分,帝王敕建的寺院还有很多,透过这些文献的描述,我们可以发现有很多国之大典皆在寺院举行,充分揭示出帝王信仰、国家意志、国家仪式在寺院这种特殊场域中的诉求,而典礼仪式中的伎乐供养实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民康老师指出:
由元明到清末,皇朝都城主要集中在北方地区,皇权、政权对僧权、寺权的影响很大,一定程度促进、保护了以携带乐器伴奏为显著特征的北派佛教声韵及佛教器乐的传承和发展……由于皇家寺院和宦官寺院遍布各地,其特殊的社会和阶层属性、结构组织和功能特征……寺院音乐传统乃至古代城市社会的整个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⑬杨民康:《论佛教丛林制度与佛教音乐风格区的相互关系》,《艺术百家》,2011年,第4期,第124–126页。
历经社会变迁,这些曾经被帝王恩宠过的寺院供养音乐多数仅留存在历史文献中,但也有一些传承到了今天,比如开封大相国寺,北京智化寺,五台山大菩萨顶、镇海寺,以及一些藏传佛教达赖喇嘛驻锡的寺院等等,无不彰显出国家在场下寺院作为国之大典场域的重要意义。
(二)佛教领袖、僧官、高僧大德的国家供养
佛告阿难:天下有四种人应起塔,香、花、缯盖、伎乐供养。何等为四?一者如来,应得起塔,二者辟支佛,三者声闻人,四者转轮王。阿难,此四种人应得起塔,香华缯盖伎乐供养。⑭〔后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译:《长阿含经》,载大正一切经刊行会《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第1页。
上述文献揭示出符合伎乐供养对象的四种标准,除了佛祖之外,还有修行级别较高证得果位之人(辟支佛、声闻人、转轮王)。类比,在中国的礼乐制度中也有这样的规定,从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皆有不同的用乐规定。因此,当佛教进入中国,伎乐供养和中国的礼乐制度融合发展,形成了佛教领袖、高僧大德、喇嘛活佛的伎乐供养传统。《广清凉传》载:
朔州大云寺惠云禅师,德行崇峻,明帝礼重,召请为此寺尚座。音乐一部,工技百人,箫笛箜篌,琵琶筝瑟,吹螺振鼓,百戏喧阗,舞袖云飞,歌梁尘起,随时供养,系日穷年。⑮〔宋〕延一:《广清凉传》,载大正一切经刊行会《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1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第1,101页。
《高僧传卷》第八记载:“是为明帝,仍敕瑾使为天下僧主,给法伎一部,亲信二十人,月给钱三万,冬夏四时赐并车舆吏力,凡诸外镇皆敕与。”⑯〔梁〕慧皎撰:《高僧传》,载大正一切经刊行会《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0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第322页。
上述文献是经常被引用的案例,是南北朝时期帝王敕赐高僧大德与僧官音乐供养的有力佐证,唐朝依然如此,高僧玄奘法师被迎请进慈恩寺,充任上座,帝王为其举行了盛大的典礼仪式,送僧、送佛像于寺内。《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七:
以玄奘为慈恩寺上座……十二月戊辰,又敕太常卿江夏王道宗将九部乐,万年令宋行质、长安令裴方彦各率县内音声,及诸寺幢帐,并使豫极庄严,己巳,旦集安福门街,迎像送僧入大慈恩寺……太常九部乐挟两边,二县音声继其后……中书褚令执香炉引入,安置殿内,奏九部乐、《破阵舞》及诸戏于庭前,讫而还。⑰〔唐〕慧立,彦悰:《玄奘传》,北京:东方出版社,2019年,第120页。
太常九部乐、二县音声、破阵舞,这些官方层面的音乐典礼仪式,既是对慈恩寺的国家供养,也是帝王对高僧玄奘的礼遇,与世俗之官品待遇有相通之处。《资治通鉴》记载:
胡僧不空,官至卿监,爵为国公,出入禁闼,势移权贵,京畿良田美利多归僧寺,敕天下无得棰曳僧尼,造金阁寺于五台山,忻州五台县有五台山,释氏相传以为文殊道场,铸铜涂金为瓦,所费钜亿。⑱〔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二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7,315页。
高僧不空官至卿监,爵为国公,在唐代,国公堪比郡王,位从一品,一品官员按照当时的制度均有相应的礼乐配备。《明集礼》载:
卤簿鼓吹,唐制一品二品丧备本品卤簿,五品以上灵车动,鼓吹振作而行,六品以下无鼓吹,宋制二品以上设卤簿鼓吹仪,三品止陈卤簿,无鼓吹。⑲〔明〕徐一夔等:《明集礼》,载《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45页。
三品以上有本品鼓吹彰显出官阶的不同,这是以制度的形式彰显的国家行为,不空虽是和尚,但官至国公,享用世俗官员的待遇,玄奘如此,不空如此,义净亦是如此,《宋高僧传》:
唐京兆大荐福寺义净传:经二十五年历三十余国,以天后证圣元年乙未仲夏还至河洛,得梵本经律论近四百部,合五十万颂,金刚座真容一铺,舍利三百粒。天后亲迎于上东门外,诸寺缁伍具幡盖歌乐前导。⑳〔宋〕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544页。
唐代高僧义净著有《南海寄归内法传》与《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并首传印度拼音之法,与鸠摩罗什、真谛、玄奘被称为四大译经家,武则天亲自接见,礼乐供养。
《宋高僧传·志通传》:“晋凤翔府法门寺志通传……以天福四年己亥岁,天王锡命于吴越,遂附海舰达浙中,时文穆王钱氏奉朝廷之故,具威仪乐部迎通入府庭供养,于真身塔寺安置,施赉丰腆。”㉑〔宋〕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544页。
如是观之,历代高僧在帝王的礼遇中,除了物质上的供养之外,音乐供养也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世俗的礼乐文化传统中来分析,他秉承了中国古老的礼乐制度,从帝王到诸侯士大夫都有相应的音乐与其官阶相匹配,而具体到寺院的高僧也是如此。如是,印度的伎乐供养传统与中国的礼乐文化制度相通相融,形成了高僧大德的伎乐供养传统。元代亦是如此,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
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至元十一年(1274),皇上专使召之……王公宰辅士庶离城一舍,结大香坛,设大净供,香华幢盖,大乐仙音,罗拜迎之。㉒〔元〕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21卷),载《大正藏》49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707页。
大乐仙音,罗拜迎之,元代番僧被奉为帝师,其接待规格甚至超过了王公贵族,音乐、仪仗若佛出世。张昱《辇下曲》:
驼装序入日精门,铜鼓牙旗作队喧。一听巡阶铃钹振,满宫俱喜出迎恩。华缨孔帽诸番队,前导伶官戏竹高……组铃扇鼓诸天乐,知在龙宫第几重。㉓〔元〕柯九思等:《辽金元宫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3页。
元代如此,明清亦是如此,对高僧大德、喇嘛的优待具有传承性,清代诗人查慎行:“西僧迎辇列香幡,击鼓吹螺动法门,香界从来知佛大,而今更识帝王尊。”㉔任月海编译:《多伦文史资料》(第1-4辑合编),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87页。
综上所述,从国家供养的对象来看,一是体现在皇寺、官寺、大寺中国之大典的伎乐供养;二是体现在对现实世界中僧官、高僧大德的伎乐供养。说到根本,还是表现为对佛、法、僧的尊重、礼遇,希冀通过这种虔诚的供养方式,获得佛祖、高僧的加持,获得一种潜在的“功德”,供养越多,功德越大,加持力就越强。佛教所特有的“供养与护佑成正比”的供养价值观吸引着皇权的拥有者,供养音乐成为被赋予了非常意义的“神权音乐”,这是其世代传承的根本动因,也是当下北方寺院中有大量笙管笛音乐传习的根本原因。汉传寺院如此,藏传寺院亦是如此。
二、藏传佛教寺院汉传音乐供养
甲林是汉地唢呐的藏式发展,藏传佛教寺院虽然较多,但是有“甲林”和“笙管笛”音乐供养者并不多见,有“甲林”供养的寺院不一定有“笙管笛”音乐,反之,有“笙管笛”音乐者则一般都有“甲林”,分开厘清,其中原因更为清晰。
(一)藏传佛教寺院的“甲林”供养
何为甲林?格桑曲杰在《独具特色的西藏佛教旋律乐器甲林和铜钦》一文中指出:
“甲林”的“甲”字在藏语中泛指中国藏区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具体也指中国内地、印度、俄罗斯等,甲林的甲字在西藏普遍理解为中国内地。“林”是藏语林普的缩略,意为笛子……在西藏的有些寺院中(如桑耶寺等),在神舞羌姆中迎请诸神出场时甲林的演奏乐僧……显示出清军中乐的唢呐与西藏寺院乐器甲林之间的某种渊源关系……甲林是中国内地唢呐传入中国西藏后的变体更确切一些。㉕格桑曲杰:《独具特色的西藏佛教旋律乐器甲林和铜钦》,《西藏艺术研究》,2006年,第4期,第36–37页。
西藏是多元文化的交界处,藏传佛教也是从中亚与汉地先后传入,受到毗邻地区文化的影响实为必然,但是,从格桑曲杰的研究以及当地的惯称来分析,“甲林”受到内地的影响更大,是汉地唢呐进入西藏之后的变体,只是外面增加了很多装饰性的东西而已,在藏传佛教中达赖、班禅、宗喀巴、呼图克图、三大法王等驻锡地的寺院实为一种普遍性的存在。
表1罗列了西藏、甘肃、青海、内蒙古、辽宁、北京、山西等地存在“甲林”供养的部分藏传佛教寺院,涵盖了四大活佛以及三大法王㉖大乘法王萨迦派贡噶扎西;大慈法王格鲁派释迦也失;大宝法王噶举派得银协巴。的驻锡地。藏传佛教的第一座寺院桑耶寺,格鲁派的祖寺甘丹寺,噶玛噶举的主寺楚布寺,宗喀巴大师的诞生地塔尔寺,多伦诺尔会盟之地汇宗寺,帝王行宫雍和宫等等,这些寺院并非一般的寺院,皆与皇家、官府有关,实为官方典礼音乐的敕赐、效法与接延。究其主要原因,是藏族政教合一的历史制度及帝王对于藏传佛教领袖的“尊崇”所致。

表1 甲林音乐供养的部分藏传佛教寺院

表2 藏传佛教寺院中的汉传音乐一览表(部分)
元朝帝王独宠萨迦派,明代多封众建,“来者皆授官”。清代承继元明,尤礼格鲁派,四大活佛分而治之,换言之,这些寺院的教主、活佛、领袖基本上都是元明清帝王所册封,其本质是“僧官”,身份尊贵。政教合一的身份使他们既有世俗政权的官员身份,也有宗教领袖的身份,因此世俗社会的典礼仪式所使用的卤簿鼓吹、仪仗也被拿来应用,当然这种“拿来主义”既有帝王敕赐,也有的是主动地效法所致。《元史·释老传》云:
元起朔方,固已崇尚释教……于是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于西土。百年之间,朝廷所以敬礼而尊信之者,无所不用其至。虽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为之膜拜……正衙朝会,百官班列,而帝师亦或专席于坐隅……帝师比至京师,则敕大府假法驾半仗,以为前导。㉗〔明〕宋濂等:《元史·释老传》,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4,520–4,521页。
“帝师”配享“天子法驾半仗”,可见之优渥尊崇,这种迎请方式无疑成为其后寺院效法的基础,明代亦是如此,《皇明十六朝广汇记》:
永乐五年,三月封西僧哈立麻……领天下释教,赐金百两,银千两,彩币宝钞,织金珠袈裟,金银器皿,鞍马赐仪仗与郡王同。㉘〔明〕陈建辑:《皇明十六朝广汇记》,明崇祯刻本,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第224页。
赐仪仗与郡王同,从另一个层面揭示出,番僧领袖本身已经享有了世俗高官的品级与待遇,政教合一使他们成为一种特权阶层,其仪仗、伎乐供养、前呼后拥成为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与上述文献互为佐证,详细地罗列了当时永乐皇帝赐予的仪仗及其物品:
赐尚师哈立麻仪仗、牙仗二、瓜二、骨朵二、幡幢二十四对、香合儿、拂子二、手护三对、红纱灯笼二、骨灯二、伞一。㉙多吉才旦主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一册),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第97页。
张昱《辇下曲》:
驼装序入日精门,铜鼓牙旗作队喧。一听巡阶铃钹振,满宫俱喜出迎恩。华缨孔帽诸番队,前导伶官戏竹高……组铃扇鼓诸天乐,知在龙宫第几重。㉚〔元〕柯九思等:《辽金元宫词》,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3页。
凡是被帝王敕赐的国师、帝师皆配备仪仗、幡幢、伞,番僧的盛宠,遭到大臣反弹。《明宪宗实录》梁本卷58:
陛下崇信异教,每遇生愍之辰,辄重糜资财,广建斋醮。而西僧札实巴等,至加法王诸号,赐予骈蕃。出乘棕舆,导用金吾仗,缙绅避道,奉养过于亲王,乞革夺名号,遣还其国,追录横赐,用振饥民。仍敕寺观,永不得再讲斋醮……今朝廷宠遇番僧,有佛子、国师、法王名号,仪卫过于王侯,服玩拟于供御,锦衣玉食。㉛《明实录宪宗实录》,载顾祖成等汇编:《明实录藏族史料集·二》,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68页。
上述记载是明朝大臣魏元与康永韶等人的谏言,魏元时任“六科给事中”;康永韶则为“十三道监察御史”,两人皆属于谏言、监察官职,如此进谏,从另外一个层面也反映出当时对番僧的优待。
清代诗人查慎行:“西僧迎辇列香幡,击鼓吹螺动法门,香界从来知佛大,而今更识帝王尊。”㉜同注㉔。
由于蒙藏地区政教合一的特性,历代帝王为了更好地怀柔蒙藏地区,对其宗教领袖给与大力册封,从政治上确立君臣关系,但又不同于内地普通意义上的君臣,而是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君臣,不论是在物质上、在精神上,还是在外在的典礼仪式、仪仗卤簿都是如此。“奉养过于亲王、仪卫过于王侯。”恰恰彰显出帝王对于宗教领袖不仅仅是在宗教领域内的敕赐,而且在世俗社会内让他们享受到了政治首领待遇,这种高规格的封赏会代际传承、被效法,直至今天,我们依然可以从各地藏传佛教活佛、班禅迎请的仪仗中感受到文献中描述的情状,逆向考察,恰恰也是对历史场景的补白,西藏布达拉宫管理处边巴琼达指出:
一方面西藏的仪仗吸收借鉴了很多中原地区的习俗,甚至有些器具都是直接从中原地区赏赐或借鉴过来的,形式上与中原地区有不少相似之处。另一方面,西藏地方在借鉴中原仪仗习俗的同时,也将其不断的本土化,反映出自身的特点。特别是随着西藏地方政教合一制度的逐步建立,仪仗形式与中原地区的最大区别,一是在仪仗队伍组成人员以僧人为主,二是仪仗中增加了相当多的藏传佛教法器,体现了更多的宗教元素。㉝边巴琼达:《清代西藏地方仪仗浅析—以布达拉宫馆藏仪仗为例》,《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41页。
仪仗队伍中除了传统的华盖、旗、法器之外,“甲林”藏式唢呐的进入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事情。据格桑曲杰老师研究,甲林大约是在明清时期传至藏传佛教寺院,那么这与内地“鼓吹”逐渐运用到宗教仪式紧密相关,清顾炎武《日知录》:
鼓吹,军中之乐也,非统军之官不用,今则文官用之,士庶用之,僧道用之,金革之气,遍于国中。㉞〔清〕顾炎武著,〔清〕黄汝成集释,秦克诚点校:《日知录集释》,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第168–169页。
明清时期,唢呐逐渐流行起来,并逐渐成为“卤簿鼓吹”的组成部分,《清史稿》载:
太宗崇德元年,备大驾卤簿……锣二,鼓二,画角四,箫二,笙二,架鼓四,横笛二,龙头横笛二,檀板二,小铜钹四,小铜锣二,大铜锣四,云锣二,锁呐四。世祖入关,一仍旧制。㉟〔民国〕赵尔巽:《清史稿》卷一〇五志八十。
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喇嘛打鬼》:
初八日弘仁寺打鬼,其制:以长教喇嘛披黄锦衣乘车持钵,诸侍从各执仪仗法器拥护……前以鼓吹导引,众番僧执曲锤柄鼓,鸣锣吹角,演念经文。㊱〔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8–9页。
“鼓吹”进入到藏传佛事活动中,唢呐又进入到鼓吹的乐队编制中,它与铜钦的组合是明清时期卤簿鼓吹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这其中的某些寺院不仅仅有“甲林”的迎来送往供养,而且亦融入了汉传“笙管笛”音乐。
(二)藏传佛教寺院的“笙管笛”音乐供养
格桑曲杰《西藏佛教寺院音乐中的汉地器乐形式—楚布寺甲瑞居楚乐(汉乐十六种)》,㊲同注④。田联韬《藏传佛教寺院的汉传佛教音乐》㊳同注①。,包·达尔汗《蒙古地区藏传佛教器乐“经箱乐”初释》㊴同注②。,和佳庚、吴学源《中甸县藏传佛教音乐考查》㊵同注③。分别针对西藏、内蒙、云南、蒙古地区存在的藏传佛教寺院笙管笛音乐进行了分析研究,揭示出当地藏传佛教寺院里汉传笙管笛音乐的大量存在。田联韬指出:
甘肃夏河县拉卜楞寺的“道得儿”音乐、青海西宁市湟中县塔尔寺的“花架音乐”;在康方言区,有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当卡寺的“加若音乐”(译意为“汉地音乐”)。据西藏音乐家格曲调查,在卫藏方言区,有西藏堆龙德庆县楚布寺的“甲瑞居楚乐”(译意为“汉地十六乐”)。此外,在藏传佛教寺院北京雍和宫也保存和使用着汉传佛教使用的乐器与仪式乐曲《佛乐》。㊶同注①,第24页。
楚布寺是噶玛噶举教派的主寺,是大宝法王得银协巴和历代噶玛巴活佛的驻锡地,也是活佛转世制度的发源地;塔尔寺是阿嘉呼图克图驻锡地,从这个寺院里诞生了很多的驻京呼图克图,是喀巴大师诞生地,也是格鲁派6大寺之一;拉卜楞寺是嘉木样呼图克图的驻锡地,是甘南地区的政教中心,也是格鲁派6大寺院之一。瑞应寺桑丹桑布·呼图克图,素有“东藏”之称。当然还有云南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松赞林寺、北京的雍和宫、山西的五台山,这些全国乃至世界著名的寺院里都有汉传笙管笛音乐的供养。格桑曲杰针对楚布寺甲瑞居楚乐(汉乐十六种)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研究:
据楚布寺乐僧和已过世的西藏社科院副研究员楚布寺16世噶玛巴瑞贝多吉活佛秘书仁青巴桑介绍,楚布寺的甲瑞乐器是噶玛巴黑帽系二世活佛噶玛拔希、四世活佛乳必多吉、尤其是五世活佛得银协巴时期从内地带进来的,并逐渐形成了甲瑞乐。㊺同注④,第45页。
时至今日,楚布寺金刚舞仪式中依然有笙、管、笛演奏,演奏者皆穿明代官服,以纪念五世噶玛巴被明代永乐皇帝接见的情景。楚布寺僧人加央次仁说:
五世噶玛巴(得银协巴)当年进京,受到明代永乐皇帝的接见,仪式很隆重,为了纪念这段历史,十四世噶玛巴把明朝的服饰以及明朝大臣们的形象作为角色编进了噶玛噶举神舞表演里。㊻CCTV-4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走进西藏寺庙·楚布寺》,https://www.iqiyi.com/w_19rsk3puyl.html2014-09-13。

图1 楚布寺僧人在神舞仪式上演奏竹笛(CCTV-4报道)
楚布寺僧人加央次仁所言应为实情。至今在寺里依然保存有明太祖朱元璋与明成祖朱棣的两道诏书,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明朝皇帝赐给西藏楚布寺噶玛活佛的两件诏书》有详细的研究。㊼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明朝皇帝赐给西藏楚布寺噶玛活佛的两件诏书》,《文物》,1981年,第11期,第42–44页。楚布寺的五世活佛得银协巴是被明王朝册封的第一个大宝法王,楚布寺的僧人阿多说:
神舞礼的汉族乐器,明朝时期只在很隆重的时候场合演奏,后来明朝皇帝作为礼物赏赐给了五世噶玛巴,这些乐器的演奏方法都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每三年我们都会选拔演奏技艺优秀的僧人,他们把技艺传授给其他僧人。㊽CCTV-4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走进西藏寺庙·楚布寺》,https://www.iqiyi.com/w_19rsk3puyl.html2014-09-13。
噶玛噶举三世活佛攘炯多吉、噶玛巴第四世活佛乳必多吉、噶玛巴第五世活佛得银协巴皆有被明代帝王召见进京的历史,尤其是得银协巴被封为大宝法王,这样特殊的经历使得楚布寺从京师带回了笙、管、笛、唢呐音乐。
楚布寺是噶玛噶举的主寺,而在距离比较遥远的青海省玉树自治州“当卡寺”也是噶玛噶举教派的寺院,其中的“加若”音乐不论是从僧人的穿着(清代官服样服装),还是从音乐的名称无不彰显出对主寺楚布寺的传承,田联韬先生已有专门的研究。㊾同注①,第30–31页。而对于云南香格里拉地区的汉传音乐究竟是不是与楚布寺也有关系,格桑曲杰做过专门研究,指出楚布寺的九世活佛旺曲多吉与第十世活佛与云南吐司联系紧密:
第九世活佛旺曲多吉(公元1556—1603)还与云南丽江纳西族的木氏土司进一步加强了联系,噶玛噶举教法在云南丽江为中心的周边地区急速传播,黑帽系第十世活佛却英多吉(公元1604—1674)所处的时期是西藏历史上噶玛噶举教派和新兴的格鲁教派为争夺西藏的政教大权而剧烈角逐的时期……格鲁派在蒙古和硕特部固始汗的支持下击溃了后藏王政权藏巴第斯,取得了绝对的胜利,却英多吉从拉萨逃出来后,最后逃到云南纳西族木氏土司家中……噶玛噶举教派至今在云南丽江、中甸、德庆等地有很大的影响,在这一片地区有为数众多的藏传佛教寺院,其中有不少为噶玛噶举教派的寺院。㊿
这是噶玛噶举教派向云南传播的重要文献,也是上述香格里拉地区噶丹·松赞林寺具有笙管笛音乐的重要原因之一。云南、四川由于地理位置上与西藏距离较近,加之历史上忽必烈远征云南,必然将藏传佛教传播到云南,导致在三省交界处都有藏传佛教的传播。而云南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是噶丹·松赞林寺,其建立、扩建都与达赖政权紧密相关,其寺名源于五世达赖喇嘛亲赐,并且与七世达赖剌嘛格桑嘉措避难有一段法缘,享有“小布达拉宫”的美誉,这种独特的历史与其有笙管笛音乐的存在重要关联。
五台山与拉卜楞寺亦是如此。五台山是中国唯一一座汉藏并存的佛教名山,汉传佛教寺院与藏传佛教寺院毗邻传承,并且藏传佛教的寺院是从汉传佛教寺院改建而来。从北魏孝文帝算起,历代帝王都大力支持五台山佛教的发展,“割八州之税”进行供养,当然不止有物质的供养,还有“音乐工技”随时供养。换言之,五台山寺院里之所以存在大量的“笙管笛”音乐,恰恰是因为“皇家尊崇”所致。唐代成为“国山”,文殊信仰传遍国内外,当然也会传播到西藏、敦煌、韩国、日本等地。元明清时期成为皇家道场,藏传佛教在五台山得到了迅速的传播,顺治十三年,菩萨顶被改为喇嘛庙,敕命“大殿覆琉璃黄瓦”皇家规格,既是帝王行宫,也是皇家道场。康熙四十四年又将十大青庙改为黄庙,青庙和尚就地变为黄庙的喇嘛,五台山汉、藏佛教出现了戏剧性的交融发展,汉传佛教音乐也在藏传佛教寺院里传承。康熙与乾隆先后11次前往礼拜,实为帝王行宫与皇家道场,每年皆有“奉旨道场”,既有与其他藏传佛教寺院相同的藏式法器,也有汉传的笙、管、笛、唢呐乐器,藏式唢呐(甲林)主要用于大喇嘛出行时的仪仗,“笙管笛”主要是用于“上师供养”仪式以及“跳布扎”巡行时的演奏。
通过这种历史的分析可以发现,凡是存在笙管笛音乐传承的寺院几乎都与帝王、皇家、官府、宗教领袖相关联,只不过有的是直接,有的是间接而已。王云峰《活佛的世界》:
生于1728年的第二世嘉木样晋美旺布,以清明能干、博学多才闻名藏传佛教界……31岁被西藏地方政府授予“具善明教班智达诺门罕”的敕印,并赠送堪布服饰、伞盖、乐器等全套用具。1759年返回拉卜楞寺后……担任本寺总法台的同时,又先后兼任青海塔尔寺、佑宁寺等寺的法台。1768年,他接受青海乌都斯王的敦请,赴东蒙49旗讲经传法。之后取道前往北京,会晤了清朝大国师章嘉呼图克图。1772年返回拉卜楞寺后,被乾隆皇帝封为“扶法禅师班智达额尔德尼诺门罕呼图克图”的称号。51王云峰:《活佛的世界 金席大师贡唐仓·丹贝旺旭传》,北京: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13页。
二世嘉木样活佛受到西藏政府的嘉奖,配备伞盖、乐器等全套用具,并且受到乾隆敕封,这些无疑为拉卜楞寺汉传音乐的引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拉卜楞寺概况》载∶
四世嘉木样活佛-嘉木样,噶藏图旦旺徐四十三岁时,赴山西朝礼五台山,又去北京朝拜雍和宫,朝觐光绪皇帝。返回途中,经内蒙古地区,广传佛法,每日前来顶礼的僧俗达万人之多,一八九九年返回拉卜楞寺。52杨贵明、马吉祥编译:《藏传佛教高僧传略》,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15页。
二世嘉木样活佛与四世嘉木样活佛皆有去北京、五台山传法的经历,效法其中的笙管笛音乐,并将其传入,才传承了如此之多的汉传音乐,田联韬、53同注①,第24;27页。银卓玛54银卓玛:《拉卜楞寺“道得尔”与五台山佛乐的比较研究—以拉卜楞寺〈色和〉与殊像寺【万年欢】佛曲为例》,《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第65–79页。都有相关研究并做出详细的比较分析,揭示出拉卜楞寺道得尔音乐与五台山佛教音乐的一致性存在。
塔尔寺的花架音乐源于何处?田联韬分析:“可能也与山西五台山寺院音乐有关。”55同注①,第24;27页。都本玲指出塔尔寺花架音乐是酥油花的“灵魂伴侣”56都本玲:《塔尔寺花架音乐:酥油花的“灵魂伴侣”》,《中国民族报》,2020年7月14日,第8版。,但两者都没有揭示其音乐的真正来源,笔者认为这与塔尔寺的高僧、活佛领袖有关,与10位驻京呼图克图有关。清西宁县令靳昂《塔尔寺观灯二十四韵》:
寺在湟郡西南五十里。四山环迎,殿宇宏丽。住持番僧三千余众,为前、后藏总汇之所。岁于上元日,抟五色酥油作佛像、楼阁、花鸟、虫鱼,炳耀陆离,备极工巧。层累寻丈,矗若锦屏。下列铜盏酥油灯,参差星布。屏凡二十四,灯以万计。笳鼓动地,幡幢幕天。外藩蒙古及番汉顶礼,有不远数千里来者。附近游人、商贾,蜂屯蚁集。57邓承伟:《西宁府续志·艺文志》,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84页。
《西宁府续志·志余》:
西宁府属各寺院,每岁元宵节,皆燃酥油花灯。其中灯最多而花样最奇者,莫若塔尔寺酥油灯。其花样年年改变,所不变者,惟左右较大之佛像耳。每于一定地点搭彩棚两处,上悬玻璃灯数十对,旁列花架数层,所有庙宇、宫殿、花卉、人物,皆以酥油制成……架前燃铜灯百千万盏,光辉相映,笙箫和鸣,远近观者,人如山海。58邓承伟:《西宁府续志·志余》,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09页。
上述两条文献出自《西宁府续志·文艺志》和《西宁府续志·志余》,此续志是西宁府知府邓承伟于清光绪三年组织编撰的,主要记载的是乾隆十三年(1748)到光绪四年(1878)的事情,其《志余》是解放后基生兰补纂的,主要辑录的是光绪五年(1879)到1928年之间的事情。换言之,《西宁府续志·文艺志》的“笳鼓动地”和《西宁府续志·志余》中的“笙箫和鸣”应该是在清朝就已成为惯例,其花架音乐已经存在。作为青海省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它连接内地与西藏,不仅是宗喀巴的诞生地,而且也是班禅、达赖的行宫,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寺庙诞生了10位驻京呼图克图(见表3),即清代帝王钦点的管理蒙藏佛教事务的驻京喇嘛。

表3 塔尔寺喇嘛担任“驻京呼图克图”一览表
根据清朝《钦定理藩部则例》记载:“章嘉呼图克图、噶勒丹锡哷图呼图克图、敏珠尔呼图克图、济咙呼图克图、那木喀呼图克图、阿嘉呼图克图、喇果呼图克图、察罕达尔汗呼图克图历世驻京掌印,以上八人并情愿呈请驻京之呼图克图等,均于转世后来京瞻仰天颜之日,裁撤呼弼勒罕字样。”59张荣铮等编:《钦定理藩部则例》,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94页。在驻京的八大呼图克图中,有五大活佛系统来自于青海,而五大活佛系统中又有三大活佛系统阿嘉呼图克图、喇果呼图克图、噶勒丹锡呼图呼图克图是来自于塔尔寺。这足以看得出塔尔寺在驻京喇嘛中的重要性。
《蒙藏佛教史》载:“全蒙藏之呼图克图,有百五十八名之多。呼图克图所驻锡之寺院,朝廷待遇极隆。”60妙舟法师编:《蒙藏佛教史》(下册),上海:佛学书局,1935年,第6篇第1章。
在从1719年第一个驻京喇嘛二世拉果·喜饶群觉入京开始到五世拉果·罗桑曲觉嘉措1904年返回西宁长达185年的时间内,塔尔寺与北京的文化交流非常频繁丰富,活佛们得到的待遇之丰厚不仅仅体现在物质上,而且其相应的仪仗音乐固不可少,从当下遗存的音乐可窥一斑,这是历史地位所决定。
至于北京的雍和宫为什么有如此之多的音乐,皆因为它是两代帝王的龙潜之地,也是三世章嘉活佛的驻锡地,清政府掌管全国藏传佛教事务的中心,更是历代班禅的驻锡地,尊贵至高无上,历代传承有笙管笛音乐也就不足为奇了。
综上所述,将藏传佛教寺院中存在“笙管笛唢呐云锣”供养的寺院进行梳理就会发现,这些寺院一般皆有官封活佛、喇嘛的历史,要么是皇寺、官寺,要么是帝王敕封、敕建,是集政治权利与宗教特权于一体的政教合一的高规格寺院,其宗教领袖即享有国家官员封赏,备有仪仗、卤簿鼓吹,又享用宗教教主的伎乐供养,因此,才有了笙管笛唢呐音乐的传承。
元明清三代,朝廷对番僧的封赏达到极致,三大法王、四大活佛以及众多的驻京呼图克图实质上是国家委任的僧官,僧官也是官,帝王敕封,有品有秩,衣饰伞盖仪仗不一,除了享有世俗官员的待遇之外,还享有佛教首领的特权,喇嘛活佛直接是藏区政教合一的领袖,不仅拥有一般的随侍,而且配备有专门的仪仗鼓吹,待遇堪比王侯将相。这种双重的配享是笙管笛唢呐音乐在寺院留存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