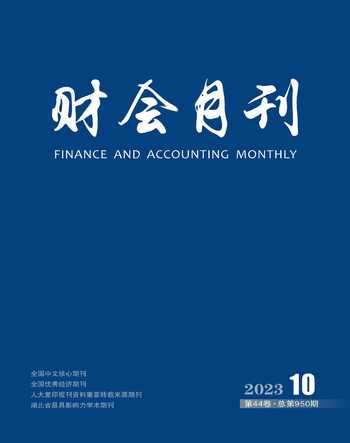全面注册制下的IPO发行:更易或者更难
黄悦昕 罗党论 张思宇



【摘要】随着全面注册制的落地, 我国资本市场迈入新阶段。在全面注册制下, 企业的IPO发行究竟更易还是更难?本文以2004 ~ 2022年我国资本市场IPO项目为样本, 重点研究自注册制试点以来的IPO发行情况。研究发现: 自注册制试点以来, IPO项目的终止数量在上升, 过会率则持续下降, 注册生效时间也在不断拉长, 这些发现似乎与国家推行全面注册制的初衷相悖; 进一步分析后认为, 注册制压实了IPO发行中各个主体的风险与责任, 对IPO项目进行了质量严控, 使得“有问题”的IPO项目发行更难, 但并不影响高质量IPO项目的发行效率; 并且, 响应国家产业政策的IPO项目的发行效率得到进一步提高。在此研究基础上, 本文从政府、中介机构和企业的角度对全面注册制的推进提出相应建议。
【关键词】全面注册制;IPO;过会率;终止数量;注册生效时间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23)10-0132-8
一、 引言
2023年2月, 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正式启动①。从2013年党的第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起, 我国资本市场对注册制的讨论和探索已历经10年。此后经过4年多的注册制试点, 到如今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正式落地, 一场牵动资本市场全局的里程碑式变革, 已然拉开大幕。
新股发行制度是证券市场的基础制度之一, 对于发行上市公司质量、 价格的形成与稳定、 资源配置起到决定性作用。那么, 在全面注册制下, 新股发行有没有更加市场化?值得关注的是, 深交所于3月18日终止了对芯微电子创业板IPO的审核, 若不考虑全面注册制下未平移也未获得批文的主板IPO项目, 这是2023年以来第58家主动撤单的拟上市企业。另外, 还有5家拟上市企业上会被否, 共计63家公司IPO终止, 同比增长16.67%②。这不禁令人疑惑, 在全面注册制下, IPO发行为何愈发困难重重?
那么, 在实行全面注册制的情况下, IPO发行表现与之前相比有何区别?现在企业的IPO发行是变得更难了还是变得更容易?当前的改革还存在哪些薄弱环节有待改善?
本文通过梳理我国上市制度的变迁, 对2004 ~ 2022年我国资本市场的5367个IPO项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发现: 自注册制试点以来, IPO项目的终止数量在上升, 过会率持续下降, 注册生效时间也在不断拉长, 这些发现似乎与国家推行全面注册制的初衷相悖; 进一步分析认为, 注册制压实了IPO发行中各个主体的风险与责任, 对IPO项目进行了质量严控, 使得“有问题”的IPO项目发行更难, 但并不影响高质量IPO项目的发行效率, 国家产业政策越支持的IPO项目发行效率越高。这比较好地解释了全面注册制下IPO项目的发行效率问题, 总体来说, 全面注册制还是提高了IPO发行的质量。
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 第一, 结合注册制试点的总体发行情况, 解释了注册制试点下的“悖论”, 从而丰富了注册制改革的相关研究成果; 第二, 针对注册制下的悖论问题, 从政府、 中介机构和企业三个方面提出建议, 为改善资本市场环境提供了有益参考。
二、 IPO发行: 中国的制度变迁
综观全球股票市场, 每一种股票发行制度都与其所在国家或地区的政治格局、 社会经济状况、 体制模式、 经济环境、 监管力度以及法律法规相适应。我国证券市场已走过将近40年的历程, 其股票发行制度大体经历过审批制、 核准制、 注册制三大阶段(如表1所示)。其中, 注册制自2013年11月在党的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首次提出以来, 经过10年的推行和试点, 其发展历程备受瞩目、 意义重大。
我国股票发行制度的历次改革, 其动因均是克服现行制度的弊端。围绕着以市场為导向还是以政府监管为导向, 学术界在资本市场改革的路径选择上存在诸多讨论, 注册制也频频被拿来与核准制, 甚至与早已尘封的审批制相比较(鲁桂华,2019)。
表2对三种股票发行制度的特征进行了梳理。可以看出, 审批制的特点是政府主管部门对发行规模、 数量和节奏进行严格控制, 行政控制的特征突出。彼时, IPO发行制度逐步市场化是大势所趋, 由此诞生了核准制。但核准制下企业IPO发行也存在如下四大问题。第一, 上市条件严苛。企业需要经过漫长的培育才能符合既定的连续盈利、 资产规模和销售收入标准(田利辉,2010)。第二, 上市审核进程缓慢。核准制下新股发行政策不连续, IPO间歇性暂停, 使得企业上市进程停滞(宋顺林和辛清泉,2017)。第三, 上市成本高昂。核准制下公司能否成功上市基本上取决于政府的“隐性担保”和“显性背书”, 不少企业更愿意为“抱病通关”投入巨额的行政开支和公关费用(杜兴强等,2013), 总体上不具有对高质量审计的内在需求。第四, IPO定价效率低下。由于核准制下新股发行数量和节奏被严格控制, 导致发行市场严重供不应求, 高市盈率、 高发行价、 高超募资金等问题更加严重(张劲帆等,2020)。不难发现, 行政控制的问题在审批制和核准制下都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即在这两种制度下, 证券发行上市不再是一种纯粹的市场行为, 而是一种行政控制下的市场行为(邢会强,2019)。这显然有违自由市场的原理。
注册制则以信息披露为核心, 强调市场化, 由投资者自主进行价值判断, 真正把选择权交给市场(胡志强和王雅格,2021)。注册制下三大发行特征, 即股票的发行资格、 发行价格、 发行规模及节奏, 均由市场决定。例如, 美国实行的双重注册制(Dual Registration), 便是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United State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SEC)负责甄别企业披露的信息并有针对性地开展部分实质审核; 州层面则强调实质监管。无独有偶, 日本的“双系统监管”, 由金融厅负责企业公募发行注册审查, 证券交易所、 证券业协会经授权进行上市审查; 金融厅下属的证券交易监视委员会负责监管市场交易、 信息披露等行为。注册制要求主承销商和发行公司将发行申请材料按照规定报送证券监管部门备案。后者只对发行人提供的申报注册的登记文件进行形式审核, 即只审核登记文件所公开信息的完整性、 准确性和全面性, 其真实性和充分性仍由发行公司、 主承销商和会计师事务所保证。这就使得注册制很大程度上弱化了证券监管机构的行政约束和人为控制作用。若企业本身不为市场投资者所认可和接受, 即便通过了证券监管机构的发行注册, 也无法成功发行, 后续的交易等亦是化为乌有。如此环环相扣, 使得注册制下的IPO发行对资本市场的整体性影响深远。
针对资本市场现存的问题, 全面注册制可能具有如下发行优势:
第一, 規范上市条件。注册制设置了包含市值、 营业收入和研发投入的组合上市条件, 且对红筹企业和同股不同权企业单独设置上市标准, 极大地降低了核准制的硬性要求。第二, 缩短企业上市进程。注册制允许未盈利企业上市, 大大节约了企业上市时间; 同时又专注于提高审核效率, 以增加上市进程的可预期性。第三, 降低企业上市成本。注册制从优化市场资源配置的角度出发, 缓解了因行政干预而加剧的“壳资源”问题(屈源育等,2018), 降低了企业上市负担。第四, 提高新股定价效率并提升信息披露质量(赖黎等,2022;俞红海等,2022)。
总而言之, 全面注册制的初衷在于补偏救弊, 一革审批制和核准制的瑕玷, 使得企业IPO发行更加畅通。注册制的推行因而备受期待, 其在IPO发行环节的表现更是万众瞩目。
三、 注册制下的IPO发行“悖论”: 更易抑或更难
注册制的发行市场化, 有赖于坚实的政治基础、 发达的资本市场、 高效的监管部门、 完善的信息披露、 专业化的中介机构以及必要的严刑峻法。但正如逾淮之橘, 注册制在有别于西方自由主义经济主张和小政府传统的中国环境中, 产生的效果亦是截然不同的。已有观点指出, 注册制并未提高新股发行定价效率(董秀良等,2020), 且对具有科创属性的企业要求过高, 甚至可能对上市企业的发行价格或者风险投资的减持退出价格产生不利影响, 造成风险投资亏损(彭涛等,2023)。在全面注册制下, IPO发行环节的表现孰优孰劣, 值得深究。为此, 本文收集2004 ~ 2022年我国资本市场IPO项目, 从项目终止数量、 上市概率以及注册生效时长三个方面刻画注册制下的IPO发行现象。
1. 注册制下的项目终止数量有显著提升。项目终止数量能直观地反映资本市场IPO发行的终止状态。注册制通过放松行政限制的股票供给和取消市盈率倍数上限的发行价格约束③, 在资本市场设置更加多元包容的上市条件。注册制既允许符合条件的特殊股权结构企业和红筹架构企业上市, 又积极推进询价机制和定价流程与成熟市场接轨(吴锡皓和张弛,2023), 致力于提升潜在符合上市条件的企业数量, 推动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 以促进买卖双方的博弈, 谋求供求关系市场化程度的提高。
图1详细列示了2004 ~ 2022年我国资本市场的IPO项目终止情况④。从图1中可以看出, 自2019年科创板注册制试点以来, IPO项目终止数量呈明显的递增趋势。尤其是2020年创业板注册制试点后, 终止项目数量急剧攀升。尽管注册制降低了营业收入、 利润和资产规模等方面的门槛, 但对企业的自主专利、 核心技术、 研发投入等设定了更高的要求。这种“拔尖”机制意味着企业需要克服研发周期长、 失败率高且资金需求量大等不足, 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达到上市标准。换言之, 注册制在提升潜在符合上市条件的企业数量的过程中, 对企业的质量把控愈发严格, 也使得项目的终止注册和审核未通过数量大幅上升。
2. 注册制下的项目过会率显著下降。注册制主张降低上市成本、 提高发行审核效率。上市概率与IPO的资源配置效率、 风投入股概率(曾庆生等,2016)、 中介机构的社会资本(陈运森等,2014)等密切相关, 能有效体现IPO发行环节的“寻租”行为(黄亮华和谢德仁,2016), 反映发审委的审核效率、 透明度和独立性。
图2反映了2004 ~ 2022年我国资本市场IPO项目过会率⑤的变化趋势。从数据可知, 自注册制试点以来, 过会率整体呈明显的下降趋势。其中, 2021年的过会率为64.4%, 2022年持续走低, 仅为61.7%, 明显偏低。作为股票市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注册制试点中出现的项目过会率下降情况, 显然有悖改革初衷。
3. 注册制下的注册生效时长在增加。缩短企业的上市审核周期亦是注册制一大重要功能。繁琐的审批程序和频繁的IPO停摆大大延长了上市公司的发行时间, 无形中增加了与之相关的隐性成本, 比如为获得媒体偏差或“有偿沉默”效果的财经公关费用(方军雄,2014), 还有政府公关费用(汪弘和罗党论,2013), 补税支出以及其他机会成本等。
图3分别列示了科创板、 创业板以及北证的IPO项目注册生效平均时长变化趋势。从图3中可以得出, 三大板块下企业从提交注册到注册成功的平均时长不断提高。2022年, 北证注册生效的平均时长达170天, 然而科创板项目注册生效的平均时长已达322天, 创业板项目注册生效的平均时间更是长达507天。注册制下强调发行审核权下放交易所, 证监会保留备案权, 仅做形式审查, 致力于简化审查程序, 让时间更短, 过程更透明。但注册制试点下所呈现出的注册生效时长的延长, 客观地反映了企业发行的难度, 明显与预期不符, 极有可能对企业上市后的大股东行为和公司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四、 当前注册制下IPO发行“悖论”: 一种可能的解释
前面的分析发现: 自注册制试点以来, IPO项目的终止发行数量攀升, IPO过会率持续下降, 发行周期也变得更长, 加大了企业发行过程中的不确定性, 这似乎与国家推行全面注册制的初衷相悖。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何在?
本文进一步对2012 ~ 2022年我国资本市场IPO项目的审核周期进行分析。从图4可以看出, 自2019年注册制试点以来, 企业从提交审核到审核通过的时长呈现明显下降的趋势。一种可能的解释是, 当前暴露出终止数量攀升、 过会率下降、 注册生效周期过长等问题, 是因为压实了各个主体的风险与责任, 对IPO项目进行了质量严控, 导致整体表现在现阶段有悖预期。所以如果从IPO的质量来说, 是“有问题”的公司更难上市了。
资本市场要服务于实体经济, 尤其是服务于国家的战略产业。在注册制下, 有必要进一步探究国家支持产业的资本市场效率问题。
从图5注册制试点后的注册生效项目数排名前五大行业统计数据可以看出, 注册生效项目数量位居前五的行业分别是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医药制造业,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五大行业的注册发行数量均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 这与我国的科技强国战略相契合。中微半导体、 中科寒武纪等均在三个月内便鸣锣上市, 也充分说明了包容性更强的注册制更有利于国家大力扶持的科创公司的发展。
笔者认为, 之所以会出现所谓的“悖论”, 可能的解释大致可归结为三方面因素。
1. 信息披露要求的提高。上市委审议结果频繁出现“暂缓审议”, 是注册制不断深入发展, 以及证监会部署“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背景下的现象, 需要中介机构和监管部门不断探索注册制下信息披露尺度和规范性要求, 交易所的问询流程和上市委审议重点也需要磨合厘清。注册制强调的信息披露涉及IPO抑价程度(姚颐和赵梅,2016)、 股价同步性变化(沈华玉等,2017)、 新股破发(罗党论等,2022)等一系列问题。市场化对信息披露合规性的严苛要求, 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拟上市企业为顺利发行股票而采取的盈余管理行为。而注册制的现行标准本质上是变相的筛选。如若企业信息披露质量较高, 包含更完整、 更前沿、 更多维度的行业信息和企业特质信息, 就能有效提升资本市场的信息丰富度、 降低投资不确定性(Edmans等,2011)。但若企业的信息披露出现偏差, 那么多轮问询带来的发行隐形成本叠加满足披露要求的发行显性成本, 就无形中提高了公司的上市发行门槛。拟上市企业在审核中被监管机构发现了疑点, 或因底稿工作不到位在新规下经不起更高标准的检查, 使得IPO主动撤回现象频发。
2. 中介机构职责的加强。注册制明确提出“卖者有责, 买者自负”的观点, 强调“监管机构形式审核, 中介机构实质把关”的思路。学界已经就中介机构在股票发行审核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达成了较为一致的意见(李敏才和刘峰,2012), 诸如IPO阶段的会计信息质量是影响新股定价效率以及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因素(Willenborg等,2015)。推行注册制后, 监管机构的审核重点将转移为申报文件的全面性、 准确性、 真实性与及时性, 由市场根据披露的信息进行新股定价。发行制度的转变必将对中介机构提出更高的要求。一方面, 拟上市企业为了提高发行定价, 向市场传递公司信息披露质量高、 财务报告可信的信号, 对中介机构的要求必将提高。另一方面, 注册制发行更强调事后监管, 拟上市企业申报材料是否真实, 主要由中介机构进行核查和担保。如若后期发现存在信息披露不实、 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欺诈行为, 中介机构将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这一责任追究机制使中介机构面临的发行风险大幅增加。中介机构为了规避相应风险和寻求过会往往选择投入更多的资源。这一举措同样具有两面性。一方面, 更多资源的投入可能会形成高质量的信息披露, 这无疑是利好的; 但另一方面, 对于质量不佳的拟上市企业, 这种制度设计可能过于严苛和琐碎, 造成发行成本的大幅增加, 同时使得发行注册生效的项目数量大打折扣。
3. 发行制度尚待健全。我国IPO发行的诸多现象存在制度性原因(Tian,2011), 注册制也重点对其进行了修补, 诸如在科创板和创业板的试点上分别提出了“1+2+6+N”⑧和“8 + 18”⑨的制度规则体系。注册制一方面针对拖沓的上市用时问题, 极力想缩短发行审核和注册总时间; 另一方面在试点中有意区别科创板和创业板侧重扶持的融资企业类型, 突出行业特殊性, 努力提高过会率。前者强调两大板块都应在赋予市场更多选择权、 优化资源配置、 加大双向扩容的目标上达成一致; 后者則解释了两个板块对应的注册制规则的差别, 腾出空间和精力有针对性地帮助优质企业快速成长。但上市企业的质量决定因素颇多, 现有行政机制和披露机制并不具备甄别好坏的功能。制度设计者和监管机构既然要把更多对公司质量的甄别权交给市场, 用市场的淘汰机制来筛选, 就必须要有成熟稳健的发行制度加以保障。现阶段, IPO发行的准备材料繁杂, 耗费企业及中介机构的精力, 也给监管机构带来了困扰, 变相阻碍了企业上市, 对注册制的市场化发展显然是不利的。另外, 监管层对IPO市场设置的诸多限制以及在市场低迷时动辄实施IPO停摆(暂停新股发行业务), 使得企业IPO表现并没有达到监管层的预期效果。而在企业发行进度条时不时被中断的情况下, 相关的发行成本也随之攀升, 注册发行时间不断被拉长。
改革必然有阵痛期。上述三方面的归因反映了注册制改革的目的是杜绝企业“抱病闯关”和“炒壳”的乱象, 使规范的企业IPO发行通道更为通畅, 依旧深度契合注册制改革的宗旨。
五、 更好地推进全面注册制: 一些建议
全球注册制的发行方式五花八门, 产生的问题亦是名目繁多, 需因势利导、 对症下药。本文研究发现的终止数目攀升、 过会率下降、 注册生效周期延长的注册制发行问题, 是当前全面推进注册制面临的表象问题。
当下全面推行注册制, 要取得“既保质又保量”的效果, 高质量的信息披露是基础, 中介机构实质把关是关键, 严刑峻法是保障, 具体可以从政府、 中介机构及企业三方面给出建议。
1. 优化法规制度体系。加强资本市场法治建设是全面实行注册制改革的必然要求。我国目前实施注册制的基础不够扎实, 存在投资者回报制度体系尚未建立、 民事赔偿责任的规定匮乏、 信息披露制度过时且繁复等一系列问题, 亟须完善以《证券法》为基础的法规制度, 统筹兼顾法律的稳定性及灵活性, 深化立法层次。
一是要完善信息披露制度。要明确发行人、 中介机构信息披露责任制度, 严格区分行政、 民事及司法责任, 加强信息技术支持, 降低信息披露和获取成本, 确保信息的真实性、 准确性、 完整性、 及时性。
二是要完善与之配套的行政规章制度, 诸如《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制度暂行办法》《保荐人尽职调查工作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等。要积极与国际接轨, 提升制度框架的国际化程度, 提高对外资的吸引力。
三是要厘清证券监管部门、 交易所与市场的边界。要明确证监会、 交易所在股票发行、 上市中的职责分工, 通力合作, 相辅相成。要通过行政规章规范发行审核操作, 压缩发行审核资料, 砍掉重复的提交和审核环节, 降低企业的发行成本。
2. 建立功能监管组织架构。在全面推行注册制的过程中, 减少政府行政性管制是关键所在。政府要注重完善宏观市场以及法律的整体框架构建。
一是要逐步淡化监管机构对拟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判断, 转向留意证券市场各参与主体的微观行为变化, 引导市场各方更加积极地顺应市场化变革, 全过程、 多角度地提升资本市场信息披露质量。
二是要站在为投资者自主判断企业价值提供真实信息的角度制定披露标准及监管要求。相关标准应以功能监管为核心, 组成包括发行、 上市、 稽查、 处罚委、 投保局等部门的功能监管链, 使事前审核、 事中事后监管与处罚移送等形成整体联动的证券监管组织架构。
三是IPO注册登记审核和上市审核应公开透明地操作运行, 尽量缩短发行审核时间, 抑制审核权力寻租和腐败, 提高上市企业质量, 保证发行环节的专业性、 有效性和权威性。
四是要加强市场自治, 大力推进监管转型和审核权移交。在全面注册制下, 政府的角色应从审核人转为监管人。要明确证券监管部门与中介机构各自的职能责任, 各担其责, 真正把证券市场运行机制的支配权移交给市场, 使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3. 强化中介机构的“看门人”职责。中介机构作为联系多方的桥梁以及发行前申请材料审核的最终把关者, 在全面推行注册制进程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一是要完善《中介机构执业规范》。中介机构要强化自律管理, 尽心尽力为市场做更多的事情。主承销商、 会计师事务所、 评估机构及律师事务所有必要分别加强在企业的尽职调查、 审计、 评估及法律咨询等方面的质量保证和风险提示, 确保自身服务的专业性和规范性。
二是要明确中介机构归责原则。各类守门人要明确自己的职责范围, 与监管机构进行有效沟通, 自觉遵守道德规范。要将保荐人责任与其他中介机构的责任, 特别是连带赔偿责任和过错赔偿分别适用的情形规定得更具體, 并增加补充责任的适用范围。
三是要强调监管要求与独立要求并行不悖。相关制度要赋予投资者更大的维权空间, 强化投资者保护, 督促中介机构做好自我约束。要保持事后监管高压态势, 加大中介机构违法违规查处力度, 震慑违法违规者。
当然, 处罚过严会阻碍注册制的发展, 故而更要求监管方精准执法, 强调对个体的责任, 让中介机构成为资本市场合格的“看门人”。
4. 增强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对资本市场的信心。 注册制改革的本质是把选择权交给市场。当前, 国家十分关心实体经济的发展, 利用好资本市场是企业做大做强的关键所在。在全面注册制推行的背景下, 民营企业更要主动抓住政策红利, 选择合适的时机、 合适的板块大胆拥抱资本市场。
一是企业要充分认识到“打铁还需自身硬”的道理, 之前为了上市而进行的各种“花式包装”和“牵线搭桥”已渐渐失灵, 唯有自身质量过硬才是进入资本市场最有效的“入场券”。
二是企业要严格遵循信息披露规则, 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努力向市场规范靠拢, 降低信息不对称风险, 提高市场信任度和声誉度。尤其是民营企业, 更应该通过正确的市场化方式积极进入资本市场, 帮助自身摆脱融资困境, 以此增强市场竞争力和生存能力。
当然, 进入资本市场不可能一蹴而就。在不同的阶段, 企业应根据自身实力, 利用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条件, 因利乘便, 找准时机发展壮大。
六、 结论与讨论
资本市场基础建设尚需时日。实现全面注册制在资本市场基础设施、 监管能力、 政策环境等方面所需的准备和调整, 需要时间的沉淀和有关各方的努力。因此, 在发展中暴露出的一些“悖论”可能在意料之外, 却在情理之中。我们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 认清全面注册制对提高IPO发行质量的积极作用。有关各方, 尤其是民营企业, 要给全面注册制一点耐心, 既不能急于求成, 亦不能因噎废食。
在我国资本市场目前的制度背景之下, 注册制实施依旧任重道远, 更应该循序渐进, 扎稳法律根基, 不可贪功冒进。完善全面注册制, 还需要持续不断地改善整个资本市场环境, 包括提高民营企业信心、 强化中介机构责任意识, 以及必要的严刑峻法。
【 注 释 】
① 2023年3月17日,首批10家主板企业首次公开募股(IPO)获得证监会批复,同意上述企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3月19日晚,全面注册制下首批主板IPO企业启动发行;3月23日,首批主板注册制新股发行价出炉;3月27日起,10只首批主板注册生效IPO新股陆续开始申购、缴款。
② 《年内IPO终止审核企业增至63家 全面注册制下更需严把“入口关”》,吴晓璐,2023年3月20日,证券日报,网址为http://epaper.zqrb.cn/html/2023-03/20/content_924626.htm。
③ 自2014年起,监管机构对于A股市场新股发行价格具有市盈率不超过23倍的限制。
④ 根据交易所的审核状态,这里的项目终止包括审核未通过项目、取消审核项目和注册终止项目,剔除了重复项目。
⑤ 根据交易所的审核状态,这里的过会率=过会家数/(过会家数+取消审核家数+未通过家数+中止家数+暂缓审核家数),剔除了重复项目。
⑥ 注册生效时长为项目注册生效日期与项目提交注册日期之差。
⑦ 审核时长为项目审核通过日期与项目提交审核日期之差。
⑧ “1”是指《关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实施意见》;“2”是指证监会发布的《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和《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6”是指《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审核规则》等6项规则办法;“N”是指《上海證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等。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home/search/。
⑨ “8”是指《创业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规则》等8项主要业务规则;“18”是指《创业板企业发行上市申报及推荐暂行规定》等18项配套业务细则、指引和通知。详见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aboutus/trends/conference/t20200613_578411.html。
【 主 要 参 考 文 献 】
陈运森,郑登津,李路.民营企业发审委社会关系、IPO资格与上市后表现[ J].会计研究,2014(2):12 ~ 19+94.
董秀良,刘佳宁,满媛媛.注册制下科创板首发定价合理性及高回报成因研究[ 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20(6):65 ~ 78.
杜兴强,赖少娟,杜颖洁.“发审委”联系、潜规则与IPO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 J].金融研究,2013(3):143 ~ 156.
方军雄.信息公开、治理环境与媒体异化 —— 基于IPO有偿沉默的初步发现[ J].管理世界,2014(11):95 ~ 104.
胡志强,王雅格.审核问询、信息披露更新与IPO市场表现 —— 科创板企业招股说明书的文本分析[ J].经济管理,2021(4):155 ~ 172.
黄亮华,谢德仁.核准制下IPO市场寻租研究 —— 基于发审委员和承销商灰色关联视角[ J].中国工业经济,2016(3):20 ~ 35.
赖黎,蓝春丹,秦明春.市场化改革提升了定价效率吗? —— 来自注册制的证据[ J].管理世界,2022(4):172 ~ 184+199+185 ~ 190.
李敏才,刘峰.社会资本、产权性质与上市资格 —— 来自中小板IPO的实证证据[ J].管理世界,2012(11):110 ~ 123.
鲁桂华.从科创板看中国资本市场改革的路径选择[ J].财会月刊,2019(4):3 ~ 8+178.
罗党论,杨文慧,张思宇.冲动抑或贪婪:注册制下新股破发研究 —— 基于中小股东权益保护视角[ J].财会月刊,2022(24):19 ~ 29.
彭涛,朱冠平,王俊,经菠.股票发行制度与初创科技型企业估值:基于准自然实验的证据[J/OL].南开管理评论:1-23[2023-03-19].
屈源育,沈涛,吴卫星.上市公司壳价值与资源配置效率[ J].会计研究,2018(3):50 ~ 56.
沈华玉,郭晓冬,吴晓晖.会计稳健性、信息透明度与股价同步性[ 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7(12):114 ~ 124.
宋顺林,辛清泉.新股发行隐性成本与上市后业绩表现 —— 基于IPO停摆外生事件的经验证据[ J].经济学(季刊),2017(4):1449 ~ 1476.
田利辉.金融管制、投资风险和新股发行的超额抑价[ J].金融研究,2010(4):85 ~ 100.
汪弘,罗党论.商场亦官场 —— 创业板公司独立董事政治背景调查[ J].北大商业评论,2013(6):90 ~ 99.
吴锡皓,张弛.注册制改革对资本市场定价效率的影响研究 —— 基于IPO抑价率的视角[J/OL].南开管理评论:1-32[2023-03-25].
邢会强.我国资本市场改革的逻辑转换与法律因应[ J].河北法学,2019(5):26 ~ 39.
姚颐,赵梅.中国式风险披露、披露水平与市场反应[ J].经济研究,2016(7):158 ~ 172.
俞红海,范思妤,吴良钰,马质斌.科创板注册制下的审核问询与IPO信息披露 —— 基于LDA主题模型的文本分析[ J].管理科学学报,2022(8):45 ~ 62.
曾庆生,陈信元,洪亮.风险投资入股、首次过会概率与IPO耗时 —— 来自我国中小板和创业板的经验证据[ J].管理科学学报,2016(9):18 ~ 33.
张劲帆,李丹丹,杜涣程.IPO限价发行与新股二级市场价格泡沫 —— 论股票市场“弹簧效应”[ J].金融研究,2020(1):190 ~ 206.
Edmans A., Goldstein I., Jiang W.. Feedback Effects, Asymmetric Trading, and the Limits to Arbitrage[ 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1(12):3766 ~ 3797.
Tian L.. Regulatory Underpricing: Determinants of Chinese Extreme IPO Returns[ J].Journal of Empirical Finance,2011(1):78 ~ 90.
Willenborg M., Wu B., Yang Y. S.. Issuer Operating Performance and IPO Price Formation[ J].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2015(5):1109 ~ 1149.
(责任编辑·校对: 黄艳晶 许春玲)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救助抑或‘接盘:政府纾困基金运行的动因、机制与效果研究”(项目编号:72272157);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项目编号:20JZD014);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广州民营企业家参与涉企政策制定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22GZYB21);中山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项目编号:22wklj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