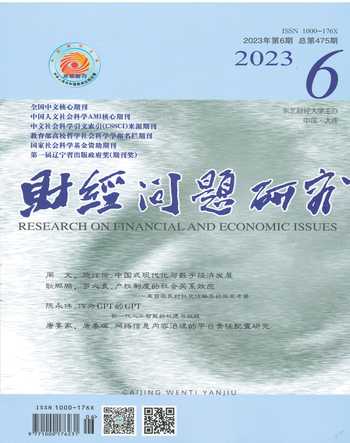中国式现代化与数字经济发展
周文 施炫伶
摘 要:在数字经济时代,中国式现代化与数字经济发展密不可分。从历史纵向维度看,数字经济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关键力量。从横向对比维度看,发展数字经济是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突破口。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考察数字经济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主要包括:一是创新驱动的数字经济发展增强中国式现代化的协调性;二是系统观念的数字经济发展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体系性;三是人本逻辑的数字经济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性;四是制度保障的数字经济发展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优越性;五是和平发展的数字经济发展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基于此,笔者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上数字经济发展需要健全平衡保护与共享的数据产权政策、兼顾公平与活力的数字平台竞争政策、统筹安全与发展的数字经济监管政策。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数字经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
中图分类号:F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23)06?0003?13
一、引 言
历史学家罗荣渠认为,广义的现代化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狭义的现代化是指落后国家有计划地进行“经济技术改造和学习世界先进,带动广泛的社会改革,以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和适应现代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1]。马克思认为,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实质上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中历史变迁的过程。然而,“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2]。《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3]
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后的新经济形态,也被看做开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钥匙,数字经济时代中国式现代化与数字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2016年《二十国集团数字經济发展与合作倡议》中定义数字经济为“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4]。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发展数字经济,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和国家大数据战略,建设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近年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加速创新,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以“加快数字化发展 建设数字中国”为单独篇章,从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加快数字社会建设步伐、提高数字政府建设水平和营造良好数字生态等四个方面进行顶层设计和规划,随后各地陆续出台数字经济发展相关政策方案和行动计划。2012—2021年的10年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从11万亿元增长到超过45万亿元,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现在移动支付遍及神州大地的每个角落,年交易规模达527万亿元,领先全球的移动支付正深刻改变着每个人的生活。中国构建起先进完备的数字产业体系,算力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5万亿元,近5年平均增速超过30%,云计算市场规模超过3 000亿元,有10.5亿用户接入互联网,形成了全球最为庞大、生机勃勃的数字社会。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在数字经济时代,只有将数字经济发展纳入中国式现代化的框架下考察,才能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突破性与超越性,以及对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大意义。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探究数字经济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特征和内在逻辑,并提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数字经济的发展路径。
二、中国式现代化与数字经济
(一)历史纵向维度:数字经济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关键力量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出现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拐点,因而马克思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阐述了现代化发展的一般特征,包括机器大工业普遍应用下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商品经济发展推动世界市场的形成发展,以及建立在物的依赖上的人的独立性[6]。
在生产力方面,数字技术变革促进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引发了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变革。现代意义上的先进社会生产力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上的现代生产力[7]。现代科学技术的创新和突变通过工业转型使人类走向更高文明阶段[8]。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中强调,“科技事业在党和人民事业中始终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9]。正如马克思所言,“一个工业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必定引起其他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有了机器纺纱,就必须有机器织布,而这二者又使漂白业、印花业和染色业必须进行力学和化学革命”[10]。一方面,数字技术变革通过更新生产方式和塑造劳动力形态,促进个别劳动大规模转化为社会劳动,进而推动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变革通过促进产业内部生产方式变革而促进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水平的提升[11]。
数字经济发展在推动中国科技力量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迈进,从“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迈进的过程中发挥战略作用。在生产关系方面,数字经济发展引发了生产关系的变化。正如马克思曾指出的,“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12]602“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12]602。马克思在《工资、价格和利润》中写道,“科学就是靠这些发明来驱使自然力为劳动服务,劳动的社会性质或协作性质也由于这些发明而得以发展”[13]71-72。数字劳动过程中出现了“众包”“零工”“共享”“劳资合作”等新形式,具有“去劳动关系化”的新趋势[14],推动数字经济时代劳动关系的新变革。
数字化是继以蒸汽机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以电力和自动化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以计算机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后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新一轮科技革命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产生了颠覆性影响。数字经济发展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关键力量,利用数字化缩短落后产业追赶周期、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是中国由“跟跑”迈向“领跑”的历史机遇。
(二)横向对比维度:发展数字经济是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突破口
谈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之“新”,其横向对比的参照系是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和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神话,拓宽了数字经济时代世界现代化尤其是后发现代化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发展中国家通过发展数字经济推动现代化提供了中国经验。
资本逻辑驱动下的西方现代化道路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马克思曾解释机器大生产下科学技术对资本增殖的作用,“不仅是科学力量的增长,而且是科学力量已经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尺度,是科学力量得以实现和控制整个生产的范围和广度”[15]。同样地,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主义攫取剩余价值的本质没有变,只是攫取方式更加灵活、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16]。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哈维[17]指出,新科技和组织形式对于资本主义摆脱危机从不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所谓人类社会现代性(文明)危机本质上是资本逻辑蔓延至人类社会生产生活全部领域造成的危机”[18]。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围绕资本—权力中轴所形成的单线发展观,带来了财富两极分化、“民主空壳化”、生态环境恶化、等级化的国际秩序下全球矛盾冲突升级等一系列失格与失序。数字经济的发展加剧和深化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矛盾与冲突,产生了资本主义社会新的资本樣态——数字资本,即“运用数字技术,通过发现、利用、创造差异来获取利润,追求持续不断积累资本的体系”[19]。
数字资本主义的扩张造成一系列的时代困境:一是数字异化与剥削问题。劳动与资本二元对立趋势的扩大,加剧了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自身关系的异化,“数字化的异化意味着我们所有的个体和个体的交往,已经完全被一般数据所穿透,是一种被数据中介化的存在,这意味着,除非我们被数据化,否则我们将丧失存在的意义”[20]。二是数字平台垄断问题。数字平台组织凭借其规模效应、网络效应和数据的潜在生产力,通过大平台对小平台的控制、大平台间的垄断竞争,逐步强化集中和垄断的趋势。此外,数字平台造就了愈加庞大的产业后备军,劳动对资本从形式隶属向实质隶属的转变表现为就业不稳定化趋势。三是数字拜物教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了物与物之间的虚幻关系掩盖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商品拜物教秘密,在数字经济时代形成了更抽象的“数字拜物教”形式。一方面,劳动产品向商品交换价值的转化需要通过数字网络平台或中介才能实现;另一方面,纯粹的数据量化关系成为数字劳动者的劳动关系和交换关系间接表现的唯一途径。四是全球数字鸿沟问题。数字资本的全球化扩张表现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强权打压其他国家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从而主导“逆全球化”过程,同时,国际数字霸权导致国际数字鸿沟日益扩大[21]。
数字资本主义导致了“财富分配悖论”,即数字革命在创造社会财富的同时,导致大多数劳动者所享有的财富没有增加反而有所减少。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数字经济,不仅是培育中国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新优势,提升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在现代化道路上实现“换道超车”的关键所在;更是避免数字资本主义带来的弊端、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突破口。在发展数字经济的过程中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既体现了后发现代化国家在数字经济时代推动现代化进程的一般规律,也蕴含着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内在价值,具有解决人类共同问题、推动人类进步的世界意义。
三、数字经济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
(一)创新驱动:数字经济发展增强中国式现代化的协调性
在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的背景下,创新驱动的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推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解决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两大难题,增强中国式现代化的协调性。
首先,数字技术全面赋能文化产业,推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2017年,《文化部关于推动数字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将数字文化产业定义为“以文化创意内容为核心,依托数字技术进行创作、生产、传播和服务”,并指出数字技术的更迭有利于文化产业的生产数字化、传播网络化和消费个性化,其既能培育新供给,又能促进新消费[22]。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变革使文化产业生产效率明显提升,同时,数字技术对文化生产结构、市场结构、消费结构产生颠覆性影响[23]。一是数字技术以高便捷性和低财富能力门槛,极大扩展了文化产业的渗透力和影响力,从而有利于扩大消费规模。二是数字平台下“产消者”的新型劳动形式使大众用户成为平台文化内容的创作者,突破了文化创作的固有模式,增强了文化产业生产的规模性与多元性。三是数字技术对消费者潜在需求的分析和预测提升了文化产业供给与需求的匹配度以及文化传播的精准性。2020年,文化和旅游部发布《关于推动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强调“坚持导向,提升内涵”的基本原则,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社会效益为首要目标,通过文化数据资源的融通融合、产业技术成果的集成运用,为高质量文化供给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强有力支撑;突出内容建设,激发和引领文化消费,在满足人民文化需求的基础上,增强人民尤其是青年的精神力量和文化自信。
其次,数字经济助力乡村振兴,有助于缩小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差距。2018年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首次提出“数字乡村战略”,强调弥合城乡数字鸿沟的重要性。事实上,乡村振兴的本质是农业农村现代化,其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目标和落脚点。在产业数字化方面,“互联网+”的深层应用能够减少信息不对称,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从“精确化”生产、电商化转型经营、农资供给和金融服务方面推进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24]。在生态数字化方面,物联网技术的发展有助于实现农业生产过程的绿色化和透明化;数字化检测平台有助于提升乡村污染防治的智慧化水平,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在文化数字化方面,利用“数字平台+文旅”模式将地方特色景点与传统戏曲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相结合,可以经济高效地提升乡村文化的吸引力和传播力;利用互联网培训模式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可以提升其文化素养。在治理数字化方面,2020年印发的《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进一步指出,基层政府管理数字化和村民自治管理数字化是推动多元治理的重要举措。在服务数字化方面,数字技术凭借信息整合功能和数据共享特征,突破时空限制,通过农村教育信息化、医疗信息化和便民服务信息化实现改善民生的目标。
最后,建设“东数西算”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协同创新体系,有助于缩小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的区域差距。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区域差距主要源于工业化进程和城乡差距[25],需要在数字要素跨区域流通推动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过程中逐步缩小区域差距。目前,中国东部地区在用地用电成本、能耗指标等方面严重受限,阻碍了数据中心产业发展。“东数西算”着眼于解决中国算力资源布局失衡问题,以东部地区算力需求有序引导至西部地区为手段,致力于实现东西部地区协同联动的目标。在数字经济时代,“东数西算”通过数据要素跨区域的充分流通,有助于发挥物流、人流和资金流在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逐步构建产业优势互补、区域协调发展的高质量区域经济布局。具体来说,“东数西算”能够带动东部沿海地区的数字经济相关企业将产业链布局延伸到西部地区,有效拉动数据加工、数据清洗、数据内容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就业;“东数西算”能够推动构建完整的数字经济产业链条,利用数据和信息要素的新型集聚作用,推动中西部地区向经济网络中的产业链高端迈进[26]。
(二)系统观念:数字经济发展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体系性
现代化不是一个单一维度的概念,而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综合性概念,现代化是一个蕴含着总体性思维的复合式概念。现代化绝不单单指工业化,中国式现代化摒弃了以单一工业化发展程度衡量国家现代化发展水平的传统现代化理论,是具有全面性文明指向的,全方位推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相协调的新型道路。根据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观点,统筹把握各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要素和环节的体系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因此,中国式现代化以数字经济的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和广覆盖性助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搭建以实体经济为发展着力点,形成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突破和超越了单向度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
首先,数字经济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是推动实体经济产业结构优化。在微观层面,数字经济发展使数据要素嵌入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在与其他生产要素融合的过程中调整各类生产要素的投入比例与组合方式,从而重塑实体经济传统业务流程模式,推动实体经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在宏观层面,数字技术在市场需求挖掘和分析领域的应用有利于减少产品和服务的低端和无效供给,缓解实体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二是推动实体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数字平台带来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长尾效应将提高同一产业上中下游经营实体间的关联性,进而改变传统实体经济的发展方式,由束缚于自身有限资源和流动障碍转向各主体间通过更高效的资源共享、更自由的要素流动实现共同发展[27]。三是推动实体经济增长动力转换。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制造业在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中,瞄准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先进轨道交通装备、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培育新竞争优势和实现绿色转型,形成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是中国制造业迈向全球中高端价值链的突破口。
其次,数字经济与科技创新相辅相成。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发展拓宽了科技创新的发展空间、提高了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效率。在发展空间上,数字经济知识结构和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发展能够进一步驱动多层次、多方面的知识创新;在转化效率上,数字经济实践中产生不同消费场景下的新技术、新产品的新需求,助力科技创新面向现实需求的新发展。另一方面,科技创新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底层支撑和发展动力。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科技挖掘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底层技术支撑;5G基站建设、特高压、物联网、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技术创新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新型基础设施支撑。此外,科技创新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为数字产业化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再次,数字经济推动现代金融脱虚向实。一是提升现代金融的普惠性。数字技术催生的新型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和融资方式不仅降低了投资者的进入门槛、拓宽了投资渠道,而且大数据技术和智能算法的应用降低了交易成本,极大地提高了金融运行效率,使现代金融在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的同时惠及大众。二是增强现代金融的安全性。一方面,分布式数据存储的区块链技术构建了低成本的信任机制,公开透明、可追溯、不可伪造的数字货币发展增强了金融交易的安全性。另一方面,数字技术通过快速识别和分析海量金融数据形成新型风险控制系统,提高了金融风险的管理和控制能力。其中,金融科技创新带来的去中心化促进了储蓄向投资的转化。三是提高现代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精准性。金融机构利用大数据智能分析工具更好地感应产业发展动态和市场需求变化,提升和完善了金融产品的供需匹配,促进社会闲置分散资金向生产性资金的集聚,将对过剩产能行业的信贷支持转向高科技、高附加值的数字化实体经济。
最后,数字经济驱动“人口红利”向“人力资本红利”转变。一是通过服务业的产业数字化吸纳大量劳动力,并随着第一和第二产业数字化水平的提升,劳动力跨产业、由边际生产率低的部门向边际生产率高的部门自由流动,既能提高人岗匹配效率,又能提高就业质量。二是数字技术通过提升教育的开放性和普惠性,为欠发达地区的人力资本培育降低成本、拓宽渠道。三是数字平台更高效地整合对接了政府、企业与高校的资源,通过“产学研”深度融合培育高端人力资本,同时释放促进产出效率提升的内在效应和知识溢出、科技扩散的外在效应,从而驱动实体经济发展。
(三)人本逻辑:数字经济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性
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式现代化旨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价值追求上超越了追求资本的无限增殖和剩余价值绝对化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将人民置于现代化主体性地位的人本逻辑决定了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独特性,是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根本属性。
首先,数字经济发展具有“做大蛋糕”的效率导向。一是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在生产环节提高劳动生产率。马克思曾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13]179。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取代传统实物性要素,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劳动对象;算法程序和人工智能设备成为劳动工具;劳动者的基本知识和技能也向数字化方向转型。数字经济通过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实现劳动对象、劳动工具和勞动者等实体性要素数字化的创造效应,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了数字生产力[28]。数字技术变革还使组织方式更加扁平和灵活,使管理方式更加科学化和智能化,进而提高了社会化大生产组织资源的效率。二是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在流通环节提升资本周转效率。相较于工业经济时代,数字经济时代的信息流通方式发生了颠覆性变革,5G网络、云计算、数字存储技术的发展实现了更短流通时间、更低交易成本、更高流通效率的数据收集、传输、处理和挖掘。可以说,数字平台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流通的时空限制,企业能够利用数字技术在线上搭建全球性交易平台,在线下形成智能化、精准化的现代物流和仓储系统。流通环节的数字化发展实质上提高了资本周转和价值实现的效率[29]。三是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在消费环节扩大内需。马克思曾强调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也就是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后者是生产的前提”[13]9。在数字经济时代,消费场景变得多元化和虚拟化,消费内容变得多层次、个性化、更倾向精神享受型,消费的方式转向平台化和网络化。数字技术在零售场景的应用不仅能更高效精准地对接和满足国内市场大规模、多层次、多元化的需求,而且能够挖掘和刺激智慧生活、智慧健康、智慧养老和智慧交通的潜在需求,推动消费结构转型升级。另外,数字金融产品的创新发展也为扩大内需提供了更多消费信用的实现形式[30]。综上可见,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为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夯实物质基础。
其次,数字经济发展具有“分好蛋糕”的公平导向。一是数字经济发展使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参与社会再生产,充分考虑数据要素在劳动过程中的贡献并参与分配,体现了对要素所有者的公平性。坚持以共享作为发展数字经济的基本原则,通过非对抗性的分配模式提升广大劳动人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劳资关系的重要路径[31]。二是数字经济增加了就业岗位和形态,有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目前,数字经济与第三产业的融合发展最为成熟,在创造就业岗位、扩大就业容量、提升就业质量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在数字经济发展的推动下,现代服务业和信息化、智能化行业的劳动者劳动报酬逐渐提高,从而使得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第一和第二产业的数字化水平提高促使劳动者技能和素质水平提高,可变资本比重的进一步增加将使社会中等收入群体扩大,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纺锤形分配结构。三是数字经济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数字技术推动电子政务的发展,提高了政府的数字治理能力,形成公众需求导向的便捷化,并形成互动式公共服务体系。此外,信息高速公路等数字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成为提升落后地区公共服务水平的坚实基础,数字平臺凭借其广泛的覆盖性为补齐偏远落后地区公共服务短板提供支持。
最后,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本逻辑还体现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理念,重视统筹“代内发展”“代际发展”,突破和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发展与保护的“二元悖论”难题。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32],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的大计,扭转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是对中华民族和子孙后代的历史责任。将大数据算法和区块链技术引入电力交易、碳交易、新能源消纳等领域,将极大提高新型电力系统、交易系统全周期记录和分析、智能决策、精准控制的能力,是中国坚定不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举措[33]。
(四)制度保障:数字经济发展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优越性
首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体现社会主义属性的根本保证,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优越性的根本来源。中国式现代化被动地起始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全球扩张,但最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被动转为主动,开辟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优越性。一是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处理好数字经济时代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有机融合关系、国家现代化建设目标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有机统一关系,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能有效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合力”“接力”,避免西方现代化道路中因政治上实行多党制和议会制民主而在现代化建设方面难以实现“合力”“接力”的弊病,一以贯之地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路线、方针和重大政策[34],是渐进式接力推进数字经济发展的根本保证。二是中国式现代化探索之所以具有连续性、递进性和成长性,就在于坚持党的领导。1921年以来,在党的领导下,中国探索并形成了符合实际的新民主主义工业化道路、过渡时期工业化道路、“四个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及新发展阶段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35]。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结合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实际与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重要特征,不断丰富拓展数字经济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三是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在发展数字经济的同时驾驭资本,就在于坚持党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是党领导经济工作的重要内容。”[36]坚持党的领导是全面提升资本治理效能、克服数字资本主义加剧生产领域不稳定性和价值分配领域不平等性、防范化解数字化过程中系统性风险的根本保证。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同时,让人民群众共享数字经济发展带来收益的制度保障,是中国式现代化优越性的集中体现。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数字经济时代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所有制优势:(1)保障了数字经济时代的劳动平等。数字经济发展使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结合方式产生了诸多新变化,可能出现不同所有制、不同群体和性别的数字不平等问题。中国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实质上蕴含了不同所有制企业劳动者地位和权利的平等性,是未来进一步弥合“数字鸿沟”的基础。(2)保障了和谐劳资关系的构建。公有制企业率先完善工会等民主协商机制,弘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并通过市场和文化对其他所有制企业产生引导作用。国家积极修订和出台保障数字劳动者劳动权益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现出数字经济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属性。(3)保障了数字经济的发展活力。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是激发数字经济与服务业融合发展活力、促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拓宽数字平台初创发展空间的基础性政策。混合所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私人资本向社会资本转向,形成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运用数字技术高效集聚不同所有制的资本成为社会资本、共有资本,能够在大型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采和环境保护等长周期、大规模的投资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二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是数字经济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收入分配是民生之源,是改善民生、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最重要最直接的方式”[37]。不同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分配方式,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决定了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以及多种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方式。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重要性不断提升,2020年4月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将数据列入劳动、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之列,既体现了数据要素的经济价值,又保障了数据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公平性。同时,按劳分配为主体强调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促进了数据共享机制的发展,是解决“数字鸿沟”贫富分化的重要途径。三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伟大创造,是数字经济时代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体制优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市场在效率方面推动现代化与政府在协调、共享方面推动现代化相结合。(1)数字经济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匹配。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突破了传统市场经济信息不完全、配置空间受限的问题,提高了城镇和农村劳动力配置的效率。(2)数字经济对打破行政垄断和地方分割,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意义重大。数字平台下构建基于平台的竞争性劳动力市场,有利于突破制度分割和地方保护的藩篱。依托数字平台而发展的共享经济通过降低排他性、提高灵活性而推进劳动的平等性[38]。(3)数字经济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新型举国体制的建设。在数字经济时代,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显得尤为重要。只有以新型举国体制为支撑,才能牢牢掌握发展数字经济的自主权,协同多元主体共同促进数字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驱动力。
(五)和平发展:数字经济发展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但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不会走扩张主义和殖民主义道路,更不会给世界造成混乱。”[39]更进一步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数字经济时代“我们也要着力解决发展失衡、治理困境、数字鸿沟、分配差距等问题,建设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40]。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西方现代化“国强必霸”“零和博弈”的逻辑,推动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首先,数字“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缩小全球数字鸿沟。全球数字鸿沟是指由于不同国家数字化信息与网络通信技术发展程度不同引致的信息落差、知识隔离以及贫富差距等现象,其加剧了数字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两极分化[41]。2016年9月,中国作为主席国发起《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次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加强“一带一路”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与建设,建成“21世纪的数字丝绸之路”。数字“一带一路”建設致力于解决沿线国家数字发展需求与基础设施不匹配、核心数字技术和数字型人才不足等问题。一方面,通过资金援助和技术支持加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利用大数据等数字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培育和创造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新业态、新模式;另一方面,通过开展数字技术研发和数字经济项目的多边合作,提高沿线国家数字技术软硬件的信息共享程度,推动国际数字化技术标准的制定。总体而言,实现数据驱动的跨越式发展是缩小全球数字鸿沟的重要途径。
其次,数字贸易发展有利于重构全球价值链。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实质上是以位于价值链中低端的“外围国家”的资源和市场服务于位于价值链高端的“中心国家”,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全球贸易规则制定的主导权,不断强化“中心—外围”格局。相较于传统全球贸易,数字技术发展既提升了全球贸易的效率,降低了交易成本,又扩大全球贸易的时空范围。更重要的是,随着数字产品和服务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逐渐超过传统贸易产品,数字贸易的发展将推动形成新的全球价值链。在数字经济时代,世界各国的“比较优势”被重新定义。随着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的普遍应用,消费市场成为比廉价劳动力更重要的竞争优势。这就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利用自身比较优势将数字产品嵌入全球价值链、突破低端锁定地位的历史机遇。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了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重要性。中国将自由贸易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有利于推动数字贸易发展,是积极参与和推动新兴领域经济治理规则制定的重要途径。
最后,数字经济治理有助于引导全球治理机制变革。在数字经济时代,西方发达国家凭借自身的数字技术优势垄断封锁数字市场,维护数字科技领域的竞争优势,激进引导歧视性数字经济治理规则的制定,进一步强化数字壁垒的垄断新优势。可以说,数字经济的发展与治理正在重塑国际地缘政治格局。作为全球数字经济的主要参与者,中国应积极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一是通过数字“一带一路”建设、数字经济南南合作等,在畅通数字资源全球化配置的基础上引领数字经济包容性对话平台建设,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42]。二是在数字确权、交易、流通和保护等方面探索完善数字经济治理规则,并在数字政府建设的基础上提升国家数字治理能力,掌握全球数字治理的制度性话语权。三是积极参与数字经济规则谈判,抵制数字霸权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引导形成多元协同、公正合理、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全球治理新机制。
四、数字经济时代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新路径
在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数字资本无序扩张和数字平台垄断会引致大数据杀熟、平台“二选一”、捆绑交易、算法共谋行为等不可忽视的现象和问题,其不仅会侵害消费者权益,而且会造成竞争失序进而损害市场效率和社会福利、阻滞数字技术的创新发展[43]。为了使数字经济发展在更大程度、更高水平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应当从数据产权政策、数字平台竞争政策和数字经济监管政策三方面着手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
(一)平衡保护与共享的数据产权政策
数字经济时代平台流量垄断和市场垄断的基础是数据垄断。只有明确数据的产权归属、规范数据保护与共享的体制机制,促进数据在保护中应用、在共享中发展,才能奠定数字经济治理的基础。
首先,明确数据的产权归属和保护是推动数字经济健康良序发展的前提条件。根据不同用途,数据可分为商业数据和非商业数据。其中,非商业数据一般是指公共部门负责统计的、与公共服务相关的数据,以及公共部门内部运行的数据。这部分公共数据不具有排他性和明确的产权归属[44]。关于商业数据,学界目前仍在探索数据产权的归属和界定问题,有学者主张因为个人用户是数据创造者,所以产权归个体用户所有;还有学者主张因为平台是数据使用价值的开发和实现者,所以产权归平台企业所有。因此,应在推动数据分类分级的基础上,探索符合数字经济特征的产权实现方式。进一步完善数据产权相关法律体系,健全数据归谁所有,数据如何交易、使用和管理,数据安全如何保护完善的数据产权政策。此外,数据收集的隐蔽化和数据使用的黑箱化要求建立分类治理的数据保护机制。一是强调个人原始数据的隐私权保护。通过制定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形成有效的隐私保护和防止数据非法采集、流通和滥用的法律保障体系,体现个人用户对隐私数据的自决权,有利于增进消费者信心和数据平台发展的可持续性。二是强调商业数据的财产权保护。为企业投资创新性数据开发提供激励和保护,不仅有利于进一步释放数据增长潜能,还有利于规范数据市场主体的交易行为和交易规则,更是培育数据市场、促进数据要素优化配置和价值实现的重要抓手。
其次,建立和完善数据共享机制是扩大数据使用价值实现范围的重要手段。一是公共数据在不同部门之间的共享有利于打破“数据孤岛”,加强公共部门间的协同合作,提高数字经济治理能力。二是合理的数据共享机制有利于打破超大型平台的数据垄断。由于数据收集后使用的边际成本为零,有学者提出建立公益性的数据共享机制,或类似合作社机制的平台合作机制。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健全各类数据的开放管理机制成为必要之举。形成高效流动、开放和共享的数据共享机制有利于数据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上提高数据开发利用水平。
(二)兼顾公平与活力的数字平臺竞争政策
马克思主义垄断理论是全面认识垄断本质及其二重性的理论基石,为平台经济反垄断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并将重点放在对垄断行为的制裁上[45]。2021年2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明确,一方面,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要遵循保护市场公平竞争、激发创新创造活力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要依法科学高效监管,维护各方合法利益。只有针对平台垄断的潜在风险,建立推动创新创业、保护中小企业公平参与的竞争政策,才能促使数字平台竞争兼顾公平与活力。
首先,要深化对数字平台垄断的认识,有针对性地研究中国互联网平台的新型垄断行为。相较于传统垄断行为,互联网平台的新型垄断行为更具有隐蔽性和不易识别性。在反垄断规制中,界定相关市场标准、判定平台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判定共谋协定等方面的工作困难重重。因此,平台竞争政策和反垄断规制的首要任务就是对包括滥用平台管理权歧视非自营业务、滥用数据和算法控制权阻碍数据共享兼容、滥用并购手段进行“扼杀性收购”和使用内部整合手段形成结构性垄断[46]的新型垄断行为进行研究,创新发展数字经济反垄断理论的分析范式。芝加哥学派认为,反垄断规制的理论基础和目标是通过充分的市场竞争提升经济效率,以价格中心主义作为反垄断规制的基本分析范式,然而,数字经济时代的市场竞争逐渐由价格竞争转向质量和创新竞争。中国数字经济反垄断急需在研究新型垄断行为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非价格竞争评价工具的分析范式。
其次,要客观认识反垄断规制的高度动态竞争性和渐进性,制定阶段性的反垄断重点和目标。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等法律法规的修订和完善,对市场竞争的不完全性进行有效弥补,维护市场的良序竞争。借鉴发达国家数字平台反垄断规制的有益经验,并结合中国数字平台发展的实际情况,动态调整和创新数字经济反垄断规制政策。
最后,要运用数字技术服务于经济治理,不断加强反垄断执法队伍及其执法能力建设。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迅猛,要求数字平台反垄断执法队伍不断更新专业知识、提升素质培训水平、迭代监管工具和加强人才队伍管理。数字经济的跨界特征要求培养执法队伍跨区域、跨国家开展调查和执法的能力,提示不同执法队伍的协调与合作能力,并在国际层面借助外部专家和第三方专业机构的力量加强反垄断国际合作的能力。
(三)统筹安全与发展的数字经济监管政策
数字经济发展对国家安全有积极作用。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遏制虚假信息、网络谣言和电信诈骗等新型国家安全风险,数字化建设有利于形成应对重大风险挑战时的应急资源调配和管理能力,数字技术与军事科技的融合发展有利于推进强军目标。但是毫无疑问,数字经济发展也造成个人隐私安全风险、平台垄断风险、金融系统性风险等国家安全的新隐患。因此,统筹安全与发展的数字经济监管政策成为数字经济治理工作的重中之重。
首先,要秉持包容审慎、精准施策的原则。保障数字经济安全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安全战略、关键基础设施保护、个人信息保护、安全信息供给等方面的法律、政策和战略[47]。包容审慎原则体现在以适当的限度将约束力度最大化:一是让数据发挥生产要素作用的同时,加强数据安全保护,做到数字经济发展安全可控。当用户转换成本较低时,平台的市场份额具有高度动态性,新平台进入可竞争市场将对市场份额造成较大影响。数字平台的发展依赖其流量优势,即市场份额优势,如果单纯地以市场占有率为标准进行监管,将对数字平台的持续创新和社会资源配置优化产生消极影响。二是在个人信息和数据隐私保护、防止平台过度使用或不正当使用数据的同时,推动个人数据商业价值的开发。2021年6月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规定,互联网平台收集和使用个人信息要遵循“合法、最低、必要”原则。互联网平台挖掘数据价值必须遵循尊重个体知情权和选择权的“明示同意”原则。
其次,要推动监管常态化、法治化和精细化。一是要转变监管思路,制定科学灵活的反垄断监管目标。规避单一、局限、静态的传统监管模式的缺陷,完善主管部门和监管机构的协同合作机制,强调监管前置,强化事前和事中监管的常态化和动态化。二是要加快健全数字经济市场准入、公平竞争审查和监管相关的法律法规,及时弥补规则空白和漏洞,提高全方位监管的法治化水平。三是创新政府监管模式,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算法推进科技监管与法治监管的融合,把监管和治理贯穿创新、生产、经营、投资全过程,提高监管的科学性和精准性。四是按照行业特征分业监管,按照数据平台的不同业务类型分类监管,提高监管的精细化水平。例如,根据金融科技风险传播迅速、波及面广、负面外部性强等特点,加强将数字金融监管与传统金融监管的标准和法规相统一的建设,不断增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能力。再如,对数字平台收购和内部整合之后的经营行为、数据开放共享行为、内容分发算法行为进行监督,提高不正当竞争监管的有效性。
最后,要提升市场化监管水平,打造统筹安全与发展的良性监管环境。一是要引入行业协会、消费者协会等第三方主体直接或间接参与监管,健全第三方主体监督管理和反馈举报的机制,形成多元共治的监管格局。其中,要突出信用体系建设在市场监管社会化中的基础性作用。市场经济也是信用经济,当一个社会的信用水平越高,市场化监管水平将越高,社会的经济运行成本将越低,交易也将越安全。因此,要引导全社会树立信用意识,自觉抵制违背市场竞争原则和侵犯消费者权益的行为,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让信用成为财富创造的基石。建立平台企业的信息公示制度,强调信息公示和信用约束,使平台企业信用状况同其品牌声誉密切结合。二是要全面提高民众数字素养水平,发挥社会、媒体和公众的监督合力。促进信用监管、强化协调监管,利用数字技术加强社会各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推动信息资源开放共享、监管执法协作配合机制的发展完善,构建部门联动响应机制,达成企业“一处违法、处处受限”的信用约束机制。充分发挥数字经济时代社会力量在市场监管中的作用,形成企业自治、行业自律、社会监督、政府监管共同发力的社会共治新机制。
参考文献:
[1] 羅荣渠. 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7.
[2]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824.
[3]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1-07-02(2).
[4] 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EB/OL].(2016-09-20)[2023-02-20].http://www.g20chn.org/hywj/dncgwj/201609/t20160920_3474.html.
[5] 把握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和规律 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N].人民日报,2021-10-20(1).
[6] 何爱平,李清华. 马克思现代化视野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逻辑进路[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2(1):13-22.
[7] 洪银兴. 论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学维度[J].管理世界,2022(4):1-14.
[8] 金碚. 工业的使命和价值——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理论逻辑[J].中国工业经济,2014(9):51-64.
[9] 习近平. 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J].求是,2022(9).
[10]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思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40.
[11] 王梦菲,张昕蔚. 数字经济时代技术变革对生产过程的影响机制研究[J].经济学家,2020(1):52-58.
[1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4] 韩文龙,刘璐. 数字劳动过程中的“去劳动关系化”现象、本质与中国应对[J].当代经济研究,2020(10):15-23.
[15]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50.
[16] 白刚. 数字资本主义:“证伪”了《资本论》?[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4):53-60.
[17] 大卫·哈维. 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M].许瑞宋,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19.
[18] 王水兴.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J].学术界,2021(10):105-112.
[19] 森健,日户浩之. 数字资本主义[M].野村综研(大连)科技有限公司,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35.
[20] 蓝江. 从物化到数字化: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异化理论[J].社会科学,2018(11):105-114.
[21] 徐宏潇. 后危机时代数字资本主义的演化特征及其双重效应[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2):125-131.
[22] 文化部关于推动数字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EB/OL].(2017-04-11)[2023-02-20].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7/content_5230291.htm.
[23] 江小涓. 数字时代的技术与文化[J].中国社会科学,2021(8):4-34.
[24] 秦秋霞,郭红东,曾亿武. 乡村振兴中的数字赋能及实现途径[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5):22-33.
[25] 王梦奎.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两大难题: 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J].农业经济问题,2004(5):4-12.
[26] MOWSHOWITZ A. Virtual organization: a vision of management in the information age[J].The information society, 1994, 10(4):267-288.
[27] 胡西娟,师博,杨建飞. “十四五”时期以数字经济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路径选择[J].经济体制改革,2021(4):104-110.
[28] 韩文龙. 数字经济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21(2):98-108.
[29] 王晓东,谢莉娟. 社会再生产中的流通职能与劳动价值论[J].中国社会科学,2020(6):72-93.
[30] 韩文龙. 数字经济中的消费新内涵与消费力培育[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5):98-106.
[31] 张敏,李优树. 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主义劳资关系演变的内在逻辑:批判与超越[J].财经科学,2021(10):43-55.
[32] 习近平出席领导人气候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21-04-23(1).
[33] 王宇航,王栋. 新发展阶段促进共同富裕的数字路径[J].社会科学家,2021(10):99-104.
[34] 温祖俊,颜晓峰. 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独特之处[J].人民论坛,2019(18):115-117.
[35] 任志江,林超,汤希. 从新民主主义工业化道路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道路的百年探索[J].经济问题,2022(2):17-26.
[36] 依法规范和引导我国资本健康发展 发挥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N].人民日报,2022-05-01(1).
[37] 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关于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治理[N].人民日报,2016-05-06(9).
[38] 胡莹. 数字经济时代我国劳动过程的制度优势——基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新概括的视角[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2(1):59-66.
[39] 习近平会见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N].人民日报,2018-06-28(1).
[40]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513.
[41] RIGGINS F J,SANJEEV D. The digital divide: current an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J].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ystem,2005,6(12):1-54.
[42] 周文,冯文韬. 在全面对外开放中推进新型南南合作[J].开放导报,2018(3):38-42.
[43] 周文,何雨晴. 平台经济反垄断的政治经济学审视[J].财经问题研究,2021(7):3-10.
[44] 宋冬林,孙尚斌,范欣. 数据在我国当代经济领域发挥作用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学术交流,2021(10):60-77.
[45] 周文,刘少阳. 平台经济反垄断的政治经济学[J].管理学刊,2021,34(2):1-9.
[46] 刘云. 互联网平台反垄断的国际趋势及中国应对[J].政法论坛,2020,38(6):92-101.
[47] 马化腾,孟昭莉,闫德利,等. 数字经济——中国创新增长新动能[M].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231-232.Chinese Moderniza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ZHOU Wen, SHI Xuan?ling
(Institute of Marxism,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China)
Summary:Digital economy is a new economic form after the agricultural and industrial economies, which is also regarded as the key to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ath to Chinese modernization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In the era of digital economy, only by integ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into the framework of the path to Chinese modernization can we deeply grasp the breakthrough and transcendence of the path to Chinese modernization over the Western capitalist modernization, as well as its significance in promoting the change of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explore features and internal logic of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promoting Chinese modern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and proposes the development methods of digital economy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 path to Chinese modernization is inextricably link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Historically speaking, digital economy is the key force driv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In terms of productivity, the transform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zed mass production and triggers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In terms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leads to changes in production relations. Besides,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is a breakthrough to transcend Western modern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in the era of digital economy are analyzed as follows. First, the innovation?driven digital economy promotes the coordination of material civilization and spiritual civilization, solving problems of urban?rural gap and regional gap, and enhances the coordination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Second, the systemic concept of digital economy contributes to the systemic natur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creating a new road to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material civilization, political civilization, spiritual civilization, social civilization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ird, the humanistic logic of digital economy promotes the uniquenes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 humanistic logic determines that common prosperity is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a fundamental attribute that is different from the Western modernization. Fourth, the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of digital economy reveals the superiority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dhering to the CPCs leadership is the fundamental guarantee to embody the socialist attribute in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fundamental source of the superiority of the path to Chinese modernization. Fifth, the peaceful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overcomes the logic of ‘a strong power being bound to seek hegemony and zero?sum game in western modernization, which is essential for improving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Finally, if we want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benefits Chinese modernization, we need to secure a series of policies that balance protection and sharing of data, take into account fairness and vitality of the market, and integrate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Key words:Chinese modernization; digital economy; the path to Western modernization
(责任编辑:徐雅雯)
[DOI]10.19654/j.cnki.cjwtyj.2023.06.001
[引用格式]周文,施炫伶. 中国式现代化与数字经济发展[J].财经问题研究,2023(6):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