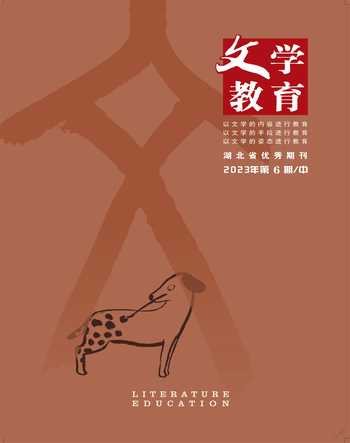魏晋士人的精神嬗变及当代启示

驴鸣、长啸、谈玄、打铁、纵酒佯狂、顾影自怜,这便是魏晋,是宗白华先生所谓的中国史上最混乱和最苦痛的魏晋。魏晋易代之际,政治黑暗,社会动荡,时代的夹缝割裂了士人的道德和行为,他们的理想人格发生了从君子到名士的转型,他们醉心于清谈、饮酒和吃药,无论在朝在野,只为保家,不想卫国,只为明哲保身,不想造福百姓。史学家曾这样描述:“当时的士族,做人以行如畜生为通达,谋职以不走正道为才能,当官以不负责任为高尚。官场里充满奔走之士,朝堂不见让贤之人。”[1]P108可见魏晋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畸形、扭曲的,这是士人在对黑暗现实审时度势后的选择,是魏晋世界观的心灵外现,尽管消极堕落却体现了当下的人格理想和务实精神。
一.病态自由与矛盾人心
曹魏篡汉,司马氏易代,如出一辙的杀戮使魏晋充满了血腥。儒家的道德规范失去了约束力,独尊的儒术也失去了原始生命力,华夏民族的精神支柱倒塌了。于是士人开始追求新的人生体验:回归自然与人性,在及时行乐中实现自我。这是玄学的心灵外现,也是魏晋士人痛苦内心的外化。就连曹操都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忧患和感慨,更何况士人崇尚自由、任情放荡、不拘礼节。然而他们所追求的自由是病态的,病态的主要表现是吃药和酗酒。
吃药的风气始于何晏。何晏曾说“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世说新语·言语》十四)于是在他的影响下,五石散广泛流行。五石散有毒且药性燥热,食用者须以饮酒或快走的方式散热解毒,于是魏晋便出现了一群衣衫不整、散发狂奔的男子。不仅如此,长期食用五石散会使皮肤敏感,一挠即破,难以愈合。因此,魏晋士人大多宽衣大袍,且不敢沐浴,就算身上长了虱子也不以为然。“桓温入关,猛被褐而诣之,一面谈当世之事,扪虱而言,旁若无人。”(《晋书·王猛传》)这便是“扪虱而谈”的来源。然而这些行为在当时却被竞相推崇和追慕,甚至有人佯装药性发作,宽衣倒地,抓耳挠腮地装出抓虱子的样子,这就是魏晋的时尚。然这一时尚也有其意义:68岁位高权重的王戎就是在危急时刻假装药性发作,跳进茅坑装疯卖傻才得以保全性命。
魏晋士人不仅吃药还酗酒,如“竹林七贤”中的刘伶。据《晋书·刘伶传》记载,刘伶经常乘坐鹿车出门,一边喝酒,一边前行。随行的仆人扛着锄头,准备将醉死的刘伶就地掩埋。有一次刘伶甚至赤身裸体地躺地上饮酒,对于旁人的讥笑他反驳:“我以天地为栋宇,房屋为裈衣,诸军何为入我裈中?”(《世说新语·任诞》六)酗酒是刘伶的生存之道,对于司马政权,刘伶不想像嵇康那样公然反抗,也不愿像阮籍那样委曲求全,面对司马氏他借着酒劲撒泼狂言,答非所问,流露出百无一用的样子,最终得以寿终正寝。刘伶为避祸而酗酒,阮籍亦然。为了拒绝与司马昭联姻,阮籍醉饮两个月。正如阮籍所说的“天网弥四野,六翮掩不舒”(《咏怀》四十一),既然谁也飞不出魏晋这一弥天大网,那就饮酒作乐,明哲保身。然而,他的内心是痛苦的,就像王大所说“阮籍胸中垒块,故需酒浇之”(《世说新语·任诞》五十一),所以阮籍嗜酒如命。
“既有凌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世说新语·言语》七十六)支道林放鹤归去。这是出于对向往自由的感同身受。同样渴望自由的还有“与猪共饮”的阮咸、“曝裈当屋”的刘伶、“顾影自怜”的何晏。他们在醉生梦死或药性发作的时候享受自在,于是狂放和堕落。但这只是士人在苦中作乐中自欺欺人而已,因为那样的自由是虚幻和病态的。病态的同时,他们的人生还充满矛盾。据载,王述在做王导的属官时,经常与同僚聚会畅谈。见大家对王导极尽阿谀奉承,王述说:“主非尧舜,何得事事皆是?”(《世说新语·赏誉》六十二)这是王述的率真。率真的王述还很贪财,刚上任不久便收受贿赂。面对批评,他回答:“足自当止。”(《晋书·王述传》)但后来做州郡长官时他却将俸禄和赏赐散发给亲朋好友。王述的口无遮拦与大言不惭正如当代青年对率真而不扭捏,真诚而不造作的想象和追求。难怪简文帝评价他“直以率真少许,便足对人多多许。”(《世说新语·赏誉》九十一)而谢安“掇皮皆真”(《世说新语·赏誉》七十八)的评价说的便是王述的善隐真意。
魏晋士人的率真犹如孩子的纯真,但也不尽相同。孩子的纯真是未经世俗影响,没有浊气沾染的“不懂事”,而士人的率真是主动扭曲的所谓个性,有时近乎“痴”。因人以为“痴”,才能保全性命,这是时下的生存之道。然而,无论是雪夜访友后“造门不前而返”的王徽之(《世说新语·任诞》四十七),失子后“豁情散哀,颜色自若”的顾雍(《世说新语·雅量》一),还是侄儿大败前秦依然“意色举止,不异于常”的谢安(《世说新语·雅量》三十五),都无非是“长于自藏”罢了。(《世说新语·赏誉》四十四)可见,士人的率真只是喜怒不形于色的隐忍,是他们赖以生存的能力。
“竹林七贤”中王戎让人印象深刻。据说他富可敌国却一毛不拔,送给侄儿的结婚礼物随后又要了回去,为了不让别人占便宜竟将李子核逐一钻孔再卖,但父亲死后他却拒收帛金。让人不解的还有阮籍。在“男女不杂坐”的礼教下,阮籍醉卧美人旁;对嫂子不仅有辞行之礼,还亲自护送;听闻母亲去世的消息后仍继续下棋,守孝期间还尽情饮酒吃肉。不仅如此,“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晋书·阮籍传》)的阮籍竟以青白眼示喜恶。“稽喜来吊,籍作白眼,喜不怿而退。喜弟康闻之,乃斋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晋书·阮籍传》)王戎、阮籍皆是时代的缩影,他们的率真不一定是真实,毕竟“在一个不真实的时代追求真实,这本身就是悖论。因此,魏晋对核心价值的种种追求,就只能变态畸形,充满纠结。”[2]P159可见,魏晋士人集奋发和堕落,洒脱和执拗,漂亮和丑陋于一身,矛盾又统一。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说:“外表尽管装饰得如何轻视世事,洒脱不凡,内心却更强烈地执着人生,非常痛苦。”[3]P105
“竹林七贤”的政治态度分歧明显,但除了嵇康被杀,其余六人皆寿终正寝。因为阮咸虚浮,王戎装疯,刘伶卖傻,向秀见风使舵,阮籍委曲求全,而嵇康嘲弄权贵,公然反抗。嵇康的死改变了很多人,向秀从隐居深山到官至黄门侍郎,阮籍从酗酒避亲到醉写《劝进表》。情感的流露虽然可受外界的影响,但“哀而不伤”的自我节制还需付出更大的代价,所以顾雍“以爪掐掌,血流沾褥。”(《世说新语·雅量》一)阮籍葬母后“因吐血,废顿良久。”(《世说新语·任诞》九)魏晉酗酒吃药正如当代的享乐主义,都是放纵逃避的心理体现。当代青年沉溺于网络,缺乏对现实世界的正确认知,于是消极、堕落,甚至自残、自杀。因此,当代青年应以魏晋为鉴,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分析矛盾,解决问题,摒弃及时行乐和“朋克养生”的矛盾心理,不断在社会现实中改造自我,实现自我。
二.审美情趣与伤逝情结
魏晋爱美,男人更甚。男子重仪容、以阴柔为美是魏晋的审美情趣。生性残暴的石勒在诛杀王衍时,因不忍看到美男死后的惨状,竟让人推墙活埋这一“岩岩清峙,壁立千仞”的男子。(《世说新语·赏誉》三十七)魏晋唯美,士人不仅追求容颜之美,更追求情志的美好体验。因此,既能美容又能使人亢奋的五石散便让士人义无反顾,哪怕将全身溃烂或血管爆裂而亡。这独特的审美让本已充满杀戮的魏晋更增添了一道血染的风采。
魏晋唯美,美在自然。魏晋时期儒学走向教条和僵化,玄学开始大行其道,备受推崇。玄学以崇尚老庄为根本,魏晋的山水诗始终不离老庄思想。无论是“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嵇康,还是“江南倦历览,江北旷周旋”的谢灵运,都将自然与玄理相渗透,藉山水以体玄理,在山水中追求清静无为,清微淡远,清高自赏。自然山水第一次成为文学独立的审美对象。正如徐复观说的:“由庄学而来的魏晋玄学,可以说是‘清的人生、‘清的哲学。”[4]P269“清”作为人生哲学的至高境界,是魏晋士人自然美与人格美,审美理想与人生理想的圆融和统一。然而“自然有成理,生死道无常”(阮籍《咏怀》五十三),士人唯自然之美的同时也悲悯人生,忧患生死。正如王戎所说的“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世说新语·伤逝》四),魏晋之人是极重情的。王济生前喜听驴叫,孙楚吊唁时便学驴叫为其送行。顾荣好琴声,死后,张翰为其弹奏琴曲,放声恸哭后竟“不执孝子手而出。”(《世说新语·伤逝》七)哭友情尚且如此,哭亲情更是悲切。王徽之和王献之晚年相继病重,王徽之竟愿折寿以换其弟性命。曰:“吾才位不如弟,请以余年代之。”(《晋书·列传》五十)后来王献之去世了,王徽之悲痛万分,一个多月后便也死去。
魏晋士人多伤逝,为他人也为自己。王濛病重时摇动着手中的麈尾感慨:“如此人,曾不得四十!”(《世说新语·伤逝》十)他所惋惜的是自己的才华和容颜。而嵇康死前遗憾的则是广陵曲的绝响。嵇康的人生向死而生,面对招安他屡次拒绝,态度强硬,言辞犀利,最终枉死。比起嵇康,阮籍更加长情,因为阮籍爱哭。他为失去母亲而哭,为才貌双全却红颜薄命的兵家女而哭,最后他“车迹所穷,辙恸哭而返。”(《晋书·阮籍传》)阮籍最后的恸哭既为嵇康也为自己的穷途末路,但真正让他嚎啕大哭的是尽管日暮途穷、孤独无助却还要活下去。最终,在嵇康死后几个月阮籍抑郁而终。
魏晋重情,就连“既不能流芳百世,亦不足复遗臭万载邪”(《世说新语·尤悔》十三)的桓温也有柔情的一面。桓温攻蜀时,军中有人捕获一只小猿猴,母猴一路追赶哀啼,最后断肠而亡。桓温得知后“怒,命黜其人。”(《世说新语·黜免》二)不仅如此,一介武夫的桓温还多愁善感。有一年北伐路过金城,见到自己曾种下的柳苗已成大树,于是感慨:“木犹如此,人何以堪!”然后扶着柳枝潸然泪下。(《世说新语·言语》五十三)可见,尽管魏晋多屠戮,而士人仍重情。在功利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价值取向多元化的今天,独立自主、仁义礼信等人格品行逐渐缺失,人际关系逐渐淡漠。而魏晋士人崇尚自然、重情爱人的情怀将启迪我们对人生价值的观照和思考:个人存在于社会,个人的价值和利益影响着社会,更影响着个体的进步与发展。只有秉持爱人与爱物之心,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相统一,才能达到自我价值的实现。
三.傲慢人生与务实精神
魏晋的门阀制度保障了士族成为上品官宦的世袭特权,于是士族有了“贵族”的气质和傲慢的性情。虽然东晋政权是倚靠士族建立的,士族在经济和政治上也曾与皇权相抗衡,但皇帝依然可以对其惩治甚至灭族。在魏晋,决定士族身份地位的是本世族的门第和名望,而非皇帝的宠爱与恩典,因此对于士人而言,光耀世族便能享千秋之荣华。于是士族们企图在谈玄论道中展现自我,以此提高本族世家的名望和地位,清谈于是成为魏晋的另一时尚。空谈玄理,不论政治,不问百姓,魏晋士人沉醉于玄学中自命不凡。然而,当残酷的现实与理性的思辨背道而馳时,迷茫、恐惧、无助和绝望便笼罩着士人的心。尽管如此,他们仍要以“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的清高和豪迈给后人留下回忆。(左思《咏史八首》其五)正如苏力教授所言:“一个群体的长期‘愚蠢,从功能主义视角看,很可能就是他们在生存的具体情境中被逼出来的唯一选择,因别无选择,所以是智慧。”[5]P3个人可以愚蠢,人类则不会,群体的长期“愚蠢”定是当下的智慧。而魏晋两百年间无论清高还是惊俗,豪迈或是风流,皆是当下的务实和别无选择的智慧。魏晋的智慧体现在处世之道、人格精神,更体现于言语。魏晋清谈常以高妙的品题和精彩的辩论彰显个人的思辨能力和语言艺术,谈玄者每到浓烈之时尽管通宵达旦仍感意犹未尽。然而,除了谈玄,士人有的聚敛钱财、比财斗富,有的骄奢放纵、腐朽堕落。他们也曾有济世之志,却又在现实中执迷不悟,如王徽之、谢安等人。他们一边享受着朝廷的高官厚禄,一边又在山水的闲散和自由中流连不返。这就是士人务实的表现,正如罗宗强先生所评价的:“而其实入世之深,机心之重,亦莫过于晋人。”[6]P181
自古中华文化注重现实,崇尚实干,即所谓“大人不华,君子务实”(王符《潜夫论》)。然而只有权贵显要才能不尚空谈,德高望重才能致力实干,魏晋则不然。因为务实的前提是求真,魏晋的“真”是分裂割据与谋朝篡位,门阀傲慢与皇权虚伪。于是士人寄情山水,谈玄论道。他们以傲视古今、狂放叛逆的姿态直面现实,追求个性解放和精神自由。这种不为外物所累、实现自我、以“人”为本的人生观和务实精神在当代仍有其意义。在社会急剧转型、经济迅速腾飞的今天,我们一边享受着科技带来的智能化体验,一边承受着被工具化和模式化的压力。网络技术的发展更滋长了孤独、焦虑和敏感等情绪,影响了当代青年正确人生观的形成。在此重压下,我们需要“虑周流于无外,志浩荡而自舒,飘颻于四运,翻翱翔乎八隅”(阮籍《大人先生传》)的人生理想,因为只有心灵自由才能不滞于物,自信自强才能立足于世。
魏晋士人一生充满矛盾,他们因儒家的入世观走上仕宦之路,而后儒学式微了。于是他们放纵出格,有悖礼制,积极避祸,消极抵抗,哪怕苟延残喘,也要实现自我,这是魏晋士族最深沉的悲剧和最强烈的苦痛。如今的我们处于长期的和平时代,即便有着身先士卒的情怀和济世救国的抱负,只要不置身于刀光剑影的社会现实,是很难理解古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无论是避世或者背叛。而实际上不仅只有消极和堕落,魏晋士人肯定自我、实现自我、追求自由、热爱自然等精神仍值得我们学习。不仅如此,魏晋的文学与文化对后世也有着深远的影响:由于对文学的重视,文学题材的开拓,中国文学史上出现了魏晋这一文学自觉的时代。自觉的除了文学还有人。魏晋士人在乱世中觉醒,他们以独树一帜的目光和姿态批判社会、警醒世人,以焕然一新的理念和价值体系重塑人生。在艺术文化上,魏晋的门阀制度使音乐、绘画、书法、诗歌以世家的形式传承下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起了重要的作用。魏晋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魏晋的人格精神、文化艺术、审美追求将穿越千年成为新时代的序章,引发我们启迪和思考,供我们借鉴和学习。
参考文献
[1]谢圣明,黄立平.《白话二十四史》第五册《晋书·孝愍帝纪论》[M].中国华侨出版社,2004.
[2]易中天.易中天中华史II·魏晋风度[M].浙江文学出版社,2016.
[3]李泽厚.美的历程[M].三联书店,2009.
[4]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5]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M].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
[6]苏力.大国宪制——历史中国的制度构成[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作者介绍:许小婷,泉州华光职业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