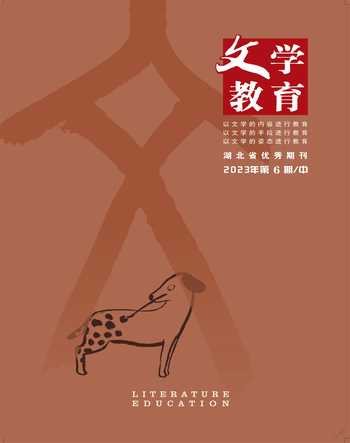河东碧梧桐《中国游踪》中的宁波书写
李媛
内容摘要:河东碧梧桐(1873-1937)是活跃于明治、大正、昭和时期的俳人和随笔作家,他于1918年游览中国多地,并在次年出版游记《中国游踪》。碧梧桐的此次中国行意在以中国为参考,为日本国民带来启迪与暗示。因此他作品中的宁波书写始终统一于以西方文明为标准的审美视角,其在现实中国中对固有认识进行了重新体验,并再次确认了早已扎根于日本人心中的中国形象。而他与日本近代知识分子身上共通的“中国趣味”在面对现实的中国时产生的巨大落差,又使得他的文字中所反映的中国观是复杂且矛盾的,而这种心态在近代日本来华文人的游记书写中亦不少见。
关键词:河东碧梧桐 《中国游踪》 宁波书写 中国观
日本近代有大批的文人怀着各种目的到访中国,以游记的形式记录下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并留下许多以中国为题材的作品,而这些作品中的“都市书写”因为独特的文学价值和历史文献价值,近年来逐渐成为日本文学中的研究成为学术界的热点之一,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有着悠久的交流历史,而宁波、古称“明州”, 地理位置的优越性使其历来都是中日之间的交流的窗口,在中日交流史上扮演着不容忽视的重要角色,也是日本文人游历中国的重要一站。
时至今日,日本文学中的“上海书写”“北京书写”研究都已初具规模,但针对日本文学中“宁波书写”的研究仍处于被忽略的地位。而关于河东碧梧桐的相关研究情况,中日双方的研究现状也呈现差异。在中国关于河东碧梧桐的作家研究与作品研究比较稀少。彭恩华版的《日本俳句史》[1]和郑民钦版的《日本俳句史》[2]中的部分章节都对河东碧梧桐的俳句生涯以及碧梧桐自身的“新倾向运动”都做了详细的介绍。此外,国内学术研究中也有涉及碧梧桐的杭州印象的研究[3]以及以碧梧桐的“无中心论”为主要研究对象,对“无中心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讨的相关研究[4]。而在日本关于河东碧梧桐的研究相对较多。阿部喜三男的《河東碧梧桐》是第一部关于河东碧梧桐作家论的著作,其由“作家研究篇”“鉴赏篇”“作品抄”“纪行篇”四部分组成,卷末附有参考文献、年谱和俳句索引[5]。瓜生敏一曾评价以阿部喜三男的研究为首,使得碧梧桐的全貌得以清晰,奠定了碧梧桐研究的基石[6]。同时也有研究关注了碧梧桐与日俄战争的交点,讨论了碧梧桐形成了怎样的俳句观最后走向了新倾向俳句[7]。除此之外,日本学界对于碧梧桐的研究基本集中于“新倾向俳句”的俳论探讨和作家论研究上。
总的来说,中国学界对河东碧梧桐的研究还不成熟,尚无关于其的研究著作,基本还停留在初级的介绍作家作品的阶段。而针对《中国游踪》,此本书尚无中文译本,学界对于碧梧桐的中国经历与中国观的研究很少。在日本,虽然有很多关于碧梧桐的作家论和作品论的学术成果。但日本学界几乎都忽略了碧梧桐的旅游经历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所以针对《中国游踪》中“宁波书写”的探讨不仅成为旧中国近代化和国民性研究的重要参照,也为河东碧梧桐相关作家研究的提供了新路径。除此之外,也是探讨宁波在中日文化交流中历史地位的一个新视角。
一.河东碧梧桐与《中国游踪》
河东碧梧桐生于爱媛县首府松山市,本名秉五郎,又号如月、青桐、桐仙。其父河东静溪是朱子派学者。明治二十三年(1890)成为子规门人,在正冈子规膝下进行徘句革新运动,活跃于日本徘坛。子规逝世后,碧梧桐成了《日本》徘句栏的编辑,就《温泉百句》与高滨虚子展开论战,从此以后逐渐发展成为虚子、碧梧桐两派的对立,后来甚至矛盾表面化尖锐化。明治三十九年(1906)和明治四十二年(1909)均受到句佛上人的支持进行了两次全国旅行,于旅途中提出“新倾向派俳句”[8],大力提倡“新倾向俳句”和“无中心论”。之后,“新倾向俳句”迎来全盛时代,碧梧桐的纪行文《三千里》和《续三千里》也先后出版。碧梧桐一派与大正初期的以子虚为代表的号称守旧派,强调尊重定型和传统的季题的观念相矛盾,最后斗争结果是碧派势力逐渐下降,而虚子派的影响和威信则越来越高。大正七年(1918)四月至七月游于中国,大正九年(1920)至十一年(1922)游于欧美。昭和八年(1933)在六十寿辰的祝贺会上宣布退出俳坛。昭和十二年(1937)二月一日,因伤寒病发败血症逝世,享年六十五岁。
《中国游踪》[9]是河东碧梧桐于中国旅行之后在大正八年(1919)十月,出版于大阪屋号书店的旅行记。碧梧桐在大正七年(1918)四月十二日从东京出发,十八日在神户坐上诹访丸,受到船长关根海峰的邀请延长了旅程。从上海出发游历了香港,以及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五月十八日返回上海,之后先后游览了杭州、宁波、苏州、南京、芜湖、庐山、武昌、大治、汉江、宜昌、河南龙门、北京、天津、济南、曲阜、泰山等地。七月二十一日从马关(山口县下关)登陆,二十五日回到东京。在这期间,碧梧桐的旅行记和旅吟均发表于《海红》和《日本及日本人》杂志,第二年以《中国游踪》出版[10]。碧梧桐在《中国游踪》的序记中关于此书的内容构成以及他来中国的缘由,这样写道:“回国后我着手于写旅行游记,约一年时间才完成半数,写完了在中国南方的经历正要起笔有关中国北方的见闻。现在,将在中国南方的游记汇总起来编成本书。作为日本人,有紧要的原因需要我们必须去认识中国,认识中国人。要完成这件事,直接去观察和接触无疑是最有成效的方式。书中将毫不保留地介绍我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所感。这样做的缘由,是我确信在对不可不知的中国与中国人的解读的过程中,一定会给国人带来些许启迪与暗示。[11]”
从这一段叙述中,我们可以一窥碧梧桐来中国的原因。作为文明母国的中國“有紧要的原因”而“不可不知”,这些形容体现了自幼深受汉学熏陶的碧梧桐对于向日本人介绍中国这件事的重视程度。而解读中国的目的是“一定会给国人带来些许启迪与暗示”,可见在碧梧桐看来,以西方文明作为标准,在此标准下所书写的中国形象,可以作为一种“方法”来服务于日本国家本身,为日本自身发展带来多样化的思考与启示,成为日本人构筑起自我形象和身份认同的装置。
二.《中国游踪》中的宁波人物书写
河东碧梧桐一生游历多处,他在《中国游踪》的开头部分中曾写道“无论是游于中国行于印度,还是住于南洋老于北美,这都是我的自由。感念平生是不可能平静地死于榻榻米之上,我要任性地行使个人的权力[12]”碧梧桐从游览广东回来后,他受朋友邀请,同行前往杭州,他参观了西湖的三潭印月、钱塘江、灵隐寺等处,随即乘车返回上海。之后他又从上海出发乘船前往宁波,并且先后前往宁波的天童寺、阿育王寺、普陀山。《中国游踪》中的第八章“宁波”、第九章“天童寺育王寺”,第十章“普陀山”中记录了他在宁波的经历[13]。碧梧桐在宁波的经历中很少与中国人直接打交道,所陪同旅行的则是日本友人S君和兼吉君。在宁波游记中碧梧桐所记载的基本是他听说或亲眼目睹后对中国人的笼统的整体印象。
宁波人留给碧梧桐最深刻的印象,便是他在游记中多次提到的民众的“不洁”。碧梧桐在前往天童寺时乘坐当地的游船,就这样记述道“顺着甬江穿过脏乱不堪的后街,就来到了运河的码头。几艘船连在一起,船篷都是用竹子做的草席。谈好船费后,我们登上了其中一条还算整洁的船,仔细一看船内却像垃圾船似的肮脏难闻。[14]”而当他提到人们的饮水“陆地上生活的人们的可怕愚昧的饮水观念是用明矾将混有泥土浑浊不堪的水过滤后饮用[15]”,游览美丽的普陀山时“气清而景明,环境的庄严震撼心魂,我们如同游于画中。但眼前却出现了一坨过分真实随意、让人不可忽视的人粪。[16]”碧梧桐对宁波的“不洁”这一印象,准确地说是对于在宁波遇见的中国人的印象,正是同时代日本社会对中国人的一种普遍共识。
早在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之时,日本对于中国的新闻报道,文学作品和流行歌曲等各种宣传中,就充斥着对于中国人的丑化。比如甲午中日海战中日本的一名骑兵在给友人冈部亮吉的信中就这样描述中国的牛庄:“以前支那人垂流下来的粪尿隐居在冰雪之中,现在粪尿露出表面,不可不谓其肮脏。最过分的是,就算是支那人上等人家的大门口也流淌着粪尿,不会在别处设置便所。虽然知道这是一个野蛮国,但也大出意料。[17]”
除此之外对于中国人饮水的“不洁”田山花袋在自己的从军记《日露戦争実記》中,写道“西洋人视支那人为动物,不得不说,他们实际上就是动物,是下等生物。试想一下,他们不是满不在乎地喝着水坑里的,泥沼里的,马蹄印里的积水吗?[18]”早在1897年,台湾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之初,日本的当政者们就担心,“中国人的风俗中诸如鸦片、赌博、淫秽、不洁、破廉耻等会传染给国人。[19]”在明治维新以后逐渐形成的蔑视中国的风气之中,中国人的“陋习”被夸张放大后,反过来又为蔑视中国的风气提供了依据。带着这种认识来到中国的日本人不知不觉间经历了一个对此重新体验的过程,更加深信不疑。而他们出版的一系列中国旅行记,对于日本国民的中国认识产生了直接的或者潜移默化的影响,让蔑视型的中国观在日本人中得到了普及[20]。
除“不洁”之外,碧梧桐在来到宁波前就听说了关于宁波人的传闻,就是“善经商”,他这样写道“说起宁波,如今以盛产海鲜而闻名。在上海说起宁波人,和在京都聊到江州人一样,通称为会做生意的人。[21]”他也具体介绍了宁波人善于经商的一个例子是他在船上看到的甬江岸边的茅草冰室,“巨大茅草屋的一部分逐渐浮现出来,这就是传说中的冰室。而现在据说是这是为了将此处的海鲜运到上海而设的冰储藏室。[22]”宁波很早就在全国各地展开了商业发展,尤其是在上海。早在1876年的《沪游杂记》一书中曾记录“沿江数里,皆船厂、货栈、轮舟码头、洋商住宅,粤东、宁波人在此计工度日者甚众。[23]”反映了在上海近代宁波人的从商情况。宁波人为了出口海鲜在甬江岸边利用茅草屋作储藏海鲜的冰室则佐证了碧梧桐对宁波人“善经商”的看法。
但是,“善经商”并不是为了凸显宁波人的优点,碧梧桐认为善于经商的宁波人和文明传播的窗口宁波如今却成为了一个接受他国文明的文明输入地,这反而凸显了近代中国的衰落。他写道“无论是要入唐渡天修行的日本僧人,还是其他的遣唐使,留学生,他们第一步踏上的中国土地就是宁波。[24]”宁波作为自古以来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在千年的文化交流中更多的在于输出和彰显古代中国的文化与实力,是古代中国繁盛的象征。而如今却物是人非,碧梧桐写道:“宁波曾是文明输出的源头。正因为是文明输出之源才有很多值得骄傲之处,所以宁波人或许将引入他国文明看做是国家的耻辱。对外夸夸其谈自己国家的中国人,在面对不管是上海、汉口、天津还是青岛都是依存国外文明才建起的事实面前,都只能哑口无言。[25]”
从两次鸦片战争过后,日本人对中国的态度从依附走向质疑,甲午战争中国失败后,日本人更是逐渐从质疑到丑化、蔑视中国。日俄战争的胜利,日本自信成为世界一等国。宁波人自古的善经商善于输出文明到如今反而凸显了近代中国的落魄,这代表着昔日的礼仪之邦的失落。日本妄图成为新的东亚盟主国,自甲午战争以来在国内就不断出现了“日本盟主论”和“中国亡国论”的论调[26]。在这样的思想加持下,来华观光的日本人都带着强烈的优越感,他们认为中国一切不文明都是国家即将落后和即将灭亡的象征,并且他们企图认为曾经老大帝国的失落需要日本人来拯救,日本对中国的侵犯是先进文明对落后文明的宣战,结果是为中国人带来幸福。
三.《中国游踪》中的宁波风景书写
河东碧梧桐在第一次进行全国旅行时,曾发表关于旅行的见解,一观其景,二观其古迹,三观其风俗,四观其人情,五聽其传说古碑,均融合为一[27]。而地方传说是碧梧桐此番来宁波的重要原因。他曾在书中写到:我来到宁波一是基于上海总领事有吉先生的推荐,二是因为此地与日本渊源最深,受到几分好奇心的驱使[28]。与之对应,他在宁波部分的游记中多次提到诸如阿倍仲麻吕、荣西、道元、雪舟、慧锷等日本古代与宁波有着深厚渊源的名人,游览过的地方也都是与这些人有关的历史遗迹。
碧梧桐对于宁波城内的记载基本集中于他乘坐前往宁波的轮船时,自己看到的甬江两岸的风景和人情,而他并没有继续在宁波城中观光。到达宁波的当晚碧梧桐一行人住宿在日本人开的旅社“中村酒店”,第二天便和友人一起前往与雪舟曾巡游过的天童山。
而碧梧桐在这短暂的轮船观光中对于宁波的第一个印象便是甬江两岸成片的坟墓。他这样写道:无论是眺望前方还是回看身后,尽是层层叠叠的小山。坟墓真是令人震惊!这些土馒头的数量也令人惊讶。无论中国人的死亡率有多高,无论这里记录了多久的历史,排列这么多的土馒头就非常不容易。[29]碧梧桐看到这样的景象除了觉得中国人本身愚昧迷信,还认为这是中国人自私自利,没有国家观念的体现。他这样写道“一旦确定了埋葬灵柩的公墓,就会用土馒头建起一个城,放眼望去是一望无际的土馒头平原。彻底贯彻个人利己主义的中国人,在墓地上面也将利己主义贯彻到底了吧。[30]”而碧梧桐对于中国人“自私”这个特质的提及,也反映了大正时期日本人对于中国人的整体印象。早在甲午战争时期,中国人文弱、贫穷、自私、不洁形象就深深扎根于日本民众的思想。这样丑化中国人的“自私”的一面,德富苏峰曾在《七十八日游记》的“支那无国论”以及“病态的利己心”两节中便大肆宣扬过。德富苏峰说“支那有家无国,有孝无忠,这是某位支那通的警句,今天的支那不仅没有国家观念,而且过去也没有国家观念之类的东西。[31]”他辱骂中国人是个人利益至上,缺乏公德心的国民。这种观念在日本的传播又助长了日本人蔑视中国人,而这也非常多的体现在日本人的旅华游记中。被麻痹了的日本公民大力支持政府侵华的行动,最后也导致日本人在中国犯下滔天罪行。
甬江之行途中,碧梧桐还发表了对于中国吸收西方文明,进行近代化的看法“如今在新兴地上海,从前的通商港口,贸易港急剧增加,说起来尽是不忍目睹的丑态。与唐宋明时期可以随心所欲使用楷书文字的时代相比,如今世界的文明正发生着巨大的颠覆。[32]”从1868年明治维新起日本开始全面西化,但由于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和文化的渗透,日本人无法准确定位自己的民族的位置,对此在脱亚入欧浪潮中的日本知识分子也进行了反思。夏目漱石于1911年11月在关西以“西方的开化是内发的,日本现代的开化是外发的”为主题,发表了题为《现代日本的开化》的演讲。夏目漱石说:“一言以蔽之,现代日本的开化是肤浅的开化。[33]”,并得出了日本的发展是外部压力造成的结论。漱石认为日本的近代化与其说是基于对西洋文明的理解而进行的,不如说日本的文明开化只是单纯地模仿了西洋文明。而夏目漱石也曾作为正冈子规的门生学习俳句,其对近代化的观念一定程度上可能影响了碧梧桐。碧梧桐在游记中对中国上海一味地追逐西方近代化的现状进行批判的同时,也包含着对日本自身的近代化发展和日本与西方关系的反思。
碧梧桐一行人在到达宁波当天晚上住宿在“中村酒店”,第二天一早便怀着与雪舟同行的心情前往天童寺。碧梧桐一行人穿过被他形容为脏乱不堪的后街,乘上了一条垃圾船。此时他便感叹道:“如果要去天童寺恐怕不管谁都要乘艘船吧。无论多想来一场奢华的旅行,这艘破败脏乱的小船上肯定是没有轿车和轿辇的。(中略)不管是道元、荣西还是雪舟,都一定搭乘过这条船吧。我不禁能想象到当时他们被视为劣国国民,在乘客众多的船上也只有一个小角落栖身。总之,如今我能够租一条整船并且神气十足地前往天童寺,凭此就必须感谢这个时代。[34]”
从想象中道元荣西“栖身于船的角落”到“租一整条船神气十足”地前往天童寺的转变,可以看出甲午战争后日本通过战争的胜利,使得传统东亚地缘政治中的中日主从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颠倒,中日两国的相互认识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改变[35]。日本国民沉浸在浓厚的蔑华氛围之中,而这种意识都以文字的形式体现在来华旅游的文人旅记。
除了关于交通工具的感想,来到天童山少白岭的碧梧桐路过“揖让亭”时还记叙了关于这座亭子的传说。
揖让亭的来历则是大慧宗杲禅师与正觉禅师在此地相遇,入亭暂憩时,两师谦让不已。看到此情形的张安国不胜感动,说:“三代礼乐,今归释氏矣!”于是就为这个亭子写下“揖让亭”匾额。无论是揖让亭名字的由来,还是看到此情形感叹三代礼乐等等的故事,都仿佛是中国风格的戏剧,十分有趣。[36]
碧梧桐的父亲河东静溪是朱子派学者,老师正冈子规有着深厚的汉学基础,碧梧桐以先贤的经历为向导来宁波重温观光,并且途中“十分有趣”的“揖让亭”传说的记述,都反映了他自身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认同,而这也折射出日本近代知识分子身上共通的“中国趣味”。总的来说,来华的日本近代作家大都从小便受到中国古典文学的熏陶,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有很高的评价,并抱有浓厚的兴趣。但是对当时接触到的中国社会现实感到失望,现实与理想的巨大差距使很多作家对现实的中国表现出蔑视、不满的情绪,这与他们一直以来的观点相悖,因而这一时期日本文人的游记中反映的中国观都是复杂的、分裂的、矛盾的[37],这在稍晚于碧梧桐,于1921年来华参观的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游记》中可见一斑。
碧梧桐在寧波的最后一站便是与慧锷有关的普陀山,陪同旅行的是中村酒店的负责人兼吉君。与之前的论调均不同,碧梧桐眼中普陀山,是一座海中的孤岛,风景如画,仿佛世外桃源。他这样写道:“这座海中的孤岛处处都有像冰一样澄澈的泉水涌出。无论是近海还是山顶,都有不会干涸的丰富水源。正因为是观音的圣地,所以才出现了这样的奇迹吧。这片中国海的方圆三四十里都漂浮着骇人的赤黄色泥土,而在这却有一座春暖夏凉、处处涌出清澈泉水的小岛。就如同污秽的矿渣中提炼出的一块金子,让人感到不可思议。[38]”
在普陀山上碧梧桐评价法雨寺的精进料理颇有风味,让人感到身心放松悠然自得,更说道“普陀山之旅到此已经是十分完美了。[39]”游览这么多地方,为何碧梧桐会对普陀山所持的态度与其他地方迥然有异呢?总的来说,其原因可能在于普陀山的美景与清澈泉水更符合他所喜欢的风景,这与碧梧桐自身所提倡的俳句“新倾向论”的主张殊途同归。碧梧桐所代表的碧派倡导的俳句“新倾向论”与代表古典派的高滨虚子最大的不同,就是是否严格遵循俳句季题与十七字音限制。虚子主张要像能、歌舞伎那样规范俳句,碧梧桐则主张吸收西欧文艺思潮,不受传统季题和摆脱俳句格律制约。以西方自然主义为标准,他认为创作俳句应摆脱人为的规制,不受束缚地表现自然[40]。而碧梧桐在记述普陀山时经常提到这座受菩萨保佑的小岛处处流露这自然原始的气息,而此种不受人为因素干扰的自然,可能正是碧梧桐思想主张的具体体现,也是其思想主张和审美标准的再确认。
在中国旅行的近代日本人见到的中国,不是书本上间接的、或象征意义的中国,而是在实在的历史空间里接触到的现实中国。《中国游踪》中的中国书写就像一面镜子反映出了近代中国在特殊历史时期的真实面貌,形成以他者的视角来分析旧中国的近代化和国民性的重要参照系。而《中国游踪》是河东碧梧桐全部作品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本人的思想观念也或多或少地渗透于游记中,也成为其作家研究的一条新路径。
通过对《中国游踪》中关于宁波书写的研究,反映了河东碧梧桐统一又矛盾的中国观和对宁波的认识。一方面,碧梧桐对于宁波风景人物的评判始终没有摆脱同时代日本对中国认识的固有框架,始终统一于西方文明的标准之下。因此,碧梧桐他以高高在上的傲慢态度去再次確认中国人早已深深扎根于日本民众心中的不洁、自私、迷信、落后的形象,这也体现了当时日本人思维中强固的蔑视型中国观。与之相对,因为普陀山的风景符合西方自然主义的审美标准,故而碧梧桐又喜爱这座与他主张的“新倾向论”志趣相似的海上孤岛,这也是对其自身文人身份与审美观念的再次确认。另一方面,碧梧桐追随日本先贤的脚步来到宁波,体现了他自身的汉学修养和对古中国文化的认同,但是这种日本近代知识分子身上共通的“中国趣味”在面对现实的中国社会时产生的巨大差距,又使得他的文字中所反映的中国观是复杂且矛盾的,而这一点也折射出近代日本来华文人的主流心态。
参考文献
[1]安善花.近代日本中国观的变迁及其东亚强国地位的确立[J].日本学论坛,2008(03):55-60.
[2]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中国的日本认识日本的中国认识[M].中华书局,2015.
[3]荆晓霞,李莉娜,孙立春.明治、大正时期日本文人的杭州游记研究——以内藤湖南、河东碧梧桐、青木正儿、村松梢风为中心[J].语文学刊(外语教育教学),2016(05):71-73.
[4]高洁.佐藤春夫《南方纪行》的中国书写[J].中国比较文学,2012(04):113-123.
[5]葛元煦.沪游杂记卷1[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6]李铃.明治时期日本人中国游记中的中国认识研究[D].北京外国语大学,2021.
[7]李炜.都市镜像近代日本文学的天津书写[M].天津古籍出版社,2016.
[8]刘亚男.河东碧梧桐的“无中心论”[D].河北大学,2020.
[9]彭恩华.日本俳句史[M].学林出版社,1983.
[10]宋协毅.日本俳句的历史、现状及其发展趋势[J].日语知识,2001(04):24-26.
[11]杨栋梁.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M].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12]尹晓亮.近代日本人的中国观与对华行动选择[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2,49(02):49-50.
[13]郑民钦.日本俳句史[M].京华出版社,2000.
[14]阿部喜三男.河东碧梧桐[M].東京:南雲堂桜楓社,1964.
[15]瓜生敏一.阿部喜三男氏著「河東碧梧桐」[J].連歌俳諧研究,1965(28):41-42.
[16]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近代日本思想史第3巻[M].東京:青木書店,1956.
[17]近藤直美.1900年代以降の日本人の中国観の変遷について[J].経済史研究,2011(14):197-203.
[18]正津勉.忘れられた俳人河東碧梧桐[M].東京:平凡社,2012.
[19]田部知季.剣花坊·日露戦争·碧梧桐[J].日本近代文学,2018(99):33-48.
[20]東アジア近代史学会.日清戦争と東アジア世界の変容上卷[M].東京:ゆまに書房,1997.
[21]徳富蘇峰.七十八日遊記[M].東京:民友社,1906.
[22]夏目漱石.漱石全集第9卷[M].東京:漱石全集刊行會,1925.
[23]博文館.日露戦争実記(47)[M].東京:博文館,1905.
[24]春山明哲.近代日本と台湾:雾社事件·植民地统治政策の研究[M].東京:藤原書店,2008.
[25]藤田昌志.日本の中国観―明治時代―:日中比較文化学の視点[J].三重大学国際交流センター紀要,2015(10):46-61.
[26]山本健吉.明治文学全集第56高濱虛子,河東碧梧桐集[M].東京:筑摩書房,1967.
注 释
[1]彭恩华.日本俳句史[M].学林出版社,1983:86.
[2]郑民钦.日本俳句史[M].京华出版社,2000:118,128,135.
[3]荆晓霞,李莉娜,孙立春.明治、大正时期日本文人的杭州游记研究——以内藤湖南、河东碧梧桐、青木正儿、村松梢风为中心[J].语文学刊(外语教育教学),2016(05):71-73.
[4]刘亚男.河东碧梧桐的“无中心论”[D].河北大学,2020.
[5]阿部喜三男.河東碧梧桐[M].東京:南雲堂桜楓社,1964:1.
[6]瓜生敏一.阿部喜三男氏著「河東碧梧桐」[J].連歌俳諧研究,1965(28):41-42.
[7]田部知季.剣花坊·日露戦争·碧梧桐[J].日本近代文学,2018(99):33-48.
[8]阿部喜三男.河東碧梧桐[M].東京:南雲堂桜楓社,1964:47.
[9]原名《支那に遊びて》,“支那”是近代日本对中国的蔑称,抗美援朝战争后逐渐废止。此书尚无中文译本,本稿中采用李炜《都市镜像:近代日本文人的天津书写》中对本书题目的译文。另外,文中引用的《中国游踪》原文均为笔者拙译。
[10]阿部喜三男.河東碧梧桐[M].東京:南雲堂桜楓社,1964:84-85.
[11]河東碧梧桐.支那に遊びて[M].大阪:大阪屋號書店,1919:1-2.
[12]河東碧梧桐.支那に遊びて[M].大阪:大阪屋號書店,1919:4.
[13]本稿中的提到的宁波范围,除了2022年宁波市辖范围的六区二县二市之外,也包括1918年河东碧梧桐來中国时属于宁波市管辖范围内的普陀山。
[14]河東碧梧桐.支那に遊びて[M].大阪:大阪屋號書店,1919:209.
[15]河東碧梧桐.支那に遊びて[M].大阪:大阪屋號書店,1919:236.
[16]河東碧梧桐.支那に遊びて[M].大阪:大阪屋號書店,1919:234.
[17]東アジア近代史学会.日清戦争と東アジア世界の変容上卷[M].東京:ゆまに書房,1997:392.
[18]博文館.日露戦争実記(47)[M].東京:博文館,1905:25.
[19]春山明哲.近代日本と台湾———雾社事件·植民地统治政策の研究[M].東京:藤原書店,2008:176.
[20]杨栋梁.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M].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79.
[21]河東碧梧桐.支那に遊びて[M].大阪:大阪屋號書店,1919:198.
[22]河東碧梧桐.支那に遊びて[M].大阪:大阪屋號書店,1919:197.
[23]葛元煦.沪游杂记卷1[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
[24]河東碧梧桐.支那に遊びて[M].大阪:大阪屋號書店,1919:199.
[25]河東碧梧桐.支那に遊びて[M].大阪:大阪屋號書店,1919:201.
[26]杨栋梁.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M].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99.
[27]正津勉.忘れられた俳人河東碧梧桐[M].東京:平凡社,2012:54.
[28]河東碧梧桐.支那に遊びて[M].大阪:大阪屋號書店,1919:208.
[29]河東碧梧桐.支那に遊びて[M].大阪:大阪屋號書店,1919:194.
[30]河東碧梧桐.支那に遊びて[M].大阪:大阪屋號書店,1919:195.
[31]徳富蘇峰.七十八日遊記[M].東京:民友社,1906:232,260.
[32]河東碧梧桐.支那に遊びて[M].大阪:大阪屋號書店,1919:201.
[33]夏目漱石.漱石全集第9卷[M].東京:漱石全集刊行會,1925:881.
[34]河東碧梧桐.支那に遊びて[M].大阪:大阪屋號書店,1919:210.
[35]杨栋梁.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M].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102.
[36]河東碧梧桐.支那に遊びて[M].大阪:大阪屋號書店,1919:214.
[37]孙立春.日本近现代作家访华游记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36.
[38]河東碧梧桐.支那に遊びて[M].大阪:大阪屋號書店,1919:237.
[39]河東碧梧桐.支那に遊びて[M].大阪:大阪屋號書店,1919:236.
[40]山本健吉.明治文学全集第56 高濱虛子,河東碧梧桐集[M].東京:筑摩書房,1967:378.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指导老师:李广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