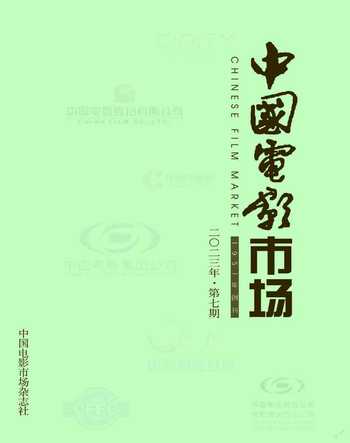浅谈京剧“四功五法”在电影表演中的应用
蒋勤勤
京剧,作为汇中国戏曲百家之长的“国粹”艺术,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间曾在中国乃至世界的舞台上大放光彩。京剧艺术与中国电影艺术存在着紧密的联系。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创办人任庆泰拍摄了由著名京剧演员谭鑫培主演的《定军山》片段,这是中国人自己摄制的第一部影片,标志着中国电影的诞生。此后亦不断涌现出以京剧故事、京剧演员为题材的影片,如:《梅兰芳》等。较之于电影艺术在内容、题材方面对京剧艺术的吸收借鉴,包括表演形式、表演方法在内的京剧表现形式对电影艺术的表演所产生的影响则更大也更为深远。
本文仅以京剧表演基本技能与技巧的“四功五法”为例,浅谈演员如何在电影中合理运用“四功五法”,以及這种化用所产生的效果。
(一)“四功”,即:唱、念、做、打,是京剧表演必备的四项基本功。
1.唱:顾名思义,指的是戏曲中的唱功。表演者需要运用程式化的节奏、曲调唱出有韵律的戏文。唱功是表演中最重要的基本功之一,也是评价京剧演员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准,历代大师多是因为其具有独创性和高度美感的唱腔得以成家立派。由于经典戏曲作品中的唱段往往兼具诗文的韵律美和推动情节的叙事性,演员在学习过程中需要反复研习、推敲每个唱段的内涵,并需要认真模仿大师所创的成熟唱腔。在日复一日的练习和模仿中,演员的进步不仅体现在发声和演唱的能力方面,更体现在用声音塑造人物、抒发情感,同时兼顾叙事的能力方面。
2.念:指念白。京剧演员在表演时需要以白佐唱,在文学性较强的唱段中间夹杂更加通俗易懂的念白,向观众解释唱段内容、叙述故事进程、表达角色的内心情绪。演员在处理念白时有较高的灵活性,这也更考验其利用语言表情达意的能力———演员需要通过清晰的声音和恰当的情绪节奏,将念白内容准确生动地传递给观众。
3.做:指武打以外的表演动作。做功充分体现了京剧表演艺术程式化的特点,要求演员在舞台上每个动作都做到规范、准确。演员只有经过长期投入训练,才能将这种舞台动作规范融入到表演习惯中,实现表演时全程保持对肢体动作的控制。
4.打:指京剧表演中的武打、武术动作,是传统戏曲舞台上最具观赏性和视觉刺激的表演元素。打功包括“毯子功”,即:翻、腾、扑、跌、滚、跃等;“把子功”,即:手持刀、枪、剑、戟进行表演应用。打功对演员身体素质、动作技巧的要求很高。京剧中的武戏是对传统的武打、格斗技艺的舞台化、艺术化的提炼,具有独特的动作美感。
(二)“五法”,即:手、眼、身、法、步,原取自武术,所谓“手为势,眼为灵,身为主,法为源,步为根”。
1.手法:指京剧表演中手部的动作,通过手部的不同手势,表达出动作的不同含义。如花脸的“虎爪式”、旦角的“兰花指”等,都是手法中经典的固定手势。当然,手法往往离不开其他四法的配合,如“云手”这一固定范式中,手法与眼法的配合,就形成了一套基础的组合动作。
2.眼法:京剧艺术中,演员会通过眼睛及其周边肌肉动作强化面部表情的情感表达,这是京剧表演中非常有特色的一种表演方式。角色进入某种情绪时,演员需要配合使用眼法外化该情绪,例如:喜悦时,要微微睁眼、张嘴、动眉;思索时,要左右转动眼珠等,这是使用面部表情展示情绪的经典方式。
3.身法:指表演者的身体姿势。京剧表演对演员的仪态有着非常高的要求,关键在于演员对全身姿势的控制。演员在舞台上的一起一落、一进一退、一收一纵,都需要有程式、有美感。演员在扮演不同的角色时,需要根据规范使用不同的身法,从而体现出角色身份、性格特征等。
4.法:对于“法”的解释,行业内外众说纷纭。一说“法”为“发”的谐音,代指甩发功夫;又有说“法”是“合规”之意,是对演员表演规范性的要求;甚至有解释认为“法”只是梨园师徒授受过程中,口口相传产生的误会。因此,不少名家曾以自己的理解重新定义“四功五法”,如程砚秋先生将“法”改为“口”,规范演员唱、念时的发声方式。
5.步法:步法是要求演员在台上要走“台步”,即根据一定的程式和规则进行移动。京剧演员要根据不同的角色要求和剧情要求,恰当地使用不同的步法,用移动方式进一步精细化塑造人物形象。如“碎步”“云步”“醉步”等,都是京剧传承过程中形成的程式化舞台脚步。
(一)电影中的戏曲“基因”
由于电影的大众性、娱乐性特征,随着电影的普及与发展,看电影迅速成为大众的主要娱乐方式之一。而京剧作为中华文化中最成熟、最有代表性的艺术形式,其表演方法和文化内涵早已融入创作者与观众的潜意识。因此,我们在电影作品中,尤其是以古代历史、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中,往往能发现不少戏曲的影子。前文所提及的“四功五法”,在一些电影中便有明确体现。
(二)从“四功”看《英雄郑成功》中“薛良”一角
笔者在21世纪初参演了吴子牛导演的古装电影《英雄郑成功》,在影片中饰演了帮助郑成功收复中国宝岛台湾的民女“薛良”这个角色,并很荣幸地获得了中国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提名。角色的魅力也正是源于我在塑造这个形象时,适当地运用了京剧表演的一些技法,从而更好、更生动地表现了该人物巾帼不让须眉的性格以及柔情与侠义并重的古典韵味。
薛良一角在剧中设定为中国台湾少女,其父母在反抗荷兰人的殖民统治中丧生,薛良从台湾岛逃往福建时,在海上被郑成功的母亲救起,此后其流落异乡、卖唱为生。机缘巧合,薛良在酒楼卖唱时,再次遇见郑成功和郑母,郑母得知薛良悲惨的身世后,将其收为义女。在此之后,薛良也成为了郑成功的红颜知己。由于薛良这个人物本身有着良好的艺术造诣和文艺气息,因此在对角色的每个动作、神态的设计中都融入了戏曲的表演方法,这对塑造明朝末年流落他乡卖艺为生的少女这一角色,有重要参考意义。
古装历史剧不同于真正的戏曲,除少数经特殊设计的创作外,较少使用“唱”来表情达意,往往仅通过人物间的对话推动剧情。但薛良这一角色,在剧中有一段琵琶弹唱的表演,恰好能够很好地运用戏曲的表演风格。与弹唱声音上的塑造相比,薛良的体态和动作更能凸显戏曲特点。我在处理该角色时,有意在动作和体态上运用了戏曲中“做”“打”二功,一坐一动都做到对姿态有控制,既可以呈现温婉雅致的琵琶歌女形象,也能展示拿起刀剑凌厉果断的刀马旦风采。动静结合与张弛有度间,塑造出一个立体而丰富的人物形象。
(三)表演中“五法”的运用
前文所述的“四功”从整体概念上建立起了人物基本形象,而“五法”则帮助演员为人物增添了表演层次和细节。例如:影片中的两段弹唱琵琶的段落,第一次是薛良在酒楼卖唱,第二次是为救郑成功用曲传信。随着剧情的不断变化和发展,在情绪与情境变化中运用快步、慢步等步法的变化展现人物的内心,都是“五法”基础动作在电影表演中的化用。
电影是镜头的艺术,有大量近景、面部特写等画面,因此戏曲艺术中表情达意的“眼法”在电影表演中就具有了更强的借鉴意义。角色沉思时眼睛远望,忧愁时半搭眼帘,喜悦时眼半睁、嘴半张、眉梢上提,紧张时眼睛流动,愤怒和惊讶时双目圆睁……观众往往不需要台词的解释,仅通过角色脸上的表情,便能理解此时人物的情绪,这是戏曲“眼法”在传递人物内心情感时的优势,而这种优势离不开中国观众与戏曲艺术表演程式的文化默契。
今天当我们回望中国传统艺术时,可以发现其中仍有无穷宝藏有待发掘。严格的表演程式虽然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演员的创造空间,却也凝结了数百年里一代代艺术家的艺术审美和实践。正如1935年梅兰芳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见面时所说的:“在(戏曲)表演当中,全身的力量都是平均的,身体各部分所用的力量是相称的。这样,一指指出去,往往能把戏中人物的喜怒哀乐聚集在指尖上,传给观众。”
当下我国电影作品中不乏令人印象深刻的现实主义表演,然而却也存在不少松懈、随意、缺乏美感的现象。如果我国的艺术工作者能在演员训练和电影表演中借鉴包括“四功五法”在内的传统戏剧表演形式,再配合上斯氏体系对人物内心的深刻体验,相信会创作出一批兼具古典美与真实感的优秀电影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