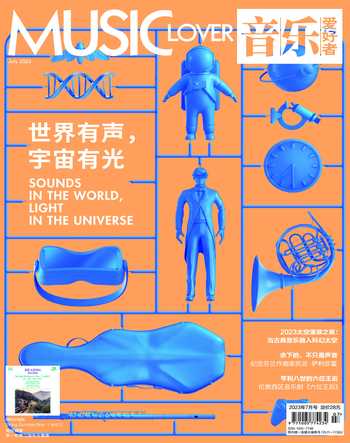西方音乐作品中的中国
甘芳萌

二十世纪上半叶,法国作曲家拉威尔(Maurice Ravel,1875—1937)在成熟时期的创作以繁复、华美的织体而著称。正是这样的精雕细琢,使他的作品经常表现出精致、清晰甚至小巧的特征。拉威尔一生未娶,没有子女,但是他却为儿童创作了颇具规模的两部作品——《鹅妈妈组曲》和《孩子与魔法》,为儿童写作的兴致有增无减。尤为有趣的是,这两部作品都包含了对同一个意象的描绘——“中国瓷”。
法国在十九世纪逐漸形成了体系化的汉学研究,知识界、艺术界对中国文化的兴趣直至二十世纪依然方兴未艾。用来指代以中国为代表、遥远而神秘的东方文化,起源于中国、在欧洲经久不衰的瓷器当之无愧。拉威尔对于远离当下法国文化的历史情景和异国风情一直十分着迷,而在对“远世”“远方”的探索中,他以法国式的敏感和精美呈现了许多可贵而新颖的可能性。在这两部儿童作品中,拉威尔用精美的音乐仰慕着以“中国瓷”为代表的那份精美。
女王驾到!——《鹅妈妈组曲》中的“中国瓷”

《鹅妈妈组曲》最早的版本是钢琴二重奏或钢琴四手联弹,是拉威尔为朋友戈德布斯基(Godebski)的两个孩子创作的。在和孩子的相处中,拉威尔时常要为他们读童话书。这部作品之所以被冠以这样的标题,就因为题材蓝本全部来自法国童话故事集——无人不知的《鹅妈妈的故事》。
《鹅妈妈的故事》是法国的一部童话故事集,拉威尔《鹅妈妈组曲》中的故事就选自这部童话故事集。《鹅妈妈组曲》钢琴四手联弹版作于1908年,1910年出版,同年首演。虽然拉威尔朋友的两个孩子未能成为众望所归的首演者,但这部作品却在另外两个孩子——时年六岁的勒卢(Jeanne Leleu,日后赢得“罗马大奖”,并任教于巴黎音乐学院)和十岁的杜罗尼(Geneviève Durony)手中,名副其实地成为一部采用儿童题材、为儿童创作、供儿童演奏的儿童组曲。
帕凡舞曲是一种盛行于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早期的宫廷舞蹈,性格沉稳,通常为两拍子或四拍子,常被作为引入性的行进舞蹈。第一首《睡美人的帕凡舞曲》(Pavane de la Belle au bois dormant)的题材来自法国童话作家佩罗的故事《林中睡美人》(La belle au bois dormant),柴科夫斯基的芭蕾舞剧《睡美人》的故事蓝本同样来自于此。公主被施以魔法沉睡在森林中,只有等到一百年后一位王子的爱情之吻才能将她唤醒。作为这个童话组曲的开篇,帕凡这种古朴、庄重的宫廷舞曲再合适不过了。优雅的公主沉睡于幽静森林之中,高音区温柔纯净的音乐,就像是为她蒙上了一层轻纱。
第二首《小拇指》(Petit Poucet)的题材来自佩罗的同名童话:父亲欲将拇指般大小的男孩“小拇指”遗弃在森林,但他沿途撒下面包屑作为回家的记号。不幸的是,鸟儿吃掉了这些面包屑。比起第一首《睡美人的帕凡舞曲》,《小拇指》柔和中增加了阴郁,音乐线条在无规则的不断变换的节拍中绵延,绝望的小拇指在森林中漫无目的地寻找着出路。对位织体好似那趋之不散的迷雾,欢快的鸟叫声既是对小拇指的提醒——他没料到鸟儿会吃掉面包屑,也反衬出小拇指的孤寂。音乐行将结束时,下行长音符的附点是这个可怜的孩子叹息般的抽泣。最终,森林回归了寂静和空旷。pp的极弱力度,也许会让我们忽视音乐最终微弱地解决在明亮大调式的那一刻——“小拇指”最终还是离开了那布满不祥与危险的森林。

第三首《宝塔女王莱德罗娜》(Laideronnette, Impératrice des Pagodes)的题材来自法国作家德诺瓦夫人(MarieCatherine dAulnoy)创作的《小绿蛇》(Le serpentin vert)。被施以魔法的公主变成了丑姑娘,和被变成绿色小蛇的王子一起来到瓷偶王国,想要恢复漂亮的容貌。丑姑娘在洗浴时,瓷娃娃们载歌载舞、奏响各种乐器,到处充满了瓷器碰撞时清脆的叮叮当当声。宝塔女王庄严地出场,公主和王子恢复了美丽的容貌,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由于瓷偶王国是一个非常遥远的国度,这首作品的调性与之前两首拉开了最远的距离。为了表现瓷器非乐音的叮叮当当声,五声音阶的旋律中夹杂着其他声部半音的碰撞,表达出拉威尔对遥远东方的音乐律制的感受。在光彩和俏皮中,音乐达到了纯真而快乐的高潮。有序的节奏中锣鼓喧天,一扫前一首作品《小拇指》所表达的孤苦心境。宝塔女王出场时的中段,欢愉转为庄重,低音伴奏中的切分节奏与第一首《睡美人的帕凡舞曲》中高贵的帕凡舞曲节奏形成了呼应。
第四首《美女与野兽的对话》(Les Entretiens de la Belle et de la Bète)的故事选自博蒙特夫人(Leprince de Beaumont)创作的故事《儿童杂志》(Magasin des enfants)。凶猛外貌的野兽其实是被施了魔法的王子,只有真诚的爱情才能破除魔法,使王子恢复人形。这首作品的背景是轻盈、优美的圆舞曲,美女与野兽两个角色之间展开对话。高音区调式化的旋律表达了美丽女子的妩媚轻盈,低音半音化的长线条表现出野兽虽然面目丑陋,却并无攻击性,甚至可以说非常温柔的特点。第一次对话的结束是野兽以上升模进询问“你愿意嫁给我吗”,美丽女子并无回复,音乐安静、内敛地收束。而第二次对话已经是两个旋律线条以对位方式同时歌唱,美丽女子已经接纳野兽,两人以二重唱的方式互诉衷肠。最终,魔法在真挚的爱情下消失得无影无踪,野兽的半音化旋律在高音区轻柔地出现,王子恢复了优雅俊朗的人形,有情人终成眷属。这首作品承接了第二首《小拇指》中弥漫不散的阴郁、紧张,但是最终解决在光彩与辉煌上。

第五首《仙境花园》(Le Jardin fèerique)是睡美人故事的美好结局。这首作品顺延了前一首的甜美,但是圆舞曲转为带有附点棱角的萨拉班德舞曲,这种高贵的宫廷舞蹈与第一首帕凡舞曲的气质遥相呼应。整个乐章从pp力度中音区的恬淡、飘逸,攀爬至引吭高唱的美好颂歌。万物复苏,森林重现生机,整个组曲在光辉圆满中结束。
其中第三首《宝塔女王莱德罗娜》是整部组曲中非常重要的轉折环节:调性的明亮色彩和欢快的节奏型,都与其他几首作品中的凝滞、阴郁形成对比,在情绪上又为接下去的《美女与野兽的对话》和《仙境花园》的美好结局做出重要的指向。可以说,在拉威尔心中,只有像中国瓷器这样美好的事物,才能使恶魔法消失。换言之,如果没有瓷偶王国的宝塔女王,就无法形成美好所拥有的强大魔力;如果没有精美的“中国瓷”,就无法呈现“美好”无以复加的魅力。在《鹅妈妈组曲》中,拉威尔将自己对精美的感受,赋予在了“中国瓷”之上。
跳狐步舞的甜姐儿——《孩子与魔法》中的“英国茶壶与中国茶杯”
“一战”后,拉威尔创作了他的第二部歌剧——独幕童话歌剧《孩子与魔法》。歌剧脚本系法国女作家科列特(Sidonie-Gabrielle Collette,1873—1954)所作,讲述了一个粗鲁的孩子如何被他损坏的东西以及被他折磨的动物惩罚而最终成长的故事。科列特非常关注角色的心理活动,细腻、生动地描绘了多姿多彩的乡村和城市生活,是法国第一个享有国葬礼遇的女作家。《孩子与魔法》原本是科列特写给自己女儿的,最初的名字是《写给女儿的芭蕾》。她笔下的童年时代尤为有趣:不仅是美好的,还是野性、顽劣而充满恶作剧的。因为拉威尔没有子女,所以将标题改为了《孩子与魔法》。
歌剧的第一部分发生在室内。男孩不做作业,被妈妈关了禁闭。他大发脾气,破坏了屋里所有的物件——沙发、挂钟、茶具、墙纸、童话书等。魔法发生了,男孩惊奇地发现房间内的物件都活了:它们开始说话了,唱着、跳着,埋怨着男孩使它们遭受的苦难,警告他要为自己的恶行接受惩罚。

跳舞的沙发和靠背椅这两个笨重的角色之间形成了滑稽而诡异的主题对话。机械运转的大钟在抱怨,男孩淘气地拿走了它的零件导致它无法准确地走动、报时,最终不得不减慢速度、停止走动。
这时,长号、低音大管与大鼓引出了英国茶壶与中国茶杯之间的对话。长号的滑奏、唱段中加了重音记号的附点节奏是那胖滚滚的英国茶壶,木管组不和谐音的碰撞好似茶壶中水开时冒出的蒸汽。与粗笨的英国茶壶形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细腻柔美的中国茶杯。这两个角色虽然都是4/4拍,但有着重要区别:茶壶是进行曲,而茶杯却是狐步舞。抒情而气息悠长的五声调式主旋律配以钢片琴三连音流畅的音型以及弦乐十六分音符拨奏的和声伴奏,充分表现出茶杯晶莹剔透、丰润精美的特点。
天色暗下来了,男孩的视线转向了壁炉中跳动的火苗:花腔女高音呈现了火的忽明忽暗、忽大忽小,半音使男孩越来越不安,这令人想起了莫扎特歌剧《魔笛》中同为花腔女高音的夜后带来的华丽与危险。被撕坏的墙纸和童话书也发出了抱怨:牧羊人唱段的中间段落带着装饰音的轻松音调,愉悦地回忆着草原清澈的天空、美丽可爱的羊群、幸福祥和的生活,但是又突然转回充满不和谐音的小调,哀叹着壁纸被撕坏,美好的生存环境已经不复存在。
乖张的竖琴充满了半音,神秘、幽静地引出了男孩与童话书中公主的见面。长笛、花腔女高音二重唱线条悠长、婉转悠扬,但是阴森的铜管是魔力强大的恶魔,因为童话书被撕坏了,公主失去了幸福的归宿,魔法无法被破除,花腔女高音只能慢慢逝去了。男孩用pp的极弱力度嗫喏出充满懊悔的情绪。
被置之不理的数学作业也发出了声响。短小有力的节奏在渐强中重复,数字成了喋喋不休地指责的数学老师。孩子彻底崩溃了,发出了绝望的呐喊,屋里所有物件都在和孩子作对。这时,单簧管引领着灵活矫健的猫咪出场了,人声与乐队模仿着或悠长慵懒、或妩媚可爱的猫咪叫声。猫咪既可以休憩于室内,又可以欢跑于户外,是贯穿于两个部分即室内、户外的重要转折点。虽然都在“拟人”,但是室内、户外的角色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在猫咪出现之前,除了男孩以外,场上出现的都是没有生命的、人工做出来的东西;而在猫咪出现之后,场上出现的就都是有生命的角色了。
第二部分的场景变成了户外的花园。对于昼行性生物人类来说,户外的夜晚似乎是寂静的。但是,无论是随风摇曳的树木,还是啁啾的小鸟、鸣叫的青蛙、一掠而过的蜻蜓和蝙蝠,都呈现出勃勃的生机,这让“做尽坏事”的男孩在不安和躁动之下产生了恐惧。这些植物、动物也都遭受过男孩的虐待,男孩希望和他们做朋友,但它们拒绝了他。男孩在孤独中喊出了“妈妈”,他开始求救了。妈妈再如何训斥他,也是能够帮他解决问题的人。动物们发现他也有脆弱的时候,于是咆哮、愤怒地攻击他,一只松鼠在争斗中受了伤。

轻盈、可爱的小松鼠带来了温和与柔美,它唱出了对自由、对大自然的渴望与向往。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孩子也真正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他包扎了松鼠的伤口,在筋疲力尽中昏睡过去。就在这一刻,事情发生了转变。动物们看到男孩有着如此柔软、善良的心灵,改变了对他的态度。它们听到他在叫“妈妈”,于是决定帮助他回家,给他一个改变的机会。它们带着他回到屋里,歌唱着称赞他。男孩唱着“妈妈”,他终于与妈妈、与这个世界和解了。
拉威尔将这部综合了歌剧与芭蕾元素的戏剧称为“幻想抒情歌剧”(A Lyric Fantasy),在芭蕾元素之外,大量吸收了美国音乐剧、讽刺剧等戏剧舞台表演的元素。舞蹈由俄罗斯编舞大师、当时还非常年轻的巴兰钦(George Balachine,1904—1983)设计,巴兰钦也为其注入了大量丰富的风格,比如“中国茶杯”的唱段就运用了狐步舞的节拍与音乐。狐步舞因其创立者福克斯(Fox)而得名,舞步优雅高贵、舒展流畅。1957年派拉蒙影业公司出品的爱情片《甜姐儿》(Funny Face)结尾处,奥黛丽·赫本饰演的女主角身着白色婚纱,与男主角在教堂前的草坪、池塘边翩翩起舞,赏心悦目地在狐步舞中演绎了才子佳人的童话结局——王子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但是,如瓷器般精美的公主,真的会一如既往地精美下去吗?
瓷器是冰清玉洁的,但也是易损的、无法修复的。《孩子与魔法》中的孩子最初拒绝写作业,其实就是在拒绝这个世界,也拒绝成长。正是在中国茶杯的唱段之后,孩子才真正发现自己毁了最心爱的东西。他重复着中国茶杯五声调式的旋律,开始为自己将中国茶杯打碎而懊恼不已,进而也为因书本破损而不能打破魔法的公主真心感到難过。屋内被打破的瓷器的“伤口”是无法复原的,但是在大自然中,小动物的伤口却可以包扎、愈合。孩子的确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然而通过自己的“成长”和别人的“原谅”,所有人的心灵都得到了解脱。

在《鹅妈妈组曲》和《孩子与魔法》中,“中国瓷”的意象表达出作曲家拉威尔心目中永恒的精美。这两部作品展现出“一战”之前与之后的不同时代对“精美”的态度,折射出时光变迁的光泽,充分体现出旧的世界秩序转变至新的世界的精彩。《鹅妈妈组曲》中的童话精致美好,似乎现实总能像童话般,会有一个好的结局;《孩子与魔法》中的现实破碎了,世界被破坏得不可收拾,心灵被残害得伤痕累累,但是信心的重建并非完全不可能。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精美”的化身——中国瓷,是拉威尔不断探索孩童和幻想世界的一枚钥匙。瓷器精致而美丽,这种美好令人欢欣雀跃,但如果不精心呵护,心爱之物也将一去不返。拉威尔笔下的“中国瓷”,深入孩子们心中构成精美的形象,唤起强烈的情感,对成人来说亦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