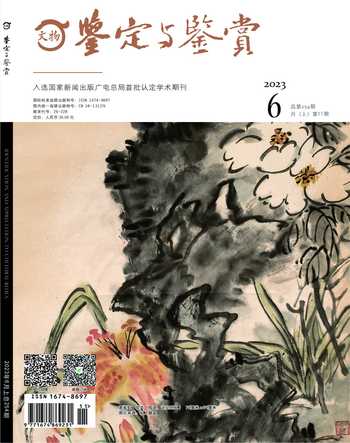唐墓树下人物屏风画的区域性特点研究
吕照青 张泽龙


摘 要:唐墓中的树下人物屏风画以关中地区和太原地区分布最多,因此文章以两地树下人物屏风画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其进行区域性特点分析后发现:两地树下人物屏风画各有特点,主要体现在绘画题材、故事母题、使用者身份、绘画风格等方面;南朝的竹林七贤拼镶砖画、顾恺之的粉本和对现实世界屏风的模拟对树下人物屏风画都有着重要的影响;数量众多而丰富的树下人物屏风画共同起着图画道德鉴戒、标榜墓主德行等多位一体的作用。
关键词:唐墓;屏风画;树下人物图;关中地区;太原地区
DOI:10.20005/j.cnki.issn.1674-8697.2023.11.031
0 引言
中古时期墓葬壁画中出现了屏风画,画工模拟实际生活的屏风在墓室墙壁上描摹出带画框的屏风壁画。唐墓中绘屏风图像继承了北朝壁画墓的传统①,常可以见到屏风画与树下人物这一题材相结合。墓内埋葬空间的墙壁上,屏风画围绕棺床以模拟现实世界屏风的形式表现树与人,这是唐墓屏风画非常典型的图式。因此,虽然树下人物图案从广义上来说具有相当丰富的意涵,可见于世界其他地区、其他绘画媒材之上,但是树下人物屏风画是一个相对狭义的概念,通常所指的是唐墓中屏风壁画上兼有树与人物的图式。
目前,出土树下人物屏风画的区域较广,除了陕西关中地区与山西太原地区最为丰富以外,还有宁夏、新疆、湖北、河南等地也有分布。在关中和太原两个最集中的地区,树下人物屏风画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显示出各自独特的区域性特点及发展脉络。
1 树下人物屏风画的区域性特点
关中地区和太原地区两地的树下人物屏风画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使用树下人物屏风画者的身份、绘画题材、故事母题、绘画风格等方面,两地在独立发展的基础上,又随着传播影响与融合。
1.1 关中地区
关中地区的树下人物屏风画有树下仕女图和树下老人图两种。树下仕女图有的人物褒衣博带,衣袍呈现较为飘逸的圆弧形,属于并非唐代的“古风样式”,称之为古装树下仕女图,女性形象呈现跪坐、行走、似乎与人交谈等行为,可能内含某种故事主题,如李绩夫妇墓和燕妃墓中的屏风画;有的人物身穿唐代女性所穿时服,甚至还有女着男装者,与唐墓中的石椁线刻、墓道壁画影作木构下的侍女形象相似。时服树下仕女图多为女子游玩图像,最早可见于王善贵墓。古装树下仕女图出现于高宗朝,时间较早而后逐渐消失;时服树下仕女图从高宗年间至玄宗天宝年间一直存在,后期数量相对更多,如苏瑜墓、南里王村墓树下人物屏风画,展现了从叙事性图案向装饰性图案转变的趋势。
关中地区的树下人物图开始主要流行树下仕女图,后来加入了树下老人图,如公元708年的韦浩墓发现了目前关中地区较早的树下老人屏风画。树下老人图屏风画加入后,树下仕女图屏风画并没有消失,仍然被使用、流行,二者并行不悖。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苏瑜墓,苏瑜墓棺床附近的屏风画上仍然是树下仕女图,似乎保持了当地的传统,但是在墓室东壁的壁画上出现了非屏风画形式的树下老人图,有可能是太原地区树下老人图传统西传的一个早期反映。结合苏瑜墓中出土的墓志,苏瑜曾为绛州(今山西运城)司士,绛州处于陕西关中和山西太原之间的位置,有可能吸收了太原地区的树下老人图风俗。
关中地区的树下仕女图不见于太原,而树下老人图与太原相比也有些区别,大多只有树与人物两种关键元素,人物多为拱手站立状,形象较为飘逸,此外还有一些飞鸟或山石等装饰性元素。由于缺少榜题及关键元素,难以判别故事主题,这种简化仅保留其象征意义,具有关中的地域特色。
关中地区使用树下人物屏风画的墓主身份大多较高贵,如李绩及其妻、燕妃、韩休等均为唐代上层贵族。关中上层人士使用屏风画,可能还是一种哀荣的体现。《新唐书》和《旧唐书》都描绘了同一个故事,田神功(玉)死后,“上悼惜,为之彻乐,废朝三日;赠司徒,赙绢一千匹、布五百端;特许百官吊丧,赐屏风茵褥于灵座,并赐千僧斋以追福”②,《旧唐书》对此的描述是“哀荣无比”。高级贵族们死后在墓中用屏风画,可能也是一种展示尊贵和身份的方式。
1.2 太原地区
太原地区的树下人物屏风画发现较早且数量较多,主要依托北壁配置于东西向棺床之后,这一壁画配置模式也被称为“太原模式”③。太原唐墓中的屏风画基本上均为树下老人图,缺少关中的树下仕女图屏风画。而树下老人图屏风画除了树与人物两类基本的绘画元素以外,还有一些关键元素,如笋、蛇、坟墓、斧头、云等,用以指示图像所代表的的故事主题。相似的图式组成元素背后往往指向同一故事母题,常见的故事有孟宗哭笋、王裒(蔡顺)泣墓、季札挂剑等。太原地区墓中树下人物屏风画选择的故事比较一致,整体呈现也比较程序化,在影作木构下绘屏风式树下老人图:许多树下人物皆着宽袍大履,头戴莲花冠或者方冠,形象十分相似;图案排布可以看出明显的相似甚至雷同,各种元素杂糅、组合。但是在这一背景下,也有的屏风画故事一致而呈现不同版本的图画④。如经考证为“渊明嗅菊”的树下老人图(也有蔡顺为母采椹、食芝草的说法),其中郭行墓、金胜村M4和焦化厂墓较为相似,而与金胜村M6有着明显不同,主要体现在人物的身形、元素中多了飞鸟、山石描绘方式不同等,这样的不同推测可能是因为有两种不同的粉本或画工群体(图1)。
太原地区的树下老人图较单一且持久。太原地区使用树下人物屏风画的墓葬墓主,应具备一定政治、经济实力。经考证,树下人物屏风画墓葬集中的金胜村为初唐胡裔贵族墓地,胡裔贵族曾随李渊建功立业,因此他们的墓葬或在墓葬规模,或在墓葬壁画内容,或在随葬品等方面都得以使用超越其政治等级的规格⑤。在功成身退后,他们选择以孝义、仁爱、归隐等题材来对自我立场进行剖白,也对自身德行进行标榜。
与关中地区一样的是,太原地区的屏风式树下人物图缺少榜题,并在形式上追求图像的同一性而可能回避故事情节的高潮,榜题的缺少和一些图式元素的简略造成难以释读的情形,使这类屏风画达到帮助墓主升仙的作用⑥。树下的人物身份可能有孝子、高士、隐者、仕女等,这些人物作为集合式的肖像变成墓主升仙途中的同道者或伙伴,共同构建升仙图像系统⑦。有的人物呈現飘飘欲仙的姿态,有的头戴莲花冠、方冠,以及绘画中与长寿成仙有关的仙桃⑧等元素,可能都和道教成仙思想有关,画面以此来营造升仙的氛围,以帮助墓主人逝世后及至永生世界。
2 树下人物图式的来源
唐代之前仅以树与人物为构图元素的广义树下人物图式就已广泛存在,如:汉画像石中孔子拜老子图、射侯取爵图、仙人王子乔与浮丘公图;北朝葬具以树下人物模式表现《孝子传》;甚至树仅仅只作为装饰图案之一,陕西旬邑百子村壁画墓中,绘有女性人物立于树下,旁有榜题“亭长夫人”。如此广泛地存在,是因为树在图像中常能分隔画面、进行装饰,以及古人对树木的圣树崇拜和树有象征德行的含义。山东莒县东汉石阙上刻有许多历史人物,其中尧、舜坐于树下,而背后刻画树木的搭配不见于该石阙中其他历史人物,可知圣贤常与树木搭配⑨。
关于树下人物图式源流的探究,学界多普遍认为树下老人图源自南朝的竹林七贤题材图式,典型例子为南京西善桥墓中的拼镶砖画,虽然不是屏风画,但是确实为典型的树下人物图,树木既是隐逸之志的象征,又起到区隔画面的作用。北朝崔芬墓和八里洼墓将树下人物这一题材置于屏风中展现⑩。太原地区的树下老人图直接继承了东魏北齐壁画墓中这一传统,分屏单幅成像,进一步汇集孝义、仁爱、归隐避世等传统历史文化题材作为屏风画的题材,传播至关中地区后逐步简化,仅保留树和人物两个关键构图元素(图2)。关中地区古风列女屏风画,在图式、服装上与司马金龙墓木板漆画中的仕女较为相似,同时与目前我们所见到的顾恺之摹本《列女仁智图》(图3)、《女史箴图》等绘画很像k,考虑到使用该类屏风的墓主身份高贵,可能借鉴了顾恺之的粉本,同时也借用了一些故事母题。《历代名画记》卷二中记载:“好事家宜置宣纸百幅,用法蜡之,以备摹写。(顾恺之有摹拓妙法)古时好拓画,十得七八,不失神采笔踪。亦有御府拓本,谓之官拓。国朝内库、翰林、集贤、秘阁,拓写不辍。”l名画家有拓本流传不足为奇,后世的画匠很有可能借鉴了这些画家的拓本。绘画《列女图》的传统可以上溯至汉代,这或许也是唐代列女屏风壁画图像古意浓厚的间接原因。而身穿时服的仕女屏风画相较于前者,装饰性更强,带有强烈的享乐色彩。女子形象身穿唐代衣饰,与唐墓天井过洞、墓室等壁画和石椁所刻画的现实女子形象十分相似,可能直接模仿了现实世界的仕女画作,将其与屏风相结合,如韦慎名墓中的树下骑马仕女可能为盛唐流行的鞍马人物画题材之翻版m。
3 鉴戒与溢美:树下人物屏风画的作用
汉代之后,屏风逐渐成为具有自省教化作用的最主要鉴戒载体之一,并同时向公众进行展示。
屏风凝聚道德鉴戒意义后,在私人领域空间中观看并省诫。西汉时文献中已經记载列女图屏风的鉴戒作用,中古时期继承了这一传统,《旧唐书》中记载:“太宗尝命写列女传以装屏风,于时无本,世南暗疏之,不失一字。”n唐太宗下令将《列女传》装于屏风,其目的在于自省与鉴戒后妃。同样可以印证屏风劝诫作用的还有《新唐书》中的记载:“(玄龄)治家有法度,常恐诸子骄侈,席势凌人,乃集古今家诫,书为屏风,令各取一具,曰:‘留意于此,足以保躬矣!”o谢赫《古画品录》和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两本重要的画论作品均在开篇就将图像的道德教化功能放于首位。比起在屏风上书写的文字,绘制叙事性鉴戒画的优点非常明显:图像较文字更直观易懂,观者完全可以通过画面了然图像属于其所熟悉典故的哪一故事情节,真正起到了道德鉴戒的作用。唐代墓室空间是对现实建筑的模仿,棺床象征的坐榻与屏风共同形成墓主所用的围屏床榻,模仿了墓主生前的内宅场景。《历代名画记》中曾记录现实中画家绘有《列女仁智图》屏风、孝子屏风等作品,因此墓中屏风画可能模仿了地面屏风的内容题材和装饰手法p,现实生活中人们对屏风画的青睐可能影响到了墓内空间的陈设。墓室中的树下人物屏风画可能直接来源于对现实生活中屏风的模拟,同时也继承了现实屏风中的鉴戒作用。
唐代墓葬中的屏风画对营造礼仪空间与丧葬空间有着特殊的作用,丧葬空间以屏风画为装饰,与棺床具有明确的组合关系q。屏风壁画上的树下人物与墓主人相互联结,在视觉和意义上建立起画像与死者之间的联系r,将墓主形象代入人们耳熟能详的典故中以宣扬墓主品德崇高、德厚流光。如燕妃墓中的列女图屏风,考虑到墓主的女性身份,赞美了燕妃奉行儒家女德规范,展现了对墓主人德行的颂扬。而李绩夫妇墓同样选择树下列女图,则可能是因为李绩妻早于李绩亡,棺床后的屏风画有可能是为先去世的李绩妻所准备的。总的来说,屏风画以其独特的方式展现着墓主人的德行品质,通过孝子、高士或列女等图像来表明对墓主人的溢美,墓主人也通过屏风式树下人物图来进行自身德行的标榜、自我立场的剖白,此外还有帮助墓主升仙以及展示身份、家族后人孝行多位一体的作用。而随着屏风画的不断发展,叙事性的树下人物图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装饰型图案不断增多,后期数量更多的时服仕女屏风画正迎合了叙事性减弱而装饰性增强的趋势,屏风画的鉴戒教化及标榜自我的作用也逐渐式微。
注释
①李星明.唐代墓室壁画研究[M].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162.
②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3533;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4703.
③王炜,张丹华,冯钢.赫连山、赫连简墓壁画的绘制、描润与配置:兼谈唐代壁画墓的“太原模式”[J].文物,2019(8):72.
④张丹华.太原地区唐墓壁画研究[D].太原:山西大学,2020:35-38.
⑤沈睿文.太原金胜村唐墓再研究[M]//沈睿文.墓葬中的礼与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259.
⑥贺西林.道德再现与政治表达:唐燕妃墓、李绩墓屏风壁画相关问题的讨论[M]//贺西林.读图观史:考古发现与汉唐视觉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110.
⑦郑岩.南北朝墓葬中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画像的含义[M]//郑岩.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203-211;郑岩.北朝葬具孝子图的形式与意义[M]//郑岩.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295.
⑧赵伟.山西太原赫连山墓“树下老人”图试读[M]//贺西林.汉唐陵墓视觉文化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244.
⑨林圣智.中国中古时期的墓葬空间与图像[M]//颜娟英.中国史新论:美术考古分册.新北:“中央”研究院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0:184.
⑩杨泓.北朝“七贤”屏风壁画[M]//杨泓,孙机.寻常的精致.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118-122.
k陈志谦.昭陵唐墓壁画[M]//陈全方.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一辑[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117;巫鸿:中国墓葬和绘画中的“画中画”[M]//上海博物馆.壁上观:细读山西古代壁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310-311.
l张彦远.历代名画记[M].南京: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07:50.
m冯筱媛.论唐墓屏风式壁画“树与人物”题材的母题与来源[J].宁夏社会科学,2015(6):165.
n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2566.
o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3857.
p赵超."树下老人"与唐代的屏风式墓中壁画[J].文物,2003(2):74.
q李梅田.唐代墓室屏风画的形式渊源与空间意涵[M]//贺西林.汉唐陵墓视觉文化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105-129.
r郑岩.北朝葬具孝子图的形式与意义[M]//郑岩.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2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