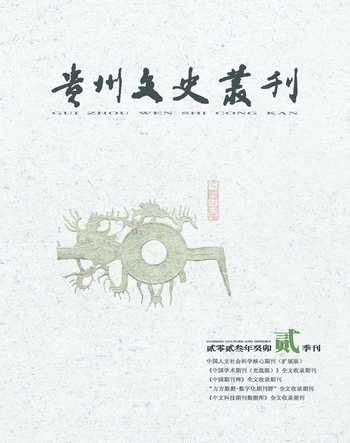历史时期云南境内的马种演变与坝区农业转变
耿金
摘 要:元代以前历史文献中多记载云南境内盛产善于奔跑的名马,从汉代文献中的“滇池驹”到唐宋时期的“越赕骢”“大理马”,皆为体型俊美之骑乘马匹。元明以后,文献中记载的“云南马”以善行山路、驮物为主,并最终形成明清时期对云南马的认知形象。马种的交替演变,背后的原因是云南坝区农业生产方式在元代以后发生根本性转变,即坝区由元代以前的畜牧、农耕并重,到元明后以农耕为主,饲养良马的土地资源农田化,此过程也伴随着坝区饲养马匹的民众因农业生产方式的差异而向山区转移。农耕经济对于马匹役力的使用更强化其驮物功能,故体型略小的“云南马”在元明以后成为云南地区的主要役力马种。这一过程随着清代农耕向山区推进而形成“云南马”在山区使用普及化,由此改变了云南马种的分布格局。
关键词:滇池驹 越赕骢 大理马 云南馬 坝区农业
中图分类号:K8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23)02-34-42
一、引言
元代以前,许多历史文献中都有云南地区盛产名马的记载,无论是汉代的“金马”形象,还是唐代樊绰《云南志》中记载的可日行五百里的“越赕骢”,以及宋廷曾向大理购买马匹作为战马的记载,都说明历史上云南地区曾经出产过名马。这种名马以“善奔跑、体健硕”而著称,在云南地区乃至西南地区历史上的经济社会发展变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元代以后,云南地区的名马记载就较少出现了,被史料记载的马匹多是体格较小,善行山路,主要用于搬运物资的役力家畜。那么,是云南地区马匹品种的基因发生了转变?还是这种名马自我消亡了?回答此疑问即为笔者撰写本文之原因。经过阅读有关史料,笔者认为,这种变化还不能完全从动物自然种群演变史的角度进行解释,而需要关注其背后农业生产方式转变的进程、内在驱动因素,以及地方民众驯养情况等多重因素。
从考古学、历史学方面研究的成果看,早期云南境内的马匹品种并非明清时期西南地区普遍使用的小马。张增琪从考古学的角度进行研究,论证了云南境内早期马种与北方草原马种的关系密切;李晓岑对唐、宋时期的云南马种进行了研究,认为当时云南地区商人贩卖给宋廷的马匹基本为西蕃马。1但是,已有的研究并未对元代以后云南马匹为何变化的问题进行讨论。除历史学者的研究外,动物学主要关注历史上云南境内马匹的种属问题,认为历史上云南地区的马种是一种中等偏小、具有许多原始性质的单独马种。1此外,一些研究者将云南地区的马种纳入到“西南马”的范围,并认为“西南马”有多个母系起源,且与蒙古马亲缘关系较近,部分西南马起源于普氏野马或蒙古野马,2等等。总体而言,已有研究成果大多并没有解释历史上云南马匹演变的细微过程以及背后的深层原因。对云南坝区农业转变的历史过程,仍缺少对其细致转变过程的研究与展现。本文通过对历史上云南典型马种的长时段演变考察,分析云南农业发展史、区域经济与社会演变史、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史,以期为学界的深入研究提供参考。
二、元代以前的高原名马
(一)滇池及周边地区的“滇池驹”
目前所见,历史文献中记载的云南地区最早的名马称“滇池驹”。“滇池”一词最早出自《史记》。《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载了古滇国位于滇池之滨,乃楚国将领庄蹻率兵进入滇池流域后,收服整合而成,“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3。而春秋战国时期的滇国大致到东汉后期就从滇池流域“消失”了。张增祺言:“滇国出现的时间不晚于战国初期,战国末期至西汉早期为其鼎盛时期,西汉中期以后开始衰落,西汉末至东汉初在云南历史上逐渐消失,东汉中期以后滇国已完全销声匿迹了。”4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云南的历次考古发掘中,春秋战国时期的滇国逐渐被世人所了解,出土了大量文物,诸如“滇王金印”等,印证了司马迁记载的可靠性。而在出土的大量古代文物中,马的形象是比较多的。在两汉时期的历史文献中,也多次出现滇池流域盛产名马的文献记载。如东汉光武帝时期,汉廷派刘尚攻打益州郡少数民族头领栋蚕,获得马三千匹;又如《华阳国志·南中志》中记载,诸葛亮平定南中后,令当地提供“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给军国之用”5。从这些史料中可以看出,历史上的云南不仅盛产马匹,而且盛产战马。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历次考古发掘中,云南各地出土了大量铸有马匹的青铜器,这些马匹多数出现在当时的战争和狩猎场景中。春秋战国时期,云南的不少地方都有驯养马匹之风,在江川李家山墓地中出土一件贮贝器,盖子上就有驯马场面,在同一地方出土的青铜器中,还有诸多马具等。此外,此地出土的战国时期马具从制作工艺上看还相对原始,没有出现络头和马衔等装饰配件,青铜器图像中的乘马人手中有缰绳,但是直接系在马口中,马背上也没有鞍件,仅有较长的坐垫。到了西汉中期,渐渐出现了变化,马具开始逐渐完善,有额带、鼻带、颊带和咽带皆备的络头,还出现衔、镰、鏑组成的马衔,以及鞍垫、攀胸、后鞦、腹带齐备的马鞍和相应的带扣、策子等铜质饰件。进入西汉中晚期后,出现了马的防护用具“面帘”和“当胸”。同时,在西汉中期,云南境内一些地方的战马上已普遍使用马镫。在云南发现西汉中期青铜器上的马镫图像,是目前我国也是世界上发现的最早和最原始的马镫。张增祺认为,云南早期的居民多骑马而不乘车,马具中的攀胸、后鞦齐备的马鞍与马镫都是由当时居住在山地的民族发明的,后来才逐渐向平原地带推广。1因此,早期云南境内的马匹,更多是以作为乘骑之用的战马形象出现的。
由上述可知,早期云南地区的马匹主要作为乘骑之用,以擅长奔跑为主要特点。《华阳国志》中记载了日行五百里的滇池驹:“池(滇池)中有神马,或交焉,即生骏驹,俗称之曰‘滇池驹,日行五百里。”2郦道元《水经注》中记载为:“池中有神马,家马交之则生骏驹,日行五百里。晋太元十四年,宁州刺史费统言:‘晋宁郡滇池县,两神马一白一黑,盘戏河水之上。”3受此影响,唐代以后的历史文献几乎都记载为“神马与家马交,则生骏驹,世称滇池驹。”4这些记载正如任乃强先生所说,是民间神话传说,但神话传说的背后也折射出滇池良好的水土环境为出产良马提供了自然条件。《南中志》载:“夫马、龙异类,不可能媾交,何得云龙驹?只缘河湖岸草美,而风浪能激励马志,故成良马种也。”5言下之意,滇池边的马匹因当地水草丰美,加之风浪之故,所以能成为优良品种。而滇池流域的“金马碧鸡”神话传说,也说明当地确实曾经出产过名马。
(二)越赕骢与大理马:唐宋时期的云南名马
唐宋时期,云南地区的马匹不仅十分有名,而且在当时的军队中大量配备,樊绰在《云南志》6中有如下描述:
马出越赕川东面一带,岗西向,地势渐下,乍起伏如畦畛者,有泉地美草,宜马。初生如羊羔,一年后纽莎为拢头縻系之。三年内饲以米清粥汁。四五年稍大,六七年方成就。尾高,尤善驰骤,日行数百里。本种多骢,故代称越赕骢。近年以白为良。藤充及申赕亦出马,次赕、滇池尤佳。东爨乌蛮中亦有马,比于越赕皆少。一切野放,不置槽枥。唯阳苴哶及大釐登川各有槽枥,喂马数百匹。7
越赕,又名腾越,在永昌以西,过高黎贡山而后至。唐代称敕化府,宋代改为腾冲府。8当时的这种良马主要产于腾冲以东地区,多为杂毛马,这种杂毛马称“骢”,《说文》言:“骢,马青白杂毛也。”9从历史文献看,这是一种毛色黑白相间的马匹。除澜沧江以西的腾越地区以外,滇池流域的马匹质量也很好。当时云南境内的马匹几乎都是野外放养状态,不设马槽,半野生,只是在大理洱海周边地区有设槽圈养。这表明在当时的云南,不仅有许多地区产良马,而且不少坝区有大片野生草场。
到了唐代,云南地区擅长驯养马匹与骑马的族群主要是“望苴子”。《云南志》载:“自澜沧江以西,越赕、扑子,其种并是望苴子。俗尚勇力,上又多马。”10《云南志》对“望苴子”的情况有详细记载:“(望苴子)在澜沧江以西,是盛罗皮所讨定也。其人勇捷,善于马上用枪,所乘马不用鞍。跣足衣短甲,才蔽胸腹而已。股膝皆露。兜鍪上插犛牛尾,驰突若飞。其妇人亦如此。南诏及诸城镇大将出兵,则望苴子为前驱。”1笔者从史料中对比分析发现,这种跣足骑马形象与云南省博物馆中的青铜骑马形象十分吻合。因此,如此质地優良的马匹自然会被资以军用。木芹言:“南诏常备军中有精兵,望苴子为其中之突出者。”2从历史文献看,在当时的军队中,马军是必备的配置,而这些马军基本上是寓兵于农,官府不负担军队开销,遇有战事则征召参战。《云南志》卷九言:“战斗不分文武。无杂色役。每有征发,但下文书与村邑理人处,克往来月日而已。……每家有丁壮,皆定为马军,各据邑居远近,分为四军。以旗幡色别其东南西北,每面置一将,或管千人,或五百人。四军又置一军将统之。”3历史文献中记载“每家有丁壮,皆定为马军”,在《新唐书·南诏传》也有类似记载“壮者皆为战卒,有马为骑军”4,即有马匹的人家可作为马军。木芹先生认为,这些军队其实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常备军,数目不多,但却是主力,人数大概常年在三万左右5;二是寓兵于农部分,平时农耕,并以村邑为单位,以战时的方式编制起来,农闲加以训练;三是征调军,被征服的边境部族,以开南、丽水及永昌三节度为多,诸如扑子、寻传、黑齿等。6“望苴子”既尚勇,当地又多良马,所以成为当时军队中的主力。
据史料记载,在当时的军队中,马军的攻击力是很强的,训练也极为苛严,既要求熟悉射箭、弄刀、耍枪,还要能记算书写。在当时的城镇乃至乡邑,大都会在空地上立一柱子,农闲时有马的人就会骑马围绕柱子练习刺杀,“每农隙之时,邑中有马者,皆骑马于颇柱下试习”7。每年十一、十二月农忙后,兵曹长就带着文书巡查其境内诸城邑村谷,“各依四军,集人试枪剑甲胄腰刀,悉须犀利,一事阙即有罪。其法一如临敌。布阵罗苴子在前,以次弓手排下,以次马军三十骑为队。如此次第,定为常制。临行交错为犯令”8。
到了宋代,虽然史料文献记载较少,但仍有不少中原地区与大理进行马匹交易的记载。比如,北宋由于有北方辽国的军事威胁,一直在各地大量购买马匹用作战马,以提高其军队的作战能力。宋廷购买的马匹主要有两种,即战马与羁縻马,战马主要从陕西、四川、广东等地购买,而羁縻马主要产自西南地区,体格短小。9《宋史》载:“故凡战马,悉仰秦、川、广三边焉。”10北宋时的军队战马以西北马最多,其次为川西的马;南宋以后,陕西马来路断绝,所依赖者,川马、广马为主要。11宋代洪迈言:“国家买马,南边于邕管(治今广西南宁),西边于岷、黎,皆置使提督,岁所纲发者,盖逾万匹。”12但由于山路崎岖,在四川购买的战马数量没有在南边的两广购买的多。据相关史料显示,宋廷在这两个地方购买的马匹,其实大都来自云南。周去非在《岭外代答》提出,南方诸马“皆出大理国,罗殿、自杞、特磨,岁以马来,皆贩之大理者也。”1《玉海》也载:“今之买马多出于罗殿、自杞诸蛮,而自彼乃以锦彩博于大理,世称广马,其实非也。”2这两条记载,是比较可信的,不仅如此,在这些记载中,还列出了来自大理的马匹与两广本地所产马匹的区别,称广马出自岭南者,体格较小,质量不佳,“岭南自产小驷,疋直十馀千,与淮、湖所出无异”。因此,在市场上交易量价均高,颇受购买者青睐的,更多是质量较佳的大理马。在当时,大理马也被称为“西马”,文献史料记载:“大理连西戎,故多马。虽互市于广南,其实犹西马也。每择其良赴三衙,馀以付江山诸军。”3从当时的情形看,产自云南的马匹是直接可以选配到军队里的。
宋代云南地区出产的马匹被视为西南诸马中的上品,在不少历史文献中都有记载,如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中就曾提到过大理马:“出西南诸蕃,多自毗那、自杞等国来。自杞取马于大理,古南诏也。地连西戎,马生尤蕃。大理马,为西南蕃马之最。”4周去非也曾对当时的南北方马匹的特点有过评价,他说:“南马狂逸奔突,难于驾驭,军中谓之拼命抬。一再驰逐,则流汗被体,不如北马之耐。”5从整体上看,南马狂逸奔突,不好驾驭,而且奔跑后容易出汗,耐力不如北马。但如果遇到南方马中质量较优者,则北方马又不可能与之相比,“然忽得一良者,则北马虽壮,不可及也,此岂西域之遗种也耶?是马也,一匹直黄金数十两,苟有,必为峒官所买,官不可得也”6。以此观之,当时大理的越赕所产马匹,被认为是南方马匹中的上品,当地人也将其称为“座马”,“座马,往返万里,跬步必骑,駞负且重,未尝困乏,……日驰数百里,世称越睒骏者,蛮人座马之类也”7。从以上史料上看,越赕所产之马,在当时不仅价格昂贵,而且耐力极好,颇受当地人喜爱。
三、元明以后的云南马匹形象
元代以后,西南地方文献中关于唐宋时期“名马”的记载似乎就一下“消失”了。明清时期文献中记载的云南马,更多是体型较小、善于奔走山路的马匹。这让不少人产生疑惑,为何同样产于云南的马,在唐宋时期以善于奔跑见长,到了明清以后却变成了以善驮运见长呢?通过查阅资料和实地了解,笔者认为,云南地区明清时期以善于驮运见长的马匹与唐宋时期以善于奔跑见长的马匹并非同一品种。对此,研究云南马匹历史的学者较少有过关注,一般都将早期文献中记载的滇池驹、越赕骢与后期的西南马皆视为云南马。为了不致引起叙述上的混乱,本文将史料所载元代以前善于奔跑的马匹以本名称呼,如“滇池驹”“越赕骢”“大理马”,而将明清以后体型较小、善于山路行走的马匹称作“云南马”,明清以后的文献所记载的,多是这种善行山路、体型较小的马匹。
到了元代,马可波罗从滇池(鸭池城)地区向西骑行十日后到达大理城,他在此行的《行纪》中曾提到,云南洱海流域有一种体形高大的骏马。当时的大理城属“哈剌章州”(即明清时期的大理府),马可波罗到达该州后,在其记载中是这样描述的:“亦产良马,躯大而美,贩售印度。然应知者,人抽取其筋二三条,俾其不能用尾击其骑者。尚应知者,其人骑马用长骑(montent long)之法,与法兰西人同。”1其中所提到的“抽取其筋二三条”的养马习俗,正是当地人为了让马尾高高翘起而使用的方法。而《云南志》中提到的越赕骢,也是尾高而“尤善驰骤”的。以此观之,《云南志》和《马可波罗行纪》中关于大理骏马的体形描述是很一致的。有学者针对《马可波罗行纪》中所记马匹体型描述,指出:“‘大而美之马,疑为传写之误。广西高地及云南省中固产健马,然其躯小而健,故玉耳以为其文应改作多数之马。”2这种说法或许并不准确。由以上史料可知,元代以前,云南境内的马匹虽然整体上不如北方马高大,但体格不算小,而且善于奔跑,完全不是后来有的资料中所指的那种明清时期的体型矮小、善行山路的“云南马”。认为马可波罗所见“驱大而美”的马是记载错误,其实是对当时马匹认知的错位。
笔者查阅有关史料,历史上云南境內的马匹有多个亚种,在动物学分类上将其统称为“西南马”。但即使在“西南马”种属内,也存在两种明显不同的马种,可能是由于称呼上的习惯,有的学者将这两种马混为一类,将历史上云南地区的马匹种类皆视为“西南马”。李晓岑曾提出,唐宋时期云南境内的“大理马”属于西北马种,并非当时西南地区躯干矮小的“羁縻马”。“大理马”不仅躯体高大,当时经常被用作战马,还通过贵州等地输送到广西市场上出售,成为宋王朝重要的马匹来源。3这一观点笔者是认同的,但李晓岑并未解释宋代以后云南的马匹为何变成了“羁縻马”。对此问题,笔者通过分析研究认为,唐代的“越赕骢”、宋代的“大理马”,都是云南马的另外品种。动物学的研究也显示,腾冲境内的腾冲马应该即为唐代的“越赕骢”后裔,这种马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调查中还显示有明显的草原马种特征,马匹体格粗壮结实,头比较大,体躯较深广,腹部膨大,四肢粗实,关节明显,健肌发达。4从目前对云南境内的名马记载看,汉代至元代是一个连续性阶段,而元代以后,这种名马就逐渐减少了。
明代文献中仍有提到过这种善于奔跑的马,不过从马匹活动区域上看,应当是集中到了滇东的陆良地区。正是由于马匹活动区域的转移,历史上出产骏马的滇池流域和大理地区,就很少再出现这种善奔跑的名马的记载了。因此,有关历史文献只有在介绍陆良地区民间风俗时,才会提及此种马匹。有明一代,陆良坝区一直是云南良马的产地,这是因为当时的陆良坝区有大片的湖泊水域,据景泰《云南图经志》记载,陆良坝区有被称为“中埏泽”的湖泊水域,“中埏泽,在州治(陆良州)东丘雄山麓,宽衍六十馀里,有一十八泉注其中,而潇湘之水5亦入焉。鱼虾甚富。其傍地为牧马场,而所产多良马,亦其土地之所宜也”6。这一水域为陆良的马匹生长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明清以降,随着当地湖水的逐渐干涸,这种养马的自然条件逐渐消失了。明代的陆良坝区,是汉族和少数民族共同生活居住的地区,但存在少数民族向山区转移的趋势,当地世居的少数民族在史料上多被称为“罗罗”,当时他们的人口数量占当地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居止多在深山,虽高冈硗垅,亦力垦之,以种甜、苦二荞自赡。又以畜马为生,牧养蕃息,剔去尾骨二节,谓之雕尾,以此为贵。刻木为鞍而无?,剜木为镫,状如鱼口”1。此种“风俗”在万历《云南通志》中又被原样记入。2明代的陆良地区与唐宋时的大理地区在养马方法上基本没有变化,仍习惯“剔去尾骨二节”。沾益、陆良周边的民众与剑川地区的民众均以养马为生,在马的驯养方式上也完全相同。史料记称剑川山后的民众“尤为犷悍……与沾益州同俗”3。
在元代及以前的文献中,我们更多关注的是善于奔跑的马匹,以“滇池驹”“越赕骢”“大理马”为主,不太留意善于行走山路的马匹,这当然是文献记载的偏向导致的,但文献记载偏向善奔跑的名马,证明这种马无论是在饲养数量还是在利用上,在当时都是很重要的。对后一种马匹,其实汉代文献中早有记载,以“筰马”为代表,只是长期没有成为文献记载的重点。《汉书》载:“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关蜀故徼。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筰马、僰僮、旄牛,以此巴蜀殷富。”4“筰马”今称“西昌马”,躯干较蒙古马、西宁马为小,善走山地。5明清时期,这种马匹在云南山区极为普遍,是山区民众的主要畜力。在明清以降的历史文献记载中,云南境内的马匹基本上被描述为整体体型矮小,多以“驮马”出现,善于在山路负重行走。清初刘崑在《南中杂志》中言:“滇中之马,质小而蹄健,上高山,履危径,虽数十里而不知喘汗,以生长山谷也。上山则乘之,下山则步而牵之,防颠踣也……上下山谷,皆任骑坐,则百不得一也。而其中又有高大神骏,远过西马者,则千不得一也,此种异物,甚为土司所珍,亦甚为土司之累。”6这些历史文献记载让人觉得,云南境内体型较小之马较多,高大良马少见。
到了晚清,相关历史文献记载中的云南马,也更多为小马形象。清末,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在云南、贵州考察,在贵州他记录了当地的马匹情况:“然贵州、云南所产马匹,遗传下古时苗族饲养的特殊能力而不同于普通中国马匹,这在中国旧方志上也屡有记录。直到现今,山区的苗族仍都利用马匹,最适应山间行走。”7“途中与数十匹马群相遇,仅几名马夫带领,一声吆喝便都自己行走,颇驯服。一眼看去马匹非常温驯,与日本马大相径庭。这些马匹均为驮马,用于云贵之间的货物驮运。我曾读过一些关于中亚或云南周边的旅行记,知道这些马的存在。然第一次亲眼目睹,却是在此次旅行中。”8进入云南后,鸟居龙藏对云南府市场上交易的马匹印象深刻,他说:“(此种马匹)为云南特有之物产,在中国历代文献中,皆记载过去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多饲养马匹之事,然至今仍普遍饲养。这些马相比山西马稍小,较驴大,且性格温驯,最适合旅行骑乘。无论多么崎岖陡峭的山路,只要骑上它,就可以通行无阻,可谓是奇珍异宝。”9这些记录说明,马匹在当时西南山区民众的生产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旅行中,鸟居龙藏也多次称赞了云南马在山区的行走能力:“山路极险峻,坡面陡急,路边到处都横躺着滚下的石头。在如此崎岖险峻的山路上,我仍然骑马而行。并非因自己骑术高超,而是骑乘为云南马,日本马是不可能在此攀援的。”10当然,鸟居龙藏记录中所提到的这种清代西南马善走山路,与唐宋时期的名马有所不同。
四、坝区农耕化与役用马匹的转变
如上所述,云南历史上元代以前记载的高原“名马”,并非明清以后善于行走山路、体型矮小的云南小马。从马种上看,前后两种马并不存在种群进化关系,各自属于不同的品种。元代以前云南农业经济中主要是畜牧业,特别是平坝地区的畜牧业占非常重要的地位,所畜养的马匹更多被骑乘之用,文献中所记载的也更多是这种善于奔跑的名马形象;明代以后,云南文献中被记载的善走山路、以驮物为主的小马,其实是另外一种云南马,上文中所提及的《汉书》中记载的“筰马”就基本属于此类马种。出现这种马种上的“转变”,笔者认为,这与元代以后云南的农业经济转型有极大关系,随着坝区农耕环境变化,加之人们对马匹使用的偏向发生转变,导致历史文献中前期更多记录的是善于奔跑的高原名马,而后期更多关注的是善于在山间行走、以驮运见长的云南小马,即人们对马匹役用重心的转变与农牧环境的变化,引起了云南马匹种群的演变。当然,这种演变并不是指马匹种群的自我进化,而是由于人们农耕方式与役用马匹的重心转变而导致早期善奔跑的马匹在数量与分布区域上,逐渐缩减甚至是消失了。
元代以前,云南的坝区由于水草条件良好,但农业耕种技术尚未普及,所以民众大多以畜牧业为生,马匹是其驯养的主要品种,而且这些马匹大多数是野外放养,这种优良的畜牧环境,为宋代云南境内马匹大量进入中原地区奠定了基础。元代以后,更多先进的农业耕种技术逐步从中原、江南等地传入,使当地的农业生产模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这种生产模式的转变首先是从滇中、滇东的坝区开始的。以“海”或“海子”的命名为例,这种称谓最早出现在元代以前的北方地区,1后来却在云南地区广泛使用,笔者结合相关史料分析,基本可以肯定,这是大量北方地区的汉族人口进入云南地区从事农业耕种的结果。因此,云南坝区的众多湖泊,逐步开始以“海”或“海子”命名。到明代以后,这种命名方式已成为了本地的习惯。明代天启《滇志》中载:“滇俗,潴水处皆称海子。”2笔者在国家地名信息系统中检索以“海子”命名的地名,共有四千三百九十五条,其中云南省就有一千五百九十二个,其次是四川省八百一十一个,贵州省五百八十四个,内蒙古自治区三百三十三个,陕西省一百七十六个,山东省一百五十八个,甘肃省一百四十一个,宁夏回族自治区一百一十八个,其馀各省区数量则在个数至数十个不等。从分布地区看,西南“海子”最多,几乎占到三分之二,尤其以云南最多。在云南境内,“海子”地名主要分布在曲靖市(五百七十九个)、昭通市(三百九十九)、昆明市(一百六十五)、大理州(一百一十九个)、楚雄州(一百一十八个)、文山州(五十三个)、丽江市(三十八个)、保山(二十六个)、普洱市(二十六个)。3可见,云南称“海子”的地名集中在滇东、滇中及滇西大理、丽江附近。而明代军事屯垦移民主要集中在坝区,这进一步推进了坝区农耕化进程。而云南南部的傣族先民聚居区,却很少有以“海子”命名的。
五、结语
综上,推动历史时期云南马种交替演变的,有以下驱动因素:一是坝区由畜牧业逐渐向农耕转变,农耕与畜牧饲养马匹形成了资源竞争关系;二是畜牧业向农耕转变后,对于马匹使用的定位也出现了转变,即从用于骑乘向用于驮物转变。此外,农耕向山区推进,也加速了山区矮小的“云南马”的普及化,最终形成元代以后,云南马种利用上的交替演变。元代以前,云南境内的坝区虽有一定范围的水田农耕,但在农田周边有大范围的牧草地带,这是当时云南境内畜牧业的重要资源;元代以后这种情况急剧变化,特别是明代的移民屯垦主要集中在坝区,使坝区农耕化程度进一步提高。本质上看,元代以前云南境内以畜牧业、农耕业并重,甚至在滇东、滇中、滇西的大片坝区,畜牧业占主导;元代以后随着坝区农业的开发,明清时期汉族移民的大量进入,确实存在农耕上山的问题,这与前期的山区水田化背景的内在机制有所不同。对于云南境内的土地利用问题,元代以后的坝区农耕化,也直接导致了坝区畜牧资源被压缩,使得元代以前善于在坝区奔跑、饲养的名马,到明代以后逐渐让位于役力使用的驮马,即所谓善于行走山路、善驮重物的马匹成为云南马的典型代表。
The Evolution of Horse Specie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Plain Agriculture in Yunnan during the Historical period
Geng Jin
Abstract:The most of the documents before the Yuan Dynasty recorded that Yunnan was rich in famous horses that were good at running, from the "Dianchi Ju" colt in the Han Dynasty to "Yue Dan Cong" and "Dali Horse"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After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Yunnan horses recorded in the literature were mainly "Dian horses", which were mainly good at walking in mountain roads and piggybacks, and finally formed the cognitive image of Yunnan horse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The core factor behind the alternating evolution of horse species is the fundamental change in the mod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the dam area after the Yuan Dynasty, that is, from animal husbandry and farming before the Yuan Dynasty to farming after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and the land resources of raising good horses are turned into farmland, and this process is also accompanied by the transferring of ethnic minorities who raise horses in the plain areas to the mountainous areas because of different farming methods.The farming economy put more emphasis on the burden function of horses, so the smaller "Yuannan horse" became the main service horse breed in Yunnan after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This process promoted the popularization of the use of "Yuannan horse" in the mountain areas with the advance of farming to the mountainous areas in the Qing Dynasty, which further strengthened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Yunnan horse breeds.
Key words:Dianchi Ju;Yue Dan Cong;Dali Horse;Yunnan Horse;The Plain Agriculture
責任编辑:张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