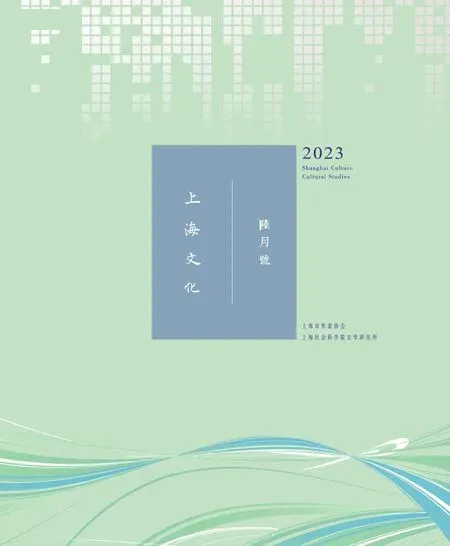诗人之死与疾病之身:“漫长的90年代”视域中的青年叙事
梁钺皓
一、“漫长的90年代”
如今似乎是一个“90年代”在当代文学研究中重新浮出水面的时代,有大量关于20世纪90年代文学状况的学术研讨会,还有许多重要的学术期刊不约而同地开始关注这一时期,为其开辟专栏,比如《当代作家评论》的“新生代写作30年”,《当代文坛》的“90年代文学再出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的“90年代文学研究”,等等。这些努力事实上都试图从今天的角度重新展开90年代的内在状态,呈现一个过去无法把握的历史主体。这首先就表现在对90年代与当下关系的重新把握上。汪晖曾经借用霍布斯邦“短20世纪”这个名词来形容中国的漫长革命时代,他认为80年代作为革命时代的尾声,终结了一个短促的20世纪。由此,90年代获得了作为一个崭新世纪起点的合法性。回望9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实践,足以发现90年代成名的作家、出产的文本、萌发的问题及其影响,都延续到了当下的文学创作与研究之中。陈思和曾经用“中年”一词来概括这种90年代创作特征的延续状态。一个相对于“短20世纪”的“漫长的90年代”,成为一种审视90年代的新视域。
除了“短20世纪”的参照之外,“漫长的90年代”还与西方世界的“漫长的60年代”(Long Sixites)有着某种类比关系。这种类比关系来自于它们都作为一个剧变的时代,并且对当下世界产生了持久、不可磨灭的影响。只不过,“漫长的60年代”作为20世纪西方的一个黄金时代已经终结,一般认为它的终点是70年代中期。但是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写作来说,90年代远未终结,这一点无论在作家代际、审美观念还是创作实践中都可以看到。另外,对于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来说,“黄金时代”这个充满着怀旧意味的赞美显然已经被安置到了80年代之上。当然,“漫长的90年代”并非是为了争夺这个赞美,因为正如詹姆逊讨论60年代时说的那样:“对60年代光辉业绩的追忆、纪念或悲惨兮兮地公开承认那十年的诸多失败和错失了的机遇,都是一种无法避免的错误。”①弗雷德里克·詹姆逊:《60年代断代》,王逢振主编:《六十年代》,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第1页。
正是在“漫长的90年代”这个语境中,当代文学写作对于90年代的呈现存在着一个双重结构,这个结构以历法意义上的90年代终结作为标志,呈现为90年代的当下书写与新世纪的90年代书写这两个相互呼应的部分。②杨庆祥在《九十年代:记忆、建构与反思》一文中有类似的表达,他将关于90年代的文学分为“九十年代的写作”和“二十一世纪关于九十年代的书写”。所有发生在90年代的文学写作都被他归为第一类,如《白鹿原》。我这里强调的不仅是发生学上的,还强调文本内容和90年代的直接相关性。这种呼应在许多的文本中都可以找到,譬如“新现实主义冲击波”与班宇等“新东北作家群”的写作,鬼子和王十月笔下的南下打工者命运等。除去这些直接关涉历史重大事件以及社会重要进程的书写,这种双重结构也存在于某些普遍的文学主题之中,最为显著的就是90年代青年生活的书写。一方面,在90年代大量的年轻作者不遗余力地书写着当时青年的生存状态,其中绝大多数的创作都与作家本人的青春经历有关。这些作家通常以“新生代”“70后”作家的面貌出现在我们今天的文学史叙述中。另一方面,21世纪至今的纯文学写作中最受欢迎,也可能是最富有活力的青年叙事,绝大多数也是关于90年代的书写,比如路内的“追随三部曲”,班宇等人的90年代“东北往事”。新世纪的90年代书写本身就有双重性,即它既是属于90年代的,也是属于新世纪的。当然,这种双重性在“漫长的90年代”这个语境中其实是一体的。但是重视文本所体现出来的90年代状态,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进入90年代,金理就曾经以路内《十七岁的轻骑兵》为文本讨论90年代青年的情感结构。正因如此,当我们试图讨论90年代文学中的青年时,应该引入一个在新世纪召唤了90年代的作者或者文本。
在此基础上,我选择了丁天和路内这两个“70后”作家来进行讨论。事实上,这两个作家本身就具有某种文学史的互文性。丁天在90年代中期开始发表作品,原本被视作是“新生代”的一员,在世纪末金仁顺、棉棉等“70后”作家登场之后又被纳入到“70后”作家群体之中。从当时的评论文章来看,无论是对“70后”作家抱有期待的李敬泽、施战军等人,还是对“70后”作家激烈批判的黄发有、洪治纲等人,对他都有很不错的评价。李敬泽评价丁天的写作有“一种‘无我’的想象,一种包容和呈现世界之广阔丰富的欲望”,③李敬泽:《穿越沉默——关于“七十年代人”》,《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4期。并直言要押宝在丁天的身上。丁天辜负了众多90年代评论家的厚望,他和另一位在90年代被看重的作家朱文一样,在历法意义上的90年代终结之后就基本结束了自己纯文学的写作。尽管他在新世纪最初的两年陆续出版了两部长篇小说,但是《玩偶青春》(也叫《伤口咚咚咚》)事实上是他90年代的创作,《像一场爱情》绝大多数篇章也由他发表在90年代的中篇小说改写而来。后来他以剧本写作为生,并短暂以恐怖小说作家与报纸专栏作家回归过。在他后来的一次自述中,他借用了一位评论家的话来总结自己的写作:“早慧必定早衰。”①丁天:《我这一辈子》,《博客时代的爱情之男人缘》,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8年,第161页。同时,在现在的“70后”作家研究中,丁天也几乎被刨除,成为历史的遗迹,譬如在何锐主编的两本关于“70后”作家的研究合集中,丁天的名字几乎没有出现。这当然是一种不健康的研究状态,不过这同时也意味着,即便我们严格地从历法意义上定义,丁天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90年代写作者。同样作为“70后”作家的路内,如果我们只将他千禧年前后在同人性质的网络纯文学论坛上的写作视作一种写作的早期训练,而把《少年巴比伦》在《收获》上发表视作他写作的出道,他的写作可以视为是从新世纪开始的。事实上,在路内的自述中,《少年巴比伦》的写作时间也是新世纪。路内已经成为当下“70后”作家群体中最不容忽视的存在之一,不仅仅因为文学评论对于他的重视,还有读者对于他的认可。
与此同时,将丁天与路内放置到一起,也再一次提醒了我们一个来自90年代的陈旧问题,即“70后”作为一个作家群体命名的孱弱。正如“新生代”这个同样来自于90年代的作家群体命名一样,“70后”作为一种时间意义上的先验命名,没有任何创作意义上的指代功效。尤其是当我们将丁天与路内这两个都曾经是“70后”作家群体中的重要代表人物放置到一起以后,就更加显示出它的尴尬。我们无法走出“漫长的90年代”是因为种种源自于90年代的问题都被我们以一种“历史进化论”的观点悬置,期待在将来能够得到解决,所以“70后”这个命名才会在今天的叙述中成为一个约定俗成的语词。在最近一篇关于“70后写作”这个命名的历史梳理以及辩诘的论文中,论者认为现在的“70后写作”已经获得了命名上的合法性。②参见曹霞、陆立伟:《“70后写作”:命名的辩诘与批评的形塑》,《文艺争鸣》2022年第12期。不过正如论者自己所说,这种合法性的来源是创作实践的丰富性,而不是创作与艺术的一致性。所以我们应该试图寻找一种新的命名方式,同时也是一种新的叙述逻辑,在创作层面上对直至今日还含糊不清的作家群体做一种阐释与划分。
本雅明在他的《历史哲学论纲》中说:“历史是一个结构的主体,但这个结构并不存在于雷同、空泛的时间中,而是坐落在被此时此刻的存在所充满的时间里。”③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王斑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273页。本雅明相信,历史不是线性的、进化论式的存在,而是以一种废墟的或者碎片的形式存在于当下之中,他将此比喻为“星丛”。我将丁天与路内视作本雅明式的历史与当下所形成的“星丛”结构,如果说,路内的创作是那个背向未来、目视废墟的“历史天使”,那么丁天的创作正是“历史天使”所注视着的历史废墟。通过对于路内的审视,我们可以“虎跃”一般回到90年代的历史中去,去把握弥散在我们周围的90年代历史碎片。这也意味着对于我们来说,需要做的正如本雅明要求历史学家的那样,而不是安于一种因长久使用而稳定的概念之中。本雅明说:“他会转而把握一个历史的星座,这个星座是他自己的时代与一个确定的过去时代一道形成的。这样,他就建立了一个‘当下’的现在概念。”①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启迪:本雅明文选》,第276页。其实这也是“漫长的90年代”所指向的终极目标,即我们重新讨论90年代文学,是为了重建“当下”这个概念,重新审视当下的写作与生活。
二、诗人之死
欧阳江河曾经在他的文章中写过:“对我们这一代诗人的写作来说,1989年并非从头开始,但似乎比从头开始还要因难。一个主要的结果是,在我们已经写出和正在写的作品之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中断。”②欧阳江河:《1989年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站在虚构这边》,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28页。他以诗人的敏锐追溯到了发生在80年代末期的文化断裂,提示了一个有别于“新时期”的“后新时期”已经到来。另一位诗人海子则以自杀的方式向我们提示了这种转变。作为一种历史的后视,我们会发现从海子之死到欧阳江河完成这篇文章的1993年,至少还有三位年轻的诗人死去,他们是骆一禾、戈麦以及顾城。
海子自杀所代表的“诗人之死”现象以及产生的轰动效应,事实上已经成为文学文本失效、文学事件轰动的90年代的一个神话原型,成为90年代写作的某种“集体无意识”。正因如此,在90年代的文学写作中,尤其是关于青年生活的写作中,“诗人之死”或者说诗人的消失,几乎成为一个90年代文化上的史前隐喻。徐坤《斯人》的主题就是大学中一个年轻诗人的死。李洱的《午后的诗学》虽然不涉及一个诗人肉体的毁灭或消失,但也讨论了一种精神上的“诗人之死”。最具有代表性的文本,应该是朱文的《食指》。这篇小说的主人公是消失在90年代前夕的诗人吴新宇,他坚持要把诗歌还给人民,最终却走向了失踪的命运。朱文在小说中将当代生活的表面符号堆砌在一起,以此来说明世俗生活的“拼接”状态。吴新宇所期待着的人民就生存在这种生活中,然而他们没有办法为吴新宇和他的诗歌让出一小块儿地来。吴新宇的失踪正是一种诗人的自我与俗世生活针锋相对之后的结局,也是一场将所有诗意驱逐出当代生活的城邦的审判。
正因如此,丁天的《告别年代》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文本。这个主要讲述了一场都市爱情的中篇小说,其中还描述了诗人孟东在90年代的死亡。和徐坤以及朱文关于“诗人之死”的写作类似,一开始对于诗人孟东之死的叙述笼罩着一种神秘的气氛,他究竟因为什么死,怎么死的都是一个谜团。伴随着丁天的叙述,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失败的理想主义者,一个生活在自己的艺术家幻想中的人。诚如丁天在小说中写的那样,他“当然是要被我们这个注重现实的时代淘汰的”。③丁天:《告别年代》,《青年文学》1999年第4期。甚至于孟东的死亡,也被别人视作是对于海子和戈麦的一次庸俗模仿。“我”试图以孟东的死为主题写一篇小说,但最终放弃了这一个想法。孟东死前留下的笔记告诉主人公,死亡在他看来已经成为一种迎接明天与抵抗恐惧的法宝。这是一种对90年代诗人悲剧性宿命的想象,面对90年代的世界,诗人似乎注定走向灭亡。
在丁天这个关于“诗人之死”的故事的叙述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他格外强调了“我”19岁的那一年,也就是1990年,然后列举了一系列诸如处决齐奥塞斯库、世界杯德国捧杯、海湾战争等历史重大事件。这样的手法也出现在他其他的小说中,比如《欢乐颂》中他也一次又一次地强调1990年和那年的世界杯,《饲养在城市的我们》中强调自己离开学校后的两年里发生了海湾战争、东欧解体等事件。《告别的年代》不同的是,丁天还提到了在他19岁前后有两位诗人先后死去,这似乎在向我们强调这是典型的90年代事件,与世界杯、海湾战争这些牵连了全世界人民的事件一样开启了90年代的世界。
这个中篇小说后来被改写为长篇小说《像一场爱情》中的一个章节。丁天的改写删去了诗人孟东之死和主人公试图为他写小说这些情节,转而变为构思写一篇关于青春和爱情的小说。这样的删改恰恰说明所谓的“告别年代”,不仅仅是在向一场都市爱情故事和它的女主人公告别,同时也是在向一位早已死去的诗人告别。与此同时,将关涉孟东之死的情节删去,完成了一次文本情节与现实生活的互文,这预示着“诗人之死”悲剧性的彻底完成,一种诗人在世俗生活的历史中的完全退场。
90年代“诗人之死”的核心主题就是青年人身上遗传自80年代的诗人式浪漫主义自我想象与现实生活庸俗化的急剧加速之间的矛盾。事实上,这一核心的矛盾变形为丁天小说中“身体/欲望”书写的隐喻。两个经典的情节来自于他的小说《饲养在城市的我们》。第一个是“我”与高中同学林雪的地下恋情,这是一场发生在90年代前夕的爱情,伴随着进入90年代以及林雪考上大学终结。高中时的林雪是一个标准的文艺女青年,但在大学毕业后的第二年就嫁给了一位生意人,并且在婚后找到“我”想要与“我”偷情。小说最后发生在“我”和高中好友黄力之间的情节则更具有隐喻性。“我”高中毕业以后游荡在城市里,最后成为一个作家,黄力则考上了大学,然后成为90年代北京的成功人士。黄力在某一天将“我”约到酒店,并引诱“我”与一位陌生女人搭讪,当“我”以为自己遭遇了一场爱情的邂逅时,却被女人告知她只是黄力找来的妓女。于是爱情邂逅成为招嫖事件。这场来自黄力的恶作剧是90年代世界的最佳隐喻,一切过去被视为有意义的东西,爱情、性爱也包括文学,都被金钱以及世俗的成功毫不留情地嘲弄与戏耍了。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丁天曾经在《数学课》中写自己十六七岁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朝气蓬勃的纯真年代。丁天用他的性书写完成了对80年代和90年代的描述。这让人想起朱文的《弟弟的演奏》。在朱文的小说中,以主人公们大学毕业为界,对于性有着截然不同的姿态。如果说大学时(80年代)性还代表着一种不安的躁动,那么毕业后(90年代)就成为一种苦恼,以至于小说的最后主人公得了阳痿,却高兴地向全世界通知这个消息。
“诗人之死”以及用“身体/欲望”来讲述它的本质矛盾也是路内小说的重要内容。在《追随她的旅程》中,路内设置了三个类似诗人的角色,分别是路小路的语文老师丁培根,于小齐的青梅竹马李翔,还有重点高中的女学生欧阳慧。前面两位是不折不扣的失意者,李翔热爱文学却没能考上大学,丁培根时常在报刊上发一些散文,却始终无法得到学生以及身边人的尊敬。最后,丁培根在90年代因为心脏病去世。欧阳慧则是一个典型的路内式女性角色,她就像是年轻版的白蓝,决绝地离开了无聊、逼仄的戴城,走向了远方。
另一方面,《追随她的旅程》故事开始的那个夏天,是一个人人都在追求“破处”的夏天,除了主人公路小路之外,所有人都有了性的体验。路小路想要追求爱与性的统一,却一直没有办法实现。直到后来他所在的化工厂与附近的水泥厂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冲突,他逃亡到于小齐的学校里,然后在学校宿舍中于小齐用手帮他完成了“破处”。这个“破处”之夜与路内其他的写作可以形成互文。在他的另一部小说《少年巴比伦》中,路小路与白蓝之间的第一次性爱就发生在一场地震之中。工厂的骚乱和地震,都代表了一种非日常的极端状态,似乎在路内眼里,只有这样的混乱时刻,90年代世俗秩序短暂崩毁了的瞬间,爱与性才完成了结合。而《追随她的旅程》中其他的性爱却都呈现出某种错位关系,大飞是先和小怪有了性关系才爱上了她,杨一和欧阳慧在暑假里频繁地保持性关系,最后欧阳慧却发现自己其实根本不爱杨一。和丁天的小说一样,“性爱”成为路内小说的一个90年代隐喻,意味着一个古老的世界正在不可阻止地向我们远去,那个古老的世界相信诗人、文学、爱情以及一切诗意的东西。但是在他们要面对的一个崭新的世界里,这些都被视作是一种疾病,他们自己则是这个世界的病人。
三、疾病之身
有必要先提及路内写作的早期历史。尽管路内在2007年才发表他的长篇处女作,但是在千禧年前后他就已经混迹于互联网上的同人文学论坛。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暗地病孩子”(sickbaby)。除了路内,近期凭借《潮汐图》获得“理想国文学奖”的林棹,也曾经活跃于这个论坛。①这个论坛还活跃过杨海崧、安妮宝贝、李傻傻,诗人外外、乌青。正如名字所展示的,这个创建于1998年的论坛的青年用户们向所有人承认了自己是一个有病的孩子,并自称为“烂掉的一代”。现在进入遗留下来的网站还能看到首页的中间有这样一句话:“我们病了,寄居在腐烂且安逸的城市之中。”
苏珊·桑塔格在《作为隐喻的疾病》的引子中写到:“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尽管我们都只乐于使用健康王国的护照,但或早或迟,至少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每个人都被迫承认我们也是另一王国的公民。”②苏珊·桑塔格:《作为隐喻的疾病》,《疾病的隐喻》,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5页。她同时也提到,健康一般被视作是社会秩序的象征,疾病则被当作是骚乱的象征。并且,因为疾病长久地与死亡、人类的软弱联系在一起,所以有病的人往往不被视作正常社会的组成部分。与桑塔格不同的是,“暗地病孩子”向我们传达的是对于“疾病隐喻”的主动认领,他们不再被动地被划分为另一个王国的公民,而是提前就与现下的世界保持了距离。这种疾病的自我指认,不仅仅是青年试图展示自己与世界格格不入的姿态,同时也代表着曾经的青年世界观的崩塌。《人生》中青年改变世界的冲动,在90年代的青年看来更像是一个遥远的神话。他们相信自己的无能为力,也承认自己的软弱,承认面对城市与世界,他们只是正在腐烂中的病人与寄居者。
90年代青年疾病最显著的表现就是“怀旧”。斯维特兰娜曾经对“怀旧”这个词做过一个词源上的溯源,她发现“怀旧”最早被一名医生用作描述士兵的“源于返回故土的欲望的那种愁思”。①斯维特兰娜·博伊姆:《怀旧的未来》,杨友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3、5、91页。这说明“怀旧”一开始就是一种“思乡病”的症状。同时,我所要讨论的,与丁天以及路内的文本相关联的“怀旧”,事实上是“城市思乡病”的表现。之所以强调“城市”,是想要与通常认知中的那种“思乡病”以及乡土写作区别开来。正如斯维特兰娜在导言中说的:“初看上去,怀旧是对某个地方的怀想,但是实际上是对一个不同的时代的怀想——我们的童年时代,我们梦幻中更为缓慢的节奏。”②斯维特兰娜·博伊姆:《怀旧的未来》,杨友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3、5、91页。也就是说,这里“思乡病”不再指向一种空间概念上的远离,也不延伸到“乡村/城市”的二元结构之中。这里试图指向的是一种时间概念上的远离,它可以延伸向前文提到的一个古老的、相信诗意的世界的远去,也可以延伸向作家本人少年与青春记忆的远去,还有城市本身的变化。也正是在时间的意义上,作为“现代化”符号的城市,才从一个反怀旧的场域转变为了一个怀旧的场域。
这种“怀旧”在丁天和路内的文本中有两个表象特征。第一个是文本中的城市景观纪念。比如路内笔下戴城变迁的细节展示,还有丁天在《饲养在城市的我们》中对护城河、安定门等与青春记忆有关的北京景观的召唤。对于身处90年代的他们来说,“城市本身就是一种濒危的风景”。③斯维特兰娜·博伊姆:《怀旧的未来》,杨友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3、5、91页。第二个是文本的感伤风格。大多数90年代评论家,都认为丁天的写作带有着明显的感伤风格。在丁天和张钧的对谈中,他自己也承认了将生活中感受到的伤感失落投射到了小说人物身上。路内的写作也时时刻刻都包裹在伤感的气氛之中,比如《少年巴比伦》第一章的题目“悲观者无处可去”就为全书奠定了伤感的写作基调。
“怀旧”更为重要的作用在于,它成为叙事中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的一种中介。斯维特兰娜将怀旧分为“修复型”和“反思型”两种类型,前者以一种严肃的集体式语言来重建历史,后者则更多地从个人出发,以一种讽喻的方式来追溯与叙述过往。在斯维特兰娜看来,第二种怀旧与历史之间是保持着某种距离的,它不会对于“历史废墟”有修饰与美化,它更注重的是将过去投掷到现在中来感受,正类似于本雅明所理解的历史与当下的关系。丁天和路内的写作,显然要更靠近“反思型怀旧”。他们通过个人成长故事的回忆与写作,向我们传递了“诗人之死”“疾病之身”这样的90年代主题,也同时向我们传达了这些主题背后的90年代青年集体情绪。
路内《追随她的旅程》中有一个章节名为“我们都是残疾”。在小说中,“残疾”是主人公路小路给来自莫镇的李翔取的外号。之所以取这个外号,并不是李翔在生理上真有什么缺陷,而是一种精神气质上的感受。李翔是一个小镇文学青年,在他身上有一切纯真年代的美好品质,善良、执着、热爱文学,然而他在戴城的遭遇却是一个他这样的人身处90年代的缩影。他面对饭店里喝醉后来找茬的男人,陷入到了一种完全无能为力的境遇之中。李翔的无能为力,正是过去一切被视为属于青年的美好品质在90年代的遭遇,生活以一种倒置的方式将“美德”转化为了“精神孱弱”。在其他许多人的作品中我们都能够窥见这样的叙事,比如余华的《兄弟》中,善良的宋刚与狡猾的李光头的对比。前者面对一个崭新的时代,完全无能为力,最后以一种走向“女性化”的隐喻终结了生命。宋刚最后给自己隆起来的胸,正是一种女性所代表的无用且软弱的美德在经济时代的奇观化。与宋刚相反的是,李光头成为一个典型的当代英雄。
同时,这种青年人的“精神孱弱”还以另一种似曾相识的疾病情节被凸显了出来。路小路的发小杨一,在考上大学以后急速地走向了一种堕落生活,与曾经那个励志要考上清华大学的少年形象愈行愈远。杨一大学毕业以后回到戴城,买了一个游戏机,经常找楼上的傻子陪他打游戏。结果是傻子厌倦了和他的游戏,要跑出去看风景。相似的场景出现在过朱文的小说《去赵国的邯郸》中。小丁每天和一个强壮的弱智比赛做俯卧撑,最后也是弱智厌倦了比赛。由于路内曾经提到过,在90年代的作家中他最喜欢朱文和毕飞宇,①张丽军、路内:《小说存有我全部的热情——70后作家路内访谈》,《雨花》2017年第10期。所以有理由相信《追随她的旅程》中的这个情节和朱文小说存在某种联系。事实上,与傻子的游戏或者比赛,是孤独的杨一以及无聊的小丁对抗生活的最后方式,在这一方式宣告失败之后,杨一终于干起了工作,小丁则陪着同事们去了邯郸游玩。这意味着,他们实际上完成了一次疼痛的自我疗愈,如果过去的自己是那个被社会“他者化”和被遗弃的病人,那么傻子的厌倦迫使他们不得不意识到自己已经失去了最后一次发疯的可能。在他们眼前剩下的,除了如同“诗人之死”的毁灭,就只有复归到生活之中。
丁天的小说中也同样出现了这种疾病的自我指认。在《欢乐颂》中,丁天这样写:“思考不是一件好事,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实在得算是一种恶习。”②丁天:《欢乐颂》,《人民文学》2000年第10期。并且他将主人公以及他的大学同学管飞关于人生意义、自我与环境之间关系的思考都视作是一种传染病式的思考状态。把一切有意义的思考都视作是一种疾病,正是一种“美德”和“精神孱弱”颠倒的表现。《饲养在城市的我们》中,丁天通过主人公和他的高中同学的遭遇不断地质询着这个问题。丁天在小说中写:“黄力和齐明应该说是正代表了幸和不幸的两种命运。”③丁天:《饲养在城市的我们》,《逼近世纪末小说选》卷5,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62页。老实、高大、漂亮的齐明犯事进了局子,善于伪装、富有心机的黄力却获得了世俗上的成功。他写进这个“幸运/不幸”对比中的,还有当兵复员的刘军死在小贩的刀下,成为作家的“我”被黄力戏耍。正因如此,丁天这篇小说的题目尤其值得我们注意,正是城市以及时代过去用来饲养“我们”的一切美德,造成了“我们”在90年代的不幸。或者说,正是城市和时代遗弃了它们所饲养出的“我们”。所以在《告别年代》里,主人公认为自己就像被丢在陌生站台的旅人,有时渴望回到正常秩序中却永远无法回去。于是丁天在小说中借徐星之嘴说:“这社会就像是一辆行驶的火车,而我们都是跳车者。”①丁天:《告别年代》,《青年文学》1999年第4期。
这种被遗弃的状态,路内在《追随她的旅程》中用了一个很好的词汇来概括,即“乡逼”。这是戴城人用来羞辱乡下人的词汇,同时也被一个在上海的戴城女孩用来刺痛路小路和杨一。这个词汇很好地展现了青年的一种不被接纳的状态,这种不被接纳的状态不仅仅是空间上“中心”对于“边缘”的排斥,同时也是这个时代对于青年的抛弃。这样说,是因为尽管路内在他的小说中一再试图展示富有暧昧性的地域景观,即在对戴城的描绘中总是试图给予读者一种非都市的幻觉。但是许多细节都出卖了他,比如《十七岁送姐姐出门》中他写到了戴城大学,《少年巴比伦》中提到戴城在1992年有了肯德基。1992年整个中国只有10家肯德基。这都说明了,戴城或者说路内真实的故乡苏州,空间上的边缘不过是相对于上海而言。所以这个词汇指向的,其实是90年代社会极速前进中的掉队者。它给90年代初的路小路和杨一带来的恐惧,也不是对于城市的恐惧,而是一种被“他者化”和被遗弃的恐惧。也就是说,它是“病人”的同义词。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90年代初的路小路,也许并无法想到,在完整地经历了90年代以后,他会摆脱这种恐惧,活跃在一个名为“暗地病孩子”的网络论坛里。在那里他会承认并接受自己的“他者”身份以及被遗弃状态。这不仅仅是路内的个人成长传奇。我们会发现,在20世纪末,这种指认自己为病人的心态只属于一部分文学青年。然而在“佛系”“宅文化”“躺平”等词汇盛行的今天,这早已经成为绝大多数青年的普遍心态。这就是“历史的90年代”举起的投枪,对名为“漫长的90年代”的当下的偏侧一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