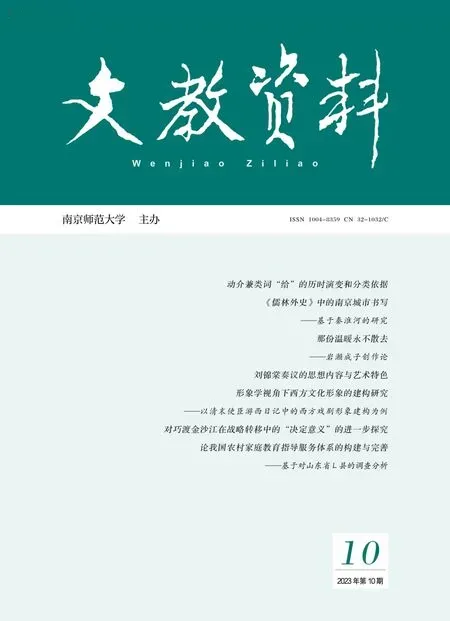对巧渡金沙江在战略转移中的“决定意义”的进一步探究
李 祥
(中共寻甸县委党校,云南 昆明 655200)
一、对象界定、文献综述、研究视角
(一)研究对象界定
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从狭义来说,指的是中央红军于1935 年5 月上旬北渡金沙江的军事行动。从广义来说,指的是在扎西会议和四渡赤水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人的正确指挥下,基于敌情、地情的不断变化,多次适时调整具体目标任务,佯攻贵阳、调出滇军,再入云南、巧获地图,威逼昆明、调虎离山,抢占先机、渡江北上的宏大的战略实施过程及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本文基于后者探究其在战略转移中的“决定意义”。
(二)相关研究综述
当前,涉及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文献资料和研究成果较多,有红军将士的回忆资料,如刘伯承的《回顾长征》、陈云的《随军西行见闻录》、聂荣臻的《聂荣臻回忆录》、沈阳军区政治部编研室编写的《红军将士忆长征》等;有党史和文献部门编写的专题资料,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写的《红军长征史》、《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写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中共云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的《红军长征过云南》、成都军区政治部宣传部编写的《红军长征在西南》等;有相关重要历史人物的年谱,如《毛泽东年谱》《毛泽东军事年谱》《朱德年谱》等;有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如徐焰的《红军巧渡金沙江》、徐继涛的《红军长征过云南述略》、史石的《金沙江的记忆:红军长征过云南纪实》等。这些文献资料和研究成果中都不同程度地叙述了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过程,明确指出了巧渡金沙江对成功实现战略转移、胜利完成长征壮举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不少资料中特别强调了巧渡金沙江对于战略转移的“决定意义”。
刘伯承在《回顾长征》中写道:“从此,我军跳出了数十万敌人围追堵截的圈子,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1]《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综述大事记表册》中有如下表述:“打破敌人数十万重兵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滇黔地区的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胜利。”[2]徐焰在《红军巧渡金沙江》中将其表述为:“从此跳出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圈子,取得了战略转移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3]徐继涛则在《红军长征过云南述略》中以“红军完全跳出了几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4]简要阐述其“决定意义”。
(三)本文探究视角及总体思路
1. 探究视角
巧渡金沙江的“决定意义”主要是相对于战略转移而言的,论证和阐述其“决定意义”可以从战略转移的目的入手,对比巧渡金沙江前与巧渡金沙江后的形势变化,分析论证巧渡金沙江对于达成总体战略目标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2. 总体思路
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目的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因为博古、李德“左”倾错误指挥导致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党和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以解决自身生存问题,保存壮大革命力量;另一方面是因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侵华步伐,妄图吞并全中国,为解决民族危机,党和红军需要通过战略转移开进到抗战最前线。从开始长征到巧渡金沙江前,党和红军虽然在浴血奋战中转战多个省份,但是既没有真正摆脱敌人的重兵追堵,也没有实现北上抗日的目标。而巧渡金沙江的伟大胜利,使中央红军跳出了数十万敌人围追堵截的圈子,在事实上开启了北上征程。因此,巧渡金沙江是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二、基于“摆脱追敌”的视角理解其“决定意义”
(一)红军在长江以南地区始终面临着敌人的重兵围堵
基于消灭党和红军的图谋,蒋介石嫡系“中央军”、各地方派系反动军队以及各地民团武装一直没有停止对红军的围追堵截。在中央红军通过国民党军第三道封锁线时,蒋介石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原“围剿”中央苏区的西路军和北路军中的薛岳、周浑元两部共16 个师77 个团近30 万人,专门负责“追剿”仅有数万人的中央红军。此外,还令粤系陈济棠4 个师,桂系李宗仁、白崇禧5 个师进行布防截击,并命令黔系王家烈派其得力部队进行堵截。可见,在长江以南各地,蒋介石在中央红军长征初期便投入了数十万兵力竭力围堵中央红军。
遵义会议后,湘、桂、黔、川、滇军阀虽然各怀鬼胎,但迫于蒋介石的压力,并基于“保护”其自身既有地盘和维护其反动统治的考虑,都在一定程度上与蒋介石的中央军相互策应,围堵红军。1935 年2月2 日,为集中力量追堵红军,蒋介石发布电令,将国民党吴奇伟部、周浑元部、王家烈部以及龙云的滇军合编为由四个纵队构成的“剿匪”军第二路军,由龙云任总司令,薛岳任前敌总指挥,“专事‘追剿’中央红军”[5]。
中央红军南渡乌江后,虽然以威逼贵阳迫使蒋介石调动部队增援贵阳,形成了红军转兵西进、再入云南的有利条件,但敌人并没有就此停止追击红军。中央红军从贵阳向云南西进之时,蒋介石命令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和第五十三师迅速掉头向西,在中央红军右侧沿着黔滇公路向西急追,命令孙渡纵队在红军后面紧咬紧追,企图迫使中央红军“向安顺、镇宁北窜故道”[6]。
经过艰苦跋涉,中央红军于1935 年4 月下旬从平彝县(今富源县)的黄泥河再次进入云南。蒋介石一面积极部署军队在外线防堵截击中央红军,一面接连给龙云、薛岳发电,命令其“剿匪”军第二路军的第一、第二、第四纵队和第五十三师往北向宣威、威宁开进,滇军孙渡纵队则继续在后面追击红军,还命令川军1 个师集中到贵州毕节机动。
第二次进入云南时,中央红军面临着“滇军及国民党数十万军队层层设防、处处围堵”[7]的严峻形势,蒋介石和龙云企图在金沙江南岸构筑新的包围圈,将中央红军消灭在这一地区。
(二)巧渡金沙江前夕敌人在多个方面占据优势
一是兵员数量。中央红军在北渡金沙江前夕,兵员数量只有三万余人。同时,中央红军与红军的另外两支主力部队(红四方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相距甚远,难以相互策应,总体上处于孤军奋战的状态。而蒋介石则调集了七十个团以上的兵力对中央红军进行追击、围堵,数量远远超过中央红军。
二是武器装备。相较于中央红军而言,蒋介石及各地方军阀的军队武器精良、弹药充足,“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8],地上还有汽车和火车运送物资和士兵。而中央红军的将士们,只能依靠双腿在敌人重兵之间不停地穿插、奔袭、作战。
三是后勤补给。敌人的后勤补给及时、充足,而中央红军的情况则是:一方面,因处于战略转移之中,难以携带大量物资;另一方面,川、黔、滇边境地区的人民群众长期遭到国民党反动派和土豪劣绅的搜刮压榨,生活贫困、物资匮乏、缺吃少穿,虽然百姓全力支持红军,但红军仍然难以及时获得足够的补给,在吃、穿、住、行等方面经常面临困难。
四是地形条件。中央红军第二次进入云南后,根据缴获的云南军事地图和行军中的实际观察,发现“云南境内的地形条件,不像湖南、贵州有良好的山区可以利用”[9]。在毛泽东看来,昆明东北地区属于“平川地带”。陈云则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写道:“虽觉云南之地势甚高,但在滇东北有很大的平原。”“地势层层向上,且每一县城及镇市周围又有几十里几百里之平原,俗称昆明坝子、大理坝子、曲靖坝子等等。坝子者即县城周围之平地也。因云南之道路平坦,兼以道路甚宽,可行北方之骡车,在交通事业之开展上又觉便利,如修汽车路则较黔省之凿山开路容易多矣,故云南汽车路发展甚早。”[10]从对敌斗争和军事作战的角度来说,以游击战为主的红军在这一“平川地带”失去了与敌周旋的自然屏障,“不便进行较大的作战机动”[11]。这一带的地理地形于蒋介石和龙云“追剿”红军有利,而于中央红军回旋作战则不利。
五是天险金沙江。金沙江水流湍急,风浪较大,两岸峭壁耸立,自古就有天险之称。横亘在红军面前的金沙江为国民党军队构筑包围圈“围剿”红军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央红军第二次进入云南之时,蒋介石和龙云多次命令沿江各地销毁一切船只和可以用于渡江的资材,盘算着利用金沙江,加以重兵追堵,将中央红军消灭在金沙江南岸。
(三)巧渡金沙江后中央红军跳出了数十万敌人围追堵截的圈子
面对敌人的重兵围堵及种种不利因素,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人的指挥下,正确研判形势,抓住有利时机,大胆果敢决断,与敌巧妙周旋,经过艰苦奋战,最终从云南的皎平渡、树桔渡、鲁车渡、洪门渡等渡口渡过了金沙江,跳出了敌人重兵围堵的圈子。
红军总政治部于1935 年4 月30 日发布的《总政治部关于渡金沙江转入川西的政治工作训令》中预判了渡江后的状况:“在政治上,在川西及西北地区创立苏区根据地,是首先就在使中国苏维埃运动及工农红军两大主力——野战军(此处“野战军”指中央红军,引者注)与四方面军更形接近,更能直接地互相配合作战,走向汇合,以实现赤化四川,而为苏维埃在全国的胜利定下确实的基础。”“在军事上,渡江之后,敌人难于调遣兵力,使作战便利争取伟大的胜利。两主力之接近地配合作战,能够使我们易于取得胜利,而且胜利亦更大。并且因为地理与政治的各种条件,使敌人无法包围我们,我们能够背靠西部而无后顾之忧。这对于野战军,能够使我们极大地缩短无后方的大规模游击战争,变为有后方依托的运动战。”[12]渡江后的实际状况证明了这种预判的正确性。
中央红军成功渡过金沙江,使得曾经横亘在红军面前的天险金沙江变成了阻挡尾追之敌的有利屏障。在渡过金沙江后,各渡口的红军及时捣毁了使用的船只(其中对属于群众的船只予以赔偿),以阻滞追敌过江。同时,中革军委又命令红九军团顺江而下,沿江搜索,结合实际情况通过排渡、偷渡或隔河射击等办法,以烧毁、捣沉、击沉等方式破坏两岸所有船只,使敌人无法迅速过江,掩护主力部队行动。
中央红军于1935 年5 月9 日全部渡江完毕,三天后,即1935 年5 月12 日,朱德在《关于红军在会理附近停留五天进行休整的部署致各军团电》中指出:“我军渡过金沙江,取得战略上胜利和进入川西的有利条件。现追敌正企图渡江跟追,但架桥不易,至少须四五天,西昌来援之敌前进甚缓,并企图从两翼迂回。”[13]据《毛泽东军事年谱》中所述:蒋介石于5 月10 日要求薛岳率领部队渡过金沙江,企图在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砻江以东地区构筑新的包围圈,但是“由于渡河器材缺乏,敌军于十六日才渡江”[14]。据此可推断,红军渡过金沙江,与追敌至少拉开了七至八天的行程。
《毛泽东年谱》中有如下记述: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国民党数十万‘追剿’部队被甩在金沙江以南”[15]。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写道:“红军之渡金沙江为自离江西以来,最险要亦最得意之事。”“我曾亲自渡过金沙江,我亦觉此事为平生一大幸事,使我永远不能忘却者。”[16]就连在遵义会议上完全不同意别人对他的批评的李德,也高度评价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这一伟大胜利,认为红军“渡过金沙江以后,在战略上形成了一种新的比较有利的局势”[17]。巧渡金沙江的伟大胜利,使中央红军跳出了数十万敌人围追堵截的圈子,取得了更大的斗争主动权,是自身逐步转危为安的重要转折点,对于保存壮大革命力量具有“决定意义”。
三、基于“北上抗日”的视角理解其“决定意义”
(一)北上抗日是党和红军战略转移的目标之一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行径愈演愈烈。1934 年7 月7 日,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冲破国民党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围剿”,红七军团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由军团长寻淮洲率领从瑞金出发开始北上。7 月15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正式提出了北上抗日的口号,并声明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为了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将不辞一切艰苦,以最大的决心派遣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红七军团向闽浙挺进作战,大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开展抗日民主运动,开辟浙皖闽赣边新苏区。
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虽然自身生存发展已面临较大危机,但仍然坚持以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为重,将北上抗日确立为自己的总体战略目标。在战略转移中,虽然中央红军的阶段性的落脚点和行动目标因时、因势而不断调整,但抗日救国的使命任务从未更改。
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写道:“红军兵心之所以团结,一方面确因共产党在红军兵士中进行许多教育工作,红军兵士是自认抗日救国、解放工农是自己的责任,这就使红军士气大振。”[18]党和红军北上抗日的决心从长征中对抗日救国方针的宣传中也可见一斑。中央红军进入湖南后,总政治部在《关于目前瓦解敌军工作的指示》中,针对何键部队中的士兵的宣传口号包括:“不替豪绅、地主、军阀当兵,大家起来打土豪分田地,赤化湖南;参加过大革命时代农民运动与湖南暴动的兄弟大家到红军中去;派代表到红军中来,共同组织停战抗日同盟。”红军在长征途中宣传抗日的口号还包括:“白军兄弟!让日本占了中国,你我都是亡国奴,联合红军打日本,莫替日本打红军!”“不替蒋介石当亡国兵!”“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士兵不打士兵!”“联合抗日红军打日本”。红军总司令朱德在召集俘虏中的中上级军官谈话时,也着重“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抗日主张,希望全中国的军人结成统一战线,为拯救中国共同奋斗。”[19]可见,长征的目的既包括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也包括北上抗日。
(二)长征初期几次欲往北走均未成功
在当时,抵抗日本侵略者的主战场和最前线在北方,要解决民族危机就必须北上。中央红军的长征共历时一年,但是,在从位于南方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出发后的近半年时间里,中央红军几次短程的北进尝试都未成功。
渡过湘江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命令中央红军“继续西进至通道以南及播扬所、长安堡地域”[20],目的在于北进至湖南西部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但是,早在湘江战役前,蒋介石就已经制定了“湘水以西地区剿匪计划大纲”,其主要目的便是阻止中央红军北进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在红军过湘江后,蒋介石已识破红军意图,命令其部队按“大纲”实施相应军事部署。“调集14 个师共约16 万多人的兵力”,分别进到城步、新宁等地,由此形成一个大的口袋等待红军,而尾追红军的桂系敌军“2 个军约6 万人也紧跟到通道以南的湘桂边界,企图围歼红军于北出湘西的路上”。[21]若中央红军此时执意北出湘西,将陷入敌人重兵包围之中,后果不堪设想。在毛泽东极力主张之下,红军最终改变原定计划,向西转入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贵州,避免了一场可能导致全军覆灭的失败。
遵义会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22]。为达成这一目的,中央红军原计划沿赤水河北上,从四川的宜宾和泸县之间渡过长江,北入四川。但是,中央红军在长江以南的土城一带与敌作战失利,前进受阻,只能改变计划,向西渡过赤水河,向古蔺、叙永地区前进,并进入云南威信地区。蒋介石又急令川军加强长江南、北两岸防备,命令军舰及装甲商船日夜巡逻,并以优势兵力分路向中央红军逼近。据此形势变化,中央红军只能放弃北渡长江计划,改为在川、黔、滇边境地区建立根据地以作为落脚点。1935 年2 月16 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布了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党中央“曾经决定中央红军渡过长江向川北发展”“然而这一决定由于川滇军阀集中全力利用长江天险在长江布防,拦阻我们,更由于党与中革军委不愿因为地区问题牺牲我们红军的有生力量,所以决计停止向川北发展,而最后决定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创立根据地。”[23]中央红军北上计划被迫再次暂时搁置。
(三)巧渡金沙江后真正踏上了北进征程
在四渡赤水后,中央红军佯攻贵阳,调出滇军,再入云南,经大胆穿插,艰苦奋战,终于将尾追之敌甩开了三四天的行程,并以威逼昆明,调虎离山,进一步造成了金沙江南岸的空虚,创造并紧紧抓住了“中央过去决定野战军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现在已有实现的可能了”[24]的宝贵时机,按照战略部署,成功渡过了天险金沙江,真正开启了北上征程,并最终落脚陕北。
中央红军的长征路线整体上呈“L”形,“L”的拐点正是巧渡金沙江战役。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出发后,直到巧渡金沙江前,中央红军的行进方向总体上是自东向西。在金沙江以南的寻甸县鲁口哨村发布《中革军委关于野战军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后,中央红军才真正转为由南向北前进。这是中央红军事实上的西进终点、北上起点。
巧渡金沙江的胜利,使中央红军在长征初期便已确定但多次尝试均未成功的北上征程终于成行,正如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所写的宣传鼓动诗中所述:“工农红军钢铁样,强渡天险扬子江,两大主力大会合,北上抗日敌发慌!”[25]这对于党和红军开进到抗日救亡最前线,并在革命斗争实践中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团结凝聚抗战力量,开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运动新局面,成功应对全面抗战爆发初期的复杂局面,以中流砥柱作用扛起全面抗战大旗,以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维护民族利益,拯救民族危亡具有“决定意义”。
四、结语
中央红军在十数倍于己的敌人的围堵中,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为引领,大胆穿插,机动作战,准确把握机会,逐步掌握斗争主动权,取得了巧渡金沙江的伟大胜利。渡过金沙江后,中央红军摆脱了数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使革命力量得以保存,使北上抗日征程终于成行,它对于推动实现战略转移的目标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是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伟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