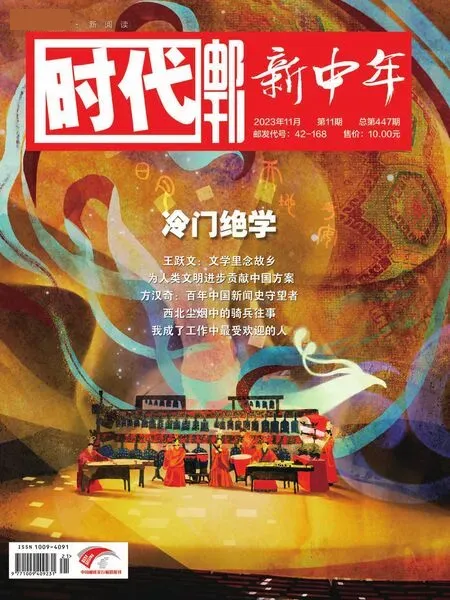方汉奇:百年中国新闻史守望者
● 徐雪莹 安英昭
身为新中国资历最深、教龄最长的新闻史学家,从27岁到97岁,方汉奇一以贯之地将目光投向中国新闻史的求证与书写。
如今,满头鹤发的他依旧神采奕奕,保持着每日读报的习惯,关注着中国新闻史学界最新动态。走入方汉奇家中,约30平方米的书房里,三面墙都是书,墙上、书架上摆放着往日和梁漱溟、金庸等大家的合影。“顶天立地”的特制书架分里外两层,说是藏书万册也毫不夸张。

2022年10月,方汉奇将所藏3045本新闻传播学科相关图书,尽数捐赠给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这些书,收藏时间跨度从1959年到2021年,是新中国新闻史发展的写照。
中国新闻史的“第一幅地图”
1953年,方汉奇来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教学,新闻史是必修课,可他却面临着“没米下锅”的局面。
中国新闻教育,始于1920年上海圣约翰大学设立的报学系。“旧中国的办学是参考西方的,新中国成立以后,那些只能作为参考借鉴,不能全部拿来。”方汉奇说,“重要历史信息资料,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是教学的主要方面,必须加强投入,加强搜集。”
当时,全国大学中教中国新闻史的,只有曹亨闻和方汉奇两个人。新闻史教学,基本依赖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为文本,内容远不够丰富。
为讲好新闻史这门课,方汉奇5年内读了2000多本书。他先是读了胡乔木所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然后以此为主线,到各地图书馆、档案馆查看报刊原件。那时,每逢节假日或寒暑假,他就去上海、扬州跑书店,有时还会去各校图书馆借书。
“一个礼拜要上两个钟头的课,你得有点说道。我只好从秦朝说起,说了两个多礼拜了才说到汉朝,然后再过两个礼拜才讲到唐宋。戏台上管这叫‘马后’——底下那头角儿还没来,台上演员就开始慢动作,把戏拖着唱。当时上课就是这样。”方汉奇无奈地说。
直到1954年,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新闻班组织丁树奇、李龙牧、黄河、刘爱芝四位专家合作编写了《中国报刊史教学大纲(草稿)》,“等米下锅”的状况才得以改善。
1984年,方汉奇成为中国第一批新闻学博导之一。5年后,他和宁树藩、陈业劭等人发起成立中国新闻史学会,如今这个学会是新闻传播学领域唯一的全国一级学术团体。1997年,在方汉奇、丁淦林、赵玉明等人的努力下,新闻学从中文系中国语言文学专业下的二级学科提升为一级学科,定名新闻传播学。
探秘、考证,追溯历史的切片,方汉奇如同历史的记者,和众多学人一步步拼织起中国新闻事业史全景。他撰写或主编的著作,从断代史铺展至编年史。由他所著的《中国近代报刊史》《中国新闻事业简史》,以及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中国新闻传播史》等,影响了几代学人。
“这些基础性研究是功德无量的,对于后来的研究者来说犹如第一幅地图,上面标记了主要的河流、矿产所在位置。”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王润泽这样评价。
“不是新闻专业,我不报”
1926年12月27日,方汉奇生于北京南城丞相胡同的潮州会馆,祖上是广东普宁人。外曾祖父林启,是浙江大学前身求是书院的创办者。外祖父林松坚,曾和鲁迅做过教育部同事。或许是因为敬慕汉代史学家司马迁,祖父方云石为孙儿取名“汉迁”,后因谐音“汉奸”常引同学戏谑,外祖父遂为其更名“汉奇”。
高中时,方汉奇喜欢上集报,向往成为“相机身上挂,足迹遍天下”的记者,“不是新闻专业,我不报”。
1946年,全国开设新闻系的高校屈指可数。最终,方汉奇考取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今苏州大学)新闻系。四年大学生涯,方汉奇没回过一次家,因为父亲供不起苏州往返汕头的路费。
“那个时间段,我学的是新闻,我喜欢的是新闻史,我关注的是报纸,旧报旧纸。”大学期间,方汉奇根据个人收藏的千余份小报,撰写发表了首篇学术论文《中国早期的小报》。
毕业后,他未能如愿当上记者,成为上海新闻图书馆研究馆员。1953年,方汉奇被北京大学中文系副主任罗列“挖”去教新闻史。5年后,随北大新闻专业整体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
他的新闻史公开课甫一开场,连教室窗外都挤满了学生。讲梁启超,他随口即可背出一篇千字政论,一边背诵,一边踱步;讲到某个历史人物或事件,与此相关的正史、野史、人物、掌故,信手拈来,“就像刘宝瑞说单口相声”。
作为新中国资历最深、教龄最长的新闻史学家,方汉奇迄今培养了50多位博士生。他的学生后来多成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新闻学院的中坚力量。
“老师对我们在学习研究上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包括要看什么书、写什么读书报告、写多长时间。”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程曼丽回忆,“但他也特别关心学生的生活,给学生介绍过对象,还让师母熬粥,他给生病的学生送去。”
1997年,程曼丽应邀访问台湾。在她生日那天,同行的涂光晋教授打开方汉奇委托自己带来的亲笔贺信,令她既惊喜又温暖。
冷板凳上“打深井”
2023年6月17日,《〈大公报〉全史(1902—1949)》首发。该研究被称为中国新闻史研究中“个案史的重要成就”“‘打深井’的样本和标杆”。方汉奇的书房里就放着这套书。
方汉奇一直提倡“打深井”、多做个案研究。这意味着要达到前人未至的深度,要重视报刊原件、新解密的档案资料和口述历史的搜集整理工作。
早在1985年,方汉奇就在《新闻史是历史的科学》中强调“一手资料”的重要性。当时的中国新闻史研究,一度存在“以论带史”甚至“以论代史”的问题。
“史论结合,没史怎么论呢?有的放矢,实事求是,得有个‘事’才能求到那个‘是’吧?所以,客观存在的媒体是第一性的,对它进行研究是第二性的。这方面,是一个本和末的关系。”在上海新闻图书馆工作的3年里,方汉奇读完了27000余期《申报》。写文章,他一般都从原件入手。
历史人物,聚讼纷纭。获得大量原始资料,才不会误判研究对象。
过去,史学家们一度认为胡政之是采访巴黎和会唯一的中国记者。但2007年《胡政之文集》出版后,新材料推翻了旧说法。方汉奇遂在《谁采访了巴黎和会?》一文中更正指出:有关巴黎和会进展情况的信息,是通过几个传者的群体,协作完成的。
“西方国家说《每日纪事》罗马时代就有,但没有证据。中国唐代有进奏院状,宋代有‘小报’,明代有报纸原件,我们不断有新的发现……原件最有说服力,比据说什么的要强得多。”方汉奇说。
为全面了解邵飘萍,方汉奇曾前往北京、上海、无锡等地专程拜访他的妻子和儿女,并走访罗章龙,请教萨空了。他还拿着20倍的放大镜观察邵飘萍在日本的照片,记录书刊171册,可见书名16种。
考证中国最早的报纸始见于唐代,为《大公报》摘掉“小骂大帮忙”的帽子,确认邵飘萍中共党员身份……如此这般,遍读文献,寻访人证,抽丝剥茧,成为方汉奇年复一年的治史日常。
做卡片,是他做学问的一个基本程序。所有看的材料、写的文章、引文根据,都要做成卡片。以图书馆卡片为样式,标题点明性质,正文下接出处,一般按照人物、事件、类型等来写,摆在桌上方便进行综合分析。
这个方法他也教给了他的学生们。在他的影响下,学生程曼丽制作的学术卡片塞满了三四个大抽屉。
“实际上,我写的书里那些统计数字、引文都是平常做卡片积累的,这么多内容哪能全部都记住,但是做了卡片,它一辈子为你服务。”半个多世纪以来,方汉奇写了近10万张卡片。
“感兴趣是新闻人的基因”
2004年,方汉奇退休了,但他一直没闲着,70岁学电脑,80多岁开微博,年近90岁用微信。过去的手写卡片,变成了现在的“电子卡片”:电脑硬盘里,有条不紊地放着各类新闻史资料,一个个文件夹全部按内容、地区等分门别类。墙上,挂着国学大师梁漱溟赠予他的题词:“何思何虑,至大至刚”。
如今,97岁的方汉奇独居北京。儿女在国外,和父亲保持微信联系。妻子晓芙去世后,方汉奇不愿找一个住家的保姆,怕保姆无聊时会看电视,影响他工作,只请了定时送饭的钟点工。
2017年,方汉奇获得第六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100万元人民币奖金,他决定全部捐给中国新闻史学会。去转账的时候,银行工作人员误以为这位白发老人遭遇诈骗,差点报警,成为“冬日里最暖心的乌龙”。
除了买书这个最大的花销,方汉奇节俭了一辈子。书房的皮沙发上,贴着膏药做的“补丁”。方汉奇为客人准备了精致的茶具,但他自己的茶杯,却是一只款式老旧的玻璃杯,杯壁早已不再透亮。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陈昌凤回忆,师母在的时候,连开灯都有讲究,规定几点之后才能开。
书斋之外,方汉奇是“行万里路”的践行者。他的学识,得之于书山文海,也取诸山南海北。除了西藏,他去过中国其他所有省份。“现在铁路修到林芝了,希望有机会去一趟西藏。”在方汉奇看来,旅行能提升对人文社会和历史的了解,是很好的积累。
音乐和体育,也是他的兴趣所在。他喜欢京剧,演过话剧,指挥过合唱,闲暇时弹弹钢琴,曾是人大新闻系乒乓球代表队的“绝对主力”……
谈起对新闻学子的期望,方汉奇说:“学新闻,就应该是对所有的事情都感兴趣,凡是新鲜的事儿你都感兴趣。当然,搞新闻史还得对历史感兴趣,要多做这方面的积累。所有人类感兴趣的我都感兴趣,这就是学新闻的人的一个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