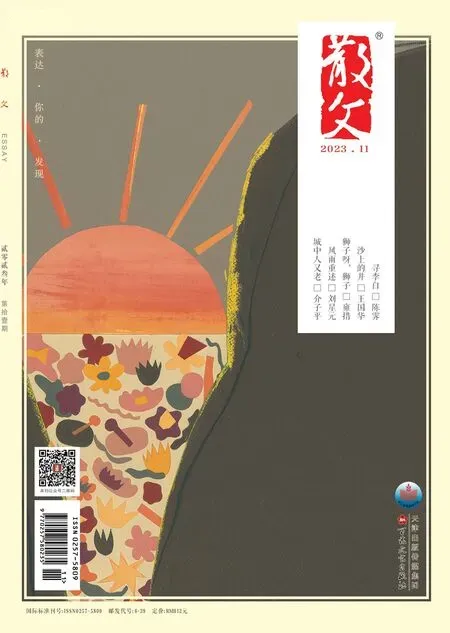麻与木
孙远刚
一
苎麻有宿根,无须栽种。成熟的苎麻一人多高,拇指粗细,叶子三分像桑。苎麻重头戏在收,一年两季,头麻和二麻。虽是只收不种,头遍二遍的麻草要锄,不但要锄,还要精锄。父亲说:“锄头底下有黄金。”
年后天气好,东风瘦马,残雪比马还要跑得快。冻土从下往上开化,表面一层硬壳,内里松软得像一块酥,一锹裁下去,“扑哧”一身。春耕还没有开始,最勤快的人家也没到田里望一眼。这时,铁匠店开门点火,初春的山野弥散着湿煤燃烧的气味。昼长,人易饿,麻地开始出麻头。麻头肥嫩,是纯正的草原绿,让人不忍加害。赶在清明之前要锄头麻草,清明之后锄头就进不去了。
见到春分,麻开始贪条子,蹿得很快,到了夏至,头麻可以上手剥了。这时候,水田里秧事完结,暂无他事,出现的空当,正好剥头麻。剥麻一般在一天中的这样两个时段:下午三四点到天黑前好一大会儿,另一个时段是从天麻麻亮到太阳出山管事。
剥麻徒手,左右配合,右为主手:弯下腰,在离地一尺左右的地方将麻秆往怀里一折,顺势往前一送,麻皮裂成两片,右手食指一抠,往后一带,左手一撕,再一勾一带,两片麻上手,右手往左手一交,暂由左手集中保管,一棵麻剥皮成功,直一下腰。地上戳着半截麻桩,躺着一根长长的麻秸。
剥麻不是重体力,只是费腰,麻农到老,大都腰肌劳损,在村道上边走边捶腰眼。除了腰,就是手指。左手不是太费,右手食指的一勾一带,最是吃劲。长期剥麻的人,右手食指都格外粗壮有力,像钢钩一样,这一异常,也是丘陵剥麻人的一个标志。
左手的麻片越积越多,满把叫作“一手麻”。成人三手麻扎一个麻头。父亲手大,母亲和姐姐手小,三人搭班合伙,父亲要快,姐姐要赶,母亲居中就好。三手麻都交到父亲手中,父亲拎着麻尾,兜头一绾,抽一片麻在颈部一扎,往地上一扔,一个人偶一样的麻头就成了。
二
晚上剥回的麻头挑进村子,扔到涧湾里泡着,早上剥回的麻头自带露水,现剥现刮,不用泡。
吃过早饭,已经不早,在门口树荫下,一条长板凳配两只二号板凳,长板凳两端各放开一个麻头,父母对坐,开始刮麻。母亲坐下就刮,草绿色的麻皮翻飞,去皮后牙黄色的麻肉交到左手,左手满了,一拧一窝,放到板凳中间。父亲不慌不忙。他先把收音机打开,吱吱地调台,调到中意后,才坐下来开始刮麻。
父亲打花(磨蹭),母亲并不说,她知道,男人一上手,她是赶不上的。等父母同时刮麻的时候,树上的蝉就忘记了鸣叫,脚下的一条石涧也安静下来,只听见麻刀和麻筒撞击的声音,叮叮当当,合铙钹一样,回响在山坳里。
刮麻的工具是麻刀和刀筒。麻刀是在一个冬瓜形的短小木柄上装一块矩形黑铁片,长五厘米,宽两厘米,厚一毫米,刀面略呈弧形,刃厚,或说无刃。刀筒套在右手大拇指上,是一个五厘米高、一厘米厚的玛铁圆筒。刮麻时,刀在下筒在上,麻片夹在中间,刀筒配合。具体的步骤是:伸左手捏住一片麻根部,皮朝上肉在下,刀在右手,右手大拇指一翘,虎口一张,带动刀和筒张开,于离麻皮根部二十厘米的地方,用刀和筒将麻片叼住,夹紧,略微翻腕,刀口稍稍上扬,用力顺手往右一拉,皮飞肉现,皮是皮麻是麻,干干净净。再掉过头,刮掉另一端。父亲手大刀沉,一次叼三片在手,一拖三,母亲两片,姐姐只能刮一片。
晴好的日子,只一个太阳,麻就能晾干。麻晾在一根根粗大的草绳上,草绳两头固定在地上,中间用木叉撑起来。傍晚,在影子斜长的晒场上收扎,一仔归一仔,长度相同的归一仔。卖麻的时候,根据色泽和长度分级,色泽越亮,长度越长,等级越高,价也最高。同一块麻地长的麻,长度几乎一样,倒是无须劳神去分。
负责“扎晒”的一般是父亲。这时,母亲带着姐姐扛着麻秆,迎着暮色,又下地去了。
除了“扎晒”,父亲还要负责砍麻桩。父亲挥动长柄大弯刀,那刀横着扫,一扫一大片,像是蒙古人在草原上打草。
二麻过夏,秋天结籽,又有麻蚕吃麻叶,产量不比头麻。剥、刮、晒、收的程序是一样的,不一样的地方有三:一是剥二麻已是老秋天气,风冷,早晚要穿打糙的旧袄;二是二麻不需要砍桩,麻桩在冬天的雨雪里自己烂掉;三是二麻后要挑麻土压桩护根才能过冬。
三
山中多树,山里不缺好木匠。木匠分粗细,做全堂家具的叫细木,架屋割材的叫圆木。不叫“粗木”,“粗”字不好听,叫“圆木”。能做细木就能做圆木,能做圆木的不一定能做细木。只做圆木的,常常是那些学艺不精的木匠,把“吃师父掴溜子”的笑话背在身上背一生。我师范同学俊生的父亲就是“圆木”,他在乡农具厂工作,靠着一把小斧头,培养出三个老中专生,也是一方佳话。
八仙桌是木器江湖中的首领,结结实实,浑身不用一根钉,方正而有稳定性,有点反几何。在木匠这一行里摸爬滚打,能打一张上好的八仙桌,是一个好木匠的标志。说起自己的手艺,木匠一般不会自吹自擂,往往会说得很含蓄:谁谁家的八仙桌是我打的,你可以去看看。又幽幽地补一句:从十层楼上摔下来,你看有没有事。
皖中丘陵人家,八仙桌传代,讲究“槐(怀)中抱梓(子),四时有榆(余)”,即槐树边,梓树堂,四条榆树腿。
八仙桌摆正堂,享有尊位。生产队时,按户头分东西,算不算一户人家,不凭人多,不凭嘴说,要看你家里有没有一张八仙桌。有,一人也算一户。遇到红白喜事,全村的八仙桌相互拆借,不能不借,本村不够,还要上邻村去借。八仙桌上分席次,上横坐尊者长者,一席二席坐贵客娇客,和使壶的“酒司令”坐一条凳子,叫“叨陪末席”。厅堂里摆了不止一张八仙桌,要分主席、次席、余席。席上若是凑不齐八位,倘或只有六位,要忌讳坐成“乌龟席”,有年轻人不懂,就那样坐了,会有长者上来提醒:“坐爬得了!”
四
铁头木柄,是一种合作,知长论短,然而木柄终究难脱指使的嫌疑。
铁木的代表,要数一张犁了。一张木犁的组件有:榆木犁弓、檀木犁梢、榉木犁底,雪亮的犁尖和失聪的犁耳。几大组件到位,一张犁就有了行动的自由,也有了在大地上作画的冲动。牛在前头走,泥向左手翻,一块块泥筒,一道道绳纹,带着浆,起着旋,耳畔似有父辈的喝牛声回响在山坳。
伴手的小件农具,大多为铁木器。镰、锄、铲、锨、镐、叉。常见有一种半月锄,叫“荷锄”,“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锄者,助也。一把好锄,有这样两项标准:一是吃土不沾土;二是锄柄非笔直而是带一点向下的“肚子”,使起来趁手省力。锄是手的延长,时间久了,锄手合二为一,物我一体,“以神遇而不以目视”,这是锄禾的上境。
齿类铁木,分四齿和二齿,没有三齿也没有五齿。四齿曰耙,二齿叫抓。刚出铁匠店的四齿耙和二齿抓,齿尖都是方形的,像年轻人的门牙。击壤叩石,累月经年,就不同程度地“战损”,有的豁了口,有的卷了刃,有的尖了嘴。
春头上,秦记铁匠店动火,连夜赶工,火星飞溅,仿佛天明就要起义似的。地上摆着的都是各家送来待修的铁家伙,脑门上用粉笔号着字,“世主”“自仁”“荣寿”“华道”“远新”。
铲子是最小型的铁木器,小到可以放进竹篮里或是藏进袖筒里。可别联想到锅铲,它完全不同于锅铲。它由两个部分组合而成,铁质的三角形铲头,T 形木质手柄,柄长约莫二十厘米。铲子用于那些精细的耕作,除草或是栽插,取蹲姿,常用于菜园子或高秆密植作物的间隙,也适合那些太小或太老、拿不动锄头的家庭成员。铁吃土,土也磨铁,可终究是土吃了铁,和吃了它的主人一样。“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
丘陵易旱,盛水运水的木盆和木桶,数量上比别处要多,用起来也伤。抗旱的时候,家中劳力要人手一担桶,这也是别处做不到的。早先有专门的箍桶匠,我记事时就没有了,木桶全部交给了木匠。
木盆木桶都用铁箍,铁箍从铁匠店买现成的,板与板拼接用竹钉。常常,盆散了,桶碎了,板也不知去向,只剩下铁箍。桶箍可以用来推圈。放学路上,一个人推一个圈,一队孩子,走在高高的大埂上。
我曾有一只乒乓球拍,是用旧粪桶板自做的,桶板有弧形,瓦一样的不平,接发球总是跑偏,小伙伴们笑我“臭球”。
五
山里有一种鸟叫“渔郎”,不鸣,善捕。父亲有一张搭网,棉网线,网眼密,用猪血煮过,滤水极快。
这里山多水少,鱼不上斤,虾不足两,山中捕鱼,空劳身心。好在父亲有一张好网。他的网,削桐作浮,熬铅为坠,两支长竿,竿底装“木脚”,竿中有挡水的橡皮圈。父亲身背鱼篓,站在埂上,将那一对“木脚”顶在大腿正面,身子弓起,用力一甩。“唰”的一声,网撇出去,撒得很满。待网落实,肩扛竹篙,抖动,向中间,再慢慢起网。网口出水要慢,慢,鱼不惊。有时,网绳绷得笔直,竹竿压得弯弯,我以为一定是有“大货”了。父亲却很淡定,知道那不是大鱼,他手上有分寸,一定是网到了石头,或是网底挂住了水中的木桩。
“捞鱼摸虾,失误庄稼。”父亲不顾这样的教训,打鱼令他快乐。起网时,他常常念唱:“十网打鱼九网空啊,打到一网就成功哎。”自嗨的样子,有点像《水浒》中的阮小七。每一网都满怀希望,穷日子里,快乐和希望,是比鲜鱼活虾要强上百倍的东西。
父亲一直想要而又一直没有的,是一把鸟铳。我堂叔有一把,油桃木柄,乌黑的枪管,紫铜的鸡头,黄牛角的药盒。堂叔的枪倒不外借。父亲服过兵役,戴过船形帽,用过俄制莫辛纳甘,那可是“二战”名枪,他见不得堂叔宝贝自己的枪。
冬天日暮,我跟堂叔进竹园打鸟,鸟宿在竹园中间的一棵大朴树上。堂叔持枪在前,枪口朝上,我蹑手蹑脚地跟在后面。到了大树跟前,他示意我后退,举起枪,一扣扳机,“轰”的一声,堂叔面前腾起一团火球。一树的鸟像树叶一样朝天上飞去,半天,一根鸟毛也没有落地。
堂叔猎获的最大动物是一头獐。那是一头棕黄色的獐子,闪着恐惧的眼神,偶蹄,穿着精巧的“皮鞋”。它被堂叔用一根绳子拴在院中的芭蕉树下面。蕉叶覆鹿,不知所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