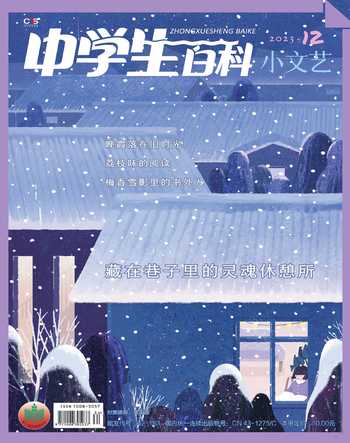果味空间
说不清从什么时候养成的习惯,每周都会去一两次果味空间。有时候是看免费放映的小众电影,有时候是买票看爵士乐三重奏之类的演出,有时候是去旁观或参与“读点什么”的活动,也有时候没有特定的目的,在沙发上坐一会儿,随便点一杯什么来喝,翻翻架子上的出版物,也会觉得非常惬意。

最早知道果味空间,是因为喜欢一支乐队,乐队里的吉他手和几个朋友一起创建了它。起初他们常常在某个社交平台更新活动的消息。这些消息对一个被早晚自习和考试包围的学生来说,是一种期待与美好。那时候,我常常想,将来要去看看,但后来这个平台停更了,我还以为这个空间正如许多文化场所那样因为收入没法维持运转而寿终正寝,惋惜了几秒,便没再多留意。
在北京生活了许多年,如愿去看了乐队的演出,但从没有人向我提起这个场所。直到几个月前我偶然刷到这个吉他手演出的视频,他用化名自弹自唱了一首《几度夕阳红》。我这才恍然,原来果味空间一直存在,只是活动的消息更新转移到了别的社交平台。
这个地方很不好找,我跟着导航走,几次都走过或者到了马路对面,费了不少周折,最终才找到它。原来墙上探出来的那个小小的水果图案处便是入口。果味空间在地下室,要顺着咯吱咯吱响的木头梯子走下去。进门后右手边是个买饮料的地方,再往前有个售卖唱片和二手物件的小开间,最里面则是演出和放映的场所。这个场所有可供投影的白墙,也有一些演出设备,还有二十来把椅子立着。
第一次去,看的是一部格鲁吉亚电影。电影讲了前总统在全国各地收集各色古树,搬到自己庄园里来的故事,那奇诡而壮丽的画面动人心魄。

与电影院或者剧场相比,果味空间实在不是个舒适的场所。它在社交媒体上的简介非常实在:“东城区美术馆东街13号的一个音量没法很大,人一多什么都看不见,网也不好的破地下室,附近还没有好吃的。”如果不及时赶到,抢到第一排的位置,几乎看不清字幕,有时候半边投影都会被前面的人挡住。椅子也非常硬,半个小时便会坐立难安,纷纷开始伸展脊柱,按腰揉背。免费的放映不能要求太多,有时候连关灯都靠老板指挥观众,也有时候画面突然卡住,一群人眼看着鼠标在投影上挪移,调试一两分钟才能继续放映,但我依然忍不住一次又一次地去到那里。
我在果味空间里还认识了一些新的朋友,有画画的,有写小说的,有做音乐的,也有热爱文艺的普通上班族。我和他们聊起喜欢果味空间的原因。有人喜欢这种地下的氛围,在阴暗幽深的空间里聚会,远离了地上的车水马龙和吵闹喧扰。有人喜欢这里的独立乐队,享受看着一支不为人知的乐队成长起来的美妙成就感。但我想这些都不属于我喜欢这里的真正原因。
念书的时候,我常常和朋友聊起一些师兄师姐的人生轨迹,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一个私密的发现:人的生活道路似乎并非越走越宽广,相反常常是越来越狭窄。上学的时候,同学来自天南海北,有全然不同的出身,父母从事着不同的职业;上班的時候,找一份还算体面的工作,接触同一领域优秀的人,每天与相似的工作打交道,时光就这样一天天流逝了。对很多人来说,倒也算平安顺遂的一生,但对有些人,特别是创作者而言,却需要格外警惕。我想我就是那种对他人的生活永远葆有旺盛的好奇心的人,一成不变的生活不但给不了我安全感,反而会使我空虚。
果味空间于我,意味着生活空间的暂时更迭。我走出写字楼,也走出蜗居狭小的空间,去果味空间,这看似是去逼仄的地下室,实际上却是去更广阔的世界。摩肩接踵的环境可能没有高级餐厅的优雅与宁静,却能让我清楚地听到旁边人聊天的内容,在自然的契机里认识一些平时根本不会有交集的新朋友。那些对话中乍现的金句令我们大笑不止。果味空间常常播放一些网络资源并不好找的纪录片,展现异国他乡不为人知的生活。那些陌生又新鲜的画面能唤醒内心相似的情感,让我久久不能忘怀。
在果味空间之外,我也寻找着别的场所,对陌生事物的探索使我精神振奋。我与朋友在白塔寺旁的胡同里品尝美味的湘菜,在东四大街上闲逛已经罕见的唱片店,也会独自去看一些展览或演出。这些行径是注定与过往不同的体验和生命经历。正如在中学时代,我与朋友穿过城市地下的防空洞,探寻我家附近废弃已久的宾馆,爬郊区鲜有人至的野山。这些片段或许不能帮我得到怎样的分数,拿下怎样的奖项,进入怎样的院校,但它们丰富着我的心灵,使我成长为更加独特的人。我想,这正是探索与发现的意义。
顾一灯
北京大学法学和经济学双学士,现居北京。小说、散文见于《儿童文学》《少年文艺》等刊,获第六届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第七届“周庄杯”全国儿童文学短篇小说大赛三等奖及第八届二等奖。已出版长篇小说《冰上飞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