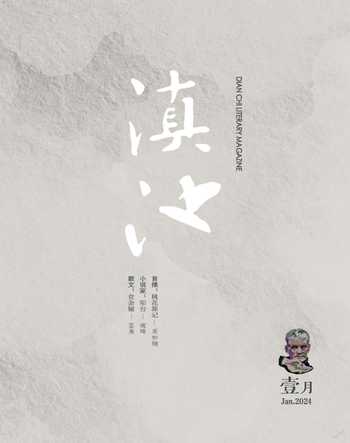事物的语言化(评论)
徐建江
本人并没有能力在《风窗辞退了鼓手》中的各首诗之间做出优劣的选择或判断,但为了避免赏析时可能遇见的语言的盲目,就需要对内容做一个选择。选择《长安书》进行赏析,仅出于个人的直觉喜好。
“大巴车淌过早春单行道。翻腾我七秒钟的小心思——”
大巴车、早春、单行道的命名,正试图将一个存在之“所在”给揭示出来:在这由句号隔开的前半句中,一個“有所安置”的在场样态,正在被诗人尝试召入眼前。而“七秒钟的小心思”这样的语词,则被塞满了现时代(或曰流行语)的语言特色。这样的语言特色,直接地给诗人的言语打上了过于明显的眼前之未经沉淀的时间印记。
“九公里、三个侯到令人发绿的十字路口
啃着大号电池的水果摊喇叭,像站错位置的
急救电话”
一个较长的命名:在对事物的诸样态的昭示之中,似乎正试图将某种隐而未现的存在解蔽出来。而在诗歌里的这种解蔽过程,本质上正是诗歌之言语的创造活动本身——诗歌之语言正尝试道出自身。
“又一次警示我:
你正坐在寂静的弯曲处挑拣惺忪的碎发。”
存在在这里获得了稳定的“在场性”——诗人之境况的被警示,坐在寂静的弯曲处——诗人完成了对自我的安置。这是诗人与自我相遇的方式:通过眼前之物提出的警示——“事物的语言化”正是从这里开始。眼前之物不仅仅在“道说”着自身,不仅仅作为有所存在之物不断地将自身“给出”,而且在其发出的警示之中,完成了对诗人的“安置”。
在某一首诗中的这种由事物发起的安置活动中,正是诗人实现天、地、神、人之相晤的可能之一。
在接下来的两段中,诸能指材料并未能精确地将其所指指明。这或许是诗歌语言的一种“开放性”——它总是想要尝试让诸意象自行道说,但这种道说能否成功,则在于诗人之有意识的编排是否有序。而这也正是事物之“语言化”真正开始的时候——语言与诸存在物之存在各行其是,又在它们的类似之中得以互通——语言指示着存在,存在在语言中获得澄明。
“游戏、短视频”等“现实性/此刻性”的意象再次出现。就语言自身意义的不可阻断性来说,它们揭示了诸“现时性”存在物之存在的不稳定性——它们将在自身的“临在”之中不断地塌陷。在这种存在之塌陷的境遇之中,建筑于其上的诗也面临着自身“完整性”的缺失。或许诗人接下来会对这种缺失的完整性做一个“寻回”的努力。
直至“为了讨回一块不存在的糖果”,诗人似乎标明了一个永恒的主题——找寻。但这种找寻指向何物?或者说,指向何在?或许正是指向与之前诗句中闪现过的临在之物的反面,即“永恒性”之所在。这一次指向,也对诗歌的完整性做了一次弥补。
“早春风剪去二月的第一根灰指甲,淌过田野
充血的疼。”
在第二首的开场处,诗人展开了现代精神分析学流派的扩展:将生活中的一种具有代表性的病痛赋予风,而这种风又被赋予了“早春”的限定。灰指甲,从本原上来说,它并不具有通常意义上来讲的“诗意”——它并不“美”,甚至是携带着一种厌恶感。但正是在这种厌恶感之下,掩藏着诗人(患者)由肉体侵入的精神的病痛折磨。它为后半句中“充血的疼”提供了一个可靠的依据,当这种可靠的依据被赋予“疼”这个字眼的时候,诗人获得了精神的抚慰——语言成了一种麻醉剂,诗人通过对疼痛的“指明”,来获得安慰。事物的语言化进程,也在这里与诗人的精神结合。
“剥开这些渺小的事物:一枚红橘,几只搓脚的蜜蜂
掬水的鼓瑟的歌谣 。”
这里诗人真正独立地完成了自己的“命名活动”:剥开这些渺小的事物,是诗人的一次真正地“召唤活动”。红橘、蜜蜂,被诗人先后召唤出来,并且赋予了“红”和“搓脚”的颜色和动作上的限定——真正的命名。然后赋予它们以真正的“存在”——歌谣。在这里,“歌谣”或许是诗人的另一个对其做出了“掬水的”限定的命名物,也或者是对前面红橘和蜜蜂的“安置”——将它们置入歌谣之中,让它们获得了一个“在场性”。
“田野间一只料峭的屋子,门进进出出
打着手势,我们怎么也走不进
它的视线里。”
在这里诗人又完成了一次精神分析学的创造:将我们“置入了”田野间的屋子的“视线”下。人在这里寻求着精神的归宿,而“屋子”作为一个古老的意象,对主体的这种搜寻提供了“应答”。但它的这种应答的方式,则是一种更具精神分析学原理“梦境式”的解析,即它选择无视我们。
这里可以引入一个更古老的精神现象学原理的公式,黑格尔:“辩证法是在别他之中自我永恒的反思”。
“如果燕子还未衔来最早的观众,它将有一节
早餐盒般长短的
排练时间:……”
诗人在这里完成了神话学原理的创造,即将主体之“思的主动”赋予了物(燕子)。在这种古老的创造形式中,主体寻求着人类最早的精神庇佑。即通过赋予在世之物以“思与动”的主观能力,以将自我安置入由诸神代表的在世之诸物间——不再觉得孤独,不再感受恐惧。
而这种创造活动一直延续下去,因为燕子一直扮演着它的角色直到下一段,直到它被油菜花取代。
“油菜花除了油菜花
什,么,都,不,承,担。”
诗人最后获得了觉醒,这种觉醒在最后一次命名中得以完成:油菜花只是油菜花,它只是它自己,并不承担他物。诗人抛开了前面的精神的反思,以及神话的创造,而选择让事物“各是其所是”。
这是否意味着事物的语言化的进程在此失败呢?事物开始言说其自身的时候,是在我们赋予它们能思与能动的主体性的时候呢,还是在我们对它们做出本质的还原的时候呢?帕斯卡尔说:“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那么芦苇是不是一个能思想的人呢?
但无可置疑的是:诗的语言,是一场凝滞的等待展开的“对谈”。在那里,万物开始藉由它们的存在,而向我们道出其自身。我们做着精神的反思、做着神话的创造,都只为了能在一个充满原始暴力的在世之诸物间,寻求一个足以安置自我的合理依据。
本栏责任编辑 胡兴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