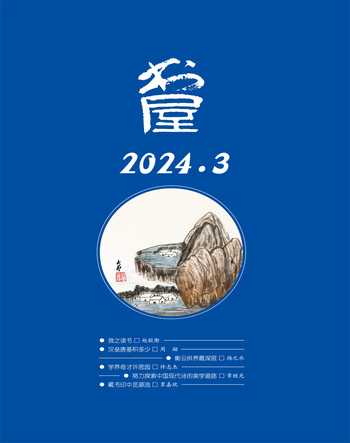我之读书
赵毅衡
首先申明,这个文章的标题不通,不过我的一生许多事情都说不通。“我、读书、读我”,一辈子无非就是在读书中读我;“我读书,书读我”,书遇到了我,是我之福;“我读,书读我”,没有我读的书,我也不成为我。我写下这些,只是给自己看,或者说,给自己一个交代。
籍贯
有些人根本就没有童年,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九岁之前,我的记忆是一片空白。要回答究竟何处是家乡,竟然是我一生说不清的事,让我很难为情。经常有人问到我对“家乡”桂林的山水之忆,其实桂林只是我的出生地。中国人至今认为籍贯重要,籍贯却是一个任何人都说不清楚也无法翻译的奇怪概念,对人生有意义的是在何处度过童年。这三者之间的混淆,让我成为一个“需要解释的人”。
勉为其难地解释一下。姓赵,这没什么可解释的,百家姓第一姓,我不认为与有荣焉。我的“籍贯”(“父亲的故乡”)应当是浙江金华府的东阳。童年最糟糕的记忆是被小伙伴笑“东洋人”。现在东阳很神气,是全国著名“先富起来”的出口大县,横店影视城是东阳人的绝招,紧邻的义乌是著名的“世界小商品之都”。不过,过去的谐音耻辱,今日的生意智慧,都与我无关。其实东阳在哪里我都不甚了了,一辈子没有去过;东阳方言是奇怪的噪声,从来没学会一句。父亲与来访的亲戚说话,听来如鸟鸣。
父亲会自豪地说:我们东阳姓赵的,是中原皇族之后。宋高宗南渡,中原人大量迁居,多散布于浙北。父亲还不忘辩明一句:“我们或许是赵光义的子孙,不是赵匡胤的。”这个历史精确性却让人丧气,妄吹的祖宗是读书积弱始创者。
“毅”字是否出自辈分,不清楚,我从未看到过家谱,只能姑且当作如此。至于“衡”字,才是生平关键。父母亲是抗战时期的逃亡青年,母亲家乡是宁波,外祖父在上海开布店,她自己在著名的“立信会计学院”就学。日军占领上海,爱国青年经过浙江、江西、湖南南下,途中母亲遇到了从浙江南下的父亲。他们在哪里结婚的,我没有能力考证,不过我的“衡”字来源于湖南衡阳,因为“孕于衡阳”。我可能是中国人中少有的“以孕地取名”者,解释起来颇为不便。
所以,母亲是带着肚子里的我从湖南“逃到”广西桂林。1944年,日寇发动在中国大陆的最后一场攻势,试图“打通南北交通线”。“湘桂大撤退”之中,我这个战乱之子尚无记忆。桂林山水之美,我竟然未能欣赏。我作为婴儿太钝感,感受到家国沦亡痛苦的是父母那一代人。
日军的“最后攻势”竟然势如破竹,直到贵州才被挡住。父母的逃亡继续,但路径亦非我能描述,给母亲带来的痛苦却可想而知。胚胎或襁褓中的我对此无记忆,或许也注定了我一辈子是流浪漂泊之人,很少有安定的可能。既然说不出一个任何意义上的家鄉,也就一辈子没有家乡。
不过,我大概从小就知道世间充满苦难,人生不易,所以脸相呆板,举止不灵活。从小被包着拖来带去,连爬行的机会都很少,运动能力很差,社交能力差更是可想而知的了。
童年
我那时六岁,在东江湾路小学上学。东江湾路不在上海郊区,而是市区的一条路名,在四川北路北端,是从我家居住的多伦路通往虹口公园(现在的鲁迅公园)一条不长的路。路的一边我们从来不走,那儿有日军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建的一座巨大的钢筋水泥堡垒式建筑,占满一整个街区,当时叫“港口司令部”。这个建筑已有百年,式样特殊,圆角以防射击死角,异常坚固,至今都在使用。在许多战争片、谍战片里,都可以看到这座上海人记忆中熟悉的“司令部”有摩托车驶出、日伪出动。
另一头就是我家住的多伦路,现在成了上海赫赫有名的“名人街”。原名叫窦乐安路,以1912年在此筑路的西方传教士名之。1943年改名多伦路,那是太平洋战争时期,占领上海的日伪军也看不得西方人名字。我的记忆中,这是一条石砌路(块石夯入地下做成路面),当时的南京路也是木砖砌成,现在电影中就只能用沥青路代替了。
多伦路不长,几百米而已,但是有若干大铁门的高院大宅,据说是白崇禧公馆、孔祥熙公馆、汤恩伯公馆,反正我没有见到过任何一人进出。整条街大部分是普通弄堂民居住宅。据说“左联”机关曾设于此,因此茅盾、郭沫若、沈尹默、叶圣陶、冯雪峰都曾寓居于此。当时这些人大多居无定所,也缺乏今日的购房热情,曾经租住过一阵而已。我们住的是进口第一条里弄“燕山别墅”,不过普通的民居,妄称“别墅”。据说离我家不远曾是张国焘逃港之前的居所,这点我也无从证明;李白烈士也曾住于此,他是《永不消逝的电波》的主角的人物原型。所以这一带是历史发生地。
现在的多伦路,不让拆迁,所以弄堂底子依旧,居住条件并不好,而且“化妆”太多,全是雕像之类。
最清晰的记忆是鲁迅故居,在多伦路对面的山阴路(原名施高塔路),那是比多伦路优雅的民居区,每家有个小院,就是《黄金时代》中萧红坐着不愿离开的地方。让我最感兴趣的是路口的一家书店,也就是文学史上不可能不提到的“内山书店”。抗战后,内山完造先生离开上海,书店由民主人士王造时接手。我喜欢这个书店,因为它允许我一个小孩在里面乱翻书。无人来赶我走,也不觉得我妨碍生意。我可以有根有据地吹嘘:我在鲁迅先生足迹所到之处,翻过他读书的书架,我杂乱读书的一生,就从鲁迅足下起步。
我十二岁时,此书店并入新华书店。书架被玻璃柜台和严肃的管理员挡住了,乱翻书的幸福时代就此结束。前几年我曾经经过那里,特地绕过去看了一眼,杂乱堆满了各种刊物,门面似乎不太景气。数字时代来临,很难办好一家书店了,但是这家书店应当办好。
病秧子
十岁那年,我忽然大吐血。邻居急忙把母亲从办公室叫回来,我被救护车送到医院,诊断是肺结核。
二十世纪中期,肺结核似乎专门集中攻击城市青少年,一时称作“少年肺结核”。青少年开始长身体时,营养需求量突然增加,一不注意就会跟不上。南方城市阴潮缺乏阳光,更是适宜于结核分枝杆菌传播。不过无论如何一个十岁的孩子,突然没有预兆地咯血,病情凶险,全家惊骇。
我被送到专门的肺结核病院,整个医院都是暮气沉沉的老年病人,只有我一个“儿童”,令医生护士们大为高兴:总算可调节一下气氛。拍片的结果是:有结核病灶,不大,但是正附着在支气管动脉旁,容易造成大出血呛入肺部。在医院住了不久我就出院了,但是却无法继续上学,因为病灶开放,“有传染性”。于是,初中一年级时,我第一次休学。
十九至二十世纪上半期,肺结核是一大杀手,好像专门针对文化人:鲁迅、郁达夫、瞿秋白、柔石、萧红、曹禺等都得过;国外得过肺结核的文人,名单更为显赫:契诃夫、卡夫卡、拜伦、雪莱、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似乎必须生肺结核才能成为名作家。林黛玉、茶花女似乎也是名著中得肺结核的人物。病态却是相当一致:脸色苍白,时而潮红,神态疲乏,情绪不稳。
我不是在骄傲地说我有“肺结核的文人气质”,没那样自以为是。但是小学与中学时读时辍,至少给了我不按课程读书,不管考试成绩的机会,大把时间花在读自己感兴趣的书上。放在现在,我可能连初中都无法毕业。此病纠缠我近十年,好好坏坏。病灶虽然不大,一旦“阳性”,理论上就有传染性,就必须休学。休学若干次后,我的同班同学,就换得糊涂了。最后到二十岁才算摆脱了疾病纠缠,但是一直比正常读书的同学年龄大一两岁。
少年时期,经此大病,久治不愈,大概所有的人都认为我寿数不长。现在八十出头,来写这段病史,恍如昨日。
孤僻
长期与非同龄人做同学,就缺乏与人说话的欲望,少言少语、独自静思,成了我性格的最大特征。对于那些在聚会中时而隽语连篇,时而扬声大笑,与人勾肩搭背、杯盏交错的人,我心里一直艳羡。一旦我自己模仿这样做,反而把自己吓住了,时髦话叫“社恐”。
我一直被夸作“文静”,其实是生性不善交际,一生都是独处居多,很难交上“好朋友”。加上是“有病的人”,所以体育课都是免修,运动感一直比人差,操场上交流更少。
我的运动感差,还有一次出了险情:荡秋千时,我掉了下来,幸好跌得不重,刚抬头,秋千板重重地荡了回来。我赶紧一缩头,木板从我头皮上擦了过去。事后回想,我的求生敏感还是起了作用,不然非死即伤,至少头脑不好用了,草草了此一生。这次事故我谁也没有告诉,因为连我自己也不相信我有此反应能力。
还记得少年时,伙伴们分两队踢球,人不够,我必须进入一队。但是一上场,看见球飞来,忍不住用手去挡,马上被罚下。队长怒吼:哪怕少一人也不能要你。我很惭愧,但不知道如何解释自己的失态动作。
从运动场上消失,也就是从年轻同伴中消失。从课堂上一再消失,也就从来没有固定的同学。一直到今日,我身体的灵敏度一直是所在集体中最差的。到了电脑时代,我连“筷子打法”都做不到,只能用一根手指打字。最要命的是不能盲打,必须注视键盘,打完半句话再看屏幕选字改字,速度之慢,让我羞于在人前打字。当然,用一根手指我也写了七百万字的书和文章,但是光打字花的时间都比别人多许多倍。无能就是无能,不承认没有用。
此刻想到要把这本几万字的书敲打出来,任何兴致马上消失,这劳动太艰苦。所以写此书非我所愿,实为无奈,各位将就着看。
习惯的养成
不是说我不喜欢读书,也不是说我应当成为浪漫文人,恰恰相反,我喜欢理工科的课程,只是屡被打断,难成系统。初二开始学几何,让我高兴起来:原来从几条无须证明、似乎是常识的“公理”,就可以推出整个宏大体系,解决千奇百怪的问题;而一旦改变这几条公理,就可以推演出一套完全不一样的体系。
到了高中,物理老师跟我们讲起了相对论:如果改变牛顿体系的速度与参照系关系,设定光速对于任何参照系都是不变的最高速,那么就只能变化速度的另外两个参数——时间与空间,也就是说,光速运动中的人永生不老。这又是一个好例子:公理是出发点,略一改动,就能导致整个体系的变化。哪怕公理是显而易见的常识,只要认真挑战,就会带来整个思维世界的变化。
此种改变始发公理,就能改变整个体系的“思想实验”,使我极端着迷。可能也是我自己学术生涯潜在的一个基本处理方法。也就是说,最要紧的就是思考出发点是否牢靠?是否能撑起全部要说的论述?这也成了我后来“研究学问”的路线:我必须回到基本定义再出发,不管是符号的定义、文本的定义、叙述的定义,还是艺术的定义,我都会强迫自己不断回到定义上,直到想明白了,我才能安心于这个基础上的体系。光的“波粒二象性”也使我着迷,几十年后我把它用到了叙述者的“框架-人格”二象论上,作为广义叙述学的出发点。
自学外语
到1960年,我从高中毕业后,因病升学无望,只能自学,也只有外语能一个人自学。休学后,我就很快读完了各年级教科书,然后读了一系列读物,为免读书时不断查词典,我干脆把陈昌浩编的《俄华辞典》读了个遍。后来我才知道,此种只顾“读懂”的学外语方法非常糟糕,外语并不是“知识”,而是技能。不过我当时自己得意:总算有门学问,不让高考也无奈我何。記得在高三毕业后,我翻译了著名俄国作家柯罗连科的一部中篇小说,那算是我的俄语“最高成就”,以后俄语就淡出了我的生命,现在犹如一门全新的外语。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虽然学校里还在教俄语,但已没有了用处,自学的俄语不会说也不会听,不知如何才能提高。我只有再拾一门外语才能不让自己的“休养”时间白白过去。
后来,我下定决心自学英语,学法如旧,幸亏英语语法易学,只是英语读音混乱,得靠国际音标自己想象。没有老师,我又只能重复一厢情愿的老路,拿一本《英汉词典》背下来,那样就可以不需要时时翻词典,可以直接读作品。一旦多读,语感就自己来了。
当然,这学习方式完全违反今日的“听说写读”四会要求,我的听与说能力,是后来在英语国家的教学生活补上的。至今我的语音不漂亮,不像“牛桥”英式,也不像新英格兰美式。不过这可能与学习方法关系不大,而与我感觉迟钝有关,哪怕我一开始就全力以赴跟读“灵格风”唱片,也不会像嘴巧舌利的同学那样惟妙惟肖。此种默读先行的方式,也许正适合我的处境。这不是狡辩:我至今嘴笨,方言学不会,说普通话却乡音难改。
我最后一次休学是在十七岁高中毕业后,长期“休学”,实际上就是失学,我变成了一位不属于任何学校或单位的人。
休养年月
我十七岁高中毕业后,因肺结核病人不能考大学,就成了一个失业又失学的无身份的人,上海话叫作在家“吃老米饭”,当时称作“社会青年”,即无职无业者,现在的说法叫“啃老”,总之,都是很让人屈辱的名称。
休息了一阵,发现身体里的结核分枝杆菌很坏,我越着急它们就越不愿离开。我就开始找临时工作。最简单的就是当中小学代课教师,我唯一“系统”学习过的科目就是俄语了。上海学校多,代课教师工作好找,按课付酬,因此我到各种中小学上过俄语课,反正教的都是字母表与最简单的几句话。我的教师生涯极其失败,遇到的困难几乎是一个样的:学生对一个小青年模样的瘦弱家伙,有什么必要给面子?不闹白不闹,于是下狠劲扰乱课堂秩序。
我能不能维持代课,完全看我镇住课堂的能力。记得教一个小学,我头一背过去到黑板上写字,下面马上炸开了锅:乱打乱闹,乱扔纸团泥团,直接打到黑板上,我回过身去,刹那间全班静坐。我看到几个捣蛋鬼,大多是坐在后排,但是我知道代课教师不能去惩戒。于是课上越闹越凶,直到校长站到门口,教室里已经满地狼藉。
好不容易到下课铃声响了,校长叹口气,说你可以找中学班试试,这些“小赤佬”拿你开心呢。于是我找了一个女中,心想初中女生会规矩一些。不料女生比男生还会闹腾,还加上一些尖叫哭闹,依然要弄到校长来,教室才安静下来。我这才明白:上课不需要知识,上课需要威慑手段、压服能力,需要有一些领袖人物的魅力。我二者俱缺,根本不是当老师的料子。从此不敢教年轻学生,本科都不太敢,中小学学生则避之不及。
1963年高考
1963年3月,我按常规检查胸部,突然发现肺结核病灶已经吸收纤维化,也就是说不再有传染性,可以考大学了。的确以后一辈子也没有再犯过。我想原因是那年我二十岁了,“少年肺结核”在年龄上已经不适合我,加上1962年底,所谓“三年困难时期”早已谢幕,营养稍微好了一点,所以就“突然好转”。
正好赶上1963年,这一年的高考“政治上”是最松的,对我这样的“出身不好青年”比较宽容一些。总之,天赐良机。
当时离6月考试只剩三个月。我原先的志愿是建筑,这下子无论如何来不及准备了。三年来,我的时间基本上献给外语。高考机会难得,理应求个保险考俄语,但是我知道今后的日子会很难受。虽然我的英语只是自修所得,我还是决定冒险考英语。
这个选择是对的。虽然冒了可能失去唯一一次高考机会之险,但是避免了今后一辈子的苦恼。我那一届外语系的邻班俄语专业,不久就教学两疲,完全失去学习目的,因为知道在学一个绝对“无用之学”。那时连中小学都停止学俄语,不再需要教师。全班年轻学子,面对完全无用的课业,那种无出路之颓唐,让我今天想起都为之心摧。
读者(如果这些笔记会有读者的话)可能会觉得我的整个青少年时期一片灰暗:从小多病,出身不好,屡遭不幸。其实这是因为不愉快记忆比较难忘,回忆起来冒在头里。实际上年轻还是有其快乐:看了不少“杂”书,看了不少电影。离家几里路有个电影院专放旧电影,票价一毛。而且经济上不太发愁,父母亲工作上遭贬抑,降薪受罚,但是工资还是稳定。我们子女每个月有十多元生活费,后来读大学时有二十元,毕业后有了自己的工资,每月四十多元。虽然一直是“月光族”,从来无法渴求奢侈品,但也没有为生活摆过摊。
而且,回忆中始终有些小得意的是:我一直不怕考试,无论是高考还是考研,无论是初试还是复试,只要给我时间准备,就经常是第一。这种能力让我极端欢迎任何考试,甚至任何“业务”评比,而努力躲开任何不透明的暗箱选拔。一句话,书呆子的事,我能做得比别人好,恐怕不是比人聪明,而是我比较善于集中心力。下面我会讲到,这并不全是好事,因为绝大多数人會“索取心理赔偿”,在各种场合有意无意地使坏。
读杂书的好处
前面说过,我因为嘴舌并不灵巧,口语上模仿能力很一般。只不过由于多年乱读书,加上来自上海“十里洋场”,在读书与写作上,在词汇量上,在广义的知识储备上,的确远远超过许多同学。上大学时,低年级课程的内容对我来说太容易,我往往拿了一本英文小说,坐在后排,老师们也知道,让给我一点空间,两得其便。
本来此事也可以理解,毕竟我多读了几年的书,毕竟我来自一个不缺少书的环境。说实话,我没有故意炫耀,也没有什么显摆的机会。我想只有一两次被同学“考词汇”,他们会挑一个词问我,如“guam”,我脱口而出:“关岛。”“那么‘guano呢?”“鸟粪肥料。”我的词汇量已成传说,经常会有人挑怪词来考验一下。
现在我已过了八十,依然经常考自己:见到一物,要能说出英文。不然,我会立即去翻词典,非要记住不可。因年纪渐渐丢失的词汇不多,伤心的是,时代创造的新名目越来越多了。
我在中学屡次休学养成的乱读书习惯一直保持了下来。在三十五岁考取研究生之前,我读书一直很随性,抓到有趣的书就读,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也不管是什么内容。任何影印出版的书,科技书、历史书、地理书、心理书、生理书、算命卜卦书。总之,只要有书便是节日。只要你不挑拣,总能找到书;只要你愿意,总能找到时间读书。有时我看见不喜欢读书的人,百无聊赖打发时间,觉得心痛:不是心痛他们的时间(那无法强求),而是心痛没有用起来的时间本身。
我在无人布置、也无读书目标的环境下,过了几十年乱读书的岁月,没有方向,也没有计划。或许幸好书太难找,只能找到就读,没有让我过早地进入一个“专业”。此种经历,对我今后好处无穷。今日的青年学子,无论在校还是离校,都已经不再如此读书:一旦读什么书都要有个目的,讲究个用处,既失去了自己找书读的乐趣,也不再有多方向扩大视野的福气。相比于用常规方式读书的人,或许我的知识面更宽一些。这貌似浪费精力,但当我正式开始“做自己的学问”时,也不太会过于局限于本专业的现成意见。
一生中有此种“自我得意”的機会不多,大部分时间读书的困难不在书难读,在于读书难……
军垦农场
1968年大学毕业后,我们这批毕业生无工作可分配,连中小学也不要教师。于是全部到军垦农场锻炼两年。所有新开垦的农田都会碰到鼠灾。原先湖边上勉强生存的田鼠,忽然得到巨大的生存空间和粮食供应,包括垦荒人群的生活残留物,鼠类巨大的生殖能力被激发出来。特别猖狂的是一种黑线鼠,它们携带着“出血热”病毒。这是一类病毒的总称,大量出现于新开垦的荒地。得病之初症状令人迷惑,大抵是发热38℃或略高,此时必须送医院紧急治疗。一旦发展到中期,肾肺衰竭,会突然死亡,无药可救。
这就出了大难题,因为秋冬之交,极易感冒,发低烧机会太多。也许是记取了汕头“牛田洋”军垦农场海难的教训,只要有风险就不敢怠慢。农场有人发烧,就紧急送往霍邱县城团部医院。从驻地送去几十里,没有公路,交通极为困难,要四个男生用大杠子抬门板,另加四人同行,以便轮班换肩。病者发热大半是晚上,下决心送县,已是半夜。八人抬到城里已是凌晨。到达目的地,抬者累得躺倒下来即睡。深秋之夜,醒来感觉不正常甚至发热者也常有,只能留下观察。如此一来,连里可用的男劳力就不多了。
就这样,噩耗还是不断传来。光我们这一百多人的“学兵连”中就去世二位,其中一位是上海外国语学院的教师,从印尼回国的爱国华侨。我也抬过两次人,第二次到达后就出现低热,在医院享受了两天“观察”。半夜抬担架,高喊号令以使步调一致。另外四人手里举着火把,在一片漆黑的田野中照路。天昏地暗中,出现这样一群奇特的寻路者,在精疲力尽中与死亡赛跑,寻找地平线上可能出现的灯光。此情此景,经常出现在后来的梦中。
不过,平心而论,农场的锻炼,也把我身体练好了。不管你原来体质如何,是否抬得起担子,不管你是否做过农活,也只能整年与泥巴打交道。不管你是否扛得住风寒,大风大雪天气也只能睡在四处漏风的自搭“营房”里。身体不好也得好,没人会怜悯你。不像读书可以得个马虎及格,这里没有折扣可打。
一道下农场的还有一些年轻老师,因为最初把我们送到农场时,口号是“边劳动、边学习”。整整两年,我只记得在某个雨天,下来命令,可以“学习业务”了。于是,大家把英语教科书翻出来,半天很快过去,下午指导员训话,从此以后在农场就没有拿过英文书。
煤矿
1969年自军垦农场“再毕业”后,几乎整个七十年代,我在一个小煤矿里做杂工,挖煤或打钢筋。我发现小煤矿的技术员有资格订购国外的技术材料复印件,于是托这位县城高中来的青年技术员帮我订一些英语技术材料,并答应教他读英文,当然后来也没教,那未免过于“明目张胆”了。就这样陆续读到一些英语建筑学、矿业、植物学,甚至心理学的文集。我总算有不少有趣的材料可读,当然读这些书,我的英语不会有太多长进,但至少让我的生活中透进一点外界的光线,也知道这个世界还在转动。
这个局面几乎是“世外桃源”,干点活,出点汗;读点书,无人管。这个“桃源”黑灰蓬蓬,看起来太“脏”,但也逍遥自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开始传来风言风语,说是学校要上课了。其实小学初中大致上一直维系着。高中学生终究要毕业,要上山下乡,从学校里消失。据说1969年就开始用推荐制招收“工农兵大学生”,但是八年中只招了九十万学生,大致是一年十万多一些。对于全国上千所高校,平均一年新招近百人,几乎等于空校开学。
我为什么抓住书就看?纯粹无目的的习惯而已,不然有什么事情能让我看得见时光的流动?不是说不辜负岁月,而是硬给时光里塞一点东西。
信号
在长年累月“无所事事”的时光快要结束的时候,终于传来了冰面裂开的声音:1977年9月传来消息,大学准备恢复考试招生,考试时间是11—12月。当年有六百一十万考生,录取不到三十万人。二十人选一,可见需求之强烈,竞争之激烈。
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实际上“文革”之前研究生是个别选拔的,因此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研究生考试。5月在地方上初试,6月到大学复试,9月份得到最后通知。规定是自愿报名,不需领导批准。我参加初试领导是同意的,条件是立即到地方师范专科去报到,服从组织分配。
但是我的忧虑不在此,而是没有针对考试的书籍,光靠英文技术资料无法准备英语文学考试。我从十多岁开始,二十多年瞎看书,没有一个专业方向。这时唯一的办法,是借一本上海商务印书馆翻印的英语文学史,以及一本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纸张已经朽烂。就凭苦读这两本书,我就去参加了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英语文学考试。
当时我已经明白自己的长处:只要给我几个月时间集中精力对付某个特定任务,我就能做得不比别人差。终于成功考取研究生,与我初试、复试都考第一有关。记得复试时满分是一百二十分,多出二十分是因为加了几道“卷外题”,无非是指出一些名句的出处,此时就用上了多看的那些杂书。
最后要说一句:我的回忆中似乎困难与委屈太多。其实我没有如此忧心,毕竟是好是坏,有利不利,都造就了今日的我,不管今日的我是否有些微成绩,毕竟没有虚度一生。我不是说天降大任必先劳其筋骨,我是说毕竟我是我的经历形成的,我经历的一切,也包括自己的许多错误。人生固然苦多乐少,没有苦的人恐怕乐也不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