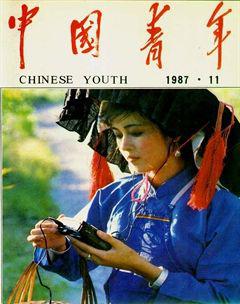“隐秘王国”中的几个问题
魏群 段跃
心理惯性与启动阻力
记者:杨冠三同志(中国社会调查系统负责人),您曾把改革的社会心理比喻为“隐秘王国的波动”,您能把这个“波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杨冠三:改革中的社会心理主要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
十二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入城市。城市居民耳闻目睹了改革给农村带来的神奇变化,昔日不得温饱的农民,短短几年间,不仅有买汽车的,还有买飞机的,甚至还有人飞到国外观光。在这种对个别实例的片面宣传鼓舞下,在也有可能当“万元户”的憧憬中,“改革=立即提高收入”的公式潜入人心,成为当时比较突出的一种心理状态。
长期的低收入、低消费使人们厌恶旧体制,欢迎改革,这种情绪无疑是有利于改革的,但是在人们对改革抱有过高收入预期的同时,却忽略了对改革长期性、艰巨性的认识,缺乏承受各种风险的心理准备,这就预示着一种可能—思想混乱和社会失稳。当以农副产品价格放开为主的价格改革全面展开以后,面对物价上涨、价格波动以及物价管理上的一些漏洞,不少人瞠目结舌,不知所措。甚至怨声载道了。从这时开始,我国现阶段社会心理结构的最显著的特征开始表现出来,这就是支持改革的积极心理特质与高依赖性、低风险承受能力的保守心理特质并存。这种高动力,低能力的矛盾状态可能会在相当长时期内存在。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大锅饭”体制下生活惯了的城市居民,艰难地接受了市场生活的锻炼,逐步适应从价格冻结到价格放开的变化。这一时期人们对改革的理解和支持已不同于改革初始仅仅源于多年来累积的改革愿望,而已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改革本身的效果。效果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效果二:消费者“主权”地位的上升。这两大效果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心理效益。在此基础上,人们愿意为过更好的生活而承担风险,这是此间社会心理的特点。
于得海(中国社会调查系统工作人员)人们从习惯的生活走进不熟悉的新生活,产生心理震荡是很正常的,就象一个你已经很适应的环境突然要改变,你总感觉别扭一样。我们权且把这种“别扭”称作对原有生活的“心理惯性”,那么由此带来的必然是对新事物的“启动阻力”。当一件不被人们所了解的事物开始出现并影响社会的时候,人们对它的疑虑,担忧、恐惧和好奇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不管成功与否,人们都要为之付出代价。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人们了解和接受了它,“启动”时产生的阻力就随之消失。对旧体制的“心理惯性”与对新体制的“启动阻力”是现阶段社会心理的重要特点。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对改革不拥护,其间没有价值判断。
既想要这个,又想要那个
记者:如果说不满点的扩散反映着人们对各自利益的追求,那么人们最关心的一个现实则是,改革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人们的需求和愿望,能给人们带来多大的好处?
杨冠三:这实在是一个需要说清楚的问题。在我看来,现在对于改革的最大心理障碍莫过于人们既留恋旧的,又向往新的;既想要这个,又想要那个。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迄今为止的任何一项改革都是在增加人民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即风险。可以回想一下,从农村包产到户,到城市价格改革,再到劳动制度改革,没有哪一项不是在增加人们生活中的风险,只有增加了风险,人才有动力,不然,安安稳稳,全由国家给长工资,包下来,干多干少没关系,人哪来的动力?因此可以说,改革的任何一项好处都是与风险、代价相伴生的。一位法国人在《多多益善》这本书中写道:“假定原则上把三大奖励:生活水平、收入有保障和职业稳定,以既得权益的形式统统归入某些彩票,这种方法是造成不公正的源泉。如果我们承认,我们的财富是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那么谁也不能既要财富又不接受市场经济的某些不利条件的制约。因此,必须在这三张王牌中减去随便的一张王牌。”他的这种说法不一定准确,但很有道理,只能在不同的选择之间作出取舍,一些人自担的风险应换来更高的收入,而另外一些人工作上的保障换取的应是较低的收入。他说得好:“情况不同而又要保持公正,世上没有比这更难办的事了;然而下个命令:要么都当领工资者,要么都有保障,世上也没有比这更荒谬的了。只要有可能做到多种形式,就应该鼓励而不是取消。人有多种多样,这是天赐良机,应该抓住不放,一刀切的办法历来是最不灵的办法。”应该实行一种人人都要作出努力的分配体制,任何人不得置身竞争之外,另方面有功必赏,谁也不例外。这样,强行分牌的社会就会逐步成为自己选牌的社会。我们希望群众能在这方面理解改革,既要享受旧体制下的低物价,又要享受新体制下的市场丰富;既要享受旧体制下的职业保障,又要享受新体制下的挣钱机会多,两者在现阶段是不可兼得的。抽象地说,公平与效率是不可兼得的。为什么改革越深入,人们的不满点越多?
记者:改革带来了经济的振兴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是人们有目共睹的。可是从街谈巷议中却发现人们的不满点越来越多,情绪似乎挺消极,应该怎样解释这个问题呢?
杨冠三:这确实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从我们进行的社会调查分析中就可以看到,一是群众不满的方面在明显增加,由过去集中于物价上涨,扩大到以权谋私、任人唯亲、法制不健全,不能自由选择职业、收入不平等等多方面。二是人们对改革的期望已不再集中于收入多一点,参与期望—参与社会生活的政治要求,社会期望—提高社会地位或实现自我的要求;机会期望—获得更多自由择业和公平竞争机会的要求,都已成为改革期望的重要内容。三是随着改革的推进和利益格局的变化,不同的社会群体在改革期望、承受能力和改革态度上的差异日趋显著。
于得海: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着,不满点的扩散和分化,是一种趋势。作为一个保守和封闭的社会,人们普遍受一个东西制约,一种东西就可能代表一切。改革开放后,人们的自由度大了,不同的要求就出现了,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的需求也不会只集中在物质方面。从西方一系列发展后的结果分析可以看到,分化是其中的一个结果,对政治参与冷漠也是一个结果,这就涉及到你们所提出的为什么感到人们的心理状态较为消极的问题。这个问题需要有一个正确的理解。所谓冷漠,是对总体参与的冷漠,而人们对关系到自己利益的事情并不冷漠,也不会冷漠的,,只是关心的范围不一样了,更关心自己所在的单位以及与自己利益有关的集体了。积极的意义在于,这使人们把那种空泛地对改革的支持变为具体的行为,把那种抽象的参与变为比较具体的参与。改革进行到微观程度,也就到了改变人们自己的时候。比如简政放权以后,企业增加了自主权,成为一个比较独立的实体,这就需要工人大量参与工厂的、班组的日常事务,以前提出的“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就是一个在现实生活中你自己怎样支持改革的很实际的问题,引导得好,会产生积极的结果。
杨冠三:对,社会心理的这种变动对进一步改革提出了约束条件,也为进一步改革带来了新的机会。我们拿群众不满的等级次序与要求改革的等级次序进行相关分析,发现群众最不满的,也就是改革要求最迫切的。改革的不断深入,使人们对旧体制增加了不满,从这种不满中又引出更广泛、更高层次的改革要求,进一步改革肯定还会诱发出人们更多的不满—这种循环本身就为改革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中间组织不能是摆设
记者:改革使整个社会的利益格局发生了变化。人们有了不同的利益就有了各自利益表达的需要。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建立和健全各种集团的利益表达渠道是一件非常紧迫的事情,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薄弱环节,你们对此看法如何?
于得海:这确实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如果没有正常的利益表达渠道,人们就会自觉不自觉地采取某些不正常的、过激的方式反映和表达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如骚乱,游行、罢工等等,在心理学上把这种现象称为“心理外逃”。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波兰。波兰为什么有团结工会,就是因为原来的工会起不到表达工人利益的作用,而团结工会组织罢工反对物价上涨,满足了工人这种利益表达的要求,所以团结工会发展很迅速。我们应该汲取和借鉴这些经验教训。东欧国家的改革告诉我们中间组织的功能不健全,没有正常的利益表达渠道,让政府直接面对群众,这一方面增加了群众对政府的直接冲突,加大了政府的负担,另一方面群众的利益要求也不能很好地“下情上达”,如此这般,很可能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因此,提高群众团体这些中间组织的地位和作用使我们的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真正成为其成员的利益代表,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应该说,长期以来这些中间组织的作用发挥得很不够,从我们最近的调查中看,人们对群众团体的期望与群众团体的现实作用和地位不符。在回答“群众团体的最主要职能应该是什么”这一问题时,分别有29。%、23.2%和16.2%的人认为应该是“为成员争权益”,“代表成员反映意见”和“维护成员合法权益”。人们已经产生了提高群众团体地位,扩大群众团体代表成员利益作用的要求。我们以为、中间组织的作用随着简政放权等政治体制改革措施的深化,已经越来越被提到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