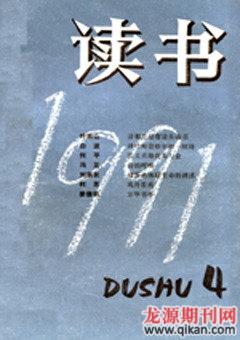“是在阅者矣”
白 玛
《品花宝鉴》在文学史上,被归入狭邪、倡优小说一类,在评论家那里,无甚声誉。此固缘其表现手法上未脱“才子佳人”小说旧套(不过“佳人”易为伶人),或也在于因专意描写才子与伶人的同性恋而难以入品吧。
其实同性恋不论中西,皆是自古有之(西方古典文明的黄金时代,此风就盛得很呢)。潘光旦先生在《中国文献中同性恋举例》一文中说:“同性恋的现象在动物生活史里就有它的地位,它和人类的历史是同样的悠久,大约是一个合理的推论。一般的历史如此,中国历史大概也不成例外。”中国自然不例外,但反映在《品花宝鉴》中的情况,却恐怕有些特殊。
狎优之风,明季即已称盛,而入清为烈。写作《品花宝鉴》的陈森活动于道光年间,所写大约总不脱所闻所见,总是当日的社会情状。其刻画一般欺侮残害梨园子弟的皮肤滥淫之辈而外,又别申一旨,以名士才子“好色不淫”,与伶人结为生死之交的
未知这是生活的浪漫还是艺术的浪漫(作者在序言中道:所言之色,皆吾目中未见之色;所言之情,皆吾意中欲发之情;所写之声音笑貌,皆吾私揣世间所必有之事),总之,在这里才子与伶人间的同性恋是迥异于常人的,即越出色欲一界,而臻于精神之域(是为警幻仙子所云之“意淫”吧)。构成这一奇特的“恋爱”景观的,不妨说,是由才子与伶人因容貌、品行、气质、才华的互相吸引而产生的一种艺术视角,伶人以“出污泥而不染”自居,才子亦因此而益重之,以是形成一个高层次的文化上的审美心理距离。这一审美距离的有无,是双方品性高低的尺度,若不欲被对方轻视,就必得保持它的“适度感”。“发乎情止乎礼义”,这一中国传统中爱情的最高原则,在这一特殊的同性恋现象中也无例外地发挥着“文化”作用。《品花宝鉴》中的“太虚幻境”,到底不失根据。
一种风气,必由多种因素促成。狎优之风亦自有其历史的社会的人生的诸种原因(王书奴著《中国猖妓史》对此已略作分析)。据蔼理士说,同性恋是变态,而非病态。(详见《性心理学》)那么也可说它是人的本能中的一种,只因不合乎文明社会的伦常道德,而被视作反常,并为人类所不取。更据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中所说,任何性的反常都是对一夫一妻式暴力的性文化的压抑的反抗,是对以生育为目的的操作主义的“现实原则”的反抗,则相对于以繁衍种族延续生命为目的的两性恋爱,同性恋的无目的性、享乐性、消遣性,其爱欲的本质倒是一种本能的“自由”发展了。当然这里并非论证同性恋的合理性(称引诸家之说也难免断章取义),《品花宝鉴》亦决非以“爱欲与文明”为主题,但只意在表明,对这一复杂的社会现象,说反映了一种“腐朽的生活状态”,是难以概括的。
《品花宝鉴》的作者半生佗傺,一第蹉跎,乃将胸中丘壑,满腹牢愁,发为文章,对现实的失意而使之在一个变态的情感世界中转求一种只有爱而没有欲的“纯情”的慰安。“噫,此书也,固知离经畔道,为著述家所鄙,然其中亦有可取,是在阅者矣。”(《品花宝鉴序》)观其于结尾处写道,诸伶脱身梨园之后,乃“当着众名士之前”,熔化钗钿,焚弃衣裙,将烬时,“忽然一阵香风,将那灰烬吹上半空,飘飘点点,映着一轮红日,像无数的花朵与蝴蝶飞舞,金迷纸醉,香气扑鼻,越旋越高,到了半天,成了万点金光,一闪不见”,毕竟这是象征灵的世界的终结还是新生,抑或这晶莹而又飘渺的灵的世界本来就是一个“寓言”(作品中两位主人公一名梅子玉一名杜琴言)?“是在阅者矣”。
(《品花宝鉴》,〔清〕陈森著,尚达翔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年七月第一版,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