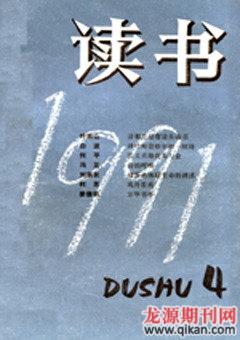“不怕它只是我个人的莲灯”
成之隅
访问古建筑:梁思成与林徽因
有一留学海外的朋友,前不久写信来,说起苦想家乡种种,最是北京的胡同儿牵肠。胡同儿?不就是那被青色斑驳的墙垣瓦脊、一扇扇吱呀作响的木门和片片槐荫所夹着的巷子么。不过,我理解朋友的心情,我们好赖也在北京生活了几十年了。而且我知道,对这地方,风土的感情,所依之深,深而不可言传,恐怕是在与家乡拉开了空间与时间上的距离之后,更能得着铭刻的。老舍在离了北京后曾写道:
可是,我真爱北平,这个爱几乎是要说而说不出的……我所爱的北平不是枝枝节节的一些什么,而是整个儿与我的心灵相粘合的一段历史、一大块地方。多少风景名胜,从雨后什刹海的蜻蜓一直到我梦里玉泉山的塔影,都积凑到一块儿,每一小的事件中有个我,我的每一个思念中有个北平,这只有说不出而已。真愿成为诗人,把一切好听好看的字都浸在自己的心血里,像杜鹃似的啼出北平的俊伟。(《想北平》)
在上一辈文人里,郁达夫根本算不上北京人。可是他描画北京的秋,也像是一首诗,可以永远地寄在乡亲们心头:
……到了秋天,总要想起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虫唱,玉泉的夜月、
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或在破壁腰中,静对着像喇叭似的牵牛花的蓝朵……(槐树)像花又不是花的那一种落蕊,早晨起来,会铺得满地,脚踏上去,声音也没有,气味也没有,只能感出一点点极微细极柔软的触觉。”(《故都的秋》)
倘若朋友能读到这些话,该会重温一番“老北京”的梦吧。北京固然在日新月异的变化着,但往昔总还似残梦一般悠长,或者就成为一种记忆的背景、感情的纽带,或深或浅、或明或晦,总不会不伴了你到天涯去。再放大些,“寻根”的想法,“皈依”的心理,以至于带有传统色彩的人格、经历,也因此而产生出来。通常的说法,称为“民族感情”、“爱国主义”等等。在这方面,可纪念的,有梁思成、林徽因夫妇。
梁、林夫妇并不是政治家、思想家,严格说也不是文学家,虽然林徽因“业余”曾发表过不少诗以及很少的小说。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主要同中国古代建筑遗产有关,也同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体形环境”有关,还有,同培养人才有关。梁思成是清华建筑系的创立者,任系主任多年,还曾任东北大学建筑系主任、中国营造学社法式部主任,既首选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也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北京城市规划委员会副主任。林徽因也一直任建筑系教授。夫妇俩均故去多年了。梁思成于大动乱(一九七二)时逝世,林徽因中年即多病,久而不支,先于一九五五年故去。
梁、林二位留下的文字不多,典型的学者遗篇。读它们却觉得,虽然属学者的眼光手笔,处在枯燥的建筑概念、公式、图表之中,却与不会说话的对象保持有心灵的交流,诚如所谓不仅用科学家的头脑,而且用中国人的心来对待。比如他们在合作的《平郊建筑杂录》中写道,观摩建筑能感到一种“建筑意”的愉快:
顽石会不会点头,我们不敢有所争辩,那问题怕要牵涉到物理学家,但经过大匠之手艺,年代之磋磨,有一些石头的确是会蕴含生气的。天然的材料经人的聪明建造,再受时间的洗礼,成美术与历史地理之和,使它不能不引起赏鉴者一种特殊的性灵的融会,神志的感触,这话或者可以算是说得通。
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殿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于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由温雅的儿女佳话,到流血成渠的杀戮。他们所给的“意”的确是“诗”与“画”的。但是建筑师要郑重的声明,那里面还有超出这“诗”、“画”以外的“意”存在。眼睛在接触人的智力和生活所产生的一个结构,在光影可人中,和谐的轮廓,披着风露所赐与的层层生动的色彩;潜意识里更有“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凭吊与兴衰的感慨;偶然更发现一片,只要一片,极精致的雕纹,一位不知名匠师的手笔,请问那时锐感,即不叫他做“建筑意”,我们也得要临时给他制造个同样狂妄的名词,是不?
这样的意见,表面看,是讲怎样欣赏古建筑,进一层,早就涉及了一种结构中“积淀”的历史文化意味、审美意味。寻常的看法,或以为那不过是一堆堆这样那样的“封建糟粕”,或以为是早已死去的古董。在“厚今薄古”的跃进时代,这样的意见也只好不当一回事。但梁思成大概不曾改变对历史文化尊重、同情、理解的态度,因为面对一笔遗产,在没有充分的了解和比较分析之前,还能有什么更合适的态度呢?自然,在不同的趣味后面总流动着或朴素或造做的感情。梁思成看北京的“城”:“城墙加上城楼,应称为一串光彩耀目的中华人民的璎珞。”林徽因也写到北海:“在二百多万人口的城市中,尤其是在布局谨严、街道引直,建筑物主要左右对称的北京城中,会有像北海这样一处海阔天空、风景如画的环境,据在城市的心脏地带,实在令人料想不到,使人惊喜。”建筑家的眼睛也是心灵的窗口。
大地上散落着被风剥雨蚀的古建筑,第一次遇上了有现代眼光和同情心的斟察者、探秘者,也作为技术史、文明史的材料被整理,尽管仍然可能被战火吞掉,被“革命”革掉,被“建设”除掉。
一九二八年梁思成夫妇在美攻读建筑与美术后返国任教。尔后直到抗战爆发的一段时间,他们除了教学,主要从事古建筑的调查研究。当时北方土地上犹是战乱未息,交通不便,工作、生活的条件都在难以想见的“糟糕”里。几个书生“孤掌而鸣”,诸事烦难,却不弃恒心及难被世人理解的志趣,尽其心力,寻访古迹,做一种别人不屑干、不愿干、不能干的事情。倒也没谁差使他们,他们满可以呆在客厅里品茗闲谈,感叹着:“‘保存古物,在许多人听去当是一句迂腐的废话。‘这年头!这年头!每个时代都有些人在没奈何时,喊着这句话出出气。”
后来,收在《梁思成文集》一、二集中的调查报告,反映了他们当时所做的“有限性工作”的意义,也反映了对古典庄严,智慧的一份同情理解,孤寂者的苦乐。
一九三七年,梁思成、林徽因等四人深入山西五台山,发现了佛光寺极具价值保存仍好的唐代木构建筑。后来在追记中写道:“到五台县城后,我们不入台怀,折而北行,径趋南台外围。我们骑骡入山,在陡峻的路上,迂回着走,沿倚着崖边,崎岖危险(八五年我乘汽车去佛光寺时还能感到山路的陡险——笔者)……近山婉婉在眼前,远处则山峦环护,形式甚是壮伟。到了黄昏时分,我们到达豆村附近的佛光真容禅寺,瞻仰大殿,咨嗟惊喜,我们一向所抱着的国内殿宇必有唐构的信念,一旦在此得到一个实证了。”也是“不看不知道”,长途苦旅后的收获,亦非个中痴人所难以理会。这种考查,他们在冀东、冀中、京郊、山西等地开展了多次,兵荒马乱,举步维艰,不能有安心观摩的条件。要乘火车,然而车很糟,“加之以‘战时情形之下,其糟更不可言。沿途接触的都是些武装同志,全车上买票的只有我们,其余都是用免票‘因公乘车的健儿们。”(《正定调查记略》)要住,但“打听住宿的客店,却都是苍蝇爬满,窗外喂牲口的去处。好容易找到一家泉州旅馆,还勉强可住,那算是宝坻的‘北京饭店。泉州旅馆坐落在南大街,宝坻城最主要的街上。南大街每日最主要的商品是咸鱼……每日一出了旅馆大门便入‘咸鱼之肆,我们在那里住了五天。”(《宝坻县广济寺三大士殿》)当然,更艰苦还在工作本身:(佛光寺正殿)“斜坡殿顶的下面,有如空阁,黑暗无光,只靠经由檐下空隙,攀爬进去。上面积存的尘土有几寸厚,踩上去像棉花一样,我们用手电探视,看见檩头已被蝙蝠盘踞,千百成群地聚挤在上面,无法驱除……照像的时候,蝙蝠见光惊飞,秽气难耐,而木材中又有千千万万的臭虫(大概是吃蝙蝠血的),工作至苦。我们早晚攀登工作,或爬入顶内,与蝙蝠臭虫为伍,或爬到殿中构架上,俯仰细量,探索惟恐不周到,因为那时我们深怕机缘难得,重游不是容易的……”(《记五台山佛光寺的建筑》)
没有奖金,更没有奖章以及“知识分子事迹报告团”什么的,“左右萧条,寂寞自如”。自如,无非意味着“做该做的事”,也就是卑之无甚高论的责任感。除了做得不够,无他遗憾;除了得到学术发现,也无更大的慰藉:一旦在遗建中发现精美奇特的构造,每每又高兴到发狂,疲乏顿然消失。
从整个建筑学或古文化研究来看,梁氏夫妇的努力只能是有限的、小规模的工作。社会也不大帮助他们,不过连老子也说过“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的话,其实并不宜把大小、新旧、急缓作为判断学术工作价值的唯一标准。人们也该承认,既然祖先留下了创造的形式,既然它们负载着一定的历史文化信息(甚至成为后世的旅游资源),研究它们,便不能不从获取第一手的实证材料入手,以之为基础。寺庙、佛像、栏干、牌楼、塔、桥,民居、店面,既是建筑形体也是人文景观的主要因素,无论你喜欢不喜欢,觉得有用没用,打算肯定还是否定,恐怕都需要先了解,认识它们的结构、材料、背景,鉴别、辨证、比较,然后是阐释。如果没有这一不惮繁琐、吃力的过程,开辟初始的古建档案,大概梁思成后来便无法到美国去讲中国古代建筑艺术。林徽因也无法在那篇成为专业基本读本的《清代营造则例·绪论》中阐述中国建筑的基本特征、结构方法。他们的影响会长久存在。
在一个动荡的时代里,传统与现代的思想冲突时时以各种形式泛起。而对传统建筑文化尚未有充分认识之前、许多文物建筑便已荡然或被破坏。“反封建”、“模仿欧美”,“厚今薄古”、“深挖洞”以至于“文化革命”,每一次浪潮,都或多或少株连到古代建筑文物。能为古建筑说话的人,如梁思成,不是很多。如北京的城墙,梁思成曾力主保存,提出过辟建环城花园的建议。大概是说了也白说,到城墙彻底拆除,城砖被挪去修防空洞、市民小厨房时,梁思成更是失去了说话的权利。我还记得,一九六八年到六九年,城墙大规模拆除之际,西直门城楼拆到半截,露出一座元大都的小城,跑去看,虽然是外行,仍觉得很有意思,可惜照了张相,还是毁平了。不知道当时梁先生是否知道,有何感想。毁了的便永远毁去了,只能说是“学费”而已,由此想到梁先生“宁肯保存”的主张,不能不感慨于孤寂者的远虑。四十二年前,他说过:“北平市之整个建筑部署,无论由都市计划,历史,或艺术的观点上看,都是世界上罕见的瑰宝,这早经一般人承认。至于北平全城的体形秩序的概念与创造——所谓形制气魄——在在都是艺术的大手笔,也灿烂而具体的放在我们面前。……我们除非否认艺术,否认历史,或否认北平文物在艺术上历史上的价值,则它们必须得到我们的爱护与保存是无可疑问的。”(《北平文物必须整理与保存》)由早期“建筑意”概念的提出,发展到“体形环境”——大建筑秩序观,梁思成坚持着偏于保守的非简单激进的态度,确立优先考虑“体”,以及与“体”协调的“用”。他警告说:“爱护文物建筑,不仅应该爱护个别的一殿一堂一楼一塔,而且必须爱护它的周围,整体和邻近的环境……摹仿或摹仿不到家的欧美系统建筑,庞杂凌乱的大量渗透到我们的许多城市中来,劈头拦腰破坏了我们的建筑情调,渐渐麻痹了我们对于环境的敏感,使我们习惯于不调和的体形或习惯于看着优美的建筑物被摒斥到委曲求全的夹缝中,而感到无可奈何。”(《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不幸而言中。八十年代的北京虽然尽可能地维持古城风貌,也不能不承受“不破不立”产生的无可挽回的后果,而且在城市功能膨胀中在“体”与“用”的矛盾中处于尴尬,处于生态失衡中了。晚生者不知道白塔寺、隆福寺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走到朝阳门,崇文门、西直门……竟没有门,“东四”,“西单”何以为名,说到××大厦,××饭店却如数家珍……长城既然是骄傲,城墙,为什么不能手下留情?梁思成在解放初期提出过一个较合理的方案,即保存旧城,在京西五棵松一带建新城,它南起丰台,北至圆明园福海,形成一条新的南北中轴线,与老北京的旧中轴线比翼双飞,长安街一路兼挑二者,一头是现代中国的政治心脏,一头是古老中国的建筑博物馆。梁思成的设想,不用说,早已被否定了,原因恐怕谁也说不清楚。
不过,梁思成毕竟坚持过作为学者的独立意识,不入云亦云的性格。他是被时代所挫败的。这往事的意义,如马寅初关于人口的主张,在于为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提供了深刻教训。
梁思成、林徽因都是名门之后(一个是梁启超长子,一个是曾任民国司法总长的林长民之女),并有通家之好。林徽因而且多才多艺。二人结婚前,林曾随父赴欧洲,与诗人徐志摩结交。回国后逢泰戈尔来华,林徽因与徐志摩陪同翻译,时人记云:“林小姐人艳如花,和老诗人挟臂而行,加上长袍白面,郊寒岛瘦的徐志摩,有如苍松竹梅一幅三友图。”(吴
如果我的心是一朵莲花,/正中擎出一支点亮的蜡,/荧荧虽则单是那一剪光,/我也要它骄傲的捧出辉煌,/不怕它只是我个人的莲灯,/照不见前后崎岖的人生——/浮沉它依附着人海的浪涛/明暗自成了它内心的秘奥。/单是那光一闪花一朵——/像一叶轻舟驶出了江河——/宛转它飘随命运的波涌/等候那阵阵风向远处推送。/算做一次过客在宇宙里,/认识这玲珑的生从容的死,/这飘忽的途程也就是个——/也就是个美丽美丽的梦。
一九九○年八月北京小街
(《梁思成文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后印行;《林徽因诗集》,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第一版,0.69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