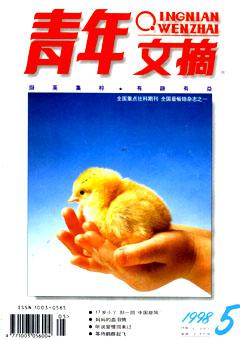从丑小鸭到到白天鹅
帕蒂.拉贝尔 詹妮编译
小时候我长得很难看,相貌要多古怪就有多古怪,如果说在我的心中对此有任何疑问,看一下我的3个姐姐就全明白了——我是一个生活在3只美丽的天鹅中的丑小鸭,并且我们之间的差别还不仅仅限于容貌,就连性格气质都完全不同——她们高贵典雅,我却笨拙拘谨:她们落落大方,我却胆怯害羞。
我似乎总和别的孩子不大一样,我的害羞情绪是如此严重,以致一想到要在别人面前说话——实际上只是大声说话——就会令我万分紧张。
许多孩子为了摆脱家庭的束缚有时会离家出走,而我却无处可去,因此我用歌声放飞自己的心情,是音乐改变了我的性格。
从我记事起歌声便一直飘扬在我们家里,父亲的嗓音如歌唱家纳特·金·柯尔一样圆润,在家中总能听到他演唱的小夜曲。
每周日下午我们几个姐妹和邻居的一些小孩就会听父亲教我们如何演唱多声部和声,他会一遍遍耐心地给我们示范,直到我们学会为止。
而家中并不只有父亲一个音乐爱好者,姐姐维维安每天下班回家就立刻打开电唱机,唱片中的音乐声一直到她上床睡觉时才会停止,至今我仍记得她随着节奏布鲁斯的音乐尽情摇摆的样子。
然而我对音乐产生真正的兴趣,还是在我上初中以后。那是一个普通的晚上,我独自待在楼上的房间里,突然听到一阵浑厚、美妙的歌声从楼下传来,我走到楼梯口,看到弟弟朱尼尔正坐在客厅里听音乐。
“这歌是谁唱的?”我问他。
他指着身旁一堆唱片说:“是葛劳利亚·林·蒂娜·华盛顿和萨拉·沃恩。”
从那时起,我被音乐深深地迷住了,我的卧室变成了我的俱乐部、我的音乐舞台、我的避难所,每天放学回家,我就会抓过一把扫帚、一个酒瓶或一把刷子——任何可以让我假装当作麦克风的东西——站在卧室的镜前唱出自己的心声。
我不在乎谁听到我的歌声,我发现自己甚至希望能够被别人听到。突然之间我不再是丑小鸭,而变为一只会唱歌的白天鹅、一位拥有众多歌迷的大歌星。
1956年秋天,我开始慢慢地钻出自己的贝壳,虽然我仍然文静而腼腆,但我却不再害怕去面对人们,在此期间我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这一转变完全改变了我的人生。
那时我家附近有一所教堂,原本我对其并不太在意,后来他们组织了一个唱诗班,住在附近的孩子几乎都要参加,就这样我经常要去教堂,不是为了去听神父布道,而是去练唱。
差不多有50多个人参加了唱诗班,就连唱歌跑调的姐姐芭芭拉也参加了。我们的唱诗班被命名为“青少年唱诗班”。
教堂的组织者哈瑞特·查普曼夫人任我们的指挥,每周二的傍晚她都会带我们在小教堂练歌。从第一天起我便知道自己属于这个唱诗班,我喜欢圣歌的旋律,但却是查普曼夫人温和的鼓励与支持让我产生信心,每次排练我们都能感受到她的和蔼、耐心与爱心。
正是因为查普曼夫人,我发现自己在努力尝试以前从来不曾想过的事情。一天傍晚我们正在排练一首新的圣歌,每一次唱这首歌我都会被深深地感动。后来查普曼夫人说需要一位领唱,即使现在我都不明白当时自己怎么会举起了手。
“我想我能担任领唱,查普曼夫人。”我说。
查普曼夫人惊呆了,从参加唱诗班以来,我最多只对她说过“你好”、“再见”,如此害羞的小女孩怎么会突然要求做领唱呢?
但查普曼夫人很冷静,她笑了笑,招手让我到前面去,“帕蒂,如果你认为自己行,我相信你的能力。”她说。
我紧张得竟颤抖起来,心中暗想:“‘我做了什么?”但还来不及等我改变主意,查普曼夫人已弹起了歌曲的前奏,我只好硬着头皮闭上双眼唱了起来,神奇的是恐惧感随着歌声竟逐渐消失了。感觉上就好像我并不是站在全体“青少年唱诗班”的团员面前演唱,而是在我卧室的镜前拿着扫帚把歌唱。唱到一半时我感到自己不再是教堂唱诗班中唱歌的少女,而是站在天堂的台阶前歌唱的上帝的使者。
歌声结束,屋中变得鸦雀无声,查普曼夫人吃惊地看着我,有些唱诗班的团员竟被歌声感动得哭了起来。
“帕蒂,”查普曼夫人温柔地说,“从现在起,你就是我们的领唱了。”
自我开始在唱诗班唱歌起,星期日对于我们家便成为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全家人都会充满活力、兴高采烈地前往教堂,而我总是第一个跑出家门的。
不久费城的西南部就传开了:“‘青少年唱诗班中有一名被圣灵‘点化的小姑娘。”结果每次唱诗班演唱,教堂中便会挤满来听我唱歌的人们。
后来上高中时我最敬爱的老师艾琳·莫兰组织了一场由学生指挥、表演的艺术节演出。当时的我非常矛盾,一方面我想参加演出,另一方面又担心自己应付不了那么大的场面,毕竟在教堂中为上帝唱歌是一回事,而为全校的同学唱歌又完全是另一回事。
没有唱诗班的团员们的支持,没有查普曼夫人的鼓励,如果别人讥笑我,我可怎么办?那今后我就再没有脸去学校了。
最后终于还是唱歌的欲望战胜了我的恐惧感。然而参加选拔赛那天轮到我上场演唱时,我却站在台上一动不动,完全被吓呆了。
开始大家只是盯着我看,等着我表演节目——跳舞、讲笑话或变魔术,最后还是莫兰小姐打破了沉默,她让我放松,不要紧张,准备好了再开始表演。
我点点头,深吸了一口气,艰难地说:“我唱首歌吧。”
唱歌?多年后莫兰小姐告诉我,当时她吃了一惊,与查普曼夫人一样,她们眼中的帕蒂一向都是文静而腼腆的,平时甚至不会举手提问,她怎么能有勇气在众人面前放声歌唱呢?
我的歌唱完,评判员们竟打破了暂不宣布评判结果的惯例,立刻通知我已被人选艺术节的演出。
6个星期后我站在学校的礼堂中惊奇地看着观众全体起立,为我的歌声欢呼、喝彩,我成为全场演出的焦点,我知道这正是自己一直希望获得的热烈反响。
那次艺术节表演之后,我并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得那样迅速和顺利。没过几年,作为60年代美国最受欢迎的节奏布鲁斯演唱组的主唱,我应莫兰小姐之邀再次站在泰尔登中学礼堂的那座舞台上演唱,但这一次我演唱的不再是别人唱过的歌曲,而是我们演唱组在R&B;排行榜上名列第15名的歌曲。
此时,我不再是昔日害羞的丑小鸭,而真正地成为一只会唱歌的白天鹅。
(郑毅摘自[美]《读者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