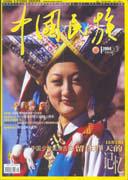再现民族的社会事实和历史走向
一
我国55个少数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积累了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留下涵载这些历史文化的卷帙浩繁的古籍文献。这是一笔价值难以估量的财富,是中华民族智慧与创造力的结晶,也是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完善新文化、创造新生活可资借鉴的宝贵历史遗产。
中国少数民族古籍(简称民族古籍)是指55个少数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文献典籍和口头传承及碑刻铭文等,其内容涉及政治、哲学、法律、历史、宗教、军事、文学、艺术、语言文字、地理、天文历算、经济、医学等领域。
民族古籍中以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最具特色。我国古代少数民族创制使用的文字有30种左右,以这些文字形成的典籍文献难计其数,形式千姿百态,内容博大精深,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内容和对实践经验的深刻体察。许多著作曾经照耀过一代代各民族的先民披荆斩棘、艰苦创业、生息繁衍的历程,为后人留下了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生的特殊认识与深邃思考。由于各民族先辈所处的自然、人文和社会环境不尽相同,他们对事物的认知体验也存在着差异,而正是这种差异,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兼容性,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格局。但由于少数民族文字流传空间狭窄等因素的限制,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一直很少为世人所了解。
有关少数民族内容的汉文古籍,历来是研究我国古代少数民族历史和文化的主要依据。这些汉文古籍包括二十四史和《清实录》,各个朝代史家的记述、地方志书、旅行家的笔录、赴边官员向朝廷的述职报告、当地政要文人的著作等。倘若没有这些记载,我们就无法知道古代的三皇五帝、夷蛮戎狄,也无法知道春秋战国时期北方的匈奴、南方的百越,以及后来数千年中各少数民族的演变发展。这些记载一代又一代地延传下来,勾勒出了中国多民族历史的主要脉络。这些典籍文献蕴涵着十分丰富的文化资源,对其进行系统的整理、编纂,可以拓展少数民族古籍的研究空间。
各少数民族在历史上口耳相传下来的各种史料,以其独特而浓厚的民族性、群众性、文学性,充实和完善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这部分口传古籍在形成的时间上往往十分久远,大都可以追溯到相关民族的起源、早期历史和最初的宗教信仰、原始的文学形式。原始宗教的颂词最初都是以口头形式传承的,无文字民族一代代地口耳相传,有文字民族则以文字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宗教经典,也就形成了这些民族最早的古籍文献。在传播过程中,口传古籍具有很强的变异性,无文字民族口传的原始宗教资料有的演绎为神话故事,有的变化为创世史诗,有的成为这些民族迁徙流变的历史记述。随着时间的推移,少数民族口传古籍更趋丰富,还包括诸如战争的传说、反抗压迫奴役的故事、发明创造的掌故、生产活动经验的积累和生活习俗的叙述等方面的内容。在表达形式上,既有神话、史诗、故事,还有歌谣、谚语和谜语等诸多文体。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少数民族的口传古籍所含有的历史文化价值并不逊于文字古籍,同样是我们不应该忽视的重要文化遗产。
二
民族古籍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长期的传播交流过程中,发挥了积极进取的价值取向和经世致用的社会功能。民族古籍中的一些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品,其价值已超出了自身专业范畴,往往代表了一门学科、一个阶段,甚至一个时代,再现了一个民族的社会事实和历史走向。
首先,民族古籍蕴藏着丰富的事实知识,充实了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内容。我们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如果没有少数民族古籍作为必要的补充,仅仅依靠汉文古籍,就不可能得到全面而完整的记录。民族古籍在微观层面上是对少数民族历史和社会文化进程的客观描述,在宏观层面上是真实反映中国历史的重要依据。在这方面,民族古籍有着许多突出的成就与贡献。比如,纳西族是一个文化发达并珍重传统的民族,纳西族在古代创造的独特文化,被今人称为“东巴文化”。东巴文是现今世界上最完整、沿用时间最长的图画—象形文字,现已成为东西方学术探讨的热点;青藏高原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它不仅以其独特的地质地貌和藏民族多彩多姿的生活令人向往,更以神秘的宗教和发达的古代文化为世界所瞩目,其藏文古籍数量之多居我国少数民族之冠,其中成书于14世纪的大藏经《甘珠尔》、《丹珠尔》堪称藏族古代学术的集大成者;地处欧亚大陆交接处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曾是中西文化的荟萃之地,11世纪前后是维吾尔族文化发展史上的辉煌时期,其许多传世巨著便是这一时期的产物,其中《突厥语大词典》、《福乐智慧》和《金光明经》三部作品,被誉为维吾尔族古典著作的三大瑰宝;居住在我国北部辽阔草原上的“马背上的民族”——蒙古族在探寻本民族历史方面成绩卓著,《蒙古黄金史》、《蒙古源流》、《蒙古秘史》即是蒙古族古代三大历史著作,为今天人们研究这个民族的历史源流、文化风貌和中国北方社会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还有我国少数民族的三大英雄史诗——蒙古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和现今世界上最长的史诗藏族的《格萨尔王传》,可以与《荷马史诗》和印度史诗相比美,它们以宏大的篇幅、精湛的语言、丰富的内容,表现了草原民族和高原民族雄健的气魄和炽热的情感。所以,我们说这些优秀的民族古籍所蕴含的内容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的象征,它们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都已成为研究的热点。值得一提的是,元、明、清及民国中央政府赐封西藏地方政府最高权力的金印、金册,还成为西藏自古以来就是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事实最有说服力的证据。从这一角度着眼,民族古籍除了代表着一种文化现象以外,还被赋予了重要的政治意义。
其次,民族古籍提供的各民族创造的文化成果,可以为学术研究提供较为真实可信的资料,有利于中华各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把我国各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妥善保存下来,不至于失传,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要使命。民族古籍内容广博,涉及领域众多,并且带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大多是汉文文献没有涉足的,它所记载的每一项内容相对汉文文献都是新鲜和充满生命力的。由于历史上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的歧视,汉文文献所记载的历史大多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作记述有欠公允。经过长期的反复承传,这些文献的记述又往往被视为事实而得以播散。因此,就出现过一些不够客观和错误的认识和看法。随着民族古籍保护、整理和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这方面的欠缺将会得到弥补,历史将会更完整地再现出真实的面目,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宝库也必将随之不断得到丰富和充实。
再次,各民族的古籍文献都是各民族对特定环境的适应能力及其适应成果的映射,可以为我们提供新的认识世界的视角和方法。在远古时期,由于各民族所处的环境不同,其适应社会的方式、观察客观世界的视角和方式也会不同。游牧民族看到的动物种类就比农耕民族多,渔业民族看到的水生动物就比山地民族多。在思维方式上,有的民族整体性思维强一些,有的民族则偏重于对事物作具体分析。就是同一民族,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思维方式也存在着差异。在原始宗教古籍中,神本主义明显占据主导地位;随着生产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们认知能力的提高,人本主义逐渐兴起,观察问题的视角和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化,使得人们对自然界、社会及人类自身的认识也更趋于客观、准确。民族古籍对此都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作了广泛而大量的记载。因此,从人类认识史的进化角度考量,借助民族古籍提供的信息,对有关少数民族先辈思维活动的视角、方式、特点加以诠释和总结,从而提高对人类认识能力的更全面把握,更真实地认识客观世界,也具有重要意义。
另外,通过挖掘整理少数民族古籍,能够提炼和反映少数民族的民族精神,增强少数民族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意识。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和发展。一个民族要屹立于世界民族文明之林,必须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有充分的理解,对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有所继承和发扬,这是增强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尊心的一个重要条件。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的祖先几千年来就在这块辽阔富饶的土地上劳作、生息。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各民族都有着自己特殊的形成和发展过程,都留下了异彩纷呈的民族历史文化,并为共同缔造中华文明作出了各自的贡献。各民族古籍文献就是这一历史进程的最好见证。我们应该通过保护、整理和研究民族古籍的有效工作,对这方面的精粹进行深入的挖掘,来反映中华民族成长和发展的光辉历程,以密切中华各民族源远流长、血肉相连的民族关系,繁荣我国的民族文化。这对提高各民族的历史地位,增强民族自强、自立、自尊、自信意识,推进各民族之间的思想文化交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培养各族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一代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精神,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
伴随着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体系逐步在我国的确立,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起,有少数专家学者开始将关注视野转移到少数民族研究领域,陆续深入到民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和研究工作,其间保护、抢救、挖掘了一批珍贵的民族古籍。但这相对于浩瀚的民族古籍资源而言,只是沧海一粟。由于得不到国家的重视和有效保护,丰富的民族古籍资源长期陷于被埋没的境地,甚至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散失情况十分严重。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坚持大力发展少数民族经济文化事业的方针,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古籍的保护、整理和研究工作。在国家尚处于百废待兴的20世纪50年代初期,就开展了全国范围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和语言调查,在调查过程中,发现、搜集到了大量的民族古籍文献,为进一步开展民族古籍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国的民族古籍工作迎来了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党和政府对民族古籍工作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政策措施不断完善,投入力度不断加大。
四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整理古籍、编纂目录的传统。从西汉时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大型汉文图书目录《七略》开始,此后各个朝代都有目录版本存世,其中清代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汉文古籍解题书目的最重要成果。但是在多民族中国数千年发展的漫长岁月中,历朝历代的中央政府从未对各少数民族典籍文献进行过系统的整理和研究,更没有编纂过一部全面反映少数民族历史和文化精华的民族古籍目录和提要,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缺撼。
过去我们常说,少数民族古籍浩如烟海,但具体到各民族拥有古籍的数量,谁也说不清楚。因为要把各民族的古籍文献汇总起来,查清楚每个民族有多少古籍,有哪些古籍,每种古籍是什么形式,有些什么内容,保存在哪里,做到心中有数,这绝非专家学者通过个人或某些团体的努力所能实现的。有幸的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的综合国力迅速增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进一步发展,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组成部分的少数民族古籍工作,越发引起政府和社会各方面的关注。
1996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少数民族古籍工作会议。会议根据江泽民同志关于“整理出版古籍,继承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的重要指示,提出了集中力量编纂《总目提要》的设想,认为在当今时代实施这一设想的条件已基本具备,时机已基本成熟。会后,经过充分酝酿、论证,于次年正式通过了编纂《总目提要》的立项申请。
通过《总目提要》的编纂,一方面能够使我们比较全面地掌握少数民族古籍的整体情况,可以确保今后的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做到重点突出,目的明确,成果的质量也就更有保障;另一方面,有助于增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做到资源共享,相互学习,相互尊重,共同充实和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的大团结;同时,也进一步促进我国的民族古籍资源为世界所了解、所享用,进而增强各国研究者对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的关注和兴趣。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一些外国传教士、探险家和少数研究者曾经到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收集资料,做过有关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和古文献的研究工作,但这些工作都是在当时非正常的情况下进行的。如今开放的中国正在日益走向世界,我们把自己的财富不加保留地呈现于世人,既能够开创一个互助合作、友好研讨的新局面,又能够增进国外对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全面认识,还能够振奋我国各族人民的民族精神,弘扬民族文化。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国各少数民族祖先留给后人的民族古籍文化遗产,不仅属于创造它的民族,不仅属于中华民族,更属于全人类。古为今用,古可喻今,古可鉴今。我们相信,随着《总目提要》诸卷的相继问世,少数民族先辈经世致用的智慧,必将越来越显现出其对人类无可估量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