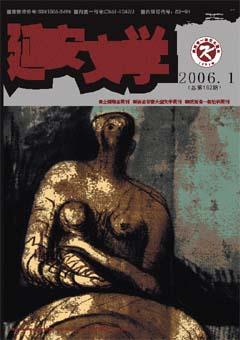唢呐父子
常胜国
凌晨,安妮和她的父亲、母亲从睡梦中醒来,只有安妮的弟弟虫子还在熟睡中。父亲和母亲接连地打着呵欠,边穿衣边叙说各自的梦,母亲说她梦见自己在山上安种,想净手,转到坡弯子里解裤带,却看见邻居家的男人在弯子里蹲着抽烟。她又转到一条沟里,想蹲下去,可沟里长满带刺的酸枣树;她转了几座山都没能找到能够净手的地方。父亲说他梦见自己开着一辆大车满世界跑,自己哪会开车呀!愣是心惊肉跳地把车开到一个地方,却也平安。这梦好不好?父亲和母亲互想问,又互相说好。
父亲把还在睡觉的虫子推了几把,浑身溜光的虫子在一条被单下面蜷着身子打滚儿,他听到炕栏地上十五“嗯嗯”地叫唤,便睁开眼睛,从被单下面爬出半截身子,伸手去逗十五。十五是条毛茸茸的杂毛小狗。邻居把狗送给安妮,那一天正好是农历六月十五日,月亮升起来的时候,安妮想到了这个名字,她先告诉了弟弟虫子,虫子说,啊呀!这名字不好听,哪里有狗叫十五的。安妮的两只手不停地比划着,又扯住虫子的胳膊,她告诉虫子,狗是她的,狗的名字叫十五。
安妮从炕上溜下来,却找不到拖鞋,鞋不知被十五叼到哪去了。十五也刚刚从睡梦中醒来,它正舒服地打着呵欠,把背高高地弓起来。看到安妮,它起劲地摇头摆尾,又很快把一只拖鞋从灶坑那头叼过来。
安妮蹲下来,把十五抱在膝头,用手比划着告诉十五,她昨晚梦见了什么。
母亲把热好的饭端到炕桌上,是一盆鸡蛋汤和几张葱花烙饼。安妮是刷了牙才吃饭,虫子是端了一碗蛋汤到外面去,撒了尿后吃饭。吃过饭,父亲催着姐弟俩去取锣鼓家伙。姐弟俩走到另一孔空着的窑洞门前,安妮怕老鼠,把虫子推进窑洞里,虫子摸着黑,把一件件家匙递出来,先是两把唢呐,接着是锣、鼓、镲。虫子从窑洞里钻出来,一看还少了鼓槌和鼓架子,又摸着黑钻到窑洞里去。
一家四口各带了东西出得门,十五在每个人的脚下蹿来蹿去。母亲挑了一付水桶,她要去浇她那七畦种着菜豆的园子。昨天,安妮还和母亲一起去园子里收菜豆,看上去园子里的豆蔓子黄中带绿,可钻到蔓子下面收豆子,却一个也找不到。安妮在七畦园子里钻来钻去,只摘了六个豆角。母亲说天气太旱,太阳太毒,小河里的水也瘦成了一条线,眼看就要干了哩,庄稼也和人一样,没有吃喝,哪能长出身体来?母亲担了桶到一个水浍子里舀水,一瓢下去便见了底儿。母亲让安妮站到背处去,自己在太阳底下等着水从浍子里生起来,好半天挑得半桶水半桶泥,颤歪歪往园子里去。
这是一日之中最凉爽的时候,天空晨星依稀,村子还在沉睡着。父亲背着锣鼓家伙,开始大声召呼另外的两个伴当,供粮、供和兄弟,“噢——供粮”随着父亲的声音,村子里的狗叫了起来,十五也跟着细声细气地叫。不一会儿来到大路上,大家聚齐了,父亲让供粮供和兄弟检查唢呐上的哨子,“吱吱”的哨子声过后,静了一会儿,路边草跟儿下的蟋蟀又接着叫起来。
在十五焦燥不安的转悠当中,几个人登上了往城里去的巴车,母亲在路边拦着有点生气的十五,一边还在给安妮和虫子交待一些事情。大家把装在袋子里的锣鼓家伙收拾在一起,这时,安妮发现虫子把左脚的鞋穿到右脚上了。安妮急切地比划着告诉虫子她昨天晚上的梦境:“一—只—大—眼—眼—的—怪—兽—在—高—高—的—山—岗—上—冲—着—我—吼……”
又是这个梦。虫子说。
几个月前,父亲跟城里来的下乡干部拉闲话,父亲对下乡干部说,自己的看家本事是几代祖传的大唢呐吹手,方圆十里八村的吹手没有能敌过他的。父亲把一支唢呐拿给他看,说唢呐是自家制作的,制唢呐有诀窍,这诀窍由父亲的祖爷爷发明,从来不向外传。城里来的干部是个外行,他摸着紫红色的管子,不知道诀窍在哪里,父亲就拿起唢呐给他吹了一支曲子,音色圆润清亮,有决帛裂石之响。城里来的干部点头称是。父亲又对他说,如今乡下人口不旺,有点体力的都出外打工去了,这个村已经有四年没娶回一个媳妇了,村里是只办白事不办红事,吹手的生意是日见得少了,哪还能维持生计?城里来的干部又点头称是。父亲说,要是老婆身体好,我也出去打工了,这点手艺还是撂不得。那干部的父亲终老,消息恰好给安妮的父亲打听到了,他进城找到那个干部,道了悲苦,说要给他的白事上送一台鼓乐,可已经有人送了,再多一台显得张扬。父亲说也不多我这一台,我也不收你钱,就图扬个名声。
父亲对安妮和虫子说,你老爷民国年间拿一把唢呐走南路卖艺,吹一首曲子换几个零钱,人家不给他就不走。做这个活就得这样,哪有几句话就把人打发走的?那次办事,吹打了三天,又上坟、又迎街,那个干部给了父亲的乐班子五百元钱。
在一个饭店门口,供和供粮兄弟选好场子,摆了桌凳,支起鼓架子,拿出锣鼓家伙,它们是:两把大唢呐,一付小镲,一面乳锣和一面羊皮小鼓。两个唢呐手,父亲吹上手高音,供粮吹下手低音,供和是鼓手,安妮和虫子一付小镲一面锣。这已经是第三次进城吹奏了。这次是吹红事。父亲有个想法,瞅时间让安妮吹两支曲子,但他没告诉安妮。乡下人办红白事,有的人不愿让女人当吹鼓手,嫌女人腌臢。都是老辈子人留下来的讲究。
看主人家在饭店的玻璃门上贴出大红对子,放了鞭炮,父亲和供粮“吱吱”地试了哨子,乐班人手各自已准备妥当。父亲掌过号,先高音吹一个“套吹”过鼓调,接着供粮的低音跟上来,随后鼓乐齐鸣。“大开门”“小拜门”“大摆队”一路吹下去,登时热闹了半条街。
稍时,主人家吆喝开围观的人群将酒菜端进鼓乐队的场子里,一样样摆在桌子上,也有糖果碟子和人头香烟。父亲鼓起腮帮子一口气不断头地吹,手指头在唢呐杆上灵巧地动弹,眼睛却瞪着虫子,生怕虫子抢了桌上的糖果香烟,没了规矩。虫子两手起劲地拍着小镲,缩着脖子,翻着眼睛看桌上的糖果香烟,再看父亲瞪大的眼睛,又一个人独自傻笑。
安妮看见饭店门口一对穿戴鲜亮的新人在笑盈盈招呼前来赴宴的客人,那新娘挽着高高的发髻,桃腮杏眼,一件旗袍勒出鼓鼓的胸部和细细的腰肢,真真的画中人一般;这时,新娘也把眼瞅定了安妮,并对新郎轻声耳语,新郎也转过头看着安妮,一对新人很快就看出新鲜来,他们越发快乐了。安妮却收回目光,一下子从脸红到了脖子上。
这日是陕北传统的黄道吉日,城里多有办红白大事的,因此鼓乐班子也极多。父亲在吹奏中间看见越来越多的人群当中有几张特殊的面孔,他一眼就认出他们也是大唢呐吹手,父亲的腮就越发鼓胀起来,一张黑脸又添了紫亮,本来一双大眼,这时却眯成一条缝,那手中的唢呐高高扬起,吹得气足音满,越发地不同凡响。
第一拨客人开始入席,盘成堆儿在桌子上,酒肉混合的浓烈气浪涌出饭店的门庭,涌上街道,引得叫花子们携老带小,个个伸着长长的脖子,眼珠子早滚到门里去了。
歇息时,父亲和供和供粮兄弟挪在桌子跟前喝小酒,虫子先抓了一盒香烟,眼不见也抢了一盅酒吞进嘴里去,直呛得鼻涕眼泪直流。安妮剥 了一个糖吃。这时,有人从人堆里挤进来,和父亲打了个招呼,蹲在地上去摸父亲的唢呐,“奇呀!”那人瞪大眼睛说。把唢呐端起来细细端详,那杆唢呐管紫里透红,光鲜晶亮,用手触摸,像孩儿屁股般光滑滋润;父亲说,你吹一回试试。那人双手捉了唢呐,运足气吹了一个过鼓调,毫不费力气,吹出的音却厚实宽阔。“奇呀!”那人又说。接着拿起架势吹了一个延川的坐场“满天星”。父亲说,“你也吹得可以了。”从提包里拿出一把小点的唢呐,碗子、链子都如日照积雪般亮白,通体鲜亮雅致,递给安妮,安妮有点不好意思,却不忸怩,接过唢呐与供粮换过位置,坐端了,试过哨子,锣鼓手各自预备着。这回安妮吹上手高音,父亲拉下手低音,安妮先吹一个绥德的“粉红莲”起调,父女俩和了一曲“粉红莲”,接着“满天星”、“南瓜蔓”,再用“粉红莲”收调。安妮吹得神定气清,口技、指法、运气、换气、连奏、单吐样样娴熟。那时,第二拨吃饭的客人已陆续来到,直把饭店门庭里里外外围了个水泄不通。
收场时已到正午,满天通红,并无半点云翳,地上已热不可挡。父亲收了工钱,连酒饭钱也一并折合了,带着乐班子拣一个小馆子去吃饭。那个与父亲一样的黑脸唢呐手仍满头冒汗、傻瓜似的当街站着。
“民国十七年呐……!”父亲喝过一点小酒以后就对安妮和虫子说。“米脂城里有名的铜匠吕五……”
老爷有一次给一个大户人家办白事,站在坟里吹招魂调,那调子已经失传了。老爷办完了事,见坟地里丢着几块孤坟里挖出来的旧柏木棺材,就扛了两块回去,自己锉了个唢呐杆子,比当时流行的尺寸短了一寸,做成一尺一寸的,做好后试吹,声音出奇地清亮,色如重枣,质如脂膏,老爷喜得一夜没睡着觉。后把杆子拿到户外,任风天雨地,烈日寒霜,那杆子也不破裂,反而更加晶莹鲜亮起来。老爷把杆了牢牢包裹了,从绥德起身往米脂城里去,找有名的铜匠吕五,做了一个略大一点的唢呐碗子,气牌、喉子、束子、链子都选了上好的铜质,最后缀上两根鲜红的穗子,当时看见的人都傻了眼,说从没见过这么美的东西。老爷把唢呐带回家,时值春暖,庄稼人正好收工回家。老爷仔细地洗漱毕,扎裹了衣裤,取了唢呐往硷畔的碾盘上圪蹴着,运足了气,吹了一个“鞑子攻城”,村里听到的人都痴痴地站着,鸡不飞、狗不叫、牛羊赶不到圈里去……。
老爷说那一次给大户人家办事,是这辈子吃的最好、最饱的一顿饭。大户人家请了总管,又请了有名的厨子,席面上酒泛羔羊,汤陈桃浪,八个碗子肉,十六个浑素菜在桌子上堆得山也似高。客人一拨一拨,从中午直吃到掌灯时分。老爷带了一个儿子去沾点儿浑腥,只怕儿子吃不饱,结结实实给儿子喂了浑的喂素的,猪羊肉,鸡鸭鱼,不歇气地往儿子嘴里送,直吃得儿子一古脑全吐了出来。
老爷后来被国民党抓了丁,带着一班子鼓乐手给国民党吹大会,吹小会。有一次,红白两军在一个山头上过仗,老爷被白军用枪托子砸着后腰去山上吹军歌,那时,白军已经被红军打下了半山腰,老爷把手里的唢呐吹响,白军个个勇猛起来。老爷心里想,这还了得!他们打得可都是咱老百姓自己的队伍呀!老爷把唢呐杆子往地上一扔,踩了个稀巴烂。老爷气吞山川,对他的乐班子说,我也有儿有女咧,活出名堂来了,以后谁也不要给国民党龟儿子吹吹打打!你们各逃生死去,我就在这里做个了断……说完纵身往崖下一跳,粉身碎骨。白军的队伍一败涂地,乐班子四散逃命去了。几天后,老爷的儿孙们到崖下找寻老爷的尸体,哪里找得见?乡亲们不说老爷被野兽分着吃了,只说老爷驾鹤西游去了。
乐班子的人后来都投了红军,有五个人战死沙场,个个都是铮铮铁汉。从前,唢呐手的地位十分卑贱,死后不能入祖坟。那五个人战死以后,乡亲们自发组织了抬埋队,倾其所有,隆重入葬。从此鼓乐手地位渐渐提高。
爷爷那一辈人仍然吃不饱肚子,任你庄稼人怎样流汗受苦,地里总是长不出好庄稼来。爷爷多才多艺,不仅吹得好唢呐,而且会弹三弦,说书,唱道情,他熟悉一百多首传统唢呐曲牌。爷爷拿一把唢呐走山西,上内蒙,下延安,挣些钱物贴补家用,常常被公家当盲流遣送回来让全村人批斗,挨过了批斗,肚子仍然吃不饱,于是又偷偷溜了出去。到了结婚的年龄,却没人给爷爷说媒,都说爷爷那号人,吹鼓手卖艺,跟要饭差不多。因此爷爷结婚得极晚,娶了吴氏寡妇为妻。婚后听奶奶约束,也把唢呐杆子踩个稀巴烂,发誓再不吹拉弹唱,可他哪里能管住自己,没了唢呐,找个擀面仗捅了几个窟窿眼儿,制成的唢呐俗称“鸡腿子”,照样吹得哇哇响,见了说书艺人,自己仍要弹起三弦定一个音。奶奶雨点似的点着他的脑袋骂他,你这人是:老骡子拴在背巷里——成就(陈旧)了,可儿女们说啥也不能动那尺二的杆子。偏偏儿子们都是门里出身,胜人三分,拿起杆子谁也不怯乎,个个吹得音是音,调是调。奶奶打了这个儿,又打那个儿,直打得自己没了精神。
家里五孔窑,有一孔挖得极深,充做地窨子,那窨子并不存粮存菜,却存着几块从坟里挖出来的未朽的柏木棺材板。父亲把祖上的几把唢呐卖了,给母亲看病,找了几个医生看,也没看明白。母亲的肚子疼起来真叫厉害,疼的跪不住,坐不住。若是在庄稼地里疼起来,就只能就地打滚。个个医生都给母亲吃胃药,却一点儿也不管用。过了半年三个月,父亲把母亲带到城里去看病,做了B超才知道母亲得的是胆结石,做手术要四千元。医生说也可以不做手术,吃一点消炎药回家捱着去。母亲说,家里的奶奶已经80岁高龄了,奶奶今年的身体全不如往年,说不行立马就不行了,要做手术也得等把奶奶抬埋上山去。这病要不了命,就是肚子疼,让它疼去。
父亲请木匠给奶奶打棺材,自己却像当年的老爷一样,悄悄钻进地窨子用柏木材板锉了几根唢呐杆子,有一根锉得短了一截,只有一尺长,他舍不得丢,也做出来,就是后来安妮拿的那把唢呐。当时安妮在村里上五年级。父亲把做好的光杆唢呐递给安妮,也没装哨子,只当是个玩具让她玩。安妮得了唢呐学着父亲的模样吹,虽然一点声音也出不来,却照样乐得鸟雀似的跳跃。第二年秋天,奶奶不行了。奶奶健在时最疼安妮,去年冬天还给安妮做了一条掩心棉裤,费了老辈子工夫,常给安妮扎一头小辫子,花儿布儿绷得满头都是。奶奶说安妮我娃是九天仙女下凡,嘴上虽不说话,心里却灵醒着哩。安妮浓眉大眼像父亲,白净水灵像母亲,极惹人疼爱。
奶奶穿了老衣,已被抬到秆草床上。奶奶这时还有一口气,但人却不灵醒了。全家人都围着奶奶放声哭,安妮哭不出声。供和供粮兄弟给了安妮一枚芦管哨子,安妮把它装在唢呐芯子上,独自跑到地窨子里边哭边吹。
那时,父亲正和奶奶作最后的告别。父亲听到窨子里有乐声传来,细听却是唢呐大曲“水龙吟”,曲声委婉清丽,如过涧水泉般浸润过来。父亲心里“咯噔”了一下,谁还有这本事呢?
“看!”趴在奶奶床边的虫子叫道。大家寻着虫子的目光看去,见奶奶眼睛里流出一行清泪来。
供和供粮兄弟寻声往地窨子里去,那声音又似在院前的几棵椿树上缭绕着,蓦然抬头,那满树的叶子忽如雪片般唰唰飘落下来。
葬罢奶奶,父亲急切切包裹了安妮吹响的那把唢呐杆,拿了家传的一个白铜水烟壶子,奔了米脂城,找了城里一个银匠,那银匠有名叫姜崇山,豁着两个门牙,叼着个烟嘴子,戴一副古老的水晶眼镜,祖传的手艺极是精巧,又写得绝好文章。姜银匠听了父亲的来意,把过水烟壶观看,开口说,如今白铜和白银同价,水烟壶又是个古物,我有些干银子存着,你不如把水烟壶留我这儿,再折些钱,干脆就做个银的吧。父亲那时脑袋发热,只管应诺。老姜拿称过了银两,立时动起工来。
老姜按尺寸给那杆唢呐打制了银碗子,银束子,银牌子,银链子,妙处镂花,好处落叶。装好以后转着圈儿端详,觉得美中似有不足,又在八个音孔中间镶了六个银箍儿,上面用老篆体打了一付对子,写的是:
有事皆呈祥端
无管自生佳音
一切完工后再看,那管唢呐小巧玲珑,通体流银飞雪,中间透出几段腥红,恰似雪落红梅一般。夜里,老姜又拿出唢呐观看,有揽星夺月之姿,忙收起来,一夜兴奋未眠。第二天又等身做了一个锦缎盒子,把唢呐妥当收存了。
老姜把唢呐交给父亲,连工带料算得五千,父亲吓出一身汗。安葬了奶奶,家里的积蓄已经罄尽,哪里去寻这许多钱?老姜爱吃猪肉炖粉条,父亲花五元钱请了他一顿,老姜只得让父亲赊了账。
供和供粮兄弟都长着一个蒜骨嘟鼻子,两肩中间只见脑袋,不见脖子。两兄弟都憨厚实诚,常与父亲一起喝点儿小酒,父亲就教他们吹打技艺,可两人天生是拉下手的胚子,离了父亲就吹不成调子。于是和父亲一起搭成一个乐班子,四处去吹打。
父亲拿出那把精美的小唢呐让安妮吹奏,安妮吹了一曲“照灯山”,音分雅、燕、清,调入宫、商、徵。
安妮第一次梦见大眼兽冲自己吼叫,是身上来月经的那天夜晚。以前看见母亲身上流血,安妮吓得不敢动弹。母亲忽略了这件事对安妮的影响,直到有一天深夜看见安妮在褥子上的一滩血污当中瑟瑟发抖。以后,每当母亲肚子疼痛呻吟的前一天晚上,安妮差不多都要梦见那只怪兽。虫子一看见安妮说梦,就腻烦地皱起了眉头。
绥德的滨河大道由南至北足有五里路长,大道修得宽敞明亮,中间花草树木,亭台回廊,迤逦连缀,处处都有休闲漫步的好去处。大道的北段围墙上镶着365幅石版画,它像一卷史经,从轩辕皇帝的事情说起,直说到如今现在;大道的南端立一座牌楼,号“天下第一牌楼”,楼高五丈,宽十丈,上下地伏、丁马、须弥座……;雀替、额坊、走马板,拱出五门六柱十九个浮楼,楼下有八尊石雕瑞兽守卫,威猛不可触摸。
大道自开工以来鼓乐就不曾断过,竣工后,各处都有人扭秧歌、跳场子,自日至晚,鼓乐延绵不绝。
安妮第一次走上大道时,看见桥头有一个狗市,市上有一人,挽犬提笼,笼中驻一只黑色大鸟,两眼发亮,似有发话状。狗是有名的沙皮狗,个儿虽小,性却极烈,脖项上一条铁链,牵着那人在桥上走。那人已经年事老迈,倒着脚步蹒跚不前。
人都说那人姓霍,家里养着十来辆大桥车、两匹马、八条狗。凡狗市上有看上眼的,那人都买回养着,玩够了就送人。唯有沙皮是他极喜爱的。去年冬天,他闲得没事,要给沙皮缝衣裤,找了个裁缝,裁缝太忙,不接他这活,他就自己扯了布缝,缝时忘了给沙皮留撒尿的口子,沙皮穿上后没法撒尿,急得死去活来。
霍老儿架鹰走犬,原本看着扭秧歌的人群就烦,来来去去总是绕着走。这天被沙皮牵着往大道的人群里去追一条京叭儿,看见安妮在一个台子上给秧歌吹唢呐,觉得新鲜,就找个地方坐下来,听着也新鲜,看着也新鲜,又忍不住挤上台子细细端详那把唢呐,雪也似照人,心里喜欢,不舍得离去。
又一日,霍老儿忍不住扯了安妮的一只手,倒着步子把安妮扯到围墙跟下,问安妮那把唢呐卖不卖。霍老儿一张口,下嘴唇就使劲地兜着嘴里的涎水,不让它流出来,等到说话,涎水还是顺着嘴角流下来,这时,父亲也跟了过来,父亲说,老先生,这东西是我们的吃饭家伙,没有多余的,所以卖不成。“先甭说不卖……”霍老儿发话,声音像一把铁勺在锅底上刮,极沙哑,也极深沉。“问一问价是多少?”父亲说给多少也不卖。霍老儿就和沙皮灰溜溜地站在那里。
霍老儿不服气,又把儿子找来,用手指着安妮手中唢呐说,“要那把唢呐!”儿子说,爸,我可忙哩!你怎就为了一把唢呐缠住我不放!说着忙,自己走上台去观看,方知那物件确实漂亮。向安家父亲问过价,回头对霍老儿说,爸,人家凭多少钱都不卖,你就坐这儿看看,过过眼瘾行了。霍老儿又一次灰溜溜地走了。
过了几天,霍老儿又去大道看那个物件,却不见了安妮和那个乐班子,问过塔台的人,才知道有人欺行霸市,把乐班子吓跑了。那天晚上,父亲的乐班子正在给秧歌伴场子,几个楞小子抢上台来,二话没说就砸了鼓乐场子,供和供粮兄弟上前吱唔,几个小子飞拳踢腿,打得两兄弟满地里滚。有一人揪了父亲的领口,说今后不许在这里吹,否则见人就打。第二天,这里的唢呐班子就换了牌头。
霍老儿问:伤了人么?没有。伤了物件么?也没有。霍老儿说,“谁那么大胆子,敢在绥德街上踢蹶子尥脚!”一打听知道是北头龙湾村的几个小混混日得鬼。霍老儿是个坐不住的人,牵了沙皮,倒着脚往龙湾去,路上跌了一跤,甩脱了鸟笼子,把一只大鸟飞了。直到晚上才把几个小子都召见了。霍老儿把住“呼呼”叫的沙皮,问小子们:“认得霍老儿么?”小子们都回答:“认得。”霍老儿看准一个小子,扬手就是重重的一巴掌,说认得就好,强似我再介绍。绥德街上有你们这样混事的么?古来就没有!混吃混喝可以,混黑皮混无赖不行!霍老儿说,就算我替你们父母教你们学好,今儿我做东,请你们孙子撮一顿,以后再不可行短,与人为善才好。小子们都说,知道错了,以后再不敢了。
霍老儿下嘴唇兜住涎水,当着众人的面,把后来的唢呐班子数落了个够,说是你们这等德行,以后就不要在绥德城里混了。那班人当时就胳夹了锣鼓家伙溜了。那时,安妮父子已经在城里租地方住了下来。霍老儿倒着脚,费了好大劲,才在城南拐子巷一个院子里找到安家父子,请他们再上台吹打。霍老儿走后,安妮告诉父亲:把唢呐卖给霍老儿吧,他是个好人。
父亲知道安妮舍不得卖她的唢呐,平时擦呀,洗呀,像宝贝一样爱护着,安妮带着那把唢呐,给家里添补了不少钱。安妮比划着告诉父亲:“卖—得—钱—给—妈—妈—看—病!”
父亲说,好个孝顺女子。可是咱花了大价钱的东西,若是卖,怕是不值钱。
听说父亲肯卖那把唢呐,霍老儿大喜,立时把儿子叫过来,带着安家父子往一个馆子里去,点了菜吃着。霍老儿也不等安家父亲开口,支起一个手指头给安家父亲看。
“一千?行哩!”
“一万。”
“多了,不值那些钱。”
“不多。”霍老儿说。“我别的事憨哩,这个贷我却识得,值!”
安妮把带来的布包袱抖开来,端出一只锦缎盒子,打开盒子,里面黄绸衬里,亮灿灿躺着那把唢呐。霍老儿越发喜了,把眼睛笑成一条缝,涎水流得满下巴都是。霍老儿对自己的儿子说,“哪一天我要是死了,就让安家父子来吹打,送我上路。”又对安家父亲说,“安家,你来吹,一定要闹得红红火火的。吹他三天三夜。”父亲说,“早哩,那是您老百年以后的事。”霍老儿让儿子点过了钱,抱着那把唢呐,像个孩子似的喜滋滋地对安妮说,“妮娃,唢呐可是我的了,你以后想吹,就到我家来借去吹,吹完了还给我。”
谁也不曾想到,二十多天以后,霍老儿的儿子一身孝服来到大道上请安家父子给他父亲办丧事。霍老儿殁了,享寿七十八岁。安家父亲唏嘘不已,说可惜了霍老前辈的侠义心肠,绥德城怕是再也找不到他那样人儿了。
父亲带着乐班子给霍家办丧事,果然看见霍家的大院里有一个圈场子,槽头上拴着两匹高头大马。霍老的儿子对安家父亲说,“我父亲这几年一满老憨了,小时出身富贵,到老了还惦记着肥骡子大马,又是养狗,又是喂鸟,谁也说他不下。可他临终时反倒灵醒了,把后事交待得一清二楚……”
安家父亲说,“老先生走的匆匆忙忙,我也没来得及望他一望。”
霍老的儿子说,“父亲走时交待,说你们这家是本份实在人家,要好好看顾。那把唢呐仍然要送还你们,说你们靠着它谋生,不能归到他人手里。”
安家父亲说,“这样也好,我把钱退给你就是了。”
霍老的儿子说,“我没说清楚,你也没听清楚,我父亲是要把唢呐送给你们。货是货,送是送,若是叫你退钱,父亲英灵不远,哪里肯依!”说罢取了唢呐递给父亲。
安家父亲登时泣不成声,说:“老人家人都那样了,还惦记这些事情,实实叫人念想!”
霍老的儿子说,“父亲在世时,几次说他走后,事要办得红红火火。咱就说定了,你那乐班子这几天就在我家侍应着,早晚吹一吹,好叫父亲他老人家喜欢。等事办停当了,一并算你工钱。”
安家父亲说,“就依他老人家说的,吹他三天,工钱却一分也不能收。”
霍老儿入殓时,家人亲友,依例都去棺材跟前作别。安家父亲也去看过了,这时将要盖棺,却见安妮挤近前来,双手托着那把唢呐。安家父亲说,“孩儿要把唢呐给老人家带去,老人家在世时,跟这把唢呐极是有缘分,就依了孩儿,把唢呐给老人家带去吧!”
霍老的儿了点头应允。
这时,有一只黑色大鸟扑楞楞飞近前来,可可地落在灵棚前檐儿上,那鸟两眼炯炯发亮,似有发话状。霍老的儿子说,这是父亲的鸟,飞回来给父亲送行来了,不禁失声哭了起来。
安妮又梦见一只大眼怪兽在冲她吼叫。安妮对父亲说,要回乡下去看妈妈。父亲说,你去看,要是你妈好着,你就快快回来。
天气大旱,母亲每天早上带着十五给园子浇水。十五把它的一泡尿难受地夹着,直到自家的园子里才痛痛快快地撒了。母亲半桶水,半桶泥地往园子里挑水,营务着菜豆角子,现在,园子里的豆角子长得好看起来了。
母亲这天早上挑罢第一担水,挑第二担时肚子忽然疼痛起来,母亲挣扎不住,倒在园子畔上,桶里的泥水倾倒在母亲身上。十五在园子里转悠了一会儿,捉了一只蛐蛐儿,转回来看见母亲倒在地畔上,十五慌得把嘴里的蛐蛐放了,冲着母亲汪汪叫,母亲不动,十五焦燥起来,窜到母亲身上,又是啃又是刨。忽然,十五一纵身冲下地畔,冲过小河,往邻居家院子里冲去,十五竖起前爪使劲地刨邻居家的门板,喉咙里不停地呜咽着。邻居家的小孩出门来,指着十五说:“十五,你怎哩?你疯哩!”十五一边往大门外边退,一边回头看那小孩,小孩走到墙角撒尿去了,十五又冲过去咬住小孩的鞋子,撅着屁股往大门外头扯。小孩“呀呀!”地喊着,跟着十五到大门外面去,十五自顾往坡下冲,小孩自言自语地说,“十五疯了。”
十五又回到母亲身边,母亲还是睡着不动。这时,十五看见大路的一头有一辆车慢慢地开过来,前灯的强光在路面上直直地移动。十五想起安妮每次都是坐着车走的。十五就冲过小河去,在大路中间叉开腿站着,等车子打着明晃晃的大灯开过来,十五就气汹汹地高声吼叫。车子停下来,里面的人打开了门,以为有人要乘车,十五跑过去跳上踏板,大胆往车厢里转了一圈,没有看见安妮,十五于是跳下车去,冲过了小河。
十五在母亲身边呜咽着,最后在母亲的脸跟前趴下来,身子蜷作一团,和母亲一起睡了。
母亲做了手术。十五累了,在城里的新家里躺了两天。这是一个陌生而无趣的地方,十五哪里也不想去。
开学的时候,安妮该上高中,虫子该上初中了。
父亲说,安妮就不上学了,让虫子上去。女娃娃家识得几个字就可以了,上学也没啥前途,花钱多识得几个字,有啥用处?
母亲说,安妮倒比虫子学得好。你就是死脑筋,重男轻女。
父亲说,我不是重男轻女,家里要是有多余的钱,连你也可以做个护理,烫个眉毛……
母亲说,我不做护理、不烫眉毛也倒罢了,我只想让安妮随心地去上学,安妮和人家的女娃娃不一样,要是将来能学个护士啥的,我这辈子的心事就放下了。
父亲烦恼起来,说你甭说没用的话,上学这生意谁家都难做,不见底地往学校里花钱,像二杆子引逗憨汉娶媳妇,钱花了,说你人不行,到头了不知能捞个甚?从前十年寒窗就考状元做官哩,三年冬书就做大事情哩,如今光念书就得半辈子,出来还不知道能不能有个营生干!这生意哪里是我们这等人家做的?让虫子念书,也是二杆子逗憨汉娶媳妇……
父亲问虫子,你想不想念书?
虫子说,我不想念书,除了念书,啥事都好说。父亲啐了他一口。
父亲问安妮想不想念书,安妮说,想。
父亲说,你姐弟二人抓阄儿,谁抓着一个“上”字,谁就去念书。
父亲拿来两片纸,做着样子在一片纸上写字,然后揉作团儿让安妮先拈。安妮仔细地瞧着地上的纸团儿,轻轻地拈了一个到门外头去看,父亲问,有没有?没有啊?没有那就是虫子了,虫子去念书。
安妮站在外面,站了很久。
虫子说,我上学要穿新衣裳。
父亲说,没有。
虫子说,我要一双新球鞋。
父亲说,没有。
虫子说,那就给我买个新书包。
父亲心里生起一团无名火,抬手打了虫子一个耳刮子。打得虫子杀猪似地嚎哭起来,父亲越发怒了,直把虫子打得住了声儿哽噎。
安妮抱起瑟瑟发抖的十五,安妮想对十五说,我想念护士学校,将来做个护士。安妮把十五抱上了街道,十五看见这世界如此陌生,乱糟糟的,越发抖个不停。
安妮把十五抱到狗市上,十五看到许多同类,仍然没有从恐惧中解脱出来。
安妮和十五站了很久,都没有人理会他们。安妮就抱着十五往回走,这时,有个人迎上来,问安妮是不是要卖狗。
安妮点点头。
卖多少哩?来人抓起十五的脖子观看,十五预感到自己的噩运即将来临,已经开始犯迷糊了。
安妮支起三个手指头。
三十不值。来人说,二十。把钱塞在安妮手里,抱了十五往前走去。十五绝望地盯着安妮看,嘴里却一声也不吭。
安妮跟在那人后面走,看他往哪里去。那人走不多远,走进一个饭馆里去。安妮抬头看见一块牌子,上面赫然写着:麻辣狗肉店。
安妮哑着声儿唤十五,眼睛里断线似地滚出泪来。
安妮买了一个书包回了家,虫子迎上来说,姐姐,妈妈已经给我买了新书包了。
等安妮在售货柜台外面比划着把书包退了,拿了钱,已经费了好多时间。安妮跑到那个饭馆里找到买狗的人,比划着要赎回自己的狗,买狗的人耐着性子看安妮比划,最后说,“晦气!狗跑了,你快走吧!”
安妮四处瞧瞧,不见十五的影子。
饭店门前遇见的那个黑汉子叫德全,德全自从吹过父亲的唢呐,就痴了似的四处寻访父亲。他到过乡下老家,先找了供粮供和兄弟,又一起在城南拐子巷找到父亲。德全对父亲说:“安家哥哥,自从吹了你的唢呐,夜夜梦见和你在一搭里,夜夜从梦中笑醒来,今天总算又见着了。”
父亲看见德全也喜欢,两个人就像有多年交情的老朋友。
德全告诉父亲,县上要组织一个唢呐团,要把唢呐吹到省里、吹到北京去哩,唢呐团一共要九十九个唢呐手。德全说,如果没有安家哥哥你,凭多少人也不敢撑那个门面。现在就等安家哥哥出来,把唢呐手都验过了,再行定夺。
父亲说,德全兄弟有所不知,城里、乡下吹得好的有得是,只是一样,唢呐杆子不行。
德全说,安家哥哥说得是。如哥哥肯把制唢呐的方子拿出来,我就是砸了锅卖铁,也要给绥德的唢呐汉们挣一个面子。
父亲说,兄弟这话,显得我小气。只是要制这许多唢呐,材料却不好找……。
父亲把德全领回乡下老家,一起钻进自家的地窨子,父亲用柏木棺材板锉了一根唢呐杆,又经食用麻油浸过,说:“唢呐就该这样制法。”
德全惊喜万分,说:“安家哥哥,你是怎着逐磨出这个法子来,凭谁有多聪明,也想不到这许多妙处。”
父亲说,也是祖上传下来的。祖宗这法子也是得于天地之间,今日广传天下,原还与天地。与德全商定,先做出一批样品来,再让唢呐手们相互习学,各找材料,做成一尺一寸的九十九把柏木唢呐。
父亲他们准备出门去排练唢呐合奏,遇见霍老的儿子访上门来。霍老的儿子说,一向脱不开身,耽误了这许多日子。把手里的包袱抖开,露出那只锦缎盒子。说:“父亲留有遗言,唢呐断不能随葬。况且人间雅乐,原不该随着亡人埋没了,该在世上流行才是。”
安家父子感慨万千。
德全对安家父亲说,该让安妮去给唢呐团做个示范,这把唢呐是个灵物,也让它给咱唢呐团增点儿灵光。父亲应诺。后来安妮在唢呐团吹了个“鞑子攻城”,全场人没有识得这个曲子的。在场的文化局干部问安妮懂不懂曲谱,父亲解释说,“是个哑巴。”
文化馆的干部惊叹不已。
唢呐团的成员一拨一拨在露天的牌楼广场上吹,一个个黑衣,黑裤,黑布鞋,扎裹着裤脚,腰里系着红腰带,头上拢着白羊肚子毛巾,如铁塔一般立着,唢呐声则雷霆万钧,排山倒海般盖过广宇。
德全把一万多元钱交到安家父亲手里,德全说,安家哥哥,钱是唢呐团的弟兄捐给安妮上学用的,安妮一个女孩家,不能跟咱一样吹一辈子唢呐,你就让她去上学,寻个好出路,将来寻个好婆家。
父亲说,“这钱我哪里敢受!”
德全说,“受得。你的唢呐秘诀,何止值这些……”
那天晚上,父亲又造了阄儿让安妮和虫子抓,两个人都抓了“上”字。父亲说,“那就两个都去念书,上学。”
第二天,安妮对虫子说:“我—梦—见—十五—头—上—扎—着—漂—亮—的—小—辫—子—回—家—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