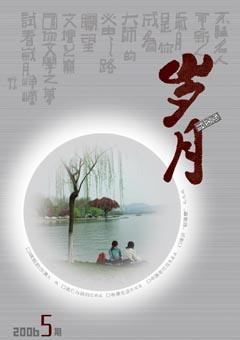逃亡与回归
范晓波
路上的秋风
我不大相信季节真的会影响内心的景色。但是第一场秋雨过后,街头的萧瑟感染了我在这江南省会上下班的脚步。电车的长辫子哗啪的闪电声、自动投币车的电脑报站、美女的瘦鞋跟叩击人行道板的脆响……我忽然听不到了它们。相反,一些更细小的声响,譬如树叶的颤抖和碰撞、窗玻璃在黄昏时的轻微震动、行走时长裤脚的摩挲声更加深入人心。视野里的色彩也变得偷工减料,蓝、绿、黄、白等纯色衰褪,灰色模糊了它们之间的层次。城市变成了一幅拙劣的水粉画,没什么生气,也没多少看头。我在街道上赶路的脚步越来越快,有种急于走出这座城市的架式。
8月上旬以来,我一直在酝酿新的远行,但方向的不确定使选择的艰难暴露到了极点,我一生的优柔寡断似乎都发生在了这个月。我今天往北京打电话说马上就去北京,过几天却告诉广州的朋友,决定还是去南方体验商人的悲欢。有时我又回到问题的起点——为什么一定要再次上路。道路于我,已不再赋有同新起点新生活有关的种种象征。这些年,我差不多走遍了全国的那些主要城市。对于以写作为中心的生活,我觉得不再有不去便是巨大损失的地方。我在社会价值方面的焦虑早已得到缓解,现在的关键是,如何在向内的方向上走得更高更远。我可能已出现某种征兆:厌倦旅行,留恋一个人坐在夏日的树阴里翻书或打盹的松散。
我不能鼓动自己精神抖擞地出发,更无法说服自己从此爱上这座正大动手术拟建成花园的城市,像我的户籍一样依附于它,与之息息相关。我总有种担心,现在就安顿下来,是否会导致日后的貌合神离和寝食难安?这个念头像火苗一样闪现在空气的寒凉走势里。它让我的心情一会儿光明,一会儿黑暗。我不停地向各地的朋友求助,但过于辨证过于负责的意见等于没有意见。我最后决定听命于一位测字老人去年在我母亲面前的胡言乱语:这孩子出门越远越好。我实际上是决定听命于多年累积下的足迹的暗示——我还没有足够的资本平息那些暂时昏睡了的种种欲念,在远景规划上,我是那样无法受制于理性而常表现得反复无常。
相比之下,北上还是南下的难题显得份量很轻了,虽然我在这方面纠缠得似乎更多更明显一些,但愿意暴露的烦恼往往不会是真正严重的烦恼。北京是我比较着迷的城市,但在北京当一名流浪作家已不能让我着迷;我不大喜欢广东的单调和“鸟语”,但它提供的高薪让我感到踏实和安全。无法两全其美不仅是我对北京和广东的选择,它实际上是人类共同的日常命运。对此我甚至愿意让一枚硬币的飞行轨迹来做出裁决。在北京某杂志社的社长打来第3个电话邀我过去面谈时,我预订了周末去北京的卧铺,同时订好了到站当天的深夜返回的车票。
载我北上的是1626次普快,没有空调。我因此可以通过打开的车窗呼吸到南方、中原和华北平原上的秋风。由南往北,它逐渐变得干燥而开阔。当它携带着玉米地的暗香从无边的大平原向我的鼻孔飒飒奔来,我的胸腔有种被徐徐打开的感觉,我忽然变得平静而松弛,如同一块皱乱的布匹找到了可以供之摊平的桌面。次日中午12时许,坐上杂志社派来接站的社长专车,在公主坟附近参观了单位办公楼,又去大兴区的宿舍区和一帮未来的同仁共进了午餐,困扰了我几十个日夜的难题在首都的秋阳下冰雪消融般一点一滴地消解了。从北京回来的第三天,我打电话给社长,正式告诉他我将在一个月后去北京报到,因为他邀我北上的第一句话不是以行政领导的口吻说的。他对我说:我以前也是搞文学的,参加过诗刊社的第二届“青春诗会”。
我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要把过渡的时间留得那么长。除了忙乱的内心,有什么东西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去收拾?或许我仍在潜意识里期待什么变故,让我不去北京去广东,或者哪里也不去。以我对这座城市里节气转换的敏感程度看,后一种可能性已几近于零了。那么,无论是向北还是往南,我注定又要一个人在秋风中上路了。没有失败感,也没有很多幻想和冲动,这种出发对我尚属首次。更何况,一个月后,路上的风已经很凉了。
我的心在这座趋向寂静的城里随着秋风的脚步一天紧似一天。
在山坡上候机
我不是在故弄玄虚,2002年2月18日,我真是坐在南昌昌北机场外的山坡上等了一下午飞机。
上午坐大巴从鄱阳赶到南昌,到自己的旧居里收捡了一下东西,就没什么事了,也没什么朋友特别想见。离开南昌才3个月,我对它的隔膜感已演化成了没多大意思的伤感,哪里都是遗迹,哪里都是时间的废墟。加上年前在广州去机场的路上饱受了堵车之苦之心惊肉跳,中午吃过快餐便早早乘车去了几十公里外的昌北机场。到了机场才发现实际情况远没有头两天飞走的朋友说的那么严重——因为各地都在这两天结束春节假期,需要提前很久排队换登机牌。我被告之我那次16点50起飞的飞机15点30分才开始办乘机手续,现在时间还不到14点。我没在大厅里瞎转,像个刚下飞机的人急急地出了机场大楼,因为在来的路上,我发现机场周围已有了春天的迹象。
2月6日飞抵南昌时,是我第一次到昌北机场,但夜幕使我什么也看不清,只是觉得空气里弥漫着家乡那种熟悉的清新而落寞的气息,和白云机场的繁忙污浊形成强烈的对比。刚才快到机场时,发现昌北机场完完全全坐落在黄绿相间的乡间,绿的是长满矮小的马尾松的缓坡,黄的是镶嵌其间的一块一块的油菜花,颜色响亮地铺展在高速路和机场的现代建筑周围,间或还点缀着几间农舍,驮着一两团恐龙蛋似的白云,整个画面极具欧洲山地风情。
正月的阳光很好,很暖很亮,几个大人领着一帮孩子围在机场的绿栅栏外看飞机起落。孩子们的情绪系在飞机的机翼上,随着它们的升降不时发出一阵阵欢呼,目光则被刺向蓝天的银鹰牵引着,不断地向天际延伸,最后随着机身的虚化变成一声唏嘘。一个年轻的妈妈对才读幼儿园的儿子说:好好读书,长大了就可以坐飞机去很远的地方了。我的目光也被孩子牵引着,体验着一种久未有过的感动。我想起了许多年前一个少年对火车的憧憬:火车是远方的使者,从郁闷的青春期驶过,将他隐秘的心动捎向地平线以外的明天。
后来孩子们发现跑道尽头的小山丘有两个小凉亭,可以将机场尽收眼里,又蜂拥着去了那边。我背着沉甸甸的挎包跟着他们走过春天的草坡,心情激动,脚步匆匆,似乎我来这里不是坐飞机,而是像这些从附近城镇和村庄赶来的孩子一样,专程来看真正的大飞机。
昌北机场比不了几分钟就有一架飞机起落的白云国际机场,即使在正月初七这个出行人数最多的日子,飞机起落的架次也不是很多,常常三四十分钟整个机场空空如也。孩子们仍舍不得离去,在亭子外的草丛里采野花,守候着飞机震颤心房的轰鸣声。我也舍不得离开,坐在亭子边的阳光里享受着这个悠闲中蕴藏着激情的下午。
从凌晨吻别熟睡的小女儿跨出父母的家门开始,我的情绪一直处于麻木的抑制状态,到机场之前,大脑里一直在回放慢镜头:春节寸阴寸金的11天,还有这之前我在南昌与老家之间甜蜜地奔波的那数百个日夜。才仅仅90多天,一切回忆都真的恍若隔世了。而我正在经历的一个经理的幸福生活是多么令我厌倦,我必须以理性为镜才能照出它对于未来的少许意义。从什么时候起,我由鹰变成了树,只有站在亲人的视线里才能枝繁叶茂、无惧风雨。只是当我看到漂亮的机场外这些满脑子好奇和幻想的孩子,才找到一些即将远行的心动。机场西侧的栅栏外有一座小小的村庄。我想不出,村庄里听着飞机的轰鸣长大的孩子,长大后在天空逗留的时间是否会更久远些。我很羡慕他们,机场边的童年,应当会为成年时代孕育更大的面对动荡和迁徙的气魄。
当孩子们随着第四架飞机的影子消失在傍晚的云层而四散离去时,我才挎起那只跟着我跑遍了全国的采访包,走出了凉亭和这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我想我会永远怀念它,因为那些孩子,因为这片望得见春天的山坡,还有坐在山坡上仰望激情的这段不会常有的体验。
逃亡与回归
那些有着流浪习气的人,青春的历史就是逃亡的历史,从大众的命运模式里逃亡,从缺少期待感的复写材料般的单调中逃亡,从不被自己满意的自我里逃亡,而这一切的前提往往是:从故乡逃亡。
我第一次企图逃离鄱阳是1993年夏天,我在许多文章里很美化地写到这段经历。现在想起来,在深圳度过的那一个月多少有些不光彩。我用惊人的速度花光了父母资助的五六百块钱和自己的一个月工资,让当时在深圳一服装公司当会计的朋友能清供养了几十天(白天睡懒觉,晚上坐在临街排档喝啤酒看美女),最后拿着他买的火车票观光客般地回了江西。我只是在夜班船到达鄱阳的那个凌晨(大概两三点钟),体味到了伤感与幸福轮番涌起的复杂心情,混合着对沿河路上烂虾腥臭气味陡生的亲切感。
1996年冬天一个寒冷的早晨,我带着一辆旧山地车坐上鄱阳汽车站的旧客车向上饶奔去。这是我第二次逃离鄱阳,这一次没像几年前那样浪子回头。在信江边逗留徘徊了一年后,最终把奔忙的脚步停止在南昌。随后,把户口也从鄱阳迁了出来。有几个朋友开玩笑说:从此你就不是鄱阳人了。超越既定命运的成就感只在很短的时间里享受过,我很快对这种说法感到怀疑。因为我刚离开家乡,就开始了从异乡到鄱阳的精神回归。
和许多经历相似的人交流对各自故乡的看法,大多数人只有逃离的快乐和庆幸。他们听了我的心情后说:应该给你颁个赤子之心奖。可是一个迷恋家乡(也许它落后并有些世故)的人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值得表扬的,只是不断地在他乡怀旧,一有机会就回老家小住:每年过年回来,“五一”、“十一”回来,许多时候不是节假日也回来。2000年的部分月份,爱人带着刚出生的女儿暂住鄱阳中学的父母家。我几乎每周末都要从南昌回鄱阳。那段日子,我不在南昌,肯定在鄱阳;不在鄱阳,就在去鄱阳的路上。
我跟一个朋友分析:一个18岁离开故乡的人和一个26岁才彻底离开故乡的人对故乡的感情是不一样的。对于前者,故乡代表童年和某个遥远的起点,适合偶尔的回忆;而对后者,故乡意味着青春和人生最华彩的章节,你已没法从生命中剔除它。而假如你是个写作的人,你对故乡的依赖还要被事实放大。
20岁时,我并不认为鄱阳会给我的写作带来任何影响,我的气质显然不适于当个乡土作家(虽然当时有不止一个前辈希望我的作品能融入鄱阳的地域特色),甚至,我一直在心里轻蔑着那些只能写乡土的前辈。但在我离开鄱阳数年之后,乡土上蒸腾的种种气息还是潜伏进了我的心脏和文字。
我的写作以散文和小说为主,散文可分为四个大系列:心灵史系列;青春史系列;城市生活美学系列;故乡与少年经历系列。前三个系列贯穿了我的整个散文写作,是我最本色最擅长的写作风格,我靠它们奠定了一个写作者的自信。2000年以来,我在进行前三个系列写作的同时,开始在稿纸上构建属于我的鄱阳。从我的出生地——我妈的老家柘港祥环村,到只去过一次的莲花山潘村,我工作过的油墩街中学,还有鄱阳镇的每个角落:芝山、高门码头、沿河路圩堤、解放街、鄱阳中学的老教工宿舍……3年间我写了二三十篇关于鄱阳的作品,它们大多发表在《人民文学》、《十月》、《美文》、《散文海外版》、《散文》、《中华散文》等一些核心文学期刊。2003年,《江西日报》副刊主编李滇敏约我开个包月的散文专栏,我报的选题是“鄱阳往事”。专栏推出后她告诉我,一个月连续发4篇关于一个县城的散文,这在《江西日报》文学副刊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我的性格和知识结构导致我没法像乡土作家那样挖掘家乡的民俗与历史积淀,我习惯于用现代人的眼光去感知和发现鄱阳。我注重的是鄱阳的文化与生态氛围对我的美学趣味的辐射与塑造。现在许多作家和编辑朋友通过我的文字对鄱阳产生了好奇和向往。他们像我那样熟悉了祥环、油墩街、潘村、芝山等奇怪(他们的感觉)的地名,并嚷嚷着要结伴到鄱阳来采风。他们的鼓励使我产生了一个隐秘的野心:也许有一天,更多的外乡人会在我的文字引诱下来到长期被外界忽略的鄱阳古镇,在这里旅游拍照,然后带着相思病离去。
鄱阳对我的另一个意义是,它越来越像我的心灵疗养院,我曾在一篇散文里使用过这个比喻。多年以来,我养成了习惯,一遇到人生或写作上的重大抉择和困难,就回鄱阳待几天,在鄱阳镇,或莲花山、祥环。并不是要和父母或朋友商量什么,只需要一个人在家乡的山水间随意地闲走,就能立刻恢复激情与写作的才华。
我有自信这样说,我肯定比90%以上长住鄱阳的人更熟悉鄱阳的那些角落。我可以大半天地静坐在火葬场后浮荡着灵魂灰烬的天空下,在那里抽烟,和偶尔路过的郊区农民谈论天气和明年的收成;正月骑着妹妹废弃的自行车在风雨山腹地一路狂奔,耳边的MP3放着《白桦林》,我在故乡的矮枞树间燃放雷王惊起野鸡无数;有时夜已深了,我从鄱中跑到西门圩堤上,在蛙声中同南昌和更远的朋友打电话。我说:我被浓稠的花香、星光和蛙鸣包裹着,幸福得窒息。
我能否有一天真正地回归鄱阳,不用再考虑谋生与虚荣(一涉及这些我在故乡将失去审美的能力)。每天写作与漫游,和老朋友喝酒?这是我活到33岁时最大的理想。几年前我有过一个小说构思,题目是《远走高飞》。这是一个长篇的格局,上半部讲一个人穷尽才能逃离家乡远走高飞到遥远的都市,下半部讲他伤痕累累从都市朝着故乡远走高飞。很显然,我早就认清了一个写作的人和他的故乡之间的宿命。
我常在半夜梦醒时想起1993年那个漆黑的凌晨踏上鄱阳旧街时的伤感与幸福。我总觉得和那种心情再次相遇的日子一定会到来。那一天是43岁还是53岁、63岁?我没办法确认,但晾在街边的鱼虾的腥臭已经闻到了,我要对每个看了我的作品后想来鄱阳走走的人说,这就是世界上最好闻最令我感动的气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