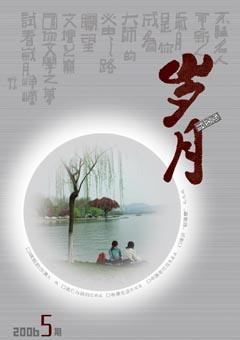老家的邻居
李广生
左 邻
我家的左面,原来是生产队的场院,四周是高高的土墙,中间是一块足球场大小、坦荡如砥的空地。记忆中,场院里总是堆满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柴草和粮食。于是,在那个贫瘠的年代,在一个个风高月黑的夜晚,我常带着几个弟弟从墙上事先挖开的豁口鱼贯而入,弄些东西来填饱肚子,烧热那间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老宅。
那时,看场院的是一个白胡子老头,姓韩,样子长得很凶,从来没有笑模样,一天从早到晚不知疲倦地手持粗壮的木棍围着粮垛和秸秆垛巡视,稍有风吹草动,便大喝一声,于是颤巍巍的棍子下便魔术般出现了一个鼻涕一把泪一把口袋里塞满了麦穗或者谷粒的小孩。
场院是我和邻家小孩的一个好去处,我们常铤而走险地在看场院老头的眼皮底下神出鬼没地在麦垛里捉迷藏。上百个雷同面孔的麦垛,人钻进去,是很难找到的。记得有一次,我钻进麦垛里很长时间,也没有被千呼万唤的伙伴们找到,最后竟然在里面睡着了,睁开眼睛时已是暮色苍茫,只见麦垛缝隙里筛进来的斑驳月光和咄咄逼人的蚊虫,这才惊恐着贼一样逃回家去了。
我十分喜爱场院,在幼年的记忆里,它已经成为我生命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每天上学、放学,总习惯于从场院外的土墙下走过,脚下是绿茸茸的小草,耳边是蝈蝈悠长的鸣叫,鼻中是麦子悠悠的清香,天是那样蓝,阳光是那样灿烂,风是那样轻柔,我们所经历的一年四季也好像只有通过场院才能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有的时候,讨得看场院老头的允许,我们还可以在里面寻些蚂蚱或者蚯蚓给鸡吃,因为听老人讲鸡吃了这些东西会下双黄蛋的,尽管很少吃过双黄蛋,但我们仍是乐此不疲。有的时候,我们还常在场院里用水灌蝼蛄或者田鼠,蝼蛄十分有趣,常常一瓶水还不到,就举着一双黑色的铁钳缴械投降了。田鼠倒是狡猾得很,因为是收获庄稼从田地里带回来的,因此有几分城府和野性。一个洞常有几个出口,即使将一桶水灌下去,也不见它的踪影,却只见旁边的壕沟里溢出水来。有的田鼠即使被堵个正着,浑身湿漉漉的浮出水面,但仍是一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样子,尤其是那双因绝望而冒着凶光的眼睛让人不寒而栗。因此,小伙伴们很少伸手捉它,或者一锹拍死,或者浇上煤油一把火点着,弄得田鼠“吱”的一声没了踪影,片刻的工夫便见场院内的一个柴草垛浓烟滚滚,于是惹祸的孩子们“哄”的一下作鸟兽散。
场院在我的印象中,尤如一幅静穆的田园山水画,画中布满了古典的事物,辘辘井、石磨、高高的麦垛,还有看场护院的老人,即使许多年以后深入了城市的浮躁与繁华后,回想起场院来,内心里总是荡起一丝甜蜜与苦涩的涟漪。
后来,生产队解体了,我家东面的场院就变成了一块块赵钱孙李的宅基地了。再后来,一户姓兰的人家在我家的东面建起了一栋砖房,成为我家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左邻。兰家的老头人瘦得很,皮包骨头,胸前的一副花镜夸张地炫耀着智慧,手里的一只脏兮兮的茶壶总是冒着热气。然而在我的记忆里,我家的东面好像永远没有这户人家的存在,永远是那个宽敞、亲和、堆满丰收和喜悦的场院。
右 舍
我家的右面,原来住着两户张姓的人家,三间土房,各住一半,共用一个灶房。两户人家好像有些血缘关系,一个称兄一个道弟,关系处得十分融洽。
称兄的是一个瞎子。从我记事时起,他好像总是成年累月地披着一条脏兮兮的被子,蜷缩在一截很少见到阳光的土炕上,目光空茫而浑浊。张瞎子既懒又馋,除了偶尔到户外晒晒太阳,其余任何时候都不出屋,力所能及的事情也从来不做,而且还常向女人要些好吃的,于是常见张瞎子的女人到街上用几个口挪肚攒的鸡蛋换回一个纸包纸裹的麻花给张瞎子吃。张瞎子的女人很能干,人虽长得瘦瘦的,可走起路来脚下生风。张瞎子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最小的女儿大我两岁,我们一个班,她因个子最高当了班长,我则因一口气能数130多个数而做了学习委员。我们是同时入学的,记得入学那一天,还是张瞎子的女人带我和她的小女儿一起去学校报到的呢。
后来,我考学离开了故乡。听人说,张瞎子早已去世,张瞎子的女人和女儿也不知哪里去了。现在只留下张瞎子的儿子一个人在村委会的一间空房里孤独地生活着,而且眼睛也已失明。
道弟的是一个车老板,一年四季总是穿着一件灰黑色的衣褂,嘴上叼着一支自卷的旱烟,脸上总是不见笑容。四匹膘肥体壮的马拉着一挂墩墩实实的车架,大鞭子一甩嘎嘎地响,神气得很。有好多次我去野外挖苣荬菜割猪毛草想搭他的车,可是每次都被他冷冷的目光和嘎嘎响的鞭子吓退了念头。车老板的女人是一个典型的乡下养尊处优的女人,我们都叫她四娘。四娘高高的个子,短发,嘴皮子很厉害,邻居们都惧她三分。尽管如此,我们两家处得还是很不错,走动也很频繁。但自从四娘家在我家的右面抢前几步盖了三间一面青的新房后,我的母亲和四娘的身体就非常的不好,总是闹病,于是有人说我们两家的房子犯说道,按风水先生的说法,左青龙右白虎,虎是不能压住龙的,否则就会出事的。于是,母亲从生产队弄了一个犁铧放在了我家房顶的西侧,光芒霍霍的铧尖直冲四娘家而去。四娘也不示弱,在自家烟囱上安上了一面镜子,把妖魔鬼怪都挡在了房子外面。因为这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两家闹得很僵。但是大人之间的争斗并没有影响我和四娘的儿女之间的感情,我和四娘的儿女们常在一起玩过家家摔泥泡骑官马杀官仗的游戏,一截矮矮的土墙覆满了我们童年贫乏的欢乐。
后来,母亲和四娘一天天老了,儿女们一天天大了,她俩之间的争斗也一天天少了,来往也一天天多了。有的时候母亲也叫我翻墙送些新蒸的馒头给体弱多病的四娘,车老板也时常热情地把去自留地锄草的我们让上他那威风的马车捎上一段路。再后来,我家屋顶上的犁铧和四娘家烟囱上的小镜子都不见了踪影。
如今,母亲、四娘和车老板都远离了这个喧嚣的尘世,在那片叫西甸子的荒原上静静地沉睡着。而我和兄弟们以及四娘的儿女们则奔波在故乡和故乡以外的土地上,辛勤忙碌,生儿育女。昨天听弟弟来电话说,四娘的大儿子正与父亲商量两家共建一栋砖房,共用一个间壁墙。两个人还常在一块儿搓搓麻将,有时候也喝上几盅,然后唠叨起那些发黄的略带苦涩的往事,没完没了,直到深夜。
前院
我家的南面,也就是前院,有两户人家,一户姓张,一户姓胡。
张姓人家一家人都很内向,很少吱声,所以来往并不多。因为我家的菜园与张家的后菜园仅一墙之隔,因此我们兄弟常偷窥张家的胜利果实,有的时候也顺手牵羊饱餐一顿,当然之后便有吃不着葡萄的人告发到母亲那里,于是免不了一顿皮肉之苦。
张家的大儿子人长得很精神,常见他身着一件军绿色大衣,威武地端坐在一架驴车上,走村串屯放映电影。那个时候我好羡慕他的小弟,每场电影都落不下,而且不像我们常常为了一场电影而跋山涉水走很远的路。每年的春节期间,张家的大儿子都会出现在村里组织的秧歌队里,摇身变成《西游记》中那位会念紧箍咒的唐僧,带着尚、孙、曹三位村民扮成的徒弟,身披袈裟脚踩高跷在大街上和人群中腾云驾雾,煞是威风。
胡姓人家的家境与我家差不多。胡家的伯伯与我父亲原来都在一个生产队。父亲在队里做会计,整天与“噼啪”作响的算盘打交道,日理万机一丝不苟地加减乘除。胡伯伯在队里做“打头的”,样样农活都拿得起来放得下,无论干什么活儿都始终冲在最前面,身后始终跟着千军万马。因此,那个时候的我对胡伯伯敬佩得不得了。
胡家的几个孩子都很淘气,从早到晚唧唧喳喳房前屋后地跑来跑去,从未见过他们消停的时候。他们当中的胡三,也就是在四个男孩中排行老三的与我们很合得来,常与我们一起玩“拍钉子”的游戏。他跑的姿势十分特殊,肚子使劲往前腆,脑袋拼命地向后仰,速度惊人,除了我之外,很少能有人抓到他。后来,胡三十三岁那一年,得了一场大病,据说是剧烈运动之后喝了大量的冷水“炸肺”了,后来就病死了。出殡的那天,我见到了躺在一张白木板上脸色铁青的胡三,样子哀怜而恐怖。从那以后,我们很少再玩“拍钉子”的游戏了,因为我们很怕跑累了喝冷水得病死掉。
现在,张姓人家已经搬走,据说仍住在镇上,但我已好多年未见他家的人了,只是常常想起放露天电影和扭秧歌的仪表端庄的唐僧。胡姓人家仍住在我家前院,上次回老家见到胡家的老二,得知他们兄弟几个都娶上了媳妇,日子过得也很富足。
后院
我家的北面,也就是后院,住的一户人家姓王。当家的在公社里当干部,据说是“四把手”,因在兄弟中排行老二,所以我们都叫他二伯。二伯人长得精神,高高的个子,嫩嫩的皮肤,一件雪白的衬衫常年扎在裤腰里,走路说话十分有派。
因大人之间地位的差异,所以平日里两家很少来往,我们见了二伯也大都是低着头很少说话,即使说话,脸色也都胀得通红,好像偷了人家东西似的。倒是二伯的老父亲人十分好,说话也很幽默,一件黑色大褂上缝着两个宽宽大大的口袋,里面总是装满了诱惑。因为每次老人来我家,都会先拿出些好吃的来,招惹兄弟几个抢着翻他的口袋,甚至有一次,口急的小弟还撕掉了老人的扣子。我印象中最深的一次,是老人从家中偷着拿来十几个肉馅饺子,那饺子香得很,流出的油把包裹的纸都浸透了。于是乎,早就按捺不住的兄弟们一拥而上,片刻的工夫,老人的手中就空无一物了。在我的记忆中,那顿饺子是我从小到大所吃过的最香的饺子了。
二伯有个弟弟,排行老四,因为智力有些问题,人们都叫他傻四。傻四很能干,一年四季手持一把扫帚或锄头,不知疲倦地清扫着院子,伺弄着园子里的庄稼。在我的印象中,从未见他歇息的时候,但总是因为活儿干不对头,而遭到老父亲的呵斥。有时我们也拿他开心,出一些脑筋急转弯的题,或嘲笑他几句,可是每次还没等话说完,就被举着扫帚的傻四追得狼奔豕突,但即使撵上,傻四举起的扫帚也不会落下,只是横眉立目地吓唬我们一下,也有胆小的哇哇地哭个没完,于是傻四又免不了被老父亲扯着耳朵拽回屋了。
如今,二伯的老父亲、母亲和傻弟弟都已过世了,儿子出国留学后定居在美国加州,二伯夫妇则与女儿在省城哈尔滨过着滋润的生活。
我常与二伯通话,可是每次都会被二娘抢断,惹得二伯在旁边直发火。当然我们聊得最多的还是老家的那些邻居和乡里乡亲,每次撂下电话的时候,都会隐约听见电话那端二娘哽咽的声音。
最近,听说年逾古稀的二伯和二娘正在办签证,要去美国投奔他们的儿子了,也不知以后能否再见到他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