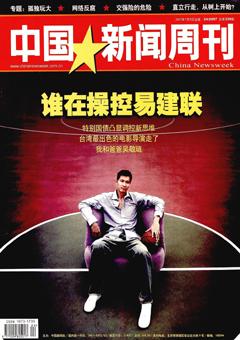孤独玩大
罗雪挥

那些“抖空竹”、跳皮筋、丢手绢的简朴“老儿戏”,变成了物质匮乏年代的象征,只有在老胡同和远离城市浮华的偏远地区,还保持着生机。而伴着豪华玩具和虚拟游戏形单影只长大的一代,又失去了什么?
“让我们借助一句歌词来开始吧!想起来是那么遥远。或者让我们以讲故事的方式来开头好吗?在很久很久以前,那时候还是上个世纪呢……”这是今年6月举办的北京潘家园怀旧玩具展上的广告语。
在这里,各种老玩具杂陈:空竹、九连环、木头弹弓叉、毽子、沙包、拐,甚至有标价为一角六分的儿童棋……参观者,常常是带着孩子来的家长。这些家长们,通常是急匆匆走进展室,而后脚步又突然慢下来,会心地露出一笑;而他们的孩子们,则像是有组织似的,转了一圈,就齐刷刷地坐在了展厅的电视机前,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上正在播放的动画片。
当成人们站在儿时的玩具前情绪激动甚至伤感时,孩子们坐在那里彼此间并不交流,只是随着剧情偶尔发出笑声。
在他们的身后,蒙着岁月尘埃的老玩具,真正地成为了陈列品。
谁还在玩“老儿戏”?
当今的城市儿童,玩的是芭比娃娃、乐高玩具、电子游戏。那些依然在“老儿戏”中流连的,只是处在物质相对匮乏中的孩子们。从事青少年素质教育工作的任伟告诉记者,他不久前去四川松潘时,看到一个村子里的小学,孩子们还在玩像“摔纸包”这样的简朴的游戏。“孩子们玩得很自然,因为他们没钱买玩具,那里也没有商店。”
在新疆一所农场小学任教的张叶介绍,那里的女孩们还在跳皮筋,男孩们还在玩玻璃弹球。只是这样的游戏也随着时代的发展有所“分化”:以前的皮筋,都是用老轮胎剪成的,现在有彩色皮筋卖,一块五一根。
家庭条件稍好些的孩子,比如那些住在场部的孩子,买得起皮筋,但往往跳得不好,只能够当“柱子”,负责带皮筋和撑皮筋,而条件差一些的孩子,要想玩皮筋,就得靠自己的实力,一关一关地跳下去。所以,真正跳得好的是这些“穷孩子”。
在北京,“抖空竹”这种“老儿戏”也还有人在玩。出身北京空竹世家的李连元,就在北京宣武区新桥胡同里的老墙根小学收了16个徒弟。当记者来到这所小学时,看见了几十个孩子正在一起抖空竹。他们花样迭出,空竹“嗡嗡”的声音交织在一起,犹如音乐合奏。师父李连元夸道:“我父亲比我爷爷玩得好,我比我父亲玩得好,现在我的徒弟比我玩得好。尽是新花样。”
宣武区新桥胡同,曾经是当年老北京空竹的发源地。现在站在胡同里放眼望去,不时能够看到大大的“拆”字,颓败的老房子与首都的繁华咫尺相对。然而,这些抖空竹的孩子们却不再是纯粹的“老北京”。
老墙根小学的校长吕仕珍介绍,老墙根小学有190多名学生,将近70%都是外来人口子弟,北京籍的学生则源自周边老城区,家庭经济条件相对都不是很好,家长一般不会给孩子们买高档玩具。
据吕仕珍观察,孩子们平时的游戏,一如数十年前的情形,也就是在胡同里跑跑跳跳,男孩子玩沙土,女孩子顶多跳跳皮筋。老墙根小学三年级女生曹元告诉记者,她常玩的游戏除了抽汉奸(陀螺),还有跳绳,做仰卧起坐。而如今,老墙根小学的孩子们人手一个空竹,“空竹便宜,简单易学,孩子们也觉得很有乐趣。”吕仕珍介绍。
“抖空竹”已经申请加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孩子们为此勤学苦练,师傅李连元甚至希望将来这些抖空竹的孩子能够走出国门。而这些担负“老北京”文化形象的孩子们,甚至很多还不是户籍意义上的“北京人”。
富裕的孩子一个人玩?
“马兰开花二十一,二五六、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建国后,从南到北,从教授家庭到工人家庭,中国儿童都是齐刷刷地哼着童谣,一穷二白地长大。
北京城管队监察员,生于1973年的著名“玩家”唐惠民表示,他如今收藏变形金刚,“有报仇的心理”,“当年买不起的,如今都收藏起来。”
唐惠民们将补偿的心思更多地放在了孩子身上。他们为孩子购买包括钢琴在内的各式高档乐器,各种昂贵的电动玩具和百科全书,中国城市新锐阶层的下一代,与父母的童年相比,几乎是有求必应,但大多都是玩具成群,形单影只。
出生于上个世纪70年代,现任北京一家广告公司负责人的林慧还记得自己和小伙伴把废报纸团成团当排球,在两棵树上荡秋千可以荡一上午的快乐时光。可是当生活进入房车俱备时代,四岁的女儿也进了价格昂贵的双语幼儿园时,她头疼的是女儿的玩具太多,却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
她总是安静地一个人玩,这些游戏固然好,林慧表示,但是玩具都是独自玩的,到底有问题。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人将来就是天大的本领,没有人合作也无济于事。
家长们对于孩子安全的极度担忧,也是孩子们独自玩游戏的重要原因。上濒翅膀科技(北京)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从事儿童素质教育的公司,其董事长兰海回忆,以前放学大家都和小朋友结伴回家,一路走一路玩,如今都是家长去接孩子,放学立即就要和小朋友说拜拜。
59岁的四川退休教师冯高琼对此很担忧。她帮着女儿在美国带孩子时,孩子每日有半天的时间都是和小区里的小伙伴一起玩。而如今回到北京,关于孩子被拐骗的消息层出不穷,胆颤心惊的家长宁肯将孩子圈养在家里。冯高琼很担心这种状况持续太长,“孩子成天关在家里,不跟小朋友玩,将来就不懂得什么叫谦让和互相帮助。”
而没有伙伴的中国城市孩子事实上也没有时间玩。北京一所大学附属幼儿园的大班孩子,在走廊上贴出了“我的晚间小计划”,大部分孩子晚上都要练习至少半个小时的钢琴,计划中还有学英语,还有读书,再加上看电视,余下的只剩下洗漱睡觉了。
“我觉得还是自己玩比较有意思。”10岁的北京小学生郑西宣布。如今,郑西的最爱是MP3和“拓麻歌子”。后者简称“拓麻”,是源于日本的电子宠物,它可以虚拟人的一生,从婴儿到成人,甚至还可以结婚生宝宝。和其他流行的游戏一样,“拓麻”当然是一个人的游戏。而正版的“拓麻”需要一百元以上,无论是在中国的特大城市还是二线城市,甚至远到徐州和兰州,拥有一个正版“拓麻”都是时尚小学生的象征。
孩子们早已经适应了没有“伴”的游戏生活。在中国的大、中城市里,小学里早已经没有了“丢手绢”的歌声,只有一种叫“手绢花”的游戏,就是一块六角形的可以顶在头上转的布,“最适合一个人玩。”曾经让小伙伴们一比高低的陀螺则发展成为电动的玩具,孩子们各自玩各自的,默默地“划地为限”。北京中关村一家玩具店的老板告诉记者,新玩具都是一阵阵的,流行的时候小朋友都来买,人手一个,比如“拓麻”,且互相攀比,可是这些玩具顶多“热卖”几个月,很快也就过去了。
即使仍然在玩“老儿戏”的孩子,也向往着代表新物质的虚拟游戏。远在新疆,13岁的刘静刚刚告别小学时代,并且获准可以偶尔去打电脑游戏,她表示,如果要论喜爱程度,电脑游戏还是首当其冲,因为“不需要大家一起玩,能够找到现实世界无法满足的充实感”。
“老儿戏”渐渐被城市的浮华淹没,或者干脆被新时代收编。《老儿戏》的作者何诚斌曾试图用文字记录下过去年代一个个快乐的游戏,包括跳绳,但当他告诉女儿“我们班的女生,没有哪个不会跳绳子”时,女儿的回答让他瞠目结舌:“你们班上的女生,会上网玩游戏吗?现在网上就有一种跳绳子的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