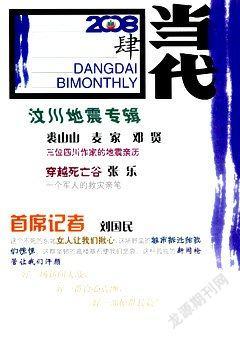地震四记
麦 家
受惊记
符合所有大灾难的特征,虽然有个别零散的征兆和暗示,但没有任何消息和风声,于无声处中,于无防备中,四川的地裂开了。
地震发生时,我正在成都市少年体育中心打羽毛球,这是我坚持已久的一项锻炼,每周一、四下午两点至四点。我刚打完一场,正在休息中,忽听屋顶发出哗哗的响声,像有一支队伍在屋顶急行军。我抬头看了一下,发现哗哗声转眼间已经变得更加汹涌。好像急行军的人数又增加了一倍。我的理智迅速做出了反映:地震了!我对馆内的人喊:地震了!一边往外跑。没人相信我,他们脸上的笑容似乎也让我有点儿不相信自己。跑到门口时,发现屋顶像筛子一样纷纷筛下了陈年尘埃,与此同时我看到屋顶在摇晃。已经不容置疑!我回头再喊同伙,急切的声音令他们深信不疑,立即丢了拍子往外冲。这一切都发生在几秒钟的时间内。又过几秒钟,我们已冲到室外。似乎有短暂的间隙,我们正在怀疑刚才的异常是不是地震时,新一轮震动开始了。明显比刚才剧烈,我感到脚下厚实的水泥地变薄了、变活了,在隐隐地动,人像站在船上,船在水中荡漾。但我不可能有这种错觉,因为我惊恐的双眼清晰地看到,两边的楼房像失去了重量,在风中晃动,随之玻璃咣当咣当地往地下砸。我的三个同伙飞身跳过绿化带,去了更开阔的空地。我比他们迟了一秒钟,却再也不敢尾随。因为,我担心就在我飞身跳过绿化带的一瞬间。旁边的体操房会倾坍,把我永远地埋在绿化带里。我置身的空地是两个室外羽毛球场,三边都有房子,看上去三栋房子晃摆得越发厉害,似乎随时都可能垮下来。如果它们同时包抄我坍塌下来,我不论选择站在哪里都必死无疑。我不想就这么死,眼睛飞快地在三栋房子间睃视,指望能及时发现谁先垮,好让我争取惟一可能的逃生机会。据后来地震局说,这次地震持续的时间只有五十四秒,减掉前面的十几秒,我捱熬的时间也就是半分钟多一点,但我感觉漫长得已经把我全部的心力都用尽了。
恐惧把短暂的时间无限拉长了。
这是一种无法形容的恐惧,回忆起来仿佛是假的。
当震感彻底消失,惊魂甫定,我首先想到的是我儿子。儿子十一岁,在上小学。我给老师打电话,手机成了一块废物,无论是打座机还是手机,都是“连接错误”。我只好开车去学校,一路上看到街头站满了人,叽叽喳喳的,不时还可以看到一些瓦砾,散落一地,围观的人把道路堵了。在繁华的琴台上,由于堵塞得厉害,我的思绪第一次回来约见了我。我问自己:震中在哪里?有多少级?会不会有人死了?
接孩子时,发现学校的一面墙上有一条裂缝,不大,不到一厘米。儿子很兴奋,说还有更大的裂缝,硬要带我去看。我拉紧他的手,默默地往外走,心里想的是要马上回去,看看我家的房子有没有裂缝。回了小区,却回不了家,物管不准每一个人进楼道,还在大声吆喝,叫楼里的人都下楼来,说还有余震。喊得人心里惶惶的,不敢往所有建筑物边站。我加入了叽叽喳喳的人群中,远远看见一个身穿睡衣的妇人,披头散发。我下意识地避开目光,孩子却冲了上去,大喊妈妈。当时她正在八楼上睡觉。一本飞来的书把她砸醒了,继而看到所有书都从书架上飞出来,继而是抽屉、衣柜上的皮箱,书桌上的台灯、茶杯、鱼缸里的水,等等,都像中了邪,纷纷往地板上扑……这时候,我想她即使没有穿睡衣大概也会冲下来的,顶多裹一层床单什么的吧。
下午五点十九分,我的手机接到了地震后的第一个短信,是在市政府机关工作的友人发来的,内容如下:发生特大地震,市政府要发公告。不要回家,赶紧购物去郊外找地方过夜。
这天晚上。我是在车上过的夜。不是宽大的房车,只是一般的轿车,挤了四个人,根本无法入眠。我一次次从车上下来,在黑暗中走啊走,不敢停下来,停下来就有成群的蚊子嗡嗡地包抄上来,还感到冷——因为我还穿着最短、最薄的球衣球裤,而天已经准备下雨了……雨在半夜里落下,淅淅沥沥的样子预示着不会立即停止,正如我身边的灾情一样。
捐款记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心伤未重深。
这次灾情无比蛮横地激活了我的泪腺,我经常像个娘们儿一样地痛哭流涕、泪流满面。我后来都不敢听广播了,每次听广播都是以哭告终。所以,特别能理解那些在电视机面前抱头痛哭的人。我住在车上,看不到电视,但可以想象电视会怎么叫人断肠破涕。
第一次落泪,是第二天清晨,儿子被击打在车顶的雨声吵醒,我便打开广播听新闻。也不知是哪个台,哪个记者,反正是个女的,她在都江堰灾区做现场报道。她告诉我,她的背后曾经是一栋五层楼。楼里有三百多个学生,现在楼房已成废墟,逃出来的只有十六个孩子,其余的人都急等着我们去营救。家长们在雨中跪在地上,求天求地。哭声震天。她一边说一边往废墟里走去,突然她听到有人在喊她:“阿姨救救我,阿姨救救我们……”她上前看,看见一根倒地的大梁下伸出一只手,里面有几个声音都在喊,要她救他们。记者的声音里早浸透了哭泣,说到这里她似乎再也说不下去,只是一味地哭,嚎啕大哭,根本没有了语言。我下意识地抱住身边的儿子,泪水哗哗地往下流,模糊了视线,同时又仿佛看见了那只从废墟里伸出来的手,它沾满鲜血,五指张开,奋力摆动着。血水随着摆动滴落在地,发出澎湃的声音……
车窗外,雨越下越大。大得已经让救援的飞机无法从凤凰山机场起飞。真是祸不单行啊,这时候居然来这一场雨!我要说,这不是一场普通的雨,它一方面像个善解人意的好人,替我们哭天抹泪;另方面它又是个落井下石的恶人,让无数本来可以生还的人永远失去了生的机会。地震第一天,虽然救援人员以最快的速度从全国云集四川,但由于空中和地面的双重阻拦,救援人员无法正常展开有效的施救,而第一天施救的成功率高达80%,到了第二天下降为30%,到第三天只剩下7%。这场雨让我丢掉了太多的乡亲!我恨它!!
八点多,我从广播里第一次听到伤亡报告:只是都江堰一个地方,只是第一天,死亡人数达到147,受伤的人有345名。随后,广播里号召大家去献血,因为血库告急。我是O型血,且不久前为补牙刚做过血项检查,一切正常。我决定去献血。当时我在乡下,距成都市区有二十多公里。医院在多个地方设了献血点,我根据所处的位置决定去天府广场。当我开车到天府广场一看,愣了!完全想不到,广场上已经排起望不到尽头的长龙。收音机说有“长龙”八百多米,我觉得无法统计,因为还有很多像我一样的“旁观者”。中国人爱旁观,但此刻我相信他们都不是旁观者,他们都是准备来献血的。
成都人的心在这一刻凝聚了!
这个城市一直以慵懒、休闲、享乐著称。有人说,这个城市每天都有三十万大军在麻将上驰骋,有个笑话,说飞机经过成都上空即可听到下面人在打麻将。我不是成都人,但在此已生活十余年、也认为这个城市少了些阳刚之气,多了些自我陶醉。正是这种偏见,让我在望不到头的
“长龙”面前越发地感动起来。雨哗哗地下着,我呆呆地立在嘈杂的广场上,对这个城市涌生了从未有过的敬爱和自豪,即使在雨中,我依然感到我的泪水是烫的,夺眶而出,灼伤了我的眼。也就是在这一刻,我开始强烈地问自己:我应该做些什么?我能为灾区做些什么?
回来的路上,我连找三家银行,终于在草堂附近的交通银行提到了49999元存款,决定捐给灾区。本来想多提一点的,因为没有预约,是临时取款,银行只能取给我49999元(五万以上要预约)。当天没有捐出去,不知道往哪里捐。第二天,因为举家往乡下转移也没时间去捐。第三天上午接到单位通知,单位组织捐款,我带着钱去单位,照旧是一边开着车一边听着广播。广播告诉我,伤亡人员在急剧增加,来自全国甚至全世界的救援人员也空前之多;车窗外,到处是露宿的帐篷、救护车、赈灾车、捐赠点……熟悉的城市看不到熟悉的景象,一切像是都变了样。人们扛着成箱的食物、矿泉水、衣服穿梭在大街小巷。不知怎么的,我突然觉得身边的钱太少了。我发奇想,给十一岁的儿子打了一个电话。我从儿子出生的那一天起,每年生日给他存一万元钱,计划是存二十年,算是给儿子将来的创业基金吧。我决定把这笔钱拿出来捐给灾区,跟儿子商量。儿子爽快地同意了,不知是出于觉悟还是无知。于是,我掉转车头,去罗家碾农业银行取款。银行给我算了一下,连本带利有十五万零几百元。我要求取十五万。按银行规定我知道是不可能的。但当得知我是准备去捐款的,负责人当场拍板。同意我一次性取出。
就这样,我有了二十万,我决定全部捐给灾区。我知道二十万对灾区来说是微乎其微的,对我来说却是个很不小的数字,取了钱以后我也一度犹豫过,我需要给自己找到一个强大的理由。我甚至给好几个朋友打去电话,征求意见,一小半支持,一大半反对。反对者认为,我儿子还小。对这笔捐款他未必能懂其中的意义,我在数字上过于高调可能也容易引人非议。但我最后还是一意孤行,似乎没有太多的理由,只是一种心情。
也许是因为我太看重这笔钱吧,当时我有个想法,希望能知道这笔钱将来的去向和用途。单位负责捐款的人无法告诉我,让我自己跟红十字会联系。我跟他们联系,也许是太忙了、太累了,也许是捐款的人太多了,也许是我的要求过分了。总之,我得到的答复不但是否定的,而且是冷淡的。我觉得非常失落。我把钱扔在车上。开车回到了乡下。这天手机已经基本正常,我跟作协领导和几个在灾区有一定领导职务的朋友联系,目的就是想把捐出去,捐到一个有名有姓的地方。锦竹一位局长朋友提示我,可以灾后援建一所学校,只是我的钱要建一所学校似乎太少了。她建议我不妨私下找些朋友,再凑一些钱,等救灾工作告一段落后,她来帮我负责联系援建事宜。
我觉得她说得在理,便开始“募捐”了。
募捐记
我最先“募捐”的对象是阿来,电话打过去,说了想法,得到的反应居然是没反应,令我很诧异。事后我才知道,当时他的三妹在震中映秀镇失踪,尚未找到。他心烦意乱。四处奔波寻找,自然难有他心。是祖坟冒了青气的运气,阿来三妹绝处逢生,失踪后第三天,徒步从灾区走出来,虽然历尽惊吓和艰险,但终归是平安了。
5月16日,也就是阿来得知三妹无恙后的次日,我和他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邀,去北京搞义卖签售活动。因成都机场忙于转运救灾物资,客运很不正常,我们自己开车去重庆搭机,一路上我谈起“捐款记”和募捐的想法。谈着谈着,来了劲,我们想,能不能以灾区作家的名义发起一个倡议,邀集更多的人来做这件事。从成都到重庆的路上,我们俩轮流开车,分头给各自的朋友打电话,朋友们非常响应,令我们非常感动和冲动。接下来,阿来与阿坝州教育局领导联系,我们提出,对我们募来的善款是要专款专用,还要接受我们的监督和管理。对方并无异议。便很顺利地达成了相关协议。虽然是口头的,但至少有了一定基础和保证。后来,我们还联系上四川儿童文学作家杨红樱,她捐款二十万,并愿意加入我们行列,与我们一起来做这件事的发起人。这样更增加了我们做这件事的信心和力量。
开始,我们只是在私下募捐,主要在朋友和作家圈内进行,后来在新浪读书频道作客聊天时偶然谈到这件事,一下得到了好多人的支持和响应。就这样,我们的“心”也越来越大,专门写了倡议书,公布于众。从此,我们有幸强烈地感受到了一颗颗来自全国、全世界各地滚烫的心,一份份沉甸甸的血浓于水的真情爱意。灾难无情,人有情。作为灾区一员,这次灾难给我的震撼和感动是破天荒的,一方面是灾区噩耗频传,令人痛心疾首;一方面是身边赈灾的感人事迹层出不穷,令人豪情万丈。为什么我的眼里总是含着泪水?因为我深深地爱着这片土地。爱有时显得那么空洞、稀缺,但在今天,在汶川,在北川,在青川,在四川,在我们身边,在我们的倡议行动中,又是显得那么的多,那么的深,那么的具体实在。连日来,我们几乎时刻都能看到、体会到人心空前清澈、善良、美丽的美好图画。汶川把我们的心紧紧相连了!如果灾难注定有这样的效应,那么请允许我说:我接受这样的灾难。
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杭州……一夜间,我们拥有了无数熟悉又陌生的朋友,有的致电,有的来信,有的汇款,我们的心一直处于不休的感动中。由于仓促,我们的倡议行动其实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没有人怀疑我们,更没有人指责或嘲笑我们,有的都是伸手、握手、拥抱,直接、间接地加入到我们的行动中来。北京的脚印,上海的袁杰伟,广州的谢有顺等人,他们不但自己捐款,还直接参与到具体的工作中,牵头在各自的城市里为我们呼吁,组织身边的亲朋好友与我们一起高唱“同一首歌”。于是,余秋雨、黄育海、路金波、冯小虎、侯洪斌等等,等等,举不胜举,都成了我们的朋友、战友,成了灾区无数孩子的知心人,他们亲爱的叔叔、阿姨,想象着,有一天,这些人的心意和愿望将变成一块块砖,一片片瓦,一本本课本,一支支钢笔,一棵棵小草,让今天还沉浸在悲痛中的孩子们绽放出一张张笑颜,在琅琅的读书声中度过每一天,在知识的海洋中欢快畅游。游过废墟,游过悲伤,游过冬天,游向春天,游向蔚蓝的天空,我们就觉得再累也要把这件事情做下去,切实地做好它。我们相信,也请广大的读者们相信,我们不会糟蹋每一分钱,我们要让每一分钱都闪光,都落到实处,都去努力抵抗今后可能有的地震、飓风、泥石流,以及各种各样的灾情。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灾难教会了我们如何去面对灾难,那就是用真心去凝聚真心,用真心去呼唤真爱,用真心去关爱需要我们关爱的人,用真心去创造美好的明天。
亲爱的朋友们,衷心地感谢你们!
灾区的孩子们,你们别怕,有无数的叔叔阿姨与你们在一起!
拷问记
从地震第三日起,约我写稿的报刊,像私下勾通好的,电话,短信,邮件,留言,纷至沓来,一
发不可止。到18日下午,举国默哀的公告发布后,形成高潮,几小时内至少有几十家报刊,诚恳向我索稿,理由充足:你是灾区作家。我一概拒之。其实,正因我身在灾区,我失去了发言的欲望。一方面,大量实时新闻、直播报道铺天盖地。席卷而来,我旁观看到的、想到的多数已经被人充分乃至重复地说了,我说无非是再重复,意思不大;另方面,我确凿想说的一点真切感受,悲痛中夹杂着巨大的愤恨,说来也不见得好。大“敌”当前,我们需要团结,鼓劲,把愤怒藏起来,把恨转化成爱,把语言变成行动。我不顾“作秀”之嫌,像个“富豪作家”一样的高调地捐款,后来又与阿来、杨红樱以灾区作家的名义发起“5·12灾后乡村学校重建行动”,四处募捐,正是因于我有些独特的所见和感受。我本不打算说出这种感受的,这中间既有个人的隐私之故。又有公理公心之因。但连日来这种相似的感受被一再放大、强调,如鲠在喉,有点不说不快的意味。那就一吐为快吧,我对自己说。
事实上,地震后第二天,我在银行取了款后(第一笔款),想捐又不知往哪里捐,开着车,漫无目的地在城里乱转一气,不知不觉中,车子已经开出城,上了三环路。要没有突然听到广播上报都江堰严重的灾情,我应该是在成温路口(成都到温江)出来,去温江乡下,那里有我临时设的避难所。其实之前我并不知道这次地震都江堰是重灾区。我以为都江堰离成都仅三十公里,成都无大碍,想必那边也不会有大灾。但广播上告诉我,都江堰的灾情十分严重,死亡人数已达324人(是当时众灾区已知的死亡人数最多的地方)。我大为惊诧,连忙给我在都江堰的三位老友打电话。电话都不通,发短信,只有一人回信告知他平安,另外两人:黎民泰和W,连发多条短信,均无回音。适时,广播上具体说到都江堰XJ小学的一栋教学楼垮了,有二百多人被埋在废墟中。这个消息让我震惊无比,因为我知道W就供职在那学校。没有思考,没有决定,我的车像认识路似的,一路往都江堰驰去。
这是灾后第二天,救灾工作尚未完全展开,去灾区的路还没有彻底被管制起来,高速路排起了长龙(也许是受了管制),但老成灌路、成青路都未见大的异常。我走的是老成灌路,虽然下着雨,路况不好,但还是能走,没有遇到交警阻拦(第二天私家车就不行了)。追究W是什么人。和我有什么特殊的关系,没意思,她如今长眠地下,我说什么都听不到了,但并不意味我可以乱说。她很年轻很漂亮,如果可能做她的男友,我会很荣幸的。但事实上,她只是我一个稍稍特殊的读者,我们在2003年相识,见过两次面,当时她还在成都某高校读书。毕业到那边工作后再没有见过面,只是偶尔会给我来个邮件和短信,连电话都没有通过。直到去年11月,她突然给我来了一个电话,我知道她结婚了,但生活似乎遇到了一些问题。所以想见见我。电话中,我听到她的抽泣声。当时我正在做新书《风声》的宣传,不在成都,只是简单地安慰了她,答应回成都再见面。后来她没有再来电话,我虽然偶尔也想去见见她,但终归没有成行。我惦记着她的生死,这可能就是原因:我没有践诺,而这本来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现在她去了地下的远方。我永远失去了践诺的机会。与她的死相比,我因为失信而难过的心情似乎不值一提。但问题就在这里,她死了,我的愧疚将永远活着。
我今天要说的不是W的问题。这是个私人问题。我个人可以解决:即使解决不了,受拷问的只是我——我乐于被拷问可以把它留着:不乐于接受拷问,也可以把它丢掉。我要说的是一个可能跟我们大家都有关的问题,当我赶到XJ小学时,开始居然有一种错觉,以为这里不是发生了地震,而是在拍电影。因为我看到只有一栋楼塌了,周围的建筑都骄傲地屹立着,仿佛塌的这栋楼不是地震塌的,而是被定向炸药爆破的。现在已经确认,这栋楼埋葬了240名师生,它就是XJ小学教学楼。提前一天,我们也许无从知道这栋楼的内部细节,现在坍塌成一堆废墟,墙体、预制板、横梁裸露在外,乱七八糟,却无法掩盖铁的事实。两名疯狂的家长对在场的记者高举着断裂的预制板。要记者看里面有什么,有没有钢筋?没有。我看到,里面什么也没有,连铁丝和竹条都没有。我马上想到,周围的楼房为什么不倒,秘密就是它们的水泥里面也许夹着钢筋,或者铁丝,或者竹条。
因为W,我不幸看到一个现场,一个真实,它让我已有的悲痛变得不再那么单纯,而是裹挟着一股无名的愤怒。我离开现场时,甚至暗暗地希望那些已经在雨中哭干了泪的家长举着断裂的预制板去上告,查个水落石出,把偷吃了预制板里的钢筋的恶鬼揪出来,判入地狱,生不如死。荒唐的是,我这么想着不久,绵竹的一位局长朋友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一件事:他们领导、也是我的朋友蒋书记今天当众跟群众下跪了,现场有记者,可能要报道,想我在媒体工作,又是名人,能不能找有关领导说一说,别报了,即使要报也找个好角度报。我纳闷书记为什么要给群众下跪,局长说他们那儿死了好多学生,家长要去上级部门告,他去劝阻,阻止不成,情急之下,跪地而求。我说这是地震哪,是天灾,有什么好告的。局长说,你不知道那些校舍建的质量差。家长们说是豆腐渣建筑,家长们气不过,要去讨说法。我马上想起刚才看到的那些“空心”预制板,心里想,看来这不是XJ小学一个学校的问题。
何止是一个学校!
我掌握的资料非常有限,据我所知,在这次地震中四川省坍塌的学校有北川中学、聚源中学、向峨坝中学、汉旺中学、漩口中学、东汽中学、木渔中学、红白中学、红白小学、映秀小学、富新二小等不下30所,倒塌的校舍逾万间。迫使我朋友下跪的就是富新二小的家长,这所学校倒塌的教学楼的建筑图纸听说是偷来的,是某中学的复印件。复印件如果按图施工,可能也不会顷刻倒塌,关键是偷来了图纸,施工中又偷工减料,一偷再偷,结果把孩子们的命都偷走了,把我朋友——一个堂堂书记的尊严也偷走了。所谓朋友,其实也是一面之交,并无多的往来和交情。印象中,他是个大块头,大嗓门,年轻时当过多年兵,后来又干过公安,应该不是那种软弱无能的人。我难以想象,他因于何故要下跪,是出于对死者的同情,哀而无膝?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但愿他是“哀而无膝”吧,这样丢失的也仅仅是尊严而已。面对那么多年轻的生命,尊严又算得了什么呢?
地震虽然才过去十多天,但有个问题已经是老得成茧了:为什么倒塌的建筑中有那么多是校舍?为什么那些校舍总是在顷刻间坍塌,以致连我们年轻活泼的生命都无机逃生?坍塌的校舍啊,你多摇晃几下再塌吧,他们会跑得很快的,因为年轻。可你是空心的,不长骨头的,又是年久失修,只会在风中摇晃,哪会在八级大地震中摇晃?如此大的地震,你没有第二选择,只能在刹那间崩溃,裂成一堆烂砖烂泥。可你为什么不长骨头?难道你的骨头全是黑心老板吃的?我刚看到一篇文章,是《南方周末》记者傅剑雄和姚江采写的《聚源中学倒塌悲剧调查》。聚源中学和XJ小学同在一城,这次地震中有两栋教学楼在瞬间化为乱堆堆,损失比XJ小学还惨重,有278名师生遇难,11人下落不明。傅、姚的《调查》在列举了众多悲剧后明白地告诉我们:四川省从1992年到1996年完成“普九”,到2005年尚欠“普九”81个亿,到去年底还欠近40个亿,其中都江堰在去年底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还在强调“普九”的债务问题。1996年应该完成的“国家任务”,十二年后还欠着几十个亿的巨债。
都说,孩子是祖国的花朵;都说,教育是国家的根本;都说,老师是辛勤的园丁;都说,龙门山脉是地球人都知道的地震带:都说,现在的孩子都是独生子女;都说……都说……我们什么都会说,说得天花乱坠,说得口沫横飞,说得津津有味,说的比唱的好听,可就是说完拉倒,过过嘴瘾,不见落实,为什么?为什么?!这个问题太深奥,我也许不配知道。
2008年5月21至24日
责任编辑:杨新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