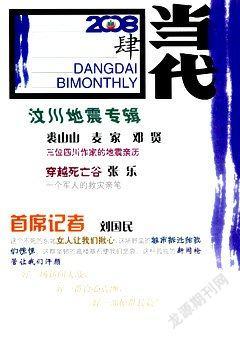最艰难的13个
王 甜
2008年5月12日晚上,一列由云南开往四川成都的火车专列神情凝重地出发了。
77208部队的一行人是晚上10点左右上的车。他们总共有50多人,在这列上千人的军列中,这个数字是微不足道的,但他们看上去却非常打眼——都身着橘黄色的救援服。这种服装像宇航服一样从头到脚整个套上,在夏季给人一种密不透风的憋闷的感觉;而鲜艳的色彩更是把他们从一火车着迷彩服的军人里生生地剥离出来,不引人注目简直不可能。更何况,这群衣着“光鲜”的大小伙子居然还带了三只狗——专业一点儿说,是三只救援犬。
他们已经惯了别人好奇的目光。橘黄色的救援服,他们穿过很多次了,几乎就是他们的工作服;至于救援犬,对他们而言完全就跟战友一样。
他们是成都军区唯一的一支地震灾害救援队成员。
救援队是部队编制,但又是和地方联合组建,全称是“云南省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自从2003年12月27日组建以来,这支救援队已经在不少地震专家的专业指导下进行了严格培训,并参加过云南耿马、普尔、盐津等地的地震灾害救援行动,算是具备相当程度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了。
但眼前,刚刚发生的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地震,将以凌厉的姿态挑战这支年轻的救援队,他们所有的专业信息、现场经验乃至心理素质都将受到严峻考验。
带队的是少校参谋长商志军,上车前就跟大家开了会,把情况通报了,也没多的话——要尽快熟悉情况进入状态,要尽一切可能搜救群众,也要坚决保证自身安全!
中尉孙自彬在硬座位置上调整了一下坐姿,让自己腿舒缓一下麻木的感觉。他长着一张充满善意的国字脸,个子不高却很敦厚。他不是搜救队员,是部队的宣传干事。宣传干事总是作为战地记者跟随部队行动,干这行的都习惯了。现在他看着脖子上挂着的厚砖头似的数码相机有点儿发愁。
“小何——”孙自彬冲对面座位的小战士轻声说。
叫了好几声战士都没听见,他正面向车窗外,拧着眉头想着心事。
“小何!”孙干事只好大声嚷。
小何一惊,回过头来,有点儿不知所措的样子。小何叫何松林,是文书,这个岗位仿佛是专给他预备的,他干得得心应手,写写画画很有一套;就是长得太奶油,一张脸白白净净,一点沧桑感都没有,这个“先天缺点”让某些战友私底下议论过,也有人为他辩护:唉,城市兵嘛,长相柔一点儿很正常!
那意思是城市兵总是很少吃苦的。
但孙自彬了解他——长的是有些“韩潮”,一上了阵地,照样是猛打猛拼的。
何松林这时不好意思地问:“孙干事。什么事?”
孙自彬说:“小何,给你个任务,到时候我管摄影,你管摄像!我一个人忙不过来。”
因为文书也不算专业救援人员,孙自彬才敢给他布置这个任务。接下来孙自彬把摄像机拿出来,对小何进行了简单的操作培训,几分钟之内,在轰隆轰隆的火车上,一个新人行的摄像师诞生了。
小何低头摆弄完摄像机,把机器小心收好,又坐在位置上,面朝车窗外凝神沉思了。孙自彬忽然觉察到什么,问:“小何,你家是哪里的?”
小何回过头,淡淡地说:“四川——绵阳。”
顿一顿,他紧接着说:“不用担心,家人都安全撤退了,只是房子裂了,不敢住了。”
孙自彬刚要说话,小何又抢在前头,倒像是安慰别人似的,说:“我们已经够幸运了,真的,人没事就好,房子也没有垮成一堆渣子。”
话都让这个懂事的孩子说完了。孙自彬最后什么也没说。
到达成都站以后。救援队坐汽车直奔最重的受灾地——北川。
那时已有少数部队到达,但尚未进驻。地震造成山体滑坡。进入北川城的路被巨大的山石堵住了。没办法,救援车只好绕行,从安县绕了个大圈,找到另一条路,开到车不能通行的地方了,救援队员们便扛着笨重的器材,带着搜救犬徒步进入北川城。
那已是14号晚上6点多钟了,通往城区的“路”是先期到达的部队用脚走出来的,被大大小小的乱石覆盖着,大家又是负重行军。行进显得相当艰难。速度很重要,对搜救工作来说,速度意味着对抢救时机的争取:而对队员们本身而言,如果不快速通行,这里随时会出现余震,造成路边的山石再次滑坡——潜在的危险像夜雾般缥缈,每个人都绷紧着神经努力前进,加快步伐,再加快……
天色渐渐暗下来,队员们打开救援帽上的灯照明,孙自彬也拧开了手中的电筒,光圈晃着晃着,忽然,扫到路边一个人!用毛毯盖住的一个人,什么都盖住了,却仍让人感觉到他是冷冰冰的,毫无表情的。
孙自彬的心脏猛地一缩,赶紧把电筒光晃到一边儿去。
是做好心理准备的,但乍见第一个遇难者,还是让人难受——莫可名状地难受。
谁都不是铁打的。到底有血,有肉,还听得见突突突的心脏,在跳,在痛。
肯定队员们也看见了,但谁也没开口说话。隐隐感觉到了,他们将应对一个怎样的场面。
进到城了。
应该是进到城了。
说“应该”,是眼前出现了明确的路、东倒西歪的房子,但却没有一般城市所具有的人气。
一片死寂。除了手电筒,没有别的光源,偶尔有人走过,都匆匆忙忙,不吭不声,在黑暗中犹如游魂一般。部队来的人都在各个救援点上搜救。在路上窜的主要是还留在城里搜寻亲人的难民。还有最早一批闻风赶来挖新闻的记者,都有些失魂落魄的样子。
“请帮帮忙!”
终于有人说话了,相当惶恐的声音。
昏暗中跑来一个人,自称是《南方都市报》的记者,他尽量控制着自己激动、紧张的情绪,万分紧急地告诉大家,曲山小学特别需要救援。
一听到“小学”,人们眼前都会浮现出花朵般的一张张脸,笑脸,世上最无邪的脸。参谋长二话没说,立即带上队伍。来到严重受损的曲山小学。
曲山小学和很多北川建筑一样,坐落在山脚,倚山而建。教学楼已经没有一楼了,上面的楼层直直地落下,现在的“一楼”就是原来的二楼。很多楼板都垮掉了,整栋建筑变成了很奇怪的罐头盒,只有外面还是楼的样子,里面却是乱做一团了。
以目前形势看,必须从教学楼背后的山坡人手,居高临下进行搜救。
前期在这里进行搜救的成都军区某集团军某师装甲团的官兵。他们尽了最大努力——冒着巨大危险,弄来一根树桩,死死卡住已经断裂但还未垮塌的顶梁,不让它掉下来;没有足够挖掘工具,他们把小学大门上做栅栏用的钢条生生地掰下来;他们探测到这里某些位置还有活生生的孩子……
他们努力而顽强,但毕竟没有专业知识与专业设备,在这样复杂的条件下,要救出稚嫩的孩子,实在力不从心。
救援队的重要性,总是在最危急的时刻、最复杂的环境、最迫切的需求中体现出来。
就像一句广告词所说的:因为专业,所以领先。
他们救的第一个,是个十一二岁的小女孩,她在“一楼”,被预制板压着腿。当时是看不见她的,只听见她说话的声音:
“叔叔,我饿……我嘴边有石头,我就吃了……”
“不要吃石头!”大家冲她喊。
“我饿……”她被压得久了,伤痛也变得麻木,倒只觉得饿了。
“好孩子别怕,不要吃石头,叔叔马上给你拿吃的……”
但是医生建议不要给孩子固体食物,可以送流质的。搜救队员想办法把一盒牛奶递给了女孩子。
还是看不见她,她头朝里面,但她一定喝得很香。
是从8点20分开始救援行动的,队员们用专业器材对板材进行切割,打破障碍物……这可不是一般的切割、打破,每一步都必须精心计算、严格策划,必须保证三个方面的安全不受威胁——被救的女孩、其他被困待救的孩子、救援队员自己。
千难万难啊!
连续奋战了2小时零7分钟。终于把小女孩救了出来!
是个短头发、小长脸的女孩子,救出来前五分钟还在说话,一出来她却昏迷了,绵阳120的医护人员对她进行了现场抢救,十多分钟以后还没有从昏迷中醒来,但脉搏仍是有的,医疗人员当即做决定,将她紧急送往医院了。
没有再见到她,不知道她挺过来了没有。孙自彬倒是挺惦记的。
对于搜救队员来说,他们与遇难者的会面。常常只是救出来的一瞬间,之前与之后,“生死两茫茫”。
这是缘分。
天地间,一些生命与另一些生命的碰撞,总是有由头的,不拘是哪种形式。
同是在曲山小学,教学楼的大厅垮塌。一条弧形水泥板扣下来。压住了大厅里的两个小姑娘。她们腰部以下的部位被压着,上半身则抱在一起,都是十一二岁的年纪,一个叫何亚军,一个叫牛钰晶。
这个情况很特殊,不好处理,必须要使用某些专业器械才能实施操作。而这些器械在救援车里,车还进不来,只有等明天路通了才能施救了。
这意味着,两个小姑娘还得等待一晚上。一晚上,说来容易,对小孩子来说,没有父母,没有灯光,这样的黑夜是多么漫长啊!
救援队队员于明华开口了:“让我留下来吧,陪陪她们,一定把她们照顾好。”这么一来,另一位队友也主动表示愿意留下。
女孩子们的眼中有了些许放心。队员们给她们递牛奶。她们乖乖地喝了,把盒子放在一边,用恬静的声音说:
“谢谢叔叔。”
过了一会儿,她们又像在家里一样,平静而有礼貌地向队员们说:
“叔叔晚安,我们睡觉了。”
说完这话,两个女孩果然相拥着睡觉了。有解放军叔叔在身边陪着,还有什么害怕呢?她们睡得很沉、很香。好像地震不过是一个童话故事,离她们远得很哪!
甜甜入睡的两个孩子,表情像天使般晶纯,仿佛被上帝恩宠着,没有一丝忧虑。和天使睡觉唯一的不同在于——身上没有盖被子,只“盖”着水泥板。
她们的坦然震撼了所有救援者。
坦然,出于信赖。
她们本能地相信,解放军叔叔来了,自己就一定得救了。
所有孩子都会这样认为吧?
第二天,路终于打通了。装着宝贵器材的救援车开了进来,可以对两个孩子施救了。在救援操作的时候,她们也平静地等待着,一点儿没有慌乱。
留着长头发、一张鹅蛋脸的牛钰晶忽然说:
“叔叔,你可以给我唱首歌吗?”
于明华说:“为什么要我们唱歌?”
“你们的歌好听,是军歌。”
“你喜欢听军歌?”
“嗯!”牛钰晶坚决地说,“我长大了也要当解放军!”
她一定也想当一个救好多好多小朋友的解放军。
可是这个想当解放军的小朋友不够“勇敢”,被救出来以后,反反复复地说一句话:“叔叔,请你不要动我的腿……”
她们的腿被压得太久了,医生当场就对其腿部进行按摩,使血液通畅,恢复功能,两个小姑娘那个疼啊,哭着叫着,“不要动腿啊”,脸上也是血淋淋的……她们已在废墟中度过了六七十个小时。
好在,姑娘们不仅保住了性命,那难以忍受的腿,最后也得以保存下来。
另一个小姑娘就不是那么幸运了。
是5月15日一大早发现的。地震发生时。她一定是想往外跑的,却被垮塌下来的整幢楼的横梁压住了左小腿,完全无法动弹。
救援三组组长李虎细心查看了一下具体情形:她在四年级教室右面墙壁拐角处,左右两边居然是一男一女两位同学的遗体,死去的小男孩左腿被砸断了,就那么血淋淋地吊在她左腿上方;离她不到一米的左墙上。悬着两块摇摇欲坠的楼板。而她面前则堆满了碎石烂砖块……
难以相信,小女孩不仅经受住了长时间的恐怖的视觉冲击,还撑着虚弱的身体,向李虎露出了艰难的、然而又是坚定的笑容:“叔叔,我能坚持……”
她的眼睛闪着晶莹的光芒,那已经不像一双孩子的眼睛了,眼睛里毫无掩饰地透露出世上最残酷的、最本质的东西——对死亡的拒绝,对生存的渴望。
李虎的心像是被什么击中了。
经过反复勘察、论证、比较,队员们决定对楼体实施顶撑和加固后再予以营救,但是挂在墙壁上的楼板是个重大隐患,还有,如果遇到强烈的震动(余震或人为因素),房屋的主体可能继续崩塌!
太难了。李虎再次钻进废墟,他需要女孩子的配合。拉着小女孩的手,他微笑着问:
“小妹乖。不要怕。叔叔们都做好准备救你出来了,告诉叔叔你坚强吗?你什么地方受伤了?你叫什么名字呀?今年几岁了?读几年级?……”
一连串的问题让女孩放松了,她缓缓地回答:
“叔叔,我很坚强,我叫李月,在四(3)班,我的腿被压在房子底下了,左胳膊也不能动了……”
李虎不愿让她纠缠于自己的伤痛,赶快打断她的话,说:“叔叔也姓李,说不定我们以前就是一家人呢……”
由于小李月身体不能挪动,救援人员不敢用任何的器材展开工作,一是怕再次伤到她,二是怕碰到或者震动旁边悬在空中墙壁上的楼板和破坏房屋现有的稳定性。只有用双手刨才是最安全的。李虎让组员陈贞彩过来照顾小李月,自己则开始用双手刨去她身边、腿边的碎石烂砖,遇到大一点儿的砖块拿不出来,李虎就用手指头向外一点点儿地抠旁边的沙土。从早上7点10分开始进行,直到小李月的左腿露出三分之二来,竟然花了近三个小时的时间!
但是再往下、往脚的方向刨,却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了,因为往下是第一层的地面,脚的方向是墙壁的“大梁”。李虎想了不少办法,比如在大梁下挖个空间,把大梁稍微向上撑起来一点——虽然很危险,但也只有这样才能完全取出小女孩的腿和脚。
经过努力,顶撑并没有奏效;李虎又把李月左边死去的小女孩抱开,看能否有点儿机会,但结果令人失望。这时,垮塌的教室深处传来另一个孩子的声音:“叔叔——快点来救救我们吧——里面有两个已经快不行啦——她们呼吸困难了——”
还有别的孩子啊!
谁不着急呢!李虎又趴到小男孩的遗体旁去摸李月的小腿,详细询问她现在的感觉,李虎发现,她的小腿由于长时间压埋已经失去了知觉!很快,医生将其确认为粉碎性骨折,建议截肢。在这种情形下,队长召集分队长和李虎紧急研究,决定接受医生建议,对李月实施截肢手术后再予以营救。
小李月怪聪明的,听到大人们这样商量那
样商量,一下子听懂了,当下就哭起来:
“叔叔……请不要锯我的腿……不要锯啊……”
一声叠一声的,听得人心里发颤!
李虎泪如泉涌。
很快,海军总医院的医疗队做好了准备,他们就在危险的受灾楼里、在尘土纷飞的环境下对小李月实施了快速截肢手术;一截掉,一位医生马上就用棉纱布将她的腿包住、按住血管,外面的战士早已排成两队,接力赛一样将担架传出去。
这是个漂亮的小女孩,扎着马尾辫,脸色苍白。
在这个年纪的漂亮女孩,大约都是喜欢跳舞的吧?没有问过她这个令人伤心的问题。因为它不再有任何意义——对一个将左小腿永远留在学校废墟中的小女孩来说。
望着膝盖以下已经荡然无存的李月,李虎流着泪,愧疚地对她说:“叔叔对不起你,没能把你完整地救出来。叔叔欠你一条腿……”
对曲山小学的救援,面对一个个天真孩子的救援,是队员们难以忘怀的一课。
孙自彬看见他“聘请”并“培训”过的何松林,根本没有进入到“摄像师”的职业状态,他动不动就把摄像机往旁边一放,抡圆胳膊帮救援队员干起来。不会玩专业的,打打“下手”总是可以的吧?干点儿技术含量不高的粗活总还是可以吧?
在网上吵得沸沸扬扬的有关“摄影摄像师的职责与对生命实施救助孰重孰轻”的讨论、争执,在何松林那里一点儿没有思想上的斗争。他做出选择很干脆——甚至他根本就没有选择,只是一种本能。
是的,当你面对那样无助的、末日天使般单纯的目光时,救助,就成了你的本能。
他们在曲山小学救出了救援难度最高的几个孩子,其余的就交给先前那支装甲部队的官兵了。连同装甲部队搜救的,这里一共救出十七八个孩子。
这个数字,已经是个奇迹了。
旁边就是北川中学的新校区,非常不幸的是,地震造成山体滑坡,滚落的山石正好从这所学校背后直扑下来,把整整一所学校埋进了泥土与山石里。整所学校,只有一面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和一块被清理出来放在前面的学校名称的牌子还可以向人们证明,这是一所学校。
还有一次搜救行动令人难忘。
那是距今为止,他们最后一次救援出活着的灾民。
已经是17目的早上了,有人来报告,在老城区十字路口的一家宾馆里还有幸存者。
那是一幢原本有七层的楼房,在这时整栋楼往地下“坐”进去很深,而露在地面上的部分也已经呈近乎45度的倾斜状态,作业难度与危险程度都是相当大的。
从这幢歪斜得几乎不真实的大楼深处传来了声音——很确切的、人的声音,根据详细考察、分析,大家断定这个人处在楼房原来的第四或是第五楼,现在,整栋楼房层数的概念被重写,他被深度掩埋住了。
分析得一点儿不错。
被埋住的是个50岁左右的中年男子,他落在楼房混乱的建筑板块中,头朝下被夹住了。这个地方,离地面还有六七米。根据种种测算后得出方案,必须倾斜着打开通道进行救援。
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既要小心翼翼不震动房子,又要打开一个生命的通道,救援队是把性命悬在45度的倾斜度上了。
队员们迅速分工协作,各人受领了具体工作,默契地干起来。45度没有吓倒腰板挺得笔直的小伙子们。
老天于是决定给这支近乎出神入化的救援队一个更大的考验。
到了中午时分,忽然一个消息传来,山上的堰塞湖出现险情,危及山下的县城,留在北川城里太危险了!不少正进行搜救工作的人员都被迫往城外撤退。
怎么办?
前来执行任务之前,上级就明确过意见:救援队必须要保证自身安全,否则,不但完不成任务,还会造成更大的伤亡事件、加重救援实力损耗,一旦连你自己也成了施救对象,就会给其他救援部队增加负担。
何况,这可是活生生的几十号人啊!再是受过专业培训,再是身怀绝技,谁又不是肉体凡胎?小伙子们的亲人把他们交给了部队,部队也有责任保证他们的安全啊!
参谋长商志军一想到这儿,把手一挥,指挥大家组织起来,以最快的速度往城外撤退。这意味着,救援那名中年男子的工作被迫停下来。
谁都做这样一个简单的比较:是一个尚不清楚伤情轻重的人的生命重要,还是几十个健健康康、活蹦乱跳的年轻生命重要?选择似乎并不困难。
然而在撤退过程中,商志军的头脑里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斗争。他算是见过大风大浪的老兵了,多年的军旅生活给他打造了一个标准的军事化大脑,使他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就算忘了自己姓什么,也不忘记——自己是个军人。
“停!”商志军把手抬起来做了个手势,顿住了。
他的部下——身着橘黄色救援服的小伙子们很自然地立定了。
孙自彬看到了参谋长脸上复杂的表情。
他们已经到了城区边缘,只要几分钟,就可以顺城外的公路一溜烟地上行,脱离受上游洪水威胁的低洼地带。
参谋长却让大家在半山腰停住了。他的目光投向堰塞湖的方向,眉头紧锁。
身高一米八的参谋长商志军是河北承德人,平时很有主见,办事果断,一副天生干军事的大嗓门,生起气来,吼一声,不是地震也是地震了。他是很有威信的,大家都服他。
“人不救出来不行。”
大家都听到了参谋长的话了。这句每个人都梗在心里的话。
孙自彬、何松林,还有全体救援队的队员,神情庄重地站在参谋长面前,等待他做一个生死攸关的决定。
“同志们,”参谋长一字一顿地说,“我没有接到我的直接领导发来的撤退命令,我们不能撤!任务还没有完成啊!”
大家都听明白了,点点头,有的人又低下了头。
“我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这很冒险,很可能险情出得突然,上级没有及时得到消息,或是,或是因为通讯信号中断,他们没有办法联系上我们,但……”商志军咬咬牙说,“你们忍心扔下还有一口活气的人吗?哪怕……只剩最后的一个……”
“参谋长!您就别说了,直接下命令吧!”
一位战士说。他的眼里是一片宁静,像灾区等待救援的孩子,一片宁静。
那是2008年5月17日的正午。灾后第五天的北川。已经片瓦无存、成为太垃圾堆的北川。头上顶着数个岌岌可危的堰塞湖的北川。
对很多很多人来说,这是个只可远观而不可接近的恐怖地带,而现在,有一群人就要以生命作注,向着北川挺进了。
因为,那里还有一条生命等待拯救。
至少有一条。
“听我命令——”商志军大声宣布,“向作业点全速前进——”
橘黄色的队伍,啪地立正,转身,全速奔袭,向着刚才的救援点进发。每个人心里都涌动着壮烈的情绪,每踏出一步,都是一句地动山摇的誓言!他们也许会成为牺牲者,可牺牲——向来是军人不惮回避的存在方式!
头上有皇皇的艳阳,底下这群鲜艳的年轻人,是当之无愧的太阳之子!
回到作业点,大家便迅速地接着刚才的救援工程忙开了,挖掘,打孔,敲击……不知忙了多久。
堰塞湖的险情终于得到了控制。撤出城的部队又都返回了。如果有人路过,一定会看见,
那支救援队就跟从来没发生过险情一样,专心致志地在一幢歪得离谱的楼前干活儿。
通道打开了,已经能够看见幸存者了,大家都很高兴,以为后面就好办了。哪里知道,这已是地震灾后第五天,这位幸存者也许因为长时间困在狭小空间,精神上受到严重刺激,已经不是一个正常人了,嘴里哇啦哇啦地说胡话:
“你们不要碰我啊,不要吃我豆腐(吃豆腐:四川方言里有比较暧昧、占便宜的意思)……”
队员们把救生索扔给他,让他套在自己身上,他拒绝配合,也不让救援队员靠近自己。真是要了命了,什么情况都有啊!
对方不配合,根本没法把他从深穴里拉出来。
“我来!”二级士官李林把心一横,躬身钻进了窄小的通道。
这条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小心打开的通道有五米多深,李林沿通道往深处爬行,为了减小自身力量对废墟的影响,他动作很轻很轻。
就在进入通道三米多深的时候,只觉得一阵令人恐怖的摇晃发作了,周围的一切都开始抖动!余震!是余震啊!然后听到轰的一声,什么东西垮塌了,李林背后的入口在瞬间被塌下的建筑材料堵上了!
完了!
这是25岁的李林最直接的想法。
他认定自己将要葬身在这陌生的小城了,身边只有一个陌生的精神错乱者。
直到外面的队友把堵住入口的水泥板清除掉,他与队友们隔了一生一世似的互相打量时,他还努力地深呼吸,确定自己没有精神错乱。
要说明的是。在他进入通道救中年人的过程中,一共经历了三次余震,最严重的就是刚才那次。
那位极不配合救援工作的受灾者,大家几乎是强行把他拖出废墟的。获救者并不清楚自己有多么幸运,他神志不清地骂人,骂着这一群以自身性命为赌注的救命恩人。
从早上8点到晚上9点55分。
这就是救援骂人的中年人所花的时间。
还没有完。
就在把灾民救出的第一时间,大家把他放在担架上,用接力形式换着抬,先火速抬到营地的救援车上,再开车火速将他送往北川县城外的医疗点。
车刚刚开出县城,余震又来了,造成一轮新的山石滑坡,他们回过头去看,刚刚走过的路又被滚落的大石头堵上了。
如果晚十分钟,车就开不出来了。伤员不能及时送去救治的话,死亡率是相当高的,这样一来,花费大力气所实施的营救很可能就失去了意义。
他们又一次抢在了灾难前面。
这是救援队在北川营救出的第13个幸存者。
也是最后一个。
孙自彬很怕别人不理解,总是要不厌其烦地解释:不能单纯用数字来衡量搜救工作。我们虽然只救出13条生命。但我们不亚于那些救了几十、几百人的部队,意义同样是很重大的。
因为,需要他们营救的,总是处在最艰难的环境、条件下的生命,总是最需要用高科技手段实施救助的生命,总是——被死神的手攫得最紧的生命。
如果有人以为“13”与庞大的灾难伤亡人数比起来实在微不足道的话,他一定没有来过灾后的北川;没有来过灾后北川的人,难以体会到,每增加一个活着的数字,都是从无情的大自然的牙缝里,一点一点,抠出来的。
2008.5.2714:57于北校场
责任编辑:杨新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