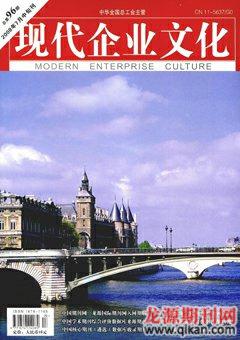职务侵占案件中国家工作人员共同犯罪的定性
曹 喆
【摘要】在职务侵占案件中,国家工作人员共同犯罪的类型比较复杂,尤其是对于国家工作人员与单位工作人员相互勾结,各自利用职务便利将单位财务占为己有的情况的定性,一直颇有争议。对于这种情形,应当依照身份者的实行行为决定共同身份犯的性质这一原则定为职务侵占罪,而不能分别定罪、以主犯定罪或定贪污罪。
【关键词】职务侵占;共同身份犯罪;实行行为;定性
在职务侵占案件中,国家工作人员共同犯罪的定性问题,在理论界一直存在争论。虽然刑法第271条第二款规定,受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的,应当以贪污罪定罪处罚。但是,在共同犯罪中,因为其情形复杂,并不能简单地以贪污罪定罪,分别定罪或以主犯定罪也不够合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了解这类共同犯罪的基本类型,通过不同的类型对于如何定罪进行具体分析。
一、关于职务侵占案件中国家工作人员共同犯罪基本类型的分析
以勾结非国有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中从事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共同侵占单位财物的行为人的不同身份为标准,职务侵占案件中国家工作人员共同犯罪可划分为以下两类:第一,非国有单位的外部人员与受委派到该单位从事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相勾结,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共同侵占单位财物;第二,非国有单位的工作人员与受委派到该单位从事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相勾结,共同侵占单位财物。
第一种类型的职务侵占罪的定性涉及共同身份犯定性标准的问题。由于旧刑法与现行刑法在总则中都没有关于共同犯罪与身份关系的一般规定,因此解决这一问题只能求助于司法解释。1985年,“两高”在《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中指出:“内外勾结进行贪污或者盗窃活动的共同犯罪(包括一般共同犯罪和集团犯罪),应按其共同犯罪的基本特征定罪。共同犯罪的基本特征一般是由主犯犯罪的基本特征决定的。”这一司法解释对于共同身份犯罪而言,意味着共同身份犯罪定性的关键并不取决于行为人的身份,而取决于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理论界对这一观点的反对理由主要有两点。首先,主犯和从犯是以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来划分的,解决的是量刑问题,而非定罪问题;另外,在主犯为二人以上,且具有不同身份特征时,无法以此标准定罪。
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其中第一条第二款规定:“与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这一规定实际上标志着共同犯罪定性原则的再次修正,从而确立了以身份者的犯罪特征作为定罪依据的新立场。也就是说,共同身份犯罪的性质应当取决于身份者实行行为的特征。可以肯定,这一认识是与传统刑法理论相一致的,因为对于共同身份犯而言,毕竟只有通过有身份者的特殊身份才能完成,身份者的犯罪特征对整个共同犯罪的性质具有决定作用。现行刑法第382条第三款的规定沿袭了《补充规定》的精神,指出:“与前两款所列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应以共犯论处。”因此,对于第一种类型的共同犯罪来说,他的定性问题正是这一条款规定的适例。因为该类型中身份者的实行行为属于贪污性质,因此应当依照刑法271条第二款以及第382条第三款的规定定为贪污罪。
第二种类型的职务侵占行为的共同犯罪情形比较复杂:根据行为人利用职务便利的情况,这一类型又可以细化为三种:第一,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单位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共同侵占单位财物;第二,单位工作人员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共同侵占单位财物;第三,国家工作人员和单位工作人员各自利用职务便利共同侵占单位财物。当然,前两种情形实质上同前面提到的第一种类型职务侵占行为没有区别。定罪时可依照前述原则分别定为职务侵占罪和贪污罪。比较困难的是第三种情形的定性问题。
二、关于国家工作人员与单位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共同侵占单位财物的定性
对于这个问题,理论界现存的主要观点大致有下列几种:
(一)主犯决定说
这是最高人民法院的观点。2000年6月最高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贪污、职务侵占案件如何认定共同犯罪几个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中,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分别利用各自职务便利,共同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的,按主犯的犯罪性质定罪。”
主犯决定说只是解决司法困境的无奈之举,在共犯与身份问题上又重复了其原有的缺陷。首先,依据传统刑法理論,共同犯罪人在犯罪行为中作用的大小,只反映了该行为人行人的危害程度,决定了其担负刑事责任的大小,而无法以次判明该危害行为的性质。这一点在刑法总则第26、27、28条的规定中都有直接的体现。也就是说,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作用的大小只是犯罪的定量问题,而不是定性问题,当然这种“定量”只能在“定性”的基础上实现。其次,再只有一名主犯的情况下,虽然共同犯罪的性质按照主犯决定的原则很容易判定,但是这种结果的获得是以牺牲从犯获得公正一致的刑法评价为代价的。因为在这种原则下对从犯的量刑处罚实际不是以其作用大小决定而是以主犯身份决定的。对于作用大小基本相同的从犯来说,完全有可能因为不同身份的主犯而受到严厉程度迥异的处罚,这显然违背了刑法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再次,主犯决定原则只能适应主犯只有一人的情形,而实践中,两名以上不共同身份行为人为主犯的情况比比皆是。在这种情况下,按“主犯的犯罪性质”定罪就缺乏可操作性。
(二)分别定罪说
这种说法主张应根据主体的不同身份分别定罪。就是说对国家工作人员定贪污罪,对单位工作人员定职务侵占罪。
持这种观点的人主张不同身份者利用各自身份共同实施纯正身份犯罪时,如果法律对不同身份者实施的行为规定了不同罪名的,应按照各自罪名论处,分别定罪不仅符合刑法规定,也不违背共犯理论。但是,这种说法事实上违背了共同犯罪的基本理论。在共同犯罪的情况下,行为人主观方面具有意思联络,指向同一犯罪目的;客观方面相互协助,指向同一犯罪结果。各个危害行为结成一个整体,体现了同一的犯罪特征和犯罪性质,因此应定为一罪。如果采取分别定罪的原则势必将打破这一统一的局面,不仅使得共同犯罪的属性难以展现,更无法与单独犯、同时犯的情况相互区别。另外,这一立论根据并不能解释无身份者与有身份者共同犯身份犯时,无身份者以身份者所犯之罪定罪的情况。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无身份者可能同样也具备独立的犯罪构成,比如内外勾结以秘密窃取手段贪污的案件中,无身份者完全符合盗窃罪的犯罪构成,何以不分别定罪而只定一罪呢?
分别定罪说的另一立论根据在于强调这一原则能够充分体现刑事立法对共同犯罪中不同身份这区别对待,对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犯罪从重处罚的精神。这对立法精神的理解是正确的,但其能否适用于共同身份犯罪呢?具体来说,在单位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分别利用职务便利、共同侵占本单位财物的情形下,采取分别定罪的方式来体现这一立法精神是不可能的。因为它背离了共同犯罪这一前提。在已经分别对不同身份者定罪的情况下,连共同犯罪本身都已被消解,又哪里能谈得上区别对待?这种处断方式与对待单独犯的处理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
(三)特殊主体决定说
特殊主体决定说认为国家工作人员与单位工作人员属于特殊主体,但由于刑法对国家工作人员从重处罚这一立法精神,使其与单位工作人员相比较更具特殊性,所以应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以贪污罪定性。
该说虽然能够维持共同犯罪定为一罪的基本立场,但其理论基础并不牢固。因为从身份犯的类型来看,贪污罪与职务侵占罪均属于纯正身份犯,行为人的身份特征对犯罪成立具有决定意义。即使在共同犯罪的情况下,这种决定性作用或独立性意义也不应当被抹杀。该原则导致单位工作人员无异于一个普通人,其身份特征毫无意义。另一方面依照该原则定罪将同样会导致量刑上的失衡。国家工作人员无论处于从犯还是主犯地位,作为同案犯的单位工作人员都可能因为全案性质的变化而上升到较高的量刑档次,接受相应较重的刑罚处罚,这对于利用自身身份便利实行犯罪的单位工作人员来说显然有失公允,不能真实地反映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危害作用。
三、结语
针对上述观点的不同缺陷,我认为应当在以下前提下确立定罪的原则:首先,该原则应是普遍和统一的,能够用以指导各种情况下不同身份这里用身份便利共同犯身份犯的定罪问题。其次,该原则的确立应当以不违背共同犯罪的基本理论为前提。因此,我们仍然可以以身份者实行行为的基本特征作为其定性的一般原则。我国刑法中虽没有明文规定实行犯,但在刑法条文和相关司法解释中均暗含有其概念,这就为该原则的确立提供了法律依据。另一方面对于实行犯在共同犯罪中的核心地位理论界已形成一般共识。一般而言,共同犯罪中教唆行为、帮助行为,都只有通过实行犯的实行行为才能完成共同预期的犯罪,而缺少实行犯,共同犯罪则难以存在。因而以实行犯的基本特征作为认定共同犯罪的基础有着充分的理论依据。这个原则面临的惟一困难在于当不同身份者同为实行犯时如何认定共犯的性质,这也是诸多论者对实行犯决定说的责难之处。其理由就在于认为这两种实行行为在本质上并不相同,难以兼容,从而为共同犯罪认定一罪设置障碍。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换个角度重新审视。
从刑法第271条第一款规定来看,行为人构成职务侵占罪的核心要件有两个:第一,行为人具备单位工作人员的身份;第二,行为人利用了该身份赋予的主管、经手管理本单位财物的职务便利侵占了本单位财物。国家工作人员侵占本单位财物构成贪污罪的核心条件也有两个:第一,具备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第二,利用职务便利将单位财物占为己有。
这里有两个问题要进一步明确:其一,委派到非国有单位从事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是否也属于单位人员?一般说来,普通行为人只要具有与非国有单位的劳动聘用关系,就具备了单位工作人员身份,而受委派从事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则是通过单位对这一委派的接受而获得单位工作人员的身份,也就是说,这是的国家工作人员具备双重身份。其二,国家工作人员利用的职务便利究竟有何特点?由于委派国家工作人员到非国有单位工作的目的在于从事公务,因而其在单位所进行的职务活动必然带有公务的性质。从内容上看,在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侵占单位财物这一前提下,其与单位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并无区别,这一职务活动只能是主管、经手、管理本单位财物,否则就谈不上“利用职务便利”将单位财物占为己有。也就是说,此时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侵占行为与单位工作人员的职务侵占行为除主体身份的差别外,没有其他不同。由此我们可以判断,在单位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各自利用职务便利共同侵占单位财产时,虽然行为人各自有独立的实行行为,但在构成要件的意义上,这两种实行行为是完全相同的:主体上都是單位工作人员实施的;客观方面,都是利用管理、主管、经手本单位财物的便利。所以依照身份者的实行行为决定共犯性质这一原则,对该共同犯罪应定性为职务侵占罪。
当然这一原则虽然维持了共同犯罪理论的基本立场,但并未体现出刑事立法对国家工作人员从重处罚的精神,反过来说,若为了实现对国家工作人员的从重处罚,又不得不背离共同犯罪的基本理论。这一两难境地的出现主要是一直以来我们都认为对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的从重处罚应上升为专门的犯罪来实现。我们仍以受委派到非国有单位从事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侵占行为为例,其与贪污行为虽然同样都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但在所侵犯的犯罪客体,即财产所有权性质上则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国有财产与非国有单位财产的性质完全不同,即使在非国有单位财产中包含有国有财产成分的情况下,我们也同样无法判断出所占有的财产性质是国有还是非国有,因此,也无法明确认定客体为国有财产所有权。此时,若按照我们的一贯想法,将这一职务侵占行为直接上升至以贪污罪论处的地位,有矫枉过正之嫌,同时也造成理论上不必要的混乱。综合上述分析,我认为,对于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的职务侵占行为可以以职务侵占罪定罪,量刑时可从重处罚。
【参考文献】
[1]马克昌.犯罪通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2]蒋莺.贪污罪与侵占罪的共犯认定之我见[J].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7,(1).
[3]蒋莺.贪污罪与侵占罪的共犯认定之我见[J].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7,(1).
[4]任剑.侵占罪探讨综述[J].人民检察,1996,(5).
[5]马克昌.犯罪通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作者简介】曹喆(1979- ),女,黑龙江哈尔滨人,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校法律系讲师,法学硕士,研究方向:刑法学。